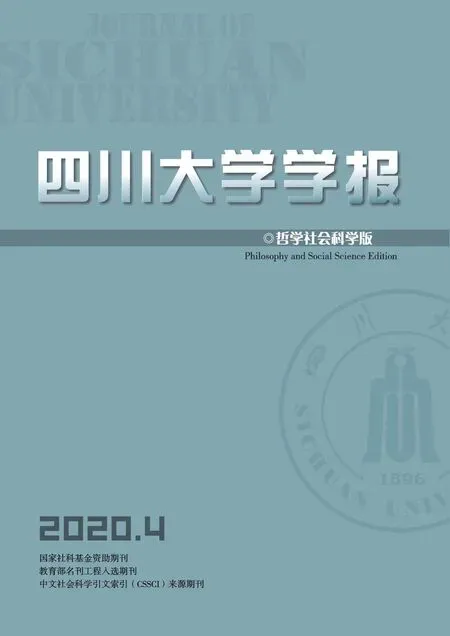论科拉科夫斯基的神话思想
2020-12-28高树博
高树博
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1)目前学界尚未统一译名,本文采用的是近年来使用较多的译名。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关注和译介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提供的检索结果显示,迄今,其著作的中译本有:《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柏格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1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宗教:如果没有上帝……》(三联书店,1997年)、《形而上学的恐怖》(三联书店,1999年)、《与魔鬼的谈话》(华夏出版社,2007年)、《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三联书店,2007、2013年)、《自由、名誉、欺骗和背叛》(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Leszek Kolakowski,1927-2009)是波兰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史家,也是当代波兰文化最重要的创造者之一。在国际学界,科拉科夫斯基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尤其是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和对基督教的哲学反思(包括从事对天主教有组织的批判)、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而闻名。美国学者罗伯特·戈尔曼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1985)将科拉科夫斯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工作”划分为“修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两个阶段”,(2)罗伯特·戈尔曼编:《“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468页。而这个转变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体而言,科拉科夫斯基在着力批判斯大林模式的教条和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成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者。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这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3)参见衣俊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54页。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基督教反思以及实证主义批判等方面的成就,已经做了卓有成效的评价与阐释工作,但对作为其整体理论重要构成部分的神话思想却探讨较少,这显然十分不利于把握其思想的全貌。更何况,科拉科夫斯基在神话探索方面的独特致思路径、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其理论所蕴含的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对我们思考当今的文化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另一方面,仅见的相关研究局限于从神话思维模式与理性和认识论关系的角度,呈现科拉科夫斯基的神话思想及其对神话合法性的论证,且有关文献的使用也不够充分,也未能有效讨论科拉科夫斯基神话理论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影响力。同时,本文也无法赞同如下判定:科拉科夫斯基推崇神话信仰模式的目的是为传统基督教复归服务。(4)参见李晓敏:《科拉科夫斯基的神话理论与现代性反思》,《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41-46页;李晓敏:《危机与救赎——科拉科夫斯基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维度》,《学术交流》2015年第7期,第30-34页。有鉴于此,本文将依据散见于科拉科夫斯基著作中有关神话的种种话语和他专门论述神话的著作,对其神话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揭示和阐释;同时,将神话理论置于科拉科夫斯基思想演变的总体框架和20世纪神话研究自身的学术谱系之下,结合该理论发表后所引起的反应来审视科拉科夫斯基神话之思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辨析科氏神话在场理论的模糊、未至之处自然也是题中之义。
一、作为文化哲学敏感话题的神话
神话及其同源术语经常见诸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一方面,他所批判的宗教神学本来就建立在一系列创世神话的基础之上,并曾断言“去神话性了的基督教不是基督教”。(5)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李志江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亦即,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基督教欲祛除其神话性简直是一种幻想。另一方面,对他而言,科学主义的代表,即由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虽然“废除了神学信仰基础上的旧式宗教”,而以“人类取代了神话中的众神”,却包含着“‘人类的宗教’的因素”。(6)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张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0页。也就是说,即使现代技术理性高度发展,也无法将神话彻底驱逐出人类思想的领域。当然,最重要的是科拉科夫斯基对学术生态的精准捕捉:神话乃是文化哲学中经常出现的敏感问题(sensitive problem)。(7)Leszek Kolakowski, The Presence of Myth,trans. by Adam Czerniawski,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x.既是敏感话题,那便意味着人们对神话态度的莫衷一是。
在20世纪的西方学术系谱中,“神话”既是学术研究的时尚对象,又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范畴。它既可以是一种文学文体或文化样式,也可以是某种思想方式或学术范式的指称,更被一般性地视为虚幻或者幻象/妄想的同义词。1925年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就提出了“作为思维形式的神话”“作为直觉形式的神话”以及“作为生命形式的神话”这三个命题来探讨神话意识/思维的内容。(8)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在作于1944年的《人论》里,神话与宗教被卡西尔定位为人类文化中最难相容于纯粹逻辑分析的现象。(9)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卡西尔曾于其临终前的著作《国家的神话》里感叹:“最令人困惑不安的不在于我们经验材料的贫乏,而在于它的过于丰富。”在他看来,尽管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宗教学家因由各自的研究所形成的答案彼此冲突、相互对立,但是“一种哲学的神话理论必然开始于这种争议”。(10)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4-5页。50年代以后,学者们将神话概念广泛运用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领域,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批评流派。例如,1957年加拿大学者诺斯洛普·弗莱出版的《批评的解剖》,在广泛地吸收文化人类学家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神话-原型批评模型。同年,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做出了“神话是一种语言”的定义,(11)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并将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运行机制与神话类比以图破解其中的秘密。到了六七十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四卷本《神话学》相继面世,开启了神话研究的新阶段。美国宗教学学者伊万·斯特伦斯基在其《二十世纪的四种神话理论》(1987)一书中比较和评判了卡西尔、伊利亚德、列维-斯特劳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神话理论,发现整个外部语境的变化和学者个人的经历构成了他们从事神话研究的动因,并得出结论:神话理论乃是“二十世纪的人为产物”。(12)伊万·斯特伦斯基:《二十世纪的四种神话理论——卡西尔、伊利亚德、列维-斯特劳斯与马林诺夫斯基》,李创同、张经纬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314页。
此外,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图谱来看,神话也已成为学者们对当今社会进行批判的一个支点和理论预设。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1947)中最著名的思考路径就是对启蒙理性进行非历史的泛化论述,并以理性/神话这样的对举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及其文化进步的悖论性。在科拉科夫斯基那里,神话则扮演着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为其指定的角色。对他而言,虽然神话与理性存在着对立,但神话并非无聊的幻想和仅用于施魅的工具,而是具有独特的文化动能和积极的人性意义,对此后文将详述。可以说,这些著述为即将出场的科拉科夫斯基的神话理论提供了丰富而复杂的思想史资源。
然而,如果仅依据以上所述就推测出科拉科夫斯基语境中的神话仅指向宗教领域,显然是不合适的。毕竟,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体系以及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神话故事非常不同于犹太-基督教的神话,尤其是那些“希腊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的神祇(13)依迪丝·汉密尔顿:《神话:希腊、罗马及北欧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刘一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3页。(神人同形同性)以及诸多英雄传说。而且,科拉科夫斯基已认识到宗教神话只是神话的一个分支,亦承认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类学家在神话研究中,虽然对宗教性故事与非宗教性故事不加以区别,却也常常得心应手”。(14)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杨德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事实上,除了散见于其著述中的神话话语外,科拉科夫斯基还专门撰有《神话的在场》(ThePresenceofMyth)一书。此书写于1966年,由于审查的原因(一种潜在的批判被认为存在于该书中)而未能在波兰出版,1972年在法国以波兰文出版,1973年德译本出版,英译本出版于1989年(2001发行平装本),1994年波兰文版在其祖国面世。《神话的在场》似乎是在构建一套神话理论,然而科拉科夫斯基在文中指出,“神话”一词勉强可以用来指称他所关心的领域。(15)Kolakowski, The Presence of Myth, p.x.而且,在《形而上学的恐怖》(1988)里,他还说:“神话不是‘真正的’理论。它们不能翻译成假设可以恰切地表达其真实内容的非神话语言。确信我们能根据这种翻译而澄清这一内容或使其成为可理解的,要比期望通过告诉某人一部音乐作品‘它是怎样的’而向其传达作品的含义还令人难以置信。神话若有形而上学的等值物,那么神话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神话可表现或者隐藏某一终极的实在,这是因为这一实在是不能抽象地表述的,是不能简化为理论用语的。”(16)莱斯泽克·柯拉柯夫斯基:《形而上学的恐怖》,唐少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99页。笔者据英文版对译文做了些微改动,参见Leszek Kolakowski, Metaphysical Horro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8, p.88.神话与语言的关系向来为卡西尔所重视,但科拉科夫斯基的这一论断显然针对的是斯特劳斯的神话素理论,尤其是从宗教神话的角度来讲,“神话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封闭的或者独立自主的”,通过世俗的符号系统无法理解终极之物或曰神圣物。(17)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第168页。确实,《神话的在场》并非是要为已有的神话“五大理论”(18)五大神话理论:自然神话论、释因论、许可证论、唤起论、仪式论,具体内容参阅G.S.柯克:《希腊神话的性质》,刘宗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7-61页。新增一派。毋宁说,它的论述重点在于神话的结构及其在现代性社会中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是“对神话的结构和作用做了最富洞见的理论处理”。(19)Amir Weiner, “The Making of a Dominant Myth: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ies within the Soviet Polity,” The Russian Reviews, Vol.55, No.4, Oct. 1996, p.639.
二、神话的普遍在场和意义
科拉科夫斯基并非从宗教学、神话学、神话艺术学、社会学和神话心理学等角度去思考神话问题,而是侧重于从文化哲学视域考察神话生产的文化地位,这条理路明显受惠于卡西尔。在术语的选择上,科拉科夫斯基坦言自己依赖于德国现象学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挪用了诸如意向、生存、存在、在场、共在等语词——他在论述中校正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庞蒂的部分观点也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科拉科夫斯基对神话的纯粹理论处理是彻底的建构主义。
科拉科夫斯基拒绝给出一个关于神话的本质主义的精确定义,他也不关心神话的叙事性质——尽管他明白这一性质在艺术想象中的重要性,而是将神话作为一个整体话语给予其以较为宽泛的、策略性的规定:神话事关人类意识的结构性特征。总体而言,胡塞尔对人类意识的意向结构的分析及其试图为知识找到不可动摇的、无可挑剔的根基的终身努力,一直激励着科拉科夫斯基。在《神话的在场》这本刻意不提供任何注释的简短之书中,胡塞尔是出现最多的哲学家。1974年,在为耶鲁大学所做的题为《胡塞尔与寻求确信》的讲座中,科拉科夫斯基更明确地说:“胡塞尔的努力并不是徒劳的。我相信,在我们这个世纪,现象学是抵达知识的根本之源的最伟大、最严肃的尝试。”(20)Leszek Kolakowski, Husserl and the Search for Certitud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值得一提的是,此讲座沿用了《神话的在场》的部分内容。科拉科夫斯基摒弃了神话的神学基础,原因即在于他认为宗教神话只是某种现象的变体或者历史的特定化。他将文化的永久性构成要素划分为神话层和技术科学层,同时也指出神话普遍存在于所有的人类交往领域:知识活动、艺术创作、语言、情感、道德价值、技术工作以及性的生活等等。在这里,理智/直觉、思想/情感一类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被他判定为无效,他的运思专注于追溯神话在经验和思想中的在场。
尽管胡塞尔、海德格尔、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都批判过技术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但在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持续庇佑下,技术的膨胀从未受到过任何遏制。科拉科夫斯基既在现实中感受到了技术主义带来的控制和灾难,也在理论上意识到科学自身的阈限。他认为,文化的器官之一——科学驯服了自然环境,并以可验证性和效用性作为标准,但科学不能解释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非经验的绝对现实/无条件现实(unconditioned reality)。科拉科夫斯基没有具体阐释何谓“绝对现实”,但他列举了存在、真理、价值作为其外延的示例。当然,绝对现实不一定有具体的指涉物,但正是它揭示了经验世界的相对性,并使有限的经验现实变得可以理解。而这项揭示的任务需要由文化的另一器官——形而上学来承担,科拉科夫斯基将形而上学问题和信仰视作神话核心的一种延伸。他认为符合论的真假判断在这里并不起作用,重要的是神话能否满足时代的需求。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终极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于有限的人类是必需的,因为人类有三大需求:让经验现实可以理解、对人类价值永恒性的信仰以及把世界看作是连续的。那么,这些形而上学问题能否转换成科学的问题,或者说,是否可以依据科学的方式对之进行证明?科拉科夫斯基认为,一旦神话变成被要求且须寻求证明的产品或教条,它就堕落了;而神话尝试模仿知识或者变成知识的一个要素便是信仰退化的表现形式。科拉科夫斯基宣布,那些让神话意识变成科学反思对象的努力是不会成功的,值得做出的努力必须要在神话意识内部进行。(21)参见Kolakowski, The Presence of Myth, pp.2-8.可以说,科拉科夫斯基为其整个论证所做的奠基性区分,明显带有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论、康德纯粹先验论以及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昭示着宗教神学(不仅是基督教神学,也包括印度神学)的信仰前提。
科拉科夫斯基一方面声称神话存在于认知活动中,另一方面又否定神话变成知识的可能性,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以及如何解释在认识论探索中的神话的在场?对此,科拉科夫斯基的策略是重启经典认识论中的一个命题:知觉之外是否存在客体或者是否存在超知觉对象?他认为,自笛卡尔提出主客体二分认识论以来,不论是哪种哲学传统(现象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等)都倾向于取消对该命题的认识论探寻:或者主张它是无法回答的,或者认为它无法正确表达,或者直接将之悬隔。然而对于该命题的需求却无法消除,因为人类的生存境遇依赖于意义的获得与累积。鉴于客体世界只有被赋予意义才成其为人类世界,而意义乃是人类实践目标的结果,所以应该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探寻保留位置。哲学在其严格界限内可以不接受信仰,但它不能否认信仰对文化繁荣做出的贡献。反过来说,如果不借助认识论的神话学解决方案,文化不可能真正运行。(22)参见Kolakowski, The Presence of Myth, pp.15-17.那么,在知觉之外存在的这一客体究竟是什么,它们是神学实体还是价值一般,以及我们如何在认识论的神话框架下对之探寻?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无法从科拉科夫斯基那里得到正面回答。毕竟,经验主义所信奉的持续抽象是无用的,又或许他的辩护初衷仅仅是在认识论中替神话正名便足矣。当然,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推断,对于这些问题,坚定信念远比弄清其实质重要。如果说科拉科夫斯基的观点中回荡着法国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哲学家吉尔松的《中世纪哲学精神》所传达的教诲,(23)吉尔松:《中世纪哲学精神》,沈清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3-218页。也符合实情。
即使在常规条件下难以感知、揭示,科拉科夫斯基依然笃信神话意识无所不在。在他看来,如果它出现在把世界理解成有价值的过程中,同样也会出现在把历史理解成有意义的过程中。由于个体行动、经验、环境的差异,必然存在价值的多元化及走向自我的相对化,由此,敌对、冲突、善恶之别在所难免,而所有宣称拥有绝对普遍性的伦理原则都面临着自我证明的问题。因此,价值的普遍性是一个神话现实。但是,历史现实需要神话,正是由于神话的存在才使我们获得了把意义赋予事件的权利,有权发声反对那些损害人的尊严、人性的历史事件。在此,科拉科夫斯基重申了其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坚信马克思的思想一直有恢复人类的人性的要求,即使黑格尔、弗洛伊德、胡塞尔、萨特等哲学家对人类现实的幸福相当悲观。科拉科夫斯基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诉求概括为三个维度:他要求的人性解放超过了政治解放;他要求消除非人的状况并把自然人化;他要求历史现实应该与人类尊严结合。(24)参见Kolakowski, The Presence of Myth, p.30.显然,科拉科夫斯基回到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最终,人类的尊严超越了事实的和历史的人性的总体性。
一般来讲,逻辑规则是理性的最高权威。科拉科夫斯基在《神话的在场》中反思了四种关于逻辑的原理和主张:19世纪的心理主义、艾杜凯维奇的逻辑经验主义、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卢卡西维茨的多值逻辑论。它们要么没有回答认识论问题,要么让发生问题无效。科拉科夫斯基对此的详细批判见于《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1966)。他认为,唯有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把通过对心理主义的猛烈批判来拯救逻辑作为思想本身的任务,但真正的拯救能力取决于神话,因为只有超验意识的神话才能解除所有事实偏见,揭开思想的本质。他指出,我们需要在逻辑规则中抱持对理性的神话的信念。当然,这个信念是一种神话选择,因为它超出了理性的范围。神话理性非真非假,因为没有神话被归结到真假的二元对立之下。神话直觉存在于我们理解逻辑规则的过程中,并且不能清除。(25)参见Kolakowski, The Presence of Myth, p.41.
如前所揭,科拉科夫斯基的理论前设是神话的结构普遍存在于在我们的理智和情感生活中,他的以上表述是对神话在理智中的在场进行了说明,但在情感中呢?情感与信仰、希望是否遵守相同的逻辑,又是否具有相同的结构?对此,科拉科夫斯基解释说,如果信仰意味着对对象的可靠性和理性的假设,那么基于爱的个人信任则意味着对他人的全部接受,它没有理性,不需要证明和计算。爱依赖直觉,战胜分裂,走向完美。在神话现实里,爱是愉悦、互惠、敬慕、崇拜,是超越时间的永恒。爱在西方文化中本就是一个内蕴丰富的概念,(26)参见Alan Soble, ed., Eros, Agape and Philia: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Love, New York: Paragon House,1989.科拉科夫斯基在行文中对这一概念实质上是做了精神化、宗教化的处理。(27)参见Kolakowski, The Presence of Myth, pp.46-49.
不论有限世界是否需要解释以及是否能解释,命名共同理性、把握存在、思考绝对的性质一直是哲学文化的渴求,但“存在”不能作为一个客体被把握,它的在场也不是组成“已在”的客体。在绝对意义上,什么是“to be”(存在)或者说“是”(is)的问题一旦被提出将不能被撤销。诚如萨特所说,存在是偶然的,在思想中能表达的不是存在与虚无的对立。在此基础上,科拉科夫斯基指出:“被要求对存在的偶然性问题做出回答的神话方案,在人类对自身环境的基本关涉中获得再生之源。”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生活在一个冷漠的世界之中,因此世界的异在性是我们的基本生存经验。毋庸置疑,这一设定是印度教思想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演化。具体来说,在科拉科夫斯基的观念中,所有对生命的否定——物理上/身体上的痛苦、生活的失败感、对超越自己能力之任务的恐惧、行动受挫、受辱、不可忍受的孤独、性爱的纠葛、死亡等等,都是冷漠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共同体,都在不断地尝试逃离或者战胜世界的冷漠,或通过技术对客体的挪用而战胜它,或拥有客体,而这构成了人类对抗命运的关键意义。但这些方式都不是完美的,也并不总会成功,只有神话创造了对存在的驯化感,消除了经验方式的片面性。(28)以上参见Kolakowski, The Presence of Myth, pp.69, 70-74.或者说,人们通过对异生感的克服、对安全的神话现实的接受,把理性推到了次要的、工具的位置。(29)Andrej Rajsk, “Religion Facing Current Challenges of Nihilistic Culture,” in SGEM 2014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Scientific Conferences on Social Sciences and Arts, p.834, https:∥www.sgemsocial.org/ssgemlib/spip.php?article1168.
综上所述,科拉科夫斯基不仅揭示了神话对生产超验的、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的必要性,也阐明了神话对证明理性和经验知识的可能性是必须的。一言以蔽之,对普遍性的追求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意识之中,所以神话思想会出现在所有形式的人类话语之中。(30)Patricia K. Felkins and Irvin Goldman, “Political Myth as Subjective Narrative: Some Interpretations and Understandings of John F. Kenned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4, No.3, 1993, p.450.有评论认为,科拉科夫斯基的洞见挑战了一些重要问题,如神话的性质、神话解释的自我证明以及知识是否仅通过理性就能受到保护。(31)Earl R. Mac Cormac, “Review of The Presence of Myth,”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Vol.5, No.1, 1990, p.65.
三、神话的辩证法
既然存在的神话层之在场让我们拥有意义成为可能,这是不是意味着神话永远为强存在?而且神话的意义是否始终是积极的、正向的,以及神话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威胁,尤其是神话会不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科拉科夫斯基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见于《神话的在场》的 “文化镇痛剂中的神话”和“神话的永久性与脆弱性”两章。由此推之,并根据科拉科夫斯基著述中所表现出的现象学存在主义,他对神话的信仰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选择问题。
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工业发达国家的文化环境中,个体的首创精神已经丧失。不幸的是,这种丧失被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意识形态景观所遮蔽,甚至形成了一种每个个体从属于共同体而必须负有群体责任的伦理强制。科拉科夫斯基正是遵循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教导而未忽视神话的意识形态特性,他把神话学抽象为两种历史变体,并明确表达了对后一种类型的尊崇。在第一种变体中,传统文化试图唤醒对存在的“负债意识”;而第二种变体则是出现在现代性社会中的相反类型(索雷尔是代表),它鼓励“债权人意识”,并期待以未来乌托邦来纠正对现实的不满。这种大胆的对比显然表达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保守主义。(32)Andrew Von Hendy,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Myt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15.不得不说,科拉科夫斯基对神话意识形态的叙述是印象主义的。在他看来,对神话的威胁来自左派而非右派,而神话的无限扩张倾向也是危险的。科拉科夫斯基指出,所有那些警告神话威胁的人(如卢梭、费希特)都是正确的,如果“神话代替实证主义的知识和规则,试图强行接管几乎所有文化领域,它就可能被包裹在专制、恐怖和虚伪中”。(33)Kolakowski, The Presence of Myth, p.104.而最糟糕的例证就是艺术谅解了世界的恶和混乱,基督教创造了欧洲第一个集权主义国家模式。这样,神话就从有效需求退化成特定的危害。在对神话积极评价转向消极评价的过程中,科拉科夫斯基实质上已经从价值和意义赋予者的广义神话概念,滑向更具限制性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狭义神话概念。(34)Hendy,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Myth, p.315.科拉科夫斯基是否意识到其中的逻辑非一贯性迹象,我们尚不清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这种差异化使用实际上表征着他的某种洞察。
神话的福祉和自我扩张的矛盾导致科拉科夫斯基提出两个终极问题。首先,“在没有神话恐怖威胁的情况下,神话是否可以发挥其必不可少的社会功能”?对此他总结说,神话只有不断受到质疑,不断受到警惕,才能挫败其变成麻醉剂的自然倾向,并取得真正的社会效果。这与保罗·利科对诠释学的永久性作用的怀疑异曲同工。不同的是,科拉科夫斯基的尖锐批评带有政治指向性,即知识分子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如何既保有作为神话守护者的尊严,又能维护自己作为批评者的尊严。对批评力量来源的疑问引导出第二个问题:“意识能否承认神话的谱系,同时又能参与神话?”(35)以上参见Kolakowski, The Presence of Myth, pp.105, 118.科拉科夫斯基的回答是一个迂回的“是”。简言之,人类特有的自我意识引导我们通过反思发现神话。但是,反思本身是一种认识形式。若如此,神话认识岂非变成了理性的形式?这难道不是对最初的区分的违背吗?若非,那它是什么?科拉科夫斯基既没有求助于康德主义的“知道”现象和“思考”本体的方案,也没有采用比喻作为理论的预设,而让问题保持开放性。(36)Mac Cormac, “Review of The Presence of Myth,” p.65.
毋庸讳言,今天我们依旧面临着神话和文化的理性秩序的持续斗争,但要裁决何者为胜则着实不易。用科拉科夫斯基的话来说,“它们必须共存,但它们不能共存”。然则,科拉科夫斯基的辩证法是无根的吗?事实上,“这种关于神话与反神话的永久辩证法概念似乎可以将科拉科夫斯基置于从黑格尔经尼采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家系列中。他们把这种斗争的某种版本视为西方现代性的确定特征”。(37)Hendy,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Myth, p.316.科拉科夫斯基相信,神话及其对立面之共存的不可避免和不可能并不会引起恐慌,因为正是这种张力使文明处于运转状态。“文化动力总是源于价值冲突,每一方都试图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来获取排他性,但又在压力下被迫限制自身的渴望”。(38)Kolakowski, The Presence of Myth, p.135.
《神话的在场》出版后引发热议。劳里·巴顿认为,在英语文化圈,神学研究必须回答解构主义对神话生产之意义的批评;宗教研究必须面对新历史主义要求基于社会和文化环境回答神话意义的挑战,而科拉科夫斯基提供了中间道路,并且他利用了非西方的资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这本‘非常非常陈旧的书’(科拉科夫斯基原话——笔者注)对于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并且可能成为文化哲学的经典之作。就目前而言,对于任何严肃的神话学者来说,它当然是必不可少的”。(39)Laurie L. Patton, “Review of The Presence of Myth”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s, Vol.73, Issue 3,Summer 1991, p.350.波兰文化人类学家沃伊切赫·布兹泽塔则引用科拉科夫斯基的神话理论以证明其观点:每一个民族都是神话共同体。(40)Wojciech Jozef Burszta, “The Frontiers of Identity, and the Identity of Frontiers,”Nationalities Affairs, trans. by Jędrzej Burszta, No.47, 2015, p.2.更有趣的是,有人基于科拉科夫斯基的神话在场思想得出结论:会计类似于神话制作技巧。(41)K. Rudkin, “Accounting as Myth Maker,”Australasian Accounting Business and Finance Journal, Vol.1,No.2, 2007, pp.13-24.
如前文所及,斯特伦斯基将神话理论视为20世纪人为的产物。美国学者安德鲁·冯·亨第(Andrew Von Hendy)在《神话的现代建构》(2001)里则将这种建构和对神话地位的提升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尤其是谢林的神话哲学。而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神话的在场》被亨第以“作为价值赋予的神话”为标题做了述评。从亨第的爬梳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科拉科夫斯基外,在20世纪将神话作为必要虚构之信念的学术确证,也存在于利科从《恶的象征》(1961)开始的对神圣的捍卫,以及汉斯·布鲁门伯格《神话研究》(1979)、埃里克·古尔德《现代文学中的神话意向》(1981)对神话性之永恒性的坚执中。亨第评论道,科拉科夫斯基和利科共享着大陆现象学和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所设定的方向,而且两人都抱持宗教启示的希望。利科的存在于语言中的整全他者和科拉科夫斯基的绝对现实的在场,都是海德格尔的存在的积极版本。(42)Hendy,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Myth, p.316.
如果指认科拉科夫斯基的神话在场思想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实为确论,而断定他意图以此化解基督教的危机、为传统基督教复归服务则不然。(43)相关论点参见李晓敏:《科拉科夫斯基的神话理论与现代性反思》,《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41-46页。毋宁说,科拉科夫斯基的神话理论弥漫着浓郁的人道主义气息:个体性、创造性是核心。《神话的在场》是构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思的重要部分。也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状态让有些学者表示该书是“特别有趣的”。(44)Wilbur Devereux Jones, “Review of The Presence of Myth,”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cience, Vol.19, Issue 3, Summer 1990, p.187.
当代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在其《论文化》(2012)中指出,在世俗化时代文化极度膨胀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宗教替代物的寻找”。(45)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张舒语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vi页。科拉科夫斯基的神话功能论实质上强调了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核心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作如是观。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其纳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进行审视。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假如伯明翰学派当时看到《神话的在场》,他们的神话解析是否在巴特的符号学之外又多了一个思想资源呢?伊格尔顿还惊人地提出,文化是社会无意识。我们又能否套用这个假设而大胆地说:神话也是一种文化无意识呢?确实,科拉科夫斯基给我们的启示意义大于他的结论。而纵观当下,神话似乎正在迎来“复兴”之势。(46)参见叶舒宪主编“神话学文库”总序,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18年。
结 语
总括起来,科拉科夫斯基以符号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为支点,把神话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来剖析它的结构和性质,并以建构主义的立场阐发神话在现代性社会中在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他对神话所潜藏的危险和所造成的灾难也进行了揭示,从而赋予神话以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和非人化的功能。在其神话理论的整体构架之中,宗教更多地被作为文化事实来对待,但宗教的某些命题得到了应有的回应也是不可否认的。当然,科拉科夫斯基的整个论述是以人道主义作为价值指引的,可以将之视为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的某种延续,但同时也要看到科拉科夫斯基对启蒙理性膨胀的警惕。通过辩证的分析和略带独断论风格的语体,科拉科夫斯基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的四种哲学思潮(47)具体可参阅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页。之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如何能在同一命题之下发生融通,尤其是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与其说科拉科夫斯基的综合是一种折中主义,不如说他的开放视野属于多元主义,借此他才能在神话阐释学、神话形而上学方面独树一帜。不可否认,科拉科夫斯基著作中的抽象和晦涩之处,例如神话理性、神话直觉一类概念,给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其要义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无论如何,科拉科夫斯基把神话指认为一种居于各种话语中的意识现象是相当值得我们深思的,他的神话哲学也启示我们对文化事实做思辨性探讨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