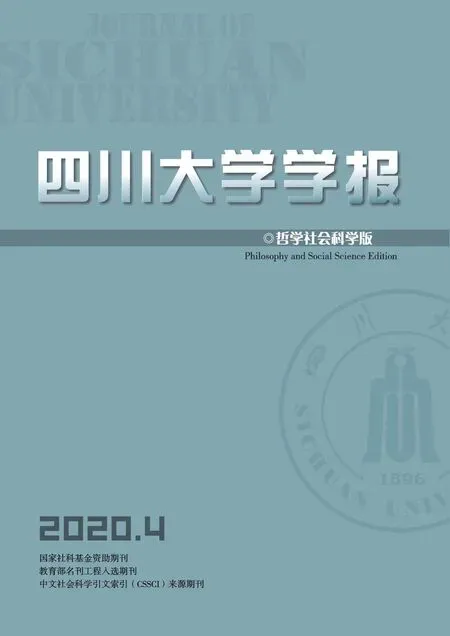类型学的文学移植:袁枚和杰尔查文自然诗比较研究
2020-12-28刘亚丁
刘亚丁
类型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大量运用于跨语言的比较研究中,中国和英美学者在此研究领域都有比较丰富的实绩,但是将类型学运用于文学研究,除了在苏联的文学研究中有运用于比较研究个案而外,在中文和英文的文学研究中尚未见其运用的例子。笔者以为,类型学在语言学研究中运用实绩,以及苏联学者的研究尝试,为文学类型学研究提供了路径和目标,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也使展开这样的研究更具可能性,本文即尝试运用类型学对不同民族的并无谱系学联系的文学家进行比较研究,以具体实例探索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一、类型学:从语言研究到文学研究
“类型学”(typology)在《新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是这样定义的:“类型学居于学术前沿,与分类学相比,它并不那么常用,但它的描述只用于对现象需得出结论的进一步研究的课题。类型学可导出相似的结构,这结构要受研究者的意图的制约,也受制于现象布局的方式。这种结构是限定于可以解释的时期内的。”(1)The New Encyclopaed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Vol.10, Chicago: Encyclopaeddia Britannica, Inc., 1980, p.221.目前在国内外语言学研究中,类型学被大量运用于跨语言的比较研究中。R. H. 罗宾斯的《普通语言学通论》中有“语言比较”一章,其第一、二节为“比较历史语言学”和“类型学比较”。其中,他指出:“类型学实际上是证明一种形式和系统的方法,它要回答初学者面对一种新的语言时会问的问题:‘这种语言像什么语言?’”(2)R. H. Robins, General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p.267.这部著作从语音、语言、语法、结构、词汇等方面展示了类型学分析的方法,注重语言类型学的普遍适用性和层次性。威廉·格罗夫特是在世界语言的多样性中来考察类型学方法的价值,认为“语言类型学的领域是探讨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以便理解它。类型学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充分关照语言序列的宽度(在给出时间限制和信息有效性的前提下),以便把握语言的多样性和其局限性。在语言研究中,类型学是被作为经验主义的、比较的、能产的方法来加以使用的”。(3)Willian Groft, “Typology,” in Mark Aronoff and Janie Rees-Miller, eds., The Handbook of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p.340.R. M. W. 狄克逊和亚历山大·Y. 艾克亨瓦尔德则从类型学的角度考察论元决定结构,分析了论元转换(Argument transferring)、论元聚焦(Argument focusing)、论元控制(Argument manipulating)和论元所指标记(Marking referential role of arguments)四种状态,将瓜贾贾拉语、菲律宾语、塔努安语、英语、纳瓦约语、阿尔冈昆语导入这四种状态进行性质比较。(4)R. M. W. Dixon and Alexandra Y. Aikhenvald, “A Typology of Argument-Determined Construction,” in J. Bybee, J. Hanman and S. Thompson, eds., 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p.71-113.这属于中观研究。当代语言类型学的代表人物格林伯格通过对欧洲、亚洲、非洲的30种语言的抽样调查,研究词素跟语序的关系,试图确定陈述的普遍性,找出一般性的原则。(5)Joseph H. Greenberg:《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陆丙甫、陆致极译,《国外语言学》1984年2期,第45-60页。这可谓宏观研究。可见,语言类型学研究排除通常所说的影响关系——尽管上述一些语言属亚马逊河流域土著语言,但研究者所观察的是它们之间非谱系性的平行关系,它强调、突出跨语言的比较,试图在尽可能多的跨语言的比较中寻找人类语言的一般共性或某些语言的个性。(6)陆丙甫、金立鑫主编:《语言类型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总体来看,类型学方法被运用于研究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它从语法、语音、词汇和语义等层面展开,以图通达语言的共性。(7)参见方经民:《现代语言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7-196页;陆丙甫、金立鑫主编:《语言类型学教程》,第25-26页。
在国内学界和英语学界,目前笔者尚未见到将类型学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案例。正因为如此,一些苏联人文学者的工作值得注意,他们将类型学移植到文学研究中,不同民族间并无直接联系的相似文学现象由此成了类型学的用武之地。如И. А. 波罗尼娜在《日本中世纪抒情诗与其欧洲相应物》中描述了日本平安时代的武士歌与法国中世纪普罗旺斯破晓歌的相似性,并明确指出:“在本文中,我们仅讨论类型学关系,即独立发展、互不联系的关系。”该文从诗歌审美原则、基本内容、题材—体裁结构、诗歌语言这四个方面讨论了这两种文学现象的关系,亦即“我们在诗歌理想、诗的基本内容的层面上分析了这两种文学现象的类型学的关系”;“我们对平安时代抒情诗和普罗旺斯抒情诗歌的比较—类型学分析表明,这两种文学现象之间存在着思想内容、一般的审美原则的相似性,这种原则通过内容、形式和表达方式的细节得以体现”。(8)以上引文参见И. А. Боронина, Японское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лирика и ее европейсо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ИМЛИ АН СССР, Типология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литаратур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 М.: “Наука”, 1974, стр.547, 557.这篇文章出自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集体著作《东方与西方中世纪文学的类型学与联系》,李福清在为该书撰写的代序言中,明确提出东西方文学之间关系有两种,其一是类型学关系,其二是事实联系(即国内学界所说的影响关系)。(9)Б. Л. Рифтин, Типология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литаратур,—ИМЛИ АН СССР, Типология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литаратур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 стр.9-116.苏联汉学的奠基人В. М.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尽管没有用“类型学”或“类型学分析”之类的术语,但实际上也进行了比较—类型学研究,他在1944年发表了《罗马人贺拉斯和中国人陆机论诗艺》,为写作此文他还将陆机的《文赋》、曹丕的《典论·论文》翻译成俄文,作为附录。(10)参见 В. М. Алексеев, Римлянин и китаец Лу Цзи,— 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2, Кни.1, стр.345-384.此外,他还撰写了《法国人布瓦罗与同时代中国人论诗艺》,分析布瓦罗与中国的袁黄和宋濂的相似性和相异性。这篇文章展开比较的层次性相当分明:首先他把布瓦罗和中国的两位诗人置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民族文化的时代大格局中来考察,然后分析了中法作者的基本观念的相似性,接着叙及中法作者的复古精神,最后得出结论:“在过去的13—16世纪两种极为不同的文化产生了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极为相似的教诲型的诗人,尽管他们所操持的语言完全不同。”(11)В. М. Алексеев, Француз Буало и его китайские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2, Кни.1, стр.396.20世纪80年代,著名文艺学家М. Б. 赫拉普琴科写出了《文学研究中的类型学》一文,对在文学研究中如何运用类型学方法作了思考。(12)М. Б. Храпченко,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ое изуч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зна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 М.: “Наука”, 1984, стр.175-209.
从苏联学者的工作看,类型学由语言学转入文学研究时,实际上经过了调试:排除不同民族之间的事实联系,不进行影响研究,将大范围的数量归纳转变为基本上是一对一对比的微观比较,同时段的现象是比较的必备条件,注重层次性或平行系统之间的比较。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不少学者注意到文学作品本身是有层次的,如英加登提出了“文学作品是层次的造体”的观念,并试图概括出文学作品普遍适用的层次:语音造体层面、意义单元或整体层面、系列观相层面。(13)参见罗曼·英加登:《论文学作品》,张振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第48-194页。这是由微观到宏观的层次分类法,它比较符合文学作品本身的构成方式。就研究诗歌这种体裁而言,加斯帕罗夫提出,可以从这样三个层面入手:即上层——思想形象层,中层——风格层,底层——音声层。(14)参见 М. Гаспаров, “Снова тучи над мною...”Медотика анализа,— О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 СПб.: “Азбука”, 2001,стр.11-26.这比较符合诗歌的体裁特征。本文借鉴加斯帕罗夫所采用的三层次分析法,根据研究对象的状况又有所调试,从观念层、意象层和织体层三个层面入手,对同时代的中国诗人袁枚(1716—1798)和俄国诗人杰尔查文(Г. Р. Державин,1746-1816)的自然诗作类型学分析。观念层试图回答以什么观念来表现自然的问题,意象层试图回答表现了自然中的什么的问题,织体层试图解释诗中的言者是如何处理描写自然与其自我言说的关系的。
二、观念层:主客无间与人神互通
袁枚与杰尔查文在各自的诗歌创作中,都有大量的表现自然的作品,对比这些创作于大致同一时代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品,进而运用类型学方法加以分析,不失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条路径。以下将从上述三个层面对二人的自然诗作展开类型学研究,首先是观念层面的比较研究,重点聚焦于二位诗人是如何看待自然与神的关系,又是如何处理仕途进退与归隐自然的关系。
与人共情的自然是袁枚自然观的呈现方式。感春伤秋,模山范水,是袁枚诗作的本色。其《随园二十四咏》之一《仓山云舍》中“看花共山笑,采药与山分”一句,(15)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周本淳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50页。以下凡引此书在正文中用括号内加数字标注页码。正表达了袁枚与自然关系的精神核心。另如《迎春》:“迎春莫怪春难觅,好处从来过后知。隔岁梅花报花信,倚门杨柳望归期。无边暖漏声声催,有脚青旗步步移。料得东皇非长官,不应厌我出郊迟。”《送春》:“骊歌树上子规啼,报道东皇出郡城。久住似嫌芳草老,轻装不带落花行。从今时节都无味,留赠云山尚有情。早识相逢遽相别,当初翻悔下车迎。”(80)东皇,即“东皇太一”,“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16)参见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0页。按照传统五行观念,东属春,故东皇被视为春之神。由此可见袁枚“风趣”——对东皇,消解其神性,对己,则抒发其人情,竟然像情人一样调侃东皇:“不应厌我出郊迟”,“早识相逢遽相别,当初翻悔下车迎”。两首诗首尾相接,写迎春与送春,合而观之,这里子规含灵、青旗移足、东皇有意、诗人怀情,圆融完成了与自然的情感交流。又如《风洞》:“地立千寻石,天藏一洞风。吹时分冷煖,起处辨西东。倾耳如闻响,扶云直到空。笑侬摇羽扇,也会显神通。”(723)此诗中,诗人直接与风洞的造物主对话:笑侬摇羽扇,自然于是化作诗人情感相通之灵物。此外,袁枚还赋予无生命的自然物以生命,如《玉女峰》:“莫道玉人长不老,秋来也有鬓边霜。”(725)而自然之物亦与诗人同喜共悲,如《荻港灯下闻笛》:“分明九曲长江水,都作回波上客心。”(777)《南山有古树》《并头牡丹诗》亦可作同样观。颇类西人利普斯所说的“移情”,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情,以物喻我,我即物之灵。
考察袁枚描写山水的作品,有一个现象颇为显著,那就是其中的“神性”人物的存在方式。袁枚即使在描写与先贤有关的山水祠观之时,也未曾将先贤视为神灵。《小仓山房诗文集》卷十一有《灵谷寺》《孝陵十八韵》《徐中山王墓》《梁武帝疑陵》等诗作怀念前贤的功绩,但都直面其已故的事实,抒发的是“黄图我欲披皇览,白骨人谁认帝羓”(228)感慨。在《佛者九流之一家》一文中,袁枚更是指摘佛家之虚妄,直言生死:“死而焚则熄,乃塔庙以神之。”(1580)袁枚的作品中大量征用先秦典籍中的神话人物,这些人物在其笔下与其说是在彰显“神性”,毋宁说是在渲染“人性”,正如东皇被描写成恋人。联系袁枚对生死的超然态度等来看,(17)详参王志英:《袁枚评传》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尤其是第十章“袁枚的生死观与饮食观”。袁枚作品中神话性人物的出现,既是对中国传统起兴手法的承继,也是古老知识在当下的转述和挪用。在其与人共情的自然观念下,无需借助神的中介,就与自然达成主客无间的交流。
与袁枚不同,人神共享的自然是杰尔查文自然观的呈现。山水庄园、春去秋来、风雨雷电以及动物植物等等,都是杰尔查文吟咏的对象。在杰尔查文描写自然的作品中,自然物或自然现象总是与神相伴随,甚至是由神来构建或发起的。可以说,神性的因素始终渗透在他所描绘的自然画面之中,如《雷霆》:“在百万分之一秒/是谁用手掌点燃了星球?/啊,神啊,这是你的法则,/你的目光造出了和平,并观察/石头擦出了钢的火花/弥特剌斯/把无边空阔中的太阳掩进暗黑。”(18)Г.Р. Державин,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Л.: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7, стр.312. 以下凡引此书在正文中用括号内加数字标注页。诗中描绘的雷霆形象,透露出诗人的自然观——自然中的各种现象,乃是神的意志在发挥作用。在这首诗里,既有一般意义上的神(бог),又有弥特剌斯(митра),后者是来自于古代印度、伊拉克的司光明与善良的神。(19)参见М. Н. 鲍特文尼克等编:《神话辞典》,黄鸿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9-200页;Мифы народов мира,Главный ред. С. А. Токарев,т.2, М.: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0, стр.154-155.对杰尔查文的诗作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各种宗教的神,他们是自然的伴生物,或自然现象的发起者,其中古希腊神话人物更是常常被呈现。如在《喷泉》中,他唤出密涅瓦(雅典娜)、阿波罗和马尔斯等希腊神来陪伴波将金。在《冬》中,缪斯回答诗人之问时说:“哎,美惠女神在哪里?”注家认为,这是借古希腊神话人物——美惠女神(Хариты)来暗喻诗人所崇敬的贵妇。(438)在《美的诞生》中,杰尔查文详述宙斯招饮,忽有所愿望,在海浪造出了美神阿芙洛狄忒。在《萨尔斯村漫步》中,诗人写道:“在石柱/与忒弥斯为致敬/俄罗斯的英雄宏楼之间/如画般投影。”(172)这里忒弥斯(Фемида)是司法律与语言的女神。(20)参见М. Н. 鲍特文尼克等编:《神话辞典》,第286页。《冬天的愿望》的开头就是:“在玻瑞阿斯的车上/伊俄罗斯在唉声叹息。”(117)诗人让玻瑞阿斯和伊俄罗斯这两位古希腊神祇,营造了冬天的肃杀之景。此外,杰尔查文的自然中,还运用了东正教的文化元素,如《雷霆》中:“雷霆啊!你是造反的天使的雷霆,/你震撼了星宿的宝座。”(313)注家认为这是借用了堕落天使路西法(Люцефер)(21)参见 Мифы народов мира, главный ред. Токарев, т.2, стр.84-85.的形象。甚至还有古代俄罗斯民族在接受东正教之前异教时代的神的影子,如《致幸福》:“在视为权杖珍宝的时日/它把佩伦遣到铁铸的城池。”(127)佩伦(Перун)是俄罗斯异教时代的雷神。(22)参见 Мифы народов мира, главный ред. Токарев, т.2, стр.306.而《乡村生活赞》一诗,更是连续“祭出了”俄罗斯异教时代的列利(Лель,爱神)、拉达(Лада,美神)、乌斯拉得(Услад,酒神),(23)参见Примечания к Деревенской жизни ,—Державин,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Л.: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7, стр.436.可说是杰尔查文对俄罗斯异教时代的神的追忆。值得一提的是,杰尔查文写了《上帝》一诗,杜纳耶夫等学者们借此证实了他的东正教信仰。(24)参见 М. М. Дунаев,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I-II, М.:“Хрести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1,т.1, стр. 284; Д. Л. Башкиров, Ода “Бог”, Г. Р. Державина,— Евангельский текст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I-XX века , выпуск 2,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Изд: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8, стр.140-150.其实仅从其对不同文化源头的神话形象的大量运用中,已经不难发现杰尔查文的神性观念。自然因神而有灵,因人而获美,杰尔查文的自然诗营造了人—神—自然互通的三位一体。显然,同为摹写自然的诗作,但不同的处理人神的方式,展露出二人自然观的差异。
在人生观念上,两位诗人亦在体现“自然”的另一层意义,即“不勉强也”。(25)参见舒新城等主编:《辞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108页;其“自然”词条中,有“言无勉强也”之义解。俄人在翻译《道德经》的“道法自然”时,也有“不勉强”的意思,如马斯洛夫的翻译“Дао же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о”(道是自足的)。参见А. Маслов, Загадки тайны и коды “Дао дэ цзина”, Ростов -на-Дону: “Финикс”, стр.181.回溯平生,袁枚与杰尔查文的志向有“合”有“分”,二人都将为官为宦视作对本性的扭曲,渴望回归自然。他们早年的志向和经历可谓相侔:21岁时袁枚拜访供职于广西巡抚金鉷府中的叔父,为金鉷作《铜鼓赋》而提笔立就,因才气横溢受金氏赏识,遂被其举荐赴乾隆元年(1736)博学鸿词试。举荐虽未能奏效,但袁枚却由此声名远播,不久于乾隆三年中举,次年中进士,入翰林院,选庶吉士。后因满文考试的败落被阻断词臣之路,袁枚只好接受外放江南任知县的别样人生。杰尔查文1743出身于喀山省的破落贵族家庭,11岁时父亲病故,母亲送他进了古典中学,19岁时参军,后因参加镇压普加乔夫起义,叶卡捷琳娜二世犒赏军功而受封了一个有三百农奴的庄园。1773年杰尔查文脱离军职,不久进参政院供职。在军队时他便利用空余时间写诗,1782年写作称颂女皇的《费丽察》,两年后相继担任奥伦堡和唐波夫总督。嗣后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秘书,1802—1803年任司法大臣。(26)参见А. А. Замостьянов, Гаврила Дерзавин: Падал я, вставал в мой век...,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3.乾隆十三年,袁枚辞去知县之职,于江宁购“随织造园”加以改造而称“随园”,以此作为归隐之地,开始了其模山范水、酬唱文友、教诲弟子、逍遥自在的诗酒人生。他多有吟诵随园的诗作。(27)参见《袁枚全集·前言》,王英志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杰尔查文在任总督和大臣之时留下的作品多数是与国家有关的政事、军事方面的诗作,但也时有流露出对自然山水、乡野闲居的艳羡之意,如后面叙及的《占领奥恰科夫的秋天》。1798年更写下了《乡村生活赞》:“无上幸福啊,那个远离庶务的人!/他像大地的头生子,欢叫于家邦一隅/劳作,不为赎身/而为自己,/为自己的意愿而劳作/……静坐在自家的花园/草花茂盛,菜蔬青翠/或用弯刀砍野树,获其果实/嫁接枝条。”(271-272)从司法大臣任上退休之后,他蛰居于自己在诺夫戈罗德省的兹万卡庄园,写出了数量繁多的“自然之歌”,如《天鹅》(1804)、《茨冈舞》(1805)、《致叶甫盖尼兼叙兹万卡庄园生活》(1807)、《农民节日》(1807)等。
袁枚辞官不久便写下《随园杂兴》十一首,其第一、二首已然道尽辞官后田园家居生活之乐。其一:“官非与生俱,长乃游王路。此味既已尝,可以反我素。看花人欲归,何必待暮春?白云游空天,来去亦无故。”其二:“喜怒不缘事,偶然心所生。升沉亦非命,偶然遇所成。读书无所得,放卷起复行。能到竹林下,自有春水声。”(111)两相对读,袁枚此诗似乎是在隔着时空与北国的杰尔查文对话。杰尔查文的《乡村生活》亦似在“呼应”此诗之旨:“我需要城市的什么?/我住在乡村;/我不要绶带和将星,/我懒得搭理宠臣;/我只想如何幸福地/享受生活;我想拥抱一切,/热爱所有的人;/谁会来,什么将发生?今天只属于我,/明天一切都淡忘,/一切都会像影子一样消失;/我为什么要虚耗分秒,/要寻愁觅恨,/不赴宴寻欢;/我不稀罕金银财宝:/夫妻和谐就是富贵;/爱神(Лель)、美神(Лада)就是富贵/酒神(Услад)才是我的好友。”(289)此诗作于1802年杰尔查文任司法部长之时,从其工作日志中可以看出已近花甲之年的他颇受案牍劳形之苦,这首诗的情绪与袁枚的《随园杂兴》颇为近似,只是他真正享受乡村生活之乐的时间比后者晚了近三十岁。
三、意象层:静态摹写与动态描状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作家作品中的意象建构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就袁枚和杰尔查文的诗作来看,时序演化、春去秋来都可以成为二人感时伤怀的起兴点。袁枚《小仓山诗文集》中可以看到题涉春夏秋冬的诗作,杰尔查文也在1903—1904年间写了以四季题名的诗。限于篇幅,以下仅选取二人题写春秋的诗作进行类型学分析,重点关注其感春悲秋主题,通过钩稽字词背后的“典故”,发现相似意象背后的异与同。
感春是袁枚和杰尔查文共同的主题。袁枚作有《春兴五首》,抒发其移居随园后的兴致和怡悦,如其五:“碧云英与玉浮梁,酌向花神奏绿章。谥作洞箫生有愿,化为陶土生尤香。春光解恋身将老,世味深尝兴不狂。爱杀柔奴论风物,此心安处即吾乡。”(240)整首诗前四句与后四句判若两诗,前重想象,后叙感悟。钱钟书先生转述王梦楼语谓袁枚诗“如琵琶”,(28)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31页。揆诸此诗,似为允当。因饮酒而脱离了当下的庸常,诗人即能直接面对花神而奏乐。花神,明代冯应京《月令广义》谓女夷为花神,《淮南子·天文》言“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兽草木”,则花神为主春夏万物生长之神。(29)参见袁珂:《中国神话大词典》,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35、151页。诗人在酒酣微醺、诗兴盎然之际,将现实与想象糅合在一起,诗的前半如梦幻般的急管繁弦,后半则渐奏渐息,直至消歇无声,对人生的至深领悟,人诗俱老的境界,醇厚而富有余味。当然从袁枚当时的年纪来看,似有为赋新诗强说“老”之嫌。
杰尔查文也有题为《春天》的诗:“法翁的呼吸融化了冬天,/美好的春天的目光掠过;/涅瓦河奔向了贝尔特海峡的怀抱,/几只船儿放下岸边。/即使在山上雪也不反光,/即使火苗闪烁也烤不热草垛,/群鸟扇动尾巴急促转弯,/马蹄敲击地面发出嘚嘚声。∥在月映的角落有泽费洛斯们/在晚霞里翩翩起舞,/唱着赞美春天的歌,/舞步连绵节拍清晰。∥太阳以百合花般的光束/把火倾向海滩,彼得城深吸/清新微风在海湾打滚;你来吧,到那里散步。∥来吧,去看金光、蓝天、绿树、碧水,/孩子绕膝的娇妻;/看着魅力无穷的自然,/你也幸福无比,利沃夫!”(298-299)这是杰尔查文写给当时在克朗什塔得海关任职的内弟利沃夫的一首诗,开篇是对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人物法翁(Фавон)的描写。法翁即诗中第二小节提到的泽费洛斯(зефир)。(30)法翁和泽费洛斯,可参阅Мифы народов мира, главный ред, Токарев, т.2, М.: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0, стр.556-557, 663.泽费洛斯较早出现在荷马史诗中,在《伊利昂纪》卷九有如此的讲述:“一如鱼群游聚在大海,两股劲风卷起水浪,玻瑞阿斯、泽费洛斯,从斯拉凯横扫过来,奔突冲袭,掀起浑黑的浪头,汹涌澎湃,冲散海草,逐波洋面。”(31)荷马:《伊利亚特》,陈中梅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第191页。史诗名称及神话人物译音,各译本有异。但在后世的诗中,泽费洛斯并非如此凄厉,往往为暖风。如1742年罗蒙诺索夫在《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颂》中写道:“何等可人的泽费洛斯吹拂着,把新的力量融进了情感?”(32)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Л.: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6, стр.85.杰尔查文在诗中以神话人物泽费洛斯们的翩翩起舞,把春天的欢愉动态化。又在第三小节引入圣彼得堡这个城市,回归人的现实世界,而且直接吁请献诗的对象——利沃夫。到第四小节,诗人描写令人愉悦的金光、蓝天、绿树、碧水,想象利沃夫在这个天地里的幸福生活。细读此诗可以发现,诗人的视点有一个由神起兴过渡到大背景的自然,接着又转到小背景的人化自然(城市),进而再到人的天地的渐进过程。若与袁枚的《春兴》其五对照来看,二诗都是前有神幻的意象,后写人生的感悟。不过,尽管大的“诗思”相似,但杰尔查文重感性欢愉,而袁枚重人生领悟,杰尔查文主动,袁枚主静。
袁枚写秋的诗歌也不少,如《送秋二首》,其一:“秋风整秋驾,问欲去何方。树影一帘薄,虫声彻夜忙。花开香渐敛,水近意先凉。从此冬心抱,弹琴奏《履霜》。”其二:“袖手凭栏立,云山事事非。雨疏分点下,雁急带声飞。枫叶红虽在,芙蓉绿渐稀。何堪作秋士,年年送秋归!”(201)诗中有一些故实,如“秋驾”“冬心”“履霜”等。其中,“秋驾”似出于《吕氏春秋·博志》:“ 尹儒学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梦受秋驾于其师。” 高诱注:“秋驾,御法也。”(33)《吕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4页下。正是因为用典,此诗似与袁枚本人所倡导的性灵家法未必相合。但诗人以平实的语言,借助树影、虫声、花开香敛、水凉、雨下、雁飞、枫叶红、芙蓉稀等意象,把秋去冬来做了自然呈现。虽然“雨疏分点下,雁急带声飞”略呈动态,但总体是静态秋景。
杰尔查文同样也有一些描绘秋天的诗作,如其写于1788年的《占领奥恰科夫的秋天》:“埃俄罗斯向玻瑞阿斯垂下白头/戴脚铐走出洞穴,/像硕大的虾一样伸展腰身,/勇士向空中一挥手;/像放牧一样赶着蔚蓝的空气,/攥紧空中的云团,/一撒手溅出云朵,/雨顷刻咆哮大作。∥秋已然露出嫣红的脸颊,/金黄的庄稼茬站满田地。/向葡萄索取奢豪,/索取美味酒浆。/鸟群烤热了天空,/茅草染白了大地,/带红兼黄的草/沿小径伸展远方。∥玻瑞阿斯向秋眨眨眼,/把冬从北方呼唤,走来白发魔女/挥着宽袍大袖;/雪、寒、霜登时而下,水即刻成冰,/因为其冰冷的呼吸/自然之眼光也凝固。”(121-122)在这首诗中,神话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动态性的画面,将金秋的收获和秋转冬的寒冷都描绘了出来。诗人反复请出了冬神玻阿瑞斯,他的“出场”为秋天的景色带来了动感,赋予无生命之物以生命。在俄罗斯皈依了东正教的几个世纪后,这首诗却借助于古希腊神话,获得了万物有灵般的效果。与袁枚的主要呈现为静态的《送秋》相比较,杰尔查文写景的动态特征更加明显,他在诗中写出了季节的动态变化。当然袁枚的自然诗中具有动态的写景也不少,只是与杰尔查文的诗相比较而言,动态略少而已。
四、织体层:客观呈现与作者现身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对织体层的考察,可以发现文学作品结构方式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所谓织体(texture)是回答作品外层的构成问题,诸如其语言、声音、形象;它的各部分的构成;它的风格”。(34)How to Read a Folktale: The “Ibonia” Epic from Madagascar, Translation and Reader's Guide by Lee Haring, Cambridge,UK: Open Book Publisher, 2013, p.21.受篇幅所限,这里不拟对袁枚与杰尔查文自然诗的织体全面展开比较研究。而主要从承载叙事抒情功能的“言者”(speaker)及其与作品中的自然描写的结构关系加以讨论,因为正是诗歌中的“言者向读者描写事件,传达情感和观念”。(35)《文学:阅读、反应、写作(诗歌卷)》(L. G. Kirszner & S. R. Mandell, eds., Literature: Reading, Reacting, Writing,Fifth Edition),“西方文学原本影印丛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第823页。“言者”作为文本的叙述者,在袁枚与杰尔查文的自然之诗中有不同的表现,其发挥的作用也同中有异。
在袁枚的部分自然诗中,言者基本上发挥着类似小说中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者的作用,只是客观地对自然之物进行描写,完全不发表对所描写之物的评价,这样自然之物仿佛在自我呈现。如《瞻园十咏为托师健方伯作》组诗,就以瞻园中的各景为吟哦对象,基本采取第三人称来客观叙述,其中《老树斋》:“老树得春光,亭檐遮几年。数椽移向后,万绿遮当天。叶密雨声聚,枝高日脚悬。新基即究础,暗合古贤缘。”这里言者作为观照者完全没有干预所描写的对象。《抱石轩》:“一轩当石起,紧抱丈人峰。花月分窗入,烟萝合户封。坐怜红日廋,行觉绿阴浓。鸟问幽居客,人间隔几重?”(356)在此诗中,除“怜”和“觉”泄露了言者的态度而外,其他也是客观呈现。另如《竹林寺》只绘寺景,“耳根疑佛语,玲铎有清音”(614)略将诗人带入诗中。其他如《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八中的《天柱峰》《老僧岩》《美人石》《展旗峰》《卓笔峰》等都是言者以第三人称客观描写景物。
在杰尔查文的自然诗中,可以看到客观性的言说者,如《农人与橡树》:“农人用斧头砍橡树根,/橡树时嗡嗡时轰鸣,/枝上树叶不停地摇,/斧头在隆起的树根不停地砍,/树林的树都在瞧。∥橡树信得过根,对此很自豪,/也轻视农人的劳动。/农人一边挥动斧头,/一边思考:/‘看它能挺几时,/根会断,树会倒。’”(287)整首诗几乎描画了一个场面,言者似乎是上帝式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他能深入树和农夫的“内心”,将其讲述出来,但不作任何评判。不过,这样的言者在杰尔查文的诗中是罕见的,在他的笔下,更多的言者是以第二人称“你”直呼被描写对象。如《山雀》整首诗以“你”来描绘飞翔的山雀。《燕子》一诗,前面采用第二人称,言者以与燕子对话的方式用燕子“视角”俯瞰世界,并在诗的末尾让作者以第一人称言者出场:“我的灵魂啊,你是世界之客。”(208)而在《蜜蜂》中,言者于第一小节就以“我”的名义直接出场:“金色的蜜蜂,/你怎么总是嗡嗡嗡,/你干吗不飞走?/莫非你在欣赏我的缪斯?”(245)相对于杰尔查文诗作中多言者现身,袁枚诗作中言者更隐匿,客观的描写更多。
袁枚还有部分自然诗可谓“多重织体”,这类诗作虽然主要是以第三人称叙述者的方式描写自然,但由于诗人主观性的言说内容——或追忆历史,缅怀先贤,或借助神话典故,将多种精神性元素融入客观的自然描写中,呈现出多重层次结构和以“我”胜“景”特色。如《赴淮作渡江咏四首》就营构了互相嵌合的多重艺术织体。在第一首中,言者作为第三人称叙述者描摹“一声篙入江,万象化为水。喜无尘埃浸,但把明月洗”,为一篇大作铺垫山水背景、情绪空间。在第二首中,言者化作哲士感叹“四海同一魂,大梦酣茫茫”,似与天地苍生彼此沟通,而“百年会有期,行役殊未央。瞻彼江湖阔,知我道路长”,更是观大化而悟人生,为后面的兴叹先伏一笔。在第三首中,言者在日暮古战场,追叙历史往事,哀矜于南宋权臣韩侂胄的生平遭际,暗含诗人对出处理想的考量:“日落黄天荡,怀古思英雄。南宋韩蓟王,于此观军容。……恢复全无功。韩公从此悟,万事慎所终。策蹇西湖滨,醉倒东南峰。举手天地动,放手烟云空。朝为大将材,暮作渔樵翁。”到第四首,言者与诗人袁枚已合而为一,从历史追忆回到现实,忆及任高邮知州而受阻于吏部,而“我今过此邦,一望无田畴”,有感于黄河泛滥之惨状,生发悬想:“如我果牧此,何以佐一筹!”在表述了自己“何不使决导,慨然弃数州。损所治河费,用为徙民谋。……泛滥病可瘳”的治理想法后,忽然醒悟:“安得陈明堂,并告东南侯。”(116-117)《赴淮作渡江咏四首》体现了袁枚的儒家本色,仕途困顿归隐随园后,仍不免有致君献策、济民理政之思。四首诗的内容浑然一体,天地—人生—历史—现实的进路,让此诗致思深邃,元气沛然。另如《观大龙湫作歌》,言者借佛道人物描写瀑布奇观,发出了“独占宇宙奇观偏” (722)的赞叹。在袁枚的自然诗中,篇幅比较大的古体诗往往以客观自然起兴,亮点则是言者与诗人合一的主观性兴叹。
同样,在杰尔查文的自然诗中,也有多重织体的作品,如在《流泉》一诗中,言者对流泉的吟诵就具有三重意义。在诗的开始部分,言者在对流泉作客观描述的时候,诗人已然以第一人称现身:“清澈的吟唱的流泉,/从高山向下流淌,/河湾饮流泉,河谷泛金光,/洒满鲜花般的珠玉,/啊,流泉,在我的眼里你是如此闪亮。”这是对莫斯科郊外的格列别涅夫斯基泉的自然实体刻画。此为第一义,即实谛。在诗的中后部,言者和诗人合一后直接抒发情感:“我满怀诗的激情,/走近你,流泉啊:/不免嫉妒那位诗人,/他饱饮你的清泉,/戴上了帕尔纳索斯的桂冠。”这里的“帕尔纳索斯”是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所居圣山,透露了古希腊神话中的卡斯塔利亚圣泉的信息。此为第二义,即圣谛,但已经包含了下面要倾诉的俗谛。诗的最后一节:“啊,你的美誉传遍所有城邦,/正如透过沉睡的树林大山在回响:/不朽的《俄罗斯颂》的写作者啊,/圣神的格列别涅夫斯基泉/流溢出你诗的灵感。”(83-85)原来杰尔查文将俗世的实在物——俄罗斯诗人赫拉斯科夫当时所居住之地的格列别涅夫斯基泉,想象为古希腊神话中表征诗的灵感之源的卡斯塔利亚圣泉,借此表达了对创作出《俄罗斯颂》的同时代诗人赫拉斯科夫的敬意和嫉妒。此为第三义,即俗谛。整体来看,自然中的格列别涅夫斯基流泉与神话中的斯塔利亚圣泉交汇呼应,述三谛,将实在地域、神话想象和世俗念想相嵌合,构成了纷繁而协和的艺术织体。另如《瀑布》一诗,言者亦先对瀑布作客观描写,然后以瀑布作为波将金公爵一生明喻,将自然与人生纽结一体,构成诗作的多重织体。
结 语
从《新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类型学的定义来看,类型学注重被研究对象的结构层次,将研究对象限定于“可以解释的时期”。因此本文选择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的中俄两位诗人,对袁枚和杰尔查文的自然诗作三个层次的对比考察。类型学的对比考察,可以具体细致地揭示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相类作品的差异。从观念层看,袁枚与人共情的自然观,使他不借助神的中介而与自然达成主客无间的交流,杰尔查文则在作品中营造出人—神—自然互通的三位一体;他们早年志趣相近,仕途虽顺逆不一,然而殊途同归,都以吟诵自然为人生盛事。从意象层看,袁枚更钟情于静态描摹,杰尔查文更多追踪自然的动态过程。从织体层看,袁枚的诗中言者客观的第三人称式的描述略多,杰尔查文诗中言者以诗人带入式的干预更显著。袁枚与杰尔查文之间关山阻隔,相识无缘,但对自然山水的喜爱和摹写则是相近似的,他们通过诗作最终归隐“山林”,则佐证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乃不刊之论。若从杰尔查文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人—神—自然的沟通无碍出发,对学界所谓西方诗歌中人与自然是分离的刻板套语似可置喙,在此存而不论。
本文从微观的角度,尝试将语言学中的类型学移植到文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当把类型学应用于不同国家的同时代诗人的类似题材的写作中的时候,实际上也达到了类型学在语言学研究中所达到的目的,即“确定陈述的普遍性,找出一般性的原则”。那么是否可以将类型学运用于中观和宏观的文学研究中呢?应该可以。从类型学研究方法来看,语言学那种大规模的多种语言比较的研究,目前在文学研究中未见有如此运用的案例。但本文认为,现在已经具有展开这样的研究的可能性:根据民间文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阿尔奈—汤普森分类法,(36)参见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D. L. Ashliman, A Guide to Folktale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ased on the Aarne-Thopmson Classification System,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将不同民族的故事的相同元素输入数据库,然后借助大数据分析,这样则可解决上文罗宾斯所提出的近似的问题:“这个语言像什么语言”,即“这个故事像什么故事”,构建起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故事元素的宏观图谱。足见,将类型学移植到文学研究中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