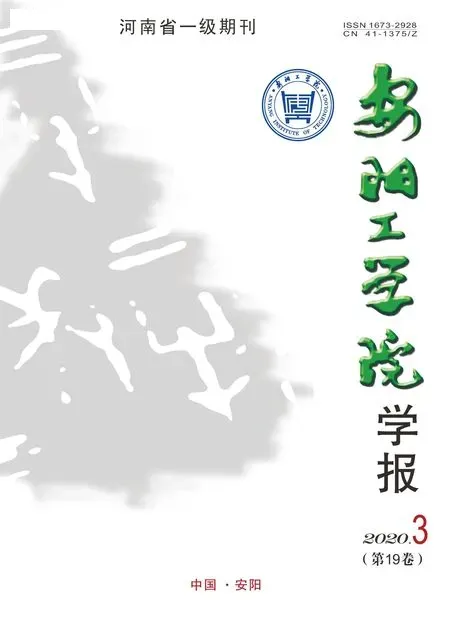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爱情悲剧的文化解析
2020-12-27周婷
周 婷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合肥230000)
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文学史上塑造的一个个经典女性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美丽、温柔、善良,但命运多舛,在爱情中处于弱势地位,成为爱情悲剧的牺牲品。中国古代文化中重男轻女思想倾向严重,妇女缺失自我主体性,包括爱情难有主导性。许多才艺俱佳的淑女对爱情有美好希冀,但现实是残酷的,她们对美好爱情的设计在残酷生活面前不堪一击,难以实现。她们纯洁、善良、孝亲敬长……但笔者认为,这些传统女性的良好品德,一方面是男权主义思想对女人要求的投射,是以男性的需要来衡量女性;另一方面它又化为一种文化心理延续在我国历史发展之中,渗透于人们的血脉之中,出现于人们行动之中。本文从文化的视角对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爱情悲剧开展探析。
一、忍辱负重:弃妇形象
贤妻孝妇是我国传统文化理想妇女的形象。她们孝亲敬长、依附丈夫、尽心抚养子女。她们是古代女性的典范,为了别人生活得更加美好默默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但是贤妻孝妇也常常被男人无情地抛弃,化为“弃妇”,由此可以看出,女性具有贤孝的美德并不一定让女性能享受到爱情的美好。《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是此类女性的代表。夫妻恩爱,爱情很美好。她孝亲敬长,任劳任怨,为家庭尽力而为,付出了一切。但是,公公为了儿子光宗耀祖,让她必须送丈夫去考取功名,她愤懑、不舍,又无可奈何。丈夫走后,磨难不断:连年灾害,食不果腹,婆婆、公公先后离世,山穷水尽只有卖发买葬。虽然她为丈夫尽了孝心,有个好的结果,但仍是在牛氏的“开明”许可下才夫妻团圆,二人共有一夫。这样的“贤妻孝妇”仍是自我个性的丧失,迎合男权标准的需要,成为一个合标的“好女人”,但弃妇之实仍不可忽视。其形象体现了三个方面:孝顺服从,男尊女卑,自我牺牲。在这三个维度中,可以看出孝妇贤妻的精神追求是利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的[1]。在此类女性身上,作为人的情感被封建伦理纲常所束缚,并使自己的行动完全符合封建等级制度要求。诚如《荆钗记》中的钱玉莲、《白兔记》中的李三娘等,她们忍受人间苦难,外部压力与内心痛苦的叠加让她们丧失了自我,行尸走肉,成为封建道义的道具,虽然结局圆满,但弃妇之实仍使人掩面叹息。她们屈服命运,个人存在的价值荡然无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戏曲之中,人的道德品质的不断升值与人的个体生命的不断贬值恰成正比,道德力量愈是强大,人自身愈是渺小,甚至不成其为人[2]。当然她们如果自我意识觉醒、自我主体意识彰显的话更大的悲剧会随之而来,被丈夫或家人无情抛弃,成为“弃妇”则无可避免。《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虽然出身于霍王之家,但因为母亲地位卑微,加上家道中落,却成为“艺妓”。她敢爱敢恨,爱憎分明,才貌俱佳,守身如玉。她与李益情投意合,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与李益同出同入,俨然成为一对真正的夫妻。世事多变,李益飞黄腾达之后,就遵从父母之命,与官宦之家结亲,虽然李益有所顾忌,但仍依照父母的意愿行事,抛弃了霍小玉。霍小玉悲愤交加,卧床不起,最后“杯酒洒地,覆水难收”,自绝而亡。她以死亡来证明自己不可欺,证明自己对封建礼教的蔑视。
从文化视角来看,中国文化的核心要义是实现和平、稳定、和谐,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仍要追求理想。于是,文人对故事情节采取了理性化的处理,用托“梦”实现正义,还世人公道;或者让清官出面,处决负心汉;或者让女性化为鬼魂,惩罚负心汉,来实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正义,让正义文化回归社会。但人们要看到的是,这些都是文人们加上的光明尾巴,却不能掩盖整个故事的悲剧色彩[3]。
二、用情专一:痴妇形象
(一)用情专一,为情而死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娇红记》中的王娇娘、《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白蛇传》中的白素贞等都是爱情悲剧中的“痴妇”形象代表。她们对爱情专一,追寻婚姻自主,感情世界丰富。此类女性的描述体现了古代文学中女性角色的变迁,也是作家对封建男权主义的有意冲撞。她们的爱情悲剧是由她们自身的观念所牵引的,也是她们对封建礼教的最有力反抗与呐喊,自身的觉醒意识也日趋强烈。在反抗封建礼教过程中,她们自主性日益彰显,是现代爱情观的萌芽。《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所奉行的爱情是“至情”,即“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生动地描述了杜丽娘对至情观点的解读。《关雎》激发了她对爱情的向往,后花园引起了她对青春的思考,“美景如画,但无心欣赏,毫无意义可言。”杜丽娘最为令人欣赏之处是不仅用情专一,而且死后面对阎王毫不畏惧,据理力争,与封建礼教的代表杜宝针锋相对,毫无畏惧,以胜利告终。可以说,杜丽娘的“至情”是一种自我个性追求,要为自身的独立与自由打通道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爱情可谓是中国古代爱情的理想模式,它打破了既往的初见为“才子佳人,郎才女貌”,进而“一见倾心,小人挑拨是非而私奔”,最后“才子状元及第,奉旨大婚”的传统套路,体现一种“自主型爱情”:男女之爱,完全是双方的自愿,自己做主,不接受外部的包办与干预,是在生活中真实发生的。“风霜雪雨,矛盾交织”的环境下更能彰显青年男女对真挚爱情的不懈追求与向往,更能体现他们的斗争精神。他们对爱情观点已经上升到了精神层面:更注重心灵相通,彼此欣赏与羡慕,不是单一的情欲之爱。他们要冲破门第的限制,超越世俗的功名利禄,因此,他们的爱情不可避免地和封建世俗观念发生冲撞。林黛玉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为爱情牺牲了大好青春年华,正面冲破封建礼教对爱情的约束,走自己独有的爱情之路。虽然宝黛爱情曲折多难,但林黛玉对爱情痴心不改,为爱牺牲,仍成为爱情悲剧的陪葬品。在宝玉被逼大婚之日难以走出痛苦深渊,步入社会,回归自我。她的生存离不开荣国府这个大家庭,不能像杜丽娘、崔莺莺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反抗,无法到荣国府之外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开辟自己爱情的新生活,这是封建社会妇女生存的残酷写照。血淋淋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时的封建主义还是一只铁老虎,它是要吃人的[4]。许多追寻自由独立的爱情都被无情的扼杀在萌芽之中,相关的男女青年成为这种杀手的牺牲品。虽然有爱,有痴爱,也难逃幻灭的命运。
纵观这几个男女爱情的演进,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礼教逐步被瓦解,妇女自我解放的意识逐步被唤醒,她们坚强、成熟的一面为人们所认可。虽然她们的爱情观念仍很幼稚,但这是我国古代妇女爱情观的一种进步。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婚恋观也不断向前发展、进步。我们也可以管中窥豹看到封建社会及封建文化逐步走向没落,女性爱情意识的觉醒及男权思想的瓦解相对而行,这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必然结果。
(二)才貌俱佳,独立性缺乏
我们认真梳理中国古典爱情女性角色的演变,可以发现作家对女性的描述有前期的重“貌”发展到更加重“才”。中国传统文化更凸显“郎才女貌”,这是天作之合,完美一对。于是乎,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都是来自“一见钟情”,作为一个现代人认为这个不靠谱,无法深入了解,无法实现爱情的天长地久。但是,封建婚姻制度主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不可能与男性面对面交流沟通,因而,体态之美成为男女相爱的最佳方式,也是促使男女爱情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条件。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体态美是“首因效应”产生的重要条件,这是男女爱情火花产生的助燃剂。一般来讲,外貌美是爱情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这种理念在我国古代爱情悲剧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诚如《孔雀东南飞》对刘兰芝被遣返娘家的描述:“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事无双。”《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天姿国色,今日插了几朵珠翠,穿了一套绮罗,十分花貌,又添二分,果然可爱”[5]。《长生殿》对杨玉环的描述“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更有“德情温柔,丰姿秀丽”[6]。后人把这位百媚俱生、顾盼多彩的美艳无比宫廷贵妃称作“绝世佳人”,她的美貌是她专宠的主要资本。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演进,人们对女性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重点放在才能方面,才女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男才女貌”发展为“才子佳人”,唯有美貌不算是一个完美的佳人,必须有才来陪衬。男人对女人的追求不单单是看外在的美,更要考量女人的才能。譬如林黛玉作诗抒情,她可以用诗词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也可以以诗词来抒发自己的远大理想,以才让宝玉羡慕不已,陶醉其中。同时,此时的女性不限于自己的文学才能,它包含了谋、勇、智等多维才华。她们为了追随自己的理想爱情与封建礼教中的男权主义斗智斗勇,刚柔并济,这些女子是我们应当大力歌颂的对象,这也是后来男女爱情文学作品发展的主要方式,《红楼梦》把古代文学这种模式推向了高潮。
此时女性在爱情中更有主动性,她们帮助才子取得事业成功,功成名就,女性已经化为男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其缺陷也显而易见,女性才能是为男性功成名就服务的,是迎合“中和”文化为中国古代政治稳定服务的。中国文化倡导稳定、平和。为了延续这种文化,文化作品中女性才能无论有多高,仍不能纳入权力群体,没有发展空间与平台。女性群体仍沦为“缺席”及“失语”境地。
(三)情欲交困,成为男性附属品
人类是感情动物,情感与欲望是人类精神满足的基本要素。清代神话小说《牛郎织女》就鲜明地提出:“无论古今,男女总难逃脱一个‘情’字。情之所钟有爱情、有怨情、有艳情、有痴情。情到最密之处,便是大罗八洞神仙吕祖师,尚有‘三戏白牡丹’故事,至今小说脍炙人口。”[7]由此表明了情为人类的本性。但是,古代个别文学作品中也浮现淫秽内容,就如杜丽娘在爱的过程中,不但有“情”的成分,更有一种“欲”的内容。对于情与欲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杜丽娘的思想意识、实际行动来分析。《金瓶梅》中有不少性的描写,但人是高级动物,不只有“欲”,更强调“情”,这才是爱情的基石。这也是痴妇为情所困,敢于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拘囿,为情疯狂,为情而亡的动力。杜丽娘为了追寻理想的爱情,实现美好生活,历经梦幻般的生死轮回;王娇娘追求“同心子”,以身殉情;宝黛之爱,崇尚高尚、美丽的爱情,早已上升到情层面的爱。他们由一见钟情发展到心心相印,思想、情趣相近。他们把爱情提高到一种新境界。诚如恩格斯所言:“现代的性爱,同古代人的单纯的性要求,同厄洛斯[情欲],是根本不同的。”[8]但无论他们对“情”多么的专注,追求挚爱多么的勇敢,他们仍是男人的附属品,仍要把自己生活的幸福全部寄托到美好的爱情、如意情郎身上。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男人状元及第,就可以割断男女儿女情长,被封为真正的男子汉。无论是草根平民,还是皇亲贵族概莫能外。人所共知,杨贵妃是“三千宠爱集一人”,但不论与皇帝之间如何琴瑟和谐,在皇权遭受威胁之时,唐明皇只能牺牲她以保皇权。这是唐明皇在中国传统文化支配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女性爱情悲剧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结语
从女性的视角来探析爱情,它可以激发女性积极有为,完善自己;但对于男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来说,女人为爱情献身,为爱牺牲成为必然的结局。男权主义横行,女性对爱情没有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她们唯有从希望走向幻灭。归结来说,男尊女卑是造成女性爱情悲剧的外部原因,而女性自身缺乏自主性,对男性的过度依附则是导致爱情悲剧的内部原因。但悲剧并非毫无意义,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9]古代女性爱情的悲剧命运毁灭了女性自身,但又创造更高层次的美,赋予了爱情更深远的价值意蕴:建立在男女平等,通过抗争、奋斗而来的爱情更崇高,也更持久,更能接受生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