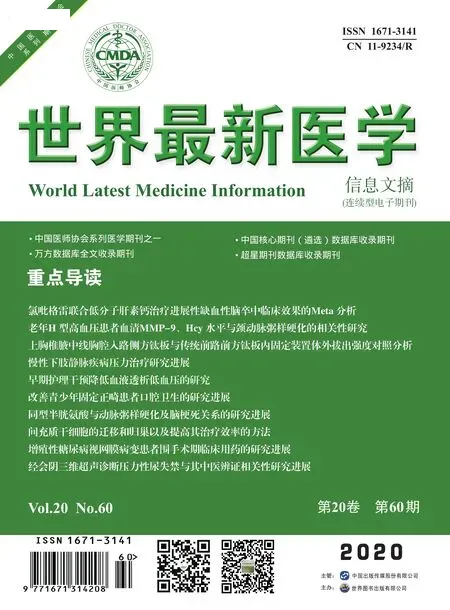浅析中医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因病机的认识、诊断与治疗
2020-12-27许飞
许飞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医院,安徽 滁州)
0 引言
在通过对病毒分离、核酸测序以及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COVID-19的主要致病因子是新型冠状病毒[1],该病毒经研究发现属于β属冠状病毒,该病毒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经官方命名为2019-nCoV,该病毒直径范围为60-140nm,基因组中含有约29.8 kb的核苷酸,其中拥有14个开放阅读框(ORF),可编码27种蛋白[2]。根据流行病学研究发现,COVID-19的潜伏期为1-14d内,多为3-7d[3]。临床上发现COVID-19患者多以发热、干咳、呼吸困难等为主要表现,部分可伴有恶心、腹泻等消化系统等症状[4]。正如《黄帝内经》中所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又如《诸病源候论》曰“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根据COVID-19具有较强的传染性、流行性等特点,可归属于祖国医学“疫病”范畴,现代医学目前尚无特效治疗,而我国传统医学在防治疫病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古代医学大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借鉴。
1 关于COVID-19的病因病机
COVID-19发病以来,中医界对其病因病机争议颇多,众说纷纭,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COVID-19的病因病机的见解。如申艳慧[5]等人认为本病病初邪气在肺卫,后波及后天脾胃,导致肺脾两伤,邪气未解,化热入营,最后气血同病而发病,常兼夹湿、毒、痰,主要病机是疫毒闭肺。范逸品[6]等认为该病的主要病因是伏燥在先,寒或湿寒居后,而气候失时,燥热湿寒相互作用导致的,其病机是疫毒湿寒和伏燥搏结,壅塞肺胸,损伤正气,导致气机痹阻,升降失常,元气虚衰。张乐乐[7]等认为COVID-19的病因为外感“湿毒之邪”,主要病机是湿毒闭肺,升降失司,甚至内闭外脱。王怡菲[8]等将我国24个省市自治区新冠肺炎的患者进行辨证分析,认为此次疫毒是由于外感疫戾之气,而此疫戾之气的性质为“湿毒”,且本病的主要病位在肺,故而由此可知湿毒壅肺为COVID-19的核心病机。由此可知,中医学者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加上地理环境区域的差异对COVID-19病因病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总体上多数人认为此疫毒与湿邪密不可分,同时可夹痰、化燥、夹毒等,且在临床实践中皆取得了显著疗效。故而在诊治COVID-19时,要充分运用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进行辨证论治,进而做到同病异治。
2 关于COVID-19的诊断
具体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9]执行。
3 关于COVID-19的治疗
3.1 古代大家治疗经验
我国传统医学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是我中华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实践中同疾病不断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它“历千劫而不朽,虽百代而长兴”,并且不断丰富完善。关于此次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的COVID-19,虽然我国传统医学未有COVID-19的相关记载,但由于其传染型、流行性,归于中医的“疫病”范畴,对于其治疗在浩瀚的传统医学史中可以寻迹。如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中就有疫病的相关记载即“温气流行”,防护措施主要是“避其毒气”。东汉末年,战乱纷争,疫病流行,人民深受其害,医圣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编纂出中医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并通过六经辨证,根据疫病的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方药治疗,如病在太阳,方选麻杏石甘汤、大青龙汤等;病在太阴,方选理中汤等;病在少阳,方选小柴胡汤等;病在阳明,方选白虎汤、小承气汤、大承气汤等;病在少阴,方选真武汤等;病在厥阴,方选乌梅丸等,仲景以上方为基础,常随症加减。金元时期,河间学派根据当时百姓的症状,总结出“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病”的传变规律,常以寒凉之方药,发表邪,攻内热。邪在表者运用双解散,邪在内者运用三一承气汤、解毒汤。温病学说经过历代的补充和完善,至明清趋于成熟。如明代温病大家吴又可,认为疫病的致病因素乃是“戾气”所致,戾气多自口鼻而入,后伏藏于半表半里之膜原,故自创达原饮治之。清代医者叶天士,根据温热病发生、发展规律,自创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并以此提出“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宜清气;乍入营分,犹可透热;至入于血,直须凉血散血”的临床用药规律,对指导临床用药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2 现代医家治疗体会
毛靖等[10]分析COVID-19由外感“疫戾”之气犯肺,主要临床症状是咳嗽、气促、气喘,均为肺系症状表现,同时根据本病病初寒湿,随着病情进展可能有湿热等表现,由此将仲景名方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等进行化裁加减运用临床(其中轻型、普通型、重型以及危重症COVID-19患者均可运用之),并重新将其命名为清肺排毒汤,效果明显。张公奇团队[11]对13例COVID-19患者运用传统中药治疗,对病初辨证为湿毒郁肺证的患者予以宣肺解郁,化湿和胃,具体方药:香附12g、黄芩10g、鱼腥草20g、焦三仙各15g,苍术10g、厚朴10g、枳壳12g、法半夏10g、藿香10g、杏仁6g、陈皮6g、草果6g、生甘草6g、炙麻黄6g等;病初辨证为湿热郁肺证的予以清热解毒,宣肺解郁,化湿和胃,具体方药:生石膏18g,焦三仙各15g、芦根30g、连翘15g、鱼腥草30g、厚朴12g、杏仁10g、黄芩10g、射干10g、香附12g、草果6g、炙麻黄6g、生甘草6g等;对于进展期的COVID-19患者根据其体质可选藿朴夏苓汤、小柴胡汤、平胃散加干姜、黄芪或连翘、麦冬、杏仁、石膏等加减治疗。对于恢复期的COVID-19患者予以健脾益气,方选黄芪六君子汤加减,同时结合西药激素、抗感染等对症处理,结果12例患者治愈出院,1例患者转院,治愈率高达92.31%,说明中西医结合治疗COVID-19能明显提高患者治愈率。马家驹[12]等根据具体实践情况,认为COVID-19患者初期主要为湿毒郁于上焦膜原,进展期则多为湿毒热化,进而淫肺、壅肺、闭肺、甚至内闭外脱。并以此进行辨证论治,初期多以芳香辟秽、宣畅气机、分消走泄、凉血活血、祛瘀通络等为主,代表方药:藿香、佩兰、厚朴、半夏、杏仁、枇杷叶、滑石、薏苡仁、通草、茯苓、猪苓、泽泻等;进展期宜芳香化浊宣肺、清营凉血解毒为主,代表方药:雷氏芳香化浊法、解毒活血汤合升降散加减;极期因患者病情加重,常出现内闭外脱之状,故予以行开闭固脱、解毒救逆之法,代表方药:参附四逆汤合三宝或苏合香丸;恢复期患者症状明显改善,但正气已亏,故常予以清解余邪、宣肺运脾以扶正,代表方药:薛氏五叶芦根汤加减,并可随症加减。吴欢[13]等认为作为中医八法之一的“下法”,在治疗温病的过程中十分重要,因COVID-19患者尤其是危重型,常津液耗损,腹中常气结,粪便淤积于肠腑,故常采用灌肠或鼻饲中药通腑泻下,一方面可以泻湿毒、祛积粪,另一方面还可以降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改善凝血功能,增强免疫等,具体方法:使用生大黄15~20g加温开水(150mL)泡服、大承气汤口服或灌肠;若疫毒闭肺可参考运用宣白承气汤合甘露消毒丹加减;若毒热炽盛,腑气不通、食药不下,可短期予生大黄煎汤灌肠救急。李希[14]等认为本病虚实夹杂,实以湿邪为主,同时可兼寒、热、毒等邪气,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病邪性质的不同,治疗方案也不同,如早期患者的代表方药:小柴胡汤,中期代表方药:麻杏石甘汤合蒿芩温胆汤、达原饮合甘露消毒丹、清瘟败毒饮,缓解期患者正确已亏,故重补虚,代表方药:生脉散合六君子汤、沙参麦冬汤。
4 讨论
COVID-19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等特点,病情常十分复杂,目前在没有特效药及疫苗的情况下,作为中医人,应当从中医理论出发,以辨证理论为基础,“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通过辨别疫病的寒、热、虚、实以及兼证,然后确立证型,最后遣方施药。然而中医在防治COVID-19的临床工作中仍有不足之处,一方面治疫方药尚未完全统一标准[15],另一方面缺少严谨的前瞻性基础和临床研究,以及中医药的作用靶点的分析等。虽然如此,但中医药在此次疫情中仍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信最后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还人类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