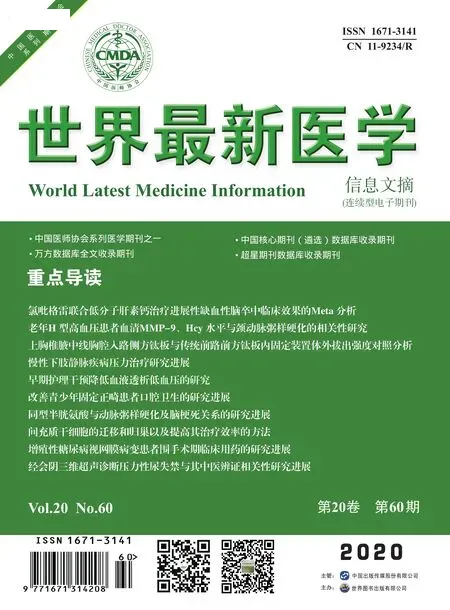亚肺叶切除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进展
2020-12-27王柯宋剑非
王柯,宋剑非
(1.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广西 桂林;2.桂林医学第二附属医院,广西 桂林)
0 引言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及死亡率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1],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 约占80%以上。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中推荐的关于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首选治疗方式是肺叶切除[2]。
目前外科发展的主攻方向是“微创”。电视胸腔镜手术(video assisted thoracoscoplc surgery,VATS)出现于上个世纪90 年代,抱着“精准外科”的理念,电视胸腔镜技术日渐发展成熟,胸腔镜辅助下切除肺占位已是目前肺癌治疗的主要方式。美国NCCN 在2006 年发布的肺癌诊疗指引中也对胸腔镜的技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持认可态度[3]。
腔镜自诞生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目前腔镜设备、器材精细度不断提高,医生操作经验不断积累,技术不断成熟,以及近几年低剂量螺旋计算机断层扫描(low- dose computed tomography,LDCT)在肺癌筛查中广泛普及,早期肺癌的检出率提升,亚肺叶切除也逐渐被重视。胸腔镜下肺段切除逐渐被应用于临床以减少因肺组织切除较多导致肺功能的损耗,从而保留更多健康肺组织。
亚肺叶切除(肺楔形切除和肺段切除)早期主要用于原位癌、磨玻璃成份高于50%结节、长时间影像学随访未见明显变化、肺功能差无法耐受肺叶切除的患者[4]。本文将重点对亚肺叶切除中的肺段切除进行综述。
1 肺段切除的手术治疗
人体解剖学显示,左肺可分为上、下两个肺叶,共八个肺段。右肺则分为上、中、下三个肺叶,共十个肺段。镜下解剖性段切可更加精确切除占位相应肺段,精细区别肿瘤和正常组织。
临床上部分患者存在解剖上的变异,尤其是肺段的血供及气管分布解剖变异相对较高,故在切除顺序及视野上需灵活变通,其游离顺序不能一成不变。手术医师需要有较强的思维应变能力,根据不同肺段选择不同的入路及顺序,同时保证操作安全、有效、快捷。在临床中相较于其他肺段,舌段及下叶背段解剖变异较少,其位置及活动度也有较大优势,故手术分离操作相对简单。但是基底段解剖位置活动空间小,血管、气管分布变异多,行腔镜下切除术尚有难度。
2 肺段切除的适应症和禁忌症
针对高龄患者,结合美国NCCN 及各研究中心资料,非小细胞肺癌(NSCLC)胸腔镜下亚肺叶切除的适应证可总结如下:(1)占位较深,楔形切除困难者;(2)病变主要位于单个肺段内;(3)疑似侵袭血管,气管的转移病灶;(4)术前临床分期诊断为TlaNOM0 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或磨玻璃样结实性成分大于50%;(5) 原位癌(adenocarcinoma in situ,AIS)。禁忌证:(1)基础疾病多,心肺功能差,不能耐受麻醉;(2)亚切不能保证切缘大于2cm;(3)隆突下淋巴结病理阳性;(4)病人不接受亚肺叶切除。
3 段切相较于叶切的优势
临床上若提倡亚肺叶切除用于早期肺癌的治疗,需要有一定价值的临床优势支撑我们的想法。
多数临床研究表明段切及叶切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死亡率和远期生存情况无统计学差异[5]。Hwang[6]等研究结果表明叶切组与段切组在手术时间(P=0.47),住院天数(P=0.31),术后并发症(P=0.1)及死亡率(P=0.36)无显著差异;随机对照试验JCOG0802 试验[7]中叶切及段切的围手术期对比结果显示瘘或漏气在段切组发生率高于叶切组(6.5% vs3.8%,P=0.04),多因素分析表明肺部并发症(包括漏气及脓胸)的独立危险因素是复杂段切(OR=2.07,95% CI:1.11-3.88,P=0.023)及超过20 年包的吸烟(OR=2.61,95%CI:1.14-4-5.97,P=0.023),其中复杂段切涉及除背段;CALGB140503 试验[8]的事后分析结论表明2 cm以下早期肺癌行意向性肺段切除与肺叶切除在围手术期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上无显著差异;日本有回顾性研发现,对于高龄患者,行亚肺叶切除与行标准肺叶切除其长期生存率无明显差异[9],当早期周围型肺癌直径不大于2 cm 时,段切似乎是老年个体的更优治疗方案[10]。然而对于心肺功能好,年轻患者,目前仍建议叶切,哈佛大学医学院领导的LCSG 也得出类似结论,其认为亚肺叶切除主要用于那些高龄及全身疾病较多的患者,但在身体基础较好的患者,全肺叶切除的地位不可代替[11]。
多项研究表明段切和肺叶切相比可保留更多肺功能。这与段切中健康肺组织切除量少,术后残腔更小有关。Suzuki等的研究[12]结果表明术后2 个月内段切组的肺功能恢复显著 优 于 叶 切 组(FVC: P[0.001;FEV1:P(0.01)];而 术 后6 个月后,两组的肺功能改变无显著差异(FVC:P=0.96;FEV1:P=0.33)。Suzuki[12]等通过定量CT 比较了两组术前及术后6 个月肺容积及质量改变,认为叶切术后同侧非手术肺叶及对侧肺叶的功能代偿较肺段切除更明显,由此导致了两者术后肺功能相差无几;Yoshimoto 的一项研究[13]通过单光子发射电子计算机断层显像,计算机断层显像灌注和常规肺功能测量来比较亚肺叶切除在保护肺功能方面的优势。其研究中56 例肺癌患者行解剖性肺段切,其结果显示行切除的第一秒通气量(FEVE1) 比叶切者高[(88%±9%) VS(77%±7%),P[0.01],故Yoshimoto[13]得出结论:在肺功能恢复上亚肺叶切除术有较大优势;与张小川等研究结果一致[14],术后14 天的部分肺功能指标:潮气量、每分钟通气量、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及动脉血氧饱和度等均较肺叶切除组高[15]。虽多项研究表明亚肺叶切对保护肺功能有优势,但考虑到术后余肺功能代偿,故肺段切除和肺叶切除对肺功能的影响尚需更多临床研究证明[16]。此外,肺段切中肺实质的切除程度、切除肺段的位置和切除肺段的数目很大程度上也影响肺功能的保留。
不少单中心的研究发现:段切术后肺不张的发生率较叶切除低,术后引流量也较少,这考虑与段切中肺组织切除量少,术后残腔小有关。段切术中纵膈淋巴结采样相较于叶切组系统性清扫纵膈淋巴结来讲,其所致创面更小,术后渗出量自然更少[14]。但也有研究结果与上相反,其解释是由于肺段相应血管、支气管位置较深,暴露困难,段门处的解剖游离尽量向远端肺组织内延伸,分离时间长、创面大[15]。故具体关于两者术后引流量的多少的比较,仍需更多研究证明。
段切相对于叶切的优势在于更能减少术后肺功能损失,减少围手术期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等,但其缺点在于切除范围不足及淋巴结清扫不足而增加术后复发率及肿瘤相关死亡率。但这几点需更多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证实。关于亚肺叶切除的局部复发,目前可辅助予以局部治疗,Lee 等予碘125 粒子植入近距离放疗可明显降低局部复发率[16]。
虽然目前多数临床研究表明段切对保护肺功能有优势,但大多数属于回顾性分析,样本量小,偏倚较大,证据级别低,所以仍需大量前瞻性研究所证明。
4 肺段切除段间平面的确定
在亚肺切除中,肺段切除解剖花费时间相对较肺叶切除耗时更长,段门处解剖结构复杂,肺段血管、支气管变异多,故胸腔镜肺段切除术操作更为精细,对医生技术要求更高,需经验积累、团队配合、增加手术量、提高手术技巧,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及术后引流量。其学习曲线从简单到复杂,可先由舌段、下叶背段、右上肺后段、左肺固有段切除起步。对于叶裂发育较好的患者,有浅至深、由近致远,依顺序处理动脉、静脉、血管、器官,在保证手术切缘足够的情况下,对于邻近段间裂的结节逐步过渡到联合肺段及联合肺亚段治疗[17]。
目前胸腔镜下解剖性肺段切除术的难点和争议点是如何准确、迅速地确定相邻肺段之间的界限[18]。现下临床医师较多采用改良膨胀-萎陷法确认肺段边界,该法操作简单,不依赖特殊设备[19],其主要是根据肺段间静脉或肺充气与萎陷界限来判断。通过选择性节段性通气膨胀肺来判断边界水平时,要保持低压力、低容积、避免过度通气使气体通过肺泡小孔后将靶肺段鼓起。对于肺气肿较严重或胸腔粘连的老年患者采用膨胀一萎陷法显示的段间平面界限不清。另外如何精确把握膨胀萎陷时间也是该方法面临的挑战。术中应用支气管镜进一步明确靶段支气管,明确解剖后进行导管高频通气膨胀靶肺段,需时15~20g,耗时略长[15],但是时间过短或过长均会导致段间平面显示不清[19]。术中电刀标记膨胀萎陷分界线,用切割缝合器分离并切割,因切割缝合器均为直线型,受限于手术切口及段间裂的方向,需要有适应的过程[15]。
吲哚菁绿荧光显像可准确,快速的显示肺段的段间平面,单次注药后可以获得足够时间对肺段间平面进行标记。吲哚菁绿本身具有低毒性,良好耐受性和价格低廉的特点,故吲哚菁绿荧光显像是一种简单,安全,有效的确定肺段段间平面的方法。但是临床实际中也发现这种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它需要应用远红外荧光腔镜系统支持,目前该类设备均价格昂贵,限制了该技术开展。其次,该技术荧光显像的基础是肺部血管的动脉分割并不是段支气管分割,所以特别适用于肺气肿患者。此外吲哚菁绿荧光显像对术前手术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术中出现动脉离断错误,将会直接导致肺段段间平面的识别错误。由于吲哚菁绿代谢较快,不能长时间显像,在进行肺段段间平面分离时不能实时显示段间平面界限[19]。
近年来,三维肺支气管血管重建(3dimensional puted tomography chography3D—CTBA)技术不断成熟,其为精准肺段切除提供了术前技术支持。术前肺3D—CTBA 可以充分了解各肺段的空间关系及血管、气管变异,有利于术前讨论规划并制定最佳的手术方案,这样可更精确,安全地实施手术,减少患者术后并发症,实现术后快速康复[20-23]。据报道更有国外学者在术中行CT 扫描以达到进行定位导航的效果瞄。故由上述可了解,在行肺段切除时,由于段间平面的辨别存在一定困难,尤其对于肺组织发育较差的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其肺段并不完全基于书本上的解剖结构,如此可造成“欺骗性或错误性肺段切除”。另外肺段切除范围较肺叶切除明显少,如果不能保证切缘的话,这也会增加肿瘤复发的风险,进而导致预后较差。故对于术前或术中证实段间或叶间有淋巴结转移者,在评估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仍建议行叶切[24]。
5 小结
近些年低剂量螺旋CT(LDCT)在肺部检查中广泛应用,早期肺癌的检出率提升。直径≤2 cm 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外科治疗方式多样化,当前三维立体真实视野胸腔镜等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术者经验的积累以及手术方法的不断更新,腔镜下肺段切可作为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优选手术方式[3。需强调肺段切需要强大的占位定位技术支持,现有的定位技术在安全性,简洁性及有效性上有一定的效果,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多项研究证明解剖性段切逐渐成为早期肺癌的优选手术方式,尚不能完全取缔肺叶切除的地位而成为标准术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