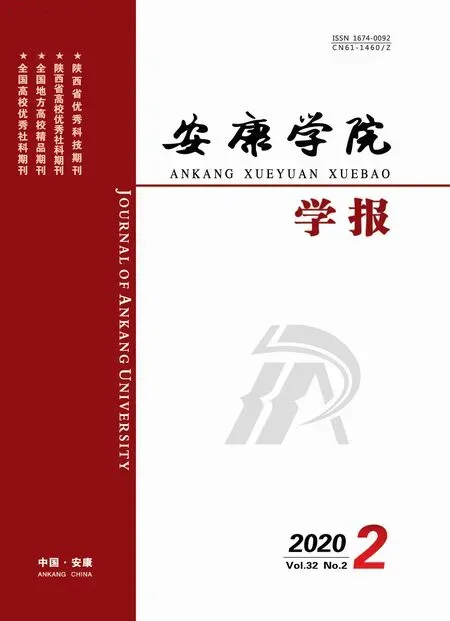从“历史三调”看太平天国运动
——以“经历”和“神话”为中心的考察
2020-12-27张雅文
张雅文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一、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
“历史三调”是关于历史的三个认知途径,即事件、经历和神话。以义和团运动为例,在“事件”这个认知途径上,历史学家描述了作为一个完整事件的义和团运动;第二个认知层面即“经历”,柯文考察的是参加义和团运动的不同人的动机,以及国内外人对此的不同看法;第三个认知层面即“神话”,主要是由神话制造者(以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为主)根据现实需要来构筑的“义和团”,这种神话的“历史”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因此,历史具有多个面相,我们不能从某一个方面来认知。
几乎所有严谨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历史本身包含两种成分:一是历史时间中的各种事件;二是该事件在人们心中的回忆和书写。同一个事件,人人眼中所看不同,笔下所言亦出入甚多,“历史”便失去了真正客观的标准。布莱德雷(Bradley)是这样回答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乃是实际的标准;而理想的标准(如其可以容许有这一反题的话)则是作为一位理所当然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而忠实于当前的历史学家,便是当然的历史学家。”[1]因此,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方面,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主观性,这是毋庸置疑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赋予历史学家重现历史的使命,然而,由于时间的一维性特点,历史学研究只会无限接近史实,而不会完全重现过去。正如柯文所说:“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实际上根本不同于人们经历的历史。不论历史学家能够选择和实际选择的史料多么接近真实,多么接近人们的实际经历,他们最终写出来的史书在某些方面肯定有别于真实的历史。”[2]2因为史料“不会‘纯粹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是“通过记录者的心灵折射出来的”[3]。历史具有解释的功能,历史学家总是以当前的眼光来理解和解释过去,经常给历史事件划定界限,何时开始,何时结束,都以某个特殊事件为标志(虽然并非一成不变)[2]72。
“凡是历史学家都难免把自身的某一部分注入他所力求表述的历史现实中去。”[4]283托克维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尽管努力地维持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然而在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他写道:“我希望写这本书时不带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未怀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起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竟然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5]。可见,历史学家在重塑过去时,他们制造出来的“历史”与史实有一定的差距。“历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用于编排和取舍历史资料的理念,均受到性别、阶级、国籍、种族和时间等诸多因素的极大影响,所以探求历史真相的行动具有很大的相对性。”[2]182这种相对性,也使我们不断地怀疑,历史学究竟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客观标准”。
太平天国运动被看作我国农民运动的顶峰,作为一个事件,历史学家将其描述得非常完整,然而我们不能妄图仅从“事件”来认清楚它,从“经历”和“神话”两个角度来看,更能认识到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太平天国运动。
二、作为“经历”的太平天国运动
“历史真正的主要课题,不是已发生的事情,而是当事情发生时人们的感受。”[6]247但是,作为经历者来说,他们眼中的历史也未必就是真正的历史。他们虽然亲历亲为,也可以有选择性,因为“人们的历史经历是以感觉为基础的”[2]47。除此以外,人们对自身经历的理解也会受到他们所处的文化空间、社会空间以及地理空间的严重制约。作为经历者,他们会带着很强的动机意识去理解这件事。“过去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的盲目性,这个特点使所有的经历变得色彩缤纷,饶有趣味。”[2]61通过“移情”①“移情”是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来的,即卸下那张紧紧地裹着史家自身的文化的、历史的乃至个人的“皮”,然后钻进他所研究的对象的“皮”中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得更加彻底:“移情就是把‘自我’全部渗入移情的对象之中。”的方法,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不同人对该事件的不同观感,从而深入理解认识历史的第二条路径。
太平天国运动对整个中国造成了深远影响,社会中各阶层的人都无法无视这场运动。但是时人的经历和感受必定是不一样的,由于人们所处的阶级不同,他们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看法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阶级属性。如当时一个清朝官员这样上奏道光皇帝:
“道光三十年五月初六日奉上谕:有人奏,广西会匪猖獗,请饬严办一折。广西向多会匪,近因楚匪窜入境内,各府匪徒乘间四起,地方官不能兼顾,以致蔓延为患。如所奏上年马平县高圩被焚劫者数十家,迁江县朴佑村焚劫至数十百家,今年正月有贵县、永福、永安等州县焚劫之案。近日,宣化、庆远、东乡、桂平等县及象州地方皆有贼首啸聚,分伙肆掠。由永福至雒容,修仁各县属村庄,被其荼毒者数十百家。惟象州报劫至五百村为最甚,而苍梧县赤火村至于烧毁一空。果如此等情形,贼之害民已极……”[7]
官员从满清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将太平天国运动描述为残害人民和社会的土匪之举。显然,作为满清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官员始终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根本目的,他们认为只要威胁到了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即是盗匪。然而这仅仅代表的是清朝官方的一种看法。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众多近代中国的文献中,《金陵被陷记》是身在太平天国治下一个多月而反对他们的文人所作,其中这样记载:“城匪下沿途喊曰:是百姓皆闭门。其未及知与街巷行走者皆被杀。可怜一日之间,尸填街巷。十一日内城陷落旗男女老幼俱杀尽……至十四五日后,则不论贫富,挨户扣门,劫取财物,虽贫家升斗之粮,亦必掳去;或将百姓合家逐出而为贼馆。数日内,通城铺户一空……”[8]171-172这条记载出自反对太平天国的文人之笔,旨在宣传太平军的残暴。仅从这两则材料来看,清朝官员和部分文人均对太平天国持一种完全反对的态度,他们从自身的阶级立场出发,只认识到了该运动对社会的破坏作用。
然而,是不是时人的观感皆一致呢?也不尽然。英国人呤唎此间正好生活在中国,“呤唎一进入太平辖境,他就看见防守边境的军士们的彬彬有礼、严整肃穆的气象与所见清朝官兵的凶残贪暴大大的不同,生气勃勃的革命军给他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老百姓熙熙攘攘地往来,特别是乞丐完全绝迹,跟他以前在清朝统治区所见市镇到处都是乞丐云集的情况恰好成为最显著的不同的对比,使他十分惊奇”[9]。可见,呤唎对太平天国治下的社会充满了好感,与清军相比,在他眼里,这里一片繁荣。除此之外,英国伦敦布道会麦都思(W.H.Medhurst)牧师对太平军的一个逃兵采访之后认为:“这场革命多么合乎道德!它引导十万之众的中国佬成年累月地戒烟,戒鸦片,戒色,戒贪欲;舍弃合法报酬,同意过没有钱的生活(在中国佬心目中,钱比生命本身还重要)所有人共享一切,一体平均……但如果上述一切属实(或有一半属实),那么,这肯定是一场合乎道德的革命,是我们时代的奇迹”[8]96。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麦都思对这场农民运动是持高度赞扬态度的。他认为这场革命运动突破了中国古代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正在朝着一种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与正统满清王朝相比,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总之,在麦都思看来,这是一场高尚的革命。
但是,同为洋人的亚历山大·米切却与前面两位看法不同。他在给安特罗巴士的一封信中这样介绍:“我对这场反叛运动会出现什么善行不抱任何希望。任何一个规矩的中国人都不会卷入其中。他们所做的仅仅是焚烧、杀戮和毁坏。除此之外,他们几乎别无所好……他们关注劫掠,仅仅依靠劫掠来维持生存……”[8]163-164亚历山大·米切将太平军的野蛮与落后毫无保留地揭示了出来,与清朝官员一样,他认为太平军是扰乱社会安定的土匪。
除清朝官员和外国洋人外,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普通百姓对太平军的看法。在清代民间笔记里,“被掳”“(女子)被污”(甚至有许多幼女被污的记录)和“遇害”三个词出现频率最高,笔记虽极其简略,却让人看到了那尸横遍野的情境。如果说笔记是被人加工过的历史事件和经历,那么在这场大动乱中,真正经历其中的民众的感受或许更加具有说服力。珍妮·艾约瑟牧师在访问南京城的一个村民时,他们这样交谈:
“你们在长毛政府的统治下感到幸福吗?”
“差得远呢,我们十分不幸。我们每个月都得奉命交纳钱粮。”
“在这一带,每一百人当中失去了多少人?”
“15或20人被杀,30到40人被掳去参加了叛军。”
“这些被征入伍的人去了什么地方?”
“很远的地方,苏州或嘉兴,或别的省份。”
“你们的女人是不是也被掳走了?”
“是的。年纪大的和相貌平平的被送了回来,但年轻貌美的并没有回来。”
“如果你们蒙受了冤屈,能到附近的地方官那里伸冤吗?”
“可以,我们被告知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们不敢……”[8]146-147
这段交谈也耐人寻味,普通民众对太平天国统治下的生活状况极其不满,然而他们只能安于现状,不敢有所作为,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并非所有老百姓都对此持不满态度,也有部分民众对太平军大力支持。夏燮在《粤氛纪事》中记载:“(太平军尚未至乐平)则土匪已先倡献城之议,文武员弁先期走匿,土匪距其城。贼至,遂指示其仓谷、漕米所在,助运入饶。贼又上行数十里,至德兴至螺丝埠,挽舟以受德人之赂。”[10]125太平军回师饶州时,“舟过石镇街,典商率各铺户犒师,备米一千石,钱二千串,运送至郡”[10]126。所以,不管是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还是一些人为了活下去,均对太平军持支持态度。因此,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对太平军的不同态度,均是以自身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
总之,对于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不同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柯文先生所言:“如果把经历视为‘文本’,把亲历者视为‘读者’,那么,不同的读者会以不同的方式阅读或者‘建构’文本,赋予文本不同的价值观、信仰和神话。”[2]67-68这样看来,经历不是“真正的过去”,除去人的主观感受,才会有真实的历史,但是脱离了人的历史,又怎能叫“历史”呢?所以,在每个人眼中,根本不存在真实,哪怕他是某一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对于每一个参与历史的主体来说,没有任何“标准”可言。
三、作为“神话”的太平天国运动——革命史观的建构
认识历史的第三个途径即“神话”。柯文教授考察了二十世纪时中国境内产生的有关义和团运动和“义和团主义”的种种神话。与“经历”和“事件”相比,受众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已经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所持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神话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所有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神话,主旨都并不在于解释义和团的历史,而在于从义和团的历史中汲取能量,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神话制造者极力地将现实与历史联系,甚至强迫现实与历史进行对话,使历史带有了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具体到太平天国运动这个事件上,作为神话的太平天国运动,最显著的就是政治精英以其为基础,进行革命史观的建构。
进入二十世纪,一些著名政治领袖开始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修饰。民族革命之初,孙中山继承了太平天国反满的传统,对太平天国运动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孙中山本人还曾以“洪秀全第二”自诩,以至于当他与好友陈少白、杨鹤龄和尤列一同谈论政治问题时,孙中山本人因为钦佩太平天国的领袖,也被起了“洪秀全”的绰号[6]21。1904年,孙中山在刘成禺写的《太平天国战史》序言中言:“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掩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而皇祀弗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知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非洪,是盖以成功论豪杰也……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虽以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遂底于亡”[11]。很明显,在民族革命初期,为进一步推动革命的历史进程,达到“排满”的政治目的,对孙中山来说,借助于推翻“清妖”的太平天国就是最恰当的选择。革命党人至此走上了神话太平天国运动的第一步,即通过对太平军采取隐恶扬善的态度,来激发人们的革命斗志。
孙中山在革命初期的这种表现直接影响了蒋介石。蒋介石、白崇禧、于右任为《太平天国诗文钞》作序云:“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而其政治组织与经济制度,则尤足称焉。……吾党总理又常为予讲授太平天国之战略战术……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纪念焉。”[12]蒋介石等人如此高度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究其主要原因,也是深入进行民主革命的需要,为了加强政治影响力。太平天国运动经过这样的表述,成功地与现实之间进行了对话。
“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便不再承认自己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而是以同治中兴名臣曾、胡的继承者自居。”[13]94-95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民党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认同以保卫传统文化自居的曾国藩和胡林翼等人,并将曾、胡二人视为国民党人的精神楷模,以此来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稳定政治统治。然而,国民党并未淡化太平天国对他们的影响。一直到抗战时期,国民党还承认国民革命与太平天国运动之间的联系。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曾言:“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惟有我们国父倡导的国民革命与三民主义为我民族复兴的惟一正确的路线”[14]。可见,蒋介石依然把太平天国运动视为国民革命的起源,认为两者之间一脉相承。在追根溯源的表面之下,于太平天国运动而言,无非是将其继续神话的一种表现。“所有的表述,正因为是表述,首先就得嵌陷在表述者的语言之中,然后又嵌陷在表述者所处的文化、制度与政治环境之中。”[4]282所有被神话的历史,都因为语言和表述而变得更加鲜活。
至抗战后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国共关系也趋于恶化。中国共产党对这件事也有所反应。1943年7月,陈伯达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写道:“中国从来显然有两种文化传统思想:一种是民众的、革命的、光明的;一种是反民众的、反革命的、黑暗的。近代中国一开始时候,太平天国与孙中山就是代表前者,曾国藩及现在中国的一切反共反人民分子就是代表后者……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国从来以至洪秀全、孙中山一切优良的革命的传统,而一切反动派则继承曾国藩、叶德辉的传统”[13]93。共产党人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也将自己的革命运动视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继承,这是在运用革命思想与反传统思想来为自身的建设进行政治宣传。
综上所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的革命运动都离不开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构建,革命党人和国共两党都运用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一系列政治宣传活动,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构建了对话。
四、余论
“历史具有伸缩性,我们把历史塑造成形,它反过来又影响我们。”[2]230而且,由于神话的“历史”多与社会(现实)联系比较密切,所以神话对人们认识过去有很大的影响力,关于某个事件的明确结论一旦深深地植入人们的心中,大多数人总会根据结论不加怀疑地认可与之相符的“真相”。这种观点或结论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大多数人只会接受,而失去了怀疑的本能。所以,不可否认,就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许多历史事件都是被神话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话不断加深。
但是,历史学终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学本位也是所有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应该坚守的。所有的文本与史料都是学者构建历史和认识历史的权利来源。历史事件总是有多个面相,事件、经历和神话都只是其中之一。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历史”,总是夹杂着历史学家和其他人的认识于其中的,即使是史料也带有记录者的主观感受和认知。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曾写道:“秦以后的2000余年里,中国专制社会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晋董狐、齐太史式的历史记录者。”[15]所以我们有理由去怀疑任何一则史料的真实性。
虽然有些已经被神话的历史不免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进一步神话,但不容忽视的是,神话存在的场域也存在一步步消解的可能,我们能够给众生历史假面一个史实聚焦。随着众多新的材料被发现,人们以后接触到的“历史”会进一步向真实靠近。正如柯文教授探讨的义和团运动一样,在“事件”“经历”和“神话”三个路径中,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更加清晰的义和团运动。我们追求真实,因为历史学的第一标准就是真实,因此,历史研究就必须坚持以求真求实为根本目的。同时,史学家要坚持秉笔直书,“书写真实的历史”永远是一个史学家的厚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