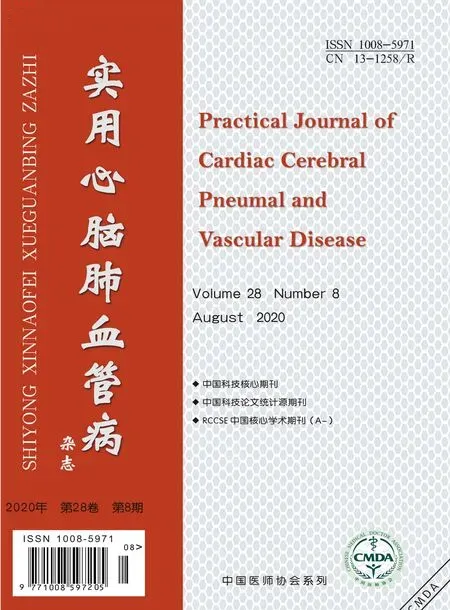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激动剂治疗肺癌的机制及临床证据研究进展
2020-12-27魏士雄
魏士雄
肺癌主要分为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两种类型,其中由腺癌、鳞状细胞癌和大细胞癌组成的NSCLC占所有肺癌患者的85%。据统计,每年因肺癌死亡人数约占癌症死亡人数的25%[1-2]。目前,已知的肺癌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基因突变、饮食不良及空气污染等,此外还包括慢性肺部炎症及感染[3]。虽然近30年来全球医疗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仍低于18%,究其原因主要为肺癌患者确诊时多处于晚期,其5年生存率仅为2%[4]。因此,临床迫切需要探寻肺癌新的预防及治疗方法,以提高患者预后。
肿瘤的形成机制主要为细胞获得去分化或逃避终末分化的能力,之后以不受限制的方式增殖并能够逃避凋亡,因此逆转细胞形成肿瘤的过程已成为癌症治疗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近年研究表明,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γ,PPAR-γ)激动剂具有限制肿瘤细胞增殖、生长等作用,此外其还能诱导肿瘤细胞分化和凋亡,因此临床上认为其存在抗肿瘤效应[5]。笔者通过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了PPAR-γ激动剂治疗肺癌的机制及临床证据,旨在为PPAR-γ激动剂作为肺癌新的治疗靶点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1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s)的作用及分型
研究表明,激活核激素受体能对几种常见肿瘤产生治疗作用,此外雌激素受体β、视黄酸受体α和视黄酸X受体(retinoid X receptor,RXR)激动剂在多种癌症中具有前分化、抗增殖和/或促凋亡作用[6]。PPARs作为另一类核激素受体,可参与脂质和糖代谢过程,但近年研究表明,转录激活或抑制PPAR靶基因在与致癌相关的细胞分化、增殖、存活和凋亡等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7-8]。
PPARs广泛存在于机体各种细胞,主要分为PPAR-α、PPAR-β/δ及PPAR-γ三种分型,且每种分型结构、功能、表达部位及表达模式均有所不同[6,8]。与PPAR-α、PPAR-β/δ相比,PPAR-γ在肺癌组织中的作用更为活跃,因此其作为肺癌抑制因子的研究价值较高[9]。根据启动子序列及拼接方式不同,可将PPAR-γ的mRNA分为PPAR-γ1、PPAR-γ2、PPAR-γ3 和 PPAR-γ4 四个亚型,其中PPAR-γ1是最主要的亚型,其广泛分布于脂肪组织、心脏、胰腺、胃肠道、肾脏和骨骼肌肉中;PPAR-γ2的分子结构较PPAR-γ1长30个氨基酸,主要表达于脂肪组织,其在机体新陈代谢、胰岛素增敏及炎性反应中发挥着多重效应;PPAR-γ3可在脂肪细胞、巨噬细胞和结肠上皮细胞中表达;PPAR-γ4的组织分布目前尚不清楚[8]。
2 PPAR-γ激动剂
既往研究结果显示,PPAR-γ广泛存在于SCLC与NSCLC患者的肿瘤组织中[10],但由于功能域的某种修饰机制或缺乏合适的配体,导致该受体在肺癌细胞中无活性。事实上已有研究表明,PPAR-γ在体细胞的功能丧失可能与结直肠癌转移相关[11]。一项针对147例原发性NSCLC肿瘤标本的免疫组化分析结果显示,PPAR-γ表达程度与肿瘤标本的组织学类型和病理学分级相关,其中分化良好的腺癌中PPAR-γ表达程度远高于低分化腺癌或鳞状细胞癌,这为研究PPAR-γ对肺癌的治疗价值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12]。
目前已明确的天然PPAR-γ配体包括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和二十烷类衍生物等,如15-脱氧前列腺素J2 (15d-PGJ2)和硝化亚油酸、硝化油酸等硝化脂肪酸;人工合成的PPAR-γ配体是以噻唑烷二酮类药物(TZD)为代表的合成化合物,如吡格列酮(pioglitazone)、罗格列酮(rosiglitazone)和曲格列酮(troglitazone)等,与天然PPAR-γ配体一样是一种强效PPAR-γ激动剂[9]。目前研究认为,PPAR-γ激动剂能通过直接与PPAR-γ配体结合、与热休克蛋白72结合后再与配体结合等多种途径激活PPAR-γ通路;但主流观点认为,PPAR-γ配体先通过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2的酪氨酸残基磷酸化和促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磷酸化而使PPAR-γ激活,再与RXR形成异二聚体(PPAR:RXR)并与靶基因启动子区的特异性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应答元件相结合,从而激活PPAR-γ的转录活性[13]。
3 PPAR-γ激动剂治疗肺癌的机制
研究表明,PPAR-γ通过直接作用于肿瘤细胞及间接作用于肿瘤细胞微环境而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微环境中的细胞成分,如周围的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脂肪细胞和血液及淋巴管系统等;此外,PPAR-γ还影响肿瘤微环境的非细胞成分,如生长因子、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等[5]。
3.1 对肿瘤细胞的调节作用
3.1.1 促分化作用 PPAR-γ是细胞分化过程中的重要调节因子,亦是代表人体抗肿瘤潜力的关键因素。细胞在癌变过程中常存在去分化或逃避终末分化等现象,因此癌细胞中与细胞分化相关的蛋白质标志物表达常被下调,如肌动蛋白结合蛋白(gelsolin)在包括肺癌在内的多种癌症中呈低表达,而诱导体外分化后其表达上调。研究表明,西格列酮(ciglitazone)和15d-PGJ2均可通过激活多个NSCLC细胞系中的PPAR-γ而增强肌动蛋白结合蛋白、Mad及p21表达,进而促进癌细胞分化,并抑制与肺祖细胞相关的谱系特异性标志物〔如黏蛋白1(MUC1)和表面活性剂蛋白A(SP-A)等〕表达;此外,西格列酮还能促进癌细胞外观形态改变,使细胞形态更接近于分化成熟的细胞[14]。另一项研究更加深入并再次证实西格列酮能诱导细胞分化:西格列酮可诱导NSCLC细胞株A549、NCI-H23的细胞分化及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2(ERK1/2)的持续激活[15]。此外还有研究表明,PPAR-γ激活后还能诱导腺癌细胞向具有极性的成熟分化表型转化[16],证明PPAR-γ激活剂在肺癌细胞中具有促分化作用。
3.1.2 抗增殖和促凋亡作用 PPAR-γ激活同样能阻碍细胞异常增殖及肿瘤生长,并促进肿瘤细胞凋亡。多种PPAR-γ激动剂在肺癌细胞系及小鼠肺癌模型中显示出抗肿瘤作用:曲格列酮通过刺激参与促凋亡的转录因子GADD153并以PPAR-γ依赖的方式抑制NSCLC细胞生长,进而诱导其凋亡[17];与此相似,西格列酮和15d-PGJ2可抑制细胞增殖,促进 NCI-H345、NCI-H2081 SCLC 细胞系及 NCI-H1838、NCI-H2106 NSCLC细胞系的细胞凋亡,其潜在机制可能与p21表达上调、cyclin D1表达下调有关[18];曲格列酮能通过介导、抑制磷酸肌醇3-激酶(PI3K)/Akt信号通路而抑制H1838、H1792、A549的NSCLC细胞增殖,刺激10号染色体(PTEN)表达缺失的磷酸酶和张力蛋白同源物,此外G0/G1期细胞的聚集和S期细胞数量的减少均能证明曲格列酮可通过引起G0/G1期细胞在多个NSCLC细胞系中的阻滞而发挥抗增殖作用[19]。LI等[15]研究表明,A549细胞周期阻滞是由于两个G1期调节因子cyclins D和cyclins E表达下调所致,虽然凋亡途径在A549细胞中未受影响,但曲格列酮介导的生长抑制是NCI-H23的NSCLC细胞caspases-3和caspases-9依赖性凋亡增加的结果;该研究组人员通过研究细胞凋亡过程的信号通路还发现,B细胞淋巴瘤2(Bcl-2)和B细胞淋巴瘤w(Bcl-w)表达下调,而ERK1/2和p38持续活化,应激激活蛋白激酶(SAPK)/c-jun N端激酶(JNK)表达下调[10]。非甾体类抗炎药作为另一类PPAR-γ配体,在NSCLC和SCLC细胞中也显示出抑制非锚定生长的作用,天然、人工合成的PPAR-γ配体及PPAR-γ过表达实验均得到了类似的结果[20]。有动物试验结果显示,曲格列酮、吡格列酮及舒林达克硫化物可明显抑制异种小鼠模型中A549的NSCLC细胞原发肿瘤生长[21];曲格列酮或吡格列酮的治疗能明显延缓自发性肺腺癌小鼠疾病进展,其机制可能为细胞增殖受抑制[22]。
因此,PPAR-γ激活后产生的促分化、抗增殖及促凋亡作用使PPAR-γ激动剂成为治疗肺癌潜力药物。
3.2 对肿瘤微环境的调节作用 新血管生成是癌细胞产生原发灶和转移灶的必要病理过程:新生血管可提供肿瘤生长所需要的氧气和营养,此外其还能帮助癌细胞进入循环通路以促进癌细胞转移。正常情况下,血管生成过程受到促血管生成因子和抗血管生成因子的双重作用,但在肿瘤发生过程中由于促血管生成因子表达上调而导致持续的异常血管形成。与正常血管不同,新生的肿瘤相关性血管具有高渗透性,可促进癌细胞局部扩散和远处转移[23]。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目前公认的强效促血管生成因子,此外还包括含有ELR基序的CXC趋化因子家族成员如白介素8(interleukin-8,IL-8)、上皮中性粒细胞活化蛋白78(epithelial neutrophilactivating protein 78,ENA-78)、生长调节癌基因α(Growthregulated oncogene-α,GRO-α)等,均被证实可通过增强形成新生血管的内皮细胞的趋化作用而促进血管生成[24]。研究表明,罗格列酮可抑制Lewis肺癌(LLC)细胞分泌VEGF,抑制血管生成,从而减轻肿瘤负担;而曲格列酮和吡格列酮可通过抑制A549细胞分泌ELR阳性CXC趋化因子和内皮细胞迁移而抑制异种癌细胞移植小鼠模型的新血管生成[25]。在肿瘤内皮细胞中高表达的PPAR-γ激活除了通过抑制促血管生成因子而间接影响血管生成外,还可以通过直接抑制内皮细胞生长而阻断血管生成[26]。此外,15d-PGJ2已被证实可诱导caspase依赖性内皮细胞凋亡,其抗血管生成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索[27]。
肿瘤微环境中以肌成纤维细胞为首的基质细胞是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MMP)和ECM蛋白的主要来源,其在肿瘤生长和转移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信号通路具有诱导成纤维细胞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的作用,而15d-PGJ2、曲格列酮、西格列酮和罗格列酮均被证实能抑制TGF-β刺激人原代肺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分化的过程[5,28]。此外,TGF-β诱导的纤维连接蛋白表达同样受PPAR-γ激动剂吡格列酮的抑制,这种对纤维连接蛋白表达的抑制作用已在PPAR-γBRL49653、15d-PGJ2或曲格列酮处理的H1838 NSCLC细胞中显示[29-30]。研究表明,包括纤维连接蛋白和Ⅰ型胶原在内的ECM成分异常增加会引起肿瘤微环境改变,最终导致癌症的发生、发展[31]。由此可见,PPAR-γ激动剂的确具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并对肿瘤微环境存在积极影响。
3.3 对肿瘤转移的影响 PPAR-γ不仅影响肺癌患者肿瘤原发灶形成及进展,近年越来越多证据表明,PPAR-γ激活后还具有抑制肿瘤转移的作用:一项异种肿瘤细胞移植小鼠模型研究发现,应用曲格列酮或吡格列酮后移植到小鼠背侧的A549癌株明显抑制[10];另一项研究表明,在接受PPAR-γ激动剂治疗的A549癌株SCID小鼠肺中检测到的转移灶较接受安慰剂治疗的小鼠体积更小、数量更少[32];一项原位肺癌大鼠模型研究发现,PPAR-γ过表达能通过削弱癌细胞的侵袭能力而阻碍一侧肺肿瘤细胞向对侧肺或纵隔转移,且进行PPAR-γ过表达的大鼠较对照组大鼠存活时间更长[33]。一项异种肿瘤细胞移植小鼠模型也获得类似的研究结果:研究人员将LLC细胞株移植在小鼠背部皮下区域,采用罗格列酮治疗后发现小鼠几乎没有发生肺内转移,从而保留了大部分肺的正常结构,而对照组小鼠肺组织中充满了转移的癌细胞;不仅如此,该研究者还观察到接受罗格列酮治疗的小鼠肺血管中存在LLC细胞,而在肺实质中未检测到LLC细胞,提示罗格列酮可能通过防止癌细胞从血液循环中溢出而发挥抑制肿瘤细胞转移的作用[34]。
MMP是ECM重塑和破坏的关键调节因子,部分MMP表达与肿瘤转移潜能及患者不良预后相关。既往有关MMP的实验证实,PPAR-γ激动剂对肿瘤转移具有明显抑制作用:罗格列酮可明显降低NCI-H157和H1299 NSCLC细胞活性和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表达[14],此外罗格列酮还可增强MMP组织抑制剂的活性,进而降低MMP蛋白水解活性[35],因此从抑制MMP角度也同样支持PPAR-γ激动剂具有抗肿瘤作用的观点。
原发肿瘤灶转移过程常伴随某些细胞黏附分子表达的改变,如E-cadherin能通过分泌细胞间附着物而将上皮细胞片连在一起,维持细胞稳定状态。研究表明,肿瘤组织常伴随E-cadherin表达下调,而与细胞迁移增强相关的黏附分子如N-cadherin表达上调,进而出现细胞间黏附的丧失和形态学改变、蛋白水解酶分泌及抗凋亡等现象,最终影响肿瘤细胞的扩散和转移[36]。
TGF-β信号通路能驱动并调节一组包括Snail、Slug、Twist和锌指结构(ZEB1/2)在内的转录因子,研究表明其在肺癌等恶性肿瘤中的表达会异常升高,且被证实与晚期肿瘤的转移潜能及预后不良相关[37]。TGF-β在A549细胞中能诱导上皮细胞-间充质转化(EMT),形态学上表现为从立方上皮逐渐演变至扁平的间充质并伴随细胞间附着丧失,通常还存在cadherin的表达改变,这预示肿瘤侵袭和转移能力增强[38]。曲格列酮和罗格列酮能阻断TGF-β诱导的EMT,阻止E-cadherin表达下调和N-cadherin等间充质细胞标志物表达上调。有研究人员尝试使用曲格列酮和罗格列酮逆转TGF-β诱导EMT的过程,发现曲格列酮和罗格列酮均通过抑制TGF-β信号的下游组分SMAD3的转录活性而具有维持细胞间黏附、抑制肿瘤细胞迁移和侵袭及减少MMP-2和MMP-9分泌等作用,这也进一步验证了PPAR-γ激动剂的抗肿瘤侵袭及转移效应[13]。
临床研究表明,癌症确诊时是否伴有局部浸润和远处转移是患者预后不良的主要预测因子且超过50%的肺癌患者在诊断时已有远处转移现象[1],而PPAR-γ激动剂不仅能抑制原发肿瘤的发展,还能抑制其浸润和转移,这使得其在肺癌治疗中具有广阔的的应用前景。
4 PPAR-γ激动剂治疗肺癌的临床证据
PPAR-γ激动剂治疗肺癌的潜在价值已被临床研究证实:国外一项选取87 678例男性糖尿病患者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发现,应用TZD治疗的11 289例患者后续被诊断为肺癌的概率下降了33%[39],但该研究人群较为特殊,其结论能否推广至一般人群仍有待进一步探索。此外,目前正在进行一项针对一般人群的临床试验(NCT00780234),应该对评估吡格列酮在预防肺癌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PPAR-γ激动剂不仅在单独使用时具有治疗肺癌的作用,其与传统化疗药物联合使用时还表现出良好的协同作用。有研究人员将PPAR-γ激动剂如罗格列酮、GW1929与铂类药物如顺铂、卡铂等联合应用,结果显示二者能协同抑制NSCLC细胞株生长[10],这一效应在异种肿瘤细胞移植肺癌模型和自发性结肠癌模型中也存在,且对试验动物并无明显毒性反应,分析其协同作用机制可能是PPAR-γ激活后降低了金属硫蛋白的表达,进而保护细胞免受铂类毒性[40]。另一项研究将PPAR-γ激动剂曲格列酮和吡格列酮联合顺铂和紫杉醇同样获得了相似的体内研究结果[41]。
除化疗药物外,近年针对肿瘤的特异性分子靶向治疗越来越受到临床医生的关注。研究表明,PPAR-γ激动剂与特异性分子靶向治疗制剂同样具有协同作用:罗格列酮能增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吉非替尼对A549细胞的抗增殖作用,曲格列酮和洛伐他汀联合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HMG-CoA)抑制剂对CL1-0肺腺癌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明显强于单独用药[19,42]。
5 小结
PPAR-γ作为抗癌药物新靶点具有良好前景,PPAR-γ激动剂不仅在单独使用时具有疗效,其与传统化疗药物联合使用时还表现出良好的协同作用。但PPAR-γ激动剂治疗肺癌的潜在价值是否能推广至一般人群仍有待进一步探索,未来仍需要研究人员继续设计多中心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以验证PPAR-γ激动剂治疗肺癌的效果及安全性。
本文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