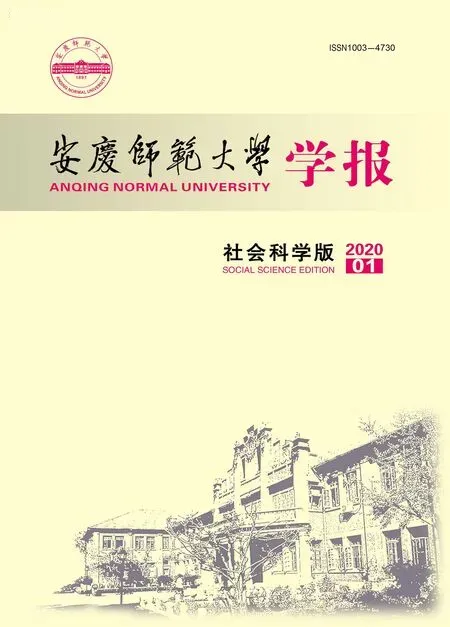藩篱中的自由:民国徽州宗族婚姻观的革新
——以徽州家谱族规家训为中心
2020-12-26汪锋华
汪锋华
(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457)
婚姻是男性和女性建立家庭关系的基础,也是繁衍和养育后代的重要前提。
费孝通说:“男女相约共同担负抚育他们所生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1]170此言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婚姻特征。作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婚姻研究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民国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在在民智大开的政治推动、经济冲击、思想浸染、文化熏陶下,其组织趋向解体,婚姻观念亦得到了一定的转变。而族规和家训则详细地记录了徽州家庭抑或家族的婚嫁观念、节烈观念等诸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宗族制度下的徽州士民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从基层社会发展的典型性来看,深刻剖析民国徽州宗族的婚姻观念,实际上亦可窥见中国基层社会的婚姻观念的某些态势。笔者全面检索并抄录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大学徽学中心等馆藏的徽州家谱中的族规家训①,拟对民国徽州基层社会的宗族的婚姻观念进行考察,旨在探讨其与中国社会的大变迁、徽州宗族小社会的变迁之间的关系,阐明大小社会的变迁对徽州宗族的婚姻观念的影响。
尽管徽州宗族的势力非常强大,“小家庭—大宗族”的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大徽州与小徽州的宗族文化圈延伸的区域亦甚为广泛,但民国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一方面拓展了宗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给宗族的发展带来新的元素,加速了徽州宗族组织的瓦解,徽州宗族的婚姻观念的革新随之产生,主要体现在对妇女的束缚与保护并存。
一、择偶标准的轻微变化
择偶标准是衡量一个时代的婚姻价值观念以及社会风尚习俗的重要尺度。择偶观念的转变,不仅反映了作为社会个体的青年男女对婚姻态度的变化,“还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价值观念的瓦解程度。因而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指标,对择偶观变迁的考察能够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家庭和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程度。”[2]69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择偶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就徽州地区而言,宗族的择偶标准较之晚清时期只发生了轻微变化。不同宗族对择偶的标准不尽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类情况:
(一)反对同宗婚、自由恋爱和早婚、童婚等现象,限制纳妾行为
徽州宗族一直认为“大婚合二姓之好”[3],而同宗、同姓配婚是乱伦行为,这是宗法观念的具体体现。对私自做主、自由恋爱的男女更是不能容忍。民国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甚至将族人的自由恋爱和同宗婚、同姓婚与奸淫行为同等对待:“人之有偶,不可乱也。……至若士耽固不可言,女耽尤不可说,见金夫而不有,乘垝垣而嘱迁。如此女流,亦不许进主。其娶宗妇及同姓者,并加黜革。”[4]该胡氏宗族将青年男女的此种自由恋爱行为和同宗婚、同姓婚一并视为奸淫行为严加惩处,足见其思想严重保守和落后的一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素有早婚的风俗,因为“徽人事商贾,毕娶则可有事于四方。”[5]287民国时期,徽商已经衰落,这一现象得到改变,许多宗族反对族人早婚。民国黟县《鹤山李氏宗谱·家典》说:“近世嫁娶多早,此中有关男女寿天及子孙体气之强弱,现律亦有早婚之禁。愿我族人各体此意,斟酌适中行之。”[6]该宗族从男女双方的身体考虑禁止早婚,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民国《歙县迁苏潘氏家谱·治家规约》说:“婚嫁切勿过早,男子以二十五岁为限,女子二十方许适人,不宜幼时定聘。”[7]这对男女的心智发展颇为有利。
徽州宗族还主张摒弃早婚的极度特殊现象——童婚、指腹为婚等陋习,这与要求男女双方家风清白的择偶标准是相一致的。民国祁门《河间凌氏宗谱·家训条款》就说:“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时,轻许为婚,亦有指腹为婚者。及其既长,或不肖无赖,或家贫饥馁,或丧服相仍,或从宦远方,遂至弃信负约、速狱致讼者,多矣。今后男女议婚诸弊,皆宜戒之,通族所宜知也。”[8]该宗族认为童婚和指腹为婚的孩童,长大后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这极易导致社会纠纷。禁止童婚与指腹为婚,对男女尤其是对女子的婚姻权的保障来说是一大进步。还有一些宗族对纳妾行为也作了限制,认为:“夫夫妇妇,家道以正,似续苟虚。亦得于一族中择贤择爱,非万不得已,慎勿广置姬妾。置嫡庶相竞自召勃溪。”[7]亦即夫妇双方都都遵守自己的道德规范,家道就正了。要求男子“择贤择爱”固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传统的择偶标准和道德窠臼,但客观上也对男女婚后的融洽创造了条件;限制纳妾是对妇女家庭权利和个人感情生活的尊重,对防止家庭纷争,维持家庭的稳定大有裨益。
(二)少数宗族允许赘婚和放松自由恋爱,不注重“门当户对”
民国以前,宗族一般禁止赘婚:一是防止财产继承权落到女子手里,二是防止乱宗,招赘来的女婿继嗣的姓氏传承也不符合宗法制的需要。民国期间,少数开明的宗族则允许赘婚,如民国《歙县迁苏潘氏家谱·治家规约》说:“故拟生女者,指本人无子者而言,准其招赘。惟所有权专属于女,女死无所出,由族中择一人为之。后若赘婿于此续他姓,即当令其归宗谱牒,列其名而于下注以“归宗”字样,此后一切关系断绝。”[7]该宗族认为赘婿立嗣的局限性在于财产落于他姓之手,主张以“归宗”弥补“乱宗”的不足,但毕竟认可了无子家庭可以赘婿,女子当家做主并享有继承权。
民国期间,在宗族组织尚未瓦解的徽州农村社会,男女的婚配仍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式婚姻占主导地位。但是少数宗族对自由恋爱和婚配并不予以禁止,甚至持宽纵态度。如民国歙县《府前方氏宗谱·祖训》只是警告青年男女“慎婚嫁以防怨偶”:“近来一般青年,醉心欧化自由结婚之习,尚已渐萌芽。但少年阅历未深,一时感于情欲不暇慎重,至婚后意见参差,酿成离异,毕生幸福牺牲殆尽,岂不悲哉?”[9]该宗族从青年男女自身利益出发,强调婚后家庭关系的和谐和幸福,重在“防”而不在“禁”,已经突破了封建传统礼教的界限。民国《歙县迁苏潘氏家谱·治家规约》只是劝诫族人道:“若男女以相识故而论婚,亦必慎终于始,并得父母或其他分,应主家庭有变如虞舜。主婚至尊长之同意事,乃克谐东,使遇顽嚣,则不告而娶,君子方许其之行权耳。”[7]要求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要对婚姻谨慎对待,善始善终,并征得父母和尊长的同意。在这里,门当户对的观念已不复存在,如同黄山徽州区村民刘子石老人在回忆他父亲(桐迁徽刘氏宗族)时说,其父在民国六年相亲时遇到一户陈氏姑娘,“(她的)父亲是歙县西门这一带著名的牛医师,雄村曹振镛跟他是亲戚,家中富有,按理说是不门当户对的。可我外公当年不重门户,是重‘小倌’。”[10]可见“门当户对”在民国徽州少数宗族的婚姻观念中已不占主导地位。
二、对婚后妇女的家庭伦理观念的改进
虽然民国期间徽州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无明显提高。但随着宗族社会外部的新思潮的不断云涌,不少徽州宗族也提出了一些尊重妇女权利、改善妇女处境的措施和规定。从宗族族规家训来看,大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家庭内部,对妇女的待遇趋向公平。民国绩溪仁里《鱼川耿氏宗谱》卷五《家族规则·禁戒事项》说:“……冀其孳生,复凌而虐之。干天和绝人道,莫此为甚!嗣后族中……有凌媳者,即鸣族处理。毋令乖戾之气隐伏于民间也。”“嗣后,为家长者,务须一视同仁,贤者亲之,不能者怜之,庶和气致祥,家道永昌矣。”[11]耿氏宗族严禁以违反传统伦理为由虐待妇女的行为,否则要发动宗族的力量给予处置。认为男方尊长对儿子、儿媳厚薄不公是导致家庭分裂和破产的重要原因;明确警戒公婆要将儿媳要与儿子同等对待,不可偏倚,这是家族永昌之道。
二是在宗族范围内,严格禁止违背妇女意志的行为发生。徽州宗族对买卖妇女、变相卖妻或逼妇女改嫁等行为深恶痛绝,给予与奸淫同等的处罚。如民国绩溪《余川越国汪氏族谱·祠规》规定:“凡派下子孙,有无故嫁妻者,……有卖其女或兄弟、叔伯、子侄之女与人为媳、妻或为嫡妇者,……有为亲长而强逼嫡妇改嫁,有非亲长而主遣嫡妇改嫁者,革出,毋许入祠。”[12]民国《绩溪城南方氏宗谱·祠谱》卷二《祠规》规定:“派下男妇,如有恃逆不孝、凌辱尊长及奸淫乱伦,并卖妻女与人为妻者,该亲房即行襄明斯文、族长,如果确实,即行革出,生死不许入祠。”[13]这些宗族都对买卖妇女、逼妻女改嫁者进行了严厉惩处。在徽州宗族社会,每个人都从属于宗族组织,生前受到宗族嘉奖或旌表,死后入祠堂上家谱是族人人生最终的价值目标。革出宗族、生死不许入祠是对族人最严厉的处罚。
三是对传统与新型夫妻关系之间作了适当调和。民国期间,由于中国城市地区新式婚恋观和家庭伦理观的出现的深刻影响,徽州宗族为了巩固家庭结构和重建伦理观念,对传统的夫妻伦理关系进行了一定调适和转换。如民国《重印新安大阜吕氏宗谱》卷五《桑园祭祀规》强调:“自夫妇而有父子、兄弟,……凡事公处,毋得以强欺弱,恃富吞贫”[14]主张家庭成员内部要保持团结和谐,夫妻之间不宜有强弱、贫富之分,这在传统伦理观念的基础上义进行了一定的调适,使夫妻关系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对丈夫纳妾行为,有些宗族也给予了限制和劝诫。民国《古黟环山余氏宗谱·家规》即规定:“凡子弟有妻子者,不得更置侧室,以乱上下之分。违者,议罚。”[15]还有些宗族提倡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因为“夫妇有恩”[4]。民国祁门《河间凌氏宗谱》说:“婚姻之礼,以仁男女;……本爱敬之心以施之,则伦理之间愈无亏矣。”[8]认为夫妇之间应以仁爱之心互相尊敬,就是最圆满的伦理。民国十九年是休宁《孙氏宗谱·先正格言二十条》引用名儒之言说:“方正学云:‘无故不出妻也’……范竹溪云:‘以爱妻子心事亲,则孝’。”[16]该孙氏宗族将丈夫爱妻与儿子孝敬父母两者相提并论,要求对休妻一事严谨对待,这是对妇女更大的善待。
三、妇女的节烈观趋向宽纵
民国时期,尽管传统妇女节烈观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和冲击,但大多数徽州宗族仍然固守着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对妇女的贞操观以继承为主,革新为辅。
对于不愿为夫守节的妇女,宗族一般给予两种处罚措施:要么剥夺改嫁妇女本人的进主权,要么剥夺其与改嫁之夫所生之子的继嗣权。如民国歙县《府前方氏宗谱》规定:“若乞养他姓之儿,或再醮妇前夫之子,在例皆不得承嗣。”“妇人之改适者,例不准入祠。即其子孙有爱孝之忱,但体母出与庙绝之义,不可私反之礼。如有故违,一经查出,除将该主公毁外,即将其子孙责革。”[9]但从宗族的族规家训来看,徽州宗族对妇女守节方面的惩罚措施要比奖励措施少得多,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从守节妇女人数来看,徽州妇女自幼受到儒学礼教和传统道德伦理的熏陶,绝大多数都养成了为夫守节的风习。守节人数远比不守节人数多,所以与之相适应的宗族规训也就出现数量上的同步反差。第二,从徽州宗族对妇女的人身控制和思想箝制程度来看,民国期间,由于宗族外部社会的政治变革和思想革新,传统的儒教伦理秩序受到冲击和挑战。宗族在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同时,对妇女节烈的观念亦有所变化,放松了对妇女群体的控制。
我们从一些宗族对待寡妇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民国期间妇女的节烈行为基本上属于个人自愿,当然这种自愿节烈行为是建立在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教条下的无奈和屈服。而对于寡妇是否守节,这些宗族给予了较为宽纵的说法。民国婺源《济阳江氏统宗谱》认为:“栢舟矢志,自古为难。不幸而有少寡,须窥其志向如何。有志则守,无志则嫁,切不可苦留,贻门户之羞。”[17]该宗族主张是否守节,应该有妇女自主选择,勉强妇女守节会让门户蒙羞。民国《歙县迁苏潘氏家谱·治家规约》从国家立法出发,对妇女守节观念提出了一定批判:“经年守寡,恒情所难。按之国法,本未有再醮之禁。譬彼男子,何不蒙继室之嫌?故夫死无赀乏嗣,意欲嫁人,宜援范式庄规,由族中善为资遣。”[7]认为既然国法对寡妇改嫁未作规定,鳏夫可以再娶,寡妇便可以再嫁;对“无赀乏嗣”打算改嫁的妇女,宗族应按照正常规矩出钱让其改嫁。但是该宗族又认为:“无财产、无子女而自愿守节者,应赡之终身,敬礼有加,无俾失所。”[7]足见宗族对妇女节烈观革新的不彻底性和保守性。但至少表明民国时期的徽州妇女,在决定是否替夫守节的问题上,有一定的自主权。
对妇女节烈观的另一个挑战即离婚。如果说妇女不守节转而改嫁是反叛封建礼教、追求个人幸福的行为,那么离婚则是对现实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直接的强烈反击。虽然大多数宗族仍强调节烈的重要性,但时代发展的潮流不可遏抑,少数宗族组织在潜移默化中难免受到新式家庭观念的影响。据生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徽州刘子石老人在讲述他的第一段离异的婚姻时告诉我们:“风俗的改变,始自民国元年后出生的那批人,到他们青少年时,正赶上徐志摩的性自由宣传,裸体画的展览。那些穿旗袍露大腿的‘月份牌’画被富贵人家,甚至是商家为‘赶时髦而悬挂’,使不少男女青少年为性爱而狂热,理性的道德爱情观渐消失!我的前妻也深受其害,当我离家六百多里去任教时,半年后再回来他就另有新欢了。奈何!”[10]民国后期,连宗族子弟都有面临这样的婚姻危机的时候,可见新的妇女贞节观和离婚观正在滋生,传统的妇女节烈观念逐渐走向了不可逆转的颓势。
四、宗族婚姻观念革新的主要特征
(一)保守性
由于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经济基础、社会因素等诸多原因,当全国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大城市的宗族改革风起云涌时,传统徽州社会的宗族组织相对稳定。因此徽州宗族思想观念的变迁具有相对的保守性,直到民国期间,徽州宗族在许多方面仍然恪守着传统儒家伦理和封建礼教思想,这从族谱中的族规家训中不难看出,如对民国时期徽州宗族的职业观的革新,徐国利就曾指出:“在这样一个较开放的社会,不少宗族的族规家训在职业观方面却是守旧多于革新,传统职业观在多数宗族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8]
民国时期徽州宗族的婚姻观念也显得较为保守。许多宗族的族规家训仍沿用古代或前代的族规家训,如民国十八年(1929年)纂修的婺源《长溪余氏宗谱》中的《祖训》、《若胜公家训四字格言文集》、《若胜公常话就近指示人家吉征》、《生养丧祭说》等均沿用道光年间的族规家训内容,上述内容的落款为:“道光二十八年岁次,戊申年冬月吉旦,清华胡柳塘撰于训蒙书社”。[19]民国《曹氏宗谱》卷一《家训·旺川家训后十则》沿用的是清代嘉庆年间的《绩溪县旺川曹氏宗族家训》;民国《鱼川耿氏宗谱》卷五《祖训》全是引用古代名儒的言论汇总,包括王朗川《言行汇纂》、(清)史搢臣《愿体集》、(明)张杨园《训子语》、(明)陆桴亭《思辨录》、(明末清初)朱柏庐《劝言》、(明)王士晋《宗规》、(明)陆桴亭《论小学》等;民国《古黟环山余氏宗谱》卷二十一《艺文》引用的是明代成化年间的《黟县环山余氏宗族家规序》;民国《重印新安大阜吕氏宗谱》卷五《桑园祭祀规》沿用明代万历年间的休宁县的《桑园吕氏宗族祀规》。再者,从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地方志来看,光绪《婺源县志》卷三《风俗》的内容与民国《婺源县志》卷四《风俗》[20]的内容几乎相同。类似文献的传承比比皆是,窥斑见豹,晚清至民国时期徽州宗族婚姻观念的革新在整体上显得较为保守和微弱。
(二)不平衡性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徽州宗族组织也趋向衰落。然而中国各个地区的宗族制度的蜕变和衰落的状况和进程不尽相同,从总体上看,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徽州宗族观念与全国其他地区宗族观念存在不平衡性。民国时期宗族思想观念的变革因地域差异而呈现出革新和保守并存,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徽州社会较为偏僻,生活方式相对封闭、资源亦比较匮乏。这在徽州历代地方志中均有记载,如道光《徽州府志》记载:“休宁僻在万山中,其人始愿而朴(王世贞《重修文学记》)”“黟僻处郡西南,于郡诸邑号为瘠,俗最朴。(金声《重修儒学碑》)”“婺食鹾于浙,然以贫无盐商。凡婺之商引,皆休商行掣告销。虽休兼婺利,而盐止于休。婺民则挑负诸土物,逾岭零星贸易,价溢而劳瘁倍之。故穷僻村氓多食淡者。”[21]民国《歙县志》中也说:“道路皆以石成之难,穷乡僻壤,入山小径,靡不石也。”[22]为了谋生,大量无法通过读书为仕的族人被迫外出经商。但发迹的徽商并不将获得的巨额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或发展传统工商业,而是积极“亢宗”,回家乡从事捐助建祠修谱、兴办书院、资助医疗卫生、抚恤孤寡等公共慈善事业,从而巩固了徽州“大宗族—小家庭”的社会结构。徽州宗族社会的族众包括全部农民群体,宗族组织既在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公益慈善等方面全面实施乡村自治,又管理着乡村社会的公共安全、司法实践、催粮纳税等事务。宗族组织形态呈现出“县—宗族—小家庭”的特征。“徽州形态是家国同构体从组织上(宗族)到思想上(理学)最为完备的典型,也是中国专制制度对农村控制最为严密的类型。”[23]215正因为徽州宗族组织结构的相对稳固性,其社会转型中的衰落才显得较为缓慢和滞后,从而决定了徽州宗族婚恋观念革新与其他地区宗族的不平衡性。
其二,徽州宗族内部不同宗族婚姻观念间存在差异。民国时期,徽州宗族趋向衰微,最终成为强弩之末。但是不同宗族的衰落速度和婚姻观念革新程度是不同的,典型的如休宁首村查氏宗族,以下是该村查国英老人在接受访谈时回忆民国时期的本宗族、本家庭的生活概况:
我老家首村和附近的一些村庄不一样,附近的一些村庄均是聚族而居的,而且宗必有祠,族必有谱,……首村却是一个“百家姓”,全村近百户人家,同姓的很少。就拿我住的上街来说,从第一户姓叶到最后一户姓姚,连续二十几户,几乎没有同姓的。
我的母亲是月潭人氏,姓朱,名娴,小脚,虽没多大文化,但能打会算,如每天早上收买柴火时,她一连秤七、八担柴,记在脑子里,回来再算账,姓名、数量一点不错,是我父亲做生意的得力助手,也很得里人的称赞。“七、七”事变以后,我家生意做不下去了,家境日渐衰落。这时,我母亲已经亡故,我只有七岁。为了生活,我父亲又娶了农家女子严氏做我的继母,改行种田务农为生,直至解放和解放以后[24]。
可见,民国期间休宁首村的查氏宗族与大多数宗族的不同之处是:散族而居,宗族组织相对分散,小家庭的特征较为明显;姓氏繁杂,被称为“百姓村”,亦使血缘为纽带的宗族聚合体显得松散;该宗族在民国初期的妇女婚姻观念虽较为保守,但是妇女不仅承担家庭义务,还参与到近代的商业经营中来,其活动空间超越晚清时代和民国时期的其他许多宗族。这些都是休宁首村“百家姓”宗族组织的解散和婚姻观念的革新要早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多数徽州宗族的重要原因。
徽州地区不同宗族之间的婚姻观念的变迁差异还体现在同一时期所修纂的地方志中。如道光《徽州府志》便记载了清代徽州地区不同一府六县不同宗族的风土人情、社会风习和婚姻观念的差异。正如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风土》所云:
邑俗四乡不同,东接绩溪,习尚简朴,类能力田服贾以欲其生。南分水陆二路,陆南即古邑东,民质重厚,耐劳苦、善积聚。妇女尤勤勉,节啬不事修饰。往往夫商于外,所入甚微,数口之家,端资内助,无冻馁之虞……北有黄山之富、蒻岭之险,……多明敏俶傥之士。习俗亦视诸乡为较侈,而尚气节、羞不义,则四境维均也。
……
婚礼俗不亲迎,惟新妇三日庙见,拜谒舅姑诸亲,属以次及。乃飨新妇,酬酢于堂,始服妇职[22]。
五、结 语
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一文中说:“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是和传统社会的性质相配合的,而且互相发生作用的。……在一个已经工业化的西洋的旁边,绝没有保持匮乏经济在东方的可能。适应于匮乏经济的一套生活方式,维持这套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是不能再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新的处境里了。”[1]347他认为,传统社会价值观念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性质决定的,其主要弊端在于只注重人伦关系的缔结而不注重经济发展——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在被西方工业化社会侵略后,中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价值体系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也就是说,传统价值观念必然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而变迁。然而,在新旧势力和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冲突的社会形势下,如果缺乏家庭、宗族、家族之外的力量进行强制性干预和推动,徽州宗族思想观念的变革势必是一个更加漫长、艰难的过程,而这个强大的推动力量便是国家政府。尽管如上文所述,在婚姻观念上,极少数开明的宗族也提出限制纳妾、禁止缠足和一夫多妻制,赋予妇女一定的婚姻自主权等观念,但由于诸如维护妇女婚姻自由权利及其它社会权利与传统宗族制度的思想体系严重对立、格格不入,这些新时代的文明新风,如果单纯依赖宗族自身的自我修正和改造来进行变革,无疑是步履维艰而且无法达到根本目的。事实证明少数开明宗族的思想观念在短期内很难在宗族社会内部传播和推广,绝大多数宗族以保守为主。
其根本原因是徽州宗族的本质属性是封建宗法组织,它的组织结构和社会职能决定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体系,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在地域上徽州宗族偏安皖南山区,生活方式相对封闭,宗族对社会改革的信息传播、接受的较为迟缓。民国时期国内战乱频繁,尤其是抗日战争消耗了政府的主要精力。无论是国民政府推行的的宪政改革、新生活运动,新桂系在安徽的文教改革,还是中共政权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对徽州宗族的势力都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改造。囿于抗战生活的牵制,政府需要社会各方势力的平衡和战时的稳定,因而徽州宗族势力一直维系到建国以后。在晚清至民国这一漫长的社会转型期,徽州宗族组织一直趋向缓慢衰落、逐渐瓦解状态,其思想观念的变迁也极为缓慢、保守。要想促进徽州宗族思想观念的革新,只有依靠国家政权强大的推动力来加以强制执行;而要彻底转变宗族的思想观念,则只有推翻整个宗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