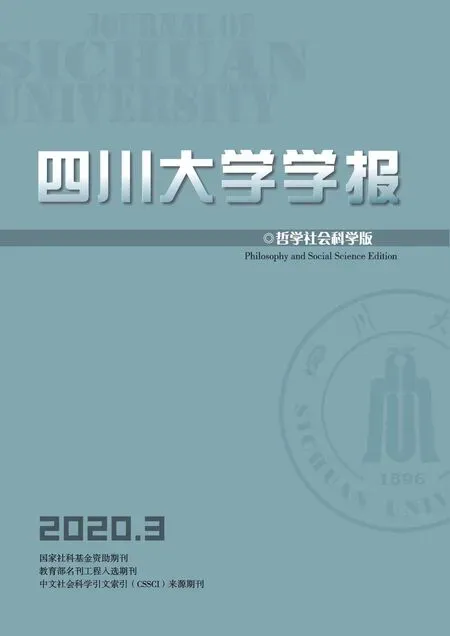疾病文化与文学表征
——以欧洲中世纪鼠疫为例
2020-12-26王晓路
王晓路
今天人们如果重新阅读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英国作家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1)这些作品国内多有译介,本文参用薄伽丘:《十日谈》,王永年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丹尼尔·笛福:《瘟疫年纪事》,许志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阿尔贝·加缪:《鼠疫》,刘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杨玲译,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以及包括莎士比亚剧作在内的世界名著,就会发现,文学其实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历史进程中的那些重大疾病或瘟疫多有描写,同时也会意识到,疾病对人类社会和群体心灵的影响实在不容小觑。人类机体是一个需要不断适应自然条件的生命形式,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各个区域的群体都必须不断地适应并利用周边条件,并由此累积为族群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样式。民俗文化的基础其实与此有关。然而,随着人类生活以现代都市为主要展开方式,加之技术的普及和交通的便捷,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活动范围业已改变,一些共同问题出现的频率也不断上升。其中,不可避免的疾病,尤其是流行性疾病及其对社会文化形成的巨大影响,就是全球各个区域的群体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人们在面对新的问题之时,总会通过对历史中的类似事件加以回顾,看到问题的连接点。欧洲中世纪发生的鼠疫或黑死病瘟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巨大的灾难,它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一场瘟疫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社会,而且还形成了持久的集体记忆。人们至今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文学,追溯这场瘟疫并通过对其研究和表征,考察人对自然、社会以及生活方式的认知。概言之,欧洲中世纪鼠疫成为考察疾病文化与文学表征的典型样本。
一、疾病及医学文化
在人类生存和发展进程中,各种疾病发生、相应的治疗手段及其防治措施也同时构成与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相并行的一条不可忽略的轨迹。疾病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更因其巨大的影响,而与人类社会交织成某种疾病文化的复杂现象。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些基本概念,诸如公共卫生、人均寿命以及饮用水和食品安全等,实际上都是在防御大规模疾病的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社会性共识。所以,疾病文化的重要性关乎当代发展模式、社会治理、群体意识以及国际合作等各种方面。有鉴于此,人们总是以种种方式对历史上发生的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或瘟疫进行回溯,其中不仅有医学史的专门论述,而且在人文社科研究和文学艺术中也有持续的成果呈现。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鼠疫或黑死病就是一个典型的疾病性事件。直至今日,学界还在对中世纪以来的大型疾病史进行不同角度的挖掘,尤其关注大型瘟疫对社会基本结构和文化形态的影响,例如影响很大的“历史重大灾难”(Great Historic Disasters)系列丛书中所收关于欧洲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的研讨著作。(2)Great Historic Disasters' series published by Chelsea House Publications, New York, 2008. 其中包括:Joseph Byrne, The Black Death; Paul Kupperberg, The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19.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重要的通史和文化史论著也将疾病列为重要的议题之一。例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三卷本的名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从第一卷开始,就对“流行病”“鼠疫”“疾病的周期性历史”进行专门分述。(3)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4-88页。“企鹅欧洲史”系列丛书中也有著作对历史阶段中所发生过的重大疾病作出专项描述。(4)参见该丛书中译本(目前共出7册)第3册,威廉·乔丹:《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傅翀、吴昕欣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9章“饥荒与瘟疫”。另外还有学者专门从医学角度讨论疾病及医学文化,如著名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的《疾病的文化史》《人与医学:西医文化史》(5)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疾病的文化史》,秦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亨利·E. 西格里斯特:《人与医学:西医文化史》,朱晓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等。这些将大规模疾病纳入文化史考察的研究方式和成果起到了双重的作用:史实应当包括那些发生过的瘟疫及其深刻影响,同时对这些史实的重新提及也在于提醒人们需要持续对其加以多角度的认知。这是因为疾病及其引发的认知过程正是人类对自身认知不断加深的阶段,“历史教我们懂得,医学专科化是一种当需求发生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基本现象”(6)亨利·E. 西格里斯特:《人与医学:西医文化史》,第263页。。显然,不断从多学科出发去探讨疾病及医学文化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人们需要在对疾病事件进行深入了解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生命文化意识并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从疾病史的角度来看,鼠疫不仅出现得早,而且因为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大以及后果特别严重等原因,所以在传染疾病序列中始终被列为高等级。仅全球性的鼠疫就有好几次,“从历史上看,一共有三次全球性鼠疫:6世纪肆虐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鼠疫(the Plague of Justinian), 14世纪的黑死病以及1894—1903年从香港爆发并导致东亚和南亚死亡百万的鼠疫”。(7)Ernest B. Gilman, Plague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9.而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中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鼠疫,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描述,“14世纪鼠疫大流行,被称为黑死病,欧洲死亡2500万人,占人口1/4;1664—1665年伦敦鼠疫大流行,46万人口中死亡7万”,(8)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7,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56页。“法国编年史家傅华萨说:约有1/3的欧洲人死于这次流行病”。(9)《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3,第774页。对于这场瘟疫的死亡人数,由于没有确切的记录,因此学界大多是根据文献和模式进行的推论。例如研究黑死病的学者斯拉维克就推论认为,“在1340年代末至1350年间,黑死病也横扫了西亚和北非。欧洲总人口的33%至60%,大致2500万至450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死亡”,因此这场灾难也被称为“大死亡”(the Great Mortality)。(10)Louise Chipley Slavicek, The Black Death, New York: Chelsea House, 2008, p.7.相对于当时的总人口,死亡人数是相当惨烈的。但人类对这一令人恐怖的疾病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人们对这场大瘟疫在早期并没有统一的命名,而主要是用一些含义接近的拉丁文进行说明,“当时黑死病的名称有‘sine contagio’‘sine aliquali contagione’‘absque signo pestico’等等”。(11)Samuel K. Cohn, Jr., Cultures of Plague: Medical Thinking at the End of Renaiss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4.实际上,“Black Death”(黑死病)是19世纪才开始使用的术语。(12)朱迪斯·M. 本内特、C. 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杨宁、李韵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58页。
欧洲中世纪的鼠疫主要是由老鼠传播的。当时欧洲一些商业城市之间的货物往来也带了老鼠。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学者乔丹就鼠疫的传播途径专门指出,“这种疫病原本是亚洲特有的,却在中世纪时期两度通过船上老鼠的跳蚤传播到了亚欧大陆的西部地区和北非地区。……1347年将瘟疫带到意大利的似乎是一艘来自黑海的船。瘟疫从意大利沿商路扩散到法国,又在1348年传到了英格兰。瘟疫也蔓延到了西班牙”。(13)威廉·乔丹:《中世纪盛期的欧洲》,第354-355页。值得注意的是,乔丹对鼠疫何以是亚洲特有的并没有详细地说明。其实,啮齿类鼠科动物种类繁多,其中“小家鼠常在人类的建筑物中寻求食物及居住,已由人类从欧亚大陆带到世界上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14)《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8,第589页。实际上,鼠疫病毒并不是亚洲特有的。但由于这一场大规模爆发的鼠疫致使欧洲人口大量死亡,许多城镇如同废墟一般,再加上大片的田野荒芜,所以,完全可以想象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和群情不安的景象。人们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慌和恐惧在文学和美术中均有令人震撼的呈现。例如老彼得·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于1562年创作的名画《死亡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就是通过骷髅过境的恐怖场景,非常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可怕情境以及人们内心的恐惧,这幅专门展现欧洲中世纪那场极其惨烈的瘟疫的画作影响深远。20世纪美国重要的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曾用《对尸体的两种看法》为题对此画加以了解读:
布鲁盖尔那幅烽烟和屠杀的/全景画里/只有两人盲目不见那/腐肉大军:/……
小说家德里罗(Don DeLillo)也用《布鲁盖尔的死亡的胜利》为题对此画进行了文字的形象转述:
死人出来带活人了。穿着寿衣的死人,成群骑在马上的死人,奏着手摇琴的骷髅……
他详视那装满头骨的囚车。他站在走道上,注视那个被狗群追赶的男人。他注视那只瘦骨嶙峋的狗啃啮死女人怀中的婴儿。那些全是消瘦、营养不良的狗,战争狗、地狱狗、坟场狗,浑身是寄生虫、狗瘤、狗癌。(15)以上参见翁贝托·艾柯:《丑的历史》,彭淮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疾病更是引发了应急性常识的书写以及文学艺术的创作。当时由于需要对疾病的症状和可能有效的防护方式进行及时的介绍和传播,于是各种类型的书写材料出现了。这些有关的书写在后期被统称为“黑死病书写”(Plague writing)或“鼠疫手册”(plague tract);(16)Cohn, Jr., Cultures of Plague, p.1.同时也因由书写的内容、形式以及表达方式而形成“黑死病话语”(plague discourse)(17)Gilman, Plague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3.、“黑死病文本”(the plague texts)(18)Patrick Reilly, Bills of Mortality: Disease and Destiny in Plague Literature from Early Modern to Postmodern Times,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15, p.1.以及一些相关的亚文类。由此,一些有关的“医学文类”(medical genre)和“医学建议文献”(health advice literature)等也先后出现。人们亟需了解疾病以及获取可能的治疗方式是这类书写获得阅读的最主要的原因。不难想象,在这一类书写中,有很多是作者关于瘟疫的猜想和发挥,带有明显的文学意味和书写手法。但是文学所特有的通过个体感受所呈现的景况却更能够对读者形成更为直接的触动。由于人们对这场巨大的灾难实在无法解释,因此神学要素在此类书写中比较常见。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形式的科恩就专门指出,“其中有基于神学的哲学观,旨在解释人类历史和疾病的‘深层缘由’(superior causes),也有直接列举防护或治疗黑死病例的”;而且这一类书写“直至16世纪才接近尾声。直至16和17世纪,医学文类(medical genre)一直保持了类似的方式”。因此可以说,是对于瘟疫的记录、描写、指南以及感叹等等书写方式“构成了15世纪欧洲第一次流行文学的样式(the first form of popular literature)”。(19)以上参见Cohn, Jr., Cultures of Plague, pp.1-3.
二、瘟疫与文学书写
欧洲中世纪鼠疫或黑死病带给人类社会的创伤记忆,使文学书写开始拥有了新的主题和表征对象。在欧洲的名作家中,意大利薄伽丘是其中最早对这场瘟疫进行集中描述的作家之一。为了有效地记录这场灾难,薄伽丘花了五年时间创作了名著《十日谈》(1348—1353)。在此书第一卷的导言中,作者就对当时的景象,尤其是对亲情和街坊邻里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述:
事实是一个市民回避着另一个市民,几乎没有一个人关心自己的邻人。……这场灾难把恐惧深深地扎进了男男女女的心中,以至于哥哥抛弃了弟弟,伯父抛弃了侄子,姐妹抛弃了弟兄,最常见的就是妻子抛弃了丈夫,还有——更糟糕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不再照顾和关心他们的孩子,就像这些孩子不是自己所生的一样。(20)玛格丽特·L. 金:《欧洲文艺复兴》,李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3页。
《十日谈》特别之处是作家通过对十个年轻人为躲避瘟疫进入一个别墅的生活的描述,进行了最为生动的疾病文学的创作,这也是以文学手法最早呈现古代因传染性疾病进行的隔离生活。作家想象性地编织了瘟疫时期的特有情节:这十个年轻人为了打磨时光,在别墅里每天每个人讲一个故事,于是构成100个相对完整的故事,而故事内容则涉及当时欧洲各个方面,《十日谈》由此而来。重要的是,薄伽丘不仅在许多故事中借瘟疫之事嘲讽教会的黑暗、罪恶(如第一天第二个故事),抨击僧侣的奸诈和伪善(如第六天第十个故事)等;同时,由于他在描写人物和叙述故事时,注重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使这部作品“塑造了不同阶级、不同职业、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典型”。(21)冯至等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I,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第172页。当然这些故事和人物都十分巧妙地围绕一个重要命题展开,亦即人文精神的张扬。由于此书成为世界名著,被翻译成了诸多语言,并进入了世界主要大学的高等教育文学史和文学选读之中,因此形成了持续的影响。人们通过阅读《十日谈》,不仅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欧洲社会文化,而且还对疾病、社会状况以及人的心理有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这场巨大灾难也使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认识获得了提升,而这对于文艺复兴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文艺复兴这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运动始终围绕人文主义的精神展开,并且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人文主义治学”(studiahumanitatis),(22)查尔斯·G. 纳尔特:《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文化》,黄毅翔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1页。就都与黑死病所带来的大面积创伤不无关联。乔丹通过对中世纪欧洲历史及鼠疫的研究,指出:“周期性出现的瘟疫确实敲响了中世纪欧洲文明的丧钟。黑死病肆虐之后的欧洲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欧洲、近代早期欧洲,也有按地域被称为都铎王朝时代的,无论如何,那时的欧洲社会都已经和黑死病之前的完全不同了。”(23)威廉·乔丹:《中世纪盛期的欧洲》,第356-357页。疾病文化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黑死病虽然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但相关的文学书写和研究一直持续至今。而且,这个命名本身就与文学直接相关。“黑死病这个术语是后来才出现的。它是在中世纪的一首被误译的拉丁诗歌中出现的。作者康文纽斯(Simon de Covinus)是一位弗莱芒天文学家。他将这个流行病命名为 ‘mors atra’,后来这首诗歌经翻译成为‘黑死病’。Atra这个拉丁词汇就带有‘可怕、黑色’的双重含义”。这场大瘟疫的惨烈景象更是使一些知识人士深感痛苦,很多学者采用当时通行的拉丁诗歌形式予以陈述和抒发,希望以此贴近不可知的自然世界。如“中世纪伟大的诗人佩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在1348年观察到了黑死病在意大利家乡的灾难。同年,他创造了一首短诗《给予他本人》(Ad Se Ipsum;To Himself)。诗人写道,‘生命不过是一种长期的折磨’”。(24)以上参见Slavicek, The Black Death, pp.9, 10.从中世纪鼠疫爆发开始,有关的书写,尤其是当时医学方面的书写,也有一个从拉丁文逐渐转化为各地俗语的过程,“黑死病书写语言从主要的拉丁文(受到既往世纪中经典医学文献的复兴的影响)转移到普遍采用俗语的表达”。(25)Cohn, Jr., Cultures of Plague, p.5.俗语的使用,除去当时各地之间减少了交往的史实之外,还出于更加有效传播的动机。其次,拉丁诗歌在欧洲一直拥有并保持了特定的神秘性和实用性,“有一种观点认为,诗歌包含且必须包含神秘的智慧,以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用知识”;而且诗歌本身就被赋予了神学阐释功能并拥有某种神圣传统,“‘poeta theologus’(诗人神学家)最初是由古希腊人提出的,后经罗马人和基督教父流传到中世纪,可以完全适应基督教各式各样的再阐释”。(26)恩斯特·R. 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林振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1、288页。大瘟疫不断带来新的书写以及阅读兴趣,各种形式汇集构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形式,“1575—1978年间的黑死病作者以新的健康记录,创造出了新的黑死病书写的形式,编织了黑死病喜剧、黑死病叙事、由死亡记录所带来的个人创伤及一些黑死病的刊物等,这些在后来从笛福到加缪等作家那里发展出了疾病的文学经典”。(27)Cohn, Jr., Cultures of Plague, p.8.可以说,中世纪鼠疫爆发以来,瘟疫的阴影一直徘徊在欧洲,由此形成的有关黑死病的文学书写也延续下来。
1664—1666年,鼠疫再次在英国等地爆发,包括伦敦在内的许多大城市都没能幸免。在伦敦全市总计46万人中,约有7万多人死亡。1666年9月2日伦敦发生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大火,直到5日才熄灭。这场大火虽然彻底摧毁了这座历史名城,但同时也使瘟疫得到了遏制。(28)《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5,第453-454页。瘟疫和大火成为英国人的历史记忆和文学想象的源泉。因写作《鲁滨逊漂流记》而闻名于世的小说家笛福,于1722年创作了《瘟疫年纪事》,这是一部以文学形式表述黑死病的最为典型的作品。作者采取了半虚构的方式,按照线性时间将17世纪中叶伦敦大瘟疫的具体地点与景象相结合,异常细致入微地逐一呈现,充分发挥了文学的图像功能和令人难以回避的历史意识感。正如杨周翰先生所分析的,作者“把这场鼠疫的发生、传播,它所引起的恐怖和人心惶惶,以及死亡数字、逃疫的景况写得如身临其境。当时法国马赛鼠疫流行,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笛福的作品满足了市民对鼠疫的好奇心”。(29)《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Ⅰ,第258页。在此书的导言部分,辛西亚·沃尔的描述完全是一种历史场景的再现:
笛福为这段黑暗、痛苦和恐惧的历史而着迷,可他也知道这无论如何都不是整体的真实。他同样了解慷慨、勇气和自我牺牲的故事:牧师给所有到来的人鼓励和抚慰——包括被逐出教门的天主教徒,犹太人,还有非国教教徒;医生免费看顾穷人;官员迅速行动,平息恐慌,避免灾难;看守人、运尸车车夫、坑边的下葬人;父母、孩子、仆人和朋友,他们受到鼓励、抚慰、照顾、处理、救治,还有哀悼。(30)丹尼尔·笛福:《瘟疫年纪事》,“导言”,第2页。
可以想象,笛福的这种非常具体的描写,对于读者了解那场瘟疫而言,会获得比读一般的史书以史实性的表述更为强烈的感受。文学所表征的历史文化功能正在于此。当时包括笛福在内的一些名作家都对这场瘟疫进行了文学式书写,“17世纪英国涉及鼠疫的作家就有琼森(Ben Jonson)、多恩(John Donne)以及佩皮斯(Samuel Pepys)等”。(31)Gilman, Plague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26.除了名作家之外,在现存的文献中,还有许多关于17世纪这场大瘟疫的书写,“1665年以来的重要瘟疫书写就有:《无处不在的哀伤》(TheMourning-Cross:Or,England'sLordHaveMercyuponUs:ContainingtheCertainCausesofPestilentialDiseases, 1665)以及《年度死亡账单》(TheGeneralBillofMortality:WithaContinuationofThisPresentYear, 1666)等”。(32)Kathleen Mille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Plagu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10.
有关鼠疫的文学作品当然包括后来法国作家加缪的代表作《鼠疫》。这部小说描述了北非一个城市在瘟疫到来时,人们所特有的冷漠与恐惧、喧嚣与骚乱以及人与生俱来的勇气和不可知因素所带来的荒谬。不过,加缪并非像笛福那样是对瘟疫本身进行叙述,而是将其作为一种隐喻,以此比喻法西斯的肆虐。小说的要点在于“人类应该不靠任何救世主,应该自己团结起来向这个荒谬的世界开战”。(33)《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I,第473页。有关笛福和加缪著作的文本意义,可参阅Jannifer Cooke, ed., Legacies of Plague in Literature, Theory and Fil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Chapter One “Writing Plague: Defoe and Camus,”pp.16-43.此外,当时的印刷业也为此类书写提供了市场,研究黑死病文化的米勒甚至认为,“伦敦大瘟疫对于早期现代印刷市场而言是一个转折点”。(34)Mille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Plagu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18.
正是由于欧洲鼠疫或说黑死病对人类认知的冲击,文艺复兴以来的许多文学家、剧作家、画家等,都不仅在各自的作品中以不同方式描述了那一场特大的瘟疫,而且将瘟疫作为某种隐喻来映衬人物的内心世界。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中就对瘟疫有一些特定的表述,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1594)中就展现了街区在瘟疫中的情景,其中有一段对话生动地描述了人们因疫情不愿意接触的场景:
劳伦斯:那么谁把我的信送去给罗密欧了?
约翰:我没有法子把它送去,现在我又把它带回来了,因为他们害怕瘟疫传染,也没有人愿意把它送还给你。(35)《莎士比亚全集》卷8,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03页。
此外,莎翁在其十四行诗里也对瘟疫和死亡有特定的表述,如那首著名的《当我死时》就特地表述了瘟疫流行期间,人的内心世界所受到的更为直接的撞击:
当我死时,你听完那阴沉钟声/向世人宣告我已遁离/这浊世,与至浊之蛆厮守/就不要再悼念我。(36)参见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Illustrated edition, New York: Gramercy Books, 1987, pp.1202-1203. 参考“莎士比亚注释丛书”之《十四行诗集》,钱兆明注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45页。
实际上,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不同区域的群体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接触,自然环境和群体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很多新的疾病和灾难。如随着哥伦布时代的开始,包括梅毒在内等一些“新”病毒,时至16世纪末都一直在欧洲肆虐。(37)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80页。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更使美洲原住民和新的殖民者均感染上“新”的疾病,因为双方都不具备对方所具有的免疫系统或抗体,由此平添了诸多的死亡。(38)详参Tim McNeese,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6.现有研究表明,在发现和征服美洲大陆的过程中,屠杀和疾病感染造成的死亡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原住民的大量死亡,“在殖民时期开始的前100年间,75%到90%的美洲土著人口死掉了,其中的大多数死于殖民开始的前50年”。(39)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1卷,蔡坚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与此同时,当时殖民者的日记、书信、绘制路线和地图等等书写却成为了文学的早期经典文献,只是由于当时的认知水平,疾病在其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总体来看,“鼠疫不过是许多疾病中的一种;由于当时人与人交往密迩,传染机会较多,鼠疫往往先同其他疾病一起传播,经过一段潜伏期后,突然冒了出来。关于流行病和瘟疫在人口密集的文明地区的蔓延,关于这些致死疾病反复流行的节奏,可以写整整一部著作。单就天花而言,1775年的一本医学书——当时开始谈到接种牛痘——认为它是流行最广的传染病:每100人中有95人得病,7人中有1人死亡”。(40)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74页。
关于疾病的这些历史的痕迹,不仅给医学界和社会学领域留下了至今有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也同时触发了人文学术,包括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在研究成果方面,除了上文提及的一些专著外,仅从21世纪以来的一些重要成果就可以看出,学界在瘟疫与文化的问题上正在持续通过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如《医药史的文化探寻》《作为文化的医药:西方社会中的病痛、疾病与身体》,以及在瘟疫与文学方面值得一提的《死亡的账单:早期现代至后现代时期黑死病文学中的疾病与命运》等等。(41)Willem de Blécout and Cornelie Usborne, eds., Cultural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New York: Palgrave, 2004; Deborah Lupton, Medicine as Culture: Illness, Disease and the Body in Western Socie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Patrick Reilly, Bills of Mortality: Disease and Destiny in Plague Literature from Early Modern to Postmodern Times,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15.这些重要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重访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均有裨益。由于文学表征的功能在疾病文化中拥有独特的作用,如前文所析,仅是在鼠疫或说黑死病的主题上,人们就一直在持续书写和研究,原因正在于,“这一类文本不仅呈现了黑死病主题曾经是什么以及现在是什么,它还表征了黑死病在心智上是如何被意识的,在美学上是如何被构思的。语言基于事实呈现意义;而鼠疫文本以意义的方式使人们审视了传染性疾病”。(42)Reilly, Bills of Mortality, p.2.实际上,疾病和医学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学表征不仅是在主题上,当然也不仅仅只有关于鼠疫的创伤记忆和书写。例如,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将叙述的故事置于霍乱的背景中,并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爱情为主要线索,探索了人类内心的复杂和迷失以及互相理解的重要性。这本以“霍乱时期”为书名的小说,不仅对读者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同时也巧妙地将瘟疫灾害作为一种隐喻,折射出与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结 语
大瘟疫的流行给人类造成巨大影响的同时,也以倒逼的方式使人们开始思考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中潜在的问题,包括革除食用野生动物一类的恶习,并且开始有组织地进行防护体系的建制,所以,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引入了“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的概念。概言之,疾病关乎所有的区域和群体,关乎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关乎科学探索与文化观念等相关联的理念。正如胡适先生曾经指出的:“但每一种新发展,不能孤立,必定有其他的文化背景,必定是那个文化背景的产儿。”(43)亨利·E. 西格里斯特:《人与医学:西医文化史》,附《1936年中译本胡适序》,第2页。而文学对包括鼠疫在内的疾病所表征的意义,不仅仅是对文学母题的扩容,而且具有历史文化功能,亦即在弥补群体所必备的公共卫生意识的同时,间接地奠定社会文化发展所需的观念基础。在过往的文学探讨中,尽管“主题”是一个模糊有待具体确定的术语,(44)Jeremy Hawthorn, 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4th edition, London: Arnold, 2000, p.361.但人们的书写往往会集中在生死、命运、境遇、情感等相关的题材要素上。对于文学书写本身所包含的疾病题材以及所涉及的相关文化,人们有必要加以关注,以对其历史文化功能加以还原并提升认知。作为全面展示人的历史境遇、张扬生命文化的文学书写,其对包括鼠疫等疾病的表征,可以使人们重拾对自然的敬畏感并奠定社会发展的观念基础。因此,有必要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中予以强化。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在讨论文化史和现代性问题时、在进行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以及艺术史的教育中,有必要将其间发生的疾病和瘟疫性事件结合起来考察。其实,疾病和瘟疫不仅仅是人类所遭遇的劫难,也是人类必须始终面对的问题。历史上每一次的浩劫,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不是一个孤立的过往,正如研究中世纪文化遗产的学者库克所指出的,“鼠疫一直就在我们的周围”。(45)Cooke, ed., Legacies of Plague in Literature, Theory and Film, p.1.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不断提升对疾病的认知,与此同时,文学的力量依旧可以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