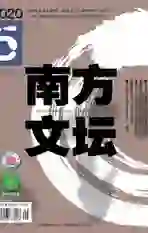黎锦晖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流行音乐
2020-12-24周映辰


一
谈到中国早期的流行音乐,必须谈到黎锦晖。黎锦晖1891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望族,兄弟八人,是“黎氏八骏”之一,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1912年,黎锦晖毕业于长江高等师范学校,经亲友推荐,到北京任《大中华民国日报》编辑,并参加了同盟会。因为该报支持孙中山、反对袁世凯被查封,他在随后任职于国会众议院秘书厅。两年后,又因袁世凯复辟帝制,他离开北京回到长沙。在长沙期间,他兼任四所小学的音乐教员,在教学中,他教风琴演奏,教流行的外国歌曲,也教中国传统歌曲,并为民间音乐填上新词。1916年,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之后,黎锦晖再次赴京到众议院任职。1918年,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黎锦晖被聘为委员,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比如蔡元培、钱玄同等,并因此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
在推广国语的同时,黎锦晖对中国传统的戏曲门类进行了充分的观摩和了解。他发现俗曲多有卑琐之词,遂提出“保留原有曲调,改变唱腔,或取作新曲主题,加以发展”的主张①。顺便说一下,这与我前面提到的李叔同的“新曲旧词”,有一种奇妙的对应关系。可以说,这一主张与李叔同的“新曲旧词”一样,包含着近现代以来中国歌曲创作所具有的空前复杂的美学经验,契合着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殊的文化状况。黎锦晖认为:“新,固然不能说都可以‘新得好,但是无论如何失败,也比旧的有价值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一句极能阻碍进化的妖言。”②在自传《我与明月社》中,他对此有更详尽的说明:
从1917年起,我接触各种音乐的机会更多了,逐渐感觉新文化运动应利用音乐为宣传工具,心想邀集知音朋友组成一个小型的音乐社,以“宣传乐艺、辅助新运”为目的。“凡事预则立”,自己必须作准备,于是进行观摩,阅读、抄谱、记谱,要求自己能结合乐理了解乐曲的结构,听懂不同的风调,哼出无法记录的韵味……我经常上天桥和城南游艺场,搜集一些民歌小曲,跟朋友们研讨,也没人干涉我们的自由。但是,把所知的俗曲歌词摆出来,深感腐朽不合时代,或者猥亵不堪入耳,绝大多数必须重新填配,进行这项工作十分困难,摸索了四年以上,才找到一条出路——保留原有曲调,改变唱腔,或取作新曲主题,加以发展。③
1921年,黎锦晖赴上海任中华书局编译所国语文学部部长及教科书部编辑。年底,教育部國语读音统一会在上海创办“国语专修学校”,他先被聘为教务主任兼教员,后又被聘为校长。后来,“国语专修学校”又创办了附小。在上海,黎锦晖终于有了一片新的天地。正是在上海,黎锦晖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
追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与黎锦晖是互相成就的关系。上海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有其特殊的优势。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上海正式开埠,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涌进上海,开行栈、设码头、划租界、办银行,上海由此进入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引无数英雄各领风骚,可泣可歌。20世纪初期的上海,外国侨民国籍最多时曾达五十六个国家。公共租界人口密度更是高达每平方英里十万余人,超过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伦敦。从欧洲的交响乐到美国的爵士乐,从好莱坞的电影到巴黎的歌舞,都在这个大都市轮番上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其中弥漫着中国别的地方闻所未闻的全球化经验。
这里需要提到学界关于黎锦晖与美国爵士乐大师巴克·克莱顿(Buck Clayton)的关系的讨论。克莱顿本是美国黑人小号手,于1935年跟随他的爵士乐队来到上海,他与逸园歌舞场签订了一份长期合约,在上海度过了两年④。很多研究者认为,黎锦晖与克莱顿曾在上海共事,彼此学习,相互影响,各自汲取了对方的音乐元素。按照这个说法,克莱顿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然也有人依此推论,克莱顿受到了黎锦晖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到了美国。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二人在上海并无接触。根据克莱顿传记作者安德鲁·F.琼斯的记载,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克莱顿在中国期间确实学唱了不少中国歌曲,其中多是黎锦晖创作的歌曲:
克莱顿——他最后于1937年7月日本人进攻上海、预示二战到来的两周之前离开了中国——在接下来旅居上海的时光中不仅演奏美国爵士乐,还演奏中国的流行歌曲。(克莱顿说)“我们发现对这份新工作,必须演奏中国音乐,这样我们就开始学习。我草拟了一些当时最受欢迎的中国流行歌曲,几次排练之后我们就像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很久那样演奏起来。中国的音乐跟我们的音乐除了有不同的音调,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只要能把它们套入美国的音调,我们就能演奏。”克莱顿在被赶出逸园之后不得不学会的中国歌曲,几乎总是由黎锦晖执笔创作,这是一位教育家和作曲家,一种糅进了美国爵士乐、好莱坞电影音乐以及中国通俗音乐被中国人称为“时代曲”的混合体式的创造正应该归功于他。黎锦晖的富有争议的通俗音乐品牌——经常被批评为“黄色”或“淫秽”音乐,受到遣散或严厉指责——以及其紧密依附的都市媒体文化,正是对这一中国爵士乐时代的音乐、文化和历史进行研究的主焦点。⑤
这个事例从侧面说明,在克莱顿来到中国之前,黎锦晖创作的歌曲已在上海大为流行。但我想强调一点,虽没有证据说明黎锦晖受到了克莱顿的影响,但黎锦晖受到爵士乐等西方歌曲的影响,却是确定无疑的。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是因为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敏而好学的黎锦晖身处其间,自然不能不受影响。当然,对于喜欢写歌的黎锦晖而言,这也是市场对他的要求。处于这种文化空间中的上海市民,需要带有爵士风格的音乐。此种情形下,这样的流行歌曲既可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望,又能满足市民的需要,还能用得来的稿酬填补办学经费的不足,黎锦晖自然要大显身手。
二
2004年春节,央视黄金时段播出了多集纪录片《一百年的歌声》,开篇即是黎锦晖的《毛毛雨》。现在,人们公认这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它音域不宽,却朗朗上口,中国音乐元素、西方舞曲的节奏以及美国爵士乐风格的配器,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早期流行音乐的兴趣。
《毛毛雨》创作于1927年,1928年由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由黎明晖演唱。关于百代唱片公司,这里也需要多说几句,因为它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的结晶。百代公司的创始人为法国人E.Labansat(中文译为乐浜生或乐班萨),19世纪末来到上海,最初靠沿街摆摊播放唱片谋生。1908年,乐浜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最初称为“柏德洋行”,是法国百代公司(Pathé Frères)的在华代理商,批发或零售该公司出品的各式留声机、唱片、电影机械、影片等,“柏德”为法语“Pathé”的音译,后于1910年改称百代公司⑥。20世纪上半期,凡提及唱片,没有人不知道上海百代公司。“百代”虽是一个唱片公司,但其产品的意义却远远超出唱片本身。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的代名词,所以论及中国早期的流行音乐,必须提到“百代”。
演唱这首歌曲的黎明晖是黎锦晖的女儿,1909年(也有1910年或1911年的说法)出生于湖南湘潭,1921年随父亲来沪,就读于“国语专修学校附小”。1925年黎明晖相继在神州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不堪回首》《花好月圆》中担任配角。黎锦晖1927年创作的《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由黎明晖首唱后,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间一夜走红,百代公司迅速邀黎明晖前来录音,然后以“特别新曲”的名义于1927年12月15日发行。这是中国最早公开发行的流行歌曲唱片。
聆听百代版本的《毛毛雨》的录音资料,可以听到它使用了西洋铜管乐器组,这是因为当时上海的歌舞厅还有涉外的大饭店,白人、黑人组成的西洋小乐队、爵士乐队并不少见,而时尚的都市流行音乐,一定会使用这些洋乐器。歌曲一开始的伴奏部分,是铜管齐奏旋律,小号吹出主旋律,紧跟着中国木鱼敲击“有板有眼”的节奏,还有钹等多种音乐色彩调和在一起。歌曲用一个曲调反复四段歌词,旋律以级进为主,运用小起伏式的十六分音符表现毛毛雨的形象,歌曲结构为一段曲式,上下两片各两个乐句,每一乐句有六小节,构成对称的非方整性结构。歌词内容似乎很简单,无非是说一位少女思念心上人,其中出现了很中国式的昵称“小亲亲”。这首歌乍一出现,便风靡上海滩。黎明晖作为首唱,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20世纪初的夜上海,歌舞厅里常常人声鼎沸,男男女女衣装鲜亮,通宵达旦地跳舞。租界林立、列强环伺的现实,仿佛都消散于这如梦似幻的氛围之中。消费的媒介即是适合歌舞厅使用的流行音乐,华尔兹、伦巴、恰恰等舞曲音乐,有很多就是使用国外的现成品,爵士乐是其中被使用最多的。当然,中西混合的舞曲音乐也随即大量出现。既然是中西混合,那么所谓的“中”,自然就属于那个时代的“原创”。这种原创,即是在西洋流行音乐的基础上,加入中国人自己的调性。这种中西结合出来的流行音乐,一经推出,就远比纯西洋的歌曲舞曲更让中国人喜欢。其中不能不提的,就是流传至今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演唱者是百代公司签约艺人周璇。
《玫瑰玫瑰我爱你》由吴村作词、陈歌辛作曲。这是一首以歌词为结构基础的ABA 三段体歌曲:主歌—副歌—主歌。A 段的四个乐句依照了歌词的结构,采用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最为常见的“起承转合”形式;B 段则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配合重复的两句歌词,这个十六小节的乐段,采用了西方音乐中最常见的平行乐段结构,两大乐句的旋律几乎完全一样,仅结尾处略有不同。作品旋律呈现出典型的中西融合的特征。整首歌曲,旋律轻松明快,歌词简单上口,以物咏情,物我两忘。在上海这个国际化的都市,这样既有地方性又有国际性的音乐,不仅深得人们喜欢,而且还会传出国门。这首歌后来被翻唱成多种版式,其中由美国著名歌星Frankie Laine翻唱的《Rose Rose I Love You》于1951年登上了全美音乐流行排行榜的榜首,盘踞数周。
三
如果说,五四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那么30年代和40年代,上海就是中国的文学、电影和音乐创作中心。这除了上海因开埠而得风气之先,还因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与南京毗邻的上海成了大批文化人的首选之地。这些文化人到了上海,自由组织社团,创办文学刊物,筹拍电影,使得“海派文化”兴盛一时。其中,上海电影业的发展,对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玫瑰玫瑰我爱你》其实是电影《天涯歌女》中的插曲,在电影中是由舞厅歌女演唱的伴舞歌曲。在20世纪初期的都市文化中,电影是重要的一环。电影公演后,里面的舞曲和歌曲更是成为舞厅音乐的模板。歌曲《蔷薇处处开》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由陈歌辛作词作曲。如果把这两首歌的歌词抹掉,乍一听,似乎很难分辨出其中的区别,因为节奏相近,旋律相似,曲式结构也一样,都是主歌—副歌—主歌的 ABA 的三段体结构。经过电影的传播后,这两首歌都成为备受欢迎的舞厅伴奏音乐。
1931年,《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的公演代表着中国有声电影的时代到来了。默片时代的20年代,全国大小电影制片厂就已经逼近两百个,年产默片四百余部。有声电影的出现,把电影的影响力瞬间提升了。特别是都市片,电影中的演员及服道化、插曲等,任何的形态都可能会迅速成为被市民模仿的时尚方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电影插曲几乎成为最受欢迎的音乐,所有的电影插曲都会及时在歌舞厅内唱响,甚至包括像《四季歌》这样纯粹的民间小调,也会流行开来,因为它是电影明星周璇在《马路天使》中演唱的。
如前所述,电影歌曲的大量出现,为歌舞厅的使用提供了便利。像引领上海娱乐业的“新卡尔登”,就是兼营电影、餐厅和舞厅的娱乐消费场所。看完电影到舞厅,给客人提供的伴舞音乐就是刚刚在电影院里听过的,所谓欣赏与体验、消费与应用一条龙服务。直到今天,像《渔光曲》(电影《渔光曲》主题歌)、《夜半歌声》(电影《夜半歌声》主题曲)、《天涯歌女》(电影《马路天使》插曲)、《何日君再来》(电影《三星伴月》插曲)、《秋水伊人》(电影《古塔奇案》插曲)、《百花歌》(电影《孟姜女》)等逾百首的电影歌曲,依然会在各种晚会、屏幕或者网络上出现。
在20世纪早期,以上海、南京、天津等为代表的几个大都市,在西方科技与文化代表着“先进”的历史潮流中,在商业需求与文化消费的驱使下,音乐家们立足中国音乐,借鉴西方创作技法创造的“新音乐”,成为中国现代音乐的重要内容。时代曲,也就是流行音乐,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音乐元素与西方流行音乐的创作技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中国化的音乐风格,也成为20世纪早期都市文明的一种文化标签。
【注释】
①黎遂:《民国风华:我的父亲黎锦晖》,团结出版社,2011。
②孙继南:《对黎锦晖历史评价的再认识》,《人民音乐》2002年4期。
③黎锦晖:《我与明月社》,《文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
④关于克莱顿在上海工作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1935—1937年,第二种说法是1934—1936年。其传记作者安德鲁·F.琼斯认为是前者,但密苏里-堪萨斯城大学档案馆的克莱顿专题资料库和《新格罗夫爵士辞典》克莱顿条目的记录均持后一种看法。见喻辉:《关于巴克·克来顿早期上海生活史料的考证》,《人民音乐》2017年第1期。
⑤[美]安德鲁·F.琼斯,朝园译:《黄色音乐:倾听老上海的爵士乐时代》,《黄色音乐:中国爵士时代的媒体文化及殖民时代的现代性》(Yellow Music: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杜克大学出版社(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见2016年4月15日“上河卓远文化”公号。
⑥羅亮生:《戏曲唱片史话》,见《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1集),上海艺术研究所,1987。百代公司的注册地址是上海英租界四川路99号,为总发行所所在地;分公司位于英租界四马路。
(周映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