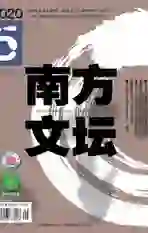囚困在乡土与都市之间
2020-12-24张红翠庞芮
张红翠 庞芮
1940年,经受都市文明洗礼的萧红,以30年饱经苦难的生命之眼反观来时路,追叙故乡人事物,书写静默的呼兰河,是为《呼兰河传》,一年多后,萧红离世。尽管萧红的死是个意外,但我们依然可以认定《呼兰河传》是萧红生命临终仪式的表达,是她“在生命即将消逝的最后时刻,回望乡土的自祭奠”①。《呼兰河传》以及萧红是文学史研究不断重返的重要现场。
一、问题的提出
有学者说:“我们当下文坛讨论的所有话题,萧红的著作中几乎都有。比如‘民族国家、文化批判、乡村溃败、底层写作、性别政治、身体叙事,终极关怀,甚至连后殖民的问题都有。”②因为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萧红从未淡出过评论界的视野。早期,以鲁迅、胡风、茅盾等人为主,形成了关于萧红的经典性评价并长期占据主流,刘禾将其总结为男性目光下民族国家文学批评范式。近年,以戴锦华、孟悦、刘禾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话语形成了与民族国家话语相拉伸的阐释倾向。以萧红《呼兰河传》为突破口,刘禾指出萧红小说中出离于民族与国家视阈的异质性声音,即女性经验的纠缠,它更多地指向男性压制下的女性生存困境。在刘禾看来,萧红的写作没有遵循民族国家的视野和意志,也不一定要在抗战以及民族救亡的背景下被理解。这一点,在萧红所在文坛的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被以民族救亡为批评主调的男性批评家注意。刘禾的论断为重新阐释萧红开辟了新可能,但也有需商榷之处:在从男性话语中剥离出女性经验内核、并以此表达对以国家民族批评为表征的男性话语相对抗的同时,也过分对立了民族国家与女性经验(自我启蒙)之间的关系,从而忽视了民族国家叙事的时代合理性。针对女性主义批评,男性理论家有相当深刻的反驳,但也缺乏与女性话语相对话的姿态。两种批评话语的拉伸凸显出男性与女性性别感受和理解的异位以及不同历史情境理论切入的自觉和不自觉,这就很难在冷静平和的情态下展开萧红的世界。
本文希望在分化的歧路之外探问萧红,并基于一个前提:作品一经诞生,即不断脱域,不断遭遇他时代生命经验的审视和叩击。本文意欲将当下持续展开的都市新经验作为拓展性视野纳入萧红阐释的历史维度,从文本、生命情绪以及时代意志三个方面开掘萧红世界中乡土与都市的复杂视角,重新追问《呼兰河传》以及萧红生命意志中的幽隐曲折。这种阐释视野的拓展源于如下清晰的阅读经验:在最后的生命回望中,萧红对故乡的矛盾愁绪仍无法释然:爱,但依然激烈地痛恨,最终未能与乡土取得和解——归乡者终未归乡。此中原因不仅在于乡土“无可救药”的蒙昧本身,还在于支持萧红文学之眼的都市目光,及其在都市漂泊中的曲折与创痛,即她对都市的纠结。因此,重读《呼兰河传》以及萧红时有三层关系需要解清:1.归乡的悲凉中既有萧红终生未平复的乡土中的旧痛,也有都市奔波中的新伤,即对乡土的情感矛盾,是对都市情感矛盾的投射。2.《呼兰河传》对故乡的批判目光背后,隐藏着一双犀利的都市之眼。3.乡土文化与都市意识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交织,是《呼兰河传》无法厘清的复杂局面。这局面所连接的是中国现代文化中,都市与乡土、现代与传统、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二元结构的基本格局,以及此格局中前者之于后者天然的先进性优势。故而,对故乡的批判实质是都市对乡土现代性批判的文化投射。因而,《呼兰河传》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萧红令人心痛的人生挣扎:无论是乡土还是都市之于萧红都有似一部双城记——入不得也出不得。当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视野中拉长萧红文学世界的背影,重新思索萧红生命中乡土与都市的矛盾时,必须指出:以《呼兰河传》为最后契机所展示的、矛盾纠缠中的都市与乡土都是被遮蔽的:乡土未被发现,都市亦未经反思。
二、呼兰围城:结构的素描
于《呼兰河传》开篇,萧红全景式再现了呼兰城冰冷凛冽的围城式整体风貌:自然之城、社会之城、人性之城。萧红笔下的呼兰小城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抹不掉的乡土中国形象。
(一)凛冽的自然之城
呼兰城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花江北岸,呼兰河穿城而过。呼兰地区的自然环境凛冽荒寒,夏秋季节也十分凉快。萧红不止一次写到呼兰地区的凛冽荒寒:“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③“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④对凛冽自然之城不厌其烦地反复再现,像一声声沉重的叹息飘荡在小说中,凄凉而绝望,有着耐人寻味的意义。其意义在于,在萧红的意识中,故乡的凛冽是穿不透的,而呼兰河人情人性的凛冽更是无法穿透。正因此,在生命最后的回望中,萧红并未完成真正的归乡,依然强烈地挣脱和愤恨地批判。于是,以再现呼兰河自然世界的凛冽为序曲,萧红始终躲在呼兰河人的墙头间、门缝里、屋檐上、窗口外来审视呼兰河的人们,向他们投去或鄙夷或嘲讽或无奈或愤恨的目光。
(二)封闭匮乏的社会之城
严酷自然环境包裹下的,是匮乏封闭的社会之城。十字街口和东西两道大街构成呼兰河社会的主要空间结构。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看似“丰富”的物质生活。东二道街在延伸十字街物质生活内容的同时,多了学校。在萧红现代文明的眼目中,学校是知识文明的传播场所,可是呼兰城中的学校,只能称作学堂,并非现代意义的启蒙“广场”。拔牙洋医生在这里最终也兼做了接生婆。西二道街的“大泥坑”是呼兰人聚焦、观望的地方,是迷信和科学博弈的地方,也是人情冷暖的试验场。“大泥坑”使瘟猪肉的兜售有了市场:人们可以一边吃着“可口”的瘟猪肉快活地解馋,一边心照不宣地宣称:是大泥坑困死的豬,绝不是什么不干净的瘟猪肉。呼兰人就是这样公开地自欺欺人,好似鲁迅笔下的阿Q。在“大泥坑”的故事里,呼兰人的卑琐清晰可见,萧红的嘲讽不屑也清晰可见。除了卑琐平凡的物质生活,呼兰人还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跳大神、放河灯、举办野台子戏……萧红讲述这些,并非要呈现呼兰河民俗多么丰富有趣,而是告诉我们“传统”和“习惯”如何囚困了呼兰人。在萧红看来,呼兰人习惯了在传统中被拖曳着向前,十分可悲:他们没有意识甚至没有力气去理解生存困境,而是惯性地循旧;他们没有意识甚至没有愿望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价值,而是自动地发生。
(三)麻木寒凉的精神之城
匮乏落后的物质精神生活使呼兰人的精神十分粗糙木然。东二道街卖豆芽的王寡妇死了独子之后疯了,乡亲们在片刻同情之后便不再“浪费感情”;染房死了年轻伙计,可缸里染出的布,人们照样用……这些在萧红看来都是呼兰人对生命悲剧及生命本身的漠然,相应的是他们“自然处之”的生活态度:“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⑤萧红的目光中,呼兰人就这样在生死之间无望流转,昏昧无知。于是,萧红无奈又愤恨地写下:“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关系,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⑥带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调,萧红在生命终点再次写下这些故事,并不是重温乡情、构建一幅民俗画卷,也不是为东北地方画像,而是拼尽力气直逼呼兰民间的昏蒙与荒芜。这是萧红始终未能摆脱的叙说故乡的视角。
三、人情人性——劣根的显影
对呼兰城三重围城全景扫描之后,萧红以特写显微的方式和令人颤抖的笔法,剖开呼兰河的人情与人性围城。
(一)惨酷可鄙的人情
呼兰河地区的人与人之间相互观望、造谣、猜测、窥探、倾轧。冯歪嘴子和小团圆媳妇的凄惨人生令萧红难以释怀。磨倌冯歪嘴子居无定所,与王大姐结合有了孩子落脚在磨坊里。因为“青龙白虎”“破了风水”,掌柜夫妇发现后将其驱逐。老板娘不顾零下十几度酷寒,取走盖在母子身上的面袋。当萧红将目光停留在这里,近似白描的笔端溢出彻骨悲凉。除掌柜夫妇,还有很多看客时刻关注磨倌一家动向:“那孩子一声不响了,大概是冻死了,快去看热闹吧。”⑦孩子没有死,于是:“他妈的,那孩子还没冻死呢。”⑧在他们眼里,冯歪嘴子一家是令人不耻的丑闻,却并不知道,他们的观望与嘲讽、冷漠与诅咒同样是“丑闻”,都在那片寒荒的天地间被摧残、嘲讽和诅咒。
小团圆媳妇的故事中,呼兰人更是不厌其烦、喜乐津津地深浸在集体的看与被看之中,十分动情投入,又十分残忍暴虐。讲述这一故事的时候,萧红于忍无可忍间直接用十一个括号将自己的愤怒表达出来。这十一个括号使作为叙事者的萧红转换为小说中的在场者,直接站到看客中间,逼问他们,观察他们,怒视他们。自认为隐忍、善良的看客兴奋地窥探着小团圆媳妇:她的身体、嚎叫、惊惧,她的痛苦和死亡。愤怒中,萧红将众人隐藏的心照不宣和伪善都撕裂开来并告诉看客们,他们也许忘记了他们窥探的何尝不是自己。创作《呼兰河传》时,萧红用哀莫大于心死的悲凉使尽全身最后的气力发出怒吼般的叹息:“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⑨
(二)人性——麻木无觉
惨烈的人情世界建立在麻木的人性之上,在于呼兰人对自我生命的无知觉:“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阳照在了瞎子的头上了,瞎子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是温暖了。……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⑩在自动流转的过程中,呼兰河人的意识里似乎从未出现对生命及自我的认知,只如野草般生长着。在萧红看来,这不是生命的坚韧,而是无知的荒昧。此间,萧红苦苦追寻的现代主体的自我意识、生命的自觉,以及对存在价值的诗意叩问,都是奢侈和“胡话”。所以,萧红无奈地感叹:“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11从呼兰河外在的物质之城到内在深层的物质之城,萧红执着地表达了她与这种生存状态的格格不入。故而萧红是必然要逃离的,并最终以逃婚的方式奔向都市,追寻生命意识的彰显,改写生命文本。于是,有了萧红个体生命与文学世界中都市与乡土的重重纠葛。对《呼兰河传》文本的细密剖析,是接下来解开萧红生命纠葛的重要基础。
四、乡土与都市:萧红的结构性宿命
来自乡土的萧红带有不可抹除的乡土印记。因而《呼兰河传》之于萧红具有不言而喻的归家意义,特别是给她无限温情的祖父、童年的后花园,都是萧红不断重温的精神之乡。然而,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只用三、四两章讲述“我”的故事、童年、祖父和后花园,故乡的温情只是短暂的闪现,其余都在历数呼兰河的蒙昧愚顽,对故乡的批评执意不减。为什么萧红的归家如此挣扎?对于萧红而言,呼兰河到底是故乡还是批判对象?答案更倾向于后者,问题是萧红犀利尖刻的批判目光来自哪里?这个问题将我们引向萧红生命的二难——乡土与都市的矛盾纠葛。萧红的一生,是她决绝地一路狂奔,从东北乡土逃向现代城市的一生。也就是说,在萧红生命的根基处,故乡是个难题,要不断逃离,并在都市的“评判”之后被定格。然而,萧红生命版图中的都市,似乎也不是她生命的归处,因为,都市间的遭逢和伤害并未使她走向生命的释然。因此,都市也是萧红未解的难题。可以说,对于萧红而言,从乡土逃向都市不过是从一个苦难场走向另一个苦难场。所以,萧红始终在乡土和都市之间徘徊,而《呼兰河传》则是萧红生命内在冲突最后的文学表达。如前所述,萧红写作中的生命两难所折射的又是个时代大命题,即中国现代文化时期都市与乡土二元对立的结构性格局。因而,要理解萧红文学世界中乡土与都市之间的情绪纠結,就既要理解她的生命文本,又要理解她所寄寓的那个时代的特定意志。
(一)都市经历的两面
都市文明曾深深吸引着萧红。经过斗争,父亲终于准许十六岁的她进入哈尔滨市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当时的哈尔滨是仅次于当时上海的老牌殖民地大都市。不难想象乡土世界长大的孩子第一次置身大都市时的震撼,都市中自由、民主、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之风更是打开了萧红的精神世界。从十六岁离家奔向都市开始,萧红的足迹遍历哈尔滨、北平、青岛、重庆、上海、香港、东京等大都市,它们串联起萧红的人生轨迹,也开阔了她的生命视野。
但萧红的都市经验还有另一面。在萧红奔向现代化大都市寻求个体的生命自由的同时,她的人生也陷入了持续的痛苦和动荡。考量萧红都市中的人生际遇,我们看到的是历经战乱辛酸、寒冷饥饿的萧红。可以说,都市也将萧红裹挟进颠沛流离、辛酸苦辣和世态炎凉。在《过夜》中,萧红有刻骨铭心的记述12。流离的痛苦深处所指向的无疑是“都市”这一具体存在。在都市间追寻精神上的自由必须以物质的基本满足为支撑,然而,都市并没有为缺乏根基的萧红提供获得自由的物质保证。在《欧罗巴旅馆》中,萧红甚至对邻居门上的面包生出“偷”的念头。此外,都市生活给予萧红致命打击的,还有爱情的背叛。萧红一生经历与四个男人的爱情,情感经历曲折起伏。为了逃避爱情的不忠,萧红孤身一人前往日本,在异国他乡品尝人生的孤独寂寥;为保住艰难的情感,萧红曾抛下刚出世的女婴,留下终生的遗憾,甚至遭人诟病。如果说爱情是都市精神自由的象征,那么,当自由的爱情也不能庇护一个女子的柔弱,萧红心中的都市神话也不可避免地会动摇,只是在那时,都市是萧红唯一的选择,别无他处可去,只能继续流转其间。渐渐地萧红的身体状况也变得糟糕,并最终在三十二岁时含恨离世。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遭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3。
考察这些,无非是想表明:深植《呼兰河传》中萧红的悲凉心境和无法驱散的创伤感,并不仅是乡土给她的,也是都市间颠沛流离的人生遭遇给她的。即在对故土人性世情的悲怨中,更有着萧红生命深处对都市遭际的不平。因此,在考量都市之于萧红生命的现代建构的同时,必须考虑都市对萧红的伤害。然而,尽管都市生活的种种坎坷不断敲打着萧红的灵魂,让萧红的都市认同出现困难。但是,与蒙昧的呼兰河相比,都市依然是萧红最后的生命选择。也就是说,在萧红生命的表层意识中,她是依靠、信赖和认同都市的。但都市中的创伤作为现实的持续性存在也不会消失,且以深层意识的方式嵌入到萧紅生命的内里,积聚为她文学创作的潜在动因。所以,在《呼兰河传》的乡土悲怨中,我们感受到了某种隐忍的释放,其所指向的无疑有都市的创伤。
萧红过世近一百年的今天,现代都市极大发展,我们对都市的认识也比萧红的时代更加具有历史的长度和宽度。当我们带着今天的视野以及都市间复杂多元的生命体验重寻萧红的精神世界,我们很自然地看到,萧红投置于文学叙事中的都市目光,既是出于生命本能,也是出于时代文化意志的植入,因而,萧红生命与文学中的都市以及都市文化意识都是未被检视的。如此这般判断的理由在于:萧红堵上一生奔往的都市文明并没有给她生命更强大的人格和精神力量,以包容和超越人生的苦难,归向灵魂的自由宁静。换句话说,如果都市治愈了萧红,支持她生长出强大成熟的人格,萧红则不会在与他人的情感依附中获得女性的自由,不会放弃孩子对母亲的生命依托,以逃避的方式追随世界。相应地,萧红投向呼兰河及乡土的目光也会多一些温和与包容,释然与超越。但是相反,即便在生命的终了,萧红也未能以包容宽大的心襟原宥历史车轮下卑微的生民。这说明,萧红并未治愈,并未走向生命的成熟,因而,遗憾的是,创作《呼兰河传》时的萧红,既没有在思想性上跳脱时代意志所赋予的都市目光的局限,也没有在主体自觉中跳脱自我的生存局境。萧红并未察觉这一点,不仅是因为萧红的生命时间仓促浅短,也因为那个时代中,我们太需要“都市的精神”来抚慰“传统劣根”凌虐下的灵魂,还没有能力“审视”都市。所以很自然,萧红一直在都市的文化幻象中评判世界,丈量过去。
(二)没有被完全呈现的乡土
如前所述,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用尽最后身力批判呼兰河的乡土劣根:荒唐与残忍、昏昧与原始、丑陋与顽劣。这批判的实质是都市对乡土的批判。萧红的时代,都市之于乡土具有天然合法的批判性优势,依据则在于五四现代文化时期现代与传统、都市与乡土的不平衡结构关系。当萧红以时代所赋予的都市眼光反观故乡,都市目光所捕捉到和感知到的乡土以及乡土中的人事与物必然是原始粗劣的。所以,在萧红的眼眸中,静止在呼兰河的家院只能是“荒凉”的,也必然是荒凉的,并且这种荒凉是要被绝对批判的:“刮风和下雨,这院子是很荒凉的了。就是晴天,多大的太阳照在上空,这院子也一样是荒凉的……若是纯然能够做到这样,倒也保存了原始的风景。但不对的,这算什么风景?东边堆着一堆朽木头,西边扔着一片乱柴火……”14
然而,萧红笔下的乡土显然不是乡土的全部。我们知道,在更早的时段里,在审美现代性的目光中,在浪漫派的情怀中,乡土还是没有成为工业化机器化规训的自然空间,具有与工业文明相对抗的、护佑现代人精神家园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在审美现代性的呈现中,萧红笔下老院的荒凉更可能被赋予苍茫遒劲的永恒的生命之美,它连接着永恒经验、超越于时间……这种经验在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眼里即具有宁静的令人敬畏的力量,比如:“你是自然界平凡的草木,神态谦恭,容颜也朴素。”15然而,这种反向的,经由乡土(自然)投向都市(现代)的审视与疏离的视野还无法进入五四时期的文化意识中,也不可能进入萧红的都市意识。因而,萧红的体验中没有丝毫可能去感受乡土的另一种美,而只有荒凉、杂乱、寂寥、无知无觉。这又从时代意志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萧红的归乡如此艰难,如此耐人寻味地千回百转。
同样,在反思现代性的审美路向中,对于漏粉的无名人家的理解也将出现与萧红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虽然这些人的生存环境恶劣,但是“他们一边挂着粉,一边唱着的。等粉条干了,他们一边收着粉,也是一边唱着”16。在萧红看来,“那不是从生活中所得到的快乐,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得。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墙头上。越鲜明,越觉得荒凉”17。在萧红的目光中,世世代代依着固有方式生活的呼兰河的人们,只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冬季穿棉衣,夏季穿单衣,往复循环;他们不懂也不想去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对于生命,他们既不思考也无力感知,这正是呼兰人的可恨可悲之处。然而,呼兰河边的卑微民众只如萧红所看到的那样吗?而且,如此卑微的小人物不仅在文学中不少见,生活中更是多见,为什么萧红的批判不能留一丝余地,不肯给他们一点生的宽纳?是否还可以存在(或者必然存在)一种不同的看待他们的目光,愿意并能够从更超然的视角去凝视这些卑微的生灵,读出他们生命中柔韧坚硬地托起生活的、野草一样的生命姿态,读出他们顺遂生命的自然?谁能说这些就一定不是呼兰河生命基因中该有之意?谁能说,这些卑微的生命就一定不该得到这样崇高的敬意?所以,萧红的评断似乎也并不必然如此。
当然,我们如此辨析与评断,并不是要在时过境迁之后驳难萧红。萧红是令人尊敬的,她用柔弱的生命经历了时代与人生的多艰世事;萧红是让人喜爱的,她用诚挚率真的笔致写出了自己眼中别样的世界。然而,尊敬和喜爱并不意味着要回避其生命与文学中的纠缠,相反,恰恰是尊敬喜爱才会格外同情其生命情绪中的进退不由自主。萧红的一生已实属不易,在时代的局域与生命的困境中,萧红也难以回身自望。只是,站在今天的历史域限内,我们可以并且应该用新的时代经验与萧红进行新的对话,在透观萧红生命格局与文学世界的重重困境之后生出清晰的新的检视:萧红或许并不必然如此,她还可以跳出自我,开拓另一种生命空间,发掘另一种生命关怀的力量与可能。然而,我们自然也知道,时间并不允许萧红穿越自己生命的限域,也因此,萧红变得更加耐人寻味。所以,萧红生命中无法驱除的悲凉既成就了萧红的文学世界,但也局限了萧红的生命视野。这种局限正是萧红生命及其文学世界中宝贵的时代性印记。
【注释】
①季红真:《哀祭:悲苦灵魂的庄严凭吊——论萧红文学的基本文体》,《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
②季红真:《溃败:现代性劫掠中的历史图景》,《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41617萧红:《呼兰河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第1、3、33、21、193、193、36、98、93-94、88、93、94页。
12萧红:《萧红散文名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第48页。
13蒋亚林:《从呼兰河到浅水湾——萧红传》,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15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诗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79-80页。
(张红翠、庞芮,大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