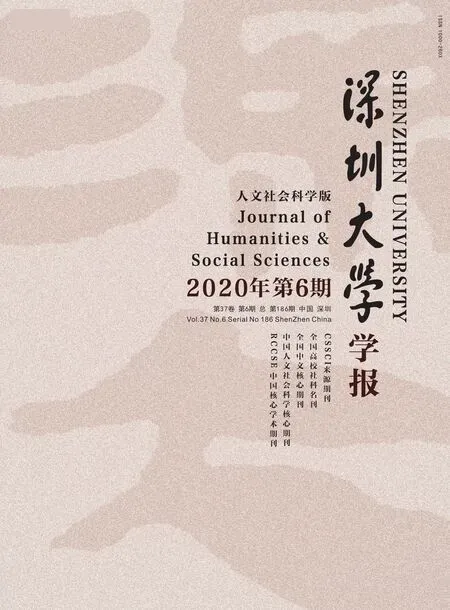审美之维与海外华人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诗学取径
2020-12-24苏文健
苏文健
(华侨大学文学院/华侨大学中外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福建 泉州 362021)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西方批评理论、海外汉学的发展更为紧密地纠结在一起。 在海外华人学者(含在海外求学且经常往返海外的台港学者)的他者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独特性的相遇中,审美现代性在跨文化语境下不断地显现出新的问题意识和话语实践:从去政治化立场对文学性/审美性的凸显,到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对文学性/审美性的淡然处之甚至遮蔽放逐,再到“后理论”时代要求对文学性/审美性、历史性、现代性的关注及其辩证关系的重新审视。 这一变化轨迹与西方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遥相呼应、互为镜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构成了跨中西文化阐释与对话进程中一个极好的研究案例。 纵观海外华人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从《中国现代小说史》到《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再到《被压抑的现代性》《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尽管受到各种西方批评理论的影响,出现过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对文学性/审美性的削弱或压抑遮蔽,但是研究者对文学性、形式性、语言性、抒情性、“颓废”等审美现代性的关注始终念兹在兹。 有论者将此变化过程描述为从夏志清的优美美学,到李欧梵的浪漫美学与颓废美学,再到王德威的怪诞美学与抒情美学这3 个发展阶段①。 不可否认,海外华人学者秉持审美观念或纯文学立场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做了重新阐释和深度挖掘,对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重写文学史形成一股强劲的海外冲击波。周宪指出, 审美现代性具有自身复杂特性和暧昧性,它包含着“审美的救赎”、“拒绝平庸”、“对歧义的宽容”、“审美的反思”4 个层面。 其中,审美的反思性又占据根本性的地位,它带有一种对现存社会深刻反思和批判的功能,体现在它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否定辩证法上, 成为抵制同一性模式的强有力的力量[1]。 面对大陆传统的启蒙(五四/左翼)文学史叙事,海外华人学者以日常生活的文学史叙事加以对抗,自觉建构起一条“颓废”文学史叙事脉络,把现代主义文学纳入到“日常生活叙事”之中。 而颓废,正是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抗[2]。
一、“颓加荡”、阴性与情感系统的知识考掘
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将“为感性正名,重设感性的生存论与价值论地位,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据的本体论地位”[3]视为现代性的审美性的实质之三项基本诉求之一。 而偏重于“颓废”的感性特质恰恰是海外华人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反思审美现代性的重要切入点。 将“颓废”与“现代性”结合起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面向,首推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和王德威。 李欧梵援引美国理论家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的相关理论,以“颓废”来指认20 世纪30~40 年代上海的一批作家作品及上海都市文化的摩登审美特质,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讨论,这与李欧梵对颓废之审美现代性的跨文化阐释密不可分。
首先,发掘重整“颓废”的历史脉络,借以解构“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道德化”,进而改写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整体图景。 李欧梵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一文中曾坦承:“我最关心的问题是颓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扮演的边缘角色,它虽然被史家针砭,在一般大陆的文学史中变成‘反面教材’,但是我觉得它是和现代文学和历史中的关键问题——所谓‘现代性’(modernity)和因之产生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密不可分的。 ”[4](P142)“颓废”在西洋文学和艺术中是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其英文是decadence,但李欧梵比较喜欢“颓加荡”的中文译名,因为“它把颓和荡加在一起,颓废之外还加添了放荡、荡妇,甚至淫荡的言外之意,颇配合这个名词在西洋文艺中的涵义”[4](P141)。 李欧梵认为“颓”和“荡”都是中性词,没有褒贬之意。《红楼梦》因其内在的“颓”——“一种颓唐的美感,并以对色情的追求来反抗外在世界中时间的进展,而时间的进展过程所带来的却是身不由己的衰废”,以及外在的“废”——“一切皆已败落,而这个败落过程是无法抑止的,是和历史上的盛衰相关”,被李欧梵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颓废’小说”[4](P142-144)。 陈建华指出,李欧梵的“颓废”偏重于感性,对于“颓废”这一久遭压抑以至湮没的文学传统的挖掘,给予一种深刻的同情,反映了李欧梵的文化史观,即把“颓废”思潮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追索的一部分,找出中西文化的链接和断裂之处,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②。 准此,李欧梵言述大陆学界不敢正视或曲解鲁迅、郁达夫的“颓废面”,除了道德因素外,还归因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不把颓废看成“现代性”的另一面向。 但在李欧梵看来,施蛰存超现实的小说世界表现荒诞类型、都市的怪诞和历史的怪异神话,“虽不能说惊心动魄,但足可称之为颓废”;刘呐鸥和穆时英笔下具有西洋作风的摩登女郎——“尤物”——表现出色情或性欲的力量,却隐喻着布尔乔亚的世俗和虚伪;邵洵美早期诗作的“颓废”之处在于,“他在花草和金石意象上作各种绚丽色彩变换的营造,而从这些意象的连接达到一种美的意境”;“叶灵凤虽着意于描写人物心理的反常,然而他写得较成功的反而是都市日常生活,偶尔也在这种都市生活中作些矫饰,添加一点异国情调,也许这就是他的颓废风格吧”[4](P160-163)。尽管如此,“这些作家并没有用颓废来反对现代, 也没有真正从传统文学资源中提出对抗现代文明的方法”,为此李欧梵激赏张爱玲,认为她是“真正从一个现代的立场,但又从古典诗词戏曲中找到灵感并进而反抗‘五四’以来的历史洪流的作家”[4](P166)。
同时,李欧梵指认张爱玲小说为“颓废艺术”,并将颓废作为方法,偏至于张爱玲小说的颓废精神气质,强调其传统的现代化或反现代性的美学特质。张爱玲的小说充满“苍凉感”,正是她对于现代历史洪流的仓猝和破坏的反应所致。 “如果现代性的历史是一部豪壮的、锣鼓齐鸣的大调交响乐,那么张爱玲所独钟的上海蹦蹦戏所奏出的是另一种苍凉的小调,而这个小调的旋律——张爱玲小说中娓娓道来的故事——基本上是反现代性的,然而,张的‘反法’和其他作家不同:她并没有完全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这是‘五四’的意识形态),而仍然把传统‘现代化’——这是一个复杂的艺术过程”[4](P167)。也就是说,张爱玲小说致力于传统的现代化,精于细节布局、叙事手法、角色设置、心理刻画、象征意味等,它的“物质化”或“道具”,恰恰昭示其“反现代性”的现代艺术特色。 譬如《封锁》《倾城之恋》等小说,一方面前景与背景重叠和交错,写实与传奇互相交织,刻画浮世苍凉的美学意蕴,另一方面用“传奇”反述历史,神话与历史的交织,但神话却又处处冲出历史背景的约束,深具现代性的矛盾性。 “传奇”侧重“流言”的私人性、感性、阴柔的一面,“故事可以拉过来又拉过去,可以超越时间和历史”,相反历史则注重“大话”宏大叙事、阳刚的一面,它叙述已发生的公共领域大事件,历史事实是固定的,因而以“传奇”来反述历史就具有解构历史的意味。“这断瓦颓垣的意义,正是张爱玲颓废艺术的精神所在”[4](P170)。 在《上海摩登》中,李欧梵更是将张爱玲定义为“沦陷都会的传奇”[5],作为讨论20 世纪30~40 年代“上海摩登”的重要证据,对张爱玲的上海都市现代性展开进一步论述,辨析张爱玲对普通日常生活书写与宏大历史叙事之间的差异。相对于男性的、战争的、革命的力量和荣耀,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苍凉的美学境界和“参差的对照”审美风格得以彰显。 在革命、启蒙、救亡的宏大叙事之外,李欧梵将张爱玲纳入“颓废”论域加以审美现代性的思考,使其成为“寓言”,呈现中国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揭示中国现代性的复杂状貌。
其次,对“阴性”、“情感系统”与“抒情式的文学传统”的知识考掘。 李欧梵言述《红楼梦》是一本“阴性”小说。 此“阴性”不但是男女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而且也和道家所说的阴阳之“阴”有内在的联系。 他认为,“把中国文化的阴柔传统发挥得最光辉灿烂的是晚明。 ……阴就是中国女性的那个字,因此我还创了一个英文字,叫Yinification……正是因为中国儒家的那个官方意识形态的阳刚之气太强……所以有的文人、知识分子反而走到比较阴柔的那一面,产生了晚明的那种文化”[6](P99)。 李欧梵重视晚明文化的原因在于,晚明文化是某一种文化过于成熟的颓废。“中国文化史阳刚之气太重”,“就是都讲大东西,用的比喻是光明的多,黑暗的目的就是要带进光明”[6](P99)。 大东西,即大时代、说大话等,都是阳性的,容易把阴柔的东西淹没掉。 颓废与“阴性”密切关联,究其实是对“情感系统”的发明与倚重。 “作为一个文人的话,可能是觉得儒家的价值系统本身不足,道德、情和欲的问题,色的问题,这一切都属于感情系统”[6](P95)。 诚然,“情感系统”与“性的问题、色的问题,包括情的问题”息息相关,但又更强调主体个人内在的私人情性,警惕过多外在社会政治的非情感因素介入。 在此意义上,李欧梵看重“《庄子》和中国魏晋以来的所谓抒情式的文学传统”,反对把言志的志“变成官方的,变成国家、民族的”,“到‘五四’以后,要救国、要救民,要革命、要抗战。那每一个任务都艰巨得很,都和体力有关系”[6](P98-100)。 李欧梵指认,“五四”以后的文学变得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失去了传统阴柔文化的“阴性”和“情感系统”,20 世纪中国文学对于之前来说是改变,也是转折,或更是危机。 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和强烈的民族危机,知识分子和文人远离审美式的抒情也自不待言。 作为中国文学特质之一的阴柔,只能以颓废的面貌隐匿于现代文学,不能正面示于人。 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错位与冲突以及由之而来的现代震惊体验,构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情感结构。 有学者指出,“颓废文学中蕴含的那种纤细的审美情感, 那种骨子里的浪漫主义,那种在‘无用’的自叹声里流转出的文人悲哀,一方面折射了特定时代风潮中知识分子的侧影,另一方面又保存了文学之为文学的某些基本质素。 这种与时代话语、意识形态‘大话’不同道的文字书写,表面上未必显示出进步、理想主义的一面,但其骨子里却流淌着浪漫、诗意的血。被意识形态扼杀和历史遗忘的那些‘颓废作家’们,由此而显示出了存在的充分价值。 李欧梵是充分认识到了这种价值并试图将其揭橥的”[7]。
李欧梵在《追求现代性(1895~1927)》一文中曾指出:“从西方的眼光看,‘现代’这个词被说成是与过去相对立的一种当代的时间意识,它在19 世纪已经获得两种不同意蕴。 ”[4](P234)在此,李欧梵所采纳的现代性内涵除了是一种当代时间意识外,还包含经济社会和艺术审美两个层面,而后者是一种反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面向。 此一观点源自于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对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区分。 李欧梵对西方现代性理论娴熟掌握和折衷损益,并挪用来阐释中国问题,试图以“颓废”为剧情主线,重整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叙事脉络。 但他也意识到这种两难困境,指出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有两个地方不甚符合西方现代性的标准:一是“在中国五四时期,这两种现代性的立场并没有全然对立,而前者——‘布尔乔亚的现代性’——经过五四改头换面之后(加上了人道主义、改良或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统治性的价值观,文艺必须服膺这种价值观,于是小说叙述模式也逐渐反映了这一种新的现代性历史观”[4](P149);二是“在中国,‘现代性’不仅含有一种对于当代的偏爱之情,而且还有一种向西方寻求‘新’、寻求‘新奇’这样的前瞻性”[4](P236),“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从而对未来产生乌托邦式的憧憬”[4](P146)。 可见,如果脱离中国现实语境,盲目地以西方现代性理论来诠释中国现代文学,就难免会导致多元现代性的削减或窄化, 洞见与不见并存。对“颓废”及其审美现代性的挖掘与张扬,颠覆启蒙、革命与救亡等宏大叙事所造成的人为遮蔽,却也释放出被压抑的感性现代性力量,利弊互现,还需辩证对待。
二、重复、回旋、衍生与颓废的审美观
相对于李欧梵,王德威对颓废的论述集中在“被压抑的现代性”和对张爱玲的研究中。 王德威既以“被压抑的现代性”考察晚清小说文化中的“颓废”这一“现代性”面孔,也对“祖师奶奶”张爱玲的“颓废”现代品格加以“招魂”,一时炙手可热。 学界对前者的论述所在多有,在此存而不论,而仅就其张爱玲研究加以分析。 王德威将张爱玲喻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幽灵,认为张爱玲“成了我们回溯中国现代文明的梦魇,无从捉摸,却又驱之不去”的“幻魅”,籍此可“引领我们重探中国现代性本身的前世与今生”[8](P27)。 王德威从“颓废”着眼的张爱玲研究的特点和意义在于:一是延伸“被压抑现代性”的论述脉络,厘定“张爱玲的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学”特征,以“魂兮归来”挖掘重整“张腔”或“张派”的谱系及其文学史定位;二是努力透过文学与历史的诗史互动,凸显张爱玲在宣传文学的狂飙年代里的异质性及其审美现代性的文化逻辑,展现文学史书写的海外视野。
其一,张扬颓废的审美观与陷溺的奇观。 “张爱玲是一个强烈意识到‘现代性’的作家,时间快速的劫毁,人事播迁的无常,是她念兹在兹的主题”[8](P63)。 张爱玲“对文化‘现代性’的掌握,其实颇有神来之笔”,王德威坦言,“我以为世纪末的张爱玲现象不只说明了一时一地的文化征兆,也折射出我们谈论(文学文化)现代性时,殊少触及的‘回旋’、‘重复’与‘衍生’的机制”[8](P21)。 “张的重复修辞学在一广义的写实/现实主义论述上,更显露了‘五四’以来‘文学反映人生’的教条。 张派作品一向以秾丽细致著称,白描人生琐碎阴暗的层面,尤是令人称道。 但我以为她的成就不在‘惟妙惟肖’这类的模拟特征;恰恰相反,正因为明白了生命的紊乱无明, 张才得以把她的精神肆意挥洒在浮世的细节里”[8](P23)。 准此,王德威认为,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其中我们的精力与欲望迫得反复求索,形成陷溺的奇观”,而《封锁》则“失去了进步革命的精气神,张自我沉溺在狭小的上海滩头,与她的角色一起‘向下沉沦’”,“这当然是极其颓废的审美观。吊诡的是,惟其此一陷溺颓废史观,反托出了中国追求现代性的不安与不足”[8](P23-24)。 诚然,“时代已在破坏中,但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张爱玲小说中漩洑着破碎断裂的时间感、历史意识、世纪末情绪,流露出张爱玲颓废的现代性审美体验。 惟其如此,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文学史叙述[9](P251-296)中,张爱玲也因其“颓废的审美观”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形成一波三折甚至“无处安放”[10]的尴尬局面。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超文典,张爱玲正巧站在众多批评探索之线的结合部。 作为文本和神话,张爱玲依然是个挑战,比六十年代夏志清那里最先提出的挑战还要严峻,她继续挑战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反复遇到的那些基本概念:文典、学科、民族”[11]。 海外华人学者对张爱玲颓废的审美观与陷溺的奇观之强调与张扬,恰恰是海内外学者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美学歧异之根本所在。
其二,强调以“卷曲内耗的审美观照”抵抗现实/写实主义的文学主流话语。 王德威指出,“张爱玲小说的魅力,不只出于修辞造境上的特色,也来自于她写作的姿态,以及烘托或打压这一姿态的历史文化情境”[8](代序P2)。 从《金锁记》到《怨女》,张爱玲以中英双语四次重写同一题材, 回忆与重复、逾越与翻译的故事交织,昭示出她对写实/现实主义的抵抗姿态。 王德威正视张爱玲“不求进取”的写作态度,“现代文学与文化的主流一向以革命与启蒙是尚。 ……张爱玲一脉的写作绝少大志。 以‘流言’代替‘呐喊’,重复代替创新,回旋代替革命,因而形成一种迥然不同的叙事学。 我以‘回旋’诠释involution 一辞,意在点出一种反线性的、卷曲内耗的审美观照,与革命或revolution 所突显的大破大立,恰恰相反”[8](P21-22)。 换言之,张爱玲反对线性的历史观,主张“卷曲内耗的审美观照”,站在革命大破大立的另一边,营构迥异的叙事学,着意渲染浮世的苍凉与世故。 苍凉内含参差的对照,世故也显现刻骨的悲凉。 “张对现实(影子似)的不可捉摸,已经与现实/写实主义主流话语互有出入,而她背向未来,耽于古老的记忆,更十足似摆明了反动姿态。 凭着记忆,她看到现实中双重或多重视景,似曾相识又恍然若失,既亲切又奇异,既‘阴暗’又‘明亮’。 由是参差对照; 轮回衍生出无限华丽蜃影;却难掩鬼魅也似的阴凉”[8](P22)。 这一观点与本雅明解读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爱玲背向未来与新天使脸朝过去,都是反抗线性的进步历史观, 是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抗或“反动”,张爱玲对现代性的独特理解于此也可见一斑。
然而,王德威对“祖师奶奶”的“招魂”不遗余力,所为何事? 在此不难发现张爱玲已然成为王德威反思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装置”,“省思她的出现,如何也改写/重写此前现代文学的向度”,也是检验内与外、左与右、古与今不同价值立场的符号能指或“道具”。 “不论左右,我们的批评者或将她神化,谓之为文化精髓的演绎者,或将她异化,谓之为腐朽堕落的代言人。 我们越急着赋予她一个一了百了的意义,反而暴露我们对意义本身无所在的焦虑。 张爱玲乃成为我们投射欲望的能指,一个空洞的‘张看’(gaze)位置。 是在这一层次上,爱玲不由自主的成为中国文学探寻‘现代性为何’的焦点,或黑洞”[8](P26-27)。在此意义上,王德威指认张爱玲作品贯穿着3 种时代意义:一是由文字过渡(或还原? )到影像时代,二是由男性声音到女性喧哗的时代,三是由“大历史”到“琐碎历史”的时代。 “看多了政权兴替、瞬息京华的现象,张宁可依偎在庸俗的安稳的生活里。 她却总是知道,末世的威胁,无所不在。她的颓废琐碎,成了最后与历史抗颉的‘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一种无可如何的姿态。 正是在这些时代‘过渡’的意义里,张爱玲的现代性得以凸显出来”[8](P64)。 王德威警惕学界对张爱玲神化与异化的做法,还原历史,自觉将张与颓废及其审美现代性勾连,由此编织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线索,其背后去政治化的政治之意图也昭然若揭。
从启蒙、革命、救亡等为主导的传统文学史观来看,张爱玲在这套“宏大叙事”(启蒙现代性)的话语脉络中,微不足道甚或沦为批评的靶子。 张爱玲因其以“流言”代替“呐喊”、“重复”代替“创新”、“回旋”代替“革命”,以“传奇”反述“历史”,“背向未来,耽于古老的记忆”的“反动姿态”,而在传统的文学史“叙事成规”中往往不是被一笔带过,就是作为批判的反面而出现。 张爱玲以“颓废的审美观”、“卷曲内耗”的反线性历史进化观为核心的审美现代性,与启蒙、革命、救亡等所规划的以线性进化历史观为内核的启蒙现代性,形成内在的张力:启蒙文学史叙事与颓废文学史叙事。 这种张力隐含着海内外学者在评价张爱玲的历史地位时展现出的两种对立却又有联系的审美标准、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在全球学术互动协商的情势下,如果将其放到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中加以审视,那么这两者形成了并非对立却互补对话的姿态。 海外华人学者的张爱玲及其审美现代性挖掘,不仅补充了大陆学者在启蒙现代性的文化逻辑下对张爱玲的历史体认,也很好地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副面孔。准此,以“颓废”作为切入口,海外华人学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审美现代性的考辨,一方面在“五四”主流文学史之外,重新发掘上海都市文学/文化,尤其是对张爱玲“颓废的审美观”的阐释,扩充了大陆一般文学史的书写内容;另一方面越过现代文学的“五四”话语论述,甚至回溯晚清的现代性,丰赡了“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脉络。
三、比较视野中审美现代性的话语交锋
如前所述,“颓废”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反思审美现代性之重要切入点,更是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华人学者对20 世纪30~40 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及张爱玲的诗学指认。 而细察这种诗学指认,便不难窥见其与大陆学者或隐或显的对话与交锋。李欧梵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对‘新感觉派’的作家似乎特感兴趣。 自从严家炎教授编选的《新感觉派小说选》出版后,就引起大陆年轻学者的一阵热潮,影响所及,美国和欧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生,也纷纷以此为题。我个人也早在80 年代初就开始研究上海的现代派文学,并曾数度访问当年《现代杂志》的主编施蛰存先生”[4](P151)。 由此见出:其一,大陆学界影响到了美国和欧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感觉派小说研究。 北京大学严家炎编选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③之一种于1985 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其二,以李欧梵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学者几乎同时开始研究上海的海派文学。 李欧梵编选了同名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于1988 年在台北允晨出版公司出版。他在注释中坦言道:“此书根据严家炎教授的原文编辑,但所选小说不完全相同。 ”[4](P172)20 世纪80年代,海内外学者先后编选出版同名但趣味有异的《新感觉派小说选》,折射出海内外学者文学观念、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的异质性,也可视为是继钱钟书等人访美(1979)、夏志清回访大陆(1983)等之后的一次跨地域的学术对话或话语交锋,初步透露出全球学术互动与话语交锋的某种趋向。
一是在文学观念上,呈现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碰撞。 李欧梵从现代主义审美立场出发,将城市文学作家施蛰存、 穆时英和刘呐鸥的文学作品视为极“城市化”的,并将他们看作中国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李欧梵肯定施蛰存以古代人物为题材的幻想小说和专门探讨变态的怪异的心理小说, 并认为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超现实试验。 施蛰存作品的历史价值,正在于他的非写实倾向。历史地看,中国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被视作主流,20 世纪30 年代初与左翼文学合流,成为“批判的现实主义”。 此后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文学技巧或潮流, 变成了作家社会良心、政治意识和民族承担精神的表现,这无疑让文学肩负历史的重担。 然而,从中西文学的关系而言,“五四”以后也有不少作家知道西方写实主义的盛期已过,已不复是20 世纪文学的主潮,代之而起的各种新潮流,因为是新的、时髦的,有“时代感”,所以也竞相介绍。在此意义上,李欧梵将施蛰存、穆时英和刘呐鸥看成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少数的几位作家也不在话下。
严家炎则从现实主义反映论视角出发,虽然也肯定新感觉派小说对现代主义和城市文学的开拓之功,但对他们书写的颓废、没落、腐朽等则持批评态度,相应地赞扬那种揭示罪恶、批判社会黑暗、显示反封建思想的作品。 这种观念影响到对入选作家的文学评价。 如严家炎认为施蛰存的《小珍集》是现实主义道路的回归,反映比较开阔的社会现实内容,揭露国统区的种种怪相,思想意义比较鲜明。相对于刘呐鸥和穆时英,施蛰存“不仅写上海这个大都市,也写到上海附近的小城镇的生活,表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环境的一些重要特点,而且作品的内容也比较干净一点”[12](P19),“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那些具有较多反封建意义,而且艺术表现上也相当精致的作品”[12](P27)。 严家炎批评穆时英前期作品的流氓气味,而肯定其后期小说如《偷面包的面包师》《断了条胳膊的人》,认为内容纯正、干净。 可见,此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意在强调小说的载道功能,凸显文学“服务于社会”的现实意义,与李欧梵所持的现代主义文学观念迥然有别。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文化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歧异。李欧梵的批评彰显出新兴的文化研究特色。 他自觉地将新感觉派的上海书写视为进入上海都市/物质文化的通道。 李欧梵指出,刘呐鸥和穆时英的作品“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对都市生活的迷恋和憧憬”, 而且 “他们都热中于描写 ‘尤物’(femme fatale)——富于异国情调、独来独往,而玩弄男人于股掌之中的神秘女郎”。 “尤物”与传统的中国女性大相径庭,她们行为大胆,追求肉欲的满足,而不为情所困,成为男人恋慕和追求的对象,甚至是幻想、欲望的投射物。 男人赢得女人青睐的方法不是情感而是物质。 “这类物质文明的工具也非写实的,而代表了一种意象和符号,它变成了都市文化不可或缺的‘指标’,象征着速度、财富和刺激”[4](P117-118)。 这种物质文明与农村恬静的基调格格不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颓废。 在李欧梵看来,穆时英的作品正是上海20 世纪30 年代都市文明的产物。 刘呐鸥的都市小说也特重物质文化,彰显资本主义式的消费心态。 李欧梵对新感觉派小说的研究,侧重挖掘其物质文化、都市文化、消费文化及都市情绪,显示出其文学研究的文化取径。
与李欧梵不同,严家炎持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运用传统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模式,对作家作品展开道德关怀式的批评,“腐朽、糜烂、空虚、堕落”成为其批评倾向的关键词。 严家炎指出,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着重暴露了资产阶级男女腐朽、糜烂、空虚、堕落的生活,他们把一切都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无所谓纯真的爱情,只剩下逢场作戏而已”[12](P8)。 “刘呐鸥的小说场景, 涉及赛马场、夜总会、电影院、大旅馆、小轿车、富豪别墅、海滨浴场、特快列车等现代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心主题则是暴露资产阶级男女的堕落与腐败”[12](P17)。 而“穆时英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流露出流氓无产者的气味,无论是作品的人物或体现的思想,都有一点不正,都有一点疯狂性”[12](P12)。 在此,无论是“腐朽、糜烂、空虚、堕落”的指认,还是“流氓无产者的气味”的判断,流露出严家炎文学研究的道德分析倾向,隐含论者的历史社会学批评方法。 这种批评观更为关注环境、时代、道德倾向等因素,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较轻易获得批评的某种制高点。
三是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超越意识形态与文学政治化的立场分野。李欧梵在《新感觉派小说选》的序言“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中指出,“由于20世纪中外文学的区别太大,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特别是在大陆)往往不重视城市文学,或迳自将它视作颓废、腐败——半殖民地的产品,因之一笔勾销, 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宰下的偏狭观点”[4](P112)。 李欧梵站在大陆的彼岸,企图采取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话语姿态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再解读,与彼时大陆的文学研究形成鲜明区隔。 “对大陆上的现代文学研究方法,我往往故意唱反调,譬如不赞成把文学史腰斩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时期。而多年来我就一直主张‘超越’大陆学术界挂帅的现实主义和革命主潮。 ……对浪漫和颓废的偏重,以及对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及文化史上的‘现代性’(modernity)的探讨,都是个人的反潮流的学术尝试”[4](序言P2)。 李欧梵编选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体现其“唱反调”的美学标准和话语姿态,即对文学工具化偏狭观点的纠偏,正面肯定上海都市文学/现代派文学, 释放颓废及其审美现代性的话语活力。 不可否认,在李欧梵对颓废的美学分析背后还隐含着某种潜在的话语政治,其从边缘位置谋求向中心滑动的企图也不言而喻。
相反,严家炎更为凸显文学作品的“倾向性”问题。 如前述,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指认新感觉派小说描写“资产阶级男女腐朽、糜烂、空虚、堕落的生活”、“没落感伤的情绪”、“半殖民地都市的病态生活”等。 究其实他还是站在“五四”主流文学的历史叙事的立场上进行价值褒贬。 “五四”主流文学叙事, 背后仍然是乡土文学主导的启蒙宏大叙事或“历史道德化”的文化逻辑。 历史地看,“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文学的基调是乡村, 它所代表的是整个的“乡土中国”——一个传统的、朴实的,却又落后的世界,它承载着作家内心的感时忧国精神;而城市文学却不能算作主流,甚至沦为边缘,尽管它代表着现代化的面向[4](P111)。 乡土与城市是纠结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两股重要力量,隐含着重要的文学批评伦理向度。 严家炎指认,新感觉派小说有一些倾向性问题和不好的后果:醉心于表现“二重人格”,较少批判地表现;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唯心史观的影响,对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不正确的解释;有一部分作品(主要是刘呐鸥、穆时英的一些作品)存在着相当突出的颓废、悲观乃至绝望、色情的倾向等。惟其如此,严家炎更容易肯定新感觉派小说在艺术技巧上的成就,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80 年代初转型时期的文学研究,新旧混杂,左右交错,在反思解构的同时其解构对象的余绪也有迹可循。
李欧梵对施蛰存、穆时英和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的态度,较为正面直接地肯定他们对色情、感性、欲望、颓废、物质、力量等“反现代性”特质的书写,彰显他们对现代都市文学文化带来的新探索及其历史地位。 李欧梵后来在《上海摩登》中更上层楼,将其发展深化,与张英进、史书美等人形成某种呼应,引领海内外学界的上海都市文学/文化研究热潮,影响深远。 而严家炎对新感觉派小说的态度,更为肯定小说艺术手法的探索,而否定批判其内容存在道德、阶级、政治方面的倾向问题,这受到研究者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 诚然,在20 世纪80 年初期, 严家炎编选出版新感觉派小说及相关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其后吴辉福、赵凌河、李今等学者顺流而下,踵事增华。 海内外学者对海派小说、上海都市文学/文化等研究蔚为大观,众声喧哗,有力推动了全球视野下海内外学者对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改写与重写,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边界格局。
四、结 语
西方20 世纪批评理论对文学与审美关系的认识,大致走过了一个螺旋过程,即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对文学审美形式的强调,到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对文学审美的压抑放逐,再到后理论时代对文学与审美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后的再出发。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此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比较地看,纵观中国大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发展历程,或更易窥见其中的影响关系。 20 世纪80 年代文学研究对此前“文学政治化”的自觉反思,使得具有向内转的文学性、主体性、审美性等因素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此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79)中译本在大陆学界得到广泛流传与之形成合流,“20 世纪中国文学史”、“重写文学史”等呼应纷纷而起。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全球化、网络媒介等的影响,在西方后现代理论大量译介的情势下,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文学性/审美性也在跨文化、跨学科等热潮中隐而不彰,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审美性向日常生活蔓延成为老生常谈,而恰在彼时众多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化转向带来的代表性成果也纷纷涌入,如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被压抑的现代性》、 刘禾 《跨语际实践》、李欧梵《上海摩登》、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等,同时海内外学者在大陆与彼岸不断游走,助推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自不待言。 新世纪以来,众多西方批评理论早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集中涌现,研究方法虽多元渗透,但在“后理论”影响下,理论热却渐生疲软,人们逐渐得以重新审视此前被放逐或被边缘化的文学性/审美性,形成了文学性/审美性,甚至抒情性研究的再出发,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等成为重要代表。 可以说,作为审美现代性的重要切入点之颓废,是海外华人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念兹在兹的,也已然成为他们不同时期推进研究的重要诗学取径。 诚然,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审美之维一直纠缠着文化政治的话语权力,个中复杂错综令人煞费思量,也是中国追求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难以纾解的现实困境。 就文化研究的意义而言,西方批评理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其发展之间的交叠缠绕但又并非完全同步的特征表明,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中西交汇的领域为平台,审美之维/审美现代性成为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共同问题。 颓废作为方法,其所凝聚的并非单向被动的文化研究“冲击-反应”模式,而是中西文化、比较诗学相互映照、对话协商的双向阐发或多元化诠释,对“重写文学史”甚至跨地域“中国现代诗学”的形成与建构都意义重大。
注:
①参见胡燕春,徐昭晖,马宇飞:《论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美学视域——以夏志清, 李欧梵与王德威为例》(《兰州学刊》2011 年第11 期)。 也有论者将此分别归纳为“道德审美”、“历史审美”和“现代性审美”。 参见夏伟《美国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审美性碰撞——以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为人物表》(《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11 期)。
②陈建华指出,“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探究和诠释是欧梵先生数十年来的一个基本目标”,“他沿着早年探求的‘五四’浪漫主义,进而探讨‘颓废’,在美学和感情系统的现代性方面展示较为隐微的、 更带有城市文化的特征”。 参见陈建华《前言》(李欧梵《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书店2000 年版,第3 页)。
③这套丛书于1983~1995 年间出版,还包括《象征派诗选》、《现代派诗选》、《新月派诗选》、《九叶派诗选》、《京派小说选》、《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等14 册,影响广泛,后来多次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