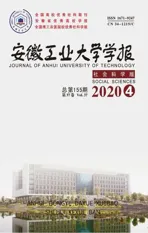生态主义格局中库切的动物权利观
2020-12-24吴大志
吴大志
(马鞍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100)
荷兰裔南非作家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是世界各地英语文学研究的热点人物之一。学界关于库切作品的研究主要从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形式、作品主题、文化身份(“他者”和流散写作)等视角进行阐述论证,但较少从生态批评视角研究库切作品中的动物生存权利。
基于动物权利理论,本文通过研究库切的成长环境、生态价值取向及其小说文论中关于动物描写的创作意图指向,对库切的主要代表作品《动物的生命》《等待野蛮人》《耻》的文本进行分析,探讨库切内在的动物权利观之维:人与动物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人性与动物性的相异又相融、对动物权利的无视践踏是人性黑暗和丑恶的一面。将生态圈中动物生存状态和人性对动物权利意识的缺乏与库切小说研究结合起来,势必为库切作品分析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动物权利理论溯源
“动物权利”概念最早于1892年由英国学者亨利·塞尔特提出, 在他看来,“动物和人类一样,也拥有天赋的生存权和自由权。人类有人类法,动物有动物法。”[1]随着动物权利论的发展,在对待非人类动物保护的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于1975年出版的作品《动物解放》。该书提出物种歧视和种族歧视是人类偏见的产物。辛格是站在物种意识发达程度的基础上来论证的,这引起了广泛争议。
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于1983年出版的《为动物权利辩护》一书中,提出“动物也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它们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生命和价值”[2],真正地阐述了“动物拥有权利”的命题。雷根认为辛格的功利主义对传统道德论证是不充分的。随之,动物权利的理论发展又走向法权思维和道德反思的激烈争论:美国法学家G.L.弗兰西恩是动物权利论的有力支持者,他主张“赋予动物以法律人格,使之成为道德主体和法律主体”[3];同时,在法权思维方面,加拿大哲学家简·纳韦逊则从契约论的角度考虑,认为契约是建立“权利”的基础,动物没有与人类的契约权,也就谈不上“动物权利”之说;从道德反思角度来看,批评主要来自于斯泰因伯格,他认为道德关怀只属于人类,不为动物所拥有,因为,“第一,人类被认为要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并因此被给予相应的尊重。第二,人类能以动物所不能的交互方式行动。动物不能被利他、道德等因素所激发,也不能对是非公正做判断。第三,人类具有自尊的期望,而动物没有。”[4]显然,斯泰因伯格的论点是建立在人类能够“给予尊重、拥有交互方式和自尊”的独有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的。
国内关于动物权利的研究始于杨通进教授,他对从西方引进的动物权利论是有所取舍的。早在2003年的《非典、动物保护与环境伦理》一文中就提出“审慎理论、仁慈理论、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这四种伦理是“以某种混合的形式发挥作用的,只引用单一的理据,不是难以令人信服,就是难以给人们的行为提供足够的动力”[5]。杨通进就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和濒临灭绝动物保护主题提出“动物福利、动物实验和素食主义”相关举措。与此同时,国内学界就动物权利与动物利用的冲突问题掀起争论热潮,具有代表性的是邱仁宗教授和赵南元教授的辩论。邱极力推崇动物权利论,而赵则认为动物没有自我意识,不拥有主体地位,没有主体地位也就谈不到权利与义务。事实上,正如张姚所言,“邱赵二人的冲突体现了西方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间的差异,如果不考虑具体国情而一味倡导动物权利,结果往往适得其反。”[6]尽管常有意见向左和争论发生,关于动物权利的理性思考和法学定性会一直延续下去。
纵观国内外研究,对动物权利的界定和论证已然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命题。无论是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还是作家,虽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对待动物权利的思考和研究从未间断过。
二、库切的动物权利观思考
具有多重文化身份和流散写作特质的库切,怀有深刻生态关怀思想,他在作品中显露出的动物权利意识,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生态批评中离不开为动物权利进行的诉求。动物权利意识萌发于作家童年的成长背景和社会环境;当目睹社会现实中动物遭到杀戮的情景,在一次次受到刺激且无处诉求后,焦虑的库切在诸多作品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提出,人类在发展工业文明的同时不该忽略动物权利,要从人性和动物性的平等角度出发,停止对动物无谓的伤害。
(一)动物权利意识的萌发
库切出生在南非,父母是荷裔布尔人,在南非荷兰语和英语两种语境和不同种族文化的碰撞中,他自幼沉默寡言,对世界尤其是生命体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体恤与同情。库切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究其缘由,这与库切1919年随父母迁至沃吉尔方丹农场(Vogelfontein)生活经历有关,正如他的自传体小说《男孩》中所描述,每个周五农庄上都会宰一只羊犒劳工人,“看过罗斯宰羊后,他再也不喜欢碰生肉了,回到伍斯特后他都不愿意去肉铺了。”[7]不难理解,这种对动物的同情和反对肆意猎杀动物的态度从小就深入库切的内心了。
库切动物权利观的出发点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诉求,而是复杂的人性拷问,这在《库切传》中能得到详实的考证。据坎尼米耶的研究,库切素食主义的缘由是多层面的,客观上来说,除了上文提到的宰羊场的经历以外还与库切因一次过敏后医生给的饮食建议有关。
库切的妻子菲利帕养过一条狗,菲利帕非常喜欢,但库切最初讨厌它。他们家门外车来车往,一般狗都被锁在院子里。有一天,库切故意打开院门,狗跑出院子,结果被过往的车碾压受伤,而后死在菲利帕的床上。目睹一个鲜活的生命因自己的故意过失而惨遭不幸,库切对动物的怜悯之情再次得以激发。当然,这次意外也加深了库切的动物保护意识。
自1974年起,库切成为真正的素食主义者,反对一切对动物的残酷杀戮,包括人类为了获得肉食而进行的机械式饲养和肉食加工的做法,他说:“如果食品供应包括美其名曰动物产品的那些东西,那么把动物变成食物的流程一定是机械化的。”[8]可以看出,库切的素食选择和对动物关怀并非简单的判断和口号,而是反复螺旋式的上升之后形成根深蒂固的信念。
《库切传》中关于动物的描述可以帮助读者确立库切对待生命的敬畏之心。库切不仅严格保持素食的习惯,还在作品中给予动物足够的怜悯,并为动物权利进行辩护。这种略显幽暗和悲悯的书写模式下,关于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在库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暗之地》就得以显现。这部小说由两个中篇故事构成:一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一名在美国工作的男子狂想出一个心理战争的故事;另一个是关于雅各布库切的故事。剥去人类文明的外衣,让真实的人性展露在读者面前,在凶猛和强势的表象背后却是人类自身的软弱、无知和渺小。作为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库切对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抑或,在经历南非社会巨变、种族文化冲突的夹缝中成长的库切,天生就具有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动物的保护意识犹如一颗种子萌芽待发。
(二)动物权利的焦虑
除了《男孩》以外,《动物的生命》《等待野蛮人》《耻》三部作品中都有主角亲眼见到动物被掠杀的描述。这绝非偶然,而是库切为了表达动物权利的精心安排。对动物权利的关注是库切作品研究多元话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暗流。
在《动物的生命》中,库切第一次发出保护动物权利的呼喊。该书原本是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稿,后收录进库切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八堂课》,其中不乏关于人权的激烈辩论,力陈动物权利保护的意义和给予动物人性关怀的必要,深层体现了动物权利的焦虑。本书由“哲学家与动物”“诗人与动物”等部分组成。“哲学家与动物 ”指控第三帝国的罪恶是把人像牲畜一样处置,并对其肆意滥杀。科斯特洛谴责人类因丧失人性的怜悯,而在行为上使自己变成了所谓的无思考能力的“野兽”。“诗人与动物”中,科斯特洛通过小说家对待动物的方式展开了对动物同情心的讨论,认为人类要放弃简单赞成或反对动物权利的哲学争辩 ,认识到动物是一个个真实存在的灵魂,而不是人类的附属品。
库切选择以小说形式而不用论文方式讨论动物维权,大概别有用意。因为论文中的用语多半是理性而抽象的,这恰恰正是人类用来剥夺动物权利的语言;相比之下,小说语言可以虚构和想象,具有无限的张力。
虚构的主角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与反对者激烈对峙,批判人类犹如法官对于罪犯,并指控他们像纳粹对待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那样对动物无辜屠杀,仅为满足自身的需要和欲望。像这样“犹太人死得像牲畜,所以牲畜死得像犹太人”[9]的类比隐喻,言明了人类残害动物与纳粹的恶行是如出一辙的,在自行隔绝心灵和同情心的时候,人类已经犯下罪行。
充满焦虑感的类比在另一部小说《等待野蛮人》中多次表现出来。这是一部由老行政长官叙述关于边陲小镇上发生的一场野蛮人要攻击帝国的故事,直到最后野蛮人也没有出现,但其实真正的野蛮人存在于帝国内部。这部多重隐喻的寓言式小说,反映了后殖民时代的社会内在矛盾,批判了种族殖民战争对自然生态造成的巨大破坏,从而展示了其同情弱者、关注人类命运、反对殖民暴力和酷刑压迫。
老行政长官在狱中被比作一头奄奄一息的困兽,他活着仿佛只是为了印证一种事实:在帝国受到野蛮人威胁之时,“凡是对野蛮人有好感的人内心就是一头动物;被俘的人也扮演着与动物相同的角色。”[10]然而,当老行政长官在一次狩猎的经历中,看到骄傲的公羚羊淌着血倒毙在冰层上的时候,他有一种“难以言述的伤感蛰伏在意识边缘,……凝视拽向了自己的内心,狩猎的乐趣已荡然无存”[10]。在寓言式的历史叙事下,曾经的执政者沦为阶下囚,动物和想象的野蛮人都处于劣势。
霸权的暴行不仅存在于人类强者对于弱者的凌辱,也存在于人类对动物的残忍行为。库切在《双重视角:散文与访谈》中痛苦地说,“世界上的苦难,不仅仅是人类的苦难,让我思绪混乱无助。”[11]这种无助来自于作家对自然界非人类物种的担忧、对动物任意被人类屠杀的愤恨与对动物的未来处境的焦灼。
对于库切来说,“动物的权利和人的权利是一样的,都需要被捍卫。”[12]这一点在《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耻》主要讲述白人大学教授卢里经历了校园丑闻案件后,辞去工作到乡下女儿的农场避难的故事。小说共分为四个部分,情节跌宕起伏。第一部分讲述卢里的丑闻并拒绝悔过道歉;第二部分描述卢里来到女儿身边在乡下的护狗所打杂;第三部分的情节最为震撼:遭到三个黑人的抢劫和蹂躏,其中一个还是孩子;第四部分是故事的结束,案件不了了之,露西怀孕,决定生下孩子。露西遭到三个黑人强暴后,放弃诉讼而选择生下与黑人的孩子,这说明露西作为殖民者的后代主动自我牺牲来消解种族间的历史仇恨。其中,卢里要写的歌剧《拜伦在意大利》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这似乎寓意深远。
其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就是卢里从大学教授沦为护狗员,他从最初厌倦农场工作,到接受并依依不舍给残疾的狗做安乐死的操作,说明主人公在动物权利选择方面的焦虑。
事实上,《耻》在鞭挞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同时,多次叙述卢里就动物问题的激烈争辩,表现了卢里明显的怀疑论者倾向。卢里一开始赞同神甫的观点,认为动物的灵魂不完善或不具备拥有灵魂的资格;到小说结尾,他却一改初衷,确信动物拥有灵魂,他和那名地方行政长官一样显示了柏拉图式存在论的影响。动物权利和人权一样不容亵渎,关于动物权利的维护构想不是理想的乌托邦,而是需要深思的生态事实。
(三)动物性与人性的哲学思考
如果说卡夫卡笔下的动物形象多数是明确的主角身份而不是人物形象的附庸,那么库切则是有意识地完成“卡夫卡式”的孤独的精神之路:赋予动物以灵性和感知,更重要的是通过书写倡导动物权利。甚者,从动物权利哲学角度研读库切的作品,作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和情感自觉、动物性和人性关怀,以及生态价值取向就可以完整地得到展现。
库切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颠覆传统哲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动物的生命》中借科斯特洛之口批判哲学中“理性”对动物权利的忽视,支持自然生态的人性和动物性的融合,坚决反驳笛卡尔对待动物的态度,“‘我思,故我在’。我对笛卡尔这个公式很不满意,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活生物,如果不能做我们称为思想的事情就是次等的。”[7]当然,库切反对笛卡尔的机械式物种歧视,人类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与其他物种一样平等,在考虑人性需求的同时也要考虑动物性。
无论是人性还是动物性,都不是单独存在,两者只有同质融合才能发展推进。在库切作品中,人性表现在对动物群体的同情。《等待野蛮人》中老行政长官收养狐狸时,对野蛮人女孩说,“我在房子里养了两个动物,一只狐狸和一个女子。”[11]在他看来,动物和人一样值得尊重,那是对生命一视同仁的敬畏;“万物皆有灵”,人类不是唯一的生命存在;动物有灵性,不囿于被人类收养的宠物或被驯化的家畜,也包括野生的所有生命体。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人类应该意识到,忽略动物性存在的人性是扭曲的、不健全的。
同样,对动物的掠夺和滥杀则是人性黑暗的一面。在《等待野蛮人》中,乔尔上校谈及一次驱车狩猎的经历,“当时成百上千的鹿、猪和熊被杀死,漫山遍野都是动物尸体,多得没法收拾,只好让它们烂掉”[11],荒唐的是这样的猎杀仅仅是为了娱乐。人性中善的泯灭,是无知和愚昧的。“动物是有理性、感情、智力和灵魂存在的。通过这些被虐待的动物,库切在拷问人类的人性。”[13]动物性在小说《耻》中可以看出,卢里那只喜欢音乐的狗“对他产生一种感情。虽然它被收养并非出自情愿,而且是无条件的,但它能为他去死”[12],动物被赋予了感情和灵性。不能说忠诚的“狗”仅仅是被人类驯化的“奴仆”,它的生命本真和动物性本质需要得到伦理归化。卢里一开始是被动勉强地接受动物收留所工作,最后在对动物的恻隐之心的驱动下做到了“可以让这条年轻的狗多活一个星期”[12]的决定。人性的善在经历磨难之后终于回归。人性与动物性并非格格不入,相互矛盾,而是相通相融的。人性的美,正是通过对生命的尊重而得到实现与升华。
三、结语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这样的警示名言: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同样,人类只有善待自然、善待动物、抛弃“弱肉强食”,才能共建“去恶存善”的生态伦理。保持自然生态平衡永远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个意义非凡的工程。
人类的愿望是美好的,就如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的生态主张一样:“人们要看到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环顾时下,人类在澳洲森林大火面前无能为力,万顷森林化为灰烬,数以万计的动物烧成灰碳;人类对虐杀野生动物所酿成的后果缺乏预期判断,给全球生态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后果。这样的悲剧源于人类中心论,如不加以遏制,人类将会走向更可怕的深渊。
库切追求人性的救赎,否定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强调人与动物平等相处,宣扬保护动物的意识。正如王敬慧对库切动物权力观的评述,“人类应该具备一种人性,这种人性指导人类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并以其约束自己的行为。”[13]当然,库切在创作中也试图找到一条对人类与自然危害较小的范式,不断洗涤人性的“黑暗”污点,不断设问,却未解答如何建立合理的生态伦理方法,如何实现动物权利的策略等问题,作家遭遇的精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对人类社会变革尚有疑虑。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对库切是这样评价的,“当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认定的信念时,譬如为动物的权利辩护,他也阐明了自己的前提,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诉求。”库切真实地描述动物的苦难,展示主人公的道德知性被一再唤醒。作家似乎要告诉我们,对生命的漠视和道德敏感的丧失是一个文明走向野蛮和肤浅的悲剧开端,人类唯一的出路只有携手敬畏自然、尊重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