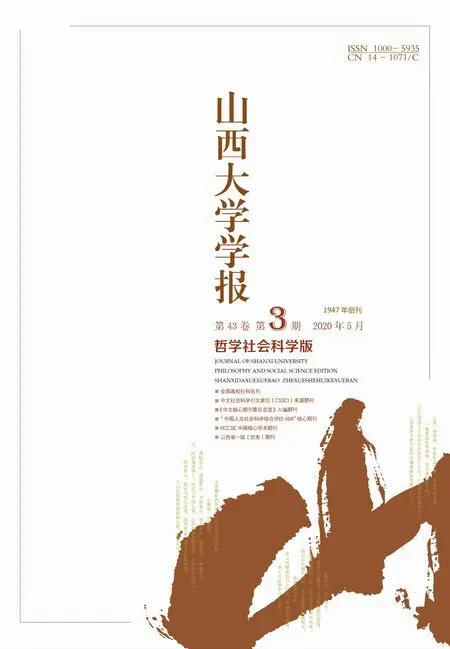“礼乐”复兴与宣王冠婚仪式乐歌考论
——以《頍弁》《车辖》《鸳鸯》等诗为中心
2020-12-23韩高年
韩高年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周宣王“中兴”推动了西周末期礼乐制度复兴,不仅仪式乐歌由于册命、燕享、婚冠等礼仪的需要而被大量创作,而且因为“采诗之制”的实行也促使贵族阶层个性化的诗歌创作也出现了高涨的局面。《诗经》二雅中周宣王朝诗独盛,就是这场礼乐复兴的结果。对于册命、燕享等仪式乐歌,学者已有较多讨论,本文以此前学者较少关注到的宣王冠礼和婚礼乐歌为中心,拟对西周后期礼乐复兴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予以概要的梳理。
一 宣王中兴背景下的礼乐制度转型
《国语·周语》载:“彘之乱,宣王在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1]周厉王其实是一位想有作为的君主,史载“厉始革典”(《国语·周语上》载周灵王太子晋语),但因推行改革(“专利”)的时机不合适[2],引发了“国人”集团的不满,被赶下了台不说,还被流放到“彘”①李峰考察了大量厉王时期的史料,尤其是铜器铭文资料后认为,对厉王被流放这一事件“最好的解释应该是当时周王权与一些有影响力的宗族之间的一场主要的争斗,在这些宗族的逼迫下,周厉王失去了自己的权利,而并非所谓的人民推翻暴君的一场革命。……因此,与其将公元前842年的反叛说成是被剥削阶级推翻贵族阶级的一次胜利,不如说贵族力量战胜王权,抑或是王权重建的一次失败更具说服力。”说见:李 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M].徐峰,译.汤惠生,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56.。如果不是召公虎用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静,连太子静也要死于这场暴乱了。在这场政治危机中,召伯虎力挽狂澜,他和周公旦的后人周定公一起,在周室危难时,保全了周室的继承人。厉王被流放后,一说是共伯和摄政,一说是周、召二公摄政。学界大多据《竹书纪年》及金文材料而倾向于前一说。
周宣王的时代号称“中兴”,有关他的“中兴”功业的具体内容,《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王子朝之语曰:“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王居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杜预注:“间,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彘之乱,宣王尚幼,召公虎取而长之。效,授也。”孔颖达《疏》:“共和之年,官之政事皆归于二相。宣王长而有志,堪为人主,二相乃致其官政于王也。效者,致与之义。”[3]其功业似主要在“效官”,即分封、赏赐和授官。这是春秋时期周室成员王子朝的评价,虽然简要,但从《大雅》之《江汉》《常武》,《小雅》之《出车》《六月》《采芑》等诗所记,及诸多可确定为宣王朝的青铜器铭文材料中多见册命和封赏的情况来看却是事实。如《兮甲盘铭》《兮伯吉父盨铭》《师簋铭》《毛公鼎铭》《虢季子白盘铭》等[4]。齐思和据此说:“宣王即位,南伐荆楚,北征玁狁,号称中兴。宣王既向东南方面推进周之势力,遂更建新国,《大雅》《崧高》《江汉》之诗,即咏宣王锡命诸侯,新建侯国之经过也。”[5]其说甚是。
周宣王的中兴功业后世史家亦有评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史记·周本纪》载:
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主,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6]
司马迁说“二相”辅佐宣王修政,效法文、武、成、康之遗风,最终使“诸侯复宗周”,意谓宣王“中兴”的功业,表现在重新获得了诸侯的支持。宣王之所以能够重新控制诸侯,在司马迁看来,是他取法文、武、成、康遗风的结果。所谓“文、武、成、康之遗风”,就是内和诸侯,外制夷狄。而其具体的方式,则是对内重整“礼乐制度”,对外解除淮夷与猃狁之患。①李峰指出:“尽管西周金文已经证实了某些在文学传统中受到称颂的王室行为,如南伐淮夷以及重建申国等,但我们不能期待周人文学中的每个历史细节都能在金文中得到确认。由于这些事件在历史文本如《竹书纪年》记载中也均有确切的年代,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来过分怀疑这些事件的发生。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宣王时期在西周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发生的看似互不相关的这些事件——包括金文中载录的王室在泾河上游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似乎反映了一系列协调得很好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很可能产生于周王室所采取的一个统一的总体战略,目的是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在周人世界的周边地区重振王室的声威。这可能是宣王朝前数十年中以积极行动为主导的中央政府的施政结果,这也促成了西周历史上有46年之久的最长的王室。现有的资料充分说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周王师的力量在一些边远地区得到了恢复,并且中央王室与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改进。”说见:李 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M].徐 峰,译.汤惠生,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61.围绕着这个中心,周召“二相”共同辅佐宣王,推动形成了西周晚期的“礼乐”复兴的局面。《诗经》“二雅”中产生于宣王朝的诸多诗篇,就是这场礼乐复兴的产物。
关于宣王朝的诗,郑玄《诗谱》和孔颖达《疏》大多遵从《诗序》而有所补充。《疏》云:“大雅《云汉》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尽《无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则宣王诗也。”《大雅》中所涉宣王朝相关各诗,《诗序》②下引《诗序》解诗文字均引自:朱杰人,李慧玲,整理.毛诗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云:
《云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
《韩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锡命诸侯。
《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
郑玄《诗谱》亦以此六首均为“美宣王”之诗。其次看《小雅》中宣王朝的相关各诗,《诗序》云:
《六月》,宣王北伐也。
《采芑》,宣王南征也。
《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竟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焉。
《鸿雁》,美宣王也。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无不得其所焉。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沔水》,规宣王也。
《鹤鸣》,诲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驹》,大夫刺宣王也。
《黄鸟》,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无羊》,宣王考牧也。
以上14首诗,郑玄《诗谱》及孔颖达《疏》均以为宣王朝诗,并进一步证成之,文繁不录。
除上述20首诗作之外,据魏源《诗古微·小雅宣王诗发微》、傅斯年《说周颂》、孙作云《论“二雅”》①孙作云《论“二雅”》:“把前人误说为西周初年诗,还原为周宣王朝诗;把前人误说为刺幽王的诗,也还原为周宣王朝诗;再加上被古今人所公认为宣王朝诗二十几首,计共得宣王朝诗近七十首。”文刊《文史哲》1958年第8期,后增补重作,收入《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刘毓庆《雅颂新考》、赵逵夫《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李山《〈雅〉〈颂〉诗篇创作年代通考》②李山认为宣王朝《诗经》创作再度呈现高涨的景象,但孙作云的研究夸大了这个时期诗篇创制的实际。他考订的宣王朝诗有:“见诸《大雅》者有《云汉》《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见诸《小雅》,有《常棣》《伐木》《天保》《出车》《六月》《采芑》《车攻》《鸿雁》《鹤鸣》《祈父》《黄鸟》《我行其野》《斯干》《无羊》《瞻彼洛矣》《黍苗》等,大小雅合计,宣王朝有二十余首。”见:李 山.诗经的文化精神[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45-232.、马银琴《周宣王时代的乐歌与诗文本的结集》③马银琴《周宣王时代的乐歌与诗文本的结集》认为:“可确定为宣王时代的乐歌共有三十三首(包括创作与写定两种方式),它们是《大雅·假乐》《公刘》《卷阿》《云汉》《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小雅·鹿鸣》《皇皇者华》《四牡》《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车》《杕杜》《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六月》《采芑》《车攻》《吉日》《鸿雁》《斯干》《黍苗》《采菽》等诗。”文刊:中国诗经学会.诗经研究丛刊:第五辑[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26-61.等论著研究确定,还有《小雅》中的一些诗篇亦为宣王朝的作品。它们分别是:《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彤弓》《菁菁者莪》《采菽》《伐木》《天保》《采薇》《出车》《杕杜》《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蓼萧》《湛露》《鸳鸯》《瞻彼洛矣》《黍苗》。除此之外,在《周颂》中也还有宣王朝的作品。对于以上诗篇产生于宣王时代的证据,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出。
由上所述,仅《诗经》大小雅中宣王朝的诗就有40多首。孙作云认为:“周宣王朝诗何以独多,应与宣王中兴有关,这些诗即宣王中兴的具体反映。”“周宣王在即位之初,重建寝庙、重修祭祀,因此造作新歌,荐之宗庙”[7]。他对二雅中宣王朝诗的考定虽有些宽泛,但指出宣王朝礼乐中兴的事实却是很正确的。
此期礼乐中兴不仅表现在诗歌数量的增加,而且还表现在诗歌创作观念的变化和“采诗制度”的实行。陈世骧曾在梳理研究“诗”字观念的正式形成时指出:“在大小《雅》中《崧高》《卷阿》得《巷伯》三篇内‘诗’字初用,细谉也可看出是辨析着一个新的观念。这三篇在全百篇中可说各有其显著的特点,而‘诗’之一字,最早在这三篇中出现也不是偶然的。……把‘诗’和‘歌’对立辨析开来说,‘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明说诗是作了才来配成歌的。那就是把原始的混茫观念之以诗与歌为二而一,现在来辨析其实为一而二了。于是诗乃初始有了独立的观念”[8]。至于采诗制度,刘毓庆研究通行诸说后认为:“宣王时诗篇急剧增多,几占《小雅》的四分之三。说明宣王实是采诗制度的设立者。厉王止谤,自取灭亡。宣王则吸取教训,采取与之相反的政策,‘采诗’‘观风’,了解民情。”[9]认为周宣王为了政治目的而设“采诗之制”的举措,很有启发意义。采诗制度的产生年代虽有不同意见,但周宣王朝实行这一制度却是可靠的。由上可见,在宣王朝的周室“中兴”大背景下,在礼乐制度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受其影响,一方面大量的仪式乐歌被创作出来,另一方面实行“采诗之制”,使仪式乐歌之外的诵诗和地方性歌谣也进入了王室的礼乐体系中,这从《诗经》中可确定为此期的诗中有充分的显现。
综合以往各家所确定的宣王朝诗歌来看,在内容上有两个方面的变化很有可能是宣王朝“诸侯复宗周”在礼乐方面的具体显现:一是燕饮诗创作的高涨;二是颂君王功臣之德、朝会和册命成为诗歌的优势主题。如《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据《左传·襄公四年》及《仪礼》的《乡饮酒礼》《燕礼》的记载,是行礼奏乐时乐工同时歌唱的诗。李光地《诗所》认为《采菽》“与《瞻彼洛矣》诸篇不相属,而在厉王之后,则必宣王朝诸侯之诗也。四章曰‘亦是率从’,言诸侯来而其左右亦来也。”[10]陈子展谓《采菽》“是诸侯来朝,王赐车马衣服之作。”[11]再如《瞻彼洛矣》,三家诗以为诸侯之世子朝王,而受天子之赐。王质《诗总闻》言:“此必宣王会诸侯东都之诗也。君子指宣王也。”
再如《黍苗》,《国语·周语》韦昭注:“《黍苗》,道召伯述职,劳来诸侯也。”《左传·襄公十九年传》杜预注:“《黍苗》,美召伯劳来诸侯。”朱熹《诗集传》云:“宣王封申伯于谢,命召穆公经营城邑,故将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上述现象的集中出现,和宣王朝的“礼乐中兴”密切相关。
二 宣王冠礼及仪式乐歌
厉王被流放到彘以后,周室大权为共伯和所掌握。《古本竹书纪年》载:“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晋书·束晳传》引)。又言“共伯和干王位。”(《史记·周本纪》《索隐》引)。《吕氏春秋·开春》亦载:“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由这些材料来看,共伯和虽实际掌握大权,但却未称天子,故史家只说其为“干王位”,也就是临时执政。大约是当初有约定,或是在厉王流于彘的十多年中政局朝向对王室有利的方向发展变化,故在共和十四年时,由周、召二公辅佐,周宣王正式登上天子之位。依周礼,此时尚“长于召公家”的太子静,须先举行冠礼,才能宣布践天子之位。周初周公辅佐成王践位执政,就是如此。学者们认为,《诗经》中的一部分,是在宣王朝编成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其中不可能不收周宣王举行冠礼的仪式乐歌。
周宣王冠礼仪式乐歌究竟是哪几首呢?我们认为,就是《小雅》中的《嘉乐》《頍弁》。先说《頍弁》一诗。《诗序》曰:“《頍弁》,诸公刺幽王也。暴戾无亲,不能宴乐同姓,亲睦九族,孤危将亡,故作是诗也。”朱熹《诗集传》不取《序》说,认为此诗为“燕兄弟亲戚之诗”,也即燕礼乐歌。其说近是。《诗序》立说的主要根据是诗末章的“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一句。仔细体味不难发现,实际此句语含庆幸,更像是经历了大乱离而不死之人相劝珍惜兄弟亲情的心理。有的学者据此以为是西周“二王并立”时的诗。[12]诗本文中虽无考见其时代的其他线索,但作者对乱离之后兄弟情谊的歌颂,与《伐木》等宣王朝诗颇为接近;而对姻亲甥舅之情的渴盼又与宣王朝的《大雅·崧高》等诗接近。故此篇产生于周宣王初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诗的作者可能是周宣王朝的姬姓贵族。
这首诗的内容涉及宴饮,除了铺陈酒食丰厚之外,各章首句皆曰“有頍者弁”,显然有别于一般的燕饮诗。此句之意,《毛传》解曰:“兴也。頍,弁貌。弁,皮弁也。”郑玄《笺》云:“实,犹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维何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为也。礼,天子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视朝。”如《传》《笺》义,此句意谓质问天子为何违礼服皮弁以燕诸侯?其实这都是从《诗序》“刺幽王”说出发来解释此句。实则不然。按《仪礼·士冠礼》“缁布冠缺项青组,缨属于缺”,郑玄注曰:“缺读如‘有頍者弁’之‘頍’。缁布冠无笄者着頍,围发际,结项中,隅为四缀,以固冠也。”显然,“頍”是冠礼中用以固定冠的发饰。此诗三章首二句用以起兴的“弁”,就是冠礼时加冠者所著的“皮弁”。依郑玄《笺》及《仪礼注》来看,这种皮弁也是天子视朝、天子和诸侯视朔等场合所穿之礼服。《士冠礼》载:“再加:降二等,受皮弁。”“皮弁服,素积,缁带,素韠。”郑玄注:“皮弁者,以白鹿皮为冠,象上古也。积,犹辟也。以素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也。”就是说在礼仪上穿皮弁服时,要求穿与首衣一样的白色上衣和下裳,且在腰间加褶子,并系黑色的腰带。《周礼·春官·司服》曰:“视朝则皮弁服。”《礼记·玉藻》曰:“天子皮弁以日视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分析其原因,其实冠礼中着视朝与视朔典礼之皮弁服,主要是象征着加冠者成人后可以进入统治集团为政的意思。
弄清了“有頍者弁”的意思,再回到《頍弁》一诗中来。为讨论的方便,先引原诗如下:
有頍者弁,实维伊何?尔酒既旨,尔殽既嘉。岂伊异人?兄弟匪他。茑与女萝,施于松柏。未见君子,忧心弈弈;既见君子,庶几说怿。
有頍者弁,实维何期?尔酒既旨,尔肴既时。岂伊异人?兄弟具来。茑与女萝,施于松上。未见君子,忧心怲怲;既见君子,庶几有臧。
有頍者弁,实维在首。尔酒既旨,尔肴既阜。岂伊异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
诗歌不同于叙事作品,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完成表达的目的,就得有“重点”。这首诗的重点,就在每章的前两句。首章前二句意谓:“这微微上举的皮弁,是为什么呢?”第二章前二句意谓:“这微微上举的皮弁,是有什么用意吗?”第三章首二句意谓:“这上举的皮弁,就是要加在君子的头上。”“頍”字本义为加固皮弁之发饰,在此诗中引申为上举的样子。①《诗》凡“有×”,皆为形容修饰语。《说文》:“頍,举头也。”段注:“此頍之本义也。……如郑说则頍所以支冠,举头之义之引申也。”高本汉解释“頍”为“分岔的带子”,认为此句意为“有带分岔带子的皮帽”[13]。也说得通。显然,如果是视朝或视朔及其他礼仪场合出现天子服皮弁,应当不劳诗人如此自问自答。正因为此处述周宣王加冠之事,十分特殊,且意义重大,故而诗人才如此措辞。
由以上的分析来看,《頍弁》是周宣王举行冠礼仪式后,燕享同姓宗室(兄弟)和异姓姻亲(甥舅)的诗。因为当时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所以诗人未将全部的笔墨都用于铺陈周宣王举行冠礼本身,而是借此表达在经历乱离后亲族姻亲应当团结一心、和睦相处的重要性。诗中屡屡言“未见君子,忧心弈弈;既见君子,庶几说怿。”“未见君子,忧心怲怲;既见君子,庶几有臧。”又以“茑与女萝,施于松柏”起兴,显然是用比兴的手法暗示宗族团结于天子周围,齐心协力。文、武、成、康治国的经验,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也就是通过礼乐而达到政治联盟的目的。《周本纪》说宣王中兴的原因是“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这和《頍弁》一诗的创作动机是一致的。
《嘉乐》为宣王冠礼诗,已有学者指出,然而对于冠礼的时间、地点和政治意义等问题,尚有未及,仍有补充讨论的余地。为方便论述,兹引《嘉乐》原诗如下:
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干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
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墍。
《嘉乐》为《诗经·大雅》第十五篇。此诗篇题,《毛诗》作“假乐”,《毛传》云:“假,嘉也”。《礼记·中庸》引《诗》即作“嘉乐”,《左传·文二年》:“公赋《嘉乐》”,又《襄二十六年》:“晋侯赋《嘉乐》”。赵岐注《孟子》亦云:“《诗·大雅·嘉乐》之篇”,《隶释》载《绥民校尉熊君碑》亦引作“嘉乐”[14]。据以上所载,诗题当改为“嘉乐”。《礼记·冠义》引先秦时人习言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郑玄注:“嘉事,嘉礼也。”[15]冠礼亦曰“嘉礼”,故宜称冠乐为“嘉乐”。从篇题看,此诗与冠礼有关。
再具体一些说,《假乐》应是周宣王举行冠礼时,辅国大臣所作的祝颂诗。王闿运《诗经补笺》云:“假,嘉,嘉礼也。盖冠词。成王抗世子法,故有冠礼。”又云:“宜王者,未王也,时周公摄政。”王氏就本诗内容和诗中关键语句的解释,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但认为是成王冠礼,则显然不确。首先,成王冠礼仪式乐歌,已见《周颂》[16],无重出之理。
其次,如将此诗同《天保》对照,即可发现在内容、语气甚至句式上都有很多共同性。如《假乐》云:“受禄于天,保右命之”;《天保》云:“天保定尔,亦孔之固。……受天百禄”;《假乐》云:“干禄百福。……受福无疆”;《天保》云:“何福不除,……降尔遐福”。考察诗中各句,也悉与宣王情况相合。“宜君宜王”者,厉王在,太子静尚未继位;“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者,正所谓“法文、武、成、康之遗风(《史记·周本纪》)”;“无怨无恶,率由群匹”者,针对厉王之刚愎横暴而言。末章写对太子静的希望,其“不解于位,民之攸堲”,正是经过乱政后寄希望于新君。具体来说,《假乐》一诗为宣王行冠礼之冠词。
前人对此诗作于宣王时已有论述。如王充《论衡·艺增》云:“《诗》言‘子孙千亿’,美周宣王之德,能慎天地,天地祚之,子孙众多,至于千亿。”[14]895魏源《诗古微·诗序集义》云:“《假乐》,美宣王之德也。宣王能顺天地,祚之子孙千亿。卿士多贤,皆德获天佑所致也。”魏氏又注云:“《毛诗》厕于成王诗内,服虔数文、武《正大雅》不及之,诸家举召康公诗复不数之,盖三家诗皆列于宣王,亦犹宣王《采薇》之三,《毛诗》错入《正小雅》也。”[17]《假乐》为宣王时作品,为宣王行冠礼之冠词,当无疑问。
业师赵逵夫先生据厉王居于彘十四年方死等事实考证,假设国人起义、厉王奔彘之年太子静六岁上下,则其行冠礼与即位的时间相近。及厉王死,即扶之即位。大约是先行冠礼而后归政,故诗中说“宜君宜王”。周宣王自幼经召伯虎抚养教诲,整个周族都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从此之后周王朝兴盛不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所以宣王之冠礼同即位一样,被看作十分重大的事件。《礼记·冠义》云:“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这些关于冠礼重要性的叙述,有助于读者理解为何在《假乐》诗中用了十分美好的话来祝愿君王。[18]他对于《假乐》一诗为宣王冠礼贺辞以及宣王即位前后周室所面临政局的论述,在前人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尤其是指出宣王行冠礼与践阼亲政时间相近,对深入理解《假乐》一诗至关重要。
其实,《周本纪》中有一个细节很重要,但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这个细节就是厉王死于彘,然后周、召二公辅佐宣王即大位。父死而继位并举行冠礼,是周礼的规定。《礼记·曾子问》载:
孔子曰:“天子赐诸侯大夫冕弁服于大庙。归设奠,服赐服,于斯乎有冠醮,无冠醴。父母没而冠,则已冠,埽地而祭于祢;已祭而见伯父叔父,而后享冠者。”[17]293
父没而冠,是正式宣布嫡长子成年且代父行使权力,故加冠和践阼仪式合而为一,或者说是一仪而二用也。宣王之举行冠礼,也是如此。
父没而冠,其目的是借此礼仪宣布权力的交接。不仅天子如此,诸侯亦如此。据《孔子家语·冠颂》载:“邾隐公即位,将冠,使大夫因孟懿子问礼于孔子。子曰:‘其礼,如世子之冠,冠于阼阶,以着代也。醮于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弥尊,导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虽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其礼无变,天下无生而贵者故也。行冠事必于祖庙,以祼享之,礼以将之。以金石之乐节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长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虽幼,其即位则尊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则诸侯之冠,异天子与?’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丧,是亦冠也已,人君无所殊也。’”[19]《孔子家语》所载应有所据,父丧,世子不仅要通过冠礼宣布接替父之权力,而且还要主持丧礼。周礼将冠礼、践阼之礼、丧礼相关联,并同在祖庙中举行,既实现了政治权力交替的制度保障,也贯穿着“礼,宜也”的制度合理性。这对我们理解《假乐》一诗的创作背景,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由以上分析看,《頍弁》《假乐》二诗,当作于周宣王初立之时,其背景是“法文、武、成、康之遗风”,其创作动机,是借助周礼关于加冠、践阼和主持丧礼的礼乐制度设计,达到权力交接、纠合宗族和收拾人心的政治目的。
三 宣王婚礼仪式乐歌
据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载:“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又曰:“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辅政。”又载:“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庄子·让王篇》:‘共伯得乎丘首。’《吕氏春秋·慎人篇》:‘共伯得乎共首。’)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崩,卜于大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归国。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20]如果此处记载可信,则周宣王的继位,先是得到了共伯和的支持,然后有周、召二公的辅佐。至于天下大旱,以及占卜以为厉王为祟,则是有意神乎其事。周宣王即位和行冠礼时的年龄大概在二十岁左右,《春秋谷梁传·文公十二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范宁《集解》曰:“礼:二十而冠,冠而在丈夫之列。谯周曰‘国不可久无储贰,故天子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妇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书》称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礼·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则速,后是则晚。’”[21]又据《左传·襄公九年》载,晋悼公在卫为鲁襄公举行冠礼,并说:“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22]这里有两个细节应该注意,一是婚礼的年龄,有二十、三十之别;二是娶必先冠。婚礼年龄的问题,范宁说可灵活考虑。但于天子诸侯来说,因为涉及权力的承接,当宜早不宜迟。今人钱玄即主此说①钱玄认为王肃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之说较合情理。其原因是“当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法统治,希望早日有法定继承人,所谓‘欲人君之继体’,必然要以早婚早生达到这个目的。从为国富强考虑,也要求百姓早婚多生,增加劳动力,增加剥削收入,增加兵源。”见其:钱 玄.三礼通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81.。据此,周宣王在二十岁冠后不久,也应当很快就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史书和金文中虽无宣王举行婚礼之记载,但《小雅》中的《车辖》《鸳鸯》等诗,很可能与周宣王婚礼有关。首先看《车辖》:
间关车之辖兮,思娈季女逝兮。匪饥匪渴,德音来括。虽无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维鷮。辰彼硕女,令德来教。式燕且誉,好尔无射。
虽无旨酒,式饮庶几;虽无嘉肴,式食庶几;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鲜我觏尔,我心写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辔如琴。觏尔新婚,以慰我心。
《车辖》为《诗经·小雅》第五十八篇。“辖”本作“舝”,《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引作“辖”,今据改。《诗序》谓“《车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无道并进,谗巧败国,德泽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诗也。”陈奂《诗毛氏传疏》申论《毛序》刺幽王之意说:“盖周人历世有贤圣之配,今幽王宠嬖褒姒,立以为后,大臣知其将有倾城灭周之祸,故篇中语气,言不必若大姜、大任、大姒之贤圣,第思得‘德音’‘令德’之女以配我君子。已有歌舞喜乐之盛,犹无旨酒嘉殽亦足以解渴而解饥。此深恶王之黜申后而用褒姒也,故诗以‘虽无德与女’作一转语,而《序》则直谓之贤女耳。”[23]综合各方面证据来看,刺幽王说毫无根据,但陈奂以为咏大婚则是。只是《车辖》应当是咏周宣王大婚之作,诗末章点题说“觏尔新婚,以慰我心”,就是说思得贤女以配君子。
具体而言,此诗所咏当是婚礼亲迎仪式。林义光《诗经通解》解释此诗首章曰:“亲迎之礼,婿既往迎于女家,先归俟于门外,妇至而与之入。此诗末章云:‘四牡騑騑,六辔如琴。觏尔新婚,以慰我心’,则诗为婿至女家见妇后,驱车先归在途之语。故闻辖辖之车声而疑妇车之逮我也。诗为娶妇之辞,非嫁女之事。……‘虽无好友’,婿谦自谓也。”[24]所言极是。诗中还说“辰彼硕女,令德来教。”“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备言新郎谦逊而有令德,此断非幽王所能有,而与长于危难而负有使命之宣王身份及个性相符合。
其次,《鸳鸯》一诗也与宣王婚礼有关。《鸳鸯》是宣王大婚仪式上表达祝福的诗。诗曰:
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
乘马在厩,摧之秣之。君子万年,福禄艾之。
乘马在厩,秣之摧之。君子万年,福禄绥之。
《诗序》云:“《鸳鸯》,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万物有道,自奉养有节焉。”从《鸳鸯》一诗的内容来看,全是祝福,并无刺意,也没有借古讽今的意思,故后人多不信《序》说。朱熹《诗集传》就驳之曰:“鸳鸯,匹鸟也。毕,小罔长柄者也。罗,罔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诸侯所以答《桑扈》也……亦颂祷之辞也。”朱子否定刺幽王说,并以为是颂祷天子,极是。
何楷虽弄错了时代,但对此诗内容的解说却可取。其《诗经世古本义》云:“《鸳鸯》,美大昏也,疑为咏幽王娶申后作。”又云:“幽王娶申后当在未即位时,诗人追美其初昏时祝以万年之福。”[25]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皆从其说。诗之前两章以鸳鸯起兴,喻指夫妇婚姻。崔豹《古今注·鸟兽》:“鸳鸯,水鸟,凫类也。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思而死,故曰匹鸟。”可证诗中鸳鸯兴夫妇。诗之后两章言“乘马在厩,摧之秣之。”均是亲迎之意。诸家以此诗咏新婚,是正确的,但认为是幽王娶申后,则既于诗义无征,又与幽王多刺诗实际不符合。故陈子展指出:“疑是颂祝贵族君子新婚之歌”“取鸳鸯同游以兴男女之乐。乘马、催秣、在厩,以兴亲迎之礼,象征隐约,在可解不可解之间。”[26]结合历史背景来看,此诗应当是周宣王大婚时的祝歌。
另外,夷考诗文,其祝福之语如“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绥之”等,也与二《雅》中可以肯定的产生于西周中后期的诗篇如《鸿雁》《既醉》《假乐》,以及《周南》之《樛木》《汉广》等十分相近,当为宣王大婚之诗无疑。
还有《裳裳者华》一诗,也应与周宣王大婚仪式有关。诗人作此诗的目的,是极力赞美宣王有威仪。《裳裳者华》曰:
裳裳者华,其叶湑兮。我觏之子,我心写兮。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
裳裳者华,芸其黄矣。我觏之子,维其有章矣。维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
裳裳者华,或黄或白。我觏之子,乘其四骆。乘其四骆,六辔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维其有之,是以似之。
《诗序》以为这首诗“刺幽王”,但诗中表达的是作者对“君子”的赞美,从中看不出有讽刺的意味。故朱熹《诗集传》谓“此天子美诸侯之辞,盖以答《瞻彼洛矣》也。”说不同于《诗序》。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谓《裳裳者华》与《瞻彼洛矣》为臣与君互相酬答之诗,可能是周宣王时用于天子燕飨诸侯之际。今人孙作云亦认为:“朱熹《诗集传》云:‘此天子美诸侯之辞,盖以答《瞻彼洛矣》也。’知此亦为宣王朝诗”[7]378亦持此说。然而所谓酬答,只不过是因为《裳裳者华》在今本《诗经》中列在《瞻彼洛矣》一诗之后。诸家之说于诗义仍未达乎本旨。
细绎诗文,首章言“我觏之子,我心写兮。”末章言“君子宜之”“君子有之”等,应是言婚姻之事。据此知酬答之说不可信。今人王宗石认为:“《裳裳者华》极赞新郎能佐佑天子,为父所钟爱,要嗣位为君,指的可能是厉王的太子静(靖),后嗣位为宣王。今青铜器存有《静敦》《静卣》《静彝》诸器铭文均记宣王为太子时,随厉王习射学宫,静学无斁,王有赏赐。时宣王静已长成,这些诗当为其婚礼之贺词。……通篇表达了新妇对新郎极其满意的心情。”[27]依当时的礼仪,新娘子不可能作诗赞美其夫,诗很有可能是“代拟”。
还有《桑扈》,也应是周宣王举行大婚时,诸侯颂扬天子所作之诗。《桑扈》曰:
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为宪。不戢不难,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
《诗序》说是“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动无礼文。”殊为无据。故方玉润谓“不知所谓,不敢妄为附和也。”(《诗经原始》)郑玄《笺》释诗中“君子乐胥,万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为宪”,说诗中所赞颂者为“王者之德,乐贤知在位,则能为天下蔽捍四表患难矣。蔽捍之者,谓蛮夷率服,不侵畔。”“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难,内能立功立事,为之桢干,则百辟卿士莫不修职而法象之。”这与其说是赞颂,不如说是诗人的美好祝愿。故陈奂《诗毛氏传疏》于《桑扈》说:“君子,谓王者也。”[23]卷二十一,11诗中这位“受天之祜”“万邦之屏”“百辟为宪”的“君子”应当就是肩负周家中兴之大任的周宣王。李光地《诗所》认为《桑扈》是周天子朝会既毕而燕诸侯之诗。这种说法也与此不矛盾,大婚仪式,不可能没有燕享,在婚礼的宴会上,人们对新婚的君王给予最热忱的祝福,其实体现了当时王室内部大乱思治的共同愿望,这种愿望又全都集中在这位在冠礼和婚礼之后就登上最高权力舞台的周宣王身上,在诗句中出现的热切的祝颂,就是最好的说明。
这首诗作于宣王朝的另一个证据是诗中的用语如“交交桑扈,有莺其羽”“万邦之屏”“百辟为宪”等,与可以肯定的宣王朝之作《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六月》(文武吉甫,万邦为宪)等相似。
综上所述,周宣王朝的“中兴”,是通过对西周对内团结宗族诸侯和对外加强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而实现的。在此过程中,西周政权的基础,即宗法制度和封建诸侯的基本格局得到了重新巩固。与表面的政治手段相配合,“礼乐制度”的复兴和转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此期燕饮诗、战争诗创作的兴盛,就是礼乐复兴的产物。《頍弁》《假乐》是宣王冠礼仪式诗,《车辖》《鸳鸯》《裳裳者华》《桑扈》则是宣王婚礼仪式诗,它们也是礼乐复兴的背景下产生的。与《诗经》中的西周早期仪式乐歌比较而言,《頍弁》《车辖》既体现了仪式乐歌的功用,也在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具有很强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正体现了西周礼乐制度的转型对仪式乐歌创作的影响,也预示着西周诗歌向脱离仪式和突出个性的方面发展的总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