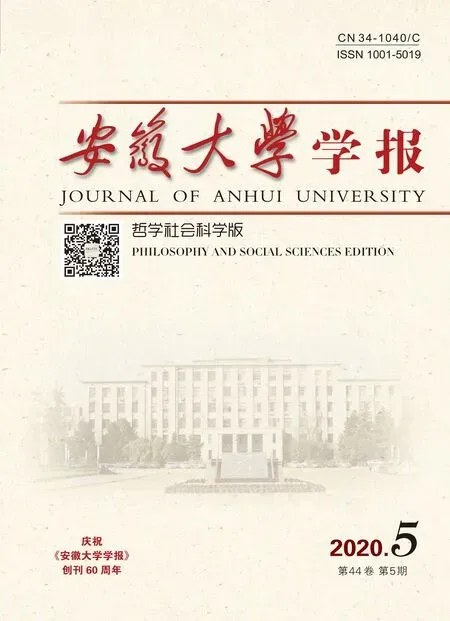清代小说中的海洋书写
2020-12-23马平平顾明栋
马平平,顾明栋
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中,长期流行一种观点,即中华文明是黄色的大陆文明,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明。轰动一时的电视纪录片《河殇》(1988)便奉该观点为圭臬,这一观点曾风靡一时且至今仍有一定影响。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汉学主义》一书中所批评的那样,对中西方文明的这种认知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话语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一种变体,是一种自我殖民和精神殖民的“文化无意识”转化为“有意识文化”的典型表现(1)顾明栋:《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中的认识论意识形态》,《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文化无意识:跨文化的深层意识形态机制》,《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研究模式并非仅仅是为了突出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差异,而是为了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黄色(中国)文明是落后和低劣的,而蓝色(西方)文明是先进和优越的;落后低劣的中华文明欲想获得新生就必须以先进优越的西方文明取而代之。该观点显然无视中华文明历朝所进行的大量航海活动以及对海疆的不断开拓与利用这一史实,亦忽略了再现中国历代征服海洋、远航探险的大量文学作品。仅以地理决定论来抹杀中西不同历史进程中的观念选择,以山与海来阻隔人的思维,这一行为或是对中西历史的无知甚或是刻意的误读(2)龚鹏程:《海洋文化怎样被土地思维的洪流淹没?》,龚鹏程大讲堂,2019-12-02取自https://mp.weixin.qq.com/s/v5uWU8xOlSnw0v-Mxgq8ZQ.。
中国传统涉海小说中的海洋主题和意象既有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基调和海洋观念,又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现实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古代的涉海文学是与古代神仙传说、宇宙观念等密切相连的文化符号(3)王立:《中国文学主题学:意象的主题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到了明清时代,西方殖民扩张直接冲击中国闭关自守的农耕文明,中国古代涉海小说也因之呈现出新的面貌,与前朝此类小说在主题、叙事、人物等方面有大不同。尤其是清代小说,无论是在数量、篇幅,还是在主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上都表现出巨大的发展与变化。明清海洋书写小说的繁盛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唐琰(4)唐琰:《明清小说视野中的海洋发展》,《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3期。从渔盐经济、海外贸易、港市和海洋群体四个方面再现了明清时期的海洋文化发展;范涛(5)范涛:《海洋文化与明代涉海小说的关系研究》,暨南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结合明代涉海小说兴盛的历史背景及明代的海洋政策,考察和分析明代通俗小说中所呈现的海洋文化。但是,现有研究大多驻足于长篇小说,对于《觚剩续编》《子不语》《挑灯新录》《淞隐漫录》等同样蕴含浓郁海洋气息和丰富海洋意象的短篇小说则关注不够。同时,现有研究对海上活动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海洋意识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缺乏足够的挖掘。
本文拟从海洋意识的自觉性、海洋活动的身行性和海洋意象的象征性三个方面,探讨在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背景下,清代小说海洋书写的迅猛发展和鲜明特征,揭示其背后所传达的强烈的海洋意识和浓郁的海洋情怀,例证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相兼容的复合文明。
一、海洋意识的自觉性
明末清初始,国人的海上活动日趋活跃,参与海洋文学创作的群体迅速增加。涉海小说的作者们力图挣脱“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大陆文明意识的长期束缚,他们的海洋意识开始由自发走向自觉,并且日益增强。这一时期作品中塑造的许多人物表现出与西方大航海时代相似的冒险精神,他们参与航海的动机更加积极明确,对海洋的认识不断深化,维护海权的意识亦明显提升。
(一)航海动机的转变
清代涉海小说延续了前代小说主人公的航海动机,或以探访仙山宝岛,搜寻奇珍异宝、灵丹妙药的猎奇目的为主,或欲通过泛海经商获取巨利。受道教思想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海洋观念一直崇尚对海外仙境的向往与探寻,现存的汉代小说大都“有浓厚的神仙道家色彩,都有求仙长生的内容”(6)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页。。清代作家的创作同样受此思想的影响,《镜花缘》中的唐敖科考受挫,功名无望,便决定“海外畅游,求仙访道,以求善果”(7)(清)李汝珍:《镜花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页。;《聊斋志异·海公子》中的张生也喜好游猎,敢于驾船探寻古迹岛屿。受海洋贸易巨额利润的诱惑,许多商人不惜冒险过海经商,成为巨富。如王谦光(《续子不语·浮海》)跟人一起走海经商,以十金为资本,初次到日本就赚了数十倍利润;杨百万(《连城璧》),靠漂洋起家,积累了丰厚家资;秦世良(《连城璧》)本为穷困潦倒的书生,他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态,跟着走番即下南洋的商客下海经商,历经九死一生后终于改变困境,发家致富。
但与前代小说不同,清代涉海小说主人公不再局限于纯粹的商人群体,众多儒生或因不屑于科举入世或因读书不得志而选择弃学经商,加入了航海人群。《聊斋志异·罗刹海市》中的马骥本为书生,后来听从父训(“数卷书,饥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儿可仍继父贾”(8)(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459页。),决定跟人一起走海经商。《镜花缘》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也都是由“儒”入“商”:林之洋进过私塾,因视岁考为“活地狱”,遂弃学从商成为贩海商人;多九公也曾拜过先生读过书,但屡次科举不中,于是弃学从商。这些人都能突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君子不言利”的传统观念,毅然放弃世人尊重的儒生身份,从事经商这一社会“末业”,甚至还冲破了海禁的桎梏成为海商。这类全新的人物形象含蓄地批评了清朝统治者“强本抑末”“闭关自守”的政策,表现出对海上贸易愈发普遍的认可与认同。
同时,清代小说中人物的航海动机也开始由“自发”向“自觉”发展。以王韬的《凇隐漫录》为代表,小说主人公们富有冒险精神,对海外世界充满好奇,主动投身海外游历与探险。《仙人岛》一篇中,泉州人崔孟涂爱好游历,当有机会登上一艘航海大船时,他便立即请求随船同行,开始他的海上猎奇之旅。《闵玉叔》中,闵玉叔特别向往书本中所描绘的海外奇境,每当遇到海外归来之人,都要向他们打听海上行程和异域风土人情。这些航海人亦“夸述瑰异,粉饰其词”(9)(清)王韬:《淞隐漫录》(卷三),上海:点石斋,1884年石印本,第7页。,令闵生更加神往。秋试下第后,同试世子邀约闵生一同回台,闵生欣然同意,实现了自己“乘风破浪”之素志。这些文学作品的记述,反映了清代国人主动了解海外世界、积极投入航海探险的热情;而这些作品的传播又进一步为海外探险推波助澜,加快了航海活动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型。
(二)海洋认知的深化
自春秋战国时代起,船只制造业日益兴盛,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进行海上探索。秦始皇时期,徐福就曾经率领船队深入东海和渤海,进行探寻活动。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唐宋时期,中国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十分发达。明代初期,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海外贸易的发展,促成了世界航海史的奇迹——郑和下西洋。通过这些海洋活动,人们对海外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但在这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作者笔下的海洋多为变异的世界,神秘而广博,如海中多有蓬莱、方丈、瀛洲这样的神仙居住地。
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国人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更清醒的了解,他们的航海诉求也随之日益强烈。因此,清代涉海小说中的仙话海洋、神魔海洋想象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海洋的现实认知。小说中的人物拥有更加直观的海洋地理认知,例如他们开始使用航海图来进行海上定位,以确保航行的安全。《淞隐漫录·仙人岛》中,崔孟涂乘坐的海船遇飓风漂流至一荒岛,船长“考诸图经,向所未载”(10)(清)王韬:《淞隐漫录》(卷一),第7页。。《淞隐漫录·闵玉叔》一篇也是如此,“舟师考诸图经,莫知其处。盖向来所未载也”(11)(清)王韬:《淞隐漫录》(卷三),第7页。。
同时,小说作者的海外想象也不再是纯粹的主观臆想,而是大多基于他们对海洋水域的现实了解。《淞隐漫录·仙人岛》中,崔孟涂思念居于仙人岛的妻子,希冀再次探访仙人岛。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舵手提醒他:“君殆痴矣!今时海舶,皆用西人驾驶,往还皆有定期,所止海岛皆有居人,海外虽汪洋无涯涘,安有一片弃土为仙人所驻足哉?”(12)(清)王韬:《淞隐漫录》(卷一),第8页。,也就是说这世上并不存在“仙人岛”,所谓的仙人只不过是由于对海洋无知而产生的臆想。《淞隐漫录·消夏湾》中,嵇仲仙每次遇到海客,都要询问海外风景,了解世界的版图。所以当“日东高僧”跟他谈起瀛洲、蓬岛、员峤、方壶等仙家胜地时,嵇仲仙完全不信,并以地理知识和航海知识与之辩驳,他认为:“按之东西两半球,纵横九万里,有土地处即有人类,各君其国,各子其民,舟楫之所往来,商贾之所荟萃,飚轮四达,计日可至,安有奇境仙区如君所言者哉。”(13)(清)王韬:《淞隐漫录》(卷十二),第11页。《北极毗耶岛》中孝廉到达的岛屿已经是大瀛海极北处。可见,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人们对于海洋异域的探索越来越广泛,海洋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人们对海外世界已经有了更加清醒客观的认识,这些认知在这一时期的涉海小说中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三)海权意识的增强
中国自北向南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岛礁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因此,无论是为了渔盐之利,还是海上贸易之利,中国人从未停止运用舟船探索海洋。同时,随着海洋探索的深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海上贸易安全逐渐受到重视。唐代以前运用舟船进行的海上贸易和海洋探索尚带有“初始、自发”的性质,当时的人们很难认识到海上军事行动对于保卫国家海航安全、维护海上航路畅通的重要性。因此,当时的海战和海防意识仍处于一种朴素、朦胧的萌芽状态。唐宋以后,海外贸易的发展让政府更加重视海洋防卫和海洋安全,“为保护海外贸易航道的安全畅通,宋代在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等主要港口的外围,设置多处兵寨,以‘控扼至要之地’”(14)黄顺力:《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第50页。。元末明初尤其是嘉靖以后的倭患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沿海人民的生命安全,封建政府进一步意识到海防的重要性。如明太祖为了防范倭寇,在福州、兴化、漳州和泉州四郡抽取壮丁一万五千多人,在重要位置“筑城一十六,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15)《明太祖实录》(卷18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2735页。,不仅构筑海防工事、加强戍兵,还添造各式战船。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七次下西洋的壮举以及郑和特混舰队的组建是明朝海上力量建设中最伟大的成就,也标志着中国海防思想的觉醒,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发展进入了高峰期。
除了倭患外,欧洲列强的海盗行为也在威胁着中国的海防安全。如葡萄牙人为了独占亚洲资源,在明中期来到中国近海,占据屯门岛,并以贸易为名,在广东沿海大肆抢掠,甚至和广东当地海盗勾结贩卖人口,大造火铳,劫掠村镇。嘉靖时期,明朝政府忍无可忍,派广东水师经过激烈海战,大破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成功收复屯门岛,将葡萄牙人赶出中国海域。明末清初之际,荷兰依靠强大的海上力量取代了葡萄牙,成为世界头号贸易强国。为抢占亚洲市场,荷兰也来到中国,一边从事商业贸易,一边干起了海盗的勾当,抢劫中国商船。天启二年(1622),荷兰进犯澳门,侵占澎湖。天启四年(1624),荷兰侵占台湾。此后,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1661)的30余年里,荷兰人以台湾为据点,从事贸易和海盗活动,妄图长期踞守台湾(16)[美]安乐博:《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1520—1810》,王绍祥译,《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进入清朝,海外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闽粤沿海地区海盗势力的不断壮大。闽粤地区因自身的地理条件并得益于清朝的海洋政策而成为清朝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但是“在清代前中期,闽粤沿海社会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严重;清朝吏治腐败,导致铤而走险之人多有”(17)刘平:《清朝海洋观、海盗与海上贸易(1644—1842)》,《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6期。,海禁和迁海政策更是让沿海百姓以商无赀,以农无产,流离失所,只能被迫为寇。同时两省不利于粮食种植的多山自然条件以及经济贸易发展造成的重商轻农之风导致缺粮现象严重。因此,最初海盗们只是为了解决生计温饱问题,抢掠活跃于南海洋面的米船,“但到了乾嘉之交,海盗动机发生了变化,其目的基本上以夺取财物为主,致使分散性的海盗逐渐结为海盗大帮”(18)刘平:《清朝海洋观、海盗与海上贸易(1644—1842)》,《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6期。。
面对海盗的侵扰、西方国家对海疆的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的海权、保护海上贸易航线以及沿海民众的安全,清政府同样采取了积极的海防措施。清初统治者加强水师建设,不断扩大水师规模,增加水师建制,水师编制也更加专业,如作为战船之一的鸟船“双战棚,两重炮位,器具重大……配水兵将百名,连战兵共有三百人”(19)(清)陈良弼:《水师辑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086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2~333页。。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海防的对象不单是以往的海盗、倭寇之类, 而是装备先进的西方强盗。清初将领施琅在强调台湾的重要性和荷兰列强的威胁时指出:“彼性狡黠,所到之处,善能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海外所不敌。若再得此地,必倡合党伙,窃窥边场,逼近门庭,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台湾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断断乎其不可弃!”(20)(清)施琅:《靖海纪事》,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第60~62页。
明清时期的海患(尤其是来自西方列强的海上威胁)同样也引发了文人们的担忧和焦虑,他们的作品也开始越来越关注这一现实话题。明清小说中的海洋意象孕育着中国的海防与海权思想。明代《天妃娘妈传》《八仙出处东游记》等小说中的海神四海龙王和妈祖履行着维护海上安全的职责,体现了中国最早的海权意识。他们是中国海疆的保护神,但他们并不好战、不好侵略,亦没有霸权意识。这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中拥有扩张与掠夺野心的海神波塞冬。《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的郑和率领规模庞大、实力强劲的舰队出使西洋,是为宣扬国威、传播中华文明、为海外诸国提供保护,而不是以强占他国、建立殖民地为目的。对于不愿意称臣进贡的国家,他们虽与之兵戎相见,却不侵占其领土。下西洋途中,三宝老爷对遇到的海盗多以教化为主,免其死罪,赐其财物,令其保证不再为盗;他同情那些为生计所迫、无奈为盗的番人们,并不严惩他们的行为。由此可见,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即使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对外政策仍以“德服海外”“安抚夷邦”为主,并不寻求霸占和殖民海外国家。
当国家海权遭到实际的威胁和挑战时,中国军队必当予以坚决反击。这一思想持续影响着我国的海权和海防意识发展,在清代涉海小说中有更鲜明的体现。首先,清代小说中海盗的形象更加密集出现,几乎所有涉海作品中均有海盗的身影。《海游记》第二回,笔商管城子乘船离开无雷国时遭到海盗侵袭,“见一船飞来,用火枪打我的船”(21)《海游记》,《古本小说集成》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14页。。《希夷梦》浮石等岛国的海滨岛民就有海盗的特征,他们一碰到外来船只,就会划艇上前,抢夺货物;第三十六回又提到沿海各郡邑海寇猖獗,荼毒百姓,他们“大肆荼毒,焚庐毁舍,淫女杀男,沿边郡邑遭寇酷虐之苦盛于地狱”(22)(清)汪寄:《希夷梦》,《古本小说集成》第二辑,第1855页。。《连城璧》中秦世良也在海上遭遇海盗,这些海盗本是海商,因遇到风暴而船货皆毁,就想再劫其他商船弥补自己的损失。《淞隐漫录·仙人岛》中,崔孟涂在寻访仙人岛时,“忽逢寇乱,盖发逆汪海洋由豫窜闽,漳泉数县,皆为贼窟”(23)(清)王韬:《淞隐漫录》(卷一),第8页。,其经历真实地描述了东南沿海海盗规模的庞大及其对沿海居民生活的影响。
其次,小说作者们开始将政府抗击倭寇、洋盗和国内海盗大帮的故事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他们对国家强大海防力量的怀念和西方列强渡海而来威胁国家海权的隐忧。小说《林兰香》中有数回描述了东海海面上闹海寇,朝廷点将剿匪的情形。彭倨、彭质、彭矫三兄弟横行东海,“沿海诸国,皆被患害。迩来渐渐侵入内地各镇,征剿屡受杀伤”(24)(清)随缘下士:《林兰香》,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53页。。朝廷震怒,决定兴师讨伐,主人公耿朗因此受命奔赴东海。海上剿匪首先要调遣适合海战的水师,小说中朝廷拥有庞大的水师力量,众将商议后,轻松集结了五万水师,“登莱水师三万有余,选其精者,可得二万。江淮各镇兵丁,内有明于舵梢者,可得三万。水师五万,亦足用矣”(25)(清)随缘下士:《林兰香》,第254页。。军舰也是海战胜利的保障之一,小说中中国的战舰船体结构坚固且航海性能良好,能够适应大规模海战。第三十六回,海上征剿三彭时,“中国的艨艟巨舰顺流而下,势若山崩,急如电转。贼船支持不住,被撞得七零八落,死伤无算”(26)(清)随缘下士:《林兰香》,第278页。。这些令人振奋的描述都表明作者海防意识的增强,他能深刻认识到只有国家拥有强大的海上防御能力,才能轻松肃清海上贼患,捍卫国家的海权。《台湾外志》更是非常全面地呈现明末清初之际政府为维护海上贸易航道的安全和国家海权所做出的努力。针对沿海海盗的猖獗,明廷首先对海盗头目郑芝龙进行招安。郑芝龙也积极响应招安,“愿充辕门犬马报效,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以赎其罪”(27)(清)江日昇:《台湾外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6页。。朝廷委之以海防游击重任,郑芝龙不负重托,当即统领海师将纠结渔船、劫掠商船的海盗李魁其剿灭。随后海盗头子刘香老焚劫明朝的海防基地小埕水寨,政府招安不成,郑芝龙又受命将其剿灭。在剿灭海盗刘香老一役中,小说详细描述了郑芝龙的排兵布阵之法。他将新旧船只分为三程,“第一程芝虎、芝豹为先锋,领船十只,快哨四只;第二程中军坐驾芝龙同卢毓英、芝鹏、芝蛟等,亦领船十只;第三程芝彪、芝凤、芝麟、芝豸、芝鹤、芝鹗、芝獬、芝鸾等,各领船一只为援剿”(28)(清)江日昇:《台湾外志》,第40页。。由此可见,郑芝龙非常熟悉海战,擅长海攻,有足够的能力为明廷守备沿海。当荷兰人依赖坚船利炮来犯闽、浙海域时,郑芝龙也展示了他的海战谋略。湄洲外洋中荷激战,刚开始荷兰人船只高大坚固,火炮厉害,令中方无计可施。后来郑芝龙决定以智取胜,利用小渔船灵活方便的优势,在船中灌满油,将船火速撑至夹板船边,点火燃着,实施火攻,成功击退荷兰人。
此外,台湾的属权问题也在清代小说中有所提及。《台湾外志》非常详细地交代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过程。荷兰人必即哩哥率领的夹板船队被郑芝龙击退后,荷兰人欲报仇,但其国王认为:“唐朝人物不少,未可恃勇。卿欲去,须相机于附近地方,先踞一处,安顿船只,收拾人心。”(29)(清)江日昇:《台湾外志》,第46页。于是,荷兰国王的弟弟揆一王便带着一众水兵,配驾夹板船十五只又来到中国海域,他们先来到台湾,见其中居民稀少,即侵占此地,修筑城墙炮台。郑芝龙之子郑成功不愿随其父降清,坚守东南,抗清北征后,退守厦门。他在审度形势后决定亲征台湾,历经近一年时间终于将荷兰人赶出台湾,中国人收回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宝岛。
因此,无论是史实记载还是清代文人的小说创作,都叙述了明清政府海洋防御的具体举措:发展水师,清剿海上倭寇和海盗,坚决击退海上来犯之列强,捍卫海洋领土。这些举措印证了清朝海防与海权意识的明显发展。
二、海洋活动的身行性
中国古代海洋文学中的海洋描述多以置身其外的“遥望”为视角,难以全面反映中国古代的人海关系。事实上,“还有一种‘进入海洋’的努力和实践的历时性存在”(30)倪浓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与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年,第877页。,即以“身行性”的视角,通过身临其境的海洋活动描述,呈现丰富且复杂的海洋意识。明清之际,虽然封建政府的海洋政策、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安土重迁”的观念仍限制人们积极投身海洋贸易实践,但海上贸易的利益驱使和海洋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使明清尤其是清代小说中的海洋描摹逐渐从“遥望”转向越来越多地强调海洋实践和海洋经历。小说人物们在海上航行并应对海上风暴,于海岛遭遇岛人积极求生,通过海上奇遇和海上贸易获利,这些书写都极具身行性特征。
(一)海上航行
中国的文人们的确鲜少有真正的航海经历,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远洋商客的见闻传说作为现实依据并结合大海的仙话原型进行创作。那些亲历亲见海洋的舟人贾客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海洋中拼搏谋生,他们自然期望自己能够得到海神及其他神祗的护佑,平安完成航程,因而他们在描述航海经历时不免会有充满仙话和神魔化特征的夸大渲染描写。但是明清之际,郑和七下西洋的大规模海洋实践证明了明代航海事业的发达,促进了海上对外交通的繁荣,民间海上贸易在海禁政策的压制下仍然呈上升势头。航海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也促进了海洋文学创作。明清小说中的涉海作品迅速增多,描写手法更加写实,具体生动地反映多种涉海活动,塑造了许多涉海人物,展现了人们在海洋实践、海洋探索方面的新发展。
与前代小说相比较,清代涉海小说对海上航行的描绘更加简洁写实。多篇小说在描写海上航行遭遇飓风时,多用白描手法,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不是带有浓重神魔色彩的虚化描写。《聊斋志异·夜叉国》中胶州姓徐的海商在海上遭遇大风,所乘海船只能任风吹去,飘到了卧眉岛。《北极毗耶岛》中道光某孝廉京城科考落第,从天津乘海船回乡,在海上“遇飓簸荡舟覆,舟子尽丧鱼腹,惟孝廉抱一朽木随风播扬,不知几千里”(31)(清)宣鼎:《夜雨秋灯录》(卷四),上海:申报馆,1877年铅印本,第39页。,后抵达一海岛。
在面临各种困境时,小说主人公因具有丰富的“身行”经验,故能更加冷静应对。《连城璧》中秦世良第一次出海就遇上了海上风暴,水手反应很快,他们分工明确,有的忙着落篷,有的忙着摇橹,将船及时驶进一个岛内。后面没有来得及反应的船倾覆了好几只。《海外美人》中,陆梅舫和妻子乘海船第一次出洋,“既入大洋,飓风忽发,船颠簸不定”(32)(清)王韬:《淞隐漫录》(卷四),第17页。,但是通过多年与航海人的交流,他非常了解海上航行的特点,表现得十分镇定,“命任其所之,冀逢异境”(33)(清)王韬:《淞隐漫录》(卷四),第17页。。《淞隐漫录·消夏湾》中,嵇仲仙在日本海滨看到一艘邮轮,游兴遽发,不顾别人的阻拦就整装登舟了。出发三天邮轮遭遇飓风,“狂飚掀天,怒涛卷地”(34)(清)王韬:《淞隐漫录》(卷十二),第11页。,而嵇仲仙却并不害怕,他感叹道:“此真所谓乘长风破万里浪矣!”(35)(清)王韬:《淞隐漫录》(卷十二),第17页。他甚至爬上舵楼,“翘首远望自若”(36)(清)王韬:《淞隐漫录》(卷十二),第17页。,连船上的外国人都很佩服他。这是中国古代涉海小说海上航行描写的一大进步。可见,人们不再“谈海色变”,总是沉浸于对海洋暴风雨的无尽恐惧中,而是通过海洋实践来增进对海洋的了解和认识,正确对待海上自然现象,真正达到“天人合一”。
(二)海岛奇遇
清代涉海小说中,面对未知的海洋世界与危险,航海者往往不再是被动接受、等待救援,而是主动探索、寻找出路。《子不语·人熊》中,浙江海商与二十多人结伴航行,途中因飓风被困人熊岛,遭人熊猎食。人熊用长藤将人耳逐个穿通了绑在树上,众人唯有等待时机,趁人熊放松警惕后,用所配小刀割断长藤逃回船去。可见,这些误入岛屿的中国人在被岛人囚禁时并没有始终沉浸于对海洋的敬畏和恐惧中,束手待毙,而是努力设法逃生。他们甚至敢于打破常规,大胆冒险,主动挑战危机。《挑灯夜录·海熊》中,戍台军士钱堂等五十余人因遭飓风被吹至一荒岛。岛上有一巨人“海熊”,以人为食,钱堂等人虽十分惊恐,但他们知道只有杀死海熊才能真正安全,于是他们趁海熊饮血已醉,各拔出所带腰刀,合力杀死了巨人。
小说人物的主动探岛意识较前代小说也是一大进步。《淞隐漫录·仙人岛》中,崔孟涂入岛后,被岛上的美景吸引,不料“夕阳既落,狂风又作,舟不胜风,随其漂去”(37)(清)王韬:《淞隐漫录》(卷一),第7页。。这时他十分慌乱,以为肯定要葬身异域了,但是求生之本能让他不得不开始探索岛屿,弄清自己的处境。他“拟裹粮以穷其境。攀萝扪葛,直跻山巅,举目远瞻,则弥望沧波,浩渺无际,俯视山腰,缕缕有炊烟腾起,林木杳霭中,隐隐有庐舍”(38)(清)王韬:《淞隐漫录》(卷一),第7页。。这样的叙述与之前的误入海岛便遭遇鬼怪或遇到仙人有所不同,更具有真实感。主人公们被困海岛时能面对现实,通过探索岛屿了解自身处境,他们敢于冒险,积极寻找逃生方法,反映了人们主动自觉的海洋探索意识和精神。
不同于中原人的海岛居民,小说中的海外岛人形象多为仙巫鬼怪或吃人肉的野人、巨人。虽然在作家笔下,这些岛人形象仍不脱神魔化特征,但是对岛人生活习性的描写仍能反映清代人们海洋视野的开阔和海洋探索范围的扩大。岛人们并不是总居于山洞或者栖于树上,《聊斋志异·夜叉国》中,“卧眉国”夜叉以山洞为居所,而另一岛屿“毒龙国”上的夜叉已经开始有房舍居住,说明各海岛原住民的文明发展程度并不一致。清晚期小说中的岛人形象愈加现实化,《淞隐漫录》中多篇小说提到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海岛居民,较之前作品中的野人鬼怪形象有了很大突破。《闵玉叔》中,闵玉叔在海岛遇到一童子,“肤黑发鬈,其状如鬼;语又啁啾不可辨”(39)(清)王韬:《淞隐漫录》(卷三),第7页。。《海外美人》中,陆梅舫在周游海外时见到了很多外国人,有日本人、欧洲人、地中海美女等。他们的形象也从被妖魔化的形态拓展为更趋于现实的人物形象。跨出国界的中国人,开始接触和认识海外存在的其他国家。文人学者们也将这种新的世界观通过作品表现出来,拓宽国人的地理观念。
不仅岛人的形象描写趋于现实化,海岛环境描写同样更加世俗写实。毗耶岛(《雨夜秋灯录·北极毗耶岛》)“嵯峨怪石。石隙古树大参天,树根缕缕若藤萝穿石达而拖于水”(40)(清)宣鼎:《夜雨秋灯录》(卷四),第39页。,完全是现实岛屿该有的风貌。《淞隐漫录·闵玉叔》中也有类似描写,海船飘至岛屿后,船上人“相约登岸。行二三里许,杳不见一人。途径荦确,林树蔽亏,以远镜踞高窥之,并无庐舍”(41)(清)王韬:《淞隐漫录》(卷三),第7页。。这些海岛描写与此前的海岛仙话描述或者草木凋零的荒岛描述大相径庭。
(三)海上获利
“重利”是海洋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与前代作品一样,海洋寻宝主题在清代涉海小说中反复出现,不仅奇幻寻宝的篇目数量较前代增多,且寻宝诸篇多以下海经商后海中或海岛寻得珠宝为主。《觚剩续编·海天行》《聊斋志异·罗刹海市》《聊斋志异·夜叉国》《谐铎·鲛奴》《淞隐漫录·仙人岛》等数篇中主人公皆从龙王、龙女、夜叉、鲛人、仙人等海洋仙怪那里获赠海中宝物。明清时期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往往使普通人无法实现理想抱负,无力改善生活环境。清代小说再现这类人群时,常为笔下人物设想出路:他们或受海洋神灵护佑或海外探险得宝,在外力帮助下改变窘迫现状。
清代小说中的海洋寻宝故事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主动性、现实性。如《镜花缘》第十三回,下海“取参奉母”的廉锦枫为报答唐敖恩情,亲自下海杀海蚌取明珠赠予唐敖。《淞隐漫录·闵玉叔》中闵玉叔在海中墟市得宝的方式已不是获赠,而是在“宝山”俯拾。这些海洋实践得宝故事表明,人们对于海外的理解已经不再是寻找仙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物,也不是遥望着感叹海外番邦众多闻所未闻的宝物,而是积极参与航海活动,取得海外宝物换取财富。
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清代涉海小说中的海商更加胆大心细、富有远见卓识,其形象突破了“施好行骗、重利轻诺”的传统形象,成为“‘忠厚甚’‘平心甚’‘不酸’的好人”(42)舟欲行:《海的文明》,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175页。。《镜花缘》中,商人林之洋通晓海外商市,能够根据市场需要配置商品、调整价格,代表了乾隆、嘉庆时期勇于进行海外贸易的商人形象。而林之洋关照亲人、忠于妻子与家庭的品质突出了他重情重义,讲究礼义道德的仁人君子形象。
海外贸易活动在清代涉海小说中有了更为全面且生动的描述。关于海上贸易市场的描述虽不脱海中蜃市的仙话想象,但从中依然可窥见当时中国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的频繁和海洋贸易的发展。《聊斋志异·罗刹海市》中的海市竟然吸引了“四方十二国均来贸易”(43)(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463页。。《淞隐漫录·闵玉叔》中的海中“趁墟”,即赶集之日,吸引了世界各国海商前来交易,“市场周围约数十里,各国之人麇至,虬髯侠客,碧眼贾胡,无不出其中”(44)(清)王韬:《淞隐漫录》(卷三),第8页。。
贸易行期和地点的不确定特征使明清时期海外贸易获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清代小说中的海商们已经能够根据自己的贸易经验和对海外贸易的合理性及其规律的一定认知,开始摸索根据市场信息配置商品的互市手段。《镜花缘》中林之洋一行就是根据海外各国市场需要来配置货物,比如淑士国的读书人多,就以货卖纸墨笔砚为主;巫咸国人不识养蚕制茧之术,就以贩卖绫罗绸缎为主等。这些交易场景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嘉庆时期的沿海商贸往来,是对当时经贸发展的有力刻画。但是,当时的封建主义经济严重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文学无法脱离所处时代的影响,作者的思想也不可能超越时代而独立。因此,“这种海外贸易还处于萌芽阶段,是不成熟的贸易”(45)陈松喜:《一部反映清代海外贸易信息的佳作——〈镜花缘〉》,《图书馆论坛》2004年第8期。。
此外,清代小说中还出现了海商造船出洋的描述,再现海商们为了入海经商所付出的不懈努力。明清两代政府对海洋的积极作用认识不够,对海外贸易防守过严而不知进取,将出海谋生、谋求发展的海商看作异己势力,对于民间出海船数、船制、人数、规模等都有诸多限制。清政府担心远航大船走漏到外洋,便禁止民间私造,如福建省曾经制造的利于远航的头船就是因为“易滋偷漏”而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被当局下令“永禁制造”(46)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这导致中国的船舶制造后来远远落后于西方,严重影响了民间造船业的发展。即便如此,中国民间海商仍然活跃在海上,他们驾驶双桅船,携带货物,逐利东西洋。清代涉海小说《觚剩续编·海天行》中,海述祖为圆其航海经商之愿,不惜“斥其千金家产,治一大舶。……治之三年乃成,自谓独出奇制”(47)(清)钮琇:《海天行记》,见张潮辑《虞初新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9页。。海述祖还与濒海商客三十八人合作,将大船舱位租借给他们贩运货物,在海外各国互市。小说中海述祖能够冲破海禁,率先造船并且为其他海商提供租赁服务,说明作者对民间海洋事业的认可和支持。
三、海洋意象的象征性
自先秦以来,海洋作为审美对象,一直是文人们情感寄托、哲学思辨的载体,他们依托诗词作品在神秘莫测的海洋中驰骋想象,创造出诸如“海槎”“海外仙山”等独具审美内涵的意象。这些海洋意象承载了许多象征性意义:宽广胸怀、离情别愁、忧戚感怀、避世之欲等。而进入明清尤其是清代,西方文明的涌入、资本主义的萌芽、海上力量的发展、海外商业的需求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皆带来了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视野的开阔。因此,与传统的海洋意象相比较,清代作家笔下的海洋更具时代特征,更具丰富的象征意蕴。在海洋意象中,现在的海舶成为文明技术之进步的象征,海上社会成为讽喻现实的镜子,海岛成为逃避现实的场所。
(一)海洋是展示文明进步的舞台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对外开放。随着西方文明大量涌入,中国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封建王朝加速衰亡没落。“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汇点上的晚清文人, 经受动荡和碰撞的历史断裂硬伤, 在彷徨徘徊的价值视野里寻找思想的终极皈依, 其自身负载之重、震撼之烈、洗礼之深可想而知”(48)王达:《沉沦与超越:晚清文人的思想立场》,《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正视自身发展的不足和西方先进科学理念的优势,决定通过远行天下、游历四方来寻求拯救国家的机会和良方。文学作品则是他们抒怀壮志的理想平台,因此以王韬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开始在作品中表达走向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此类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当时来说却难能可贵。它们表现了作者执着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有振聋发聩之功”(49)汤克勤:《论王韬的文言小说创作》,《蒲松龄研究》2007年第1期。。
《淞隐漫录·海外美人》中,陆梅舫决定造船出海。在商讨造船细节时,所有的舵工都赞同直接购买西方轮舟,毕竟西船在当时技术先进,能保证“绕地球一周而极天下之大观矣”(50)(清)王韬:《淞隐漫录》(卷四),第17页。,说明国人已经开始接受西方科技发展领先中国的事实。然而接受并不代表他们对中国的造船技术完全否定,毕竟郑和下西洋时国家空前强盛的船舶制造能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并始终缅怀。小说中陆生不同意直接购买西船的建议,他认为:“自西人未入中土,我家已世代航海为业,何必恃双轮之迅驶,而始能作万里之环行哉?”(51)(清)王韬:《淞隐漫录》(卷四),第17页。但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也没有完全摈弃,而是“师其所长”“借法自强”,用中国的传统造船技术和传统理念结合西方的现代先进技术自建一艘海船。海船“船身长二十八丈,按二十八宿之方位;船底亦用轮轴,依二十四气而运行;船之首尾设有日月五星二气筒,上下皆用空气阻力,而无藉煤火。驾舟者悉穿八卦道衣。船中俱燃电灯,照耀逾于白昼”(52)(清)王韬:《淞隐漫录》(卷四),第17页。。小说主人公对技术文明的肯定和追求,表达了作者对中国造船技术曾经显赫一时的怀念,也说明作者希望通过“师夷技”来振兴中国的航海事业,反映了由陆地向海洋观念的转变,体现了中华农耕文明渴望拥抱大海、走向世界的近代海洋意识。
(二)海洋是影射现实的镜子
海洋是影射现实的镜子,清代涉海小说作者们借助对海外国家和海外人物形象的遐想讽刺时事、抨击政府和时弊、表达社会理想。他们通过对海外国家颠倒之行的描写揭露官僚体制的腐朽、科举制度的黑暗、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以及人情世态的丑陋。《罗刹海市》中的岛国人人都以丑为美,以假面来迎合世人。《谐铎·桃夭村》中的岛国男女婚配科场腐败不堪,贿赂盛行。《谐铎·蜣螂城》中岛人以臭为香,与中原习俗颠倒。《常言道》中的小人国国民重财轻文,为了金银钱草菅人命,无所不用其极。《镜花缘》中的海外诸国更是社会弊端和丑陋现象的集大成。白民国和淑士国的冒牌儒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靖人国、两面国、无肠国等国人心性丑鄙、寡情薄义、贪婪吝啬。《淞滨琐话·因循岛》中的海岛被能够幻化人形、食人膏脂的“衣冠狼”所霸占,他们盘踞衙门重要职位,靠阿谀奉承、贿赂上司得以加官晋爵。这些海外国家的国人形象的塑造完全悖逆了五常和八德的要求,表达了小说作者们对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封建官场和尔虞我诈、苞苴盛行的现实社会的否定。
同时,小说作者们还通过对海外国家的乌托邦式描写来表达他们对理想世界的渴望。如《续子不语·浮提国》中的浮提国,《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大人国、轩辕国和黑齿国等,这些海外国家皆民风淳朴:他们有的门户不闭,却“从无淫乱窃取之事”(53)(清)袁枚:《续子不语》,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四册),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7599页。;有的好让不争,言谈举止恭敬有礼;还有的以才取人,以德为先。
上述海洋讽喻方式是海洋在民族文化中的内涵体现,是对中国传统海洋观念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发展惯以向内聚敛为特征,关注现世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和协调的现实精神。因此,在对海岛和海外国家人物形象进行异化处理时,清代小说作者们的遐想都不会超出封建道德准则的范围。在依托海岛或者海外国家的描绘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社会理想时,他们的视角始终无法脱离封建传统的束缚,对海外国家的想象仍旧是以中国政治和文化制度为参照,表达了“以夏变夷”、秉承传统的大一统思想。
(三)海洋是逃避现实的场所
中国文化主流强调入世观念,大多数中国文人的理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积极关注社会人生。但是当理想受挫,他们又往往转而独善其身,海洋遂成为他们逃避世事、寻求解脱的心灵寄托。
社会制度的黑暗和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在清代文人心中造成了强烈而持续的焦虑和困扰。他们虽愤懑不平,但是历史的局限和作家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及思想认识的局限却阻碍他们找到疗救社会、改变世风的真正出路,于是他们同样将目光转向大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小说中表达入海避世的渴求。仙人岛(《淞隐漫录·仙人岛》)“空旷无居人。稍进,则有石洞石室,几榻炉灶毕具,炉旁尚有零星木炭,似不久有人炊爨者。风日晴暖,气候温和,殊不类蛮峤。两旁皆溪涧,泉流碎石间,喧声聒耳。涧上皆忍冬花,藤蔓纠结,黄白相间,其香纷郁,爽人心脾。花多落于溪中,故其泉甘冽异常”(54)(清)王韬:《淞隐漫录》(卷一),第7页。。如此世外桃源之境让崔孟涂怀疑入了仙境,他不顾同伴的劝阻,毅然决定回船取被袱,在岛中山洞过夜。《淞隐漫录·消夏湾》中,嵇仲仙在航海途中不慎被大风卷入海中,漂至一岛屿。岛上风景清幽,“松柏参天,柳榆夹道……林鸟啁啾,山花芬馥,树头果实累累”(55)(清)王韬:《淞隐漫录》(卷十二),第12页。。岛上还住着一位林姓隐士。在这些小说中,海洋异域不再是鬼怪丛生的骇人之域,亦不是无须食寝、让人长命百岁的神仙居住地,而是有人居住的、能让人有隐世之欲的风景胜地。说明海洋的神魔性和变异性书写逐渐随着人们海洋视野的开阔、人海关系的亲密而趋于现实化发展,海洋作为人们心中的隐世之所,不再是引起疏隔之感、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而是更加世俗化和现实化的世外桃源。
四、结 语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同时也给清代涉海小说添加了新的维度和发展空间。与明代涉海小说相比,清代涉海小说神话色彩更加淡化,现实的冒险精神更加增强,“神魔”的海洋随着人们更加频繁的海上探索和海上贸易而渐渐趋向“身行”的海洋和现实的海洋。其海洋书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人们通过海上航行,积累航海知识,认识海外世界;通过抗击海盗和外侮,加强国家海防,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通过海外贸易获取财富,了解海外市场信息;通过对海外世界的想象,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危机所产生的焦虑和思考、幻想和抗争,寄托建立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海洋小说不同,在清代小说中,海洋并不是竞争、殖民和霸权的场地,其海洋书写在“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更加注重“和谐”“恕道”与“共生”。这种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延续和拓展,是大陆文明向海洋的延伸,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并非必然相互冲突,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而是可以相互兼容,共生共长。因此,中华文明不是单纯的与海洋文明相对的大陆文明,而是兼容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复合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