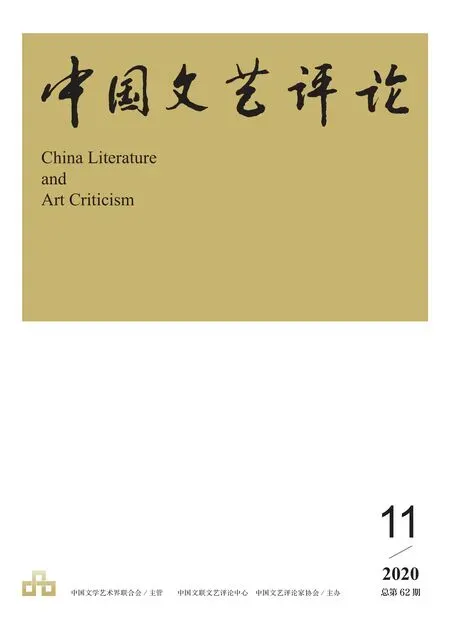古调仙声:广东汉剧艺术家李仙花的旦行表演艺术
2020-12-22王馗
王 馗
一、广东汉剧艺术传承发展中的李仙花
作为清代以来进入岭南的“外江戏”的遗存剧种,广东汉剧与孕育成长于江汉平原的湖北汉剧等剧种同源一脉,是皮黄声腔在岭南地区流传颇广的一个剧种。随着清代以来客家人族群意识的发展,广东汉剧被看作闽粤地区客家人的代表性剧种,广泛地流播于海内外客家人的生活中,与广府人传承创造的粤剧、潮汕人传承创造的潮剧,并列为广东三大剧种。作为广东汉剧的当代领军艺术家,李仙花得到广东汉剧名家梁素珍的亲传,并广泛地向京、昆大家求学,系统全面地掌握了广东汉剧旦行表演艺术的精华,不但于1993年成为广东戏曲界中第一位获得梅花奖的女演员,而且于2000年成为广东戏曲界第一位二度梅花奖获得者。李仙花在广东汉剧经典剧目和新创作品《蝴蝶梦》的表演中,技艺日臻成熟,之后不断地通过新创剧目如《白门柳》《金莲》等,将广东汉剧革新之路予以延伸,积极推进了广东汉剧在新世纪以来的传承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广东汉剧从偏居一隅的梅州,逐渐地在全国戏曲大舞台上产生艺术影响。
成功的戏曲创造必须基于对传统的掌握。李仙花对广东汉剧旦行表演艺术的推陈出新,来自于长期在基层的艺术演出与舞台磨砺:10岁进入梅州戏剧学校学习,之后进入广东汉剧院一团工作,经过20年的继承与创作,掌握了广东汉剧旦行艺术的丰厚遗存。广东汉剧中的《百里奚认妻》《打洞结拜》《丛台别》《齐王求将》《林昭德》《盘夫》《贵妃醉酒》《宇宙锋》《状元媒》《秋胡戏妻》《玉堂春》《西厢记》《十五贯》《别洞观景》《审头刺汤》《王昭君》《徐九经升官记》等传统剧目、移植剧目,《包公与妞妞》《花灯案》等新创剧目,以及《园丁之歌》《一袋麦种》《半边天》《苗岭风霜》等现代戏中的女性形象,都被李仙花演绎和再现。丰厚的艺术积累和舞台实践,不但让她多元地把握了花旦、青衣、武旦等旦角行当,而且在广阔的艺术舞台上,取法京剧、汉剧艺术正统,来提纯广东汉剧的艺术内容。她在中国戏曲学院求学期间,向京剧名家宋丹菊老师学习《改容战父》,在椅子功、翎子功、云步、圆场等技法的娴熟把握下,用高难度技巧的前探海、穿椅僵尸下腰、勾椅等动作,塑造出万香友这个将门之女的艺术形象,柔情似水而又英气逼人。她和王小蓉老师挖掘整理的《阴阳河》,复原传统的扁担功,通过肩、颈、手对于担子的平衡控制,将唱、做、表、舞的综合表演熔为一炉,成功塑造了游走在阴阳两界的李桂莲形象。同时她向昆曲名家梁谷音、沈世华等参学,转益多师,技艺日进。特别是1993年获得梅花奖之后,她进入首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学习,成功创作演出广东汉剧《蝴蝶梦》,并且与京剧名家李宏图携手,探索“京、汉两下锅”的形式,以京剧与广东汉剧同台合演《蝴蝶梦》,在京剧严谨规范的艺术体系观照下,凸显广东汉剧艺术的古朴风格,也进一步淬炼广东汉剧的舞台语言、表演范式。这种深挖京、汉传统而扩容剧种艺术体量的实践,是所有杰出的戏曲艺术家共有的成功之道,也是最能体现戏曲艺术有序传承的成功之法。

图1 李仙花在广东汉剧《宇宙锋》中饰演赵艳容
二、李仙花在《蝴蝶梦》中的创造与突破
毫无疑问,《蝴蝶梦》是广东汉剧里程碑式的作品,李仙花通过她对旦行艺术的成熟驾驭,精美地完成了对这部作品的华丽表达,也让这部被其他剧种展示过的剧目以及这个被众多剧种演绎过的题材,达到了至美至高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戏曲在化腐朽为神奇的题材转化中的一部精品代表作。
《蝴蝶梦》美在何处?高在何处?当然离不开剧作家的文本创作。盛和煜先生以鲜明的剧诗风格,将历来横加在该题材女主人公田氏身上的所有道德教条,进行了自我反观和外部审视。剧中的庄周因为少妇扇坟,萌生了对妻子田氏的试探,一个从心而起的念头,通过自身死亡的方式,幻化出了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道法自然的庄周用最不自然的方法,试探出了自己人性里最不自然的行为悖论。而心如止水的田氏在楚王孙的温柔照拂下,萌生了对于男性更加丰富的体认,为了营救病急的楚王孙,一把利斧劈开了庄周的棺椁,劈醒了自己出于生命本能的自性追求,同时也劈醒了庄周看似恬淡超然的道德伪装。人性的天然状态本该就在鼓盆而歌中走向彼此自立,但却在瓦盆骤然的破裂声中,呈现出了田氏、庄周彼此相对、却又走不出夫妻伦理道德束缚的尴尬与无奈。
剧中的扇坟少妇与劈棺田氏,生活环境有很大不同,生活定位亦有很大不同,但同为女性,同有女性的欲望与追求。剧中翩翩楚王孙与巍巍庄夫子,本身就是庄周虚实幻化,互为影像,又各为表里,他们在人性相通的认知中,既走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选择,也呈现出个体对于自我与世界共有的自觉自省。当然,剧中的庄周与田氏同样互为影像,在人之为人的生存本性中,虽然男女殊途,但却经历了自我蒙蔽、自我发现与自我觉醒,他们面对道德伦理,既想独立而又难以摆脱彼此羁绊的困惑,正是剧作家对于时代转型之间的男女关系至为真实、至为深刻的剖析。在这部作品中,不会因为田氏由人性的蒙昧到清醒,而给予她“女权主义者”一般的标签;也不会因为庄周从哲理的证悟到沉沦,而给予他“封建夫权”一般的批判。相反,剧作以最大限度的生命认知,将这种男女关系上升为对于人所依存的文化困境的一种隐喻表达,既展现着生命本能意志突破文化限定而进行的自我挣扎,同时也展现着文化个体无法逾越道德身份标识而付出的生命代价。
因此,剧终之时,随着田氏与庄周的相互审视,相互告别,在彼此回望而又决然离去的时候,那个瓦盆突然破裂喊出了一声“咦”,将人性中的情、欲、理之间分不清理还乱的状态,做了最具调侃、也最具理性的质问。当观众在完成剧场审美后,对着这一声质疑,走出剧场进行不停的讨论时,这部具有深度艺术哲思的作品,其实早已超越了戏曲娱乐欣赏的边界,走进了普通观众的生活中,走进了他们进行生命自我观照的精神拷问中。这正是广东汉剧《蝴蝶梦》从剧作家那里获得的最具现代质感的审美高度,这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戏曲致力于人性主题的表达中,用纯粹的艺术形象与戏曲创造,对一个时代的文化命题进行的高级回应,它显然超越了传统戏中的“大劈棺”,也超越了这个题材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进行的诸多改创。
在《蝴蝶梦》中,李仙花一人分饰两角,几乎不露痕迹地呈现出了两个个性、气质与命运走向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在《扇坟》一场中,以花旦应工的扇坟少妇,在一悲一啼间,始终透露着女性本来的娇媚柔美。那种纯然天成的个性,在她初次出场时,通过细密轻蝶的云步和静若玉山的身段,展现出一种袅娜与自信;而一把纨扇间闪出的窥视与观望,又以俏丽的神采,活脱脱地流宕出女性不可遏止的天性与洒脱。因此,在一席孝服的包裹下,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以人性本真的状态,展现着属于她的天然之美。在汉剧音乐的行弦伴奏中,李仙花通过手、眼、身、步的移转,在鼓板的节奏中,在一把纨扇的舞蹈中,以无声的造型变化,塑造出了不因身世凄凉而有所改变的青春女性形象。这段出场表演在【西皮导板】“快步匆匆往前赶”之后,以极尽渲染的做工,转接到了【西皮二六】“青春佳人着缟素。往日郊外来踏青,今朝执扇在坟头”,在面对孤坟而喊出的“夫啊,你撇得奴家好苦啊”的叫板后,唱出了旋律优美的【西皮原板】“原以为恩爱夫妻偕白首,谁料想你半路之上把我丢”一段唱腔,将遵守伦理捆绑而人性难以收束的气质特征,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在短短几分钟内刻画出了扇坟少妇经历失偶后对于人生寄托的所思所想、所怨所盼。
在庄周帮助她扇干坟土的前后,她从稍显庄重沉郁的状态中,通过逐渐熟络的沟通,以佻达的语气询问庄周是否需要续弦,并且取笑他“家中有一个扇坟的”。此时的李仙花只是通过身形的半蹲与侧转,在眼神顾盼轻瞟之间,就完成了她对于世理人情的感通,以真实的生活情态来展示少妇不可遮蔽的女性情态。而后面对扬起的干燥坟土,在短暂愣神之后,以眼珠快速的左右转视,既表示清理尘土后的生理反应,也传达出心理期待骤然实现后的放任与欣喜。此时的她单手扯下翘起的孝鞋,在灵动的身姿翻转中,除去头上的孝带,并用花旦特有的耸肩抽袖和花梆子碎步,通过在台口的两次表演,展现出少妇欣喜过望后的轻狂和放浪。
这种通过花旦行当的特有程式来塑造人物的方法,固然是对传统青春女性的一种普遍表达,但在这一系列轻巧圆熟的表演后,随着少妇即将走入台后时,突然间回身面向庄周深深叩拜,深情郑重地喊出“多谢先生”,并以悲情的起身和具有力量感的欠身动作,表达放弃既往生活后的释然,这就呈现出了这个少妇深沉的情感基调,显示出与同龄女性完全不同的身份背景。而面对庄周递过的纨扇,她微笑地一推,马上转身回视,在由慢渐快的脚步挪移后,以快碎步带动两手虚拳的抡转,展现少妇奔赴新生活时自由而急不可耐的状态。极其夸张的动作,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生活情态,而将其内心世界通过动作做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应该说,同一个少妇,在李仙花动用花旦技巧来塑造的时候,或者取诸生活,或者诉诸夸张,都始终围绕着少妇在扇坟前后过程中的不同情感状态,游刃有余地实现了这个人物在个性气质上的渐次变化。这种适用行当而又契合人物生命动感的表演方法,显然让具有模式化倾向的行当艺术,真正化在了演员身上,转变成为具有人性韵律的动态形式,达到了演员、行当与形象的相融无碍。
李仙花通过对扇坟少妇的创作,将花旦行当表演赋予了丰富的人性表达,显示了她对青春女性完整的个性把握,也超越了花旦行当技术层面的程式规范。

图2 李仙花在广东汉剧《蝴蝶梦》中饰演田氏
李仙花用花旦行当塑造少妇之后,紧接着在《毁扇》中则以青衣应工来展示田氏的庄重沉稳。如果说扇坟少妇是以佻达俏丽的身形体态,来渲染不被孝服遮蔽的天性,那么田氏则是将微微悸动的内心,包裹在青衣素服中,用深沉的吟唱来舒缓久经压抑的苦闷。因此在悠缓的音声伴奏中,田氏正襟而出,在保持青衣行当的沉稳身段中,加重了对其恪守庄子师教的渲染,这个出场不是一般青衣的女性体态,而呈现着浓重的庄严肃穆,这正是田氏身处南华堂、奉行庄周哲学的特有质感,由此成为田氏这个人物最初的人性定位。
在一段【西皮二六】转【西皮慢板】唱腔中,田氏吟咏的“又是一年菜花黄,春色撩人日脚长。南华堂前摘菜根,和风小送畦土香”,用汉剧缠绵的拖腔,从看似恬淡的状态中表达出深藏幽微的一点心绪。唱词中的春色、和风、黄花、土香,都是在静穆中散发着活力,这种对自然的体悟正与她之后唱出的“池塘水倒映着淡淡的天光”相契合,成为真实本心的流露,也是在这样的唱词间,她的身段和手势陡然显示出了女性特有的姿态。因此,在“心如止水无欲求”的自我表达里,她意外地看到水边的小花,以照影自怜的贪爱,本能地将花摆弄在自我陶醉中,“这一朵小花儿怎地这么香”的感慨展示出她根本无法压抑的青春企盼,她在左右扫视后,偷偷地沉浸在人面与小花相映成趣的自我慰藉中。在一段只有十数句的唱腔中,李仙花从随顺阴阳的表面枯槁,演出了春水微皱后的内心波澜,让这个人物从出场就显示出了表里有别的矛盾。她的礼法恪守是真诚的,她的天性展露是本能的,这种错位也必将带来最终的人性舒展。这个活生生的独特性,正是李仙花为田氏做出的重要诠释。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田氏”的定位,她面对世俗的姜婆婆,体现出一副凛然高贵的从容,在面对令人尊敬的庄周时,则是一副以弟子礼仪而出的恭谨,但是真正到了夫妻关系中,她才释放出女性该有的做派。面对那把撕毁的纨扇,李仙花采用青衣的本工表演,通过一套二黄对唱的展开,将她对生死、对守节的情感态度充分表达出来。这种比较短暂的本色展示,到了【二黄慢板】“那妇人捎来了这柄纨扇,搅得我古井水微起波澜”,已经完全是青衣行当所要诠释的本色的女性个性。尤其是楚王孙出现在生活中后,身着素服的田氏更加展现出成年女性所具有的成熟,她与楚王孙的对答接应,完全是师母与弟子之间的通达。
李仙花这种准确的形象定位,来自于她对旦行艺术娴熟的驾驭和超越。在塑造鲜活的田氏形象时,她已经将行当表演化在了形象的成长变化中。因此,在接下来的《汲水》《成亲》《劈棺》三场戏中,基于楚王孙的呵护、求婚以及急病,田氏形象呈现出更加多元的人性侧面,多元行当的艺术技法让这个“青衣”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气质。《汲水》一场戏中面对楚王孙深夜帮扶,感慨生命苦况而接到楚王孙递来红手帕时的方寸凌乱,以及二人同抬水桶时的默默无语,滑倒青苔后的暗自沉思,田氏展现的正是闺中女性所具有的娇柔、羞怯、袅娜,田氏以更加青春的生命风采来回应楚王孙的温情呵护,此时的表演充满着浓郁的闺门旦特色。在《成亲》一场戏中,面对红手帕,田氏心思紊乱,从手中的把玩,到断然扔在地上,再到战战兢兢地左右环顾而毅然拾起,忐忑的心态俨然如《拾玉镯》中闺中小女子第一次面对的情感试探,此时的表演则兼容了小花旦特有的情态。《劈棺》一场戏中,田氏右手执斧,左手水袖,利斧挥动,水袖翻舞,在【反二黄倒板】“顾不得胆儿惊心儿惨浑身抖颤”衔接紧打慢唱的节奏中,刚柔兼具,文戏武做,此时用跳脱于青衣之外的调度和排场,结合碎步、蹉步、跌扑、乌龙绞柱等技法,来强化心理走向极度时人物性情走向极度夸张的状态,歌舞身容表演吸收了刺杀旦、武旦的程式动作。

图3 广东汉剧《蝴蝶梦》剧照
显然,李仙花在表现田氏这个人物时,基于人际关系的变化,在青衣行当基础上,跨越了行当边界,综合性地使用了其他旦行塑造形象的方法和程式手段,让田氏真正成为一个内心与行为,从相悖相离到相融相彰的真实女人,真正挖掘出了在文化传统中被边缘化了的田氏所具有的人性本真。这样的人物形象显然是鲜活的。
三、李仙花对于广东汉剧的艺术贡献
优秀的剧本可以成就演员,但没有好的艺术,演员会因为自身的平庸而泯灭作品的灵性;同样,优秀的演员也可以成就剧本,但没有好的文学,剧本同样会因为文本的缺陷而减弱演员的努力。盛和煜先生在《蝴蝶梦》中的文心巧思,让这部作品的戏剧文学几近完美,因此,需要真正有实力的优秀艺术家进行二度演绎。文学与舞台的相得益彰,才能实现这部优秀剧作的精准表达。李仙花正是这部剧作思想深度的重要诠释者,也是舞台艺术的重要创造者,她用几近完美的人物塑造与性格定位,在舞台上实现了田氏与少妇形象的个性变化与情感挥洒,说到底,她用自己的艺术真正实现了这部戏的现代表达。
《蝴蝶梦》所创造的田氏与少妇两个艺术形象,应该说是新时期广东汉剧艺术的阶段性成就,是对黄桂珠、梁素珍等前辈艺术家传承创造的旦行艺术范式的一次成功再创造。剧中的这两个人物,既是传统程式手段塑形而成的艺术形象,也规避了类型化、模式化、简单化的可能趋向,立体展示出女性形象独立、饱满和丰富的个性情感,附带着当代审美所需要的现代立场与品质追求。
通过长期的艺术积累,以及独树一帜的表演艺术在《蝴蝶梦》中的充分展示,李仙花已完成了对于广东汉剧旦行表演艺术的个性化创造。她在旦行表演艺术领域中的多元驾驭,让她面对诸多作品人物时,始终能够游刃有余地出入于行当与形象之间,在把握行当艺术规范的前提下,创造着人物形象本该具有的人性特征。用戏曲本体的艺术手段,将人物形象作为舞台艺术创造的第一要务,这成为李仙花延展广东汉剧艺术传统的重要经验,当然这也让她更加游刃有余地出入于戏曲表演传统与现代美学追求的艺术边界。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广东汉剧长期在潮汕方言区、客家方言区流传,舞台语言的中州韵和方言白都受到了地方语音的深度影响,甚至一度出现用客家话来作为广东汉剧舞台语言的实践。事实上,广东汉剧是清代进入岭南的外江戏在闽粤地区的遗存,因为其主体是西皮、二黄、四平调等徽汉声腔,因此从学术和传统上被看作是与汉剧、粤剧、京剧等同源异脉的剧种。广东汉剧随着潮汕、客家等群体在东南亚等地区的流播,其声腔和表演在海外长期被看作是“国乐”“儒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剧之“汉”除了标识其剧种声腔源头之外,还与客家人以汉族为中原正统的“汉”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客家人的语言音韵始终保存了汉语正字文读的传统,客家人的礼仪行为始终保存了礼乐文化传统,客家人的乐名汉乐,其剧名汉剧,都与其语言文化和礼乐传统的传承秉持密切相关。这也让广东汉剧在传承传统时,更容易取法同源声腔剧种的艺术之长,广泛吸收客家文化之正,也更容易在中国戏曲丰厚的艺术传统中完成时代创造。
在这种背景下,李仙花的唱念在京、汉艺术基础上,将舞台韵白有所提纯,既不用京汉正韵来取代广东汉剧的韵白,又保证了唱念相对准确地符合舞台官话的规范,客家本地人认同是传统正音,而外地人又不因方言影响而有语言陌生感。特别是舞台散白,取法京剧京白,融入客家话文读标准,并充分地展示着戏曲语言所必须的节奏韵律。因此,李仙花的唱腔与念白有效地处理了客家土音的干扰,使传统的旋律韵味更趋于干净纯粹,也让广东汉剧在皮黄腔系统的剧种中,在保持剧种的艺术识别度的同时能在语言规范上做到齐平一律。这种舞台正音的当代实践,在整体上提高了广东汉剧的艺术品质。
四、李仙花表演艺术的当代启示
新世纪以来,随着《蝴蝶梦》的成功,李仙花的艺术实践更加主动和大胆。她主演的《白门柳》等原创作品,持续地保持着前此成功的经验,也显示出对于传统的更多出离,甚至与其曾经取得的成功经验有所背违。
例如《白门柳》对于京剧艺术的更多借鉴,以及偏重于古典文人趣味的题材选择,或多或少偏离了客家观众对于广东汉剧的惯常审美。这当然是广东汉剧院的整体发展诉求所致,同时也包含了李仙花对于这个古老剧种现代转型的思考。这当然需要时间检验和艺术评估,却也真实地展现了广东汉剧意欲快速跟上时代需求的具体实践。在这两部作品中,基于旦行表演艺术的多元化和综合化,创造边缘化的女性形象,突破戏曲传统视野下的女性形象审美,展现现代社会对于女性更加理性的人文关怀,已然成为李仙花在广东汉剧旦行表演艺术领域中的核心创造内容。这也让李仙花积极的艺术实践为广东汉剧进一步走向理性创作,提供了进行深度艺术思考的参照。
李仙花不但在舞台上展现其成熟的创造活力,而且涉足多元媒体对广东汉剧的推广和再创,将广东汉剧与现代电影艺术进行结合。广东汉剧历史上曾有过代表性的作品被拍摄成电影,例如《齐王求将》《一袋麦种》,就曾以写实的风格,将舞台剧进行了很好的艺术再现。时隔半个世纪,广东汉剧《白门柳》《蝴蝶梦》相继被搬上电影屏幕。电影版的两部力作以电影独特的镜头语言,给予戏曲更加现代化的开掘,让广东汉剧舞台上的唱念做打等技艺,转化成电影多重叙事结构中的情感和精神。

图4 李仙花在汉剧电影《白门柳》中饰演柳如是
例如汉剧电影《白门柳》采用实景拍摄,剧中柳如是深夜探视钱谦益,一首【小调】(夜深沉)以典雅幽静的优美旋律,配合着人物在传统庭院回廊间的自思自量,既突出了柳如是极具古典风范的仕女形象,也营造出了安闲恬静的江南文人环境,这一段演唱可堪与广东汉剧传统经典剧目《百里奚认妻》“叹沦落”一曲古调媲美。而在该剧的电影视觉中,李仙花或男扮、或女妆,都比较贴近人物形象在不同环境中的身份气质:在竞选花魁中脱颖而出的柳如是,具有风尘形象而又带着凌厉风骨;在钱、柳和谐的婚姻生活中,柳如是则显示出端庄风雅的气度,且饱含温婉柔媚的气质;在柳如是说情一段戏中,柳如是虽有几分佻达,但最终展示出了更多开朗和悦的随性,仿佛元代杂剧《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为夫赴险。而柳如是面对家国变乱,一袭青衣,在练达中不乏沧桑,在沉稳中饱含悲情,为最终夫妻殊途做了形象的铺陈。这些各具色彩的形象质感,来自电影视觉对于人物多元化的捕捉,以及在情感节奏中对于视觉形象的聚焦呈现。这都与舞台表演存在极大的差别。李仙花在广东汉剧电影中,同样娴熟地驾驭着对于人物形象的把握,并通过电影特有的技术手段,将其自身的魅力放大。这些创造当然也用今天的电影审美趣味对前此汉剧电影艺术做了又一次超越。
李仙花在传统剧目中,演新了广东汉剧舞台上固有的女性形象;也在新创作品中,新演了诸多贴合传统审美的女性形象;更在原创剧目中,创造了符合现代审美的女性形象;而且在戏曲借助电影、新媒体进行艺术载体的转化过程中,创新了同名剧目的表达手段。扇坟少妇、田氏、柳如是、潘金莲等艺术形象所张扬的人物个性和时代气质,都成为她用时代观念来创造广东汉剧新的女性艺术形象的重要实践。
在广东戏曲界,关注李仙花的戏曲人和理论家们用“古调仙声”来概括李仙花的创造实践。这种评价自然包含着李仙花在四十余年艺术道路上,以《蝴蝶梦》为中心所形成的表演艺术经验;当然也包括广东汉剧“古调”在追求现代转型中,李仙花为剧种所进行的各种现代化的实践。散发在广东汉剧这个古老剧种中的时代之声、时代之形、时代之质,都因李仙花自身的艺术素质和独特的艺术个性,呈现出“仙声”所具有的流派趋向。当然,是否形成流派,还需要她以及更加齐整的青年后继人才团队,在更多的艺术作品中来承载这种成功经验;还需要广东汉剧的观众群体,在接受与传习她的艺术创造中,来理解、认可她为广东汉剧所做的有效而独树一帜的艺术推动。这有赖于广东汉剧旦行表演艺术在适用她的艺术创造经验时,持续而成功的创作,精准而有效的传承,深入而理性的宣传。但无可置疑的是,李仙花在广东汉剧旦行表演艺术中所达到的高度,拓展了前辈表演艺术家的艺术范式,并且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戏曲剧种诸多领军艺术家所进行的成功实践,可以比肩并辔,并且成功拓展了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艺术库存。
笔者在1997年第五届中国戏剧节上,曾在剧场体验过广东汉剧《蝴蝶梦》的剧场效应。这部获得过戏剧节七项大奖的作品是李仙花在扎实的传统基础上,层楼再上的一部力作。之后笔者又多次观看《蝴蝶梦》京、汉“两下锅”的创作演出,以及她在中国戏曲学院创作演出的南戏复原剧目《张协状元》。这些古风极重的创新作品,都在化用古典意蕴的基础上,饱含现代品位,极好地展示了演员对于舞台境界的创造能力。李仙花对戏曲艺术的深度体会和精彩表现,拉近了广东汉剧与现代社会的审美距离,也让这个剧种以更为成熟的艺术姿态出现在当代中国戏曲的前沿创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