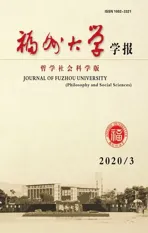论刘辰翁“尚奇”的评点特色
——以《班马异同评》之张良评语为中心的考察
2020-12-20王晓鹃
王晓鹃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刘辰翁(1233—1297)是南宋末年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曾对《大戴礼记》《越绝书》《老子道德经》《荀子》《庄子》《世说新语》《班马异同》等史书和杜甫、王维、李贺、韦应物、孟浩然等人的诗歌做过评点,在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曾说:“刘孟溪名能评诗,自杜子美下至王摩洁、李长吉诸家,皆有评。语简意切,别是一机轴,诸人评诗者皆不及。”[1]四库馆臣也曾指出:“辰翁人品颇高洁,而文章多涉僻涩,其点论古书,尤好为纤诡新颖之词,实于数百年前预开明末竟陵之派。”[2]显然,不管是李东阳“别是一机轴”,还是四库馆臣“尤好为纤诡新颖之词”的评论,都注意到了刘辰翁“尚奇”的评点特色。本文拟以《班马异同评》中刘辰翁对张良的评语为例,来谈谈这一问题。
一
好“奇”作为人的一种普遍心理,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关于“奇”,许慎《说文解字》释为“异也”,《辞海》与《汉语大辞典》则有“异常”“不寻常”“惊异”“出人意料”等意。“奇”的这些涵义,在刘辰翁的诗文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其《不平鸣诗序》言:“亘古今之不平者无如天。人者有所不平则求直于人,则求直于有位者,则求直于造物,能言故也。若天之视下也,其不平有甚于我,有甚于我而不能自言,故其极为烈风、为迅雷、为孛、为彗、为虹、为山崩石裂、水涌川竭,意皆其郁积愤怒,亡所发泄以至此也。皆人事之激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不如小决使道人之不平所不至于如天者。其小决者,道也。小决之道,其惟诗乎!故凡歌、行、曲、引大篇小章,皆所以自鸣其不平也。而其险哀有甚于雷风星变,山海潮汐者矣。”[3]显然,刘辰翁大力倡导文学要不平则鸣,创作要自觉追求奇荡变幻的风格。这一诗学思想,在刘辰翁的很多言论中也都能得到证实,如在《辛稼轩词序》中提到“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4];在《虚舟记》中,评点罗士俊时,称其“出语英妙,有奇气”[5];在《心田记》中评点章贵安时,称赞他“气概伟然,其文浩荡奇崛”[6];在《赵信之诗序》中,则提到要“用意奇崛”[7]等。
明清以来有很多学者已注意到刘辰翁“尚奇”的诗学思想,如明代杨慎就指出刘辰翁“为文祖先秦战国庄老等,言率奇逸,自成一家”[8]。庐陵后学韩敬也赞叹不已:“余偶于故簏中得记稿一帙,瑰奇磊落,想见其人,每读数过,辄恐易尽,真枕珍帐秘也。”[9]清人何属乾更是赞美道:“时而谈玄,忘乎刘之为老也;时而逍遥,忘乎庄之为刘也;……才如长吉,而非近乎思也;忠爱似子美,不悲而歌,不哭而痛也;学兼班马,不能分异同也;语多旷达,如东坡居海岛,而无谪遣之戚也;是三绝益以四绝,九种合为一种也。”[10]四库馆臣亦肯定说:“即其所作诗文,亦专以奇怪磊落为宗,务在艰涩其词,甚或至于不可句读,尤不免轶於绳墨之外。特蹊径本自蒙庄,故惝恍迷离,亦间有意趣,不尽堕牛鬼蛇神。”[11]胡思敬则谈得更具体:“文之佳者,如《阁山》《善寂》诸记之谈佛老,《善堂》《中和》《核山》《静见》诸记之谈性理,《岂畦》《介庵》诸记之谈事变,《楚翁序》之谈诗,奇诡纵横,深入蒙庄化境,其艰涩处多由舛误所致。”[12]萧正发《刘须溪先生集略序》更是高度赞扬其诗文奇怪磊落的风貌:“自有天地来,自有文章来,孰有奇于漆园者哉! ……宋之亡也,而有我庐陵须溪刘先生,先生之为文,无以异于漆园之为文也,非其时也,奇而益自晦其奇也。……庐陵故不乏第一流奇人也,而第一流奇人奇书,舍先生谁归哉!”[13]显然,他们都明确指出了刘辰翁诗文奇诡伟丽的特质。由此可见,“尚奇”无疑是刘辰翁诗文最鲜明的特色。
二
刘辰翁“尚奇”的文学创作风格,自然会在评点他人作品时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如《大戴礼记》卷四“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欤”句,刘辰翁点评此句“起得奇”[14];《越绝书》卷二“辟塞”二字,刘辰翁认为“甚奇且新”[15]。评论《老子道德经》时,刘辰翁频频使用“奇”字:第五章“刍狗喻奇,橐籥理精”[16],第二十九章“神器,语奇,谓非人之所能有也”,第四十六章“却走马语奇,常足最乐”,第六十一章“古人设喻,未有如此其奇者,其于理无不通”,第七十七章,“张弓之喻甚奇,高下左右只在弓内,未尝出于弓也。”刘辰翁评《庄子》时,更是反复提到“奇”字:“妙在‘于呕’一语,快带前后,皆活重出,愈奇”“影已无形之物,罔两又非影之比也,寓又寓者也,意奇,文奇,事又奇”(《齐物论》),“奇又奇”(《徐无鬼》),“其言肩倚、膝踦,己霍然活动说音节合拍,愈奇”(《养生主》),“前见之梦己奇,又生诊梦一段,从容不竭”(《人间世》),“观书大略如《庄子》,尤不可训诂理,其所谓性即所谓德也。其言扶疏,其字错落重出,初非有意,亦非无谓者,故其所为奇也”(《骄拇》篇首),“为报德甚奇,凡皆爱之,不知其害,欲复为混沌难矣哉”(《应帝王》),对庄子奇特的语言、文风和思想很是推崇。[17]这一评点特色,也体现在刘辰翁对唐人诗歌的评点中,如“以此寄兴,甚奇”(李贺《苦簧调啸引》)、“拈出自别”(李贺《湘妃》)和“亦自鲜丽眼前语,无苦入手自别”(李贺《南苑十三首·其八》)三条,都借“奇”“别”字点出了李贺奇崛的诗风。[18]再如,杜甫《望岳》“诸峰罗立似儿孙”句,刘辰翁评曰“奇”[19];王维《赠焦道士》“饮人聊割酒,送客乍分风”句下,刘辰翁亦批曰“奇”[20];孟浩然《同薛八往符公兰若》“谁能效丘也”句下,刘辰翁批曰“末句‘也’字似散语,亦奇”[21],以赞美杜甫和王维诗句之奇和孟浩然用字之奇。又如韩愈《秋怀诗十一首·其九》中有“空阶一片下,琤若摧琅玕”句,刘辰翁用“甚无紧要,造此奇崛”[22]八个字来形容,认为此处正是此诗的奇绝之处。因此,四库馆臣所说“其点论古书,尤好为纤诡新颖之词”的观点,准确地指出在“尚奇”的文学批评态度下,刘辰翁在阐释《史记》时,侧重“爱奇”文学风格的评点倾向。这也对我们更加明确《史记》中各种各样的奇幻意境,进一步认识司马迁诡奇的文风大有裨益。
《班马异同评》的评点中,刘辰翁多处提到“奇”:
奇计不难,用奇计难。伪游之事与儒生谋之,不惟郑重,难举疏驳,更多漏泄,尤易以一力士,自数万兵直戏耳。非奇乎?(卷六《陈平》)[23]
有“奇计”字,但言“使单于阏氏”,隐约可见,然难使之解围。(卷六《陈平》)
“反县”字亦奇。(卷六《陈平》)
“木彊”又“椎”其形容非史所当有,强上去声。“东乡坐责诸生,辄为我语”,甚奇。“椎少文”不成语,然足引用。(卷七《周勃》)
“两”字较奇。(卷七《周勃》)
传常患无奇,此“养卒”甚奇,又道逢赵王姊出,复秦使问,何叠叠也。(卷八《张耳 陈余》)
此遗汉间也,越终始从汉,而田横传谓其中立,且为汉,且为楚,将无其迹疑似故有为奇兵。(卷九《魏豹 彭越》)
最是得力处,自擅将略地,往来为游兵,或攻或走,皆自为去就,在当时刘、项对垒外,此足称奇兵。至会垓下,其末耳。(卷九《魏豹 彭越》)
此赞曲折,语意甚奇,能言豪杰意中事,取于众人所不取,亦其所遇素意如此,他人笔力几许能发明。(卷九《魏豹 彭越》)
其母死,营高冢,载之赞,以见其志,乃太史公过淮阴亲见,又奇,移之“寄食”下不类。然“常从”“常数从”颇碍,《汉书》以故欲小疏,删去下“饮”、下“寄”,是。“至城下钓”,絜诸母漂如画。(卷十《韩信》)
蓐食奇,漂母又奇,跨下又奇。“跨”胜“袴”,形容正在此。“蒲伏”,可笑耳。(卷十《韩信》)
此处取《史记》,先后亦不过乘胜传檄以摇之耳,策非奇也。事势适当然者,且委曲辗转,揣谋尽情,所长独在“牛酒享醳、北首燕路”耳。(卷十《韩信》)
子长一手自作项纪,又作哙传,看他笔势种种,不遗而健,快复自过之,如骑老马,即熟路暗行,略无顾虑。即“巵酒彘肩”与“拔剑切肉,尽之”,前纪许多从容,去一“尽”字,便彼此不相似。“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又有味而古,可为删润之祖。纪、传两样各好不相犯,最是奇俊,若曰“在某传”,最拙。(卷十一《樊哙》)
“泮”字奇,语皆切。(卷十三《郦食其陆贾朱建》)
无此“也”字,岂不可怪也哉。(卷十三《郦食其陆贾朱建》)
“斗辟”语奇,作“辟”字奇,然“什”字即“斗”字之误。(卷十三《郦食其陆贾朱建》)
此周氏奇甚,在朱家上,是能用朱家者,而其后朱家独闻。(卷十六《季布栾布》)
有从史,又有受金不忍刺之客,何奇士之多也,然卒不免。吾自绛侯、晁错屡论之,亦其资如此。(卷十七《袁盎晁错》)
“为相持重”“不用”“无势”,语皆是。正在“日”字、“独”字,语极有情,《汉书》“墨墨”字虽奇而不切。(卷二十《窦婴田蚡灌夫》)
只三语亦自奇。(卷三十四《日者》)
这些评点,或长或短,或疏或密,或解字词,或议文句,或论结构,或述语意,或评人物,或品语言,无不显示出刘辰翁对“奇”字的喜爱。如卷六《陈平》“‘反县’字亦奇”句,原文说道:
高帝从(击)〔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几)我死也!”用〔陈〕平〔谋〕(计)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乘)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女)弟吕〔媭〕(须)〔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即)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令)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周)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24]
公元前195年,刘邦击败叛军英布归来,创伤发作病倒了,但燕王卢绾又叛变,就派樊哙以相国的身份率军去讨伐。樊哙走后,有人对刘邦说樊哙跟吕后串通一气,想等皇上百年之后图谋不轨。刘邦对吕后干预朝政早已不满,立即采用陈平的计谋,密派陈平和周勃前去诛杀樊哙。二人又担心刘邦病重将死,怕控制朝政的吕后发怒,便没有冒然驰入樊哙的军营,而是在不远处故意设了个土坛,用皇帝的符节去招樊哙。樊哙见只有陈平只身前来,便立即独自骑马赶来接诏,谁料周勃忽然出现,当即将樊哙拿下,钉入囚车。周勃又立即赶到中军大帐,代替樊哙,由陈平押解囚车返回长安。果然没多久,刘邦驾崩的噩耗传来。樊哙被押回长安后,立刻被吕后释放,并恢复了官职爵位。这里,《史记》原文为“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汉书》改为“而令周勃代,将兵定燕”,《汉书》删除了“反县”二字。刘辰翁认为《汉书》删减不当,因为这二字正体现了此事的“奇”字。燕王卢绾虽然反叛,但并非所有燕地都已反叛,周勃率军攻打的正是反叛的燕地县邑。一个“反”字,渲染出时局的紧张和严峻以及燕王卢绾反叛的事实,确实用字奇崛。一经《汉书》删减,这一句便索然无味。
再如卷三十五《日者》“只三语亦自奇”句,原文道: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
这是《日者列传》开篇的三句话。太史公由史实入笔,视野开阔,气势雄健,见解深刻。太史公好奇,对《周易》也颇有造诣,他遗憾“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便将卜者司马季主的事迹记载下来,“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以此体现卜筮是古代宗教巫术活动的重要内容,对早期中国的政治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刘辰翁击节叹赏,感慨这寥寥三句话,入木三分地点出太史公“好奇”和日者“自奇”的历史事实。
至于陈平的“奇计”,韩信的悲剧人生,周勃的“木彊”性格,魏豹、彭越、季布、栾布、袁盎、晁错等历史人物的奇特遭际,前人多有评论,刘辰翁依然袭用,兹不赘。这些评论,从文章学层面,或指出字法、句法、章法、结构之“奇”的特殊修辞技巧,或指出奇文、奇句、奇语、奇字等文本表层形态,或渲染奇人、奇事、奇景、奇情等文本内指形态,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史记》的叙述特色和刘辰翁的创作风格都有一定帮助。不过,最能显出刘辰翁这种“尚奇”评点风格的,当属张良评语。
三
《班马异同评》以人物来编排,卷五便是《张良》。司马迁写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实现这一理想,他除了“实录”历史以外,还对“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着以浓墨重彩,推崇、偏爱那些功业赫赫、杰出超群的历史人物。正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说:“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25]而张良正是司马迁要大力讴歌的一位风流倜傥的历史奇人。
张良(?—前186),字子房,汉初三杰之一。他身居乱世,胸怀国亡家败的悲愤,投身于倥偬的兵戎生涯,为刘邦击败项羽以及汉朝帝国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如何将历史上这样一位风云叱咤、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无疑是司马迁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也正如刘辰翁评语所说:“太史公于此传最费心力。”言下之意,非常之人自然需要非常的叙述技巧,而从《张良》文本来看,太史公无疑是成功的,原因在于他紧紧抓住了一个“奇”字,从“奇人”“奇事”“奇计”和“奇功”等各个方面入手,形象立体地塑造出“张良形象”。千载而下,刘辰翁能否将太史公笔下的张良的神韵概括出来、能否和太史公成为旷代知音?刘辰翁做到了,原因是他也聪明地抓住了一个“奇”字。
《张良》一开篇便惊心动魄:张良的祖父和父亲曾为韩国的五代国王担任相国,秦灭韩后,为了报国恨家仇,张良“弟死不葬”,散尽家资,以全部家产重金收买刺客,找到一个大力士,为他打制一只重达120斤的大铁锤,于公元前218年在博浪沙击杀秦始皇,可惜误中车副。秦始皇大怒,下令全国缉捕刺客,张良不得已亡命天涯。两年后,张良在下邳偶遇圯上老人,跟其研习《太公兵法》十年。在这里,刘辰翁有两条评语:
1. “大父、父”不可去,写五世相韩及弟死不葬,甚恨。“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不言沧海君何如,极神奇。“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最健。“为张良故也”五字,删之是。
2. 从沧海君得力士,已怪。百二十斤椎举于旷野之外,而正中副车,虽架炮不如也。如此大索而不能得,良非自免,并隐力士,此大怪。事卒归圮上,老父又极从容,如同时亲见,乃今人以为小说不足信者,即子房时时自道,容有疑之者矣。此皆不可意测,不可语解,但觉古人如在目前,亦不足辨妙处正在“履我”,又“业”已如此,省此,顿失数倍意态,“随目之”亦不可失,此去下“曰”字换文非,盖如见其人,如闻其语。“黄石”句,“常习诵读”,秃写得皆不偶然。试使子房自己或后人得传,必为不能知子长之曲折具略不少省何也。
明代陈仁锡曾说:“子房一椎,宇宙生色。”(《史记评林》引)此处,刘辰翁接连用了“极神奇”“最健”“已怪”“此大怪事”“不可意测”几个词反复表达出对张良“击杀始皇”和“黄石授书”这两件奇特之事的直观感受,认为从沧海得大力士、为圮上老父取履,得兵书等情节都有类似小说的虚构成分,但是同时符合艺术的真实。而对《汉书》删减的部分,刘辰翁表示不满,更是用“妙处”“顿失数倍意态”“亦不可失”“秃写得皆不偶然”“不能知”等词来表述他的遗憾,认为此处《史记》的描述像电影镜头一样,具有画面感、音乐感、流动性和神秘性,一经《汉书》删改,不但影响文意的流畅,更少了许多神奇性场面。显然,刘辰翁一开评便表明他对《张良》一文的基本评点态度——尚奇。
接着,太史公简要叙述张良助刘邦智取峣关,率先进入咸阳,赢得政治上的先机一事。刘辰翁对张良深厚的谋略很是欣赏:“啖而怠之,怠而击之,乃本谋也。然用之从容,虽高帝不能尽识也,皆史笔铺叙悠然。”张良本以复韩为事业,在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后,彻底投靠刘邦,并运用“明烧栈道”麻痹项羽,使刘邦得以修养生息。此处,刘辰翁评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说得不着迹,前辈以其为韩,此语似是,‘闻项羽’字极明,《史》《汉》叙韩成,虽先后不可知,然移易分画如《汉书》为是。”点出项羽杀害韩王成是张良思想的转折点,可谓承上启下。
彭城之败后,张良向刘邦推荐了黥布、彭越和韩信三位战将,也正是这三支部队,和刘邦的大军一起把项羽包围在垓下,最终打败项羽,由此可见张良超人的智慧与独到的眼光。此处,刘辰翁评到,“子房因事进言,胸中便有三人者化作三处,仓卒数语并其人平生,无不备”,对张良的奇言异想很是佩服。汉三年,项羽大军把刘邦包围在荥阳,刘邦非常恐慌,准备采用郦食其的建议,重立六国后代。这时,正好张良来见刘邦,便有了借箸劝谏一事。这里,刘辰翁有两条评语:
1. 当疑此借箸语谓能不能,每下一箸所谓其不可,八则无其事无其语,空取桀纣、闾墓、财粟、牛马杂为六七,实不过最后游士一语,利害情实可反复。《汉书》去其二,增楚以下为八,虽是而所删不尽,未免随俗,于此传为冗,传皆若此,何以读兵法为。
2. “六国”下复出“韩、魏、燕、赵、齐、楚”,虽赘,曰“借箸而论”,与其下叠数“其”字,子长语终壮,利害紧要独在此。
刘辰翁批评《汉书》虽然有删减,但不免流于“随俗”,且叙事亦冗长。相比之下,《史记》的语言反而显得明快有力,即所谓“子长语终壮”,且“利害紧要独在此”——刘邦放弃分封六国后代实属明智之举。这也是张良的又一奇计。
汉朝初立,刘邦封赏萧何、曹参等20多个大功臣,但其他将领们日夜争功,产生极不稳定的政治因素,张良趁机劝刘邦分封雍齿,再次帮刘邦稳定了江山。刘辰翁评到:“耦语虽闻,不问不言,言即危甚,销怨之道,复非人意所及,而人意靡然各随所料,于是子长之张皇道尽矣,直至四皓称说不衰,写得突兀惊人。”所谓“突兀惊人”,当是指《史记》文字和《汉书》相比更奇特,叙述更奇崛。
随后,刘邦听从张良建议,最终定都关中。在后来张良安定太子刘盈一事上,刘辰翁评语较多:
1. 四人者,在当时必知名,又高帝常招之不出,而人不知,独子房知之,上高此四人,意见迥别。此处模写,难于梦卜。
2. 徒“疾不视事”何益?有四老人在,又以身谢事,先感动之,置酒朝廷之上,而忽有山中布衣四人从太子以来,不惟帝异之,诸臣有不异者乎?若子房常言此四人,高帝知为子房设此谋相感悟,即此诡怪,疑似多端,岂独不能感悟而已,观史别当有眼。
3. 谓《汉书》不载四人,似是,盖出于隐约,未得传闻之悉也,有之不加,无之不损。《索隐》又兼著名字,愈怪。
4. 此“愿为太子死”,险。
5. 《索隐》曰:按《陈留志》云,园公姓唐,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曰夏黄公。角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符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记》作禄里,皆王劭据崔氏《周氏世谱》及陶潜《四八目》而为此说。
6. 何物老人能使乃翁至此无可奈何,非仙乎?太史公于此传最费心力。子房为谋臣第一,不容无数事实迹,看他每事不放过,开阖如不可测,类以己意揣之,情文俱见,皆他人以为必无者。其言汉之为汉,多出其力,虽如项伯剑舞与请汉中地小者,尤系成败,末又著击代奇计与立萧相国,又仿佛不尽言,枝叶愈多。
从“此处模写,难于梦卜”“忽有山中布衣四人”“帝异之”“诸臣有不异者乎”“诡怪”“多端”“愈怪”“险”“非仙乎”与“情文俱见”等一连串奇诡怪异的字句中,不难看出刘辰翁对张良这一险计的欣赏与赞叹。此处,刘辰翁还对前面没有提到的小事件,如“项伯剑舞”与“请汉中地”等的重要性进行了补充,认为这些小事“尤系成败”,其在刘邦夺取天下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并进一步指出《张良》一文末尾的“击代奇计”与“立萧相国”也是颇有深意。
若论功绩,韩信、萧何当在张良之上,但刘邦却推张良为“三杰之首”,并大力封赏:“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张良却委婉谢绝了:“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认为自己心愿已了,“乃学辟谷,道引轻身”,全身而退,也是三杰中唯一善终的人。对此,刘辰翁评价道:
此传自东海君、力士、圮上老父以至四皓,必有姓名哉!殆以天人助兴汉业,故屡见不为怪。末著子房学道欲轻举,与黄石俱葬,首尾奇事。
刘辰翁认为东海君、力士、圮上老父和商山四皓都应是名垂青史的奇异倜傥之人,遗憾他们在历史上没有能够留下姓名,进一步指出张良最终“学道”“欲轻举”与“黄石俱葬”等情节的奇特之处不减开篇“击杀始皇”和“黄石授书”的传奇性。太史公以“奇”开篇,刘辰翁又以“奇”结尾,可谓评论与《史记》的叙述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最后,太史公论道:“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于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刘辰翁评到:
1. 两语便怪。
2. 将极言有鬼神,却从无鬼神说,满传奇怪亦不得不尔引而归之天,正郑重。及论其形貌,亦爽然自失,言笑有情,却不郑重,极间散。
在这一段,太史公用“鬼神”“怪”“天”“奇伟”等字眼描画张良,强调张良屡建奇功实属神异与天意。刘辰翁亦用“怪”“鬼神”“奇怪”“天”等总结了张良传奇的一生,并对太史公用“天意”解释张良奇人奇功表示理解——“满传奇怪,亦不得不尔引而归之天”——因为张良一生传奇的地方太多,除了“天意”,又能用什么来解释?这自是《张良》一文郑重和严肃的地方。但太史公话锋一转,对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的形貌深感意外,因为这和他想象中风流倜傥之人应有“魁梧奇伟”的体魄相去太远。对此,刘辰翁亦欣然认同,认为太史公对这一点尽管写得不够郑重和严肃,却“言笑有情”,在严谨与闲散之间,在奇人奇事之中,已然体现出太史公过人的剪裁水平和叙述能力。
四
刘辰翁的评语虽然能够抓住“奇”字对张良进行解剖,但毕竟不能忽视《班马异同》是一部历史著作的事实。因此,刘辰翁点评的重点自然也在字词句,很少涉及历史事实,正如四库馆臣所论:
辰翁人品颇高洁,而文章多涉僻涩。其点论古书,尤好为纤诡新颖之词,实于数百年前预开明末竟陵之派。此书据文义以评得失,尚较为切实。然于显然共见者,往往赘论,而笔削微意罕所发明。又倪思原书,本较其文之异同。辰翁所评,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断制,无所考证。既非论文,又非论古,未免两无所取。杨士奇跋,以为臻极精妙,过矣。[26]
馆臣认为刘辰翁的不足之处是对大家熟悉的情节和已成定论处,却往往赘论,指出其“以意断制,无所考证”的评点倾向,而从上面所引刘辰翁的一些评语和他对《张良》一文的评语,也印证了“无所考证”这一点。抛开其历史观念不看,仅从《班马异同》人物看,刘辰翁点评最多的前十人依次是刘邦(114条)、司马相如(81条)、吴王濞(68条)、韩信(63条)、项羽(55条)、陈平(50条)、周勃(36条)、张良(35条)、韩长孺(32条)、汲黯(26条)。叱咤风云的帝王刘邦排在第一,自在情理之中,紧随其后的却是一代文宗司马相如。汉初三杰中,韩信和张良分别位列第四和第八,萧何的评语只有8条,远远低于樊哙(25条)、张释之(19条)、季布(13条)、冯唐(12条)和栾布(10条)等人,显得极不平衡。而第二十四卷卫青等17人和第二十五卷公孙弘等4人,刘辰翁居然未置一词![27]仔细推敲,发现刘辰翁点评较多的都是汉初富有传奇色彩的风流倜傥之人,而对萧何这样的治世能臣以及武帝时代的卫青、霍去病等武将和公孙弘等文人,则关注较少,这似乎也可以看出刘辰翁“尚奇”的某些倾向。
其次,张良一生极富传奇性,又是第一谋臣,事迹无数,如何剪裁,大有学问。太史公以“奇”字著篇章,“看他每事不放过,开阖如不可测”;刘辰翁亦以“奇”字为关键,画龙点睛来渲染人物。不过,刘辰翁虽能抓住太史公“爱奇”的特色,但评语并非全然出于己意,在他之前,已有多人对这一点有过诸多评价,如班固曾云:“闻张良之智勇,以为其貌魁梧奇伟,反若妇人女子。故孔子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学者多疑于鬼神,如良受书老父,亦异矣。高祖数离困厄,良常有力,岂可谓非天乎!”[28]刘邵《流业第三》说道:“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29]苏轼《留侯论》亦赞道:“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30]显然,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对张良传奇的人生表示欣赏与羡慕。后出转精,刘辰翁的评语借鉴前人,亦在意料之中。
再次,刘辰翁尚奇的评点思想来自于其诗学思想。在其《不平鸣诗序》《赵信之诗序》《辛稼轩词序》等文中,他都曾反复提到这一思想。刘辰翁喜爱《庄子》和《老子》,尤其是庄子,其丰富奇特的想象和汪洋恣肆的语言对刘辰翁诗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当时,宋人提倡“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与政治变革作用,“文以载道”“明道言志”的文学思想盛行,在诗学领域便表现为追求质朴自然,恬淡隽永的风格。显然,刘辰翁崇尚奇异的文风与这些要求并不相符合,被宋人视为异端予以排斥自在情理之中,而他追求奇崛文风的实质就是要打破理学思想控制下刻板保守的文风,这也恰恰体现出了刘辰翁求新求变的文风改革意识。
另外,刘辰翁尚奇的评点倾向也和时代及他本人的遭际与个性有关。刘辰翁生活在南宋末年,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刻苦力学、早年就形成了奇特硬朗而又自视甚高的个性,而理宗景定三年(1262)廷试对策,因触忤权贵贾似道,被置进士丙等,由是得鲠直之名,更是这一性格的直接体现。刘辰翁一直郁郁不得志,后又不幸遭遇国破。南宋亡国后,他隐居不出近20年,胸中满怀遗民麦秀之感。这一点,明清人早就指明。如明陈继儒就说道:“德祐以后,军学十哲像左衽矣,万里以故相赴止水死矣,文文山入卫,征勤王师,无一人一骑至矣。大势已去,莫可谁何。先生进不能为健侠执铁缠槊,退不能为逋人采山钓水,又不忍为叛臣降将,孤负赵氏三百年养士之厚恩。仅以数种残书,且讽且诵,且阅且批,且自宽于覆巢沸鼎、须臾无死之间。正如微子之麦秀,屈子之离骚。非笑非啼、非无意非有意,姑以代裂龇痛哭云耳。”[31]此时,刘辰翁进不能辅国,退不能忘却现实,又不能屈膝投降沦为贰臣,生存状况和心态都极为复杂。面对现实,刘辰翁无可奈何,只能把对故国的满腔热忱,把文人的狂狷之风和耿直性情抒发至读书、写作、评点之中,发为含蓄奇诡之词。四库馆臣更是剖析道:“且于宗邦沦覆之后,眷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体格绳之矣。”[32]直接指明刘辰翁诗文奇诡伟丽特质产生的原因在于改朝换代。其子刘将孙《须溪先生集序》曾说,“先生登第十五年,立朝不满月,外庸无一考。当晦明绝续之交,胸中之郁郁者,一泄之于诗。其盘礴襞积而不得吐者,借文以自宣”[33],实为确论。
总之,正如李阳冰和四库馆臣所言,“尚奇”是刘辰翁诗文最鲜明的特色和成就。在“尚奇”的文学批评态度下,刘辰翁自然表现出试图阐释《史记》“爱奇”文学风格的评点倾向,而最能显出刘辰翁这种评点风格的,当属张良评语。张良一生极富传奇性,又是第一谋臣,事迹无数,太史公以“奇”字著《张良》,刘辰翁亦以“奇”字品留候,两人相得益彰。刘辰翁“尚奇”评点思想既来自于其诗学思想,也和时代及他本人的遭际与个性有关。
注释:
[1] 李庆立:《怀麓堂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2][11][26][32]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42,2184,642,2184页。
[3][4][5][6][7][8][9][10][12][13][33] 刘辰翁:《刘辰翁集》,段大林校点,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3,177,75,72,173,459,461,462,469,464,456页。
[14] 刘辰翁:《大戴礼记》,明人朱养纯花斋刻本。
[15] 刘辰翁:《越绝书》,明嘉靖二十一年刻本。
[16] 刘辰翁:《老子道德经评点》,明小筑刊本。
[17] 刘辰翁:《庄子南华真经点校》,明刊刘须溪评点三子本。
[18] 刘辰翁《笔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20][21]《合刻宋刘须溪点校书九种》,明天启刻本。
[22] 高 棅:《唐诗品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9页。
[23]《班马异同评》,明嘉靖李元阳刻本。本文所引《班马异同》文字和刘辰翁评语均采用此本。
[24]《史记》本文今用楷体,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原书以细字书之,今则按原书以圆括号标注;凡《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原书以墨笔勒字旁,今则以细方括号标注。
[25] 鲁 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81页。
[27] 王晓鹃:《〈班马异同评〉研究三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8] 班 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63页。
[29] 伏俊琏:《人物志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30] 《苏轼全集》,于宏明点校,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863页。
[31] 陈继儒:《晚香堂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