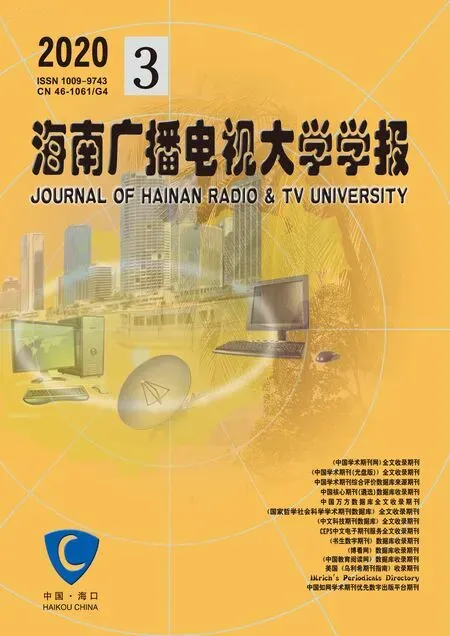论知识社会学视域下课程知识的“社会建构”
2020-12-20王超
王 超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课程知识”是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频繁出现在理论研究者的课程话语和教学研究者的实践视域之中,已经成为一个固化语词。虽然得以广泛使用,“课程知识”的内涵却尚未统一或得到权威界定。研究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与课程知识理解,赋予其不同内涵特征与价值意蕴。在《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课程知识”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在一门课程中所教授或所包含的知识(课程内容);二是指制定课程时所应用的知识。据此,本文将课程知识定义为被纳入学校教育过程中的知识,亦即课程中所包含的知识。需要注意的是,课程知识虽然是一个固化语词,却并非固化概念,由于时代变迁与理论视角差异,课程知识不断生成着或增删着新的内涵、价值与意义,呈现出多样化的价值属性。下文从知识社会学视域出发,探析课程知识的社会建构价值,以期澄清对课程知识“社会建构”所存在的模糊乃至错误认识。
一、知识社会学对课程知识“社会建构”性之研究
所谓课程知识的社会建构,是指有社会因素参与课程知识的生成过程。易言之,课程知识的建构过程受社会因素影响,具有价值负载性。课程知识的社会建构实则源于知识社会学的介入,因而知识社会学就为确立“课程知识具有社会制约性”这一基本命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课程知识研究提供了社会学分析的新路径。
“知识社会学”是研究知识(或思想)的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关联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又称思想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一词最早由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舍勒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1924)一书中首先使用,此后知识社会学便逐渐发展为一门学科,至今已逾百年。具有独特“社会情结”的知识社会学产生于反实证主义的思想背景,即反对实证主义长期以来将知识视为客观、普遍、中立的传统观点,探讨知识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传统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中的知识观变化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课程知识的社会建构。
(一)传统知识社会学渗透社会因素
曼海姆是传统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研究侧重揭示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探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决定关系。曼海姆一方面深受马克思影响,赞同马克思的“生活决定意识”,主张“知识的社会决定论”;另一方面又拓展了马克思的“存在基础”概念,并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扩大为一般知识,指出人类的思想结构本质上都含有意识形态性质,因而任何有关真理的声称不过成为一种自欺。此外,曼海姆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游离知识社会学领域,不受社会因素制约,这也导致了他与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区别:曼海姆力图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分析工具,而马克思则将其作为挫败对手主张的论战性武器。传统知识社会学将社会因素带入知识之中,但其思想仍囿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默认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在传统知识社会学看来,知识(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不再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镜式反映,不再是外在于社会的客观存在,而是社会的建构物。在此种知识观影响下,课程知识并非就是普遍、客观和中立的,而是社会地建构的。课程知识的社会建构关注的是课程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的是课程知识的社会性因素和社会创生过程。
(二)科学社会学隐含社会因素
传统知识社会学既保留“知识二分法”又坚持“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观念,成为曼海姆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矛盾所在,形成了“曼海姆悖论”。科学社会学为了不落入“曼海姆悖论”困境,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排除在研究之外,主张从社会视角来研究影响科学活动的社会因素,集中探讨“知识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科学的影响、体制性增长”(1)王彦雨,马来平:《“反身性”难题消解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年第1期,第68-69页。。墨顿是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兼代表者,科学的“精神气质”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独特性。他明确提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主要指科学制度的规范结构——即对从事科学活动的人的社会职业和兴趣的研究,对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结构的研究,对科学的产生、发展与社会因素的关系研究。简言之,科学社会学主要对科学家群体、科学职业和科学体制等方面进行社会学研究。墨顿的研究从曼海姆宽泛的传统知识社会学转换为较为狭窄的科学社会学,从对知识本身的研究转换到对影响知识的外部社会因素的分析,撇开了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研究,转向一条“外史”路径。尽管如此,科学社会学并不排斥科学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认为科学是不能与社会相脱离的,这也隐含着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观点。如此,也就隐含并承袭着课程知识的建构是不能与社会相脱离的这一传统观念。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凸显社会建构
由于科学社会学避免将科学知识列为研究对象,这一状况随着科学社会学的发展逐渐受到愈来愈多的批评,而随后出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则改变了在知识以外继续发展的研究状况。布鲁尔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所有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界限存在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的或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他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制定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守的“强纲领”——包含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反身性四个“信条[7]48”。强纲领之“强”表现在布鲁尔坚持“知识的社会决定论”立场,他认为,“没有一种信念处于社会学家的视野之外,所有知识都包含某种社会成分”,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在布鲁尔看来,知识,尤其自然科学知识,绝非完全来源于科学实验室里一尘不染的洁净试管,而是来源于社会的“人间烟火”。由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知识观:知识的分类标准开始模糊,知识的客观性逐渐消解,所有的知识都呈现出不确切性、非内在性和社会建构性特征。这使得课程知识的本质发生变化,即所有的课程知识在本质上都是可以修改的,是由社会或个人建构的,课程知识的传播途径和学习方式无疑都会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
知识社会学历经的三个阶段在本质上都研究了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也即知识的社会建构问题。知识社会学从社会角度考察知识问题的思路为课程知识提供了新视域——课程知识是被社会建构的。
二、课程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之价值
沿循着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意识,课程知识自然就成了应该加以深入检视而并非理所当然的问题。在知识社会学的知识是社会建构观念影响与启发下,课程知识研究冲破传统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哲学与心理取向,从技术取向的价值中立走向关系取向的价值关涉,课程知识的社会建构性质从此成为毋庸置疑的合理存在。
(一)使“价值取向”问题科学合理化
课程知识的表层以下是隐而不彰的社会。但是,在知识社会学兴起之前,传统认识论和知识论占据主宰地位,不管是形而上学知识论还是实证主义知识观,都认为主客体之间处于一种外在的认知关系状态,知识(尤其自然科学知识)被看作是独立于人并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且不受任何社会因素影响。这种“静态的、冷藏库式”的、独立于甚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知识,常常被视作目的本身,学生的学习目标无非就是“堆积知识,需要时炫耀一番(2)(美)约翰·杜威著:《民主主义与教育》, 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而教师则被讽喻为“觅食的鸟”(蒙田语),教育过程被描述为教师单方面向学生“传输”“传递”知识过程。由此,教育成为一种类似于存储的行为,“学生是保管人,教师是储户。教师不是去交流,而是发表公报,让学生耐心地接受、记忆和重复存储材料。这就是‘灌输式’的教育概念”(3)(巴西)保罗·弗莱雷著:《被压迫者教育学》,顾建华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6页。。
随着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和知识社会学的兴起,这种以真理自居的“旁观者”知识才开始遭到质疑。曾经那种着眼于技术层面的、传统“工艺学模式”的课程知识不再被视为价值中立的、不容置疑的“给定的”客观存在而加以授受。课程知识不仅是有价值负载的,而且是有意识形态渗透的;课程知识不再与社会生活相互断裂,课程知识与知识行动者不再存在隔离,而是有了某种程度的互动性与关联性;课程知识的选择、组织和传递有了作为社会总体性的人的主动参与。社会建构而成的课程知识,从此具有了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性”和“价值性”。
(二)使“意识形态”问题的解决趋向可能
在知识社会学影响和启发下,课程知识开始在意识形态方面崭露一角。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寻绎有别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后者旨在揭露知识被社会有意识的扭曲之处,前者则不讨论错误或受到歪曲的思想,而旨在揭示知识与社会因素的无意识的相关性。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中心问题只是一个关于“真实知识”而非“错误知识”的问题,因为它“并不怎么关心有意欺骗所造成的歪曲,而是关心客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以何种不同方式把自己呈现给主体(4)(德)卡尔·曼海姆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9页。”。
实际上,知识社会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只是课程知识中的部分“应有之义”,而非扭曲之义与全部之义。课程知识除了受制于意识形态之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实践主体等其他因素影响。就课程知识而言,其选择、整合过程也须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和知识本身的内在逻辑。而在批判理论和解构思想的理解中,意识形态被妖魔化和普遍化,成为继“价值中立”神话破灭之后的另一个新神话——人无往而不在意识形态的枷锁之中。那么,在当今“意识形态的问题被彻底地提出来,并将其所有的涵义都思考透彻的时代里,人们如何可能继续思想及生活(5)(德)卡尔·曼海姆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0页。”?课程知识中的意识形态在教育过程中又该如何被诠释、作为实践主体的师生又该如何理解它与生成它?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社会学对意识形态的揭示就已经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某种思考方向与可能解决路径。
三、课程知识的“社会建构”之启示
传统知识社会学习惯默认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免于被社会学研究的特权,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强调所有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都不能免于社会建构。因此,知识社会学内部就形成了知识观的某种对立。这种知识观的对立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课程知识。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课程知识中自然科学知识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可以独立于甚或凌驾于社会之上。 这一观点仅举一例就足以动摇:《欧几里德几何原本》被尊崇并作为教科书使用了二千多年后,直至1880年才被研究者发现其主要的逻辑漏洞,如此,我们又怎能肯定并断言自身没有被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某些理论谬误所蒙蔽呢(6)戴维斯,赫斯著:《措辞与数学》,载麦克洛斯基著:《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0页。?要跳出这些困局,我们就必须放弃对自然科学知识绝对的客观性与确定性的认识,承认自然科学知识只能具有相对的客观性与有限的确定性。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任何课程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他们否认知识存在的相对客观性。例如,“2+2=4”就带有社会属性,因为它是实验室“制造”和“加工”的结果,是“知识作坊”的产物。这种“知识全是社会建构”的笼统观点,忽视了科学知识的相对客观性与确定性,难免陷入“社会中心”的绝对主义,也难免会陷入庸俗关系论的陷阱:任何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任何知识都与社会有着缠夹不清的关系。在此种观念下,所有的知识争论与理论建构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唇舌之事。
因此,只有正确理解“课程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这一命题,才能澄清认识,发现其对于当下的课程与教学领域研究的有益启示。
(一)厘清课程中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内容与主观性措辞
那种认为“所有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的认识,实际上混淆了自然科学知识中的客观性内容与主观性措辞。美国学者戴维斯和赫斯对两者作了鞭辟入里的区分。他们认为,在欧几里得的科学世界里,人们只能找到一些不加修饰的公认概念、公理或假设,紧随其后的则是一连串极其严谨的数学定理与证明,再随其后的又是定理与证明。然而在现实的学校生活中,无数学生在课堂中囫囵吞咽着欧几里德的数学,只是所谓的“证明”已化约为一套形式化的铺陈,以左边为数学的“陈述句”、右边为例举的“原因”这两行并列形式呈现出来,并按照铁般的引证规律从“已知”到要“证明”的事项,从假设到结论。在戴维斯和赫斯看来,“定理”“公理”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中的客观性内容,而体现为“陈述句”和“原因”的“证明”就是主观性措辞。“陈述句”“原因”并非数学证明,而是一些用于数学证明的主观措辞,主观措辞不是数学证明,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只能是主观性措辞而非客观性的数学证明。虽然措辞有时是可能以数学的形式出现的,数学有时也可以是措辞的(7)戴维斯,赫斯著:《措辞与数学》,载麦克洛斯基:《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6-58页。,但措辞的主观始终无法掩盖住数学证明的客观。又如,万有引力定律不会因附加其侧的不同主观措辞而在科学知识中具有不同的结论。至于万有引力定律会不会被理论所证伪,则是科学发展的问题,在其被证伪之前仍然在课程知识中具有普遍性。由此可见,厘清这一认识混淆,有助于正确理解“课程知识的社会建构”这一命题。
(二)区分课程的学科知识和用以组织这些学科知识的教育思想
“所有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的这种认识,实际上还混淆了课程中的学科知识和用以组织这些学科知识的教育思想,从而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谬误。那种笼统地认为科学知识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看法,其实误将具体学科知识当成了教育思想,因为学科中自然科学知识是具有相对客观性的,而教育思想的目的并非意在证明科学知识的真伪问题,而旨在辨明陈述的意义,意义则必定具有意识形态特性。这一认识谬误在西方学者尤其新教育社会学者和批判课程理论学者中表现突出。阿普尔认为,所谓客观、中立的数理学科中的课程知识普遍潜藏着主流意识形态与权力。麦克·扬更是极端断言:凡课程知识都被权势者合法化,体现着权势者的价值与利益。很显然,他们将自然学科中的教育思想都当作课程知识本身,于是就理所当然地得出了自然学科知识中都蕴含着意识形态的错误结论。
实际上,自然学科知识本身较为显明而客观,教育思想则相对比较隐蔽,意识形态的分析比较困难。在对课程知识进行社会建构分析时,只有全面了解该学科知识选择的背景和相关的课程标准、目标等“背景资料”,研究者才可能揭示出其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得出较合理、较科学的结论。那种简单而习惯地将学科课程知识和教育思想混同起来,认为“课程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观点,难免会陷入一个“‘以知性逻辑来破解知性逻辑’的悖谬”(8)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页。:如果用以反驳对方的话语也在社会建构之中,其立场和思维方式与所批判的对手并无二致。
(三)规避“课程知识是社会建构”中“社会总体性”里“人”的出走
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中,“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中的“社会”指的是抽象的“社会总体”,缺少具体“个人”的向度。在论述知识社会学的具体观点时,曼海姆习惯用“社会总体性”一词来替代“社会”概念。他认为,从本意而言,知识社会学并不始于单一个人及单一个人的思想,因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虽然曼海姆也曾意识到除了各种社会决定因素外,还存在着“行动者”这个不可消除而恰恰容易遗忘的因素,但他对“行动者”的思考仅止于片言只语,未作进一步深入。曼海姆所谓的“总体性社会”,与其说是为了强调人在总体性中的复杂依赖性,不如说是为了更直接的揭示和宣扬社会本身。
同样,在课程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也存在缺少行动者及其行动、忽视教育过程中师生实践建构问题。换言之,社会总体性话语中缺少只能言说个体自己而不能代替言说总体的个体话语,个体话语成为被分离或被清除出去而漂泊他乡的“流亡话语”。由此,在知识社会学视域中,课程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体现出的是一种面目模糊的“总体性社会”,既使得清晰而具体的个人缺席,也使得独特的个人话语不在场。这一点,正是当前研究者所要规避或纠偏的。
四、结 语
在西方批判理论和解构思想流行并深入中国教育的当下,课程知识似乎正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虚假”“知识权力合谋”的存在,也处于“一切皆过程”的危险无根状态。一些研究者习惯以西方思想框架为普遍标准来批判中国教育与课程,他们指出错的却又说不出对的,这种批评模式正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正确思维。而一些所谓“揭老底”的、完全负面的批判则以釜底抽薪方式打击着人们对本国本民族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令人沮丧的是,很少有人去反思这些“揭老底”的批判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损失,也很少有人去想到这些“揭老底”的批判与社会精神崩溃之间看不见的关系,更少有人去思考关于真相的知识必须同时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知识(9)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如何才能在思考关于真相知识的同时又让知识承担对社会应负的责任?笔者以为,课程知识想要在无情批判与彻底解构的地方找到自身存在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知识社会学是一条可资借鉴之途,因为其所内隐的相对质疑与明智的批判方式,能为当今有沦为虚假意识形态之物或权力同谋者的课程知识找到一条合理生存之路,让我们能更客观地看清课程知识中的社会建构究竟应该“如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