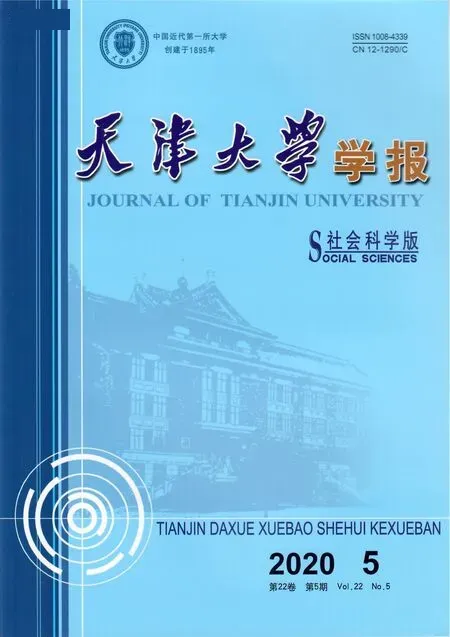唐太宗的初唐思想与文学创作中的嘉遁情怀
2020-12-19王珺
王 珺
(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 杭州 310018)
对于唐太宗与唐初文学思想的关系,学界的看法基本一致,认同其重视文学,但不乏利用的关系。在直接触及太宗思想与初唐文学关系上的研究中,梁尔涛的《走向隐逸:唐初朝野文学思想的共同趋向》对初唐诗歌的隐逸情怀作了详实缜密的论述,不过对太宗诗文作品中因道教文化而产生的“嘉遁”“尚隐”之思的挖掘尚浅,对这种情怀在初唐文人中的影响也尚有论述的空间,本文即从初唐帝王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入手,分析以太宗为代表的帝王诗歌中的因素,对当时权臣所作宫体诗和以王绩为代表的庶士文人的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唐太宗的初唐思想
高祖与太宗曾经作为隋朝的王室宗亲,一方重臣,属于士大夫阶层,无疑都受到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也将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治理国家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对嘉遁情怀的看重,更多的是出于对其现世功用的看重。《太平经》中就明确提出:“君臣者,治其乱,……。”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道教经典《老君音颂诫经》中有“老君当治,李弘应出”的字眼,起义者便多以“李弘”为托名,至隋末,《桃李谣》①盛传,李密、李轨、李渊等李姓首领皆借谶语“李氏当为天子”为自己起义作注脚。
楼观派宗主岐晖在唐公李渊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隋末就已洞察隋炀帝好大喜功,耗费国力,必不久矣,于是他投靠了关陇望族首领李渊,并授命散布李唐当王的谶语,以此为唐营笼络人心。在李渊揭竿而起之后,岐晖更是公然响应,甚至更名为“岐平定”,并“彻损衣资以供戎服,抽割菽粟以赡军粮”,率道士接应起义军,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给予李唐最大的支持。建唐后岐平定佐唐有功,李渊投桃报李,一再嘉奖。武德三年春天,高祖又亲临老君祠庭,“具千人之食以献”,岐平定率道众迎驾。“帝召平定及法师吕道济、监斋赵道隆等,并赐坐。遂令百官悉就坐饮食,谓曰:朕之远祖亲来降此,朕为社稷主,其可无兴建乎。乃降诏改楼观日宗圣观,赐白米二百石,帛一千匹,以供观中修补。”[1]
南方上清派的王远知也是有政治远见的代表人物。茅山派自陶弘景创立以来因其注重义理思辨,颇受南朝王公贵胄的青睐。到王远知这一代,也得到了隋炀帝的重视,但由于隋炀帝晚年极尽荒淫,王远知看出其大势已去,遂转而投靠李氏后人,与李渊暗中往来。不仅如此,王远知在与唐营的接触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李世民的治世之才:“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2]。王远知洞悉了李世民称帝的愿望,做出了预言。太宗登基后,对王远知礼敬有加,欲加重位,王远知深谙兔死狗烹之规律,固请归山。李世民曾在敕书中回忆当初问道于王远知的经历,并言明其言论对自己影响至深,客观上推动了上清派的发展。
二、初唐文学生态的浸染与太宗诗歌中的嘉遁情怀
武德二年五月,高祖“救楼观令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真人庙,应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赐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仍于观侧立监置官检校修造,即以岐平定主观事。”[1]296由此也为唐代文人间悄然兴起的隐逸之风,直至上演“终南捷径”埋下伏笔。
上清派的宗师多长于理论建设,对唐王朝文学的浸润影响较楼观一派更为深远绵长。成玄英是初唐玄学的大家,曾隐居于东海,贞观五年被太宗召进京师,对庄老推崇备至,均有注疏且盛行于世。在其注疏中,成玄英表达了他对王道的思考:“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顺苍生,垂拱无为,因循任物,则天下治矣。而逆万国之欢心,乖二仪之和气,所作凶悖,则祸乱生也”[3]。即顺应天道,无为而治,这种理念也一直贯穿在贞观之治的始末。
而他这种因循任物,道法自然的观念在其心性论中阐述的更为深入,他认为:“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有无二心,徼妙两观,源于一道,同出异名。异名一道,谓之深远。深远之玄,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也”[4]。在成玄英看来有与无其实是一体,玄即为“不滞”,非有非无,即有即无,是一种更大的虚空。因此他提出:“人天双遣,物我两忘,既曰无终,何尝有始?率性合道,不复师天。”[5]提倡物我两忘的内心体验,提倡率性而为的行事风格,他的这一理论也为当时的文士提供了安顿身心的新注脚。这些尚隐之思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太宗的治世和作文。
仕与隐是中国文人创作一个永恒的主题,关系着如何安顿身心,隐逸思想源自先秦,盛于魏晋,唐初文人嘉遁尚隐不同于魏晋时期的逃避现实,实则是韬光养晦,以退为进。这在太宗的言行上都可找到理据,《资治通鉴》中有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6]。高祖起兵时就曾许诺要立李世民为太子,但李世民的反应是“拜且辞”,那是因为他明白李渊在用人之时以此来笼络人心,而且他也识破了李渊心中对他的忌惮,所以以退为进。正因为深谙这样的处世之道,他也喜好从标榜隐遁的文人中寻求高士,并礼敬有加,这在他自己的诗歌中也有流露,如在《咏桃》②中太宗描述了“禁苑”中的万千桃花“迎风共一香”,却不如在仙山野岭“独秀隐遥芳”,其所欣赏的遗世而独立的形象,揭示了太宗心中对出尘脱俗的高士的向往。
这种情绪在他《望终南山》一诗中表露的更加明显。
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
出红扶岭日,入翠贮岩烟。
叠松朝若夜,复岫阙疑全。
对此恬千虑,无劳访九仙。[7]
诗中盛赞了终南山重峦碧嶂的磅礴山势,又描绘了恍若仙境的山景,抒发了在此可以乐而忘忧的心情。这种心境被杨师道在和诗《赋终南山用风字韵应诏》中一语道破。
睿言怀隐逸,辍马践幽业。白云飞夏雨,碧岭横春虹。
草绿长杨路,花疏五柞宫。登临日将晚,兰桂起香风。[7]180
首联“睿言怀隐逸”,就道破了太宗诗中蕴含的出世之想,“辍马践幽业”更指对现世名利的看轻。后面用白云碧岭、草绿花疏,这些柔美的意象描绘了终南山的旖旎风光,抒发了回归自然之乐。
太宗存诗七十首(按《全唐诗》),且诗作质量并不高,但世人多以雅正宏丽评价太宗的诗文,并认为他对初唐的文学生态影响颇深③。如在《帝京篇》其五、其九中都有“何如肆辙迹,万里赏瑶池。”“无劳上悬圃,即此对神仙。”等表达对现世享乐的满足和对神仙福地的诗句。其中,贞观十五年太宗作了《入潼关》,引用了老子骑牛的典故来比喻他的政治理想。
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
霜峰直临道,冰河曲绕城。
古木参差影,寒猿断续声。
冠盖往来合,风尘朝夕惊。
高谈先马度,伪晓预鸡鸣。
弃繻怀远志,封泥负壮情。
别有真人气,安知名不名。[7]326
《入潼关》创作于唐太宗欲赴泰山封禅,因路遇彗星以为不祥,遂中途折返经潼关之时,许敬宗有应和。全诗共七联,由写潼关之险要入笔,通过霜峰、冰河、古木、寒猿等一系列意象构绘出一幅肃杀的初冬图景。后半部份转而借歌咏公孙龙、孟尝君、终军、王元等多位与潼关有关的圣人名士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豪情。最后以老子西游经函谷关即潼关,见有紫气东来,老子乘牛而过一事点明自己不计名利的超然姿态。
这首诗并没有跳脱宫廷诗的窠臼,结构上依然偏程式化,然其表露的质朴的实感丰富了这首诗歌的内涵。此诗的深意有三:一则太宗欲赴泰山封禅之事筹谋良久,举国皆知,本是为李唐皇权扬威立万的良机,却被不详的天象所阻滞,偃旗息鼓打道回府,其心情之低落可以想见,因此诗中景致的描写也是心境的折射;二则封禅之事作罢令太宗颜面无光,他借诸多名士过潼关的境遇,特别是老子西游时的超然自况,也是为了掩饰未能借封禅扬威的失落;三则潼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从崤山起经函谷到潼关这一段一百多里的道路,狭长险峻易守难攻,他在此作诗又特别提到老子,也是提醒世人自己是圣人之后,自有神人天佑,江山稳固不可撼动,有钓名之意。
如前所述,太宗在歌咏现世浮华人生的诗作中,往往会有镌刻着嘉隐的情思表露,体现了唐初“重贞退之节,息贪竞之风”的文坛风尚,也丰富了宫廷诗歌的内涵,并影响了初唐的诗坛。
三、嘉遁思想在宫廷文人中的影响
太宗虽是马上皇帝,却一向重视文学,自作秦王时就设立文学馆,贞观年间又设弘文馆,笼络了一批谋臣学士,太宗的言行也由此直接影响到士大夫阶层。应制诗往往是对政权的歌颂宣扬,思想深度和美学价值虽普遍较低,但因其担负着宣教的功用,所以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颇大,史学价值不可估量。明代的杨慎曾云:“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8]。可以说初唐文坛就是以宫廷诗人为核心的,这些文人在皇权的威慑和恩泽下进行的创作,架起了皇权与文坛间的一座桥梁。
前文提到的杨师道,就曾代魏徵为侍中,性格周慎谨密。史书载:“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直书,有如宿构。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2]97杨师道是太宗的近臣,对文学有非常高的鉴赏力,且也被太宗所赏识,常与其切磋诗文,所以对太宗圣意的揣摩自然比一般文士要深入。从太宗与他的诗歌唱和中可以看出太宗这种在诗歌中表露的超然物外的情怀,是滋生于儒家建功立业的抱负之上的,是功成名就后的一种自谦和畅想。而太宗的其他近臣也多有勘破此中意味的,所以在应诏而作的诗歌中既要盛赞太宗的功绩,又要颂扬他的志趣,这也成了初唐应制诗的一种套路。
比如太宗命权臣许敬宗做《奉和入潼关》,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太宗借老子的典故表露的这种看似隐秘细微的心绪,所以他在和诗中运用了色彩浓重的意象,营造出凯旋回朝的祥瑞氛围。
曦驭循黄道,星陈引翠旗。
济潼纡万乘,临河耀六师。
前旌弥陆海,后骑发通伊。
势逾回地轴,威盛转天机。
是节岁穷纪,关树荡凉飔。
仙露含灵掌,瑞鼎照川湄。
冲襟赏临睨,高咏入京畿。[7]287
许敬宗乃隋时礼部侍郎许善心之子,也曾入朝为官,颇有才名,先投于李密,后被李世民招入秦王府任学士,太宗继位后官至检校中书侍郎,高宗朝时以立武后之功,被加封侍中,可见其对圣意揣摩功力之深,当为宫廷文人之冠。许敬宗曾修国史、《西域图志》《文馆词林》等文史书籍,其诗作被《翰林学士集》收录最多,达二十一首,对当时的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这首《奉和入潼关》通篇写景,歌颂太宗率领的仪仗通过潼关时威风凛凛的气势。
另外一位在初唐影响力更大的宫廷诗人,“上官体”的开创者——上官仪也曾有过类似的诗作。他在奉命酬和太宗《过旧宅二首》时也用了兴隆的意象,营造仙府妙境。
石关清晚夏,漩舆御早秋。
神摩肠珠雨,仙吹响飞流。
沛水祥云泛,宛郊瑞气浮。
大风迎汉筑,丛烟入舜球。
翠梧临凤邸,滋兰带鹤舟。
堰伯歌玄化,雇蹿颂王游。[7]514
而太宗的原诗反而更质朴放达。
其一
新丰停翠荤,谁邑驻鸣茄。
园荒一径断,苔古半阶斜。
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
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7]334
其二
金舆巡白水,玉荤驻新丰。
纽落藤披架,花残菊破丛。
叶铺荒草蔓,流竭半池空。
纫佩兰凋径,舒圭叶剪桐。
昔地一蕃内,今宅九围中。
架海波澄镜,韬戈器反农。
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7]345
两相对比,上官仪的作法就像镜子一样折射了太宗的心境。也正是因为许敬宗等人了解太宗,对游仙的生活和灵人的风姿充满了艳羡之情,更借助渲染这种情怀以标榜自己的孤高脱俗。这可在许敬宗访友人的诗作中窥见一二。
幽人蹈箕颍,方士访蓬瀛。
岂若逢真气,齐契体无名。
既诠众妙理,聊畅远游情。
纵心驰贝阙,怡神想玉京。
或命馀杭酒,时听洛滨笙。
风衢通阆苑,星使下层城。
蕙帐晨飙动,芝房夕露清。
方叶栖迟趣,于此听钟声。[7]291
此诗开宗明义,上来就点明了探访友人的目的,通篇描写了和友人畅谈妙理,把酒言欢的情景。此诗并非应制,所以写得轻松畅然,无出世高蹈的仙姿,也没有丰富神奇的想象,赋的是人间之事,全然一派现世田园自由自洽之乐。这种借助抒发隐逸情怀的田园诗作在初唐宫廷文人的创作中已经屡见不鲜。
四、嘉遁尚隐在初唐田园诗中的体现
唐初太宗出于一种矫揉造作、沽名钓誉的心理对隐逸文化的尊崇,深刻影响了文学生态,主要表现在对唐初山水田园诗歌的创作上,唐初山水田园诗人王绩的诗文最具代表性。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提出:“唐时隐逸诗人,当推王无功、陆鲁望(陆龟蒙)为第一。盖当武德之初,犹有陈、隋遣习,而无功能尽洗铅华,独存体质。且嗜酒诞放,脱落世事,故于性情最近。今观其诗,近而不浅,质而不俗,殊有魏、晋之风。”[9]
据《旧唐书》及《新唐书》隐逸篇记载,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曾在隋唐之际三仕三隐,其兄王通乃隋末大儒,与薛收、李播、房玄龄、陈叔达、李靖、魏徵、姚义等人均有交往。纪昀总结其人“身事两朝,皆以仕途不达乃退而放浪于山林。《新唐书》列之《隐逸传》所未喻也”[10]。他的诗歌风格、人生志趣深受魏晋文人,尤其是陶渊明的影响,由于家学的熏陶,又始终怀有报国之志,无奈没有伯乐识得良驹,最终隐没山林,诗酒为伴。这种作为隐逸名士待价而沽的生活状态映射在他的诗歌中,既继承了魏晋文脉,又锻造出初唐田园诗的独特诗风。
王绩在隋为官就因饮酒屡被弹劾,弃官而去时效仿陶渊明弃彭泽令后写《归去来兮辞》,做了一首《解六合丞还》。
我家沧海白云边,还将别业对林泉。
不用功名喧一世,直取烟霞送百年。
彭泽有田唯种黍,步兵从宦岂论钱?
但愿朝朝长得醉,何辞夜夜瓮间眠。[7]201
可以看出,青年时的王绩诗作风格是放浪不羁的,表达的是不愿为世俗所累的任性,是对魏晋诗风的继承,但却没有那么决绝。魏晋名士大多喜好纵情山水,竹林七贤讲求肆意酣畅、融入自然;理想主义者会对寻访而来的客人说请别挡住我的阳光,这些王绩都做不到,他的隐逸原因是未遇伯乐。
王绩在归隐期间曾赠与“辛学士”一首诗《建德破后入长安咏秋蓬示辛学士》:“遇坎聊知止,逢风或未归。孤根何处断,轻叶强能飞。”[7]232表达了他郁郁不得志的境遇。“辛学士”在和诗《答王无功入长安咏秋蓬见示》中做出了愿意提携王绩的许诺:“托根虽异所,飘叶早相依。因风若有便,更共入云飞。”[7]238也印证了王绩作诗的意图,即渴望被举荐,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
这种心理在王绩写给秦王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诗作中也有所表露。
伊昔逢丧乱,历数闰当馀。
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
余及尔皆亡,东西各异居。
尔为背风鸟,我为涸辙鱼。
逮承云雷后,欣逢天地初。
东川聊下钓,南亩试挥锄。
资税幸不及,伏腊常有储。
散诞时须酒,萧条懒向书。
朽木不可雕,短翮将焉摅。
故人有深契,过我蓬蒿庐。
曳裾出门迎,握手登前除。
相看非旧颜,忽若形骸疏。
追道宿昔事,切切心相于。
忆我少年时,携手游东渠。
梅李夹两岸,花枝何扶疏。
同志亦不多,西庄有姚徐。
尝爱陶渊明,酌醴焚枯鱼。
尝学公孙弘,策杖牧群猪。
追念甫如昨,奄忽成空虚。
人生讵能几,岁岁常不舒。
赖有北山僧,教我以真如。
使我视听遣,自觉尘累祛。
何事须筌蹄,今已得兔鱼。
旧游傥多暇,同此释纷拏。[7]198
这首题为《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的诗中,王绩通过对自己和薛收境遇的对比,表达了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和对薛收仕途显达的羡慕,以及对其不忘旧情的感念。诗中虽明写偏爱陶渊明和北山僧式的归隐,但依然关注朝堂动态,字句中的田园生活也是百无聊赖,足见其身隐心未隐,渴望被关注,被认同的心态。
于是王绩在武德中被诏征,他应诏之时写了《被举应徵别乡中故人》。
皇明照区域,帝思属风云。
烧山出隐士,治道送徵君。
自惟逢艾影,叨名兰桂芬。
使君留白璧,天子降玄纁。
山鸡终失望,野鹿暂辞群。
川气含丹日,乡烟间白云。
停骖无以赠,握管遂成文。[7]226
诗中以介子推自况,又以山鸡野鹿自谦,对出仕的喜悦兴奋之情半遮半掩,却也欲盖弥彰,正是当时天下初定怀有报国之志的文人出仕前心态的真实写照。然而这次对王绩的启用却并未如他所愿,待诏的日子很难熬,据《王无功文集序》记载:“君第七弟静时为武皇千牛,谓君曰:‘待诏可乐否?’曰:‘待诏奉殊为萧瑟,但良醴三升,差可恋尔。’侍中江国公,君之故人也。闻之曰:‘三升良醴未足矣绊住王先生也。’特判日给王待诏一斗。时人号为‘斗酒学士’。”[11]最终,王绩在“贞观初,以疾罢归。”之后,王绩曾被太乐府焦革起用为太乐丞,但不久焦革和他妻子相继病故,王绩只得挂冠而归。
在屡次仕途受挫之后,王绩开始潜心庄老之学,并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王绩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描述其生活日常:“床头素书数帙,庄、老及易而已。过此以往,罕尝或披。忽忆弟兄,则渡河归家,维舟岸侧,兴尽便返。”[12]说明王绩从庄老哲学中找到安放其身心的方式,得到了慰藉,达到了自适其适的精神状态,并且以隐士身份获得了认同。王绩的人生经历和当时的文化生态促成了其“意疏体放,性有由然,兼弃俗遗名”[11]196的个性,并“以真率疏浅之风格入初唐诸家中,如莺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13]。
王绩的诗歌在风格上淳朴自然,格律上又平仄和谐,突破了唐初宫体诗的精工婉媚,为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他最为后人推崇的《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7]209
此诗平仄相合,颔颈两联对仗工整,沈德潜认为:“《野望》五言诗,前此失严者多,应五言律诗的开始。”王绩描述了他隐居东皋看到的日色渐昏时的秋日景象。诗中化用曹操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诗句和伯夷叔齐采薇而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的典故,抒发了怀才不遇的苦闷,却写得淡然悠远。被闻一多评为:“唐初的第一首好诗”,认为“此诗得陶诗之神,而摆脱了他们的古风形式,应该说是唐代五律的开新之作”[14]。
诚如其言,王绩的诗歌上承陶朓,下启四杰,开唐代山水田园诗风之先,其诗文反映了经历了隋唐两朝大乱初定的文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王绩的为人、为文均对当朝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他在《黄颊山》中写道:“几看松叶秀,频值菊花开。无人堪作伴,岁晚独悠哉。”与王维“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以及“桂花何苍苍,秋来花更芳。自言岁寒性,不知露与霜”与“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意境几近相通,充满着对大自然的由衷迷恋和天人合一的畅然,这与他晚岁直抒胸臆的文风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诚如李泽厚所言:“由于有屈庄的牵制,中国文艺便总能够不断冲破种种儒学正统的‘温柔敦厚’‘文以载道’‘怨而不怒’的伦理束缚,而蔑视常规,鄙弃礼法,走向精神——心灵的自由和高蹈。由于儒、屈的牵制,中国文艺又不走向空漠的残酷、虚妄的超脱或矫情的寂灭……”[15]唐太宗的诗歌创作囿于儒家的礼教观念,长于雄浑雅正的创作风格,但又流露出对高蹈超脱的精神境界的向往,这就导致初唐的文坛既崇尚隐逸,又拘泥于“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的现世抱负,如此虽有助于推进了诗歌声律、内容的严整,但也导致了难有奔放绝俗的诗作产生。在当时的诗文创作中也影响了唐初的文学风貌,并为盛唐文学的走向埋下伏笔。
注 释:
①《桃李谣》:“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巫浪语,谁道许!”
②《全唐诗》卷一,全诗为:“禁苑春晖丽,花蹊绮树妆。缀条深浅色,点露参差光。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如何仙岭侧,独秀隐遥芳。”
③明胡震亨曾言:“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赡精华,最为杰作。”清人毛先舒在《诗辩低》中评价太宗的诗作:“虽偶丽,乃鸿硕壮阔,振六朝靡靡。”明都穆认为:太宗诗作“皆雄伟不群,规模宏远,真可谓帝王之作,非儒生骚人之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