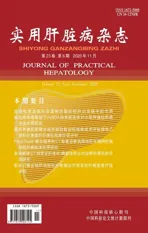肠道微生态与自身免疫性肝病*
2020-12-19王绮夏
王 睿,王绮夏,马 雄
自身免疫性肝病(autoimmune liver disease, AILD)是一类病因尚不明、具有自身免疫基础的慢性肝病。AILD的特点为机体对自身肝脏组织失去耐受,肝脏出现病理性炎症损伤,血清可发现与疾病相关的自身抗体。根据肝脏内受累细胞的不同,可将AILD分为:累及肝细胞为主的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 AIH)、累及胆管细胞为主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PBC)、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 PSC)和IgG4相关硬化性胆管炎(IgG4 related cholangitis, IgG4-SC)等。AILD的发病机制尚未阐明,目前认为遗传易感性、环境促发因素、免疫功能异常等多因素参与其中。肠道与肝脏通过门静脉、胆道和全身血液循环,在解剖和功能上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称为“肠肝轴”(gut-liver axis)。目前,肠道微生态(intestinal microbiota)参与肝脏发病机制的研究多聚焦于非酒精性肝脏疾病和酒精性肝脏疾病。近期,马雄团队首次揭示了我国AIH和PBC患者肠道菌群的组成、功能变化及其相关代谢物的改变,提示应用肠道微生态作为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具有用于疾病分层的转化医学潜力。
1 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肠道微生态特征
AIH的特点为血清出现自身抗体、血清转氨酶和免疫球蛋白G升高、肝组织检查显示中度至重度界面性肝炎,治疗上对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有应答[1]。近期,美国肝病学会(AASLD)发布了2019年成人和儿童AIH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实践指引[2],总结了肠屏障破坏、循环中出现肠道细菌来源的脂多糖等肠道微生态因素可参与AIH的发生发展,有望成为治疗新靶点。本课题组通过比较未经糖皮质激素治疗的AIH患者与健康人,揭示了AIH患者肠道菌群失调的特征[3]。该研究应用16S rRNA基因测序对91例AIH患者和98例健康人进行横断面研究,另外设置了98例AIH患者和34例健康人作为独立队列进行验证。与健康人比,AIH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下降、整体菌群组成发生改变,其特征为专性厌氧菌减少、潜在致病菌,如韦永氏球菌(Veillonella)富集。其中,殊异韦永氏球菌(Veillonelladispar)与AIH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最强,与血清AST水平、肝脏炎症程度呈正相关。应用AIH相关的四个菌属,包括韦荣氏球菌、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颤螺旋菌(Oscillospira)、梭菌目(Clostridiales)构建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其AUROC可达0.8,可较准确地区分AIH患者和健康人。随后,Liwinski et al[4]对AIH患者进行粪菌测序,证实了殊异韦荣氏球菌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同时发现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含量下降与AIH患者预后不良呈正相关。
PBC的特点为肝内进行性非化脓性小胆管破坏,可伴门静脉炎症、肝脏纤维化,绝大多数PBC患者血清抗线粒体抗体(antimitochondrial antibody, AMA)阳性,特别是AMA-M2亚型阳性对本病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高,部分PBC患者可出现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 ANA)阳性,如抗核孔膜蛋白(gp210)、抗核小体蛋白(sp100)阳性,临床主要给予熊去氧胆酸(ursodexoycholic acid, UDCA)治疗。本课题组[5]对PBC患者肠道菌群进行了横纵向研究。横断面研究纳入了60例未经UDCA治疗的PBC患者和80例健康人,纵向研究则纳入了37例UDCA治疗6个月前后的PBC患者。与健康人比,PBC患者粪菌群结构发生了改变(8个菌属上调、4个菌属下调)。其中,克雷伯菌(Klebsiella)在PBC患者中上调,与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呈正相关。通路分析显示,PBC患者细菌入侵上皮通路上调,与肠杆菌科细菌丰度增加有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经UDCA治疗后,有变化的菌属中有6个菌属趋于正常化,提示UDCA作为促内源性胆汁酸(bile acid, BA)分泌药物,可调节PBC患者肠道微生态,进而缓解病情。循此思路,本课题组[6]进一步分析了PBC患者血清和粪便BA谱以及BA与肠道菌群的关联,结果显示PBC患者BA代谢异常,表现为结合型转化为未结合型BA、初级转化为次级BA的过程受阻。UDCA治疗可降低牛磺酸结合BA水平,从而改善结合型/未结合型比例。此外,结合型BA和次级BA水平与PBC患者上调的菌属(如韦永氏球菌、克雷伯菌)呈正相关,与健康人上调的菌属(如粪杆菌(Faecalibacterium)、颤螺旋菌)呈负相关。
PSC的特点为炎症累及肝内、外胆管,引起胆管硬化、阻塞和结构破坏,导致慢性胆汁淤积、胆管纤维化,最终可进展为肝硬化和肝功能衰竭。部分PSC患者合并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其比例因地区、人种不同呈现较大的差异。有研究指出,大多数PSC-IBD患者存在结肠炎症,其肠道微生态特征类似于典型的PSC和IBD患者[7,8],提示肠道微生态失衡可能参与了PSC的发生发展。目前,国外已开展了多项关于PSC患者粪便和肠道黏膜菌群的研究,与健康人比,PSC患者菌群多样性较低,肠球菌(Enterococcus)、梭菌属(Fusobacterium)和乳酸杆菌水平上调[9-11]。
IgG4-SC的特点是血清IgG4水平升高、胆管内和肝组织IgG4阳性浆细胞浸润,常伴发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及纤维化性疾病。该类患者的肠道微生态特征有待进一步阐明。
2 肠道微生态在自身免疫性肝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
2.1 肠道细菌异位激活肝脏免疫可加重肝病进程 在生理状态下,肠道上皮细胞及相关成分(黏液层、抗菌肽、免疫球蛋白、共生菌等)共同构成屏障,同时肠系膜淋巴结、肝脏依次作为免疫“防火墙”,限制肠道菌群异位至其他器官。在病理状态下,发生“肠漏”(leaky gut),细菌及其代谢物可通过门脉进入肝脏,造成肝脏的炎症及损伤。研究表明[8],SC患者肠道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pneumonia)可破坏肠上皮,促使其他细菌,如奇异变形杆菌(Proteusmirabilis)、鹑鸡肠球菌(Enterococcusgallinarum)一同穿过肠屏障,进而引起Th17细胞介导的肝脏炎症反应。另有一项研究[12]指出,鹑鸡肠球菌可穿过肠上皮,到达肠系膜、肠系膜淋巴结、肝脏和脾脏等多个器官,从而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如AIH、系统性红斑狼疮。应用鹑鸡肠球菌特异的FISH探针,在肝脏中可检测出鹑鸡肠球菌。在动物实验应用抗生素或特定疫苗能抑制鹑鸡肠球菌生长,进而缓解疾病。
在肠道微生态失衡的背景下,机体发起针对细菌抗原的免疫反应,同时可攻击结构相似的机体自身抗原,从而诱发自身免疫反应[13]。研究表明,从AILD患者分离出的自身抗体可与特定的微生物蛋白发生反应。例如,自PBC患者来源的抗线粒体抗体(anti-mitochondrial antibody, AMA)可与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coli)蛋白结合[14],自PBC患者来源的IgG3自身抗体可与德氏乳酸杆菌β半乳糖苷酶(Lactobacillusdelbrueckiiβ-galactosidase, BGAL)结合,同时BGAL与PBC自身抗原PDC-E2亚单位的相似性可达67%[15];自PSC患者来源的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抗体(peripheral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 p-ANCA)则可与细菌细胞分裂蛋白FtsZ结合[16]。
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个体可能存在限制肠菌异位的免疫系统功能受损。多项关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的研究指出[17,18],PSC-IBD患者存在CARD-9、FUT-2和MST-1等遗传易感位点,而这些位点编码的蛋白参与肠道固有免疫及适应性免疫。FUT-2突变基因携带者发生胆道感染及梗阻的风险增高[19,20]。CARD-9则作为NOD2和TLR信号通路的下游分子,介导IL-22的产生及肠屏障的维持。CARD-9基因缺陷小鼠发生结肠炎的风险增高,可能与缺少代谢色氨酸的肠道细菌有关[21]。
2.2 肠黏膜免疫细胞迁移至肝脏可加重肝病进程 肠道淋巴细胞归巢(gut lymphocyte homing)可引起肝脏的炎症损伤。已知肠黏膜淋巴细胞表达整合素α4β7和驱化因子受体CCR9,可分别与内皮黏附分子MAdCAM-1和趋化因子CCL25结合。一项研究指出,在炎症性肝脏疾病,包括PSC患者,肝窦内皮细胞过量表达MAdCAM-1和CCL25,募集肠道来源的淋巴细胞进入肝脏,引起肝脏损伤[22]。在机制上,肝脏血管黏附蛋白(vascular adhesion protein, VAP)-1与肝脏MAdCAM-1过量表达相关,VAP-1的底物半胱胺来源于肠菌代谢及饮食,通过门脉进入肝脏后作用于VAP-1[23]。此外,研究者通过测序发现肠道T细胞TCRβ链克隆可能与肝组织来源相关,可能识别同一种抗原。除T细胞外,B细胞也参与“肠肝对话”[24]。研究表明,肝内产生IgA的B细胞亚群来源于肠道淋巴样组织,可识别肠道共生菌抗原[25]。鉴于慢性肝病,如PBC和PSC患者血清IgA水平较高,肠道产生IgA的B细胞可能由细菌活化后进入肝脏,进而参与了上述疾病的发病过程。
2.3 部分肠菌代谢物调节肝脏免疫有望缓解肝病 BA为“肠肝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理状态下,肝细胞将胆固醇作为原料来合成初级BA,后者与甘氨酸或牛磺酸结合后进入胆道、储存于胆囊。在进食状态下,BA进入小肠以促进脂肪的吸收。大部分BA在回肠末端被重吸收,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回到肝脏,其余BA则在肠菌胆酸盐水解酶(bile salt hydrolase,BSH)作用下形成游离BA,再通过7-α脱羟基酶的作用形成次级BA,通过门脉回到肝脏,BA的代谢过程受到调控,其中法尼酯X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 FXR)和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1(G protein-coupled bile acid receptor 1, TGR5)受到广泛关注。FXR位于肠上皮细胞,与BA结合后,启动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9(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9,FGF19)的转录过程。FGF19通过门脉进入肝脏,通过抑制肝细胞CYP7A1酶,可下调BA水平,维持肝脏稳态。一方面,可改善参与BA代谢的肠道菌群以恢复正常的肝脏免疫能力。研究表明,应用特定抗生素组合杀死部分革兰氏阴性菌后,初级/次级BA比例达到平衡,进而上调肝窦内皮细胞趋化因子CXCL16水平、促进CXCR6+NKT细胞聚集于肝脏,可抑制肿瘤生长[26]。另一方面,可改善BA的信号通路来治疗胆汁淤积性肝病。奥贝胆酸(obeticholic acid, OCA)作为FXR激动剂,可用于对UDCA部分应答的PBC患者。一项关于OCA双盲、对照的三期临床试验纳入217例患者,历时12个月,结果显示OCA能显著改善对UDCA部分应答的PBC患者血生化指标[27]。
色氨酸作为常见蛋白类食物中的必需氨基酸,经由肠道细菌代谢后,生成一系列吲哚衍生物,包括吲哚-3-乙酸和吲哚-3-丙酸等。这些衍生物是芳香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AHR)的配体。AHR被激活后,促进抑炎因子,如IL-10的生成,有利于维护肠屏障的完整性。此外,色氨酸衍生物能进入肝脏,调节脂质代谢、减轻炎症反应。研究表明,部分AIH患者AHR通路受抑制或非经典通路被激活,导致Treg细胞/Th17细胞比例失衡,影响其上调免疫调节分子CD39的能力。通过活化AHR途径,有望改善AIH患者的免疫微环境[28]。此外,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 SCFA)[29]、亚精胺(spermidine)[30]、氧化三甲胺(trimethylamine-Noxide,TMAO)[31]及新发现的氨基戊酸类代谢物TMAVA[32],通过调控免疫和代谢等机制,影响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它们在自身免疫性肝病发病过程中是否发挥作用,有待进一步探索。
3 总结与展望
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迅速普及和不断完善,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肠道微生态特征得以被揭示,但主要集中在前期的相关性研究。这些发生改变的肠道微生物在疾病发病机制中扮演的角色有待后续的因果性研究来进一步阐明。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热点多聚焦于细菌,鉴于肠道微生态还包括真菌和病毒等,相关系列研究的完善才有助于全面揭示肠道微生态的变化。靶向肠道微生态包括应用抗生素、粪菌移植、益生菌、噬菌体等逐步精准化的治疗手段,有望缓解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