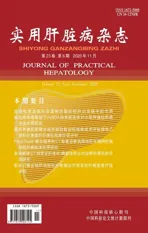肠道菌群与原发性肝癌
2020-12-19王飞雪
王飞雪,于 君
原发性肝癌(PLC)是我国乃至全球恶性程度较高的消化道肿瘤。2018年全球肿瘤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肝癌在肿瘤发病率和相关死亡率方面分别位列第六位和第四位[1]。晚期诊断、术后易复发和治疗选择局限是造成肝癌患者预后差的主要原因。提高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改善临床治疗效果对于解决目前原发性肝癌高死亡率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大量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揭示了这个既往“被忽视的器官”在人类健康和疾病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早期的借助测序技术进行的菌群分析的描述性研究到现阶段关于肠道菌群在健康状态和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探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在包括炎症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在内的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将菌群相关的研究成果转为为临床应用,包括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目前研究的方向。在这里,我们对肠道菌群与原发性肝癌的相关研究进行了阐述。
1 肠肝轴和肠粘膜屏障:肠道菌群和肝癌之间的解剖学基础
肠肝轴的概念最早是由病理生理学家提出,用来描述肠道和肝脏之间的双向联系。一方面,门脉系统收集来自肠道的血液为肝脏提供了将近75%血供,包括营养物质和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都可以经门静脉系统进入肝脏;另一方面,肝脏生成的各种物质可以经过胆道系统进入肠道,进而影响肠道的微环境。由门脉系统和胆管系统组成这种双向的肝肠轴联系是肠道菌群和肝脏疾病相互作用的解剖学基础。与肠肝轴相对应的功能学结构是肠黏膜屏障,它是维持机体稳态的重要结构。现有的观点认为肠黏膜屏障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是位于黏膜上皮细胞表面的粘液层,包括杯状细胞分泌的抗菌肽和各种免疫球蛋白,是分隔机体与外界环境的第一道生理屏障;其次,由紧密连接的肠道黏膜上皮细胞构成肠黏膜的物理屏障,保证了肠黏膜的选择性透过性;最后,位于上皮黏膜细胞间的各种免疫细胞构成肠道黏膜的免疫屏障[2]。多重屏障使肠肝轴不仅仅是简单的解剖学通路,更是维持机体稳态的功能性结构,它保证了即使大量的外界微生物和刺激因子通过肠道,只有有限的物质可以通过肠粘膜屏障参与到肠肝循环中。
2 菌群失衡和肠泄漏:肠道菌群作用于肝癌的表现
肝肠循环及正常的肠道黏膜屏障是维持机体稳态的必要条件。在肝癌患者中,肠道菌群失衡和肠泄漏(leaky gut)则是两个重要表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肠道菌群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可能作用。Qin et al在对肝硬化患者和健康人群的粪便进行菌群分析和宏基因组关联分析,得到肝硬化患者特征性肠道菌群和相关基因谱,认为在肝硬化患者中明显改变的肠道菌群组成有一定的临床诊断价值[3]。通过对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的419例粪便样本进行16sRNA测序分析,结果显示从健康状态到肝硬化阶段,肠道菌群丰度逐渐降低。但是,与肝硬化患者比,早期肝癌伴肝硬化患者菌群丰度有所升高[4]。同样,在基于西方人群的研究中,在比较分析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s, NAFLD)、NAFLD相关性肝硬化、肝癌患者和健康对照肠道菌群谱发现,不同疾病阶段肠道菌群谱与系统性炎症密切相关[5]。不同疾病阶段菌群组成的动态变化反映了肠道菌群和肝癌发生发展的密切关系。
肠泄漏是针对正常的肠黏膜屏障受损提出的一个通俗的概念。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肠黏膜通透性改变是一种普遍的病理学信号,在包括炎症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种疾病中均有所表现[6-7]。根据肠黏膜屏障的主要构成,多种检测肠道通透性的方法在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得到应用。人口服摄取探针后,通过检测尿液中分泌比例可以间接地反映肠道通透性。在活检组织,通过电子显微镜和蛋白质电泳方法检测紧密连接蛋白,如ZO-1[8]和 Claudin-1[9]表达可以直接提示肠道黏膜屏障的完整性[10]。除此之外,检测血清革兰氏阴性菌的细胞壁主要成分脂多糖(LPS)等内毒素的方法是反映肠黏膜屏障功能的间接方法。Higashi Y比较分析了肝癌患者肠道Claudin-1表达情况,发现其表达水平与肝癌细胞低分化和门脉浸润密切相关[11]。在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中,Fedirko V分析了肝癌患者血清抗脂多糖水平,结果证实抗体响应率与肝癌发生风险呈正相关,由此认为肠泄漏导致的菌群产物异位分布在肝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2]。基于人群的菌群分析和肠黏膜屏障破坏的描述性分析可以反映肠道菌群和肝癌发生发展的相关性,但并不足以作为说明肠道微生物参与肝癌的发生发展。无菌小鼠模型和抗生素介导的菌群清除的动物实验为进一步验证肠道微生物在肝癌发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提供了直接的有力证据,多个研究表明清除肠道微生物可以抑制肝癌的进展[13,14]。
3 免疫和代谢:肠道菌群作用于肝癌的主要机制
病毒感染、酒精和代谢异常等多种慢性致病因素导致的菌群失衡和肠泄漏使肝脏和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直接接触,进而引起菌群和肝脏的直接作用。现有的观点认为,免疫和代谢是菌群和肝脏相互作用的主要机制。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是肠道菌群通过介导免疫通路影响肝癌发生发展的理论基础。肠道菌群及其相关产物作为外界刺激因子可以被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引起一系列的免疫反应。目前,研究比较充分的是脂多糖-Toll样受体4(TLR4)通路。脂多糖是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可以激活TLR4,引起相关促炎反应,并能够促进肝细胞的分化,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肝癌的进展[13-15]。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证实肠道菌群也参与了肝脏肿瘤免疫微环境的调控。在肥胖相关性肝癌的动物模型中,肠道革兰氏阳性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脂壁酸(lipoteichoic acid,LTA)向肝脏移位可以调节肝星状细胞的表型变化和上调环氧合酶2(COX2),后者可以抑制抗肿瘤免疫,促进肝癌的发展[16]。
代谢是肠道菌群参与肝癌进展的另一重要机制。目前,大量研究证实胆汁酸代谢在肠道菌群和肝癌的联系中发挥重要作用[17,18]。在肥胖相关性肝癌的研究中,Yoshimoto S et al证实肥胖引起菌群代谢产物次级胆汁酸脱氧胆酸(deoxycholic acid,DCA)水平上升,通过门脉系统进入肝脏的DCA可以引起肝脏星状细胞向衰老相关的分泌表型(senescence-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SASP)转化,从而分泌各种促炎因子和促癌分子,促进肝癌进展[19]。Greten TF团队在2018年发表于Science上的研究,借助于抗生素介导的菌群清除模型和相关免疫缺陷小鼠模型,证实肠道菌群通过调节胆汁酸代谢影响肝窦内皮细胞表面趋化因子CXCL16表达,进而调节NKT细胞在肝脏中的募集,控制抗肿瘤免疫,参与肝癌的发生发展[14]。短链脂肪酸(SCFA)是另一类主要的菌群代谢产物。Singh et al研究发现可溶性纤维素饮食在改善代谢综合征的同时引起胆汁淤积并促进肝癌的发生,这一促进作用依赖于肠道菌群分解纤维素产生的SCFA而实现[20],这一研究结果对高纤维素饮食有利于健康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通过建立高脂高胆固醇饮食诱导的小鼠NAFLD相关性HCC模型,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证实高胆固醇可以通过引起肠道菌群和菌群代谢产物的改变,包括牛磺胆酸(taurocholic acid,TCA)的增加和3-吲哚丙酸(3-indolepropionic acid,IPA)的减少,促进肝癌的发生,给予模型小鼠降脂药物处理和肠道菌群调控可以有效缓解肿瘤进展[21]。现阶段,对于肠道菌群、代谢、免疫和肝癌之间的复杂联系尚需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4 早期诊断、干预和治疗:肠道菌群在肝癌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从临床发现问题,最终服务于临床是医学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如何将肠道菌群应用于肝癌的早期防治和治疗是我们进行大量基础研究的主要目的。将肠道菌群应用到肝癌的早期诊断和临床治疗是目前的主要方向。在肝癌的早期诊断方面,通过分析和比较不同阶段慢性肝脏疾病和肝癌患者肠道菌群组成,鉴定出肝癌患者的特征性菌群谱,作为临床诊断标记物是一个方向。通过分析中国人群早期肝癌患者和健康对照在慢性肝脏疾病不同阶段的菌群组成,研究者确定了最佳的30种微生物标记物,并在中国西北部和中部地区的队列研究中得到了跨区域交叉验证,证实了特征性肠道菌群标记物在肝癌诊断中的巨大的应用潜力[4]。也有研究者从血清循环菌群及微生物DNA入手,通过对肝癌、肝硬化和健康人群血清进行宏基因组学分析,结合针对血清微生物DNA的高通量焦磷酸测序,定义了一组肝癌患者特异性的血清微生物宏基因组学特征谱,并构建了基于5个微生物基因的肝癌诊断模型,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可以达到0.879,准确度也达到了0.816[22]。与传统的诊断手段相比,通过分析比较单纯肝硬化患者和肝硬化伴早期肝癌患者肠道菌群组成,基于肠道菌群和相关代谢产物寻找特异性标记物可以实现对肝硬化患者的定期无创检测,从而提高肝癌的早期诊断。
将肠道菌群应用于高危人群的早期预防和辅助临床治疗是其临床应用的另一主要方向。一方面,从肠道菌群参与肝癌发生的分子机制出发,开发相关靶点药物,包括TLR拮抗剂、FXR激动剂和相关细菌代谢产物抑制剂,应用于高危人群早期预防是肠道菌群临床转化的主要思路,临床已经开展相关靶点药物的研究。另一方面,益生菌和菌群移植是调控肠道菌群的直接方法。在基于动物模型的研究中,肝癌小鼠模型在接受混合益生菌处理后,肿瘤大小和个数显著下降,伴随肠道菌群失衡的改善和免疫微环境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可以有益菌增加、抑制炎症性代谢产物增加[23]。但是,通过直接调节肠道菌群对肝癌高危患者进行干预和治疗在临床上应用的可行性并不大,目前还没有相关的临床研究。此外,将肠道菌群应用到肝癌患者的临床治疗也是一个潜在的方向。鉴于肠道菌群在调节肿瘤免疫的重要作用,是否能够将菌群调节运用到肝癌患者的临床联合治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肠道菌群和肿瘤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答已在黑色素瘤和肺癌中得到了初步验证。那么,能否通过菌群调节提高肝癌患者的免疫治疗效果?一项在肝癌患者中联合应用PD-1受体抑制剂(Nivolumab)、万古霉素和他达拉非的临床研究(NCT03785210)目前正在招募患者阶段。毫无疑问,该研究结果将对肝癌患者的免疫治疗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们系统总结了肠道菌群参与肝癌发生发展过程的理论依据和现阶段的研究进展,肠道菌群在调节机体免疫和代谢方面的巨大潜力及其与肝脏之间密切的解剖学和功能联系为它在肝癌发生发展中发挥作用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将基于菌群在肝癌发生中相关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是目前肝癌诊断和治疗领域的一个热点,能否将肠道菌群应用于肝癌患者的早期诊断并联合应用于免疫治疗,将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