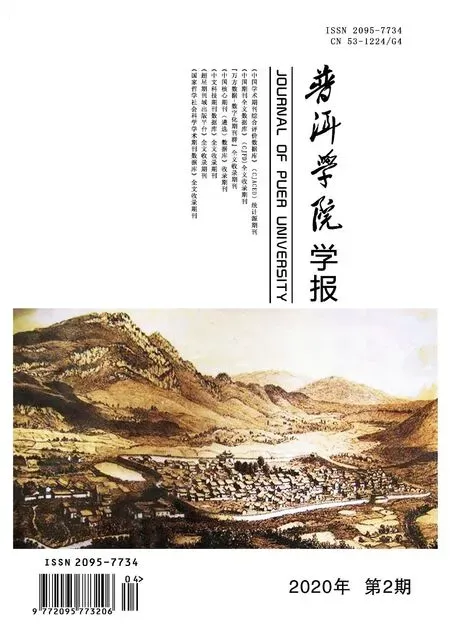山东方志鲁商义行考
2020-12-19肖红
肖 红
烟台职业学院 基础部,山东 烟台 264000
明清及近代时期山东的商品经济繁荣,许多农副产品和海产品不再仅仅用来自我消费, 而是被大批地投入市场,民间重农轻商思想发生转变。《山东通志》中描述唐朝时的泰安府,称“邹鲁旧邦,临淄遗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称一变之风”,一直蒙受东西周礼仪之教化,民俗淳朴,而到明末,“浸淫于贸易之场竞争于锥刀之末”[1],当地人转而热衷商业。各地如兖州、登州、曹州等地方志中均有类似表述。郑板桥在《潍县竹枝词四十首》里描述当时风气是:“莫怨诗书发家迟,近来风俗笑文辞。高门大舍聪明子,化作朱颜市井儿。”进一步说明了明清以后山东社会风气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商业气氛浓厚。
一、鲁商为儒商
鲁商生于齐鲁故地,长于圣人桑梓,深受儒家义理的习染,天下名之为“儒商”。鲁商根据其经商前社会阶层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官僚或地主、落第士人、平民三大类。来自官僚或地主子弟、落第士人阶层的商人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较丰富的儒家思想修养。由农而商的农民,也许没文化或文化水平不高。但因为商业活动是不同于一般简单的手工劳动或者是农业生产,它需从业者至少要识文断字、能写会算,因此农民商人也不可能目不识丁。为正常进行买卖交易,他也必须经过入行前基本的训练学习。在明清近代的中国,一切文化启蒙都不可能脱离儒教思想范畴。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明清近代山东商人多数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具备儒家的道德修养。
儒家重义。《二程遗书》中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朱熹在《朱子语类·卷24》中有:“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义利观是中国社会生活的首要问题。儒家对“利”持有超然的疏远的态度,《论语·子罕》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又有“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孔子不反对求利,但必须是有“义”之利。综合看,儒家认同在不违反公序良俗、不侵犯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个人的发展、人的价值。这样就等于强调了个体发展与社会利益的二元统一,只要合“义”,富贵、功名这些利益就具有正当性,是可以去追求的。
儒学伦理以“仁义”为基石。对于仁与义的关系,《礼记》云“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2]。认为仁爱是“义”的根本。孔子为樊迟解释“仁”的意义时,释其义为“爱人”[3]。由此推衍,义者的行为准则应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仁爱行为可以分解成三个层次:在家要孝顺亲老,主要指自己的父母;出门要敬爱兄长;由此及彼,推已及人,对待一般乡人、朋友也要有敬意而言行谨慎、诚实有信,这样就近于仁了。
二、孝悌考
鲁商多数因失去土地或家庭经济破产而入商,故他们谋利不仅是求个体之生,更多时候是为了恤养双亲、帮扶兄弟。山东各地方志中关于这类记述数量很大。如乾隆《高唐州志·卷五》所录朱美先先生,“念家贫无以奉二亲,每菽水不给……因弃去,问生计”。他进入商途后备尝艰辛,衣履痕穿,以博锱铢之入,而对父母却非常慷慨。“所过逢异乡甘膬之产,虽只旅敝装,必厚值购之,远道寄高堂者累累,皆先生饿支惫之余也。”
再如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二十六》中的商人纪学瀚,本是监生,家贫,父亲流落在外久未还家。学瀚小小年纪懂得“每伪饱以慰母”。年稍长,纪学瀚为家人团圆,三次从胶州前往辽东苦寒之地寻找父亲。前两次他一路风雪,经历“途雪没胫”“冻绝复苏”,抵达父亲所在,而父亲竟拒绝随他回家。学瀚窥察到父亲不归是因为家贫。学瀚刚刚成年,家庭贫穷本不是他的责任。正当壮年,本该养家糊口的父亲“远游辽东”,弃家不养,有失本份。而纪学瀚对父亲不嗔不怒,温和恭顺。他“弃学服贾”,在经济好转后,“备致衣履往迎焉”,而“父犹不返”,学瀚“号泣不食”,这才使父亲应允回家。归家后在已经经商但尚未致富的情况下,为使父亲称心满意,他勉力购置图籍古玩。纪学瀚的孝已达到了“克己复礼”的程度。
对兄弟鲁商同样情深义重。在他们的观念里,视兄弟不异己身。如海阳商人王铃,兄丧以后,抚养“寡嫂弱侄,恩义曲尽”“以祖遗田产生业尽让于侄”[4]。潍县侯学中“兄年老,相酬如孺子”[5]。章丘焦式泰,在妹妹的丈夫失踪以后,将妹妹及外甥迎养于家,给予三分之一田产[6]。堂邑县郭充,致富后供养父母兼及兄弟,兄长郭光“病疡甚笃”,有人说须要人用嘴将疡吸出或许可愈,“充欣然吮”,“良久,疡竟良已”[7]。
方志中还记录其他商人的孝悌,如福山萧瑶[8]、阳谷吕化蛟[9]、胶州高三重[10]等等。鲁商之孝悌有以下共性:一是家贫无计时,积极勇为,养家糊口,承担重任,不退缩、不推萎,“当仁不让”,其行弘毅果决,有君子风骨。二是“自遗甚薄”[11],厚养父母。鲁商群体常背井离乡以博微利。他们在游商途中,悭于自享,风餐露宿,筚路蓝缕。有人因过度劳累,中途染疫而死,如道光《荣成县志·卷九》中张启诚,“作贾江南,竟染病以没”。旅途中也屡有山寇路匪专门针对商人做案,杀人越货,导致鲁商身死他乡音信全无,如曹县周洇,与弟弟在河南为商,遇贼,兄弟二人被杀[12]。山东商人在资本积累的初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有时是生命危险在营商,他们的钱财来之不易。面对父母兄姊,他们慷慨将养,处处周全,令其优游度岁。
三、泛爱众考
鲁商致富后多数随着资本的增大,改善自己家族生活,进一步惠及宗族,再博施济众。如淄川人王廷柱,幼年家贫,成年后在县署充当筦库吏。后逢机会他代办本县盐运,十年之间,“盐务盛而家以渐丰”。他家兄弟三人分家已久,在兄长殁后,他的侄子“俱未成立”。王廷柱帮他们置办家当,使他们独立生活。乡里有事时,他“修桥补路,倾囊不惜”。他资助乡里几桩很大的工程,“若凿双山口二十余里崎岖之路,建六龙桥二十一空于西门外,修护城壩数十余丈于孝水滨”,县志评价他是“任人所不敢任之事,收人所不能收之功”[13]。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二十七》中许树德,“苦贫,弃儒而贾”,家道兴隆后,许氏族人生活“甚赖之”,“而不言其功”。许树德不以为意,他慷慨承担家族祭扫费用,为族人交钱免徭役,在城西设置义学,“延师训乡党子弟,择其佳者厚恤以成就之“。乡人称道他是“一世人杰”。
泽及宗族,乡邻守望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自儒家教诲。传统鲁商重视谋利,却没有因谋利而薄人情。他们以商人身份行儒家之道,践行儒家历史使命,履行儒家社会责任,做到“义以生利,利以平民”[13]。这是鲁商商业伦理的精髓,尤其在家国有难时,更显示出了鲁商以天下为任的士人情怀。
四、济天下考
清末民初及至近代,随着外国列强入侵,我国数次面临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机。这时期的鲁商艰难经营,苦苦挣扎,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命运自觉融为一体。他们的勇赴国难,兴商济世,抗击外敌,表现民族大义。
宋棐卿(1898-1956 年),益都(山东青州)宋王庄人。他在1920 年赴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兼修化学课程,1922 年回国。1932 年他在天津创建了“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亚公司。东亚公司生产的名牌产品“抵羊牌”毛线在与英国“蜜蜂牌”、“学士牌”毛线和日本“麻雀牌”毛线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维护了民族尊严。抗战期间,宋棐卿编制宏大全面的发展计划,后来将其命名为《我的梦》。该书中主义篇中有“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为一般平民谋福利”等想法,还有服务社会事业,建立康乐站、负责帮助同胞谋出路;创立平民医院;创办各种刊物等理想。它体现了一个优秀民族企业家创办实业,强国富民,为社会造福的理想[14]。
清末民初日本占领青岛,在民族存亡之际,山东商人爱国情绪高涨,积极行动与外资经济掠夺抗争。他们举行会议,共同商讨对策,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自强,商会成员一致约定“与日人断绝往来办法:(一)所有日本各银行纸币、银币等,概不兑换;(二)凡有与日商往还账项,限一星期结清,不得再通往来云。又济南通衡僻巷,各商家一律揭悬白旗,上书‘力争青岛,杀敌图存’等字样。而传单纷飞,大有坚持到底之概”[15]。
其余各地方志所载不一一尽述,鲁商的气节担当已如上例。他们在民族危难时,视国如家,视民族如父母,把国之存亡看成是自己最大的利益。在乱世咬紧牙关经营实业,把它当成自己藉以救国的手段,不到破产不肯放弃,极端情况下能做到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如丛良弼。
五、仁义动因考
鲁商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奉行儒家教诲、以义为商,对其动因进行如下分析。一是明清王朝以儒家思想化育民众,因此制定了一系列体现“仁爱”思想的乡村礼教措施。其中部分内容鼓励了商人在乡里的孝悌赈济行为。如万历《明会典·卷十七·户部·灾伤》规定:“令抚按官晓谕,积粮之家量其所积多寡以礼劝借。若有仗义出谷二十石、银二十两者,给与冠带;三十石、三十两者,授正九品散官;四十石、四十两者,正八品;五十石、五十两者,正七品。俱免杂泛差役。出至五百石、五百两者,除给与冠带外,有司仍于本家竖坊牌,以彰其义。”其他奖励政策因时而异,具有一定灵活性。有时给予官职,有时免除杂役,有时颁发匾额,有时旌为义民,还有很多是在方志中记录行善之人的善举和生平事迹。这些措施给商人带来精神上的荣光,鼓励了后续更多的孝义之举。
商人救济乡亲的行为有时也是他的内在需要。如当饥荒或自然灾害发生,乡民的正常生活受到干扰。他们或变卖家产以维生,或举家流浪乞讨,也有灾民聚众为匪。在得不到赈济的情况下,地方治安秩序被破坏。商人在这种混乱局面下,无法正常进行商品贸易。他们积蓄的金钱、粮食既为他们提供了物质的安全,同时也使他们面临巨大风险。有远见的商人选择主动与乡邻分享他的财富——粮食或衣物,通过这些举措化解他与贫穷乡民之间的对立状态,同时也为子孙后代积福,达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以免“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鲁商的孝行义举为他们赢得乡民的推崇和赞美。各地方志里商人传记中篇末常有“乡人德之”“人竞高其行”“一时义声倾动乡里”“乡人至今称之”“人皆为送匾额”等颂语。这树立了商人在本乡社群中的地位和威望,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形收益。人在物质需求未得满足时,首先会倾尽心力去争取利益,以满足所需,如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所显示的那样。而当他通过努力成功后,如果一切奢侈美好的享受都尽数拥有了,他常常会发现自己的幸福感仍有缺憾。他会回望过去,观注家乡和童年时的人,并产生高尚的利他愿望,从帮助他人中取得想要的幸福和满足。鲁商们对桑梓乡亲的恩泽,使自己从狭小的个人空间中上升,以善的姿态面对家乡,进而面对社会,并产生强烈的仁爱天下的责任感。他们因善行收获的社会赞誉和敬慕,恰好补足他欠缺的幸福,使他们精神和心灵达成圆满。他们在追求个人圆满的同时,更使他人受益,两方面可以说相得益彰。
康德说:“这个世界唯有两种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震撼,一是我们头顶的灿烂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规”[16]。鲁商以义为商的传统应从历史中走出,被新时代同行接受,转化为一代又一代鲁商最稳定的道德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