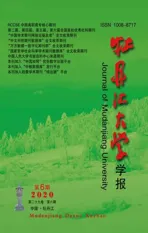确认判决可执行争议的“帕累托改进”对策
2020-12-19邢晨仰
邢晨仰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
一、引言
“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①“权利义务主体明确”和“给付内容明确”②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应该具备的条件,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应当予以审查。虽然有这些关于执行依据内容明确性的规定,但由于这些规定过于简单,没有进一步明晰认定裁判文书内容不明确的情形,以及内容不明确时的解决途径等问题。在实践中,法院对于裁判文书是否具有给付内容的判断存在分歧,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认定标准。而对给付内容有无的认识分歧主要体现在确认判决的裁判文书上。
二、确认判决是否可执行的司法认定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裁判文书发现,对于确认判决,法院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其“没有给付内容”为由,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案例一:刘某1、刘某2继承纠纷案
申请人刘某1于2017年9月28日向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日指定本院执行。本院立案后查明,(2017)冀1003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确定:被继承人刘维新位于廊坊市广阳区银河小区1号楼6单元102室房屋一套扣除增购面积44.445平方米后的部分及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理赔款中的117544.78元,由再审申请人何2某、被申请人刘某1、夏某、刘某3、刘梦齐五人各得五分之一。本院认为,上述判决确认了各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财产享有继承权的份额,系确认判决,没有给付内容。最终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刘某1的执行申请。③
这样的判决结果可以说是见怪不怪了。对于确认判决,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被驳回,即使申请复议,基本上也难逃再次被驳回的命运。以案例二为例予以说明。
案例二:北京京文联发教育文化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案
该案中鼓楼区法院判决:“变更京文公司与宏昌公司于2014年6月26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关于租赁物建筑面积的约定,自2015年7月1日起,京文公司按照建筑面积7832m2向宏昌公司支付租金。”原审法院认为,“在本案中,法院的生效判决主文并无具体的给付内容,不具有执行标的的明确性,只能作为给付之诉胜诉的前提和基础。”遂裁定驳回宏昌公司执行申请。申请执行人申请复议,又以同样的理由被驳回了。④
这样的认定思路不仅体现在裁判文书上,确认判决不能被执行的观念在与执行局的工作人员交流中也同样得到了印证。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坚持这样的观点,并将确认判决作为判断案件能否执行的标准之一。而实践之天平不是单纯向这种做法倾斜的,一些法院没有将确认判决的执行案件拒之强制执行程序之门外,反而对这些案件进行立案登记并予以执行,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也就是说一些法官跳出了“确认判决,没有给付内容”的窠臼,对所谓的确认判决的执行性予以肯定。以案例三为例予以说明。
案例三:李勇与王燕离婚纠纷案
该案判决书法院认为,虽然法院判决房屋所有权归属原告是确认所有权的判决,但结合判决书的文义等能够将执行内容明确化、具体化,即协助办理房屋不动产权属登记。因此该判决具有给付内容。⑤然而这样的执行判决毕竟是极少数的,有些确认判决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以案例四为例予以说明。
案例四:曲礼文、刘开旭与复州湾街道办事处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
该案立案后,执行法院针对生效判决判项“一、确认复州湾街道办事处在2010年10月27日公示的海域使用权人为镇南海盐场,现经营者为崔宝文、宋长利、李述傲、苏少峰、周如贤、杨占东、杜广玉、王久祥、战德强、赵玉和、赵世卫、宁波、阎德文、孙立新的12个养殖圈圈坝征用补偿款中的6744030元归曲礼文、刘开旭所有”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但被执行人提出异议,在复议程序中,法院认为只有给付之诉形成的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才具有可执行性,遂又以“执行行为的异议请求正当”为由,撤销了已经做出的执行裁定。后申请执行人又申请复议,中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曲礼文、刘开旭的复议申请,维持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4执异66号执行裁定。⑥
如果说前三个案例说明不同地区的法院在对确认判决执行性问题的认定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那么第四个案例则能说明同一个法院在执行程序的不同阶段对确认判决有无给付内容也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多数法官还是坚持确认判决不具有给付内容这一立场,当事人凭一纸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申请不予受理或被驳回几乎成为毋庸置疑的处理方法。多数法官将此标准奉为圭臬,这种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而认为确认判决结合文义等能将执行内容明确下来的做法似乎是对普遍做法的颠覆和挑战。
同样依据《规定》和《民诉法司法解释》,对同样性质的裁判文书的执行性问题出现截然相反的判定,不禁让人思考确认判决有给付内容吗?不同法官是基于何种理由做出的判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对这一问题的司法认定?这都需要带着这些疑问,在下文进一步梳理确认之诉的相关法理。
三、确认判决可执行争议的梳理
通过对前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很容易发出确认判决是否一律不可执行的疑问。实践中,关于确认判决是否可执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然而通过对确认之诉功能定位的法理分析,坚持确认判决不可执行或是明智之举。
(一)确认判决是否可执行的观点之争
确认判决是否可以执行的争议在实践中已经露出端倪,相应地,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现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确认判决不可执行。这是诉讼法理论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也是当前我国的主流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确认之诉就是要求确认争议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是否合法有效之诉,没有执行力。认定确认判决是否具有可执行性实际上是审查确认判决是否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标准的问题。因此,该观点实际上将确认判决一律排除于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范围之外。
第二种观点认为确认判决可执行。因为确认之诉经常与给付之诉混同,实践中给两者往往是被合并提起的。赞同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第一,案件起诉到法院多半说明双方的矛盾已经白热化,当事人起诉的目的不仅是想要使权利或某种关系得到确认,重要的是希望纠纷能够得到终局性地解决;第二,诉的客观合并在实务中被应用的频率较高;⑦第三,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化,法院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宣告原告享有某种权利,这必须得到尊重,人们必须承认和服从这种宣示;第四,申请被驳回或不予受理会增加当事人讼累,造成司法资源浪费,申请人若再次起诉也可能构成重复起诉。从这几点理由来看,法院应该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需要被申请人协助才能实现权利的确认判决,从而能够帮助法院解决实务中出现的如前述案例三的执行问题,让当事人权利不再停留在纸面上。但该观点似有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倒推回去再建构理论的意味,完全不顾确认之诉的法理基础。此外,如果认为确认判决可以执行,则意味着确认之诉的纠纷解决功能要比给付之诉更全面,不再具有辅助性的功能,那么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还有同时存在的必要吗?
第三种观点认为确认判决部分可执行。不能笼统地说确认之诉没有给付内容,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某些情况下承认确认判决可以执行。这一观点是欲在两种观点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地带,避开攻击,然而增加了实务操作的难度。因为该观点的支持者没有明确指出在哪些情况下应该承认确认判决可执行以及具体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他们几乎都是从分析个案入手,认为某一类确认判决有给付内容,可以执行。诚然,如果这一观点能够达到理想化的预期,争议就能迎刃而解了。但是这种以分析个案的方式论证确认判决具有给付内容,大有为了解决个案而挑战权威理论之嫌疑。况且,如此一来,确认之诉的诉讼法理便不能自洽了。同样,对于承认确认判决可执行的观点也存有这样的质疑。
(二)确认之诉在学理上的功能定位
学界普遍认为在三大诉讼类型中,确认之诉是后来者。确认之诉的功能主要有两个:第一,确认之诉具有预防功能。它只是把当事人之间的某种实体权利或者说法律关系固定下来,对此不加以改变,因此它没有执行力,自然也就不能作为执行依据。提起确认之诉只是为了达到预防纠纷发生的效果。有学者称其是一种权威性声明、[1]警示性宣告,[2]称其仅具有证据性效力。因此,确认之诉对权利的保护不够彻底,可能需要再次提起给付之诉才能完全解决争议。第二,确认之诉相对于给付之诉还具有补充功能,在给付之诉不能解决一些问题的情况下发挥辅助作用。那么,这一功能的潜在意思就是起诉时以提起给付之诉为原则,在当事人的诉求不符合提起给付之诉的条件时,才先提起确认之诉,将需要保护的权利确定下来。⑧
综上所述,在对确认判决是否具有可执行内容的观点和确认之诉在学理上的功能定位进行考察与分析之后,还是赞同第一种观点——确认之诉不具有执行力,确认判决没有执行内容为宜。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确认之诉具有预防功能,它只是把当事人之间的某种实体权利或者说法律关系固定下来,对此不加以改变,因此没有执行力,自然也就不能作为执行依据。
第二,关于确认之诉没有执行力,两大法系的学者已经用大量的笔墨加以论证,目前如果没有足够的论据做支撑,贸然颠覆权威无法回应与相关制度的矛盾如何解释的问题。比如诉讼标的、诉的分类、诉的合并、判决的既判力等一系列与确认之诉相关的法理问题。
第三,为了解决一小部分问题就否定学界通说,付出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可能严重不成正比,违背经济效率原则。
第四,撰文支持确认判决有执行内容的人多来自实务界,支持的理由也是从便于实践操作的角度出发,理论论证不充实,会导致实践与理论两张皮的现象,同时他们也没有将“确认判决可以执行”的假设置于民事诉讼法的整体框架中,考量这与其他制度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四、确认判决可执行争议的预防性对策的提出
帕累托优胜,也叫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这一概念最早在研究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时被使用,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如果在使自己处境更优的同时又未损害旁人利益的话,就在资源配置方面实现了帕累托改进,经济效率便提高了。同理可得,对于确认之诉可执行争议问题的争议来说,另辟蹊径,在坚持传统的确认之诉没有执行力的前提下,提出帮助确认判决可执行争议问题走出困境的对策,就是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本文第一部分的四个案例表明,不同地区的法院,甚至同一个法院在认定确认判决是否可执行的问题上见仁见智,各执己见。面对实践中出现的争议,笔者仍然选择支持确认判决不可执行的观点,并不是想畏葸不前,故意回避问题的解决。而是企图逆流而上,对确认判决的相关法理追本溯源,通过探究确认之诉的功能、梳理确认之诉与确认判决的关系以及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关系,希望在不动摇主流观点的前提下,提出有助于解决确认判决可执行争议问题的对策。
(一)应当限制确认之诉确认对象的范围
1.限制确认之诉确认对象的原因
确认之诉具有预防功能和补充功能,但这两个功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的实际作用是值得怀疑的。首先,确认之诉是移植的制度,其与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是一同出现的,在我国未经历一个发展的过程。其次,德日等国通过确认利益限制对确认之诉的,我国则是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里采用罗列方式明确确认之诉的多种案由,⑨主要是对各类法律关系和绝对权的确认。当事人不能以规定以外的案由提起确认之诉。但司法实务中还存在对这些案由以外事项的确认,比如法律行为构造要素效力、事实等的确认。经过仔细分析便可以发现,有些案由根本不属于诉讼法理上确认之诉的范围,其不过是专门为法院解决争议而生,却被贯以“确认”之名。⑩
也就是说,我国确认之诉中确认对象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诉讼法理上的范围,其功能被扩大使用。11因此,这也是导致一些申请人以确认判决为依据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以执行依据没有给付内容为由驳回执行申请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鉴于确认之诉补充性的特点和其解决纠纷的能力,不同国家都想办法限制提起确认之诉的条件和范围。大陆法系国家,比如德国,就用“确认利益”的概念对确认之诉地提起加以限制。12而我国确认之诉的对象范围泛化,各种物权、股权、证券权利,各类身份关系等都包含在确认对象之中的现象,不仅导致诉讼标的功能障碍,也给相关制度带来了负面影响。13随着确认之诉泛化产生的确认判决数量越来越多,当事人以确认判决为依据申请执行被拒绝的案例也越来越多。14
2.限制确认之诉确认对象的具体做法
针对上述现象,迫切需要对确认之诉确认对象的范围进行限制。理论上,确认之诉是对法律关系或实体权利进行确认,宜在此法理基础上,对法律明确规定能够确认的对象提起确认之诉。另外再针对不同类型诉讼标的的特点,设定相应的限制条件。在限制过程中应考虑的因素主要有:第一,确认的对象应当存在法律效力上的争议。这要求确认的对象不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可能包括某些事实。15第二,要求确认的应当是实体权利。因为在诉讼中,程序性事项是由法官负责审查的。第三,根据类案的特征,考虑当事人要求确认的对象在解决争议方面是否彻底。这是由确认之诉补充性的特征决定的,也应该成为本文第二个对策中法官行使释明权时的考量因素。
在对确认对象作出这些限制后,能过滤掉一部分浑水摸鱼的“确认之诉”案件。如果这些案件当事人请求确认的内容将不产生法律效力或者能够通过单独提起给付之诉或者一并提起给付和确认之诉,构成诉的客观合并的话,过滤这部分案件反而能够让当事人尽快寻求其他的救济方式,加快实现权利的速度。在此提出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对于前面提到的一些不产生法律效力或程序性的事项,不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加以解决,是否可以请公证机构进行公证,如果以后需要起诉的话,公证机构的公证可以作为对当事人有利的有证明力的证据,增加在诉讼中胜诉的筹码。
(二)法官应当行使释明权以引导当事人16
1.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可行性
(1)顺应政策的导向
明朝朱柏庐《治家格言》有云:“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挖井。”而法官通过释明,引导当事人合理表达诉求,或进行诉的合并审理,最终得到给付内容明确的执行依据。如此可以在不触动确认之诉不可执行的法理基础前提下,实现从源头解决这一问题的目标。这不仅体现出了未雨绸缪的智慧,而且与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和7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要完善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的要求以及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改革思维相契合。
(2)诉的类型之间界限的非绝对性
德日按照法官认可当事人请求时所作判决表现的效果或者内容的差别,将诉分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与形成之诉,相应地,诉的类型不同,当事人请求法院作出承认请求判决的形式就有所不同。
然而,高桥宏志教授认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形成之诉三者之间不是明朗的、非此即彼的关系。[3]日本的小山升教授认为,诉的三种分类是一种关于手段性和分类技术的概念,因而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并不是一种“依据这三种诉之类型就可以将所有诉之类型都涵盖在内的”分类,或者说,这并不是一种达到“除此之外的其他的其他分类都不能成立”之程度的全概括性分类。除了这三种类型的分类之外,也并不是不能都对判决内容作出区分了。而且对于执行法上之诉,未必都能容易地被纳入到这三种诉之类型中。17日本学者村松和德更是认为,在形成之诉的类型被人们意识到以及获得承认之前,该类诉讼的多数都被理解为给付之诉。
比如在判决仅确认了房屋所有权归属,但没有明确后续的登记过户义务的情况下,判决主文中虽有“确权”二字,但依据诉的分类,这类案件并非都属于真正的确认之诉,从而能被规范、完整地纳入某一种的诉的类型之中。[4]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官裁定不予执行的确认之诉中,事实上有一部分可能并非确认之诉,这或许是法官的误判,也或许是法官难以逃避的认识局限性使然。从哲学上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如果法官实行释明权,进行诉的客观合并是完全可以的。
(3)基于司法实践和诉讼经济的考量
基于前一部分对诉的类型之间界限的分析,得出三种类型的诉之间并非如磁铁同级相斥原理那样,它们之间会有共生的关系。依据这一分类也不能完全区分判决的内容。因为通常认为确认之诉只是与更加广义上的确认判决的一部分相对应,诉的类型与判决类型并非是一种简单对照关系。[5]在现实中,给付之诉与确认之诉往往是被合并而提起的,实践中不少确认判决之中混有给付判决的内容。这种做法一方面是考虑到确认判决在纠纷解决方面的能力较给付之诉来说相对稍弱,一并提起给付之诉更有利于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当事人不必担忧因未来可能发生的争议而再次起诉,减少讼累,法院也可以将纠纷一次性解决,节省司法资源。
综上所述,假如由法官行使释明权,引导起诉的当事人将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一并提起或者在当事人欲提给付之诉却表述为确认之诉的情形下加以引导,使当事人的执行申请满足《规定》和《解释》中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那么即使后来当事人未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胜诉一方仍然可以依该判决申请强制执行,避免胜诉方在法院以确认判决没有给付内容而驳回申请时吃闭门羹。
2.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具体做法
(1)可以释明的阶段
法官行使释明权的阶段分为两个。第一个是在立案过程中,第二个是在立案后到法庭辩论终结前。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要在法庭辩论终结前。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立案阶段法官的释明并不会与立案登记制冲突,对当事人的起诉条件进行形式审查不等于不审查,法官可以引导当事人将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18
(2)释明时应考虑的因素
即使考虑立审执协调,从源头解决执行难等因素,法官也不能毫无限制地引导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引导当事人在能提起给付之诉时就不必提起确认之诉。总的来说,法官释明时主要应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提起确认之诉的必要性和确认之诉解决纠纷的效果。这要求法官判断当事人的权利是否有通过确认之诉进行保护的必要、[6]与给付之诉等其他救济手段相比,通过确认之诉是否可以解决潜在的纠纷。假如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法官可以通过释明引导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提起给付之诉或者引导当事人在原有诉求之上增加新的诉讼请求,使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兼具给付与确认的内容。如果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能够构成客观的诉的合并的话,法院便可以依法将案件进行合并审理。[7]其实这两种路径殊途同归,均是为了让当事人最终可以得到给付内容明确的裁判文书,符合法律规定执行依据内容明确具体的要求。在当事人权利无法实现时,便可依此执行依据申请强制执行。同时也降低当事人再次起诉的可能性,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19
第二,当事人起诉的目的。当事人作为普通公民,可能无法准确表述自己的诉讼请求,不能将自己的请求精确地转化为法律专业语言。因此需要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的人的辅助。特别在没有代理律师的情况下,法官无疑是距离当事人最近的法律专业人士。因此,如果了解到当事人起诉是为了使纠纷得到终局性地解决,而不仅仅是要求法院确认自己的权利或与对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的话,仍然回到上一个考虑因素中的路径上。
第三,法官要特别注意行使释明权时不能逾越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的界限,同时要保持超然中立的态度,毕竟如果引导原告在诉讼请求中增加给付的内容,极易导致被告的不利益。[8]
注释:
①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的条件之一。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执行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权利义务主体明确;(二)给付内容明确。③参见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2019)冀1025执312号执行裁定书。
④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苏03执复48号执行裁定书。
⑤参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执异423号执行裁定书。
⑥参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执复150号执行裁定书。
⑦这是由确认之诉的解决纠纷及实现权利的实际能力较弱决定的。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伊藤真在《确认诉讼的功能》中也承认,在现实生活中,给付之诉与确认之诉往往是被合并而提起的。
⑧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如果针对特定款项的给付之诉可能由于暂时不满足要件事实而败诉,那么即使款项的数额确定,针对相同款项也可以预备合并的方式提起确认之诉。对此有权释明或者法院直接以诉讼标的在量的方面减少为由(即部分胜诉),支持确认请求 。
⑨在2011年修订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有11种三级案由明确使用了“确认”一词,四级案由中也存在一些确认纠纷。比如物权确认纠纷、确认合同效力纠纷、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等。
⑩例如,《婚姻法》第10条关于婚姻无效的规则就不属于确认之诉,而是宣告婚姻无效的非讼案件。
⑲参见参考文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