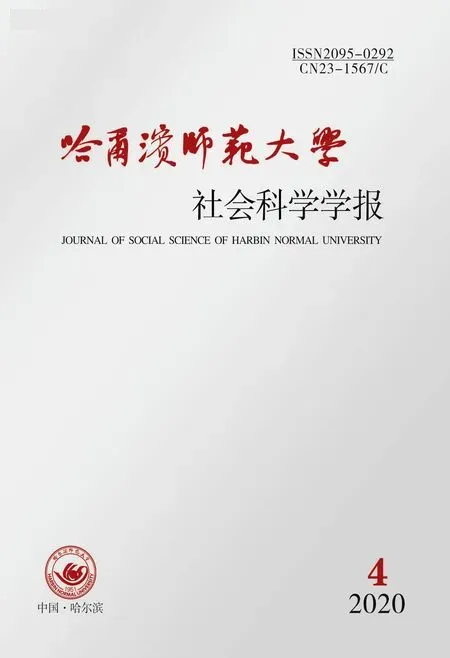自然·两性·文化
——托尼·莫里森和艾丽斯·沃克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比较
2020-12-19刘娈
刘 娈
(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黑人的民权运动在50年代中期重新兴起,到60年代后期形成高潮,黑人民权运动使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黑人女性在对父权制文化和受压抑现状的体会中,总结出妇女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此,与黑人民权运动密切相关的女权运动也迎来再一次的发展期。同时,随着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大量自然资源被掠夺,产生巨大的生态破坏,环境保护运动自此开始。生态女性主义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女性主义研究和生态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一种社会思潮。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伯尼在其著作《女权主义·毁灭》中首次提出,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和自然所受到的破坏有着直接的联系,她号召女性发动一场生态革命,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以来,西方文化的主要权力结构就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又赋予二元对立中的一方以特权,“以此类推,男人因而优于女人,白人优于黑人,富人优于穷人,第一世界优于第三世界,那些处于对立面的就被剥夺了完整的人所有的权利”[1](P57-64)。而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则从根本上“批判西方文化传统中自然与理性二元对立的思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与压迫,主张人与人之间,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稳定、和谐的关系”[2](P21-30)。这一思想将促进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作为奋斗目标,其最具革命性的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早已接受的现代科学观提出了挑战,主张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3](P20-23)。由此,生态女性主义者倡导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男女平等,种族、文化多样性的社会。
20世纪70年代,黑人妇女文学作为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碰撞下的产物也开始兴起,美国黑人女作家异军突起,发展成一股独立强大的学术力量,在世界文坛掀起了黑色浪潮。托尼·莫里森、艾丽斯·沃克就是这次黑色浪潮中的弄潮儿。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在作品中以多元的视角,阐释出人与自然,男性和女性以及多种族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都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不谋而合。艾丽斯·沃克作为黑人女权主义的辩护者,早在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出现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和榨取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征服和压迫之间的同源性,她主张自然与人类、男性与女性之间尊重差异,相互依存,和谐共处。这样清晰而明确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也在沃克的作品中展现出来,随后她又融入了更多的自然元素。
本文将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对托尼·莫里森和艾丽斯·沃克的部分文学作品进行解读,旨在阐明,这两位美国黑人女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作品中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建立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强烈企盼。通过理解她们作品中蕴含的丰富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内涵,也将更深层次地帮助读者对这两位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拥有全新的认识。
一、 女性与自然
1. 女性与自然的相似性
生态女性主义将女性与自然联系起来,揭示出自然的被统治和女性的被压迫之间是相似的。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卡林·沃伦在《女性主义与生态学》中所提出的,“对自然的压迫和对妇女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了解自然和妇女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4](P3)。自然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被视为被征服和统治的对象以及没有发言权的他者,它被迫成为被人类所开发利用的“资源”,用以服务人类的需求和目的。与自然相似,在女性与男性相处的过程中,一直扮演附属品的角色,她们受男性的支配,没有决定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她们是男人身后的影子,永远看不到真正的自己。莫里森和沃克充分认识到自然与女性之间的这一相似点,并在她们的作品中呈现出来。莫里森的长篇小说《最蓝的眼睛》中的小主人公佩科拉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黑人女性。小说分为“秋,冬,春,夏”四篇。秋天,万物成熟的季节,佩科拉第一次月经来潮,暗示着她发育成熟,渴望得到爱与关怀,然而在看重“蓝眼睛”的社会中,她遭到周围人的讥讽、男同学的围攻;冬天,最寒冷严酷的季节,她被父母打骂,被白人当面羞辱;春天,生机盎然的季节,她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强奸,扼杀了她的精神生命;夏天,她早产下一个死婴,精神失常,在骄阳似火的季节中感受到了冷若冰霜。同样,在沃克的代表作《紫色》中, 14岁的主人公茜莉活得没有尊严,没有自我,在继父眼里,她是随时可以泄愤的工具;在母亲看来,她与男人鬼混,恬不知耻。她的苦楚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只能不断向上帝写信,寻求心灵的安慰。后来继父在没有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又把她嫁给了鳏夫X先生,就好像卖出一件商品或一头牲口一样。柔弱的茜莉无力反抗,只能从命。
同时,莫里森和沃克在她们的小说中又以黑人女性的独特视角再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与迫害。莫里森小说《柏油孩子》中的骑士岛,原本是一个众人向往的桃花源般的地方,但随着白人商人瓦力连等人的到来而发生了巨变。“人类在没有起伏的地方堆积出起伏,在没有空洞的地方掏出空洞”。“河流从它原来的居住地被驱逐出来,被迫进入不熟悉的地盘,无法畅通无阻的流淌”。“云朵聚集在一起,观察着河流急匆匆地绕过林地,漫无目的地闯入山根,直到筋疲力尽,病得悲悲切切”[5]。人类对自然如此无序和无节制的开发和掠夺最终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让原本是绿洲的骑士岛成为一个连苍蝇都无法生存的恶臭岛。在沃克的小说《紫色》中,主人公茜莉的妹妹内蒂,向她描述了她所生活的非洲奥林卡村受到迫害的场景,曾经安静祥和的村庄几乎一夜之间就沦为了白人的领地,他们霸占了奥林卡村的田地,拆毁了所有的房屋,砍光了屋顶上村民顶礼膜拜的大叶子树,将他们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片橡胶园。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古老而平静的原始生活,还对原有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在小说《我亲人的殿堂》中,女主人公莉西的黑人母亲与动物们生活在丛林中,她们相互依靠,相互陪伴。随着男女部落的合并,当男性开始出现等级观念时,女性和动物都逐渐丧失了自由,女人被男人强行地占为己有,对自然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杀死动物,食其肉,穿其皮,把它们的牙齿和骨头当成装饰品,森林和自然成为可以分割的东西,一块一块地分属于各个部落。正如主人公莉西所描述的,“动物和女人孩子被逐出家园,我们一起成长、共同享受森林中最喜欢的地方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6]。莫里森和沃克在小说中对女性压迫和对自然破坏的描写充分表明,女性如同自然,代表的始终是原始和被动。
2.女性与自然的融合
由于自然与女性之间存在相似性,又使得女性更亲近自然,更懂得自然。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主张将自然和女性相联系,强调女性要与自然共同生存,和谐发展。正如沃克在一次采访中所说,“人们不仅为了生存,而且要繁荣,要热爱人生”[7](P135)。莫里森和沃克笔下的自然,永远是人类最可靠、最忠实的朋友,它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可以栖息的场所,而且永远是他们精神的庇护者。那些在男权社会中受到肉体和精神伤害的女性,在美好的自然中,总能寻求到精神的慰藉。在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赛斯的婆婆贝比用来传教的“林间空地”和赛斯的女儿丹芙的“黄杨树屋”都让读者感受到女性与自然融为一体,有更加亲密的联系。贝比婆婆带领黑人男女为活着和死去的同胞尽情地号哭、唱歌和跳舞,周围的自然与他们共鸣,大地共颤,用以宣泄心中的苦闷,林间空地滋养了人们的心灵,让黑人妇女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一个由五丛黄杨灌木交错而成的房屋帮助小丹芙躲避了可怕的哥哥们,在生机勃勃的绿墙的遮蔽和保护下,稳定了她年幼不安的心灵,让她变得坚强自信。在《所罗门之歌》中,奶娃的姑妈派拉特是一位自然的女儿,她亲近自然,“把树上的松针用来做褥垫”;她小的时候很喜欢咀嚼松针,这样“她的嘴里就有一股树林的味道”[8]。因为热爱自然,她的房子处在一片松树林中,与旷野融为一体。多年来,她像大树一样保护着家人,以宽广的胸襟帮助奶娃走出狭隘的自我世界。
在沃克的小说《紫色》中,主人公茜莉的精神庇护者不是上帝而是大自然,当她遭受到丈夫的毒打时,她会将自己想象成一棵没有感情色彩的树;来到孟菲斯创业后,她住在一所花园一般的房子里,房子按照她的设计布局,栩栩如生的动物雕像摆满了整个房子和花园。小说的结尾处,在茜莉写给大自然的信中,收信人是“亲爱的上帝,亲爱的星星,亲爱的树,亲爱的天空,亲爱的人们,亲爱的所有一切”[9],此时她成为一名真正的妇女主义者,与自然融为一体。在散文集《寻找母亲花园》中,沃克在描写自己的母亲时说:“我的母亲只有在培育花卉时才会容光焕发,这张容光焕发的脸也是她留给我的遗产,教导我尊重所有反映生活和珍惜生命的东西。在这份珍惜生命的遗产的引导下,我在寻找母亲花园的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花园。”[10]莫里森和沃克在小说中向读者展示了黑人女性在充满生机的自然中,通过努力和斗争所建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突出了在大自然中黑人女性欣欣向荣的积极形象,既彰显了自然之美,又展现了个体女性百折不挠、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二、女性与男性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由于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统治,女性和自然始终都受到男性的统治与征服。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持续恶化、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人类更应该深思如何建立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处理两性之间的关系。莫里森对于黑人男女两性之间,推崇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合作关系”,“女人承担和男人一样重要的任务,并不存在从属关系,男人并不感到威胁,因为他需要她”[11]。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在对以主人公佩科拉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受到来自白人种族歧视、黑人内部的压迫和性别歧视进行深刻揭露的同时,也刻画了克劳迪娅一家的生活,虽然也是黑人,但他们一家却过着与主人公佩科拉一家完全不同的生活。克劳迪娅的父母相亲相爱,父亲关怀备至地呵护妻子和两个女儿,在与自然的接触中耐心地教导女儿们独自生活的能力,家庭中两性的和谐让克劳迪娅和姐姐感受到爱的滋润,看到了生活的美好。在《所罗门之歌》中,奶娃受到拥有宽广胸襟的姑妈派拉特的影响,他开始学会去拥抱生命,学会如何关心别人,宽恕别人,帮助别人和融入社会。从南方回来后,奶娃逐渐意识到过去对于女性的不尊重和伤害是错误的,在妓女甜美家里,他一改以往霸道自私的相处模式,体贴成熟地处理两性关系,展现了两性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平等,变得更加和谐。
同样,在沃克看来,女性、男性、自然之间始终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三者应该相互依存、相互扶持,建立起平等融洽的关系,才能实现最终的和谐统一。在小说《紫色》中,当茜莉宣布离开X先生前往孟菲斯发展自己的事业时,X先生最初的反应是勃然大怒,他觉得自己男性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与威胁,但是在茜莉离开的日子里,X先生开始逐渐反思自我,他收集贝壳,在自然中,贝壳代表着“倾听”,把耳朵贴到贝壳上,会听到海浪的声音,海浪的声音象征着女性的声音;大海充满着无序、混乱和不安定的因素,而这似乎更多的与女性相关,因此大海也被认为是女性的象征[12](P89-95)。慢慢的,学会倾听的X先生改变了观念,他不再把茜莉当成自己的奴隶与附属品,而是一个独立的人;当茜莉回到家乡时,他第一次与茜莉坐下来面对面平等地聊天,他们探讨问题,他告诉茜莉,“我现在心满意足,我第一次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在世界上,我觉得我有了新的生活”[9]。在小说《我亲人的殿堂》中,男主人公苏威罗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开始学习平等地对待女性。他成为一名木匠,回归简单纯朴的生活方式,建造了一座形状类似于鸟的仿古房子,和他的妻子各据一侧,平等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莫里森和沃克在作品中的描写都展现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应该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男性要与女性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交流,才能获得新生,建立起和谐的两性关系,实现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平等,最终共建一个新的世界。
三、女性与文化
文化,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属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是能够被传播或传承的一种意识形态。生态女性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倡导建立一个种族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的社会。莫里森和沃克在她们的作品中都传递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现状的深刻思考与关注。莫里森“自幼在黑人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培养起强烈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豪感”[13](P54-60)。莫里森认为,黑人民族要生存下去,除了拥有政治权利和经济独立以外,还必须保留黑人文化。黑人只有返璞归真,恢复本民族古朴的风范,才能摆脱白人文化的精神桎梏,拥有自己真正的灵魂[14](P748-750)。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主人公佩科拉每天乞求得到一双最蓝的眼睛,她又觉得自己皮肤太黑,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黑人文化下的美。而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克劳迪娅,与佩科拉形成鲜明对比,在白人文化占主流的社会中,克劳迪娅也受到和佩科拉同样的文化冲击,但她没有乞求得到白人文化的认可,而是努力寻找自己在黑人传统文化下的美。当克劳迪娅的母亲吟唱起关于黑人艰难岁月的歌曲时,她陶醉其中,渴望生长在那些艰难岁月,渴望了解更多关于祖先的古老文化。佩科拉和克劳迪娅虽有相同的肤色,但有不同的命运。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下,黑人女性只有尊重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文化充满认同和自信时,才能实现自我,保持种族个性。
沃克在小说《紫色》中向读者描写了黑人女性世代相传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活动:缝被子和唱歌。“百纳被”是黑人文化传统中的美学主题,缝制“百纳被”被认为是发挥黑人女性智慧和传承黑人文化传统的统一[15](P171-173)。黑人女性缝制“百纳被”的方法是将家里废弃不用的衣服或布料剪成一片片的几何图形,再用针线将碎布片缝制起来。在《紫色》中,茜莉和索菲亚一起缝制“百纳被”,随后莎格也加入了她们,并贡献了自己的黄裙子来缝制被面,后来这个被子被称为“姐妹的选择”,这一情节体现了黑人妇女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团结协作和亲密无间的姐妹情谊。在沃克的短篇小说《外婆的日用家当》中,母亲所收藏的两床被子是迪伊的外婆缝制的,被面上的图案都是自然界中的景象:一床是单星图案,另一床是踏遍群山图。两床被子上的小布片都是从家里几代人的衣服上拆下来的,可以说这两床被子既是家族的遗产又是家族的历史,那些被子上的针线所联结的是整个黑人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传统。除了缝制被子,“沃克运用黑人文化中歌唱这一特殊意向来表达被压抑的声音,这种声音是黑人女性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它帮助她们寻找和确立自我身份,反抗父权制的压迫,并促使她们‘从边缘走到中心’”[16](P106-113)。小说《紫色》中的另一女主人公莎格的职业是一名歌手,她崇拜充满生命与爱的自然世界,并将这一想法通过歌唱表达出来;同样,小说中的其他女性也通过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她们对着大地歌唱,对着天空歌唱,对着木薯歌唱,对着落花生歌唱。唱着爱与别离的歌曲”[9]。黑人女性吟唱的对象是大地、天空、木薯和落花生,这些都是自然中的万物,是自然的象征,体现了黑人女性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对于自然的热爱之情。
莫里森和沃克在小说中对于女性和文化之间的描写表明,一个人乃至一个种族,要始终保持对自身文化的忠诚与自信,这样才不会迷失自我;对于那些处在边缘化的非主流社会中的人来说,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至关重要,它标志着一个人是谁、从哪里来,应该拥有怎样的尊严和地位;对于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中挣扎的黑人女性来说,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就是对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最有力的回击[17](P162-164)。
四、结语
托尼·莫里森和艾丽斯·沃克在妇女运动和生态保护运动相结合的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描写了黑人女性与自然、男性以及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展现了她们的生态主义人文关怀。黑人女性受到男权制的压迫与自然受到人类的迫害之间具有相似性,同时,黑人女性又从自然中获得生存下去的力量和勇气,自然成为女性寻求快乐与希望的地方,女性与自然融为一体,相依相存;黑人男性只有摆脱父权制的观念,在理解、尊重、欣赏女性和自然时,才能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黑人女性在不停地追寻自己的文化之根,进而构建出具有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身份的完整自我。莫里森和沃克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充分表明了她们对于男性、女性、自然等三者平等共生,共建和谐世界的渴望与期盼,这与当代“坚持可持续发展,共建美丽新世界”的理念不谋而合,体现出莫里森和沃克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与前瞻性。未来,这也必将为生态女性主义和黑人女性主义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积极的参考与更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