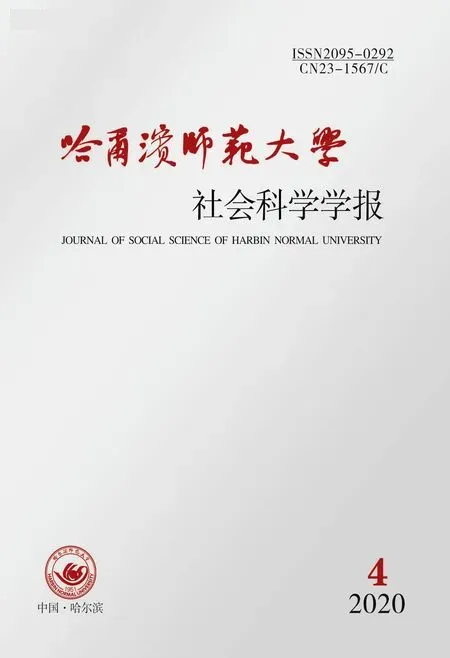在线性·地域性·韵律性:微诗核心特征的变迁
2020-12-19王燕子
王燕子
(广东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网络时代的微诗便是诗歌在“微时代”的新生儿。从文学史来看,诗歌以语言的凝练、想象空间的广袤、韵律性的美感从《诗经》开始就一直魅力依旧。随着时代的变迁,古典诗词的时代开始变迁为现代诗歌为主流,而今诗歌进入新媒体时代,诗歌的现代性是否会有所改变,或者以何种方式凸显变异以便适应于当下,这应该是网络时代诗歌界需要关注的问题。讨论诗歌变化的过程需要明确两个前提:第一,现代诗歌之所以成为“现代”诗歌,必须是用现代话语抒写现代人的心绪,畅想现代化的生活,展现现代性生命价值的现代诗歌;第二,现代是“当下”的现代,“现代”并不固定,它的状态将随社会变迁而挪移,即现代诗歌的特点将随着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而呈现出不同的诗歌内容、诗歌形式以及诗歌传播与评价方式。对“现代”诗歌一词进行定性之后,我们便可以开始讨论当下网络时代诗歌的新宠——“微诗”的成长历程,它的特征可以从媒介评价基点、诗歌应和需求的状态以及节奏形式化发展的努力等三个角度,呈现为在线性、地域性、韵律性等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的关系呈现为一个递进式过程。微诗将在韵律性特征逐渐形成且达到基本共识后,最终达到“微诗”成熟状态。
一、 在线性:微诗的媒介评价基点
在线性是网络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微诗之“微”以在线性为主导。微诗的传播媒介以微信群及微信朋友圈发布为主,因为即时在线的便捷及碎片时间的短促,使得微诗在诞生过程中必然呈现为短小精致的特点。因为微诗创作平台的即时在线,使得诗歌创作与传播的方式复原了古典诗歌时期的诗歌创作的情绪诉求,即虚拟真实的社交平台复活了古典“诗歌”原初的“诗言志”与“诗缘情”的传统,不同的只是将情志放置在即时之当下。
微诗的创作传播平台除了网络文学应用APP,更多的是社交应用的通信平台。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于2019年8月颁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2019年上半年,手机网民经常使用的各类APP中,即时通信类APP用户使用时间最长,占比为14.5%;而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文学和网络音频类应用使用时长占比分列二到六位,依次为13.4%、11.5%、10.7%、9.0%和8.8%。”在各类网络社交应用中,“即时通信,截至2019年6月,我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到8.25亿,较2018年年底增长3298万,占网民整体的96.5%;手机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到8.21亿,较2018年年底增长4040万,占手机网民的96.9%”。
从这几组数据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几个问题。第一,网络文学类应用的APP排名在网民的娱乐空间的比例上是远远低于其他视听型娱乐。由于当前网络文学行业成长重点放在跨界努力上,主要表现在网络文学与网络视频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企业开始涉足对方领域的内容创作业务,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内容生态。例如,阅文集团在2018年10月以155亿元价格完成对影视公司新丽传媒的收购,以此转型为兼具文学和影视制作能力的互联网内容平台。因此,网络时代的诗歌创作如果只是囚于纯粹的网络文学类应用的APP空间生存,可想而知,网络诗歌的空间必然是狭小局促的。第二,就APP用户使用时间而言,通信类APP使用时间最长,而社交使用率,在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hlwfzyj/,2019年8月30日。中前三名是微信朋友圈、QQ空间以及微博。网络诗歌生存空间需求突围,就数据分析而言,社交微信圈必然成为最大目标发生点。于是,在微信朋友圈进行网络诗歌生存突围,便可以看成是“文体生存”的利益最大化的趋势选择。因时(网络时代)而作,因媒(以微信朋友圈为主)而作,微诗的短小精致、即时在线,必然成为微诗的主导特点。
通信平台的即时社交应用的功能,帮助微诗复活了古典诗歌原初的“诗言志”与“诗缘情”的传统,当然,这种“复活”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以新的方式为现代人提供了适合现代人生存的深度、多元复杂的情志心态的传播方式。
第一, 在线性给微诗的媒介平台提供了立体呈现方式。例如,微信朋友圈的文字+图片、文字+视频的上传形式为微诗创作传播的形式提供了多媒体样式的可能。多媒体样式既满足适合现代人的读图控、视频控的视觉满足,也提供了图文、视频文立体呈现的补充或者悖论式的多元复杂的作用。 文字之外的图片、视频可以给微诗营造一种立体空间,视诗人的所需而定:可以用图片、视频补充文字的描述效果,以视觉感知或视听感知形式呈现;可以利用图片、视频形式与文字形成悖论,或者是以反讽形式差异化呈现,用来凸显文字的象征意义。现代人的多元复杂性生活方式以及多重情境的想象空间,在微诗所处的媒介空间得到尽可能展现的机会。
第二, 在线性诗歌给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现代社会中非理性化疏解方式的新途径。古典诗歌重视文字营造出“意境”。因为现代人丰富与复杂的社会生活,现代诗歌开始呈现出意义空白、时空跳跃,象征化非理性组合的等现代性技巧,让现代诗歌进入一种“精英”式现代创作方式。在文学史上,新诗的现代性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既要面临“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讨论,在精英化与通俗化过程中纠结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也要处理“西洋化”与“本土化”的诗歌形式内容的结合问题。现代诗歌一路走来,现代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思考模式无一不牵动着现代诗歌的呈现样式。
在线性使得微诗在现代社会中处于一个即时呈现、转瞬翻篇的社交空间,不管是微信朋友圈,还是QQ空间,或者是微博平台,随写随发、随评随改的网络活性空间成就了微诗的最大的现代性特征。当然,在线性的快捷性也造成了诗歌传播过程中的芜杂无序、转瞬翻篇的特性,不仅让经典微诗快捷传播,还让徒有微诗名头、无法打动人心的泡沫诗歌转瞬即逝。“诗言志”“诗缘情”是古典诗歌的两大根本原则,规定了古典诗歌的表现对象,原指诗歌创作者在社会性、情感性上表达需求,同时也可以看成是欣赏者在有所感悟之后,自发及自觉传播的内在需求。在线性的微诗样式使得“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需求焕发出新媒体时代的特色,“即时之情志”成为微诗存在价值的最大特征。
例如,熊国华的微诗《孙中山铜像》,“用剪断的辫子做一根/黑色手杖/敲醒沉睡的大地”以形式短小精湛、意象经典有力而传颂,被视为广州景观的微诗名片,有历史意蕴,更有诗歌内涵。此诗据诗人本人所言,这首诗原有十余行,大约写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8年在广州召开国际诗人笔会,在黄埔龙头山森林公园建“国际诗林”刻碑,要求四行以内,诗人精选了其中三行,成为独立诗篇。后在微信群等社交空间被诗友多次转发,即时传颂,成为经典微诗。从此案例可以看出,微诗的短小、快捷、互动的在线性可以帮助一首内蕴深厚的诗篇在瘦身之后快速传播。口耳相传的诗歌传统在新媒体时代获得了变身,因为诗篇本身的内在价值,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即时情志的传播需求,再一次让诗歌成为现代人表达“即时情志”的“热宠”形式,只是不再如古典诗歌般要求的那么严谨,或者如传统媒介中的现代诗歌呈现的那么“慢节奏、细品味”的格调。“短小、即时、互动”的在线性成为微诗诞生之初最核心的特征。
二、 地域性:微诗的“部落化”的“应和”需求
诗歌的欣赏是一个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心理过程。作为诗歌的欣赏者,既可以是诗人本人从创作者角色进行的转换,也可以是对诗歌进行客体认读鉴赏的“他者”。不管是自我欣赏的诗歌创作,还是希望得到他人精神共鸣的诗歌创作,都希望得到一种“审美应和”。这种审美应和的既在于可以抚平诗人创作欲望时的激情,也在于对创作成果,甚至诗人创作努力本身的价值认可。换句话说,是诗人作为创作者的审美快感的情绪应和。
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解释,诗歌的情绪应和可以看成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进行认读鉴赏时,在大脑皮层中形成了一种可以产生共鸣的力的结构,这种力的结构的产生可以看成是诗人与欣赏者通过诗作达到一种生命力的应和模式。如果将诗作本身视为有生命的主体,那这种情绪应和可以看成是诗人创作者、诗作主体、欣赏者主体,三者主体间性的应和,但是这种应和模式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又有区别。古典诗歌主要是对古人诗作的一种回顾式缅怀,既可以是审美现场在重现后进行的设身处地的诗歌情绪应和,也可以是单纯地对诗作进行当下式自我解读、自我慰藉的诗歌情绪应和,此时的应和可以不顾及诗作的创作背景、诗人的创作情绪,纯粹是欣赏者的自娱式文本语言结构式消费应和。
微诗是互联网时代的现代人“娱己娱人”的感悟之作,但是现代人丰富而繁杂的社会生活,不再如古人般单一而纯粹,在多元空间内不同身份的切换成为现代人的生存模式。如此,现代人的生存空间被切分。当下,互联网时代移动网民的身份切换,从微信群的分组可以最直观获得。微诗创作可以视为现代人在多元身份角色间,情感切换途径中某一空间内的审美行为,这类行为在网络空间内形成了特定的“部落”文化。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微诗的审美情绪应和的艺术中介是作品,而不是文本。作品的存在价值和应和的诗歌情绪,绝大部分来自诗人作为创作者赋予其中的激情。而文本的存在价值和应和的诗歌情绪,更多的是来自语言本身的形式结构和诗歌传统惯例赋予其上的一种语言魅力。微诗的创作与传播,是现代人为满足某一空间内的身份存在需要而呈现的审美行为,在互联网上互识、互动、互评是当下微诗友之间的情感“应和”。
微诗目前最活跃的社交空间以微信为主。微信与微博不一样,微博的特性是开放性的社交空间,微博的普通用户之间无须通过验证即可加为关注对象,便可对微博用户的发言进行留言互动,但是微信用户之间是对话关系,需要添加好友之后,才能关注到对方的朋友圈信息,且加上朋友圈分组功能,微信朋友圈所发信息是有针对性的私密空间中的闭环交流,由于微信功能的设置,闭环交流又不是单一的一对一,而是同一好友之间具有互动联系的组内闭环,再加上微信中拉群的分组交流功能的存在,微诗可以在一个特定主题内进行“部落”区域内部交流。诗歌的“应和”需求在新媒体时代开始了新的地域性呈现。
传统文学的地域性研究由来已久,都是以特定地理位置为论题起点来辨析文学与地理的关系。网络时代的地域性文学研究,可以从“定位性”的基点开始论述,黄鸣奋曾就网络文学的“定位性”的地域性研究撰文,指出:“‘定位性’是继地域性和去地域性、在线性和离线性之后出现的新范畴。”它与传统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息息相通,是现实地理空间在赛博地理空间的拓展性[1]。
互联网时代的微诗传播,因为赛博地理空间的特殊性,在通信区域内的差异以及通信群组的不同,也可以从“定位性”的角度将不同需求存在、不同主题目的而调整的网络空间视为新的地域性特征来讨论,信息“部落”或者是社交“部落”以自组织的形式过滤了很多非“部落”话题信息及非相关人员的干扰,形成了一个相对于闭环的“部落”组织。
在当下的网络在线生活中,网络地域性以“部落化”格局而存在,微诗的评价标准会为“部落”视野与话题流所左右,具体特征可以从身份定位、性质取向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 身份定位,“眼神确认过是自己人”。诗人身份是业余还是专职。目前专职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诗人的创作者必将是少数,而在这些少数诗群中,在群组空间内写作互评互议的毕竟还是少数,以“佛性”为主,更多是自我使命感,无需太多的外界应和之声的介入。而将身份定位为业余,但是仍具有一定审美鉴赏认知能力的诗人,他们更多地需要诗友之间的扶持与帮助,更需要诗友间的鞭策和鼓励。这类诗群的应和之声最为火爆热烈,同时也为营造良好的互动气氛,微诗创作及评议的内容多是针对身边事、身边情的感悟,更高要求的语言形式的探讨及诗歌内蕴的提升等涉及诗歌创作论层面的内容就较少出现,更多是自娱自乐的自组织形式的创作环境。
第二, 性质取向,目前微诗传播群主要是以政府或企业鼓励、高校诗社汇集、民间自组织等形式存在。政府或企业主要是根据当下的某个任务性的宣传需求对诗歌创作提出一定的要求,在此目的下出现的创作传播群。高校诗社汇集群落,主要是因为高校内因诗歌教学的需要或者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诗社的自组织形成的诗歌群落。此外,还有很多的民间诗友自组织的形式,形成的多主题的诗友会。当然,这些诗歌群落并不是单一的,也有一些交叉性存在的成分。例如,微诗创作的倡导实践最早是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的熊国华教授与广东财经大学的田忠辉教授在广东财经大学的综合楼的诗歌工作室用手机微信组织了一个“国际华文微诗群”,此群目前有两百余人,其中既有高校诗歌教学的教师、学生,还有国内的一些民间诗人。这类以诗歌实践为主旨的微诗群落因为人员多元,且分工有序,定期会有同题诗歌等形式的诗歌接龙创作以及诗评活动。这样有组织性引导的自愿参与性的微诗创作,在诗友之间互传、互评、互议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氛围。
从目前来看,微诗的创作内容大致还是以身边事为主,以片刻性感悟为主要特色,这与微诗的篇幅短小有关,微诗即兴创作、圈内传播也容易形成微诗的一种“平和”风格,反思讽喻批判的内容比较少。
三、 韵律性:“微诗体”的形式化趋势
诗歌的韵律节奏问题,伴随着诗歌的诞生而存在。从诗歌史的发展来看,诗歌的韵律节奏来源于诗歌与音乐的密切联系,从中外古典诗歌的历史来看,《诗经》《楚辞》《荷马史诗》,乃至古希腊的抒情诗都可以看到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除了外在语言词汇的节奏韵律的要求以外,诗歌最重要的还是内在节奏的呈现——情绪形成的内在韵律。即使是现代诗歌在诞生之初,努力摒弃古典诗歌的诗体束缚,但内在韵律的情感还是存在的,这是诗歌之所以为灵魂之歌的关键。诗歌的韵律来自诗人创作的激情,如何将情感形成语言形式,这便是诗人的创作过程中必须注意到的生命情绪的内在和谐性。
从中国诗歌史来看,中国现代诗歌的成长路程,也是一个韵律节奏探究史。对现代人用现代语言讲述现代人心绪的诗歌立场,最初着重的还只是自由畅达的精神诉求,打破古典诗歌的格律要求成为最重要的手段,可是在“诗体大解放”之后,诗人们又回头揣摩语言的特性,诗歌与现代汉语开始了漫长的适应过程。白话汉语也在成长,面对风云变化的社会,不断长出新的语言特征,增强了对现代生活、现代生命的表达能力。现代诗歌的成长语言的成长,同时也是诗人的成长。梁宗岱在《新诗底分歧路口》中说:“正如无声呼吸必定要流过狭隘的箫管才能奏出和谐的音乐,空灵的诗思亦只有凭附在最坚固的形体上才能达到最大的丰满和最高的强烈。”[2](P167-168)诗歌是什么?诗歌是毫无拘束的语言片段的排列,还是独具匠心的进行语言的锤炼和修饰?单纯的语言革命并不能真正带动诗歌语言的革命,诗歌的自身建设,不仅来自诗人对自己的理解,还在于诗人对语言的理解。诗歌的节奏韵律的内在化及外显性开始被现代诗人注意并强调。从新月派的闻一多的“三美”倡导(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到之后何其芳、戴望舒对“长短句”的迷恋,从朱湘在《石门集》中对十四行诗的仿效到冯至的《十四行集》中十四行诗的中国化努力,韵律越来越被诗人看重。诗歌的主题内容与诗歌的语言表达从来都是诗歌发展的两翼,不可偏废。新时期之后,朦胧诗和先锋诗派的出现,诗人们在诗歌韵律方面的摸索和调整也能在诗歌发展中瞥见一二。
自由诗同样也有着韵律和节奏的讲究,这是一种非形式化的格律,讲究的是内在情绪的旋律。换句话说,自由诗凭借情绪的表达而形成诗歌的韵律,字句组合依附的是情绪的节奏,而格律诗凭借着对字句的锤炼,用字句的语言音节生成格律,字句组合依附音节的排列调节情绪,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有一点必须明确,现代汉语的词汇、句式细密而复杂,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呈现出更替迭出的新样式。诗歌的格律化努力与自由诗韵律的实现都必须从当下语言的实际情形出发,才能形成恰当的表达样式,让词句贴合情境、烘托诗歌氛围。
互联网时代的诗歌发展,诗歌语言的形式化成熟趋势,不仅要关注汉语语言自身的特点,还得顾及互联网语言的程序化呈现方式。例如,微诗的表达限制是控制在三行,还是四行,抑或四行以上?这种诗行的设置就不是原有格律诗或自由诗的“微小减缩”版了事即可。即便是对传统媒介诗歌的裁剪处理,它所存在的互联网空间的传播及再阐释问题也要与社交网络的特征联系起来。
随着微诗的发展,诗歌经典化提上了议题。互联网时代的微诗并不仅仅是短小诗歌的简称,它的出现及发展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形式化雕琢的趋势将成为微诗成熟阶段的努力。熊国华作为微诗倡导者与践行者主将,在微诗格律上的理论设想,可以看成是互联网诗歌理论的建设。他认为,微诗要有一定的规则形式,这样才能算入真正的“微诗体”的系列中,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微小版诗歌”。
微诗,指在微信上发表的四行内诗歌。以行数划分,可以分为一行微诗、二行微诗、三行微诗和四行微诗。四行微诗因其与古代绝句多有相同相通之处,被专家称为“微诗体”“现代绝句”。
“微诗体”作为一种新诗体,有如下的形式规则。
一 体式:⑴每首诗限于四行;⑵每行诗不超过18字;⑶四行不分节;⑷排列以参差错落为佳;⑸须要题目。
二 押韵:⑴第二、第四行押韵;⑵使用《中华新韵》,韵部划分以普通话为依据;⑶如果有好句,也可以不押韵。
三 基本模式:⑴四连式(每行中不断句);⑵四断式(一行中根据需要,可以断一至多次);⑶二连二断式(四行中不计位置,只要有二行连,二行断即可);⑷三连一断式(四行中不计位置,只要有一行断,三行连即可);⑸三断一连式(四行中不计位置,只要有三行断,一行连即可)(2)此为熊国华在“融媒体时代第二届微诗理论研讨会暨国际华文微诗精品丛书发布会”上的发言内容。。
严格地说,熊国华对微诗的规则设定并不严谨。从体式来说,“限于四行”的宽泛设定,使得微诗的弹性非常大,甚至可以包括之前比较成熟的三行诗。在押韵方面,“如果有好句,也可以不押韵”的说法,让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慈爱可亲的探讨,而不是严谨诗律的宣言,但基本模式的几种描述,可以给初入微诗界的诗友一个简单指南,类似于操作手册。
微诗的生存背景是现代人在互联网社交时代,利用碎片化时间创作、传播、互动、再传播的一种限行式自由诗体。自身体式的限定规则远大于语言特点的限制,诗歌内在韵律的生成与节奏的协调是一个“好句”形成的最大要素,押韵与否只是用来测量诗人语言技巧的熟练程度。潜藏于诗歌文字深处的内在韵律才是微诗的生存力所在。熊国华的“微诗体”的理论努力可以看成是调节自由体诗在互联网时代生存的“微诗之网”,在四行之内,在18字之中,或轻重疾徐、或长短高下、或随性散漫、或蕴含深厚,碎片化的文字游戏、瞬间的人生反思。微诗在现代心绪的表达、现代语言的韵律把握方面,为现代人诗性生存空间,保留了一片净土。
从在线性、地域性到韵律性特征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微诗作为互联网碎片时代的诗性文学的一种成长努力。现代人快节奏的多元空间的生存状态,理性而焦躁,诗性文学的社交互动让单向度的人类有了可以栖息的审美空间,从在线即时互动的起步,到“部落化”聚齐的诗性认同,再到自由抒发的韵律要求,微诗逐渐成长。微诗将在韵律性特征逐渐形成且达成基本共识后,最终达到“微诗”成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