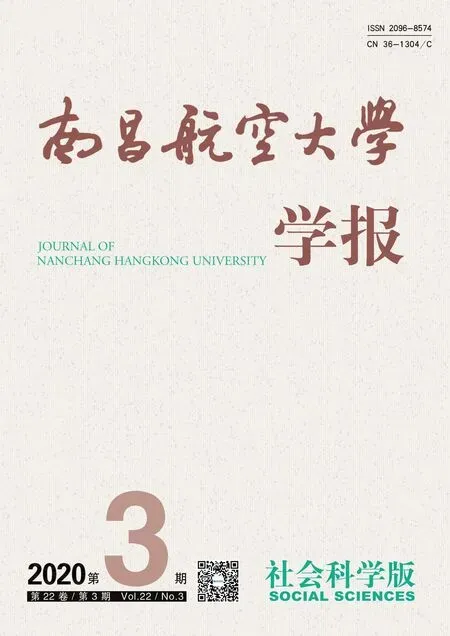论民俗文化在《呼兰河传》中的作用及意义
2020-12-14阮学云丁根发
阮学云, 丁根发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南昌 330013)
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我国30年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代表作,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茅盾在为《呼兰河传》作序中写道,“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同时茅盾也认为萧红在作品中所蕴含的独特生命感知和人生体验,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成果,“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眩惑”。
茅盾早期对《呼兰河传》的肯定,引起了中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导致众多研究方向围绕作品的散文化的笔法、儿童的视角、自传体的方式和小说的乡土特色,鲜有学者从民俗活动所透露的文化价值这一角度重新认识和发现作品,挖掘作品所包含的巨大文化含量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小说《呼兰河传》展示的东北故乡众多的古风旧俗不再仅仅只是作为小说的背景,而是直接成为了小说的主体内容。因此,本文将从小说中所描绘的民俗文化为切入点,探讨其民俗的产生和分析其在小说中的背景作用,解读民俗文化在文中所体现的艺术价值以及萧红对民俗文化的深刻感悟。
一、当地民俗的产生及分类
民俗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文化积淀,是在当地独特的社会历史和自然人文环境的共同作用中产生的,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同一个民族或者同一地域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往往会自发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精神现象。因此,了解当地民俗的产生和分类对分析当地民俗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当地民俗的产生
萧红所描写的呼兰河城处于20世纪20年代,其文化仍保持较多固有特征,带有很强的封建宗法色彩,致使它仍处在古老的村落群体文化中,尚未走出以风尚习俗作为主体的社会结构[1],呈现出落后封闭的历史格局。
历史背景因素导致的现实状况简单概括为两个字:贫穷。位于东北边陲的呼兰河城物质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从“食为天”的吃就表现出来了,人们为了能吃到便宜的猪肉,不顾饮食健康卫生争先恐后地购买瘟猪肉,并且事后各自有默契地给这一行为寻找到一个心安理得的滑稽理由:吃的是淹猪不是瘟猪,不算什么不卫生。物质生活的贫困落后直接导致文化生活的匮乏,进而引发精神生活的空虚。小城除了一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精神上的享受只能依靠当地的民俗了,促使众多特色民俗活动逐渐成为一种当地群众娱乐文化传统。有一处细节提到,老胡家跳大神跳出了新花样,若是谁没有去都会被视为一生中的不幸,大家都为他惋惜,足见市民对当地风俗的认同及依赖程度之高。
(二)民俗的分类
民俗是以一个社会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简单概括为民间流传的风尚、习俗。对于民俗的分类,中外学者不尽相同,各执一词。本文将《呼兰河传》中出现的众多当地民俗大致划分为四大类: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信仰民俗[2]。
生活民俗是指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的日常民俗。在小说中,对生活民俗的描写处处可见。在衣着上“扎红辫根,绿辫梢”,“脚上穿了蓝缎鞋,或是黑缎绣花鞋”,饮食上“吃了小葱蘸大酱就已经很可口了”“豆腐加上点辣椒油,再拌上点大酱”[3](529),可以看到小葱蘸大酱、苞米豆粥和辣椒油都是当地最典型和朴实的饮食。出行和居住方面小说着墨不多,出行方式无外乎坐马车和骑马;而住的房屋,仅有的一点描绘还是可以看出当地典型特色,如“我家的窗子,都是四面糊纸,当中嵌着玻璃”,“一律用瓦盖房,房脊上还有透窿用瓦做的花”[3](559),以及平常百姓家的火坑。生活民俗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出小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封闭的生存状态。
人生礼仪民俗指约定俗成的社交或是一生几个重要环节上具有一定仪式表现的民俗活动。《呼兰河传》中对人生礼仪民俗的描写不胜枚举,比如在社交上,向长者或者有威望的人行的作揖礼;在婚姻礼仪上,有“指腹为婚”和童养媳的说法,订婚上要喝“小礼”酒;过访送礼上讲究回礼,相聚前就要把礼物准备好,送礼时则表现得轻描淡写,“只说这么一句,看起来并不像送礼……把东西递过去就算了事”[3](543)。由于受传统习俗文化的惯性作用,当地人生礼仪民俗保留较多旧时的封建痕迹,同时也反映出当地的淳朴民风。
岁时节日民俗指在节期与活动所代表的时间框架上举行相关事宜,呼兰河城的几大盛举大部分是属于岁时节日民俗范畴。跳秧歌,时间定在正月十五,属于传统节日中的元宵节;放河灯则是在七月十五孟兰会,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鬼节”;野台子戏是在秋收时期,目的是庆祝收成比往年好,感谢天地;至于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顾名思义就是在农历四月十八日举办,在这一天无论男女老幼都来逛庙会,其中女子居多,为的就是求子求孙。
信仰民俗指民众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对神灵崇拜而产生的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又称“精神民俗”“心理民俗”。小说中针对当地的信仰民俗,萧红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使其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状态。比如跳大神,旱天向龙王求雨,“若是夏天大旱,人们戴起柳条圈来秋雨……唱着,打着鼓”[3](536),过河抛两个铜板祈求河神保佑,不把他们淹死。跳大神是作者要在文中重点展示的信仰民俗之一,跳大神源于东北土著萨满教,是东北最古老最具有影响力的民间宗教形态,是东北诸多民俗形态和民族文化的母源,对东北民众的心理状态、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具有重大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和群众性。而小说中的跳大神是东北汉人经过多年“汉化”的民俗活动,是近于巫术的一种治病方法,减弱了宗教神秘性却加强了场面戏剧性。
二、民俗文化在文中的作用
在萧红笔下,民俗文化不仅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文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塑造故事人物形象和映衬小城群体的精神面貌。
(一)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俗语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文学作品中独特的民俗事项不仅展示了地方文化和生活现象,同时也深刻反映了生活本质。在小说中萧红就是通过展现平凡生活中民俗事项为故事情节的展开设置了典型环境。
《呼兰河传》中浓郁的东北村落文化气息主要得益于于萧红对当地民俗的敏锐观察和细腻刻画。如民宅的建筑风格,居民的饮食特色,婚俗的礼节,节气的庆典方式,等等,都充满了呼兰河独有的民俗韵味。这些特色鲜明的民俗描写成为萧红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标签。这些民俗的描写不是单纯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一方面这属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民俗标本,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神秘与封闭,可以为小说故事展开笼罩一层魔幻和野蛮色彩,营造出小说整体厚重沧桑的意境[4]。
民俗活动的细致描写为小说后面人物的出场埋下伏笔。作者在第一、第二章宏观为读者描绘了呼兰城地方特色的风俗画后,人物开始鱼贯出场,包括老祖父,老祖母和一些邻居群体形象。第五章为小团圆媳妇跳大神活动前后,能上场的几乎都上场了,以团圆媳妇为首的老胡一家,有二伯,周三奶奶,杨老太太,等等。第二章出现的请神、问神、打鼓、唱词一一对应到后面的这次大事件中,前后呼应,使读者在面对跳大神中各色人物的奇异表现时不会觉得突兀。小说并没有丰满的中心人物塑造,是以营造氛围为主,将人物与一幕幕场景、一个个故事片段串连起来[5],而民俗文化就是整个脉络环节的串连点。
《呼兰河传》对民风民俗的描写揭露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大世界,映照出他们的无奈、苦难和挣扎,进一步暗示了故事人物的的悲剧命运,其中最为令人心痛的无疑是老胡一家的悲惨境遇。老胡一家本是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家,“家风是干净利落,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可是最终的结局却是令人心酸、唏嘘不已,团圆媳妇被折磨致死,大孙子媳妇跟人跑了,婆婆死了,儿媳妇一个哭瞎了另一个成半疯,家破人亡。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与小团圆媳妇“跳大神”风波有直接联系。老胡一家有迷信大神的传统,两儿媳妇为表孝心时不时会花几个钱跳一跳神给老太太乐乐,也因此在处理小团圆媳妇“叛逆”的问题上,愚昧地认为她是被狐仙上身,必须请大神出马方可根治。如此一来跳大神便成了老胡家的家常便饭,跳出了新花样,打破了记录,开辟了新纪元,最终上演骇人听闻、血淋淋的“洗热水澡”惨案。这一番折腾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更生生剥夺了妙龄少女的宝贵生命,致使家门败落一蹶不振。从中看出传统的恶习陋俗跳大神是造成悲剧的直接原因,隐藏在古老传统民俗文化后的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则是根本原因,两者互为表里,一起把老胡一家推向无底深渊。在因果上老胡一家请跳大神治病本属善因,却酿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恶果。无论是从借跳大神这一陈规陋俗民俗映射出传统礼教吃人面目,还是从充满戏剧性讽刺意味的因果关系,都表现出小说严肃和深刻的悲剧艺术。
(二)塑造故事人物形象
小团圆婆婆性格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一方面她勤俭持家、孝顺老人,为了攒钱不辞劳累地拾黄豆粒,即使手肿得跟茄子一样依然不肯松口买二吊钱的红花治,却舍得花钱跳大神给老太太高兴。另一方面对待小团圆媳妇上则显得冷酷无情甚至残忍,仅仅为了给小团圆媳妇一个下马威狠狠打了她一个多月,包括烙铁烙脚心、用针刺手尖、拧大腿拧得面目全非……在跳大神期间协助大神当众撕小团圆媳妇衣服并且狠心看着她被惨无人道地洗热水澡连续三次至死,小团圆媳妇死后她剪其辫子并诬陷其是妖怪,这些举动暴露出婆婆的毫无主见和愚昧无知。小团圆婆婆非典型的 “恶人”形象折射出民俗文化对个人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作用。在传统民俗习惯下,她是一个合乎礼仪的好婆婆,受人尊敬。一旦这些传统民俗文化显现出落后愚昧的一面,却又使她成为了一个 “恶”婆婆。说到底,她只是“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的牺牲者之一,就像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写道,“他们又是也许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害自己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方法”[6]。
小团圆媳妇是小说中为数不多健康乐观令人感受到生命活力的可爱可亲的角色。她本性天真烂漫,脸上总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充满少女般可爱活泼气息。并且有着敢于向命运反抗的勇气,即使深受婆婆的虐待依然能够坚定喊出“我要回家,回自己的家”作为强力反击,表示对婆婆的暴力管教的不满。与此同时她又是小说中悲剧色彩最浓重的人物,是落后愚昧民俗最直接的受害者。面对整个落后愚昧的民俗文化氛围的大环境,即使她已经清楚自己危险处境,“等一会你看吧,就要洗澡了。她说着的时候,好像说着别人一样”,却依旧无力摆脱噩梦的降临。也正是因为她的清醒,愈加体现出她身上的悲剧色彩,正如鲁迅所言“人最可悲的是梦醒之后仍无路可走”。
有二伯是小说着墨较多的单个人物,是萧红笔下刻画成功的一个阿Q形象。极度虚荣却自卑感强,很爱别人称呼他为“有二爷”“有二掌柜”“有二东家”等,一旦有人背后或者当面喊他“有子”,他就立马恼羞成怒,脸变成猪肝色。在他人面前一旦提及财主张家与自己同姓就显得洋洋自得,挨了打就骂骂咧咧“介个年头的人狼心狗肺”。他自己被别人贱视,却同样贱视起同是苦命人的小团圆媳妇和冯歪嘴子夫妇,与老厨子一起埋葬小团圆媳妇归来后居然“兴奋得像过年一样”。即使被主人殴打后自尊心受打击嚷嚷着闹自杀,但跳井和上吊只不过是为了引起大家对他的同情和注意。这种阿Q似的自我嘲弄、自我宣泄,是传统民俗文化教化下的产物,是精神重压下性格异化的表现。
塑造“看客”群像。所谓“看客”,其实早在鲁迅众多作品上就有相当多的鲜明刻画,在《孔乙己》《祝福》《药》等作品多有涉笔描写,这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形象有着共同的心理特征:以咀嚼他人苦难自愉,事不关己,肆意评判玩赏,甚至嘲笑讽刺、幸灾乐祸,其核心是冷漠无情。在《呼兰河传》中他们无所不在,袖手旁观大泥坑种种悲剧的发生,冷眼嘲讽着疯女人、跳井投河的、自刎上吊的,无动于衷看着小团圆媳妇被活活折磨致死和王大姑娘难产凄凉死去。于他们而言,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可视作填补寂寞空虚、麻木混沌的精神状态的娱乐消遣品,“看于是人心大为振奋……这来看热闹的……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在第五章老胡一家当众给小团圆媳妇洗热水澡的闹剧,是把“看客”嘴脸勾画最传神的一幕。这里看客们的“看”有两重含义,第一层是对大神神舞表演的观看,第二层是对团圆媳妇的受难观看。在那一刻群众的“看客”心态得到彻底释放满足,互相享受着他们的狂欢时刻。在文中,面对小团圆媳妇的惨痛遭遇,婶子、大娘,奶奶们不仅没有真正的理解和同情,她们反而通过了“看”这一形式,既“鉴赏”了小团圆媳妇的受难过程,又“欣赏”了自己的表演,还从中得到了“满足”,最后用叹息和评论的方式,宣泄、转移以至忘却那份不幸和痛苦。整个过程萧红以一种小姑娘“我”的视角,怜悯小团圆媳妇的悲剧的同时又悲愤看客群众的无所作为,使之用近乎原始的文字把看客们“恶”的残忍展现得淋漓尽致,给读者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使鲁迅创造的“看客”形象再一次得到延续和升华。这种以民俗文化作为大背景凸显出群众“看客”心理的艺术手法,是萧红小说民俗艺术化的一大特点。
(三)映衬小城群体的精神面貌
常年生活在呼兰河城的萧红对故乡小城人有直接了解和深刻体会,使她对小城市民的内在精神状态能够加以理性地思考和审视,以普通的民俗生活相和民俗意象为切割点,形象和深刻地再现了处于封建蒙昧状态下呼兰河城人保守、迷信、愚昧和麻木的精神面貌。
20世纪初的呼兰河城处于一个现代与传统力量碰撞最剧烈的时代,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尤其体现在西方科技以及现代文明意识上,但这一切好像都与呼兰河城无关,体现在小城市民的文化结构、思维方式和生活面貌上仍是死水一潭。小说开篇在对呼兰河城的宏观印象描写中,格外提到地处全城繁华地段十字街上的一家拔牙洋医诊所,这家引人注目的诊所挂着一张上面画着“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的特色大招牌,与大街林立的各种老店铺同质化“姓氏化”布幌子招牌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这家充满现代化的洋诊所境遇却是意外的坎坷艰辛,两三年来拔牙者寥寥无几,诊所的女医生不得不兼做接生婆的活,究其原因竟是那“稀奇古怪”的广告牌,让人不习惯乃至“怪害怕”。另外还有两学堂挂着新式名号,实质上还是来的老一套,有名无实。在一如既往地沿着传统的惯性沉浸在古老状态的呼兰河城中,任何有时代气息的新生事物不是受到群体性排斥就是变为一种表相的毫无意义的存在,呼兰河城人对新鲜事物的反感、抵触和排斥正是缘于传统文化巨大惰性下衍生的保守性。
呼兰河城市民的迷信和愚昧集中体现在对鬼神相关的一切事宜都抱有超乎想象的极大热情,积极而又虔诚,乐此不疲。四大“盛举”似乎都是为鬼神准备的,为治病请跳大神、送魂托生的放河灯、向龙王爷请愿的野台子戏以及祈福许愿的娘娘庙大会。这些民俗事项的盛行折射出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鬼神迷信观念和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意识大行其道。比如在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祭拜期间,祭拜顺序先老爷庙后娘娘庙,向老爷磕头烧香时一定是心怀畏惧以示尊敬,而对娘娘则不由得放轻态度甚至藐视,即便他们是为了祭拜娘娘祈愿祝福而来的。原因是市民普遍认为阴间一样遵循着男尊女卑的规矩,自然老爷的地位要高过娘娘。甚至把这套荒缪的歪理邪说应用于现实家庭生活,侮辱折磨女性时辩解道,“你看娘娘还不是一样要受老爷欺负”。市民对陈规陋俗的盲目遵从的迷信与愚昧,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每个市民的意识深处,任其摆布乃至吞噬自身以及他人生命。
小说对呼兰河城市民精神上消极与麻木的刻画主要体现了民俗生活相,“他们这种生活,似乎也很苦。但是一天天下来,也就糊里糊涂的过去了”[7],对于人生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从来就没有进一步的思考或者认识,仿佛一切都是为了苟且偷生,“人活着就是为了穿衣吃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单调、停滞、苍老和寂寞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模式造成了他们精神深处的麻木,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就是无所谓和无动于衷,即使面对生活上的困境亦是如此。比如对因当年指腹为婚造成的婚姻悲剧,母亲也只能叹道,“这都是你的命(命运),你好好地耐着吧”。
三、寄托作者的情感归属
萧红在小说中把众多东北民俗自觉地作了艺术化处理时,必然出现对当地民俗文化情感眷恋与创作主体理性思考之间冲突的两难情结。前者使得叙述者的眼光停滞在一些风情人物上,娓娓叙述间有着无尽的思慕与怀想;后者使得乡风民俗的展示始终受制于理性批判力的约束,在一幕幕热闹非凡的民俗画面中暴露人们灵魂上的病态,以及由此酿成的生活悲剧。
萧红浓厚的“故乡情结”体现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独特乡土气息上,在她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店铺经营、手工技艺、胡同叫卖、街头商贩、日常生活、节庆盛况……应有尽有,眼花缭乱。在一幅幅鲜明生动的风俗画卷中,纷纷展示了呼兰河城的风土人情、节庆仪式、历史沿革、文化教育、道德观念、民间传说、宗教信仰、婚丧娶嫁、生产特点、服饰饮食等,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特殊理解。其中某些习俗场面让人感受到家乡人脉脉温情可爱善良的一面,比如说野台子戏。野台子戏不仅仅是庆祝收成和感谢天地,更是家乡人走亲访友、团结相聚的感人时刻。父母子女,姊妹兄弟,姑姨外甥为表现团聚的尊重,服饰上各自着装整齐刻意打扮,饮食上家家杀鸡买酒,然后笑语迎门。彼此之间谈着家常,说着趣事直到三更半夜,“烛火灯光之下,一谈谈个半夜,真是非常的温暖而亲切”,离别时相互赠送好礼约定来年再聚,把相聚相别的画面刻画得极其感人。还有娘娘庙大会大街上不倒翁的有趣和富含寓意的带子,放河灯时灯光河色的繁华美丽与诗情画意,描述中皆倾注深切的怀念,如数家珍,表现出对呼兰河城民俗文化不由自主的留恋。这种对传统民族文化一定程度上的潜意识认可和皈依,正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乡情眷恋。萧红在讲述民俗风情故事时,既看到了自己的生命归宿,又看到了灵魂的再生希望[8]。
小说深刻揭露了大量夹杂封建礼教制度糟粕的恶习陋俗,除了跳大神、孟兰会、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会等显性文化,还有童养媳制度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俗等隐性文化。小城日常生活的单调、冷清和娱乐方式的极度缺乏,导致这些民俗在长年累月的历史习惯下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民众心目中的“精神盛举”。但是与此同时,可以看出这些民俗活动大多是为鬼神而做的,与大量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思想粘合在一起,于是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风俗渐渐成为与文明社会背道而驰的恶习陋俗。这些恶习陋俗的存在,一方面缓解了小城人民因庸俗平淡的生活而产生的精神压抑和疲惫感,成为弥补空虚寂寞精神世界为数不多的乐趣。另一方面又成为统治阶层向人们传送封建残余糟粕的渠道。
萧红通过小团圆媳妇之死揭示出恶习陋俗背后的封建迷信思想对人们精神的愚弄和肉体的摧残,这些陈规陋俗真实深刻地揭露了呼兰河城人异化性格和病态社会心理的产生以及形成的社会环境,而这样的社会环境也是滋养无数犯罪和悲剧的温床。
萧红始终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呼兰河城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写作生涯中一直将目光和视野投注在这块东北故土上,深情地叙述着这片土地发生的故事,向人们展示这片土地的兴盛与苦难。这是对故乡的升华,作为一个现实中的无家可归者, 萧红却自始至终在文字中的“故乡”寻找自我认同的源泉[9]。在悲凉寂寞的心境下艰难完成的这部长篇小说里,借民俗写民风现民心,演奏出一曲众生交汇的心魂乐。《呼兰河传》中的民俗文化是萧红处于理性与乡情的两难纠结和冲突下痛苦完成的。基于作者在文学上一贯坚持“作家的创作是对着人类愚昧的”的态度,所以在对这一冲突的整体把握上,显然以现代理性文明为主体,从“国民性”大背景下去观察和表现人的生活,在民俗事项的描写中包藏和浸润着深厚的文化批判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