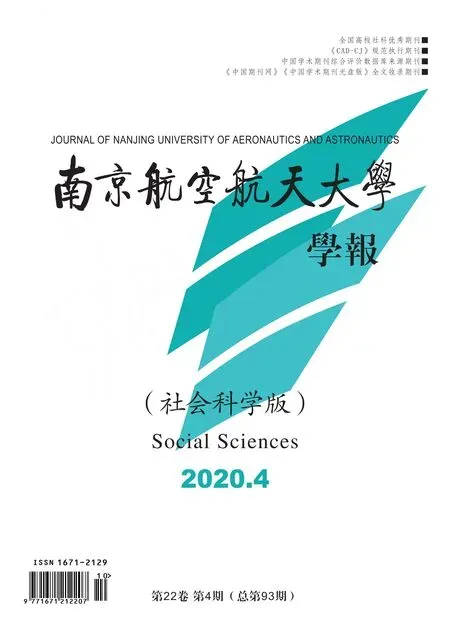五四运动为党的成立与发展所作的四重思想准备
2020-12-13唐志文郭小凡
唐志文,郭小凡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1106;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1106)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了五四运动的地位和重要历史意义:“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1]2同时指出: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1]2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既指1919 年5 月4 日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指一个时期新文化的思想运动。通过探索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所作的思想准备,可以认识到五四运动的重要历史意义。
一、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
“打倒孔家店”长期被视作五四时期的纲领性口号,导致国内外片面认识五四精神实质。实际上,全盘否定孔子和中华传统文化并非主流,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核是批判继承。一定程度上,“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2]。
“五四”初期,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与激进主义极端化、片面化倾向。批判传统的真正目的是压制文化复古派的猖狂活动,避免封建道德和鬼神迷信禁锢人们的思想,预防“帝制复辟”的反动政治逆流蔓延。在批判过程中,存在矫枉过正、以偏概全的现象:部分知识分子将剔除不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忠孝节义等纲常道德,夸大化、片面地将整个儒学甚至传统文化体系与文化复古派宣扬的纲常道德画上等号,认为一切传统文化都是应予以剔除的糟粕。毛泽东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3]
然而新思想倡导者的出身和研究造诣大多限于中国旧传统,尽管他们高呼新文化,实际上并未完全与旧学绝缘。他们一方面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深刻而明显的刺激,另一方面又批判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清末今古文之争是五四运动中打破传统偶像之风的来源,康有为、章炳麟二人的争辩激发出的疑古辨伪精神,正是在批判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五四运动中的革命首创精神和蓬勃朝气,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传统,只有依托传统,当时中国社会的新生力量才能更好地表达强烈的变革愿望。正如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中所说: 勤、俭、廉、洁、诚、信等传统道德,“固老生之常谈,实救国之要道”[4]。
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中许多富有民主性、人民性的精华值得继承弘扬。毛泽东指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5]随着运动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抛弃了前期对中华传统文化一概否定、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一概肯定的“全盘西化”形式主义偏向,从而批判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并与马克思主义构成精神互动。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社会主义最精要的论据。”[6]受跨文化翻译等因素的制约,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时,一度被理解为“大同理想”,恰恰反映了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间存在特殊的亲和力,尤其是与古代儒家的理想社会存在兼容性,两者可以相互贯通。蔡元培为李季翻译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作序,开篇即对比中国儒家社会理想和社会主义学说,认为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学说,并用《礼记·礼运》等经典进行论证,促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先知先觉者中深入人心。
五四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促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实践性得到了有力彰显。历史最终突破了“隔着纱窗看晓雾”的困境,中国共产党人举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旗,在近百年的风雨中继往开来。“五四”时期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契合为开启党的光辉历程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7]新时代更应大力学习“五四”时期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聚焦其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着力于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展现出它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二、洋为中用:传承和践行十月革命的斗争精神
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与壮大了的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组成的革命阵营有关,更与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潮流的出现关系密切。“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8]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卖国等闹剧后,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们传承和践行了十月革命以“反压迫,求平等”“敢于反抗,破旧立新”等为内涵的斗争精神,促使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十月革命发生之初,《民国日报》曲解了它的目的:“唯争人权也,故非达农民工人生活之改善不可。唯争民权也,故非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府不可。吾国之革命要求亦然也。”[9]随后,《劳动》等刊物或是从无政府主义视角剖析十月革命的本质,或是以改良主义论调歪曲十月革命的真相,均未认识到十月革命采取的是一种暴力革命的方式,自然没有理解其背后蕴含的斗争精神。
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桥梁才能深入到广大人民中去。1918 年,李大钊先后写成《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促进了人们对十月革命的斗争精神从向往到实践的转化。他在文中揭示十月革命的本质,强调其“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10]330,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1]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大钊提出:“被压迫民族应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实行‘民族自决主义’,并且把这种斗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10]269。十月革命以后,工人阶级的力量已为一般人所注意。当时,欧洲回国工人曾在归国轮船上议论:“听说俄罗斯革命了,把那些大官关进了监狱,穷人都搬进了洋楼呢”[12]。
1919 年2 月,李大钊又在《晨报》发表了《青年与农村》,提出“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10]304,直接促进以十月革命斗争精神为方针和原则的革命阵营的形成。巴黎和会、上海和会的结局,直接刺激革命阵营投入暴力斗争中。因此,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学生游行示威。途中,许多市民自发加入队伍,同呼口号。广大学生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过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直指赵家楼曹汝霖处。观看游行的市民群众深为学生的斗争精神所打动,许多人(包括部分巡警)都流下了眼泪,西洋人更是脱帽喝彩。学生代表周予同回忆:“大家相约暴动,准备牺牲,有的还向亲密朋友托付后事,我和匡互生等都写了遗书。”[13]“六三运动”中,上海群众同样展现出斗争精神。日营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五千多名工人率先罢工,并得到了日华、上海纱厂工人的响应。同一天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及沪宁、杭涌铁路的部分工人也开始了罢工。几天内上海参加罢工的人数高达近七万。帝国主义的《大陆报》不得不承认,这群中国人,齐心一致地拍着胸膛对巡捕和商团说:“你们刺吧,你们刺吧!”帝国主义越是想方设法地加紧扑灭运动,革命阵营的斗争精神越是饱满。南京、天津、杭州、济南等地工人纷纷罢工,游行示威。在传承延续十月革命斗争精神的过程中,王尽美、邓恩铭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终成为我党的革命先驱。
作为十月革命斗争精神在中国大地实践和延续的开端,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1]3-4,斗争精神最终成为我党在荆棘载途中成立与发展,带领人民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捷报的重要法宝。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4]
三、拨云见日:抨击“无政府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三次大规模论战。其中,第三次论战,即以陈独秀、李达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同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难度大,程度激烈,具有代表性。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历史久,社会影响力大,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误将互助论作为天演论的补充引入中国,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深受其影响,一度难以认清其真实面目。恽代英曾在武昌组建“互助社”,致信无政府主义者王光祈说:“我信只要一个人有了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精神,他自然有日会懂得安那其的。”[15]无锡无政府主义组织“五七团”在刊物上更是将马克思与克鲁泡特金相混淆,误以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兼有马克思、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三人的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空想革命而不知具体道路,却因其影响力和迷惑性成为“五四”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破坏力巨大。1918 年12 月,王光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国际社会之改造》,尽管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权利,无法通过“国际联盟”确保世界永久和平,但他并未指出改造旧中国的正确方向。他主张各地方自治团体联合,建立国际社会,但未明确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具体任务,错误地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宣传个人绝对自由。区声白曾致信陈独秀:“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之类,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16]他主张以“自由契约”和“公众意见”来代替法律。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从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出发,抹煞国家的阶级性,反对一切国家,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1919 年2 月,《进化》杂志污蔑布尔什维克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同年9 月,黄凌霜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系统攻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按劳分配原则,否认国家的阶级性,企图阻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结合,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准备工作。
面对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尖锐对立,1921 年6 月李达发表了《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予以还击。他引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的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用革命手段把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要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能单靠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必须创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强力压迫剥削阶级。而陈独秀在驳斥“绝对自由”观点时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建设一个‘人人同意及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是极端荒谬的。因为‘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17]292-296他还进一步指出:“主张‘绝对自由’,否认革命纪律,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非常不利。因为劳动团体底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家阶级对抗尚且不可能,慢说推倒资本家阶级了。所以说:权力集中是革命手段中必要的条件。”[17]313
论战促使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探索救国救民新道路,从而扩大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队伍。毛泽东回忆:“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观念的一种奇怪混合物……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8]104-128正是在思想论战中,他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先进性。据黎锦熙回忆:“1920 年1 月4 日下午,我到通讯社拜晤毛主席时,在桌上发现一本毛主席研读过的《共产党宣言》,毛主席还指示我精读这本书。”[19]毛泽东自己也说:“到了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8]131此时,他已对没有政治目的和严密组织,只从事经济斗争的无政府主义不抱希望,专心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学习与实践中。
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阶级与思想层面对无政府主义进行剖析,认识了无政府主义的假社会主义面目,从而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基础,促使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在论战中实现了彻底转变。这场论战,肯定了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强调了必须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起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作了思想准备。
四、开天辟地:正式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从1889 年《万国公报》上首次在中国出现马克思及其学说开始,30 年内,资产阶级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都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但这些认识大多属于简单的学理研究,或是较为零散和片面。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和思想斗争推向崭新的阶段。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从而正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五四运动的经验充分表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运动的核心力量,工人阶级具有自我牺牲、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是坚持爱国统一战线、争得爱国运动初步胜利的决定因素。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首先要求爱国知识分子发挥革命先锋作用,进一步促进工人阶级的觉醒,进而带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三个阶级的爱国统一战线,极大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反动行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20]
毛泽东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团结各阶层人民,形成爱国统一战线以孤立和打击当前主要敌人的典例。他认为,农民、工人、学生、商人四个群体构成了“最大多数党”,必须把他们发动和组织起来,才能进行广泛的革命斗争。长沙原本就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先进青年群体又创办了新民学会等组织,1919 年4 月,毛泽东由上海回长沙后立即号召会员们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注意京沪等地学生动态,准备迎接革命风暴。几个月后,他依据革命思想领导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次年又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剑指军阀谭延闿、赵恒惕。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成为了最善于学习群众革命斗争经验并依靠群众战胜敌人的革命者。他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总结经验教训,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组织民众的方法,根据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主张按产业组织工会。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结成统一战线的不同阶层,在如何选择改造中国道路的问题上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探讨。这也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兼收并蓄的优良品质,成为我党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看到了希望,加上列宁在《论东方各民族底觉醒》中强调组织革命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灌输革命理论,领导工人斗争,在斗争中建党,知识分子纷纷响应,“和劳工打成一片,灌输他们的知识,使他们有组织有办法,成无数个精密完善的团体。”[21]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相继前往工农群众中宣讲演说,并深入到工人中开展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等一大批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会应运而生。此外,共产主义小组还创办了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受众的革命宣传期刊,如上海陈独秀、李汉俊创办的《劳动界》周刊和与之呼应的由北京邓中夏、罗章龙创办的《劳动音》,均着重反映工人阶级受压迫的悲惨状况,并进行斗争方法和途径的指导。一系列通过先进分子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色。
五四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最终结果是“联合”呼声日益高涨。1920 年8 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召开“五团体会议”上总结了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唯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进一步创造新的联合”[22],反映了团结联合、共同行动挽救中国危亡的决心。一年后,党的“一大”在“联合”的呼声中召开,中国革命的面貌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也认为,改造中国的革命事业必须由革命同志组织起来,进行共同的讨论、研究、准备、破坏和建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正式开启的条件下,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具有历史必然性,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势必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五、结语
无论从文化运动还是政治运动角度来说,五四运动并未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任务。彻底完成这样的任务,除了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还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成立和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的构想变为现实,离不开五四运动作的思想准备。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3]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满足了为成立并发展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思想准备,为中国革命事业提供强大思想力量的客观需求,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1]1,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一场民族救亡、思想启蒙、革命斗争,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的伟大实践。所产生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将引领新时代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继续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