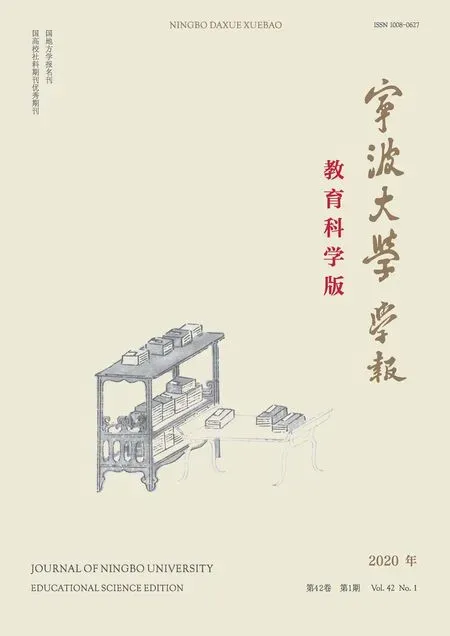个体发展的阶段性与哲学教育的审慎
2020-12-13刘铁芳
刘铁芳
个体发展的阶段性与哲学教育的审慎
刘铁芳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教育的中心问题乃是人的自我认识问题,也即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达成德性与幸福的问题。“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哲学教育的基本出发点,“认识自己无知”,由此保持自我不断地求知智慧,也即“爱智慧”,乃是苏格拉底哲学教育的基本目标,反诘式对话是苏格拉底哲学教育的基本方法。个体成长乃是从天性舒展出发,逐步过渡到理性的生成。苏格拉底哲学教育主要面对成年人而非儿童展开。儿童教育乃是从儿童身体自然出发,激活天赋本能与生命活力,走向积极而非节制的儿童生活。伴随个体成长,个体开始以反思走向个体精神自觉,教育也从诗性教育转向哲学教育,由此而显明个体成长的内在秩序与哲学教育的审慎。
哲学教育;儿童生活;诗性教育
近年来,儿童哲学教育逐渐得到重视。儿童哲学教育的探索对于彰显儿童好奇的天性、激活儿童思维,进而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无疑十分有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从儿童发展的特点出发,在廓清哲学教育的内涵、鼓励儿童哲学教育探索的同时,又保持哲学教育的审慎。这意味着我们有必要回到苏格拉底,重寻哲学教育的基本蕴含,探寻个体成长与教育的合理秩序。
一、哲学教育的意蕴:“认识你自己”
据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记载,苏格拉底曾经专门找到绰号“美男子”,并自以为“有了超越同时代的人的才智”,而且还“深信自己会在言谈和举止方面超过所有的人”[1]的年轻人尤苏戴莫斯,用典型的苏格拉底反诘式对话的方法,让尤苏戴莫斯认识到“我对于我自己的回答再也没有信心了,因为我先前所说的一切现在看起来都和我当时所想的不一样了”,[1]由此而逐步面对苏格拉底引导其曾经看到过但并没有真正想过的德尔菲庙墙上刻的“认识你自己”的问题,一个人要真正认识自己,“必须先察看了自己对于作为人的用处如何,能力如何,才能算是认识自己”“那些认识自己的人,知道什么事对于自己合适,并且能够分辨,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且由于做自己所懂得的事就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而繁荣昌盛,不做自己所不懂的事就不至于犯错误。而且由于有这种自知之明,他们还能够鉴别别人,通过和别人交往,获得幸福,避免祸患”。
显然,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教育的中心问题乃是人的自我认识问题,人的自我认识中心就是把自我置于他人、城邦乃至世界之中,认识自己作为人的用处,知道自己行为的边界,也即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终在得到自己所需以及在和别人交往中获得幸福,同时避免祸患,也即获得自我稳定而深入的内在规定性,由此而自由地立自我于爱他人与世界之中,或如孔子所言“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这里,人的自我认识实际上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本体层面,即如何认识自己究竟是什么,也即认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由此认清自我存在的使命;二是实践层面,即个体如何去行动,也即个体如何充分而又审慎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找到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边界,努力去实践;最终达成的目标乃是个体人生的“获得幸福,避免祸患”,也即个体人生的幸福与完整。这意味着人的自我认识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人究竟应该以怎样的自我来求得个体人生幸福的问题,也即德性与幸福的问题。换言之,哲学教育的中心问题乃是人的自我认识问题,也即一个人究竟该如何达成德性与幸福问题。
如果说“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哲学教育的基本出发点,“认识自己无知”,也即认识到自己在事关人生最重要的德性与幸福问题上的无知,由此保持自我不断地求知智慧,也即“爱智慧”,乃是苏格拉底哲学教育的基本目标。“苏格拉底自身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要教什么,即使是想教也不能教。所谓‘无知的知’就是苏格拉底知道的就是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这种对无知的自觉。由此,苏格拉底能够教的是从我们无意间在共同体中所培养的习惯性的智慧中摆脱。换言之,向通向世俗外个人的道路迈出。”[2]苏格拉底需要以异质性事物的引入改变个体心灵结构,转换致知方式。
如果说“认识自己无知”乃是苏格拉底哲学教育的基本目标,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路径就是苏格拉底式对话,也即反诘式对话。反诘式对话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一个人很难真正从自我既成观念中摆脱出来,用柏拉图的说法就是难以从意见的世界转向知识的世界。正如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所阐释,个体道德发展总是要经历前习俗阶段、习俗阶段与超习俗阶段,个体发展的过程总是要经历一个适应社会然后形成基于理性自律的独立自我,以此而达成对当下社会生活实际的必要超越。如果教育沦为单纯的适应社会,那么社会就无法更新;正是因为年青一代不断地拥有超越现实的独立个性,才能推进社会的更新。换言之,正是超越现实社会的基于理性自律的独立自我的诞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问题在于,一个人适应习俗化生活后要超越习俗化是十分艰难的,这正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反复论及的哲学教育之艰辛所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正是在反诘中,让对话者保持对既有惯常性观念的紧张与陌生,以刺激个体心灵朝向超越习俗与惯常的更高事物,在面对整全的过程中显现自我的无知,由此而达成“无知的知”。如果说早期的教育实践重在亲子、师生之间亲熟感的唤起与思维的激励,培育对知识的爱与探究知识的兴趣,那么哲学教育侧重个体对既有知识的超越与陌生化,由此而激励个体面向整全之思考。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反诘式的对话乃是苏格拉底哲学实践的基本路径,我们实际上并不能把苏格拉底的教育方式简单地套用到低龄阶段的教育实践中,只能借鉴其中的对话精神。
当然,我们也需要从尤苏戴莫斯的转变中清楚地意识到,人的自我认识的完善是一个过程,年轻人重在活出更多基于天赋的感性自我来,成年的过程再一步步反思人的自我存在,逐步理解世界与人生的真谛,回复到个体对自我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深度领会。这意味着哲学教育的过程性。苏格拉底的哲学教育主要地是针对青年与成人,而非儿童。①当苏格拉底要别人听他说“一个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3]之时,他针对的对象是雅典城邦公民,也就是成年人。“苏格拉底的教育其对象不是儿童而是青年和大人,其方法不是上课而是问答,其目的不是社会化而是促使人们觉醒。”[2]苏格拉底的教育不是授人以知,而是成人以觉,不是把人引入共同体,而是以超越共同体的方式促成个体理性的自觉。个体不仅活在共同体之中,以获得对社会适应;同时也活在共同体之上,以获得对习俗生活的超越,寻求更高层面的人与人的共通性。
苏格拉底的教育主要针对成年人展开,儿童教育就发生在生活之中。如果说对于儿童而言,教育的主要目的乃是让他们更多地知悉世界,扩展自我在世间存在的自信与自主,让知识的学习成为个体力量的扩展,这个阶段的教育表达式乃是培根所言的“知识就是力量”,那么,对于青年与成人而言,则需要不断地反思自我对世界的认知,避免个体自满于已有的感知性的、经验性的知识,由此而保持自我向世界的无条件的开放性,也即苏格拉底所欲求的“认识自己无知”,也即以认识自己无知的知来保持个体向着普遍性知识诉求的状态,提升个体心灵境界,使个体心灵上升到更高的知的高度,这个阶段的教育表达式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实践的“美德即知识”。这意味着哲学教育是一个过程,认识自己的无知境遇,乃是建立在个体年少阶段累积起来的对世界的必要的知的基础上,否则,反思就缺少基本内涵。
二、从天性舒展到理性生成:个体成人的内在秩序
苏格拉底的谈话对象主要是青年与成年人,并不包括年幼的儿童,在柏拉图那里,儿童教育的中心乃是音乐和体育。如果说个体发展后期侧重点乃是培育一种“爱智慧”的生存姿态,也即一种对个体既有知识经验的反思与超越,保持个体向着更高知识与智慧的开放性,那么,个体发展前期则重在扩展个体的身体感知,积累必要的知识经验,为其后的哲学反思提供基础。可以说,儿童教育就其实质而言,并非精神性的、哲学性的,而是身体性的、审美性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中没有精神性、哲学性的内涵,而是根本着眼点乃是身体与审美的。“青年人,从十四岁到二十四岁,是艺术家的年龄。热情,爱美,求知,享乐。”[4]热情、爱美、求知、享乐,都可谓个体年轻的感性生命充沛地显现自身的基本方式,是一种努力彰显自我、向外展现自我的、非反思性的更具审美特征的生命姿态,而非个体成年后趋于反省内求、审慎而节制的德性化生命样式。“青年人会向往各种主义,但要他们自己提出主义,只能是浪漫主义。”[5]年轻人思维活跃,感性丰盈,富于青春浪漫气息。这意味着不管是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教育,还是孔子式的伦理教育,都不适合儿童,或者说不能简单地施之于儿童。
当然,这并不排斥儿童期以适合儿童的,审美性的、感性的方式渗透哲学教育,儿童同样具备凭借直觉去发现他们生活中内隐的重要事物,却并不需要以深度反思来推进他们的哲学的、伦理的自觉,这样会反过来弱化他们的直觉能力。换言之,儿童阶段的教育——包括所谓的哲学教育——都应该是以凸显孩子们的基于身体的直觉能力,也即彰显儿童生命活力本身为目标与路径,而非使之显像为成人式的理智化的哲学、伦理教育。
在这个意义上,杜威提出“做中学”对个体早期阶段教育具有恰切的指导意义,或者说具有极富启发的生命意义,鼓励孩子们大胆去做,积极尝试,避免个体过早限于思虑之中,以保持个体积极而生动的身体参与,激活个体旺盛的血气,这对于孕育少年个体健全的生命姿态大有裨益。我们之所以强调早期阶段教育的审美化,正是要以美的教育来寄予个体感性所及之世界的必要迷魅,避免过多思虑,同时以审美情怀来缓和个体因为好奇心旺盛而可能带来的惶惑。《论语》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换言之,对于年少个体而言,并不需要事事三思而后行,再思即可。思虑过多,在造成个体过早限于概念化思考的同时,会让个体形成谨小慎微的个性,不利于培育刚健有为、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命个体。
有人提出,要“培养‘野性而又高贵’的孩子”,野性意味着“身强力壮、吃苦耐劳、追求自由”;高贵意味着“情趣高雅、追求卓越、严于律己”。[6]野性,当然不是指人性的生蛮性,而是突出个体自然性的充分舒展与个体发展内在力量的激活与引领,高贵则是对充分舒展的自然生命的文化引领与教化儒染,赋予个体蓬勃的自然生命力量以文化价值的内涵,把个体发展引向人类文明的方向。前者乃是基于个体人性自然的,往往具有自发的动力,而后者则是后天的、外在于个体自然的。尽管在实践中两者往往是相互渗透的,但在逻辑上则前者具有优先性。唯有建立在对自然人性与个体发展内在力量的合理引导与濡染,才能积极促成个体生命的健康向上。一旦后天的教化实践忽视、甚至替代了个体自然人性与内在力量,这样的教育就全然沦为了个体生命的规训与抑制,这样的结果就是极大地弱化了个体生命在终身发展过程中所能达到的高度与境界。
正如蒋勋所言,“青少年的身体刚刚发育,内在原始的暴力欲望会爆发出一股征服的力量,那是原始的人类在自然和旷野中,以体能保护族群的遗传基因,在现代人身上没有完全消失,只是今天我们用道德将暴力划分为不好的、不对的,于是一种在原始社会里伟大的情操变成一种被禁止的行为。”[7]149蒋勋这里所讲的暴力其实就是每个人天性中一种积极向外展现自我、彰显自我的非关善恶的原初性力量,个体成长过程中需要足够的尊重、重视这种力量,并予以合适的方式来显现这种力量,甚至给予这种力量的显现以必要的尝试错误的空间,过多的规训会抑制身体感性能力的发展。
个体发展乃是从有“我”的存在事实到无“我”的存在境界的转换过程,有“我”的存在正是以有“我”的身体及其活动的存在,也即基于身体自然得以充分舒展并在个人意识中得以凸显的存在。哲学教育乃是逐渐从自我身体欲望的存在中超越出来,达至普遍性认识的过程。个体发展前期充分的自我舒展恰恰是个体发展后期去我化的基础,而没有个体发展前期生动而充实的自我作为基础,个体的反思与超越就是虚弱而乏力的,不足以化育充实而健全的自我人格。少年时期意气风发,血气方刚,积极彰显个人主体意志,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个阶段乃是个体感性能力充分发展、而理性能力尚处萌芽的阶段,充分彰显个人的感性能力以及相应的感性存在方式的同时,显现了年轻人的蓬勃朝气。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更多地理解儿童在12、13岁与18、19岁很容易发生叛逆行为,因为12、13岁正是一个人大脑完全成熟、理智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而17、18岁正是一个人理智基本成熟,但又缺乏足够反思而显得不够成熟的关键阶段。可以说,必要的叛逆正是儿童理智发展为特征的强主体性的表达形式,是不乏野性的生命实践。恰恰是个体儿童发展阶段过于成熟、老练,弱化了一个人理智发展可能达到的高度。
三、儿童教育的身体性:走向积极而非节制的儿童生活
以培养仁德君子为取向的孔子,其教育实践中强调“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他提出“刚毅木讷,近仁”,一个人不一定要辩才无二,一个人也不一定非要急于证明和言说,一个人急于表达和显示,正意味着仁的自觉的缺席。孔子的言说显明的正是一种审慎的主体性,或者说,在孔子这里,作为德性主体,一个重要的品质就是节制,克制自我肉身欲望。显然,孔子的教育实践主要是针对成人展开,确切地说,是接近个体发展之哲学自觉阶段的教育实践。孔子所期待的个体哲学自觉的目标,偏于伦理上的适应性,不强调个体的创造性与对共同体的超越,这跟苏格拉底的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作为个体成人关键阶段的教育形式,孔子对个体人格发展的期待,依然富于启迪:一个成熟的人置身他人之中,首先不是急于展现自己的才智,而是求得人格上的平易近人,人与人的关联始终是重要而基础性的。个体成人即活在人与人的关系结构之中,做事以做人为基础,确切地说,做事以人与人的关联为基础,任何事最终回到人与人的关联,做事的根本就在做人。这里值得思考的是,一旦我们把孔子的“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过早地前置,就难免会导致个体发展的倒置,换言之,个体前期的教育恰恰是要激励个体的身体感知与表达,让他们不仅敏于行,也要敏于感知和言说,儿童发展过程中的身体姿态不应该是刚毅木讷,而是要生动活泼、自然质朴、健康向上。
《论语》中有一段经典论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在孔子这里,回复到礼的规范与要求可谓个体成人的基本目标,路径则是个人的自觉反省,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在孔子这里,回到自我的反省思维可谓其主体性自觉的基本路径。显然,自反型的思维方式乃是个体主体性发展的重要路径,但过早地强调个人的自我反思,却并不利于个体成长。反省之后乃是躬行实践,这就是孔子向颜渊解释“仁”的具体细目时所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乃是要以对礼的自觉来规约个体的日常生活,显然,这种规约所凸显的乃是对成年人道德自觉的保持,一旦运用到更具自然发展意味的儿童世界之中,就必然会导致儿童生命特征的遮蔽。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同样是针对成年人的伦理规定,如果说这个命题针对成年人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即成年人需要保持自我欲望的适度,以欲望的合理化节制来甄定自我人生的目的,那么,对于处在蓬勃发展阶段的儿童而言,则首先是如何让个体自然欲望合理显现出来,并进一步扩展、提升这种欲望,而非简单压抑之,由此而发展青少年儿童蓬勃的生命力。个体积极的欲求,正是一个人生命成长的内在基础。个体人生早期的教育重在引导儿童基于身体自然的自由自主体验的充分展开,在于教育过程的游戏与审美化,以激发个体内在生命力的丰盈,一旦我们过早地要求儿童不断地后思、反思,恰恰会极大地弱化儿童自然生命体验的充分扩展与自由生成。“一个人要成熟、成长、成功,其过程应该是不自觉、半自觉、自觉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8]553换言之,个体发展需要经历不自觉、半自觉,再到自觉的过程,基于反思的德性教育需要足够的沉潜,孔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苏格拉底的“认识自己无知”都是对成年人或即将成年的青年人所言。正如木心所言,“道德力量是潜力,不是显力……道德力量愈隐愈好。一点点透出来。”[8]555-556换言之,唯有当个体有了年少阶段累积起来的充足的生命准备,再辅之以必要的反思,促成个体生命的自觉,德性的升华就成为自然;也唯有个体发展前期积淀深厚,个体发展后期的德性力量才得以一点点显现出来。相反,过早地强调个体自觉、反思,换言之,过早地发挥个体的道德力量,必然弱化个体发展前期的德性准备,反过来弱化了个体人生德性力量不断显现、厚积薄发的可能性,也即弱化个体德性发展的高度。
当然,我们说德性教育的沉潜,并不意味着个体前期的教育是非德性的,准确地说,个体前期的教育乃是前德性的,即作为德性的准备。换言之,德性教育需要沉潜到个体发展前期的身体教育、审美教育、情感教育之中,沉潜在中期的理智教育、文学(文化)教育之中;个体前期爱的情感的培育、审美情感的陶冶与理智兴趣的发展,都是德性教育的准备,或者说都渗透着德性教育。而个体发展专门的育德形式主要以消极的方式,也即以行为规范与成年人榜样示范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柯尔伯格所言的前习俗与习俗水平阶段的道德教育,一种非反思性的道德教育。
对于儿童而言,恰恰是要从自我身体出发,积极地去感受世界、经验世界,发展基于个人身体的向着他人和世界的爱,同时学会积极表达自我、展示自我,并在表达与展示中充实自我,由此而培养积极生活的人。正是个体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自由的凸显与在此过程中个人主体性的积极建构,才会有个体成长后期之伦理自觉与审慎主体性的必要性。这意味着儿童早期对学习目标、学习过程的自觉应该是模糊的,不宜过于明晰;对儿童的教育应该是正面引导的、积极的,鼓励他们去感受生活世界的爱与自由,辅之以必要的规范约束。这也是我们需要慎行少儿读经的原因所在,以传统儒学为基本内容的古代启蒙经典,过于强调个体的反思自觉与行为规范,规训特征明显,具有浓郁的成人式教化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儒家教化体系从根本而言是针对成人的,而非儿童,儿童的诞生本身乃是近代社会与教育的产物。
即使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蒙学教材,表面上是为儿童准备的,但其实并不是为儿童准备的,只不过是把儿童作为小大人来灌输。正如周作人所言,“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9]换言之,传统蒙学教材所指向的其实只是小大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一旦把原本针对成人的儒家经典变成儿童教育的基本内容,便会过多地显示其对儿童自然性的规训意味,这样的结果就是儿童发展中的早熟,失去了基于个人自然天性的丰沛的力量与生气。②儿童教育的基本品质,或主导性品质,乃是身体性的而非理智性的,是诗性的而非理性的,是浪漫的而非现实的。如果说成人阶段中的主体性,乃是以向着他人与世界开放的、自我显现为审慎与节制品质而展现出成熟的理性,那么儿童阶段处于发展中的主体性显然并不是审慎与节制,而是自然生命的成全,也即个体自然生命的充分展开,是为个体节制品质的形成提供愉悦而充分的生命体验。儿童阶段当然也可以有,甚至不乏哲学式的思考,但儿童的哲学思考更多地乃是基于直觉的对事物的模糊性认知,而非反思性的对事物的理智性判断。年少阶段基于个人身体的充分经验,正是一个人成年过程中走向在世界之中的审慎之存在的基础。恰恰是过早的知识性的、反思性的学习,使得个体成长的中心上移,也即从基于身体的教育上移到基于心智的教育,由此导致个人身体对外在世界的感受与体验的弱化、个人身体的感受力与活力的弱化,以及身体在整体教育体系中的弱化,这样的结果就是个体心智发展所需要的个体之于世界的丰富而生动的感受力的弱化与个人身体自身感受能力及其活力的匮乏,导致身体活力与个人心智创造力的双重不足。
四、从诗性教育到哲学教育:反思与个体精神自觉
发生于青年初期而成熟于青年后期的哲学自觉阶段,引导个体在反思中重新回到自我,包容他者,寻求弱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不再显现出前一阶段经常出现的单纯理智的冲动,个体发展进入理性逐渐成熟的阶段。怀特海从自由与纪律的视角把个体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自由阶段为浪漫阶段,中间的纪律阶段为精确阶段,最后的自由阶段为综合运用阶段。[10]怀特海乃是从智性发展与自由的关系言及浪漫阶段的重要性,浪漫不仅是思维层面的,理智的浪漫,而且是生命气质的。个体发展需要历经诗性的,理智性的,再到成熟理性的。缺少了前一段诗性教育的充分孕育,理智性阶段的教育难免会缺乏动力与方向,而后一段的哲学自觉就难免空乏。如果说儿童期是个体人生的出发,这个阶段主要是自然生命的孕育与自我意识在积极寻求、充满期待中的开启,这一阶段乃是从个人自然身体感性出发的诗化教育阶段,以反思为基本特征的哲学教育阶段,可谓对个体人生出发的理性应答,是基于个体人生经验的充分反思,在个体与世界、历史之中寻求意义,引导个体活出人类精神的高度。
亚里士多德所言“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从个体发展视角而言之,意味着个体成长后期的哲学自觉正是对年少阶段基于身体与自然天性的好奇心回应,正是年少阶段所开启的基于个人身体与自然天性的好奇心的充分扩展,才使个体成长后期充分的哲学反思成为可能。
换言之,年少阶段个体与世界的感性联系中充分发展个体的身体感官,孕育、扩展个体的好奇心,保持对周遭事物的生动兴趣,这正是一个人哲学教育的起始之点。个体年少阶段诸种神奇事物的体验,虽不被个体充分领悟,但个体浸润其中,成为个体成年后对其成长之客观性的理性认同的初始依据,换言之,个体成长后期努力寻求自我完善的客观性依据的过程,其实也是对个体早期神奇事物经验的自觉回应。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年少阶段神奇事物经验正是世界之客观性以及个体人生之命运或必然性向着个体的初始性体现。个体年少阶段的多样性经验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其中不知不觉孕育着个体成长渐次显现的内在依据,可以说,年少阶段的经验奠定个体发展的内在基础。
我们重温索福克勒斯所写的两部关于俄狄浦斯的悲剧,③即《俄狄浦斯王》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两部悲剧刻画了两个不同的俄狄浦斯,一个代表青年,一个代表老年。作为年轻人的俄狄浦斯,智慧、勇敢、勇于行动,他战胜了斯芬克斯,挽救了忒拜,惠泽世人。然而他弑父娶母,遭命运惩罚,祸害城邦。年轻的俄狄浦斯既是福也是祸,既拯救也瓦解城邦。这是《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流浪中的老者俄狄浦斯来到雅典城外一片宁静之地——科罗诺斯。那里安详,密布着月桂树、橄榄树和葡萄藤,夜莺在丛林深处低语歌唱,一派明媚风光。阿波罗预言,俄狄浦斯流浪多年后会在那片圣林安息,最终果如阿波罗所言,俄狄浦斯魂归于此。年轻的俄狄浦斯弑父娶母,象征了年轻者对年长者的胜利,冲动对克制的胜利,以及自由对秩序的僭越。而年老的俄狄浦斯稳重、安详、谨慎,是理性和秩序对无节制的自由的驾驭。[11]161这其中,可以说很清晰地呈现出人的主体性发展与嬗变的基本样式:个人在知识不断增长、主体意识上升的条件下难免表现出胆大妄为,自信自己的知识高于神的智慧,并炫耀自己理性的无所不能,最终这种“妄为”使得斯芬克斯跳下悬崖自尽。导致人的盲目自信与高傲的缘由在于无知——对自己根源的无知,无知而妄为使俄狄浦斯弑父娶母,不仅使自己也使城邦遭受大灾难。消饵灾难的方式乃是以整全性知识重新认识自我,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无疑,这也是苏格拉底不停地吁求“认识你自己”的旨趣所在,也是舍勒重提人在宇宙中位置的用心所在,不管是个体的人还是人类,都需要不断地甄定自我。“人从神那里脱离出来,独自站在这个复杂的宇宙面前,惊慌失措,便蛮横地对待一切,所以人的自大其实植根于人的软弱上。人应该明白自己的软弱性,人来自肮脏的泥土,因为必须向自然表达尊重,努力学习和理解自然并与其建立正确的关系。”[11]8
我们可以进一步追溯到荷马史诗:《荷马史诗》中,《伊利亚特》讲的出征、出发,而《奥德赛》讲的则是回归。[12]伊利亚特的原意是“一系列的战绩”,奥德赛的原意是“漫长而曲折的旅程”;《伊利亚特》阳刚,具有男性意味,《奥德赛》是女性的,温和,富人情味。[13]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在诗人荷马的不断讲述中,似乎暗含着个体发展的两个阶段的不同诉求:年轻时期求战绩,成熟以后注重韧性的坚持;人生的出发总是期待着以力量的生长来寻求对外在世界的控制,回归则是在更漫长而曲折的生命意义探寻中返回自身。站在个体发展的立场而言之,年轻人血气方刚,感性能力充分彰显,不乏鲁莽地运用自己的天赋才能,这意味着年轻人在一定限度内的基于身体本能的理智冲动之合理性,换言之,年轻人的生命本质乃是更接近天赋本能的,更易于彰显个人自我天赋本能与理智能力,而非事关整体与关系的理性精神与伦理品质。
“在青少年的世界里,所有的行为都可能与暴力有关。因为他们身体发育之后,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但心智的成熟度还不能控制这股力量,使他觉得好像是身体要去做某些事情,他必须让他的手和脚去做那些事,才会觉得开心。”[7]150随着激情衰减,理性日渐成熟,个体不单是欲求运用自己的理智,而且要对理智能力的运用做出必要的后思,也即反思,以甄定个体人生的目标,求得天赋理智能力运用的意义,可谓个体哲学自觉的深化,这个阶段的生命本质乃是对天赋本能的超越,从理智性走向伦理性。唯有在这个时候,个体才真正达成柏拉图《理想国》所言的理性引导激情来控制人的欲望,在秩序中获得个体自由,而非以自由僭越秩序。④这不仅是个体精神发展的内在取向,同时也是人类精神自觉的基本方向。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不断地寻求个体精神自觉,避免个体发展特别是个体发展趋于成熟阶段的虚妄与自大,同时也需要切实地意识到个体精神发展的过程性,尊重个体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的年少轻狂。显然,如果出现个体发展秩序的颠覆,年轻人过于老成持重,这样的结果乃是年少个体生命活力的萎缩,同时也难免弱化个体理性自觉所能达到的高度。个体发展前期的重心是引导并激励个体开启生活、创造生活,而非反思生活、省察生活。正如纪伯伦所言,“你不可能同时具有青春和对青春的知识。因为青春忙着生活,不去知悟,而知识又忙于寻求自我,不去生活。”[14]年轻人更需要的是青春生活本身,而非知悟青春,过度的反思恰恰会弱化青春生活本身。这意味着我们对于年轻人的哲学教化是需要特别审慎的,特别是对于有着悠远的规训传统的我们而言,尤其需要警惕年轻人教育的过度,我们应该更多地鼓励、激励年轻人发扬自己的天性,彰显天赋才能,凸显个体生命的自然与自由,以孕育活泼、健全、广博的生命气象。
五、走向爱与智慧的融合:哲学教育的审慎
正如黑格尔所言,“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即雅典娜)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5]黑格尔用密纳发(又译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来比喻哲学,旨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是一种沉思的理性。反思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如果把“认识”和“思想”比喻为鸟儿在旭日东升或艳阳当空的蓝天下翱翔,“反思”当然只能是在薄暮降临时才悄然起飞了。黑格尔讲的哲学,这对于个体成长中的哲学教育的展开同样富于启发,只有在个体成长之初期、中期让自我生命充分地舒展、历练,得到激励,个体生命真正翱翔起来,才可能有成长后期充分的哲学反思与生命自觉。
如果说教化的本质乃是个体从偶然性的自然天性出发,向着普遍性的超越与提升,那么,这种超越的基础正是年少阶段充分发展的自然性,也即个体自然感性生命的充分彰显。年少阶段充分发展的自然生命,使得个体向着德性存在的超越成为一种内在的——而非外在强迫性的——超越成为可能。
过早地开始哲学反思,难免会导致个体的早熟,在反思中趋于静默与内敛,由此而弱化年轻生活的蓬勃舒展,导致生活形态与其年龄阶段不相吻合。⑤个体发展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精神气质,不能彼此替代,前后倒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广义上的哲学教育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包容着年少阶段基于个体肉身与天赋本能为基础的诗性孕育,以及这种诗性教育所孕育出来的个体与世界的感受性联系,以及这种联系中所蕴含的个体对世界的爱,个体成长过程中逐渐获知的知识与智慧包容在年少阶段所孕育出来的个体向着他人和世界的爱的情感态度之中,由此引导着个体知识与智慧发展的方向,进而使个体人生呈现为爱与智慧彼此融合,也即“爱智慧”的人生成为可能。
注释
①柏拉图就是在狄俄尼索斯剧院前听了苏格拉底的谈话后,丢弃自己原来想用悲剧争取荣誉的想法,把自己的诗作投进了火堆。正是从那时起,他做了苏格拉底的学生。据说,他当时已满20岁。(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6,徐开来、溥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8页。)综观柏拉图所写下的苏格拉底对话,比如,以《理想国》为代表,苏格拉底对话主要是与两类人展开,一是以克法诺斯、色拉叙马霍斯为代表的充分世俗化的成年人,一是以格劳孔为代表的尚未完全社会化的有潜质的年轻人,对于前者,苏格拉底的对话方式往往是以反讽,或强反讽为主,对于后者则苏格拉底侧重不断地梳理事情本身,从城邦何以可能的发端开始,一点点从现实城邦的建构转向理想城邦的中心,即灵魂的德性与教化,由此而显明个体幸福与城邦福祉的内在统一性。《理想国》的对话正是以跟前者的对话提出问题,以与后者的对话来逐步展现理想城邦的可能性。
②在这一点上,卢梭的自然教育理念及其对儿童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早在其《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的征文中,卢梭就表现出对近代以来逐渐涌现的日常生活中的虚饰、浮华可能带来的人性的堕落,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沛然生气的警惕,提出装饰对于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就是灵魂的力量于生气”。(参见李瑜青主编:《卢梭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个体在儿童期的早熟,直接导致自然天性在个体成长中的匮乏,由此而培养出长于虚饰而缺于活力与勇气的贫乏的个体。
③我在《古典传统的回归与教养性教育的重建》一书中引用俄狄浦斯的故事,侧重说明个体理性生长是一个过程:“索福克勒斯对俄狄浦斯的描述暗含着个体教化的路径,年轻人凭靠血气,难免鲁莽,过于自信,年长者则凭借不断扩展的理性而变得稳重、安详。这意味着理性的生长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理性的生长孕育在生活之中,孕育在人生历程之中,孕育在人类经验之中。”(刘铁芳:《古典传统的回归与教养性教育的重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此处重新引用,意在阐发年轻人与年长者在个体发展中的不同特点及其合理性。
④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发展性的视角来理解与阐释柏拉图的教育理念,以促成个体发展的合理秩序,而非简单地贬抑年轻人的肉身性存在,或者从人类整体的意义而言之,贬抑人的肉身,走向简单的禁欲主义。
⑤许倬云谈及童年时看到奔赴前线的军人一排一排从大门口路过的经历时这样写道:“站在门边台阶上一望,一排一排坐在地上的军人望不见边,他们的步枪一堆一堆架在路边上,像小山似的。身上挂了两颗手榴弹,交叉着两条子弹带,背上都有背包。这是湖北的沙市,时间是在七七事变后不久。从早到晚,一批批的战士步下码头,登轮往江下驶去,而另一批部队从街的那边来接替刚开拔的那一批部队。父亲在这个时候跟我说,这些人是真正的出征了,不是调防。母亲口念佛号,说:‘阿弥陀佛,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还能够回来。’平常她是不宣佛号的,但是那天,我看见她很虔诚地为这些军人在祈祷。很快地我们就知道什么叫轰炸,很快地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流亡,很快地我懂得母亲所说的‘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还能回来。’这个鲜明的印象,使我领悟到生与死的界限,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当时年纪还幼小,不知道其中的意义,只晓得这些人成批成批地开拔出去,或许永远不回来了。这幕景象,从此切开了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许倬云:《许倬云问学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母亲的感叹促成了年幼的许倬云的生命之惊奇感与哲学自觉的发生,也把人生的沉重加在年幼无知的童年上,童年的“蒙”(昧)因此而被过早地(开)“启”。这里实际上是儿童之启蒙教育的辩证法,合理的启蒙乃是合宜之“启”与必要之“蒙”的统一,离开了适度的蒙,就会导致童年的过度敞亮,儿童性就会失去必要的屏蔽而迅速丧失。
[1] 色诺芬. 回忆苏格拉底[M].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84:140-150.
[2] 矢野智司. 作为赠与者的教师的诞生与死亡——探寻教育起源的新视角[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4(1): 9-11.
[3] 柏拉图. 苏格拉底的申辩[M]. 吴飞,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131.
[4] 木心. 木心谈木心[M]. 陈丹青, 笔录,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92.
[5] 木心. 文学回忆录:上册[M]. 陈丹青, 笔录.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272.
[6] 柯领. 培养“野性而又高贵”的孩子[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4: 5.
[7] 蒋勋. 孤独六讲[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8] 木心. 文学回忆录: 下册[M]. 陈丹青, 笔录,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9] 周作人. 儿童的文学, 艺术与生活[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24.
[10] 怀特海. 教育的目的[M]. 徐汝舟,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55.
[11] 肖厚国. 自然与人为: 人类自由的古典意义[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2] 刘铁芳. 古典传统的回归与教养性教育的重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07.
[13]木心. 1989-1994文学回忆录[M]. 陈丹青, 笔录.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1, 43.
[14] 纪伯伦. 先知·沙与沫[M]. 钱满素, 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120.
[15]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杨, 张企泰, 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 14.
Stages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Prudence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LIU Tie-fang
(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
Socrates believed that the central issue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is human self-knowledge that can help a person acquire virtue and happiness. According to Socrates, “knowing yourself”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while “knowing your own ignorance” urging yourself continually to seek learning and wisdom, which emphasizes the “enthusiasm for wisdom” as the basic goal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in the way of rhetorical dialogue. And an Individual develops from nature to a gradually nurtured rationality. The Socratic philosophy education is mainly directed at adults rather than children whose growth is based on physical nature to activate the innate instinct and life vitality, a positive and non-restrictive life. The individual is growing into reflecting on self-consciousness in its life journey, and its education also shifts from poetics to philosophy, thus showing the internal order of an individual’s growth and the prudence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philosophy education; child life; poetic education
G40-02
A
1008-0627(2020)01-0008-10
2019-10-10
2018年湖南省教学改革项目“以经典研读深化师范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研究”(湘教通〔2018〕436号)
刘铁芳(1969-),男,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哲学。E-mail:tiefangliu@163.com
(责任编辑 赵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