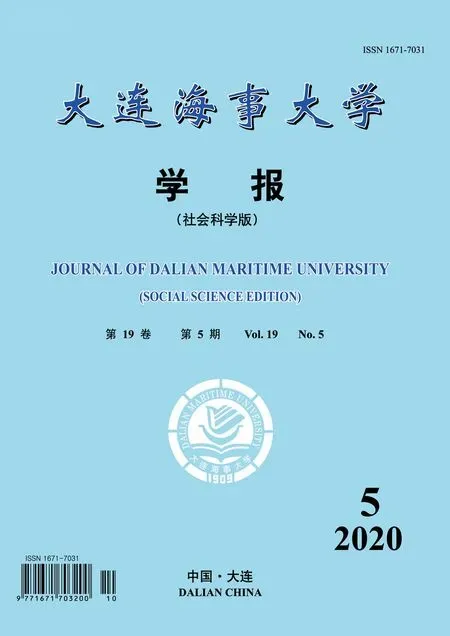“乌克兰诉俄罗斯扣押军舰案”临时措施裁定述评
——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2020-12-12郭中元邹立刚
郭中元,邹立刚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口 570228)
2019年5月25日,国际海洋法庭为“乌克兰诉俄罗斯扣押军舰案”指示了临时措施。本案涉及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UNCLOS)解释或适用的争端的范围、交换意见的履行标准、“军事活动例外”的条件等关涉国际海洋法裁判机构确定管辖权趋向的诸多重要问题。而我国与8个海上邻国存在不同程度的海洋争端,为保护本国海洋权益免受“讼累”,应提高警惕并加强对本案所涉问题的研究,研判国际司法机构对海洋争端的管辖权趋势,针对UNCLOS争端解决机制充分构建“防御机制”,充分维护本国合法权益。
一、“乌克兰诉俄罗斯扣押军舰案”概述
(一)本案背景
2018年11月25日上午,乌克兰两艘炮艇和一艘拖船从黑海的敖德萨港出发,计划通过刻赤海峡到亚速海的马里乌波尔港。乌方通知俄方其通过海峡的意图后,俄方以其领海的通过暂时被停止及乌方没有进行申请为由予以拒绝。乌方根据其与俄罗斯2003年签署的《俄乌两国关于使用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合作协定》,主张享有航行自由的权利,遂径行通过俄罗斯主张的领海驶向刻赤海峡。在此期间俄方舰船对乌方舰船采取了拦截、封堵等措施。当晚,在乌方舰船试图返航敖德萨港时,俄方海岸警卫队展开追击,并在距离克里米亚海岸约23公里处开炮命中乌方一艘炮艇,随后扣押了乌方该三艘舰船及其24名乌克兰海军人员。①之后,俄方以非法穿越俄国国界罪对该24名海军士兵提起刑事司法程序。针对俄罗斯的行为,2019年3月31日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出通知启动UNCLOS附件七下的仲裁程序。2019年4月16日,由于仲裁庭尚未组成,乌克兰依据UNCLOS第290.5条的规定,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下称法庭)指示临时措施——要求俄国立即释放三艘军舰和24名海军人员。2019年4月30日,俄罗斯通知法庭其不参加该审理程序,但在5月7日向法庭发出备忘录表明其立场。
(二)乌方的诉求及其法理根据
1.管辖权问题
乌克兰认为根据UNCLOS第286条和第288条,附件七下的仲裁庭具有管辖权。
(1)乌克兰和俄罗斯均为UNCLOS缔约国,并就UNCLOS第32、58、95、96条的解释和适用产生争端。
(2)乌克兰关于附件七争端的通知符合UNCLOS第287、283条的要求。根据第287条,乌克兰和俄罗斯都选择附件七仲裁作为解决此类争端的手段;根据第283条,乌克兰已采取合理和迅速的步骤,与俄罗斯就通过谈判或其他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进行了交换意见。(1)Request of Ukraine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under Article 290, Paragraph 5,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para.15-18.
(3)本案不适用“军事活动例外”:第一,不能仅因为涉及军舰或存在军舰就认定争端“涉及军事活动”,重要的是船只从事的活动类型。许多国家利用其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在海上执法,“军事活动例外”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涉及军舰的争端。第二,乌方军舰试图离开时,俄罗斯海岸警卫队以违反其国内法进行追捕,因此这是一次典型的执法冲突,而无论是俄罗斯海军参与这一事件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将执法活动转化为军事活动。第三,乌方计划的军舰通过行为不构成俄罗斯所谓的“秘密入侵”,船上搜出的文件的目的是避免在从敖德萨到达刻赤海峡所需的两天内与俄罗斯政府船只引发冲突,并且考虑到海峡和通航航道的宽度,“秘密入侵”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别是乌舰指挥官已向俄方通报了这三艘船只通过刻赤海峡的意图。(2)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ITLOS Case No 26, Order of 25 May 2019, paras.57-62.
2.临时措施问题
(1)乌克兰认为其军舰和海军辅助船享有完全豁免权,船上军人享受给予履行公务的公务员的习惯豁免,因此,豁免于捕获、扣押和法律程序;捕获并扣押军舰或其他海军舰艇和船上人员严重危及船旗国的权利和尊严,构成紧急情况。(3)Request of Ukraine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paras.20, 23-26.
(2)乌克兰进一步以实际和人道主义的考虑请求法庭指示临时措施:第一,对任何船只的船长和船员提起法律诉讼,将对船旗国的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是一种紧急情况。第二,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应释放24名被拘留的乌克兰军人。第三,俄罗斯对乌克兰船只豁免权的侵犯可能损害其适航能力。乌克兰军舰老旧且在2018年11月25日的事件中受到损害,若乌克兰无法对船只进行维修保养,将进一步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4)Request of Ukraine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paras.36-42.
(三)俄罗斯的回应及其法理根据
1.管辖权问题
(1)俄方认为本案争端涉及军事活动,双方已根据UNCLOS第298条做出声明,将与军事活动有关的争端排除适用强制程序:第一,根据在乌方军舰上发现的“准备航行清单”,该三艘舰船的任务是不被允许的“秘密”侵入俄罗斯领海,因此受到俄海岸警卫队的抵制和扣押。这显然是一个关于军事活动的争端。(5)Memorandum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a.28.第二,本事件符合仲裁案法庭曾对“典型的军事情形”的描述,即“涉及一方军队与另一方军事和准军事部队的结合进行相互对峙”。第三,乌克兰事后一系列声明将事件描述为“军事活动”,如其2018年11月26日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声明中提到“俄罗斯最近的交战行为”,其与俄罗斯的正式通信中提到“俄罗斯联邦的行动是对乌克兰领土上的乌克兰海军舰艇非法使用武力”、“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舰艇采取的行动造成严重后果,构成武装侵略罪”,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正式发言中提到“乌克兰确定2018年11月25日俄罗斯对乌克兰海军舰艇采取的行动是武装侵略行为”。(6)Memorandum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a.32.
(2)乌方交换意见义务尚未履行完毕。在2019年3月15日乌方给俄方的照会中提出“根据公约第283条的规定,乌方要求俄方迅速就通过谈判或其他和平手段解决这一争端交换意见”,并“任意”规定“10天内”的最后期限。在10天内,即2019年3月25日,俄方提供了书面回应。然而乌方未能等待实质性答复,在2019年3月31日发出启动仲裁程序的通知。俄方表示愿意继续就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进行对话,但乌方宣称对该途径不感兴趣,并选择坚持就临时措施举行听询会。因此,UNCLOS第283条的条件尚未满足。(7)Memorandum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a.37.
2.临时措施问题
(1)本案不存在紧迫性。第一,参照尚未组成附件七仲裁庭的期间来评估这种紧迫性,自2018年11月25日事件以来,乌方等待了4个多月才于2019年4月16日向法庭寻求临时救济。第二,乌克兰已经通过欧洲人权法院获得临时救济,“确保对被扣押的乌克兰海军人员进行适当的医疗”。
(2)构成对案件实体问题的预先判断。俄罗斯认为临时措施的要求不能预先判断案件实体问题。乌克兰在其临时措施请求中寻求与基于案件实体问题相同的救济,即既在仲裁程序中也在临时措施请求中寻求释放乌克兰舰船及其军人。如果三艘乌克兰军舰和军人获释,则乌克兰将不再需要在实体阶段寻求该释放的同类救济。
(四)国际海洋法庭的裁判
2019年5月25日,法庭认为将组建的仲裁庭享有初步管辖权,且乌方主张的权利具有合理性,所涉情势紧急有必要,因此指示了临时措施。
1.判定将组建的仲裁庭享有初步管辖权
(1)本案存在关于UNCLOS解释或适用的争端。乌方指控俄方扣押其军舰及船员的行为违反UNCLOS第32、58、95、98条的规定,俄方在5月7日向法庭发出备忘录表明了立场,法庭通过俄方的相关行为推断出其不认为其违反上述条款。因此法庭认为,两国之间初步存在关于该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8)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ITLOS Case No 26, Order of 25 May 2019, paras.43-45.
(2)本案所涉争端并非“关于军事活动的争端”。第一,乌方舰艇的通过行为不构成“未经允许的‘秘密’入侵”:其军舰两个月前成功地完成了同样的通过任务;“别尔江斯克”号指挥官向俄当局通报了这三艘船只通过刻赤海峡的意图;鉴于刻赤海峡及其航道的宽度,不可能进行“秘密入侵”。第二,争端的核心是各方对刻赤海峡通行制度的不同解释,而这种争端不是军事性质的。第三,俄方海岸警卫队是在追捕放弃通过任务而准备离开的乌方军舰过程中使用武力,这似乎是在执法行动而不是军事行动中使用武力。
(3)两国交换意见的义务已履行完毕。乌方在其2019年3月15日的照会中明确表示愿与俄方就如何在特定时限内解决争端交换意见。鉴于交换意见应迅速进行,乌方照会中设定的10天时限不能被视为“任意”。俄方在2019年3月25日的答复中说,对乌方提出的问题的“可能”评论将“单独送交”,其性质使乌方能够合理地得出结论,即在这样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经用尽。而缔约国在断定已用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时,不必继续交换意见。(9)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ITLOS Case No 26, Order of 25 May 2019, paras.68-76.
2.指示临时措施
(1)乌方在争端中寻求保护的权利是合理的。乌方舰船属于军舰和政府船只,因此乌克兰基于UNCLOS第32、58、95和96条提出的权利主张是合理的。此外,船上的24名军人是乌方军事和安全人员。(10)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ITLOS Case No 26, Order of 25 May 2019, paras.97-99.
(2)存在真实、迫切、不可弥补的损害风险。任何影响军舰豁免权的行动都有可能严重损害一国的尊严和主权,并有可能破坏其国家安全。俄方行为将对乌方军舰和军人的豁免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从本案来看,这种损害的风险是真实的、持续进行的。而且,持续剥夺乌方人员的自由还将引发人道主义担忧。在仲裁庭组建和运转之前,乌方的权利面临着不可弥补的损害的现实和迫切的风险。(11)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ITLOS Case No 26, Order of 25 May 2019, paras.110-113.
(3)法庭以19∶1通过并指示了临时措施:俄方立即释放乌克兰军舰“别尔江斯克”号、“尼科波尔”号以及“亚内卡布”号;立即释放24名乌克兰军人;双方应克制并避免激化和扩大争端。俄罗斯籍法官Kolodkin表示反对并撰写了法官个人意见。
二、关于本案管辖权问题的述评
(一)本案是否存在关于UNCLOS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及其性质
1.双方不存在关于UNCLOS解释或适用的争端
初步管辖权是指示临时措施的最基本要求,海洋法法庭应采取严格的办法来确定争端的存在。[1]
(1)在本案中,乌方主张俄方扣押其三艘舰船的行为侵犯其根据UNCLOS第32、58、95和96条享有的豁免权,法庭因此推定存在争端。然而,俄方明确表示乌方舰船违反UNCLOS第19条、第25.3条,而其采取措施的依据是第30条。[2]可见,本案双方并未就相同条款的解释或适用产生争端。
(2)根据乌方的说法,俄方海岸警卫队登临时,“别尔江斯克”号和“亚内卡布”号是在距离海岸约12海里处,“尼科波尔”号是在距离海岸约20海里处。但同时指出俄方登船时干扰了舰船的无线电传输,这可能妨碍了他们传送准确的位置。(12)Request of Ukraine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para.8.某澳籍人士的调查报告表明:俄海岸警卫队对“别尔江斯克”号军舰的炮击发生在距离克里米亚海岸12海里外500米处。[3]另一位德籍学者的调查报告持同样的观点。[4]因此,乌方和法庭以第58条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和义务、第95条公海上军舰的豁免权、第96条公海上专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的豁免权等条款来确定争端的存在是牵强附会。此外,乌方和法庭对于第32条进行了割裂性解释和适用,即选择解释和适用其后半句“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的豁免权”,而弃却其前半句“A分节和第30及第31条所规定的情形除外”。
(3)俄方海岸警卫队对乌方舰船进行追击、炮击之后并实施逮捕、扣押等一系列行为,不构成行政执法的武力使用而是武装冲突的武力使用。正如某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法庭适用后者,海战法作为特别法就会取代军舰豁免的概念,而结果就会完全不同”[5]。由于此时海战法代替海洋法的适用,则乌俄双方不可能产生UNCLOS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
(4)法庭认为本案争端的核心是当事方对刻赤海峡的通行制度有不同的解释。若乌方以乌俄之间的双边条约来主张其航行权,那么本案争端则为关于乌俄双边条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而不是关于UNCLOS解释和适用的争端。若乌方基于UNCLOS的海域制度主张航行权,然而双方存在克里米亚的领土主权争端,从而亚速海、刻赤海峡存在重叠海域且未划定海洋边界。而根据UNCLOS第298.1条(a)项“任何争端如果必然涉及同时审议与大陆或岛屿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任何尚未解决的争端,则不应提交这一程序”,则法庭不能确立其管辖权。
2.本案涉及“军事活动”的争端
(1)从乌方军舰上搜出的“准备航行清单”表明乌方此次并非单纯的通过行为,而是有目的的军事行动:第一,乌方“秘密接近并通过刻赤海峡”,(13)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Kolodkin, para.14.“秘密地驶出俄罗斯……沿海和海上巡逻区域”。(14)Memorandum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a.21.第二,虽然法庭认为鉴于刻赤海峡的宽度,乌方不可能进行“秘密入侵”,但这只是客观困难,却不能排除主观目的的存在。第三,乌方告知俄方其通过刻赤海峡的意图是在被俄方发现之后。第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事件中,乌海军司令部试图从亚速海再派出两艘军舰作为增援部队。[4]第五,鉴于此威胁,俄方用货船封锁了刻赤海峡并派出战斗机和直升机各两架对海峡进行巡逻。其他乌方三艘海军舰船均被俄方舰船封锁在刻赤海峡南侧471号锚地附近。[6]2016年《日内瓦公约》评注指出:“宣布、建立和实施有效的海上或空中封锁,作为一种‘战争行为’,这可能足以引发国际武装冲突。”[7]Para.223
(2)俄方舰船的追击、开炮,军机的拦截以及黑海舰队的监视等行为构成军事武力使用。2016年《日内瓦公约》评注指出:“在海上使用武力的动机不是国家执行适用于海上的管理制度时,视情况而定,这种情况可能属于国际武装冲突。”[7]Para.227第一,俄方炮击所在海域为毗连区,而乌方舰船并无违犯毗连区四项管辖事项的行为。第二,澳籍记者的调查报告指出俄方舰船威胁“别尔江斯克”号,若不停航将使用“致命武器”,事后该军舰上留有许多小口径的弹孔以及舰桥至少一个大口径的弹孔。[3]在“圭亚那诉苏里南案”中,苏里南海军仅对圭亚那授权进行探勘的钻井平台发出警告“若不及时撤离,将后果自负”即被仲裁庭裁定构成“程度轻微的武力使用”而属于军事行动的威胁。(15)Guyana v. Suriname, Arbitral Tribunal Constituted Pursuant to Article 287,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II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Matter of an Arbitration between Guyana and Suriname, Award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2007, para.439-440.第三,中外诸多学者认为,针对外国军用舰机或公务船舶和飞机的行为,通常应认为是军事性活动。[8]对拥有主权地位的船只使用武力显然超出了国家警察权力的范围和普遍接受的警务的目的。因此,不能合理地将其理解为执法性质。[9]执法活动及警察武力必然无法针对此类具有“公务性质”的船舶,而军事武力所针对的对象却有可能是这种船舶。[10]针对这些具有主权地位的船舶的活动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执法活动。[11]第四,即使在领海,大多数学者建议沿海国采取合法步骤要求外国军舰离开领海而不包括使用武力。[12]实际上,各国对在其领海内非无害通过的外国军舰使用武力相当谨慎。[12]UNCLOS第30条也没有明确赋予沿海国使用武力手段迫使不再享有无害通过权的外国军舰离开领海的权利。[13]457-458而在领海以外海域及其空域对外国军舰或军用飞机使用武力,极有可能构成使用武力而造成国际武装冲突。[13]459
(3)即使执法活动也可以升级为武装冲突。如本案高法官所言,“最初的执法活动可能因某种原因最终升级为军事局势。刻赤海峡事件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6)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Gao, para.49.。虽然事件发生当天的情况如法庭所述是“航行权”之争而俄方相关行为的性质可能是执法活动,但当乌方舰船准备突破封锁离开时,俄方舰机的拦截、追击、开火、逮捕、扣押乌舰船的行为使该事件升级为武装冲突。
(4)评估争端的性质应考虑相关国家的立场。乌克兰的一系列声明均将该事件定性为“军事活动”。根据“禁反言原则”,其不能在提起仲裁后又反悔不承认该事件的性质。有西方学者对法庭提出质疑:“不幸的是,海洋法法庭几乎没有触及该案提出的进一步问题。例如在乌克兰反复宣布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援引其自卫权利甚至暂时宣布戒严后是否会被禁止反言?”[5]
(5)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有关条约解释的规则,“关于军事活动”应是包括但不限于“军事活动本身”。国际法院曾在1978年“爱琴海大陆架案”(17)Aegean Sea Continental Shelf, Judgment, I.C.J. Reports 1978, para.86, p.36.、国际海洋法法庭曾在2013年“路易莎”号案的判决中对“关于”做出了类似阐释。(18)ITLOS, The M/V “Louisa” Case Judgment, No. 18, 2013, para.83, p31.有学者认为应对UNCLOS第298.1(b)条规定的“军事活动”进行广义解释,指出:“人们普遍认为,考虑到军事活动的高度政治性,必须对这个词作广泛的解释。”[14]然而本案法庭“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军事冲突以及克里米亚被吞并的更广泛背景”[15],“急剧提高了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1)(b)条豁免条款的要求”[5]。正如本案高法官所言:“军事活动例外的高门槛可作为一种‘变相激励’,促使各国通过部署大量海军舰艇和增加兵力,使冲突升级,而不是缓和冲突,以便符合强制解决争端管辖权的军事活动例外的情形。”(19)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Gao, para.45-46.
(二)本案交换意见义务履行问题
1.交换意见义务的界定及法律地位
(1)争端各方的首要义务应该是尽一切努力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16]33交换意见的主要任务是让争端缔约国就争议本身、解决争端的方式以及在可能情况下从实质性角度解决争端发表意见,从而促进争端解决制度的正确运作。[17]244交换意见是将争端提交法庭(以及诉诸UNCLOS第十五部分其他和平方法)的必要条件,[17]245也是争端方申请法庭规定临时措施的先决条件。[18]
(2)本条规定的义务并不限于在争议开始时的初步意见交换,它是在争议的每个阶段都适用的持续义务。[19]包括三个阶段的持续义务:在争端产生时应迅速就争端解决方式交换意见;解决这种争端的程序已经终止,而争端仍未得到解决时,争端各方也应迅速着手交换意见;已达成解决办法,而情况要求就解决办法的实施方式进行协商时,争端各方也应迅速着手交换意见。这实际上要求争端当事方在就争端解决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前都应先交换意见。[20]
(3)交换意见义务的履行应秉承“善意”。UNCLOS第283条在谈判文本中有“善意”的表述,后来考虑到一般性条款第300条的规定而删除了该表述。[21]在“查戈斯海洋保护区案”中,仲裁庭认为第283条的目的是确保一个国家不被强制程序启动“意外袭击”。(20)Chagos Marine Protected Area arbitration (Mauritius v. United Kingdom), Award of 18 March 2015, para 382.第283条的规定确保争端各方经过适当磋商后,才能将争端从一种解决方式转移到另一种方式,特别是有约束力裁判的解决方式。[19]
(4)交换意见的履行标准。在有关UNCLOS第283条的成例中,被告方经常以对方没有履行交换意见义务作为反对裁判机构管辖权的理由之一。而裁判机构常就达成解决争端方法的合意的可能性是否“用尽”来判断交换意见的义务是否履行完毕。如1999年“南方蓝鳍金枪鱼案”、(21)Southem Bluefin Tuna (New Zealand v. Japan; Australia v. Japan),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27 August 1999, ITLOS Reports 1999, para.60, p.295.2001年“爱尔兰诉英国混氧燃料工厂案”、(22)MOX Plant (Ireland v. United Kingdom),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3 December 2001, ITLOS Reports 2001, para.60, p.107.2003年“马来西亚诉新加坡柔佛海峡案”、(23)Case Concerning Land Reclamation by Singapore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s of Johor (Malaysia V. Singapore) List of cases: No.12, Order of 8 October 2003, para.48.2012年“自由”号案、(24)“ARA Libertad” (Argentina v. Ghana),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15 December 2012, ITLOS Reports 2012, Para.70-72, p.345.2019年“圣帕德雷·皮奥”号案。(25)The M/T “San Padre Pio” Case, (Switzerland V. Nigeria),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6 July 2019, para.72, p.20.
2.本案交换意见义务尚未履行完毕
(1)乌方要求俄方立即对解决争端的适当办法发表意见,并在10天内就此事与乌方进行磋商;俄方在第10日回复了乌方,并表示对乌方照会中提出的问题的可能的评论预计将单独发送。这清楚表明了双方就争端解决方式达成合意的可能性尚存在。在此情况下,法庭断言“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经用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2)如前所述,交换意见是持续义务,乌克兰规定10天期限不符合“持续性”要求;根据UNCLOS第283.2条的规则,即使乌方断定进一步寻求谈判的努力不会取得成果而决定提起强制程序,也应与俄方先行交换意见。
(3)乌方没有遵循善意原则。乌方一次照会后即直接转向强制程序构成对俄罗斯的“突袭”,可见其并非诚心与俄方通过交换意见寻求解决争端的方式,而是假意履行义务,绕过提起强制程序的前置条件。
三、本案指示临时措施的合理性问题及其后续发展
(一)本案指示临时措施的合理性问题
1.乌克兰的相关航行权问题
(1)有学者认为,亚速海和刻赤海峡水域的法律地位有两种可能的情形:第一种情况即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曾宣称的共同内水;第二种情况是亚速海和刻赤海峡受一般国际海洋法的规制。在第一种情况下,乌克兰可以援引习惯通行权;在第二种情况下,乌克兰可以援引UNCLOS第38条的过境通行权(若亚速海存在专属经济区)或第45.2条“不应予以停止”的无害通过权(若亚速海都是领海)。且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乌克兰均可援引2003年《俄乌两国关于使用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合作协定》主张其通行权。[22]也就是说,无论现在克里米亚的领土主权归属以及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权益归属如何,乌方都拥有在亚速海与刻赤海峡的航行权。
(2)基于乌方在亚速海与刻赤海峡的航行权,当然享有从必经海域即俄罗斯所称领海的通过权,而俄方无权阻截。俄罗斯关于通过海峡需要提前提交申请等要求损及乌方的航行权,俄方所称乌方舰船非法进入其领海的说法不成立,其采用的一系列阻截行为违反一般国际法或双方之间的条约。虽然UNCLOS第25.3条规定沿海国可在其领海的特定区域内暂停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但俄方不符合这样的条件:为保护国家安全包括武器演习在内而有必要;在形式上或事实上不加歧视;仅应在正式公布后发生效力。俄方给出的理由是“最近一次风暴之后,导致该地区的船只数量增多(超过150艘),其中包括许多有危险货物的船只”,(26)Memorandum, para.12.此理由并不符合上述条件要求。实践中,此类暂停通过主要是为举行军事演习,而俄方没有正式公布,只是发现乌方舰船后“告知”乌方。
2.本案法庭指示临时措施的合理性问题
虽然乌方诉诸国际强制程序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法庭基于敦促俄方释放乌方舰船及军人等考虑指示了临时措施,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本案在法律上存在诸多疑问。
(1)在管辖权方面,正如前文所述,法庭通过扩大关于UNCLOS解释或适用的争端、提高“军事活动例外”的要求、降低诉前义务履行的标准、降低指示临时措施的条件等做法,延续了法庭扩张其管辖权的趋势。
(2)法庭不应该指示临时措施。如前分析,在乌方军舰准备离开时而被俄方海岸警卫队追击、开火、扣押等行为构成武装冲突,在此情况下应适用海战法。有学者指出:“俄罗斯所采取的行动适用各种法律,如战时法、和平时期海洋法和武装冲突法。”[23]“如果法庭适用后者,海战法作为特别法就会取代军舰豁免的概念,而结果就会完全不同。”[5]“在本案中,海战法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海战法,俄罗斯使用武力的行为合法。”[12]根据海战法规则,俄罗斯享有捕获乌方舰船及其军人的权利,因此法庭不应根据海洋法要求俄方释放乌方舰船及其军人。
(二)本案的后续发展及反思
在法庭对本案做出裁决后,俄方并未释放乌方舰船及其军人。而7月25日乌方扣留了一艘俄油船,理由是该船2018年在刻赤海峡事件中参与封锁乌克兰军舰。随后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方正在查明该船被扣留的情况,以便“采取适当措施”。[24]可见,虽然乌方在本案中得到法庭的支持,但争端并未得到解决。从法律上说,与乌方没有秉承善意与俄方就争端解决或解决方式进行谈判、交换意见不无关系。
西方学者指出,通过外交渠道或谈判解决冲突很可能被视为更好的争端解决方式。[16]32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与主权的相关争端尤其如此。领土争端案件的复杂性与敏感性、国际法院裁判的方式及依据都使国际法院在国家领土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大打折扣。[25]各国不愿意放弃对解决争端的外交和政治选择的控制。[26]因此,UNCLOS将谈判列在和平解决争端方式的首位,这也是对普遍性国际争端解决实践的总结和首肯。
四、对中国的启示
(一)提高警惕并加强研究
我国与8个海上邻国存在不同程度的海洋争端,我国海权面临美日等国的挑战。本案对于我国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
虽然本案乌克兰将争端诉诸国际裁判机构体现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积极一面,然而本案法庭确立管辖权的一系列做法则有失偏颇。在海洋事务上,西方大国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均占据着主导地位。学者姜世波通过对国际法院的裁判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国际法院的司法政策与国际关系的格局、国际政治形势、法官的背景和偏见等非法律因素有着密切关系。[27]
我国的基本立场是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因此我国应加强对谈判与强制程序的关系研究。如有学者指出,谈判与强制程序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取代性法律关系与累积性法律关系。在两种法律关系中,谈判对法庭管辖权的影响不同:一旦取代性法律关系得以证成,那么法庭将自始不具有管辖权;而在累积性法律关系中,谈判的履行则是法庭行使管辖权的前提要件。[28]
尽管我国不接受国际强制程序解决相关海洋争端,但现实中由于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扩张其管辖权的趋势,我国难免被诉如“南海仲裁案”的例子,因此应加强对UNCLOS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要充分构建“防御机制”,如递进研究关于UNCLOS解释或适用的争端→适用强制程序的除外、限制、例外→提交强制程序的诉前义务的履行,充分维护本国合法权益。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相关海洋争端的性质
1.中国与周边国家相关海洋争议
随着中国海警加强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维权,日本海警船不断对中国海警船进行骚扰、干扰,双方多次进行对峙甚至碰撞。对此,有英国学者曾建议日本就东海问题起诉中国。[29]再如2014年“981”钻井平台事件中,越南方面即出动包括武装船只在内的大批船只,冲撞在现场执行护航安全保卫任务的中国政府公务船超千次,还向该海域派出“蛙人”等水下特工,大量布放渔网、漂浮物等障碍物。[30]越南方面报道称,中国出动军舰、海警执法船等与越方海警船对峙、撞击,并发射水炮等。[31]而近期中国海洋地质八号调查船在万安滩进行勘探作业时遭到越南的阻挠,随后双方多艘海警船发生对峙。[32]
2.中国与周边国家相关“军事活动”的争端
UNCLOS和相关司法及仲裁实践未对“军事活动”进行界定。一般而言,“军事”是指属于或关于士兵、武器或战争的,属于或关于武装部队的,由武装部队进行或制造的,军队的或与军队有关的。[33]而军事活动则应是由上述主体从事的有关活动或者与上述主体有关的活动。虽然国家实践中存在海军执法情况,但根据其目的依然可以区分二者。海上军事行动直接甚至是全部目的在于实现政治军事目的,涉及的是国防和国家安全,解决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保卫国家领土、抵御外来侵略等;后者则纯粹是为了维护法律制度和日常社会秩序。没有国防军事目的,是非军事性质的执法活动,比如在公海依国际法打击海盗或贩毒,在近海协助海警、海事等国家行政执法机关进行海上执法等。而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东海大陆架争端,以执法名义进行的各种活动,明显是出于维护岛屿和海域主权的目的,因此名为执法,实为军事性活动。[34]由此,无论是“981”钻井平台事件还是万安滩对峙,中越双方海警船等海上武装力量进行对峙甚至互相撞击的本质目的是捍卫各方所主张的主权、海洋权益和安全,而不是执行海上监管制度,属于政治军事目的,涉及的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前述争端符合UNCLOS第298.1(b)条规定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