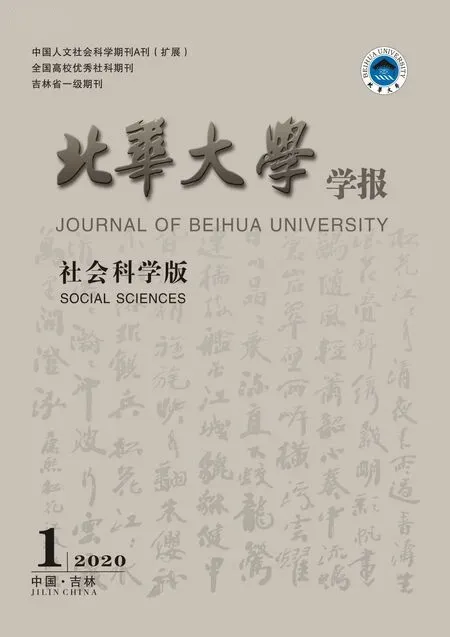唐诗中的一种特殊七言句式
2020-12-12冯广艺何婷婷
冯广艺 何婷婷
引 言
唐诗中有一种特殊七言句式。这一句式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比较复杂,有的是主谓短语,其中一定含宾语,有的是非主谓短语,为谓词性短语,也一定含宾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动宾结构为核心的偏正短语,一种是两个动宾短语连用,与我们讨论的问题相关的是后一动宾短语);后一部分是主谓短语,可带宾语,也可不带宾语。前一部分中的宾语(承前所述,有时这部分有两个宾语,这里仅指处七言第四言位置上的宾语)和后一部分的主语(处七言第五言)形、义相同,且一般为名词性的,形成短语系联的组构格式,如“昨夜看花花灼灼,今朝看花花欲落”(鲍君徽《惜花吟》)。其中“昨夜看花花灼灼”的前一部分是非主谓短语“昨夜看花”,后一部分为主谓短语“花灼灼”,两个“花”(前宾后主,都是名词)形、义相同;同样,“今朝看花花欲落”的前一部分是非主谓短语“今朝看花”,后一部分是主谓短语“花欲落”,两个“花”亦形、义相同,且都是名词。又如“把酒承花花落频,花香酒味相和春”(白居易《座上赠卢判官》)。“把酒承花花落频”句的前一部分“把酒承花”是一个由两个动宾短语构成的复杂短语,非主谓短语,后一部分“花落频”是主谓短语,第四言之“花”(宾语)与第五言之“花”(主语)形、义相同,亦均为名词。
唐诗中这一句式较为常见,且效果很好,值得深入研究。通过文献检索与梳理,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有人对此句式进行过相关研究,本文就此加以探讨。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唐诗中有一些与我们所说的这一句式貌似的诗句,如:“食之不饫饫不尽,使人不陋复不愚”,“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皇甫湜《出世篇》)。“食之不饫饫不尽”和“外人不见见应笑”虽与我们讨论的句式句面相近,但句里大为不同,其中的“饫”(饱)是形容词,“见”是动词,它们都不是名词,且在短语中充当的成分也不是宾语,因而不符合我们对这一句式的界定,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下面对这一句式进行详细分析。
一、形式特征
从组构方式看,这一句式由两部分构成,且两个部分具有一定的逻辑关联。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将前一部分标记为S1,后一部分标记为S2,那么这一句式的基本格式就是S1+ S2,如“主人忆尔尔知否,抛却青云归白云”(白居易《题崔常侍济上别墅》)中“主人忆尔尔知否”的S1是“主人忆尔”,S2是“尔知否”,“尔”在S1中是宾语,在S2中是主语,我们称之为同现项,标记为L。L在这一句式中同现,且形、义相同,均为名词性的词,只是在两个部分中充当不同的成分,具有不同的句法功能,因而在这一句式中L是非常重要的。再举几例:
(1)况妾事姑姑进止,身去门前同万里。(元稹《忆远曲》)
(2)万姓攀髯髯堕地,啼呼弓剑飘寒水。(陈陶《飞龙引》)
(3)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刘禹锡《望夫石》)
例(1)“况妾事姑姑进止”中,S1是“况妾事姑”,S2是“姑进止”,同现项L是“姑”,“姑”在S1中是宾语,在S2中是主语。例(2)“万姓攀髯髯堕地”中,S1是“万姓攀髯”,S2是“髯堕地”,同现项L是“髯”,“髯”在S1中是宾语,在S2中是主语。例(3)“终日望夫夫不归”中,S1是“终日望夫”,S2是“夫不归”,同现项L是“夫”,“夫”在S1中是宾语,在S2中是主语。“姑”“髯”“夫”都是名词。
(一)关于S1
从句法结构上看,S1中的谓语和宾语一定是显性的,其中宾语在S2中充任主语。例如:
(1)楚公画鹰鹰戴角,杀气森森到幽朔。(杜甫《姜楚公画角鹰歌》)
(2)夜光投人人不畏,知君独识精灵器。(韦应物《寇季膺古刀歌》)
(3)日暮待君君不见,长风吹雨过青溪。(张万顷《东溪待苏户曹不至》)
(4)持此赠君君饮之,圣君识君冰玉姿。(卢纶《陈翃郎中北亭送侯钊侍御》)
例(1)“楚公画鹰鹰戴角”中 ,S1是“楚公画鹰”,主谓短语。其主语是“楚公”,谓语是“画”,宾语是“鹰”,主、谓、宾都出现。例(2)“夜光投人人不畏”中 ,S1是“夜光投人”,主谓短语,其主语是“夜光”,谓语是“投”,宾语是“人”,主、谓、宾同时出现。例(3)“日暮待君君不见”中, S1“日暮待君”,是谓词性非主谓短语,谓语是“待”,宾语是“君”。例(4)“持此赠君君饮之”的 S1“持此赠君”是谓词性非主谓短语,两组动宾短语连用,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后一动宾短语的谓语是“赠”,宾语是“君”。以上4例中,例(1)和例(2)中S1是主谓短语,例(3)和例(4)中S1是非主谓短语,句法结构有别。例(3)“日暮待君”是状语“日暮”和动宾短语“待君”构成的谓词性偏正短语。例(4)“持此赠君”是两个动宾短语“持此”和“赠君”连用,二者都是谓词性短语,但结构有所不同。总之,无论S1结构多复杂,处于七言诗句第三言和第四言位置上的语言单位一定是动、宾关系。
(二)关于S2
S2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主谓短语中带宾语,二是主谓短语中不含宾语。例如:
(1)夫戍萧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王驾《古意》)
(2)歌舞留春春似海,美人颜色正如花。(唐彦谦《春日偶成》)
(3)司空爱尔尔须知,不信听吟送鹤诗。(白居易《送鹤与裴相临别赠诗》)
(4)镜水绕山山尽白,琉璃云母世间无。(元稹《酬乐天雪中见寄》)
例(1)“西风吹妾妾忧夫”中,S2“妾忧夫”是主谓短语,带宾语“夫”。例(2)“歌舞留春春似海”中,S2“春似海”是主谓短语,带宾语“海”。例(3)“司空爱尔尔须知”中,S2“尔须知”是主谓短语,不带宾语。例(4)“镜水绕山山尽白”中,S2“山尽白”是主谓短语,也不带宾语。
(三)关于L
L处于七言诗第四言和第五言位置,同形同义,但成分不同。前者在前面的短语S1中充任宾语,后者在后面短语S2中充任主语。它们位置紧邻,是组构这一句式的连接点,关键要素。例如:
(1)莫言炙手手可热,须臾火尽灰亦灭。(崔颢《长安道》)
(2)故乡不归谁共穴,石上作蒲蒲九节。(张祜《琴曲歌辞·思归引》)
(3)身情长在暗相随,生魄随君君岂知。(韩偓《惆怅》)
(4)旁人见环环可怜,不知中有长恨端。(韦应物《杂曲歌辞·行路难》)
例(1)“莫言炙手手可热”中,S1“莫言炙手”中的宾语“手”和S2“手可热”中的主语“手”同形同义,二者比邻而置。例(2)“石上作蒲蒲九节”中S1和S2中的两个“蒲”,例(3)“生魄随君君岂知”中S1和S2中的两个“君”,例(4)“旁人见环环可怜”中S1和S2中的两个“环”,都和例(1)中两个“手”的性质和作用一样。因而我们可以说,这一句式中处于第四言和第五言位置上的同形同义的两个词是组构句式的连接点,也是这一句式的重要形式特征。
二、语义关系特征
从结构上看,唐诗中的这种特殊七言句式,其前后两个构成部分因相同词语的关联而关系紧密,在语义上,二者之间的语义关系因这种结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前后语义具有结果、顺承、因果、偏转、循环和转折等丰富的语义关系。
(一)结果关系
结果语义关系类型的七言唐诗之语义特征是:这一句式的后一部分在语义上表达的是前一部分的结果。也可以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进一步表述,所以也可以称之为递进关系。例如:
(1)龙池跃龙龙已飞,龙德先天无不违。(沈佺期《龙池篇》)
(2)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李贺《湖城东遇孟云卿》)
(3)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白居易《捕蝗》)
(4)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杜甫《忆昔二首》)
例(1)的“龙池跃龙龙已飞”,前一部分“龙池跃龙”讲的是“龙”在“龙池”中腾跃的情形,后一部分“龙已飞”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叙说“龙飞腾起来了”。“飞”是“跃”的结果。例(2)的“黑云压城城欲摧”,前一部分“黑云压城”描写乌云笼罩着湖城,渲染恐怖的气氛,后一部分“城欲摧”则是进一步说“城墙都要被压塌,湖城要被摧毁了”,极言形势之严峻。“城欲摧”是“黑云压城”的结果。例(3)的“以政驱蝗蝗出境”,前一部分“以政驱蝗”说的是驱蝗的手段,后一部分“蝗出境”进一步指出这一手段带来的实际效果,也是结果。例(4)的“长驱东胡胡走藏”,前一部分“长驱东胡”写的是驱“胡”之事,后一部分“胡走藏”则进一步写“胡”被打得狼狈逃跑,四处躲藏的结果。
这一类语义关系,前面部分说的是事件或行为,后面部分讲的是这一事件或行为的结果,前面事件或行为涉及或针对的对象,是后面结果的行为主体,故前后语义内容便有了密切的关联性。
(二)顺承关系
顺承语义关系类型的七言唐诗之语义特征是:这一句式的前后两个部分在语义内容上是一种承接关系,即后一部分沿着前一部分的话题方向继续说下去。例如:
(1)楚岸有花花盖屋,金塘柳色前溪曲。(温庭筠《景色歌》)
(2)回首看花花欲尽,可怜寥落送春心。(高骈《池上送春》)
(3)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李商隐《韩碑》)
(4)今日示君君好信,教君见世作神仙。(吕岩《七言》)
例(1)的“楚岸有花花盖屋”,前一部分写“楚岸有花”,后一部分紧接着说花儿繁茂以“盖屋”。前后的话题都是“花”。例(2)的“回首看花花欲尽”,前一部分写“看花”行为,后一部分承上续写看到的情形——“花欲尽”。从看到看到的情形,话题方向未变,语义自然衔接。例(3)的“封狼生貙貙生罴”,前一部分说狼生了貙,后一部分说貙生了罴,前后语义的承接关系十分明了。同样,例(4)的“今日示均君好信”一句中“示君”与“君好信”也是同样的情形。
这一类语义关系,前后话题方向一致,表义集中,承接紧凑,连贯自然。
(三)因果关系
因果语义关系类型的七言唐诗之语义特征是:前后两个部分在语义上是因果关系,前一部分是“因”,后一部分是“果”。例如:
(2)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白居易《牡丹芳—美天子忧农也》)
(3)野花似泣江妆泪,寒露满枝枝不胜。(刘沧《秋日望西阳》)
(4)年年采珠珠避人,今年采珠由海神。(元稹《采珠行》)
(5)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白居易《琵琶行》)
例(1)的“此中多恨恨难平”,前一部分“此中多恨”是“因”,后一部分“恨难平”是“果”,表达的是“因恨多而难平”之意。例(2)的“恤下动天天降祥”,前一部分“恤下动天”意思是“天子体恤农桑感动上天”,后一部分“天降祥”意思是“上天给农桑降下吉祥”,整句意思:因天子体恤农桑感动上天,故上天给农桑降下吉祥,明显的因果关系。例(3)的“寒露满枝枝不胜”,前一部分“寒露满枝”说的是寒露太重,沾满枝条,后一部分“枝不胜”是说枝条不堪重负,难以承受。整句意思:因寒露太多太重而使树枝难以承受,极言秋日寒露之重。前因后果关系明显。例(4)的“年年采珠珠避人”,因人们年年采珠,所以,珍珠才争相避开人,明显前因后果。例(5)的“却坐促弦弦转急”,因“促弦”而“弦转急”,前因后果。
这一类语义关系,前因后果很明显,很好辨识和理解。
(四)偏移关系
偏移语义关系类型的七言唐诗之语义特征是:前后两个部分分别述说不同的语义内容,话题的核心内容发生改变。虽然结构形式没有变化,但因语义上发生了改变,因而我们称之为“语义偏移”。例如:
(1)天下有山山有水,养蒙肥遁正翛然。(陆希声《阳羡杂咏十九首》)
此外,该产品还配备了智能型高端电控系统,采用触摸式按键、高亮彩色液晶屏等智能装置。值得一提的是,找平油缸集成配有位置传感器,可实时显示找平标尺高度,并有效防止异常操作导致的大臂变形,找平、行走、振捣、输分料系统等智能一体化控制,同时,电加热系统具备自动加热、低速加热及过热保护等功能,以提升工作稳定性,保证更高的作业质量。
(2)水隔孤城城隔山,水边时望忆师闲。(齐已《宜春江上寄仰山长老二首》)
(3)西山为水水为尘,不是人间离别人。(顾况《古离别》)
例(1)的“天下有山山有水”,前一部分“天下有山”说的是“山”,后一部分“山有水”,说的是“水”,语义内容上不是续讲同一事物,而是话题一转而言他。但是,前后语义也还是有关联的,L项“山”仍是纽带,“水”是此“山”之水,而非他山或平原之水。另,“天下”—“山”—“水”,叙述对象语义范围逐渐缩小,内含递次包容关系。例(2)的“水隔孤城城隔山”,前一部分说的是“水隔城”,后一部分说的是“城隔山”,分开看是两个孤立的现象,语义内容有别。但由于“隔山”之“城”即“水隔”之“城”,前后语义就有了联系。关涉对象“水”“城”“山”与上例的“天下”“山”“水”相比,结构形式上一致,都是A—B(B)—C式,但是,语义上,“天下”“山”“水”是意义范围逐层递减,而“水”“城”“山”之间是平行关系。例(3)的“西山为水水为尘”,前一部分说的是“山为水”,后一部分说的是“水为尘”,孤立看是说两个事,前后语义发生偏转。但前后两个“水”所指相同,故前后语义有关联。与例2一样,关涉对象“山”“水”“尘”之间也是平行关系。
这一语义关系,语义内容上后一部分不是顺着前一话题说下去,而是话题一转而言他;前后两部分看似各言其事,但实则关系密切;所涉对象皆为定指;各对象之间的语义关系要么是递进包容关系,要么是平行关系。
(五)循环关系
循环语义关系类型的七言唐诗之语义特征是,前一部分语义指向是从A到B,后一部分的语义指向是从B到A,构成富有回环意味的独特表达。例如:
(1)乃知凡俗难可名,轻者可重重者轻。(赵抟《琴歌》)
(2)我语杨琼琼莫语,汝虽笑我我笑汝。(元稹《和乐天示杨琼》)
(3)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白居易《谈禅经》)
例(1)的“轻者可重重者轻”,前面说轻者可重,后面讲重者可轻;例(2)的“汝虽笑我我笑汝”,前部分说的是你笑我,后部分说的是我笑你;例(3)“摄动是禅禅是动”,这句从字面看,前部分是说静(摄动)是禅,后部分说的是禅是动,意义正好相反,但从禅学角度来看,静即动,动亦静,所以摄动与动都是禅;另,从物理学角度,动与静是相对的,摄动也是动,这样就构成了语义的回环,可视为循环关系。
这一语义关系,所涉对象只有两个。语义上是按“A—B(B)—A”的轨迹行进的,是闭合的、循环式的表达,多为强调一种事理。
(六)折转关系
循环语义关系类型的七言唐诗之语义特征是:后一部分不是顺着前一部分所言之行为或事件“正常”或“按理应该”的方向说下去,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或结果叙说下去,形成了前后语义的转折。例如:
(1)尔巫女觋更走魂,焚香祝天天不闻。(齐已《夏云曲》)
(2)谁到迎仙仙不至,今朝还有谢公来。(贯休《陪冯使君游六首》)
(3)渡江明月好携手,独自待郎郎不归。(黄陵美人《寄紫盖阳居士》)
(4)醒了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杜牧《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5)秦淮有水水无情,还向金陵漾春色。(温庭筠《春江花月夜词》)
(6)惟有寄书书未得,卧闻雁燕向南飞。(许浑《卧病》)
例(1)的“焚香祝天天不闻”,按理说,焚香祝天,天应知晓,可结果是“天不闻”,事情没有按照常理而是朝着“不料”“不想”方向去发展,构成语义的转折。例(2)的“谁到迎仙仙不至”,说的是虔诚、恭敬地大礼“迎仙”,可是神仙竟没来,同样,本应如此却没如此,构成语义转折。例(3)的“独自待郎郎不归”,前部分,苦苦在等待郎君回,后部分,可是郎君一直不回还,构成语义转折。例(4)的“对酒当歌歌不成”,本该对酒当歌”,可是却“歌不成”。前后语义转折。例(6)的“秦淮有水水无情”,常言“温情如水”,水有情,可是秦淮的水却是无情。又一破常理之象,语义反转。例(7)的“惟有寄书书未得”,该诗写的是,想寄家书以缓解思乡之情,可是却无法实现(难以送达),只好把相思托于南非的大雁。想“寄书”而“未得”,前后语义转折,表达了深深的遗憾之情。
这一语义关系,一般而言,后部分表达的意思与前一部分表达的意思是对立的,原本按常理、本应、意料之中该发生的事、该达成的意愿,结果却出现了破常理、不应该、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形。后一部分中常常带“不”“无”“未”等否定词,以凸显这种转折、对立的意味。
上述这6种语义类型,前3种,前后两部分话语走向是一致的,语义前后基本是相承关系;后3种,后一部分不是全部分所述事物、行为、现象等的延展或因果照应,没有顺着前部分的意思说下去,语义指向发生了偏转或逆转,尤其是循环关系类型的句式,更是构成了回环。故这种七言诗能够表达出丰富的意蕴和修辞色彩。
三、语用价值
邢福义先生指出:“语值有时是修辞值,特定格式有其特定的修辞效果;有时是语境值,不同句式有适应不同语境的价值。‘小三角’的语用价值,重视在比较中考察研究对象的语用效应,回答它到底有何价值的问题。”[1]我们所讨论的唐诗中的这一句式,特点突出,句式严整,语用价值鲜明。
(一)模仿运用
唐代很多优秀诗人喜欢运用这一七言句式,且形成了一种相互仿用的风气,诚如杨慎所言“唐人不厌同”[2]。例如:
(1)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李白《将进酒》)
(2)将刀斫水水复连,挥刃割情情不断。(戴叔伦《相思曲》)
(3)持杯收水水已覆,徙薪避火火更燔。(李益《汉宫少年行》)
以上3组例子都是两句连用这一句式,且表达方式都是相同的,是一种模仿语用现象,当然到底谁模仿谁,也只有从谁先用、谁后用上判断了,这里我们不做首创者考证。这一句式中的很多表达构式都有这种情况,如“今日凭君君莫辞”(卢纶《偶逢姚校书凭附书达河南郄推官因以戏赠》)和“年年奉君君莫弃”(王建《白歌二首》),下文中的“近日问花花不语”“百舌问花花不语”等都有模仿运用的痕迹。
不仅唐朝诗人善用此句式,其后的文人也多用这一句式,例子很多,如:
(1)执酒劝君君尽之,今朝取醉不当疑。(北宋司马光《执酒》)
(2)作书寄君君莫笑,但觅来禽与青李。(北宋苏轼《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
(3)以此寿君君必寿,年年新月照杯盘。(南宋叶茵《寿水竹弟》)
(4)一事避君君匿笑,刘郎才气亦求田。(清龚自珍《己亥杂诗》)
这里仅仅举L项为“君”的诸多例句中的几例。诸多例子中,北宋、南宋诗人用者居多,苏洵、苏轼等大家诗中常见此句式。甚至清代一种特定句式,如果大家都乐于仿用,说明这一句式具有一定的语用效应。
(二)辞格巧用
这一句式在运用中往往融入了辞格,有的还是多个辞格套用,因而该句式具有很强的修辞功能。例如:
(1)郎心似月月未却,十五十六清光圆。(温庭筠《张静婉采莲歌》)
(2)岳北秋空漏春风,晴云渐薄薄如烟。(司空图《携仙箓九首》)
(3)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赵嘏《江楼旧感》)
(4)数日相随两不忘,郎心如妾妾如郎。(无名氏《杂诗》)
(5)近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严恽《落花》)
(6)百舌问花花不语,低头似恨横塘雨。(温庭筠《惜春词》)
(7)仰面诉天天不闻,低头告地地不言。(戎昱《苦辛行》)
例(1)的“郎心似月月未却”和例(2)的“晴云渐薄薄如烟”都运用了比喻辞格。例(3)“月光如水水如天”中连续运用了两个比喻辞格。例(4)“郎心如妾妾如郎”中不仅连续运用了两个比喻,还兼用了回环辞格。例(5)“近日问花花不语”和例(6)“百舌问花花不语”都运用了拟人辞格,例(7)“仰面诉天天不闻”和“低头告地地不言”运用了拟人辞格,二者也构成了对偶辞格。
(三)结对运用
诗的上句和下句中都使用这一句式,形成对偶,使诗歌语言均衡匀称,富有表现力。例如:
(1)赤血沾君君不知,白骨辞君君不见。(刘希夷《伯三六一九》)
(2)君寄边书书莫绝,妾答同心心自结。(长孙佐辅《答边信》)
(3)望日蚀月月光灭,朔月掩日日光缺。(卢仝《月蚀诗》)
(4)此时望君君不来,此时思君君不顾。(郎大家宋氏《琴曲歌辞·宛转歌》)
(5)白首思归归不得,空山闻雁雁声哀。(郎士元《郢城秋望》)
(6)东海钓鳌鳌不食,南山坐石石欲烂。(皎然《寓言》)
(7)白露凋花花不残,凉风吹叶叶初干。(白居易《衰荷》)
上面的例子都是同一句式在上下句中运用,表义充分,语句对仗整齐,使诗歌语言具有均衡美。
(四)集结运用
即在诗句中集中运用这一句式,形成整体一致、表义凝练的排比形式。例如:
(1)我欲升天天隔霄,我欲渡水水无桥。
我欲上山山路险,我欲汲井井泉遥。
越人翠被今何夕,独立沙边江草碧。
紫燕西飞欲寄书,白云何处逢来客。
——顾况《悲歌二》
顾况的《悲歌二》中有四句用了这个句式,这种现象很少见。这四句同一句式的排比运用,集中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身处窘境的悲愤苦闷之情。
(五)景物描写
前后两个部分描绘景物,犹如两幅美丽的山水画组合在一起,景中有情。例如:
(1)夜深宫殿门不锁,白露满山山叶堕。(王建《乌栖曲》)
(2)危楼压溪溪澹碧,翠袅江飘莺寂寂。(吴融《赠李长史歌》)
(3)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白居易《上阳白发人》)
(4)北风吹霜霜月明,荷叶枯尽越水清。(杨衡《寄彻公》)
例(1)“白露满山山叶堕”描写秋天的夜晚,山上白露茫茫,树叶纷纷落下的景象。例(2)“危楼压溪溪澹碧”描绘高楼耸立溪边,溪水清澈透亮的画面。例(3)“青黛点眉眉细长”刻画女子精心化妆、点缀细眉的情景。例(4)“北风吹霜霜月明”描述秋夜北风劲吹、霜白月明的景色。可以看出,运用这一句式描写景物,使各句中前后两部分所描绘的画面自然而然地交融在一起,互相衬托,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表达效果。
(六)祈使规劝
这一句式的后一短语主谓间用“莫”“应”等,形成祈使语气,表达主观情感,具有“规劝”的修辞效果。例如:
(1)寄书常切到常迟,今日凭君君莫辞。(卢纶《偶逢姚校书凭附书达河南》)
(2)回昼为宵亦不寐,年年奉君君莫弃。(王建《舞曲歌辞·白纻歌二首》)
(3)不见君,心相忆,此心向君君应识。(王维《新秦郡松树歌》)
例(1)“今日凭君君莫辞”和例(2)“年年奉君君莫弃”的后一部分都用了“莫”,表达的是规劝或希望“君”不要如何如何。例(3)“此心向君君应识”的后一部分用“应”表达的是规劝或希望“君”应该如何如何,语用倾向十分鲜明。
总之,从唐代诗人乐于仿用这一句式、在句式中巧用多种辞格、组构均衡匀称的表达格式、描绘客观景物、表达主观情感等方面看,唐诗中的这种七言句式,具有独特的语用效应。
余 论
从浩繁的唐诗中选取具有一定形式特征的诗句做深入探讨,并发现其中的语法和语用修辞规律,是一种尝试。本文探讨的唐诗中的特殊七言句式,形式特征鲜明,语义内涵丰富,语用效应和价值凸显。我们主张有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多角度地研究语言现象,从语言现象中发现语言运用规律。邢福义先生提出语法研究的“小三角”理论,不就是融合了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修辞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吗?[3]从汉语修辞史的角度看,修辞学界对修辞史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让人满意的程度。[4]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是积极梳理汉语史中的修辞史实,挖掘其语用规律,厘清汉语修辞发展史的基本脉络。[5-6]汉语修辞发展史宛如一条大河,探究唐诗中特殊七言句式的语用修辞问题,只是从这条大河里舀取了“一滴水”,试图通过这“一滴水”窥测这条大河滔滔流动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