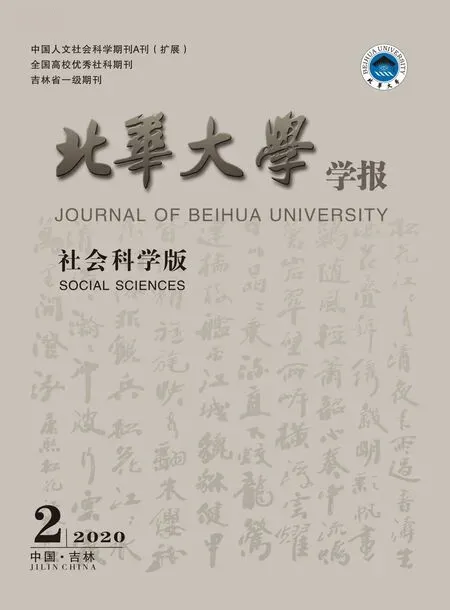战后日本的战争记忆与历史认识
——以体验与记忆的教化为中心
2020-12-12李圭洙廉松心
李圭洙 著 廉松心 译
前言——所谓记忆战争
在历史学界,记忆过去与特定事件的倾向性比较强。这可能是缘于重新阐释现代社会成员的体验与记忆中重要事件的背景、过程及其历史意义,进而展望未来可“共生”社会的问题意识。这是历史学界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作为不断追求社会变革的人文学本然的姿态。未来的历史学也将以必须记忆的、不可忘却的事件为媒介,重新阐释历史。(1)如东学党农民革命120周年、日俄战争100周年、战后70周年、日本强占韩国100周年、韩日会谈50周年、明治150周年、俄罗斯革命100周年、3·1运动100周年等各种形式的学术大会及“重读历史”活动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以日本为中心进行的日俄战争100周年纪念活动是战争记忆以“纪念”形式发挥作用的典型事例。虽然没有举行国家层面的纪念活动,但日本右翼将日俄战争视为20世纪初日本“克服”“国难”的重大事件。他们只是把日俄战争视为“克服”当时国际关系危机的最好事例,没有以他者的立场考察日俄战争真相。参看:朴晋翰《日本的战争纪念馆与国家主义——日俄战争100周年回顾》,首尔:《历史教育》98,2006年;都珍淳《超越世纪忘却——以日俄战争100周年纪念活动为中心》,首尔:《历史批评》77,2006年。
战争记忆与历史认识问题是历史学界共同的话题。为了总结被称为“战争世纪”的20世纪,必须探讨战争体验与记忆的关系问题。韩日间围绕历史、公民、教科书、“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形成的对立认识,也是由于对战争体验与记忆的不同立场和解释所导致。探讨战争体验与记忆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学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关于记忆的讨论是因对过去自己民族中心主义和“盲信”历史连续性的历史叙述提出质疑而登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所谓的传统,考察其起源,实际上是极其近期发生的事件,有时是发明的”[1],认为传统是因不同的记忆而形成的“文化构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所谓民族原来是被限制的,是具有主权的、想像的政治共同体”[2],认为民族是为政治和统治的正当化,人为“创造”的。根据霍布斯鲍姆、安德森等学者的主张,有意识的记忆是虚构,而不是传统,国家和民族是凭借“共同的记忆”而形成的政治集团。
关于认识问题,广义的认识是指人类知识的全部;狭义的认识是指对于一定范围对象的知识。但认识不只是停留在识别真伪的知识领域,而是深入于人类的无意识领域。根据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概念,认识介入于人类的无意识领域,与伦理态度、宗教信念、知识的总和即社会态度联系在一起。(2)米歇尔·福柯认为知识是指支配特定时代认识的无意识体系,或以特定的方式对事物赋予秩序的无意识基础。作为哲学用语的知识,是指实践知识和相对意义上的理论知识,或与基于感性的臆见(doxa)相对立的“真知识”。参看: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李光来译《词与物》,首尔:民音社,1986年;福柯著,李正雨译《知识考古学》,首尔:民音社,2000年。可以说历史认识是基于经验、记忆、知识的复杂多层面的关系而形成。例如,一个民族的形象与以个人的体验和记忆作为共同体验的方式密切相关。个人的经验通过历史知识记忆为集体经验,形成一个定型化的集体记忆,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体验被消除或变形。这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形成的。
民族间的相互认识是通过交流、外交关系等途径形成,这是决定未来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近代以后,经历过帝国与殖民地历史的韩日两国追求“共生”价值的时候,两国间相互认识的历史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力。考察韩日间围绕“战争与暴力”形成的历史体验和记忆这一相互认识的基础,无论对现在的两国关系还是对未来的两国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考察韩国和日本的历史体验、记忆及相互认识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的研究方法。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进行综合、深层次的分析,揭示消除矛盾关系的可能性。这种方式有助于矛盾关系普遍论特性的相对化。(3)与此相关,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记述了与人类的意志、自由、恶相关的事件和象征,提出了关于解释的多种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理论。根据他的主张,记忆是“被训练”的,违背了记忆的“真实性”,是对记忆的“滥用”。他进而把记忆的滥用类型分为“被妨害的记忆”“被捏造的记忆”“被强迫的记忆”,特别强调外部集团强加于自己所属集团的暴力性记忆,因特定力量的作用成为歪曲的记忆,有可能成为新暴力的根源。总之,记忆成为集体记忆存在,具有被特定统治权力选择、改造的可能性。参看:ポール·リクール著,久米博译《記憶·歴史·忘却(上)》,東京:新曜社,2004年。众所周知,韩日间围绕历史体验、记忆及认识问题发生的争论是由于近代以后加害者意识与受害者意识的差异所导致。但仅靠这些尚不足以充分理解韩日关系,因为在韩日间的历史体验与记忆中潜伏着仅靠现象的分析是难以说明的社会文化要素。特别是在近代以后的韩日关系中曾发生过“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合理关系,而且这种不对称关系被不断地再生产。这就是为重新构筑韩日关系,必须从多维视角考察历史体验和记忆差异的理由所在。
现在的东亚进入新的局面。韩日政府间以安倍晋三的未经东亚社会承认的单方面的“战后70年谈话”为中心,在“慰安妇”协议问题、撤除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像问题等围绕日本的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展开着争论。但所有问题都处于模糊状态,尚未找到能够形成“共识”的解决方法。特别是中韩围绕朝鲜半岛萨德问题发生的冲突、朝鲜核问题等国际社会面临新的冷战局面。因此围绕“战争与暴力”问题,更加凸显了记忆的重要性。
鉴于上述问题意识,下面拟考察日本是怎样记忆战争的,在日本的战争体验与记忆中如何反映中国、朝鲜、冲绳乃至女性和儿童的历史体验与记忆,战后历史学在战争体验向记忆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修正主义的抬头,日本对战争与死伤者的记忆如何发生变质的等问题,进而强调战争体验与记忆问题不仅要从战后日本社会脉络上去考察,还要通过包含东亚视角的相互认识的形态去重新确认。通过相互认识能够保证“体验与记忆”历史真实的客观性和效用性。
一、“战败”还是“终战”
1945年8月15日正午,裕仁天皇在日本通过广播发表了“终战诏书”。 这是裕仁第一次通过媒体向日本国民亲自发出的声音。“终战诏书”是在8月14日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后当天发表,裕仁的诏敕朗读是提前录制好的。众所周知,主张本土决战的日本顽固派和军人为了阻止此次广播,企图夺取录音带,但未能得逞。日本国民听到裕仁天皇的诏敕后才知道日本战败的事实。在天皇体制下,裕仁天皇亲自发表的广播讲话,最准确地传达了“终战”的事实,使日本国民真实地感觉到“没死,还活着”。
战争虽然结束,但在如何界定战争性质的问题上出现很大分歧。在裕仁朗读的诏敕中,没有“投降”“战败”“终战”等用语。诏敕的要旨是:面对强大的联合国武力,为了防止日本民族因遭受更严重的伤害而毁灭,裕仁天皇 “选择了和平”。日本国民是托裕仁天皇的福,获得了“和平”。日本战败后,以“终战”代替“战败”。“终战诏书”的意味在于是裕仁天皇为了日本民族的安危果断地选择了和平,这成为隐蔽日本战败事实的“隐藏的机制”发挥作用。以“终战”代替“战败”,反映了日本国家基本的历史认识。
战后,日本历史学界也强调了战争受害者意识。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开始,持续15年的所谓“十五年战争”是物质上、精神上对日本社会进行总动员的悲惨战争,是不分日本国内、殖民地、占领地,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前线和后方的战争。从1953—1954年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纂的《太平洋戰爭史》(4)歷史學硏究會编《太平洋戰爭史:全5冊》,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53—1954年。,1962—1963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纂的《太平洋戰爭への道》(5)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全7冊》,東京:朝日新聞社,1962—1963年。等书都着重记述了日本战败之前的、被隐蔽的战争实态。不能不指出,在这些与战争相关的研究中缺乏加害者意识。虽然其在承认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基础上阐明了战争真相,但把中国等亚洲国家仅仅视为战争舞台而已。虽然从反思战争的视角说明了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是谁,在侵略战争中谁动员了日本民众,为什么日本民众未能阻止战争等问题,但缺乏亚洲民众的视角,具有浓厚的日本人是受害者的历史认识。
日本历史认识的失衡现象,从历史用语中也能窥见。例如所谓“十五年战争”是从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连续性视角提出的。将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确切地说14年)持续15年的战争视为一场战争,将太平洋战争视为这场战争的第三阶段。这个用语是鹤见俊辅因考虑到“太平洋战争”名称忽略亚洲的立场而提出的。(6)鶴見俊輔《戦時期日本の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1982年。太平洋战争让人们只是联想到因日军偷袭珍珠港而爆发的美日之间的战争,而忘却因日本侵略中国而爆发此后战争的历史。太平洋战争并不是独立的、个别的事件,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近代以来发动的侵略亚洲战争的结果。要明确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以来侵略亚洲的战争责任,这是使用“15年战争”名称者的主要立场。这个名称具有能够补充完善太平洋战争“亚洲”视角的缺陷和大东亚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视角缺陷的意义。(7)这种视角的研究还有:黒羽清隆《十五年戰爭史序説》,東京:三省堂,1979年;江口圭一《十五年戰爭の開幕 (昭和の歴史4) 》,東京:小學館,1982年;江口圭一《十五年戰爭小史》,東京:青木書店,1986年;江口圭一《二つの大戰” (體系日本の歴史14) 》,東京:小學館 ,1989年;藤原彰《日中全面戰爭” (昭和の歴史5)》,東京:小學館,1982年;藤原彰、今井清一編《十五年戰爭史》(1-3),東京:青木書店,1988—1989年。
使用“十五年战争”名称的重要性在于强调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至太平洋战争的战争连续性,重视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事实。
在日本社会,到1960年后半期才出现作为加害者的历史认识。到这个时期,日军在中国战场犯下的罪行开始被暴露。1972年本多勝一的《中國の旅》(8)本多勝一《中國の旅》,東京:朝日新聞社,1972年。出版之后,开始谈论日本的战争犯罪,例如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使用化学武器、制贩鸦片、强掳朝鲜劳工等加害者的历史事实。不仅发现作为受害者的日本人,也发现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人。战争当事者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以各自的视角记忆战争。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关于士兵战争体验的回忆录被大量制作和出版,也开始关注总力战与女性的关系问题。如在《總後史ノート》(9)女たちの現在を問う會编《總後史ノート》,東京:JCA出版,1977—1985年。一书中,提出了日本女性在后方通过国防妇人会和大日本妇人会参与战争的事实,以及女性运动领导人物拥护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
东亚社会对“1945年8月15日”的视角以及对“终战”与“战败”的立场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知识阶层,甚至在一般国民当中也根深蒂固,那就是日本“虽然败给美国,但并没有败给亚洲”的历史认识。现在日本社会围绕韩日两国间的历史悬案出现的保守化现象,其根源也在于此。
二、双重受害者意识
日本社会埋没在受害者体验中,未能形成支撑民族责任与自觉的逻辑。特别是对非战争当事者朝鲜的殖民统治认识,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体验阴影下几乎没有显现。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责任意识,因自己是加害者的同时也是受害者的双重性而变得模糊,极力抗拒承担加害者责任。国家与保守右翼政治家们认为,承认加害者责任是使“为国”而“无辜”牺牲的日本人成为加害者而被两次“杀害”的事情,会伤害国民的感情。现在保守右翼政治家们以“战殁者遗族会”为重要的支持势力,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在日本社会,除了日本是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受害者意识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受害者意识,那就是日本国民既是战争受害者,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即双重受害者意识。这种将日本国家与国民分开,把国家视为加害者,把国民设定为受害者的方式是战后进步知识人在批判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的。他们的批判基于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与被压迫的民众的认识。根据这个主张,民众在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教化下,被战争牵连,支持和拥护国家的侵略政策。战时通过各种组织动员的物资,促进了协助战争的地域性民间团体的组织化。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将国民引向战争。战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是由于视国家的国体比国民的生命更重要的认识导致的。在前线不允许撤退和投降,要求坚持战斗到最后阵亡为止,即“玉碎”;因政府与军部为“国体护持”延迟投降时间,而导致了遭受原子弹攻击的惨剧。在战后日本人的记录中经常出现“上当了”的表述,正反映了这种认识。(10)安丸良夫将国民 “上当了”的受害者意识理解为 “很多民众以‘上当了’的逻辑理解和接受从战争开始到战败的过程,但其中漏掉了要承担战争责任的意识。这里反映了未经过与传统价值的深刻对决而急速接受新价值的情形。参看:安丸良夫《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前夜》,東京:朝日新聞社,1997年。战后日本社会对民主主义思想和国家主义的抵抗意识与这种受害者意识相结合得以扩散。双重受害者意识严重阻碍了日本人自身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责任意识的发展。侵略战争是少数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日本国民也是受害者,这种逻辑为日本国民从自身协助战争的犯罪意识和恐惧中摆脱出来提供了依据。但是在日本侵略亚洲国家并扩大其势力过程中,日本国民曾热烈欢迎本国的胜利和强大,增强了一等国家的自豪感,因此日本国民不能否认自己也曾是战争参与者的历史事实。
东亚成员国很难接受日本的受害者意识。韩日两国对“1945年8月15日”这一历史用语的认识差异是很好的证明。在韩国称这一天为“光复节”,而在日本称“终战纪念日”。这一天,对于韩国来说是因摆脱殖民统治而充满喜悦和希望的日子,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却是“镇魂日”。每年8月到广岛和长崎遭原爆战败之日,在日本通过各种不同的活动祭祀“为国家无辜阵亡”的士兵和民间阵亡者,回忆战争的悲惨,祈祷和平。(11)1963年5月14日内阁会议颁布了“关于实施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的决定。之后,每年到 8月15日由政府主办定期举行“阵亡者追悼仪式”。这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对过去战争的认识。 参看:吉田豊著,河棕文、李爱淑译《日本人的战争观》,高阳: 历史批评社,2004年,第119页。1995年7月下旬,即战后50周年前夕,明仁天皇举行了为期10天的慰灵旅行。为了到亚洲太平洋战争的遗址安抚阵亡者灵魂、祈祷和平而举行的慰灵旅行,象征性地反映了日本人所谓战争体验的性质。天皇的访问地是曾遭原爆之长崎和广岛、发生过惨烈陆战的冲绳以及东京等作为非军事设施遭美军空袭而导致无辜平民伤亡的地域。总之,日本人的战争体验是受害者体验。
自近代以来,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从未有过像在亚洲太平洋战争那样戏剧性的受害者体验。这场战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推测仅日本军人及军属的伤亡人数即达到200多万,冲绳居民伤亡15万,遭原爆伤亡人数,1945年广岛达13万—14万,长崎达7万—10万。另外,因遭空袭伤亡者人数达10万人以上。(12)東京空襲を記録する會编《東京大空襲の記録》,东京:三省堂,1982年;澤田昭二《共同研究廣島·長崎原爆被害の眞相》,東京: 新日本出版社,1997年,第34页。“原爆”或“被爆”是浓缩日本作为亚洲太平洋战争受害者体验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例。现代史上,广岛和长崎是在实际战争中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唯一事例,因美国对日本非军事地域投掷原子弹而导致了大量普通民众伤亡,不仅当时以令人恐惧的破坏力瞬间将整个“被爆”地域陷入毁灭的境地,而且至今还在出现因原爆后遗症导致伤亡者,这些都是日本人把原爆视为战争体验核心的主要原因。对日本人来说,虽然没有比原爆体验更具有代表性,但对冲绳战役、东京大空袭的体验也非常强烈。除此之外,因准备总力战,日本人长期过着贫穷生活,还有许多家庭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等等,日本人的战争受害者体验难以估量。(13)受害体验通过出版“战争记录物”这一非正常热潮急速扩散。“战争记录物” 的出版象征性地反映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批判意识急速衰弱的现实。 参看:吉田豊著,河钟文、李爱淑译《日本人的战争观》,高阳:历史批评社,2004年,第121-128页。所以当得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时,许多日本人一方面因战败而感到悲哀,另一方面因终于摆脱漫长的战争之苦而感到欣慰。战后日本人的受害者体验不断地被反刍,成为现代日本社会心理的重要土壤。
韩国、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遭受的战争损失远远超过日本。因法西斯侵略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人,在“皇国臣民”的名义下被动员卷入战争,成为侵略战争的牺牲者。朝鲜人遭受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伤痕至今尚未平复。美军在日本投掷原子弹时,广岛的朝鲜人居民有6万,其中2万多人遭原爆死亡;在长崎遭原爆而死亡的朝鲜人达到1万—2万。(14)关于朝鲜人原爆被害者,参看:朴壽南《もうひとつのヒロシマ 朝鮮人·韓國人被爆者の証言》,東京:舎廊房出版,1982年;鎌田定夫《被爆朝鮮人·韓國人の証言》,東京: 朝日新聞社,1982年;長崎在日朝鮮人の人権を守る會编《朝鮮人被爆者―ナガサキからの証言》,東京: 社會評論社,1989年;许光茂《关于韩国人原爆被害者的诸研究及存在的问题》,首尔:韩日民族问题研究(6),2004年。在遭原爆的朝鲜人中,包括很多被强征来的军人、军属、劳动者。这些人在战后因不是日本国民的理由未能得到任何赔偿和补偿。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以后,中国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仅1937—1945年间军人伤亡人数就达562万名,占领地区普通民众的伤亡人数达135万名,因遭受空袭伤亡人数达76万名。[3-4]
三、对阵亡者扭曲的哀悼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日本社会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为代表的新国家主义者开始把日本的侵略战争如“圣战”似隐蔽或歪曲,围绕“哀悼”阵亡者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20世纪是因两次世界大战导致1.7亿人伤亡的“大屠杀的世纪”,此应视为出现“哀悼”阵亡者问题的背景。日本把围绕这个问题出现的争论称为“历史主体争论”。这个争论的导火线是加藤典洋的《败战后论》[5]。以进步阵营学者为中心的“历史主体争论”批判加藤典洋的逻辑与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为代表的新国家主义的主张没有区别。(15)参看:高橋哲哉《汚辱の記錄をめぐって》,東京:群像,1995年3月号;高橋哲哉《哀悼をめぐる會話-〈敗戰後論〉批判再說》,東京:現代思想,1995年 11月号;大越愛子《もうひとつの<語り口>問題-どのように歷史的事實と出會うか》,東京:創文,1997年4月号。介绍日本“历史主体争论”的译著有:小森洋一、高橋哲也编,李圭洙译《超越国家历史》,坡州: 三仁,1999年;高橋哲也著,李圭洙译《追究日本的战后责任》,高阳: 历史批评社,2000年。
在加藤典洋的《败战后论》中充满了晦涩难解的文章。现在韩国社会尚未形成正确理解战后日本社会的条件,所以不可能正确理解加藤典洋提出的问题的本质。尤其是加藤典洋频繁使用的“被扭曲”“被污染”“错误”等词汇,虽然对概念的界定很暧昧,却具有能引发情绪的妙效。(16)例如,加藤对被“污染”的共同体主张“经过战争,世界变得如此污秽,但人们为什么寻求没有污染的世界?日本的战后通过这个‘污秽’连接20世纪后半期以后的世界普遍性。不存在污秽之外的外部道路……留给我们的是污染的存在,从污染的地方走向‘真’‘善’之道,不是从‘善’到‘善’,而是因‘没有其他方法’只能从‘恶’成就‘善’,没有外部的其他道路。但从新道路被消灭的事态思考这个‘被污染的世界’,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出现了被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正义完全失败的战败国。之后,这个‘污秽’逐渐向世界扩大,至今覆盖着全世界。” 加藤典洋《敗戰後論》,東京:講談社,1997年,第76-77页。虽然是难解的文章,但却是使日本的污秽变得暧昧的强有力的修饰法,与他所说的“宽容被污染的父亲”这句话一脉相通。如果退一步“肯定”地接受加藤的主张,“日本社会首先要成为能够谢罪的社会,即构筑谢罪的主体,其唯一的方法是克服人格的分裂。”[5]102-103如果把加藤的主张与靖国神社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在参拜神社问题上,主张对“亚洲2000万牺牲者”谢罪和赔偿,维护包括放弃战争条款在内的和平宪法的进步主义者的逻辑,与主张承认“大东亚共荣圈”的正当性、哀悼“日本300万牺牲者”、要修改被美军政强迫制定的和平宪法的保守主义者的逻辑相冲突。加藤在哀悼阵亡士兵即哀悼供奉在靖国神社“英灵”问题上认为,对 “哀悼”或“追悼”阵亡者问题的“根源”在于战后日本人格的分裂,具体说明如下:
战后日本的革新派主张有必要向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被杀害的“亚洲2000万牺牲者”谢罪。但他们对“日本300万牺牲者”,特别是阵亡士兵则置之不顾。因为革新派把侵略战争的尖兵即日本阵亡士兵视为“污秽的死亡者”一般厌恶。另一方面保守派则不考虑“亚洲2000万牺牲者”,沉浸在要将日本阵亡士兵的“英灵”供奉在靖国神社的“虚妄”中。如果把考虑“亚洲2000万牺牲者”的革新派视为“外向型自我”,那么考虑“日本300万牺牲者”特别是阵亡士兵的保守派就是“内向型自我”。战后日本的“根源”是如“ Jekyll博士与Hyde氏”那样死亡者的分裂。1993年细川护熙首相发表讲话主张“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之后,长野法务相因发表“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等反击细川首相的言论而遭辞职。在日本社会,一方的谢罪被另一方的反动而失去效力的现象如年终活动似重复上演。只要不消除类似的人格分裂本身,无论经过多长时间,日本都无法真正地向亚洲的战争牺牲者谢罪,也不可能承担战争责任。为了真正谢罪并承担战争责任,首先要克服人格分裂,以谢罪主体、责任主体形成统一的日本国民。[5]103-104
加藤主张战后在日本出现的保守与进步两大阵营间的对立是因没有“自我的日本”和“继承历史的主体”而导致的人格分裂,重复上演的谢罪和妄言也是因此造成的。他指出了保守与进步对立构造的根源与缺陷,即进步主义者的逻辑是在没有真正自我的日本环境下出现的轻率的自我否定,强调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日本的战败给日本人带来的侮辱,那么对亚洲的谢罪只不过是表面上的谢罪;保守主义者出于感性民族主义,主张只哀悼本国牺牲者,这是歪曲和美化侵略历史的无赖逻辑。加藤从两非论立场对日本的保守和进步两大阵营都进行了批判,似有道理。
加藤的对策是什么?总体上说,加藤通过《败战后论》向日本人提出的对策是:不能像革新派一样只考虑亚洲的受害者,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国牺牲者”,特别是要对阵亡士兵表示深深的哀悼和怀念。还说,对本国的阵亡士兵表示深深的追慕和哀悼是对阵亡士兵的“尊重”,是让战后的日本人向他们表示“谢意”。(17)参看:加藤典洋《〈敗戦後論〉をめぐる 在官方历史中,为本国牺牲的300万日本人,没有被赋予应有的地位。官方历史将对于被侵略国的人民来说不过是“恶劣的侵略者”而已的本国牺牲者“置之不顾”。对于Jekyll博士来说,因“拥抱”阵亡的侵略者,在国际社会中与阵亡者一起被打上侵略者的烙印,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人在国际社会中承担侵略战争责任的行为。例如至今日本的护宪派与和平主义者悼念阵亡者时,首先将战争中的“无辜牺牲者”排在前位,即把因亲人、原爆而导致的战争牺牲者和亚洲2000万牺牲者排在优先位置,而侵略者即“污秽”的死亡者没有被赋予自己的位置。因为日本300万牺牲者处于罪犯的位置,靖国神社问题实际上是为了弥补被隐蔽的“空白”,把日本300万牺牲者作为“纯洁”的存在(英灵)而表示哀悼的内向型自我,即Hyde氏的计划。[5]276 这种主张发展成为要把参拜靖国神社正当化的逻辑。加藤主张的“对自国死亡者表示深深的追慕和哀悼的必要性”与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对为祖国被迫到战场献出生命的人表示由衷的哀悼、敬意、谢意”有什么不同呢?在《败战后论》中所谓的“为自国牺牲者”或“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而牺牲者”与靖国神社的逻辑有什么不同呢? 加藤认为自己的逻辑与靖国神社的逻辑是不同的。他主张为了与靖国神社的逻辑断绝,首先要向本国的阵亡士兵表示哀悼和谢意。通过上面的引文可见,加藤主张日本保守派的参拜靖国神社逻辑,不是因为进步派要向亚洲牺牲者谢罪导致的,而是因为进步派将日本的阵亡士兵置之不顾而只要向亚洲牺牲者谢罪造成的。总之,加藤认为导致靖国神社问题的根源不在保守派,而在于进步派对日本阵亡者的狭隘认识。这个稀奇古怪的逻辑不过是利用玄学似的修辞为使参拜靖国神社正当化服务的诡辩而已。 历史学家井上學在与自己的独白中主张,在1960年前半期反对韩日会谈斗争过程中很容易听到关于在中国战场阵亡的日本士兵或广岛牺牲者的声音,但关于被日本强制带走的朝鲜人的声音却被忽视。他指出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观与和平思想的特征,就是“对近代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侵略战争的事实以及由此给亚洲民族和国民造成痛苦的历史认识不足。”(18)井上學《日本反帝同盟史硏究》,東京: 不二出版,2008年。根据他的主张,战后日本人的思想特征是从近现代日本历史形成的一种“体质”。因此历史学的责任是揭示历史上日本人扭曲“体质”的形成过程,展望其变革的方向。这将对近代东亚的历史认识、日本的殖民地统治责任、战争责任、战后责任以及未来民众的联合等问题的思考都提供很多启示。 围绕担心的问题,尽管出现众多研究成果和社会实践,但尚未找到解决的头绪。这不只是基于要向日本社会单方面追究“殖民地统治责任”的落后、陈旧的思考方式。考察现在的韩日关系,要克服日本社会内部“体质”的动向及对此表示反抗的“隐秘的声音”依然在发威。下面以对2017年在韩国也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的日本代表性小说家村上春樹的小说《騎士團長殺し》(19)村上春樹《騎士団長殺し》,東京:新潮社,2017年。的评判为例,进一步加以说明。 韩国媒体关注村上春樹小说的原因不在于他是畅销书的作家,而是因为他受到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集体攻击。小说主要反映了一位突然接到妻子离别消息的肖像画画家被卷入不可思议的事件后,努力克服心灵创伤的过程。但问题是他在书中提到日本右翼势力否定的南京大屠杀,而且他提到的南京大屠杀牺牲者的数量与中国的主张接近。(20)《村上春樹在新作小说中谈及‘南京大屠杀’ ,被日本右翼称“卖国奴”》,《京乡新闻》,2017年3月7日。《村上春樹在新作小说中谈及‘南京大屠杀’,被日本右翼称“卖国奴”》,《中央日报》,2017年3月7日。在此书中,村上春樹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是“日军杀害投降的士兵和市民达10万—40万”“日军占领南京城后发生了大量的屠杀,既有与战斗有关的屠杀,也有战斗结束后的屠杀。”“日军无暇顾及俘虏,所以屠杀了大部分投降的士兵和众多市民”“虽然与历史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众多市民在战斗中伤亡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他还追问“关于中国的死亡人数,有的主张10万,有的主张40万,其差异的主要原因到底在哪里?”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是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城后发生的对中国人进行大屠杀的事件,中国主张30万人被屠杀,而日本只承认屠杀事实,对被屠杀人数则持不确定的态度。就像围绕“慰安妇”问题发生的争论,围绕大屠杀真相问题的争论仍然支离破碎。(21)关于南京大屠杀争论的研究有:板倉由明《本当はこうだった南京事件》東京: 日本図書刊行会,1999年;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東京:岩波書店(岩波新書),1997年;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論争史——日本人は史実をどう認識してきたか》,東京:平凡社(平凡社新書),2007年;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日本人―戦争の記憶をめぐ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グローバリズム》,東京: 柏書房,2002年;北村稔 《南京事件の探究——その実像をもとめて》,東京:文藝春秋(文春新書),2001年;北村稔《〈南京大虐殺〉とは何か》,東京:日本政策研究センター,2016年;田中正明《南京事件の総括——虐殺否定の論拠》,東京:小学館文庫,2007年;日本会議国際広報委員会、大原康男、竹本忠雄《再審〈南京大虐殺〉——世界に訴える日本の冤罪》,東京: 明成社,2000年;秦郁彦《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東京:中央公論新社(中公新書),2007年;東中野修道《〈南京虐殺〉の徹底検証》,東京:展転社,1998年;南京事件調査研究会編《南京大虐殺否定論13のウソ》,東京:柏書房,1999年;洞富雄、藤原彰、本多勝一編《南京事件を考える》,東京:大月書店,1987年;洞富雄、藤原彰、本多勝一編《南京大虐殺の現場へ》,東京: 朝日新聞社,1988年;洞富雄、藤原彰、本多勝一編《南京大虐殺の研究》,東京:晩聲社,1992年。小说内容被传开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及其媒体攻击村上春樹为“卖国贼”,批判作者是为了得到诺贝尔奖发表了这种“自虐史观”的小说。而韩国社会则普遍认为村上春樹代表日本有良心的社会群体,因为村上春樹多次表明谢罪不是可耻的事,日本应承认过去历史,一直谢罪到对方国家满意为止。村上春樹通过小说这一大众媒体反问井上學所谓的日本人的“体质”,敦促日本社会改善扭曲的“体质”。 通过井上學和村上春樹的事例可见,日本对过去的体验和记忆被教化着。日本的新国家主义声称一直以来的历史观为“东京审判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自虐史观”“黑暗史观”,利用各种言论媒体扩散自己的主张,扩大支持势力。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日本尚未形成能够解决战争责任和战后赔偿问题的社会环境下,向以未曾体验战争的新一代为中心不关心他者诉求的大众,毫无过滤地扩散着否定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的言论。日本国内围绕《騎士團長殺し》对过去历史的记忆在大众中引起的反响,是否能够成为历史认识的转折点,改善日本人的思想“体质”,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恢复历史体验和记忆是还原南京大屠杀当时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历史真相不可回避的、也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记忆的斗争”不是单纯停留在因过去的历史负债导致的后代的民族责任伦理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未来东亚共同的历史认识与和平基础建设的重要问题。结语——以围绕《杀骑士团长》展开的争论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