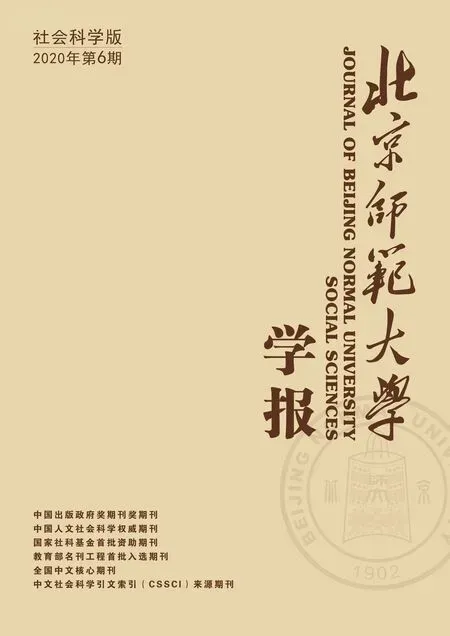“修昔底德命题”抑或“修昔底德陷阱”
——历史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缘由之不同解读
2020-12-11杨晨桢
杨晨桢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公元前431年,以雅典为领袖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展开了一场耗时数十年之久的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被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称作“比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记述”的、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影响重大而深远”(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4页。的战争,自爆发起就引起了同时代戏剧家、史学家的关注。时人普遍将这场战争归罪于在战争爆发前发表葬礼演说的雅典领导人伯利克里(2)阿里斯托芬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公元前425年发表的《阿卡奈人》(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罗念生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4页)中以戏谑的口吻展现了伯利克里因为三名娼妇而发动战争。该作品一经演出即获得了头奖,在当世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观点长期主导了雅典人的思维(3)普鲁塔克在《论希罗多德之阴险》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参见Plutarch,Moralia,On the Malice of Herodotus,Volume Ⅺ,translated by Lionel Pearson and F.H.Sandbac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6。,直到修昔底德所撰写的有关这场战争的著作问世。
修昔底德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亲历者。作为一名雅典的历史学家,他对这场战争的爆发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并不满足于人们对这场战争已有的解释,甚至不认同市井间流传的关于这场战争的细节与传说(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徐松岩译注,第69页。。战争的爆发可能确实受到了特殊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影响,但修昔底德试图寻找的是超越这场战争本身而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警世恒言。因为他的努力,后世的人们得以透过历史的迷雾看到2000多年前与战争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他们的言行对历史走向的影响。他的文稿也成为关注这场战争的后世学者们研究的起点。
一、不同学者对“修昔底德命题”的解析
修昔底德所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本质上是一部历史学著作。书中充满了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后诸多历史细节的铺陈与描绘。但在此书的首卷,作者却如同一名国际关系学者一样首先表明了他对战争爆发真正原因的判断。他写道:
(5)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lated by C.F.Smit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Ⅰ.ⅩⅩⅢ.6.这段文字在已经出版的中文译本中有两种翻译。在商务印书馆版本中,谢德风将其译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1页。而当代学人徐松岩则将这场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翻译为:“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而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徐松岩译注,第73页。译文的差异一方面反映了译者们理解的分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不同语言间转换的困难。尽管希腊语词汇的意涵在古典学者那里已经得到了破解,但语言规则和结构的不确定性依然给后世的人们理解修昔底德带来了挑战。解读修昔底德的文字成为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重要路径。
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通篇考察了修昔底德的著作后提出,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前因后果的描述表明,在修氏眼中,无论斯巴达与雅典两个城邦的人民对对方怀有何种程度的怨恨,“到头来是斯巴达人而非雅典人首先跨越对手的边界”(8)⑤ 〔美〕维克多·戴维斯·汉森:《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殷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13页。。因此,可以说,战火是由斯巴达点燃的。出于内心的恐惧、嫉妒和憎恨,斯巴达人在行动上总是反复无常。他们凭借着野性的冲动做出了那些并不总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或普遍利益的行为,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⑤。

西利的观点多少受到《修昔底德文本(卷一)注疏》一书的启发。该书作者A.W.戈姆(A.W.Gomme)提出,在修昔底德那里,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雅典的帝国主义和斯巴达对对手的恐惧。换句话说,一方面,雅典的挑衅性行为是战争爆发的原因;另一方面,斯巴达也不是出于捍卫自治原则的无私目的被迫应战,而是被对自身的地位将遭到削弱的恐惧驱动而投入战争。双方都对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这与道德评价无关(12)A.W.Gomme,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Book 1),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p.152.。
P.J.罗德(P.J.Rhodes)同样考察了修昔底德所给出的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希腊文原文。他重点关注的是aitia与prophasis两词。根据莱昂内尔·皮尔森(Lionel Pearson)的考据,前者可以被理解为指控、抱怨、不满,往往带有消极色彩,也可被理解为归咎于或抱怨的理由;而后者从词根的角度讲则是研究者对某种行为给出的解释,这种解释可能是行为者行事的原因,或者是行为者行事的目的(13)Lionel Pearson,“Prophasis and Aitia”,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1952,83,pp.205-223.。在罗德看来,雅典的崛起只是促成了两大联盟间彼此不满的加剧,因而此处修昔底德选择使用aitia一词,而斯巴达的恐惧才是修昔底德眼中导致战争爆发的真正理由(alethestate prophasis)。罗德根据修昔底德的论述推断,雅典普通民众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伯利克里身上,认为是后者拒绝给麦加拉留下活路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但在修昔底德看来,伯利克里所引发的不满并非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而只是一方发动战争的借口。真正重要的是不满为什么会逐渐演化成为一方发动战争的借口。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具体案例中,是斯巴达的恐惧帮助实现了这一转化,因而斯巴达的恐惧才是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当然,在解构了修昔底德的话语内涵后,罗德也对这一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本人并不十分认同修昔底德的解读。他认为将斯巴达的行为动机仅归纳为恐惧是不充分的。根据他的研究,雅典与斯巴达都在等待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发动战争,并且都希望自己在战争中可以代表正义的一方(14)P.J.Rhodes,“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Hermes,115.Bd.,H.2 (2nd Qtr.,1987),pp.154-165.。
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同样从上述两个希腊词汇出发,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康福德看来,修昔底德非但没有在使用这两个词汇前对其一一辨析,反而在实际运用中,还常常将这两个词汇进行混用。这一语言学的事实恰恰证明,修昔底德在撰写第1卷时从来不曾提出过“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什么”这一问题。他试图解释的问题为:“战争从何开始——战争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双方的抱怨、争吵和借口是什么?”可以说,修昔底德并没有告诉我们战争的起因,“因为他从来不用、也不能用清楚明确的语言提出该问题”(15)〔英〕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3-54页。。基于相似的论点,F.E.爱德考克(F.E.Adcock)指出,如何看待和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还需要学者们根据史料进行独立地分析,盲目地相信修昔底德并不可取(16)F.E.Adcock,“Thucydides in Book I”,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51,71,p.4.。
二、历史学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判断
作为希腊世界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重大且最深远的战争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自然受到历史学人的关注。求真的本性使他们成为最无法简单接受修昔底德关于战争爆发的论断的一批人(17)Eric W.Robinson,“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and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edited by Ryan K.Balot,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118.。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梳理历史细节出发,在关于这场战争爆发原因的问题上,得出了与修昔底德不同的结论。
(一)贸易争端导致战争爆发
乔治·葛兰迪(George Beardoe Grundy)是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之一。他在《修昔底德和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一书中谈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希腊世界的矛盾中心并不是雅典与斯巴达,而是雅典与科林斯。在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的整体实力非但没有上升,反而在不断衰落。换句话说,雅典的崛起并没有表现在其整体实力上,而是体现在贸易领域。因而,在向西扩张贸易的过程中,雅典与希腊世界另一个海上强国科林斯就产生了矛盾。科林斯为了保住自身的贸易优势,特别是对航线中重要城邦科西拉的控制,率先联合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一众小国,并最终将同盟领袖斯巴达拖入了战争(18)George Beardoe Grundy,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Vol.1,Oxford:B.Blackwell,1948,pp.323-330.。
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同样认为希腊世界中这场军事冲突最早起源于贸易争端。但根据他的观察,雅典境内的外邦人才是导致战争爆发的罪魁祸首。他在《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一书中提到,梭伦改革吸引了大批外邦人移居雅典从事手工业,到伯利克里主政时期,雅典境内的外邦人已逐渐成为城邦内部的新势力。这些外邦人与“本土的乡村人口既没有共同的传统也没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对雅典同盟过时的反波斯理想一无所知,也不关心伯利克里将雅典建成‘全希腊的学校’的设想”。对于他们而言,自身利益的实现依赖于雅典帝国对主要商业路线的掌控。当他们“逐步而稳定地摆脱伯利克里的控制”,并最终成功地号召雅典的民众为了海上的利益向伯利克里施压时,雅典便被推向了战争的边缘(19)〔英〕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第18-22页。。
另一种与贸易有关的战争起源说始于对《麦加拉法令》的解读。在修昔底德那里,《麦加拉法令》的公布是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之一。但与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叙述爱皮丹努斯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对提洛同盟与斯巴达同盟矛盾层层升级的影响不同,修昔底德对麦加拉事件的叙述是隐藏在行文的字里行间的。在拉栖代梦人召开的控诉雅典侵略行径的盟邦大会中,“麦加拉人历数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情况,特别指出他们被排斥于雅典帝国的所有港口以及雅典市场之外,这是违背条约有关规定的”(2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徐松岩译注,第87、101、158页。。修昔底德没有将麦加拉人的抱怨当作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但对于那些不把修昔底德的言论奉为圭臬的人而言,《麦加拉法令》的出台正是导致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21)Simon Hornblower,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ume I,Books I-III,Oxford:Clarendon,1991,p.111;P.A.Brunt,“The Megarian Decree”,in Studies in Greek History and Thought,by P.A.Bru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16.。对于伯罗奔尼撒同盟而言,该法令既是一种宗教上的侮辱,也是一种经济制裁(22)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Gerald Duckworth & Co.Ltd.,1972,pp.225-289.。雅典人强加的《麦加拉法令》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规避了直接违反雅典与斯巴达签署的三十年和约的技术性规定,但依然无可否认地违反了和约的根本精神,因此应被视为一种极具挑衅性的行为。拉栖代梦人曾经直言,只要雅典废除该法令,那么它就会退出战争,但雅典人选择了坚持。这一点被修昔底德轻描淡写地带过,似乎是为了避免他的核心论点遭到削弱甚至被推翻(23)Eric W.Robinson,“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and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n The Ox f 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p.119.。
(二)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质上是一场执政者关于本邦政治体制的竞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的政治派别》一书表达了这一看法。该书作者惠布利(L.Whibley)提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可能是一场民主制与寡头制之间有关政治理想的争端。情感与利益的一致性使民主派凝聚成对抗寡头派的一方。寡头派的代表斯巴达十分畏惧雅典的民主制在希腊世界蔓延,因为雅典的民主制不仅具有改变人信仰的能力与扩张性,而且拥有引人注目的内聚力与稳定性(24)L.Whibley,Political Parties in Athens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89,pp.33-34.。因而,“一旦雅典开始将其权势贪欲与一种支持境外民主的激进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斯巴达就理所当然地断定威胁超过了单纯的武装竞争,并且很可能感染每一处希腊人的情感和思想”。坚持与雅典和平共处将动摇斯巴达的政治根基,因而遭到城邦寡头统治者们的抛弃(25)〔美〕维克多·戴维斯·汉森:《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殷弘译,第11-12页。。但也有学者表示,民主政体的出现确实加剧了希腊世界内部的分裂与混乱,但战争的源头却不能因此被认定为民主与寡头之争(26)〔法〕雅克琳娜·德·罗米伊:《希腊民主的问题》,高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142页;William O.Chittick and Annette Freyberg-Inan,“‘Chiefly for Fear,next for Honour,and lastly for Profit’:An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Motivation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1,27,pp.69-90。。
(三)伯罗奔尼撒战争源于斯巴达对雅典的长期憎恶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往往拒绝将伯罗奔尼撒战争视为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承认斯巴达是因为对雅典势力增长的恐惧而发动的战争。晏绍祥就曾指出,斯巴达人因为雅典不够恭顺的表现而长期对其怀有憎恨之心,并多次入侵阿提卡半岛。斯巴达和雅典在希波战争后签订的三十年和约只是短暂地中止了双方的敌对行为,但却没有消除前者对于后者的敌意。在和约期间,斯巴达主战派一直伺机再次发动对雅典的攻击,并在战前和谈中表现得咄咄逼人。波提狄亚事件只不过是斯巴达一方用来挑起战争的借口罢了(27)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
此前,《雅典与斯巴达》一书的作者安东·鲍威尔(Anton Powell)在其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但他更加强调科林斯在休战期间态度的转变对于战争爆发的重要影响。具体而言,早在公元前440年,斯巴达内部主战派就已经对进攻雅典蠢蠢欲动了。但彼时的科林斯并不想与雅典直接交锋。没有科林斯的海上力量支援,伯罗奔尼撒同盟很难确保战争的胜利,因而斯巴达推迟了对雅典的进攻。但在公元前431年,科林斯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给予了斯巴达主战派更多的信心和发动战争的理由。在他们的一再煽动下,对雅典的仇恨之情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内蔓延开来。换言之,在该书作者看来,科林斯对战争爆发的意义不在于它说服了斯巴达参战,而在于它在是否开战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转变(28)Anton Powell,Athens and Sparta:Constructing Greek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from 478 B.C.,London:Routledge,1993,pp.113-118.。这种转变的重要性在J.B.萨蒙的著述中得到了更加详细具体的分析(29)J.B.Salmon,Wealthy Corinth:A History of the City to 338 B.C.,Oxford:Clarendon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97.。
(四)斯巴达为了维系自身的地位和联盟的团结发动了战争
与上一类学者不同,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并不认为斯巴达是因为自身的好恶而发动了对雅典的战争。相反的,他们指出,斯巴达实际是被自己的盟友拖入了战争。这里的盟友主要指同样对称霸怀有野心且对雅典长期敌视的科林斯(30)Lawrence A.Tritle,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Malden:Wiley-Blackwell,2010,pp.11-43.。正是科林斯的牵线使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城邦得以痛诉对雅典的不满,而斯巴达也是在科林斯的一再怂恿下作出开战决定的(31)何元国:《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论探微》,《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6-8页。。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德·圣·克鲁瓦(G.E.M.de Ste.Croix)等学者看出,当斯巴达主战派在公元前432年提出要进攻雅典时,这一提议因遭到城邦君主阿奇达慕斯的坚决反对而被迫流产。但当斯巴达的盟友向其指出,如果斯巴达无法在行动上对抗雅典的话,它的盟主地位将会遭到取代,此时阿奇达慕斯的反对便显得十分无力了(32)⑨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190,290-291.。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斯巴达之所以在行为上会受到盟友的牵制,本质上是因为它想要保持对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绝对控制,使它在希腊的追随者们能够继续接受自己被奴役的身份⑨。为了维持对盟友的这种统治地位,斯巴达的君主帕萨尼亚斯曾经使用过十分残暴的手段。他的这一行为已经将不少盟友推到了雅典一边。如若斯巴达在面对雅典的扩张、麦加拉的叛逃时无法及时响应盟友对雅典开战的要求,拉栖代梦人则可能会因为名誉和地位的受损而进一步失去盟友。因此,斯巴达背弃三十年和约的行为不仅是因为雅典物质实力的增长,也因为伯罗奔尼撒同盟内多个城邦的叛逃可能给斯巴达造成威望的下降。正如S.N.杰斐(Seth N.Jaffe)所言,权力的组成既与物质有关,也与心理有关(33)Seth N.Jaffe,Thucydides on the Outbreak of War:Character and Conte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133-147.。若伯罗奔尼撒同盟内城邦纷纷与斯巴达离心,则斯巴达在希腊中的权势也会遭到削弱。这是拉栖代梦人所不能接受的。
(五)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领袖的错误判断将两方拖入了战争
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在综合使用多方面材料对伯罗奔尼撒战争重新梳理后,卡根指出,在战争爆发前,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间的摩擦的重要性,要远高于修昔底德所判断的程度,甚至要高于他所言的真正理由。因为根据他的分析,雅典的势力在公元前431年前后并没有显著增长,且在经历过公元前464年的一次奴隶起义后,斯巴达对于内部奴隶起义的恐惧要远大于对雅典势力增长的担心。在卡根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爆发,主要就是因为在彼此关联的众多事件上,雅典与斯巴达的决策者对政治局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如科林斯人以为雅典不会为科西拉而战,伯利克里看轻了麦加拉的自由意志。这些错误判断或惯性思维引导着相关决策者进行了错误的行动,最终将希腊世界的两大强国引向了彼此对抗的道路。作者同时指出,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互不信任、互相猜疑,科林斯与科西拉的长期矛盾,斯巴达同盟组织结构中的弊端,以及斯巴达制度上的缺陷,都可能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34)〔美〕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曾德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Donald Kagan,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
三、国际关系领域学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
伯罗奔尼撒战争及修昔底德所著史书的特殊性使这场战争不仅吸引了历史学人,也获得了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特别是现实主义者的关注。《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的作者就曾表示:“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能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获得启发。”(35)〔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 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9页。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W.Doyle)则称:“从本质上讲,修昔底德就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对于大多数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而言,当被问及何为像现实主义者一样思考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像修昔底德一样思考(36)Michael W.Doyle,Ways of War and Peace:Realism,Liberalism,and Socialism,New York:Norton,1997,pp.49,51.。换言之,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们在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时都多少受到了“修昔底德命题”的影响。但不同的理论家在看待这场战争时仍然存在观点的分歧,并由此发展出了不同的理论(37)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学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探讨仅仅停留在战争起源的问题上,包括汉斯·摩根索、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在内的多位国际关系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引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案例。劳丽·约翰逊·巴格比则专门撰文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利用和滥用修昔底德的问题。参见Laurie M.Johnson Bagby,“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4,48(1),pp.131-153。更有学者大卫·韦尔奇近乎严肃地表示国际关系学人应当停止阅读修昔底德。参见David Welch,“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Should Stop Reading Thucydid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3,29,pp.301-319。蒂莫西·卢拜克也提出,对于国际关系学人来讲,频繁地求助于修昔底德并不利于提高我们解释战争与和平的动态机理的能力。参见Timothy Ruback,“Ever since the Days of Thucydides:The Quest for Textual Origins of IR Theory”,in Scott G.Nelson and Nevzat Soguk,eds.,Modern Theory,Modern Power,World Politics:Critical Investigations,Surrey:Ashgate,2010。。
(一)安全困境说
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问题是由约翰·赫兹(John Hertz)较早提出并进行系统阐释的。他在1950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生活在无政府社会中的群体或个人必须而且通常会“关心他们的安全免受其他群体或个人的攻击、压迫、支配或消灭。为了在攻击中获得安全,他们被迫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以避免受到其他权力的影响。这反过来又会让他者更加不安,并迫使后者作最坏的打算。在这样一个由竞争单位组成的世界中,没有人能感到完全安全,权力竞争因此随之而来,安全与权力积累的恶性循环由此展开”。这即是所谓的安全困境(38)John Hert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1950,2(2),pp.157-180.。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将此定义进一步简化为“一个国家寻求提高自身安全的多数手段会无意中造成他国安全下降的结果”,并认为这种现象与修昔底德笔下战前的希腊世界的情形高度类似(39)Robert Jervis,“Realism,Game Theory,and Cooperation”,World Politics,1988,40(3),pp.317-349.。
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一书中,具体用囚徒困境模型(40)在作者看来,安全困境是囚徒困境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特殊表现。,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影响雅典作战意图的科西拉的游说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尽管雅典和斯巴达都不希望破坏三十年和约,但科西拉代表的讲演让雅典决策者担心,一旦自己遵守了条约而伯罗奔尼撒同盟背弃条约,雅典在海上力量对比中就将处于劣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雅典接受了科西拉的说辞,决心投入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科林斯的战争。这种行为就“类似于囚徒困境中的一个嫌疑犯”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权衡利弊,选择招供。但约瑟夫·奈同时指出,雅典选择介入科西拉与科林斯的纷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雅典人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这种信念也是导致近代众多国家间战争爆发的原因。换言之,约瑟夫·奈认为,若非心存战争必然爆发的信念,安全困境未必会步步升级,最终导致战争爆发。“安全困境使得战争极可能发生,但是‘极可能’并不等于‘不可避免’。”(41)〔美〕小约瑟夫·奈、〔加拿大〕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29页。
(二)权力转移说
权力转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人解读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另一重要路径。这一理论的奠基人为A.F.K.奥根斯基(A.F.K.Organski)。他在《世界政治》一书的第12章指出,工业化的出现及其扩散带来了国家相对实力的快速变更。这种得益于国家内部的工业发展而非对外领土征服或缔结联盟实现的国家的实力变化,使得传统的均势理论逐渐丧失了其独有的解释力,因为国家不再能够通过拆解对手同盟的方式来终止敌国实力的增长。世界政治于是演进到一个新的时期,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对之进行解读。这种新的理论即为权力转移理论。在他的这种理论之下,国家依据能力大小和对现有秩序的满意程度被分为四类,其中强大且对现有秩序不满的国家被认定为现有秩序的挑战国。“这些暴发户没有参与国际秩序的建立,而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及其支持者通常不愿给予新来者超过后者已得的一小部分利益。”挑战者们于是开始寻求在国际社会中为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地位,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权力相适应的地位。这些国家高速且持续增长的实力使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在权力上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相匹敌或超越后者,他们不愿意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占统治地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和特权。”(42)⑥ 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58,pp.328,332.因而,一般当挑战国出现的时候,就会有战争爆发。而“战争最可能发生在(对现状)不满的挑战国和他的盟友的实力开始接近维持现状的那些国家的实力总和时”⑥。在他1980年与亚切克·库格勒(Jacek Kugler)合写的另一部专著中,两位学者更加系统地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了推演和验证,并强调指出,“在彼此冲突的国家团体中,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平均分配可能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挑衅者将来自一小群对现状不满的强大国家”;但是,“是那些相对弱小而非相对强大的国家最可能成为挑衅者”(43)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19.。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是另一位关注权力转移的国际关系学者。他将霸权战争视作霸权国走向衰落的过程中一种普遍出现的现象,认为有三个先决条件将会造成霸权战争的爆发。一是国家间政治和经济空间的闭合。这导致国家间争夺领土、资源、市场的冲突越发激烈,并逐渐发展为一种零和博弈,最终引发体系的崩溃和世界战争的爆发。二是体系强国对时机认知及心理发生了变化,即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折正在出现的观点,以及一个或多个大国无法被抚平的恐惧,使得他们准备在自己仍处于优势的时候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来解决问题,与这种历史转折及自身内心的恐惧进行对抗。第三是事件的发展开始超出人们的控制。他认为,根据修昔底德的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在斯巴达面对雅典的成长产生了恐惧心理后,趁自己仍有能力时发动的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其目的是击溃崛起的挑战者雅典(44)〔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杜建平、松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199页;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91-202。。近年来,因为再次提出并详细论证“修昔底德陷阱”(45)“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80年赫尔曼·沃克在海军战争学院的一场题为“悲伤与希望——现代战争的一些思考”的讲座。格拉汉姆·艾利森不是这一概念的首创者(H.Wouk,“Sadness and Hope:Some Thoughts on Modern Warfare”,Naval War College Review,1980,33(5),p.6)。而引人关注的格拉汉姆·艾利森,实际上也是这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归因为一种严重的结构性压力,这种结构性压力出现在一个崛起的大国威胁推翻主导体系的国家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无需重大的、出乎意料的事件,而仅仅是对外事务中一条普通的导火线都能引发大规模的冲突。这种现象被他称为“修昔底德陷阱”(46)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pp.53-54.。同样的结构性压力还出现在其他16个案例中。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案例都属于权力转移的范畴(47)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p.315-316.。
(三)进攻—防御理论
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三种解释出自进攻—防御理论(又简称攻防理论)。对这一理论的集中探讨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但直到罗伯特·杰维斯《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一文发表,这一理论才在国际关系领域首次得到专门的研究(48)〔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142页。。杰维斯在1978年撰写的这篇文章中将进攻—防御理论当作对既有的安全困境学说的补充而提出。他认为,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中,国家间的合作也并非绝无可能,冲突也未必不可避免,因为“如果防御性武器能够明确区分于进攻性武器,那么一国是可能在不降低他国的安全的情况下增加自身安全的。如果防御的优势大于进攻,那么一国安全的显著增加只会略微降低他国的安全。维持现状的国家因此能够共同获得较高水平的安全”。即如果防御占优,且维持现状的大国能提出合理的主观安全要求,它们或许可以避免军备竞赛。但当进攻占优时,一个国家对国际紧张局势的反应将增加战争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先发制人的动机和“对突然袭击的相互恐惧”已经通过对既有危险的分析得到了明确。国家不可能在不威胁甚至不攻击对方的情况下加强自身的安全。这种对战争进程的信念使进攻具有优势,也进一步加深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使得战争变得难以避免(49)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1978,30(2),pp.187-189.。
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ra)则通过实证和逻辑演绎得出,攻防理论不仅可以完善安全困境学说,而且帮助细化打磨了权力转移理论。即在他看来,进攻的优势使权力转移更加显著,从而增加了国家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动机。在进攻占优时,国家更加难以抵挡错误的乐观主义,因而更加容易降低谈判的意愿,而施行机会主义的扩张,使用既有的策略,作出抢先行动的决定,并强调行动和指令的隐秘性。这些都导致国家对作战形势更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而当防御占优时,“国家由于担心胜利的代价过于高昂或根本就难以实现而不敢进行侵略”(50)②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何曜译,第145、141-168页。。 他提出,当进攻占优时,国家的不安全感会更加强烈,因而更容易发动预防性战争并对他国的扩张进行顽强地抵抗,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古雅典的扩张行为就有着这方面的原因②。
哈里森·J.弗雷(Harrison Joseph Frey)则直接使用攻防理论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进行了系统地解读。他参考借鉴了查尔斯·格拉则和哈伊姆·考夫曼(Charles L.Glaser and C.Kaufmann)在1998年的文章中提出的五个衡量进攻—防御平衡的指标(51)这些指标分别为:技术、地理、军队规模、民族主义和资源的积累(Charles L.Glaser and C.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8,22(4),pp.44-82)。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战略形势进行了分析。他提出,由于雅典是一个海洋强国,且其可以有效地对同盟内的城邦课税、征收资源,因而在地理、技术和资源储备上都具有明显优势。在充分意识到自己所具有的进攻优势后,有着征服野心的雅典开始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征程,向斯巴达发起了挑衅,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52)Harrison Joseph Frey,“The Peloponnesian War:Analyzing the Causes of War through Offense-defense Theory”,Georgia Regents University Augusta Honors Thesis,2015.。
(四)认知理论
上述三种对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即把国家假设为单一理性的整体。但随着心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心理学成果被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和学理讨论,国家理性的假设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认知心理学是心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国际关系学人对于认知心理学的运用与讨论相较于心理学中的其他分支要更为成熟。由莱茨(Nathan N.Leites)(53)Nathan N.Leite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New York:McGraw-Hill,1951.提出并由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George)发扬光大的操作码理论(Operational Code)(54)Alexander L.George,“The ‘Operational Code’: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9,13(2),pp.190-222.、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设计的类比解释框架(Analogical Explanation)(55)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都可以被归入这一范畴。简单来讲,国际关系认知心理学派的学者认为,政策是由少数精英而非全体民众制定的,而作为个体的精英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而在迁移历史经验帮助理解的过程中,决策者可能被不准确的历史教训或类比误导,最终作出错误甚至灾难性的判断(56)Miles Kahler,“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pp.921-929.。国际关系学界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无疑当属罗伯特·杰维斯。他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指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国家决策者普遍倾向于夸大对手的敌意继而采取过分的行为,这导致了本来希望保持现状、避免战争的国家间冲突升级,甚至爆发战争(57)〔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70页。。
斯蒂芬·多尔戈特(Stefan Dolgert)正是以既有的认知心理学框架来解读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的。他对雅典和斯巴达的行为分别进行了反事实推理,认为战争本身未必不可避免,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相互冲突的叙事及其所带来的错误知觉导致了危机的升级。具体而言,斯巴达存在着一套叙事逻辑,将自身视为一个“温和的、传统的霸权,统治着一个松散的城邦联盟”。它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这种统治,部分是因为它的实力,部分是因为它的美德,还有部分原因是传统的泛希腊宗教权威赋予对它的认可。斯巴达的领导人认为,它的角色是维护各城邦之间的传统平衡,以使之符合泛希腊主体间性的广泛规范。而雅典则秉持着另外一套叙事逻辑。它将自己视作一支新兴的力量,认为一个国家试图在其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扩张之时,正义才可能存在。相应的,弱者应该服从强者。这符合自然法的规律。雅典的上述观点显然与斯巴达所奉行的逻辑是相悖的。双方以自己的逻辑看待对方的行为,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倘若雅典与斯巴达能够以对方的叙事逻辑来行事或看待对方,例如斯巴达国王用更加物质主义的方式而非派遣有宗教影响力的使者去向雅典彰显自身的实力与意志,或在谈判中提出更多物质主义的要求;而伯利克里若能够不一味按照“不扩张即死亡”的逻辑来判断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希腊世界的两强或许可能避免战争(58)Stefan Dolgert,“Thucydides,Amended:Religion,Narrative,and IR Theory in the Peloponnesian Crisi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2,38,pp.661-682.。
(五)认同危机
人类对于集体身份的认识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出现(59)Tracy B.Strong,“Introduction:The Self and Political Order”,in The Self and Political Order,edited by Tracy B.Strong,Oxford:Blackwell,1992,pp.1-21.。但专门针对集体身份问题进行的研究却产生得相对较晚。它最初是一个社会学和人类学重点研究的课题(60)黑格尔、马克思等人在自己的专著中虽然对身份认同问题也有所涉猎,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作品有:Michae Carrithers,Steven Collins and Steven Lukes,eds.,The Category of the Person:Anthropology,Philosophy,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John Shotter and Kenneth J.Gergen,eds.,Texts of Ident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Inc,1989。。国际关系学人借鉴了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对国际关系领域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探讨(61)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V.Kratochwil,eds.,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Boulder,Col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6;〔美〕约瑟夫·拉彼德、〔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艾弗·B.诺伊曼(Iver B.Neumann)将其总结为四种身份建构的路径:以族群作为边界的民族志学的路径、以主观感受为核心的心理学路径、以马克思辩证法为基石的大陆哲学路径,以及强调社会边缘人的“东旅”路径(62)Iver B.Neumann,“Self and Oth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1996,2(2),pp.139-174.。上述观点都可以简单概括为现已被普遍接受的两项认识:1.集体身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非与生俱来的特质;2.身份的形成源于在和他者的互动中明确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因为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往往被特别地强调,所以可能会爆发不同的身份认同的政治实体间的战争(63)⑧ Per Jansson,“Identity-defining Practices in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1997,3 (2),pp.149,153-159.。
佩尔·扬松(Per Jansson)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进行分析的。根据希罗多德的观点,共同的血缘、语言、宗教、习俗是希腊人这一概念的核心组成成分。希腊人对上述共有特征的认同是在面对波斯的威胁时才逐渐产生并得到强化的(64)John Boardman,Jasper Griffin and Oswyn Murray,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27.。换言之,自觉的希腊身份的形成与波斯的威胁密切相关。希腊人同属希腊,但从种族的角度讲,希腊并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社会,而是由拥有不同历史根源与文化特征的部落群体组成的聚合物。按照修昔底德的观点,这些不一致的特征不可能永远被支配一切的希腊观掩盖。在需要的时候,多利安民族与爱奥尼亚民族的差异性便会被游说集团利用。而这种对自我与他者区别的强调一旦出现,就会被上升到荣誉、核心价值观甚至城邦守护神优劣的高度。这些因素在公元前5世纪共同作用导致两大民族间战争的爆发⑧。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同样认为,斯巴达不是为了有形的利益,而是因为雅典的崛起给它带来了特定的身份认同价值观的威胁而走上了战争之路(65)Richard Ned Lebow,“Play It again Pericles:Agents,Structur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96,2 (2),p.253.。
四、小结与启示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十分重要且被文字记录下来的战争。它同时吸引了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关于这场战争因何爆发,不同的学者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但通过前文的梳理我们能够看出,历史学者们更多地是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个孤立的事件,把战争的爆发当作某次蝴蝶效应带来的偶然结果。他们试图通过使用修昔底德的叙述及其他各种文字记录(66)这些材料包括前文所述的同时期希腊人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载以及后来考古发现的有文字记录的草纸、陶片、石碑等。参见Stefan Dolgert,“Thucydides,Amended:Religion,Narrative,and IR Theory in the Peloponnesian Crisi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2,38,p.670。,分析、梳理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前的各种细节,通过研究不同时期的历史碎片,找出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初原因。他们把修昔底德对于战争的判断当作一个个人命题,解读它,却不尽信它。与历史学者不同,国际关系学人实际则是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当作一种现象进行研究。他们很少去使用或找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外的文字材料,大都不甚在意这场战争爆发前真正发生了什么,而更加关注这场战争是否代表了某一类情形。即当类似有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间的关系变化出现时,战争近乎必然会爆发。这与战前双方的具体矛盾无关。他们更多地尝试倚靠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内的众多国际冲突案例找到一种普适的规律,并希望这种规律能够指导现实的政治(67)如W.G.Forrest,“Theory and Practice”,Robert Gilpin,“Peloponnesian War and Cold War”,in Hegemonic Rivalry: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edited by Richard Lebow and Barry Strauss,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pp.23-50;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尽管在论证方法上存在理论先行的情况,但很难因此说国际关系学者只是将修昔底德“视为证明自身观点合法性的工具”(68)陈玉聃:《战争始于何处?——修昔底德的阐述与国际关系学界的解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80页。。那些试图用显微镜透视细胞构成的人与那些尝试用望远镜找寻天体规律的人同样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