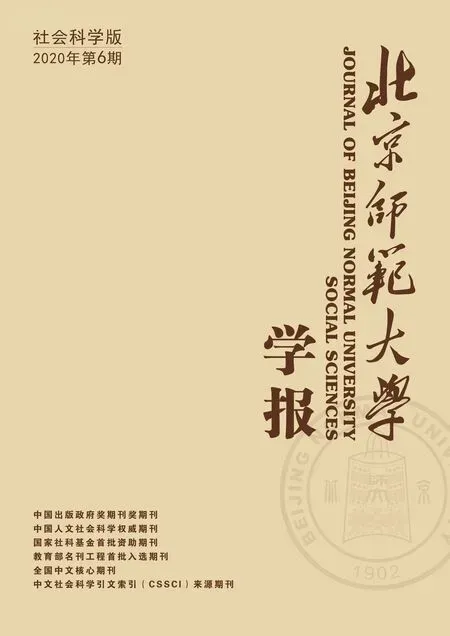维杜金德《萨克森人史》中的政治世界
2020-12-12侯树栋
侯树栋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一、问题的缘起
雷诺兹(S.Reynolds)在为《史学史研究指南》撰写的有关欧洲中古国家问题的章节中指出:一方面,学界对欧洲中古王国的经验研究有悠久传统;另一方面,有不少人却认为,把“国家”(state)一词用到欧洲中古时期,至少是大部分时期,是一种“时代错乱”(anachronistic)。因为,respublica(公共、国家)意识伴随西罗马的消亡而不复存在,中古社会的基础是私人纽带而非公共制度,只是到中古后期,“state”意义的国家观念才开始出现(1)S.Reynolds,“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Medieval State”,in M.Bentley,ed.,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London:Routledge,1997,p.109.。斯特雷耶(J.R.Strayer)就曾指出,古代希腊城邦、罗马和汉帝国都是“state”意义上的国家,但欧洲中古早期的蛮族王国则不是,因为它们建基于“对个人的忠诚而非对抽象或非个人化制度的忠诚”之上。“state”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从12世纪以后才逐渐成长,并为现代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J.R.Strayer,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13.。20世纪后半叶以来,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正是欧洲中古早期是否存在“state”意义上的“国家”?论者有很多分歧的意见,从中大体可见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强调,作为“state”意义上的国家,核心要素是公共权力(制度)与公共意识,蛮族王国显然不具备这些要素,因为私人间的纽带和习惯而非制度,才是蛮族王国的基础。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古早期史料中蕴含着秩序、权力的意识或观念,这些其实也就是国家意识或观念,只不过是以特殊的术语和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应当把蛮族王国纳入“state”的范畴讨论(3)B.Weiler and S.MacLean,eds.,Representations of Power in Medieval Germany 800—1500,Turnhout:Brepols,2006,pp.18-19(no.14).。弗雷德(J.Fried)和格策(H-W.Goetz)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被称作关于蛮族王国“国家性”(Staatlichkeit)问题的讨论。第三种观点指出,研究西欧中古早期国家,首先要关注的应是蛮族王国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国家定义。至于将其归入什么“种”或“范畴”,贴何种标签,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毕竟不是第一位的。即使讨论定义,也应作比较宽泛的界定,以保持研究对象的开放性(4)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学界关于中古早期国家问题的讨论成果甚多,这里不便一一列举,集中反映这一领域研究进展的是两部文集:S.Airlie/W.Pohl/H.Reimitz,eds.,Staat im fruehen Mittelalter,Wien:OAW,2006;W.Pohl und V.Wieser,eds.,Der fruehmittelalterliche Staat-europaeische Perspektiven,Wien:OAW,2009。。笔者认为,第三种意见或许能够更好地反映历史学家的研究实践。考察中古早期蛮族王国,要紧的是要首先考察这些王国的实际表现, 搞清这些王国本身的特点,然后再谈它们与后世国家间的联系与区别、共性与差异。
欧洲中古早期史料中的大量内容涉及战争与和平、信仰与皈依、秩序与权威等话题,这一类话题是那个时代很多文本的主题,这些内容事实上也就是蛮族王国的具体表现。用现代术语说,这些就是史料提供者笔下的政治世界。从这些史料中探寻非个人性质的抽象国家制度或脱离私人纽带的公共关系和公共意识,基本上是徒劳的,所以论者针对蛮族王国提出了“有王权无政府”、“有个人无制度”、“有私人无公共”、“有权力无政治”等一类论断。这些观点固有依据,但偏差显而易见。“私人”和“公共”、“制度”与“习惯”之间的界限在当时尚未清晰起来,在现代世界中彼此界限分明的这些范畴,在中古早期并不对立,而是相互包容。换言之,私人纽带、私人关系中蕴含公共关系和政治世界。由此观之,蛮族王国具有早期国家的一些特征。
德国学者格策总结了当前欧美中古史学界政治史研究的基本走势,指出政治史研究的焦点已从制度转向权力及其表现、象征、仪式甚至“表演”;政治文化研究日趋兴盛。与此同时,论者对历史书写及书写者意图和手法的关注远超以往。史家的焦点从证词(史料)转向了提供证词的证人,历史文本的措辞、叙述结构和内在其中的思想和意图,成为史家的中心议题(5)B.Weiler and S.MacLean,eds.,Representations of Power in Medieval Germany 800—1500,pp.19-24.。对格策概括的这种学术走势的是非得失,先存而不论。要指出的是,研究欧洲中古特别是中古早期的蛮族王国,需要借助这种方法研读史料,以窥文本作者有关秩序与权力的意识、心理及其特定的叙述意图和修辞技巧。但是,对文本的研读不应仅限于此。除了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史家还应求索作者的主观世界与客观社会的关系,揭示文本作者主观世界的社会基础。这样,从历史文本当中获得的就不只是文本作者的意识、意图及其表达手段,还有那个社会的缩影。循着这样的思路,本文拟对10世纪德意志一部重要史书,即维杜金德(Widukindi)的《萨克森人史》(ResgestaeSaxonica)作一番讨论(6)维杜金德(Widukindi),德译Widukind von Korvei,英译Widukind of Corvey。《萨克森人史》(Res gestae Saxonicae),德译Die Sachsengeschichte,英译Deeds of The Saxons。,探求作者在书中呈现的政治世界。
维杜金德(约925—973年)是10世纪德意志萨克森科维修道院的修士,《萨克森人史》是他的主要作品(7)本书德译本有多种,英译有: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tr.,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B.S.Bachrach and D.S.Bachrach,Washing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2014。本文引用据德-拉对照本: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in Ausgewaehlte Quell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Band Ⅷ,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aft,1971,同时参考英译本。《萨克森人史》一书的文献学史,参见该书英译本的导言。。本书是10世纪德意志最重要的史著之一,从中可获取有关10世纪奥托一朝政治史和军事史方面的大量知识。维杜金德的情况现在所知不多,只知他是萨克森一所名为科维(Corvey)的圣本笃修道院的修士,出身于萨克森高级贵族家族。维杜金德941年左右进入科维修道院,曾写有几种圣徒传记,但都没有传世。《萨克森人史》写于10世纪60年代,全书计有3卷,第1卷有41章,写萨克森人的起源与历史,详细描绘萨克森人与图林吉亚人和匈牙利人的战争,也叙述了萨克森人和法兰克人的关系。这一卷的后半部引入东法兰克-德意志国王亨利一世,通过展现亨利如何战胜匈牙利人、击败丹麦人并成功控制各地公爵等过程,显示作为萨克森人杰出代表的亨利的功业。第2卷有41章,第3卷有76章,这两卷集中写萨克森人的另一杰出代表,亨利之子、国王奥托一世的功业。第2、3卷着重描写奥托怎样在复杂险恶的内外形势中取得最后胜利,此起彼伏的内部反叛及奥托的应对是作者叙述的重点,也交叉记述奥托战胜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和丹麦人并干预西法兰克和意大利的过程。全书最初完成于967—968年,最后几章即70—76章的内容结束于973年奥托去世,所以这几章的内容显然是后来增添的。续写者是维杜金德还是另有其人,学界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每一卷书前有题辞,致献奥托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Mathilda),她在966年进入奎德林堡(Quedlinburg)一所圣本笃修女院修道。
维杜金德《萨克森人史》的主体内容是军事和政治史,这些资料对于认识10世纪东法兰克-德意志王国的价值不言而喻,所以此书一直以来为治德意志中古史和欧洲中古史学的学者所关注。鲍曼(H.Beumann)1950年出版专著(8)H.Beumann,Widukind von Korvey,Unterschungen zur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Ideengeschichte des 10,Jahrhunderts,Weimar:Boelau,1950.,从文献学和思想史角度对《萨克森人史》作了全面和精深的研究,被誉为经典之作,后来的研究往往是在鲍曼奠定的学术基础之上前行的。2002年巴格(S.Bagge)出版史学史专著(9)S.Bagge,Kings,Politics and the Right Order of the World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c.950—1150,Leiden:Brill,2002.,该书第一章专论维杜金德的《萨克森人史》。作者从各个角度考察维杜金德的历史写作,分析其意识和心理,关注其思维和写作特点,是为有关维杜金德的较新的研究成果。巴格在2012年又发表论文,剖析维杜金德在《萨克森人史》中对奥托一世形象的刻画,并将其与爱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对查理曼形象的塑造进行对比(10)S.Bagge,“The Model Emperor Einhard’s Charlemagne in Widukind and Rahewin”,Viator,2012,(2),pp.49-78.。还有学者探讨了维杜金德《萨克森人史》中的族群意识和族群建构(11)B.Scheidmueller,“Widukind von Corvey,Richer von Reims und der Wandel politischen Bewusstseins im 10,Jahrhundert”,Historische Zeitschrift,Beihefte,New Series,Vol.24,Beitraege zur mittelalterlichen Reichs-und nationsbildung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1997,pp.83—102;S.Latisos,“War and Nation-building in Widukind of Corvey’s Deeds of the Saxons”,in J.Koder and I.Stouraitis,eds.,Byzantine War Ideology between Roman Im perial Concept and Christian Religion:Akten des internationalen Symposiums,Vienna: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2012,pp.57—68.下文将结合特定问题,对论者有关维杜金德的具体见解进行讨论。。
二、《萨克森人史》中的族群与族群认同
论者通常认为,维杜金德的《萨克森人史》有两大主题,即部族史(萨克森人的起源和发展)和国王史(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的功业),全书内容由这两大主题交织而成。其实,两大主题的旨趣是一个,即颂扬萨克森人(当然包括作为萨克森人杰出代表的亨利与奥托)的“美德”与“业绩”。通观全书,维杜金德的书以鲜明的萨克森人的立场示人,作者明确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令人瞩目。全书记叙的是萨克森人的“事迹”,歌颂的是萨克森人的“勇武”和“智慧”。当维杜金德的叙事从萨克森人这一族群转入萨克森人的杰出代表国王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时,对萨克森人的颂扬与对国王的赞誉便合二为一。在维杜金德的笔下,亨利与奥托的“德”与“能”,不只是个人的,也是萨克森人这一群体的,是萨克森人的“优良品行”造就了东法兰克-德意志的杰出统治者亨利和奥托。由此可知,《萨克森人史》首先是一部萨克森人的部族史。维杜金德在第1卷开篇就说要致力于描写“我的家园和我的人民”(12)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21;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5.,这里的“家园”是萨克森,也是亨利与奥托的“祖国”(patria),这里的“人民”是萨克森人。作者强烈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于此可见。《萨克森人史》的叙事基石和逻辑起点,正是所谓“萨克森爱国主义”(13)巴格的书使用了“萨克森爱国主义”(Saxon Patriotism)这一词句, 参见S.Bagge,Kings,Politics and the Right Order of the World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c.950—1150,p.30。。
维杜金德直言他的写作是“扼要的、有选择的”(14)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17;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4.。他讲述的是在他眼中最能集中展示萨克森人之荣耀的历史事件,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国之大事”——战争。战争无疑是《萨克森人史》中的第一主题,这不仅仅表现在有关战争的篇幅上,更表现在全书的叙事逻辑上:萨克森人的强大、奥托王朝执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以及基督徒共同体的存在,无不以萨克森人能够克敌制胜为前提。在一个缺失强大中央权威的时代,各个族群冲突不断,战争频发,战胜对手成为族群生存的根基。这正是维杜金德进行写作的社会背景。他详细叙述了8—10世纪萨克森人与图林吉亚人、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的战争。对这些战争的记述保留着萨克森人的集体记忆,展现了萨克森人族群认同形成的复杂过程(15)S.Latisos,“War and Nation-building in Widukind of Corvey’s Deeds of the Saxons”,pp.57—68.。在维杜金德的书中,没有这些战争就没有萨克森人的发展和壮大,也没有亨利与奥托那些“丰功伟绩”。是战争哺育了萨克森人,并且造就了这一族群最杰出的代表亨利与奥托。萨克森人和东法兰克-德意志其他族群在他们的统率下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正是这些胜利为基督徒共同体的生存提供了根本保证,也为亨利与奥托执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在维杜金德的笔下,勇武尚战是萨克森人最杰出的品性,而这正是在频繁的战争中锻造的。甚至他对萨克森人起源和萨克森这个名称的解释已经隐含了萨克森人英勇善战的特点。维杜金德指出,有关萨克森人起源的情况虽然已经模糊不清,然而人们却普遍认为萨克森人是“古老而高贵的人”。他说在自己年轻时曾听到一种意见,认为萨克森人原本是希腊人,是亚历山大统率的马其顿大军的后裔。他还解释说,“萨克森”一词来自萨克森语“sahs”,意为“刀”,这是萨克森人随身佩带的主要武器,他们靠这一武器战胜敌人,开疆辟土(16)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p.23,25;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5,10.。维杜金德还通过不同族群间的比较彰显萨克森人的刚毅勇猛。法兰克人曾与图林吉亚人作战,前者请求萨克森人给予援助。当萨克森人前去支援法兰克人时,萨克森人的装束和武器令法兰克人既好奇又忌惮,最终萨克森人帮助法兰克人击败了图林吉亚人,法兰克人亲眼见证了萨克森人的不可战胜(17)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p.35,37;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18,20.。这些描写意味着,萨克森人的勇武尚战是与生俱来的品格,这是萨克森人能够战胜一切外敌的前提。这也表明,战争是族群关系的常态,也是族群集体记忆和认同形成的直接土壤。
对萨克森人以外的族群,维杜金德的记述有着亲疏远近之别。图林吉亚人一直是萨克森人的重要对手,萨克森人与图林吉亚人开战的“合理性”,在于萨克森人为解决生存问题而必须开疆拓土。他们与图林吉亚人先战后和,后又通过黄金换土地的“智慧”占有了图林吉亚人的大片土地(18)详见第1卷第5章,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p.23,25;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7-8。,并导致与图林吉亚人的再次冲突,最终消除了这个对手。维杜金德在讲述萨克森人与图林吉亚人冲突的同时,穿插着萨克森人、图林吉亚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萨克森人最终成为“法兰克人的伙伴和朋友”,他们共同对付图林吉亚人(19)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p.39,41,43;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21-24.。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是萨克森人在东部的主要敌人,构成对萨克森人的严重威胁。不过相对而言,维杜金德对萨克森人与斯拉夫人的战争场面渲染不多,对斯拉夫人笔下留情。匈牙利人则是萨克森人最强劲、恐怖的对手,维杜金德称之为“我们的宿敌”,所以他对萨克森人和东法兰克-德意志其他各族群与匈牙利人之间的战争作了大量生动和详细的描绘。亨利933年对匈牙利人的决战里亚德之战(Riade),奥托955年对匈牙利人的决战莱希费尔德之战(Lechfeld),都是维杜金德用浓墨重彩精心刻画的战争场景(20)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p.75,77;151,153,155,157,159;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56-57,123-129.。维杜金德把这两次战争视作为东法兰克-德意志奠定根基之战,因此用自己的笔将之传诸后世。大战之前亨利和奥托都发布了动员令,着眼大局,痛陈利害,调动宗教热情,号召人民奋勇抗敌。亨利指出:
各个方面的威胁曾经无休止地折磨着你们的帝国(imperiumvestrum),现在解放了。你们当然知道这个国家在内斗和外战的重压下痛苦呻吟。现在,承蒙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努力和你们的斗争,我们实现了和平与秩序,击败了蛮族并使之臣服。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团结起来击败我们的共同敌人阿瓦尔人。(21)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75;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54.维杜金德视阿瓦尔人为匈牙利人的同义词,见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47;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28。
面对匈牙利人的威胁, 奥托则对周围战士言道:
到现在,借助你们强壮的手臂和战无不胜的武器,我已经越出我的土地和帝国征服各地。现在我莫非要逃出我的土地和王国吗?我知道我们占优势的是兵力,而不是力量和武器。我知道敌人大多根本没有盔甲。对我们来说,更大的慰籍是,敌人没有上帝的帮助。鲁莽是他们唯一的保护。我们有神佑的希望。对于我们,作为几乎整个欧洲的主人,投降敌人是耻辱。我的战士宁愿光荣地战死疆场,如果说这应是我们的结局,也不愿像奴隶般生活,或者臣服于我们的敌人,或者像劣兽般遭受鞭打。我不再向我的战士说更多,除非我相信我可以用词句增添你们的力量和勇气。现在让我们开始这场刀剑而不是词句之间的对话。(22)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157;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127.
亨利大获全胜,赢得“祖国之父”和“皇帝”的称誉。奥托的胜利则是一场“此前两百年国王不曾取得过的胜利”(23)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159;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129.,他也被战士欢呼为“祖国之父和皇帝”(paterpatriaeimperatorque)。维杜金德的这些文字充分显示出他生活其中的世界和他的基本观念:族群构成这个世界的基本单元,族群关系特别是相互间的战争,是第一要事;领袖是族群的核心,领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于他能够统领人民战胜敌人,赢得战争;亨利与奥托的作为,是萨克森人“德”与“能”最集中的展现。这些内容进一步表明,维杜金德还有着比族群更广阔的视界。以“祖国之父”和“皇帝”称誉亨利和奥托,表达了他对更广泛秩序与权力的诉求。
三、维杜金德笔下的帝国与基督教世界
“萨克森爱国主义”固然是维杜金德叙事的基点,然而他的视界没有止步于此,他描绘的政治世界没有局限在族群和族群关系上。他笔下虽然没有出现可以等同于德意志王国的术语,书中所谓德意志(Germania,德译Deuschtland)是地理范围而非政治体,然而他使用了帝国、基督教世界、欧洲等概念,用以描述和指称更广泛的世界和秩序。所以维杜金德书中的政治世界是多层面的,族群只是这个世界的基础层面,其上有帝国、基督教世界或欧洲。
帝国一词在《萨克森人史》中多次出现,通常指称法兰克人的帝国。从对萨克森族群的认同再到对法兰克帝国的认同,维杜金德需要说明萨克森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对此,他在书中是有明确交代的。他说道,萨克森人与法兰克人早已建立友谊,曾共同对抗图林吉亚人。萨克森人皈依基督教以后,就从“法兰克人的伙伴和朋友”变成了法兰克人的兄弟,两者“在基督教信仰下成为一族”(24)⑤ 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45;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26,27.。王位更替时萨克森人和法兰克人的团结与相互信任,也展现了两者的一体。东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路易无嗣而亡,此时“整个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都希望萨克森公爵奥托登基称王⑤,他推辞不就,反荐法兰克人的公爵康拉德继承王位。康拉德临终又把“国家”交到萨克森公爵亨利手里(25)“国家”一词,维杜金德的用语是“rerum publicarum”,德译为“Gemeinwesen”,英译为“state”。,康拉德之弟爱伯哈德(Eberhard)领兄长之命,在“整个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面前立亨利为王(26)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59;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39.。
对“整个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的认同,意味着对法兰克帝国的认同,对帝国作为多族群共同体的认同。面临匈牙利人的威胁,亨利要求全体人民为保卫“你们的帝国”而战。亨利临终时指定其子奥托为继承人,由他统治“整个法兰克人的帝国”(27)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79;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59.。在叙述亨利之子奥托登基称王时,维杜金德再次强调这是“整个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选择的结果,并称奥托统治的是“整个法兰克人的帝国”(28)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p.85,89;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61,63.。《萨克森人史》有两处更是集中展示了维杜金德对作为多族群共同体的法兰克帝国的认同,其一是对奥托加冕宴会的描写,其二是对莱希费尔德之战这场对匈牙利人决定性一战的叙述。据他所述,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巴伐利亚和洛塔林吉亚四大公爵共同出席了奥托的加冕礼,并且在加冕宴会上象征性地担任宫廷职务,为奥托服务,以示各个族群和公国之间的团结与和谐。在莱希费尔德之战中,实际参战的萨克森人并不多,他们当时正忙于跟斯拉夫人作战。奥托的大军主要由巴伐利亚人、法兰克尼亚人和士瓦本人组成,与奥托建立了友谊的波希米亚人也组成了奥托大军的一个军团。然而,这一点没有妨碍基于“萨克森爱国主义”立场进行写作的维杜金德,全力歌颂奥托统领的大军对匈牙利人的胜利(29)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153;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124—125.。
《萨克森人史》中还出现了基督教世界和欧洲这些概念。对基督教的认同使维杜金德把萨克森人皈依基督教之前的宗教崇拜称作“祖辈的错误”,称皈依之前的萨克森人过着“错误的日子”,他们“一直被这种祖辈的错误束缚着,直至查理曼时代”。维杜金德称赞查理曼的“丰功伟绩”,认为他的强大与智慧无人可及,是查理曼把萨克森人从“错误”当中拯救出来,使他们皈依正确的信仰。基于此,维杜金德基本回避了查理曼对萨克森进行的长期的、残酷的武力征服活动,只是含蓄而简短地说道,查理曼“有时通过战争”迫使萨克森人皈依基督教信仰(30)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p.41,43,45;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22,23,26.。史学史上把维杜金德的《萨克森人史》通常作为基督教史学传统较淡,而所谓日耳曼部族传统较重的一部中古早期的史著,“萨克森爱国主义”一说一定程度体现了这种观点。但应指出的是,在维杜金德那里,基督教无疑是比“萨克森爱国主义”更加基础的逻辑起点。他对萨克森人的认同以此为前提,查理曼对萨克森地区的军事征服也才因此而正当化、合法化。
基于对基督教的信仰,维杜金德笔下的奥托不仅仅是萨克森人的首领和法兰克帝国的皇帝,还是基督教世界或欧洲的领袖。奥托的一个根本职责,在于实现所有基督徒的和平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希望(31)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p.89,165;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63,135.。有时维杜金德又用欧洲这一概念表达同一意思。他写道,匈牙利人曾经严重威胁着法兰克帝国,是祖辈和父辈的艰苦努力“使几乎整个欧洲获得解放”。他在第1卷的最后称赞亨利是“欧洲国王中的最伟大者”(32)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p.49,79;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59,63.,奥托则是“几乎整个欧洲”的主人(33)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157;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137.。在这些语境下,欧洲与基督教世界是同一的。
帝国、基督教世界和欧洲这些概念,使维杜金德对战争的叙述有了广阔的视角。内战(bellumcivile)和外战(bellumexternum)是《萨克森人史》中的两个重要范畴,蛮族是又一个重要范畴,它们是维杜金德的“内”与“外”之别意识的明确反映。所谓“内战”与“外战”的区别,已经超越萨克森人和萨克森公国的界限,甚至也超越东法兰克-德意志的范围。说到底,基督教世界才是维杜金德划分“内”与“外”,区别“我”与“他”的根本标准。
《萨克森人史》对内战的叙述集中在第2、3卷。他笔下的内战决非仅限于萨克森人的内部冲突,亨利和奥托与东法兰克-德意志各公爵的冲突,各公国之间和公国内部的冲突,都属于内战(34)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p.63,99,169;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45,73,138.。萨克森或东法兰克-德意志其他部族与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等所谓蛮族间的战争,则是“外战”。内战和外战的性质不同,这一点维杜金德非常清楚。奥托之子、士瓦本公爵柳多尔夫(Liudolf)和奥托的女婿、洛塔林吉亚公爵红发康拉德(Conrad the Red)联合反叛奥托,奥托的指控与叛方的辩护都把叛乱与蛮族的威胁作了区分,而把匈牙利人作为“共同的敌人”(35)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147;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117-118.。萨克森贵族小维希曼恩(Wichmann the Younger)等人串通蛮族搞叛乱,被宣布为“公敌”(36)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161;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132.“公敌”(hostibus publicis),德译为“Landesfeinde”,英译为“public enemies”。。在维杜金德的意识里,有分别适用于内战和外战的不同伦理。他叙述了奥托时期发生的几次严重叛乱:937—938年奥托的异母兄弟唐克马尔与法兰克尼亚公爵和巴伐利亚公爵的反叛;939年奥托的兄弟亨利和法兰克尼亚公爵及洛林公爵的反叛;953—955年奥托之子、士瓦本公爵柳多尔夫和洛塔林尼亚公爵的反叛。这些反叛活动既曰内战,就有适用于内战的伦理。维杜金德对这些反叛行为一方面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却很少严厉指责,反倒怀同情之理解,并且通过奥托对这些地位显赫的“冒犯者”的“宽恕”与“安抚”,来显示奥托的宽容与仁慈。维杜金德几乎不认为这些活动是不可宽恕的。但他对蛮族的态度就根本不同了。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是《萨克森人史》涉及的主要蛮族,维杜金德对待斯拉夫人的态度相对客气,还提到奥托曾与斯拉夫人的首领建立的友谊。不过,他对匈牙利人却十分严厉。他一直把匈牙利人作为对萨克森和基督教世界的主要威胁,突出匈牙利人的粗暴和凶悍。亨利和奥托的战前动员都诉诸基督教信仰,以充分调动人民的宗教热情,强调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的对立。莱希费尔德之战后对匈牙利几个首领的处决,表明适用于蛮族的伦理与适用于内战的伦理根本不同(37)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157;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128.。这也说明,基督教世界不仅仅是一个信仰的世界,也是政治世界。
显而易见,《萨克森人史》中的政治世界是多重的、复合的,族群是其基础性构成,其上有帝国,还有基督教世界或欧洲。当然,基督教世界或欧洲并非一种国家实体,但却是时人政治思维当中的要素,是维杜金德判断事务是非曲直的道德基准。维杜金德生活其中的政治体是东法兰克-德意志,也就是维杜金德说的奥托“帝国”。从“萨克森爱国主义”到对奥托帝国的认同,在维杜金德的思维中是一脉相承的。
四、维杜金德刻画的奥托帝国
《萨克森人史》表现的社会和政治思维是具象的,读者能够直观到的是作者对一件件具体事件的描述。有关国家、政府的一些现代概念,例如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法律与制度等,在《萨克森人史》中都具象化为对有关战争与和平、权威与秩序和信仰与皈依等话题的具体描述当中。不过,细究起来,可以看到书中的具体描述又显现着作者有关社会和政治的好恶和情愿,表达着他的追求与期待,其中传递着他对秩序与权力的诉求。如果说还是能够梳理出维杜金德社会和政治思维的基本逻辑,那就是:和平与秩序的存在有赖于权威,权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又取决于和平的实现和秩序的维护。
《萨克森人史》中的“主角儿”亨利和奥托,正是这种权威的化身。维杜金德是从几个方面塑造亨利和奥托的形象的:上帝的忠诚卫士,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平与秩序的维护者,宽厚仁慈的君父。《萨克森人史》第2卷开篇对奥托的涂油加冕典礼和加冕宴会具体而生动的描绘,集中展示了这些形象。这段著名文字成为解释奥托王权和维杜金德权力意识的重要材料。维杜金德说道:“整个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选择亨利的儿子奥托为他们的统治者,而奥托早已被其父指定为王”;达官贵人“向他宣誓效忠”,这样就按他们的惯例“将奥托认可为国王”。主持大典的美因茨大主教希尔德贝特(Hilderbert)宣称奥托为“上帝选定的、早由万民之君亨利指定的,现在由所有达官贵人认可的”统治者,并对奥托说,“上帝把整个法兰克帝国的全部权力授予你,以便实现所有基督徒的真正和平”。在奥托的加冕宴上,法兰克尼亚、巴伐利亚、士瓦本和洛塔林吉亚四大公爵象征性地分别充任宫廷职位,为新国王服务(38)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p.85,87,89;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61,62,63,64.。这段文字几乎没有明确交代有关国家制度方面的内容,书中其他地方也很少述及。此段文字倒是极富仪式感,对涂油和宴会仪式的渲染显示出的是仪式政治,其象征主义的味道颇浓:庄重、威严的加冕大典和盛大宴会,表现的正是奥托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欧洲中古早期有关王权正当性与合法性观念中的几大要素,即基督教元素、世袭权利和达官贵人的认可,都被仪式化地展示出来。
基督教元素在维杜金德的政治思维中占据何种位置,是学界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肯定维杜金德史著的世俗取向,即强调他的叙事其实在淡化基督教元素。二是强调他的基督教取向。还有论者采取折中观点,一方面突出维杜金德书中的基督教元素,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些元素的意义需置于特定语境下理解:维杜金德凸显的,说到底是亨利和奥托的个人魅力,基督教因素是为此服务的。上帝与亨利和奥托之间是一种个人式的关系;维杜金德没有这样的理念:亨利和奥托代表的是上帝确立的世界秩序(39)S.Bagge,Kings,Politics and the Right Order of the World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c.950—1150,p.89.。其实,这三种观点均可从《萨克森人史》中找到证据。亨利登基时并未领受涂油礼,尽管他解释说是自己德不配享这一圣礼,但这种“谦逊”还是让人们看到了亨利与教会刻意保持一定距离,进而也看到了亨利王权中的非基督教传统(40)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59;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39—40.。维杜金德的书还有一点令人关注,那就是他在书中只字未提奥托于962年在罗马称帝一事,这又导致论者的不同解释。有观点认为维杜金德未记奥托称帝是偶然,不能由此推断他否认皇帝头衔与基督教传统的内在联系(41)S.Robbie,“Can Silence Speak Volumes? Widukind’s Res Gestae Saxonicae and the Coronation of OttoⅠReconsidered”,Early Medieval Europe,2012,20(3),p.333.。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维杜金德帝国或皇帝观念中的非基督教传统(42)维杜金德在《萨克森人史》中主要是在征服并统治多个族群的军队统帅的意义上,而非基督教传统上使用皇帝一词的。东法兰克国王康拉德称亨利终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国王和很多族群的皇帝”(imperator multorum populorum),见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57;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38。亨利和奥托战胜匈牙利人之后都被战士称誉为“皇帝”,而且,维杜金德常以“皇帝”指称955年莱希费尔德之战大胜匈牙利人以后的奥托。。再有就是书中对很多事件给出的“人事”方面的解释。例如,在叙述战争时维杜金德重视双方的兵力和武器,并由此说明战争的胜败,这表明他的叙事时常不那么“宗教”或“教会”。不过,书中毕竟有很多关于基督教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是维杜金德社会和政治思维的逻辑前提,这一前提在书中时隐时显,但无论怎样并不影响国王的“功业”是“救赎史”的组成部分这一根本观念。分析维杜金德思维中的基督教元素,不应当从后世形成的宗教与世俗相互对立与矛盾的理念出发。在欧洲中古早期,宗教与世俗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一体的,宗教与世俗当然存在对立与矛盾的一面,然而这一面还远不突出,还不是时人竞相关注的问题。在维杜金德的眼中,亨利对教会涂油礼的婉拒,于其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不构成问题。《萨克森人史》叙事中所谓的宗教取向和世俗取向,都是后人的总结,它们在维杜金德的思维中不是相互对立与矛盾的两极,而是共存于他的历史叙事之中,是他表达奥托帝国之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两个维度。
欧洲中古早期蛮族王国的王位更替过程大都是世袭权利与权贵选举并存。维杜金德又是怎样看待王位更替过程中的世袭权利与权贵选举间的关系呢?对此,学界也有不少讨论。在《萨克森人史》中,世袭与选举是并存的,它们都是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来源。他提及法兰克人的老王过世后,老王之女、已嫁给图林吉亚人的国王的阿玛尔贝嘉(Amalberga)依据世袭权利要求王位(43)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31;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13-14.。然而,当身为萨克森公爵的亨利从法兰克人手里接过统治大权时,“血统”问题在维杜金德的意识中似乎又不是障碍。东法兰克国王、法兰克人康拉德临终时对自己的兄弟爱伯哈德道出了亨利掌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我们有能力调动和指挥正规军队和征召来的战士,我们有堡垒和武器,我们有国王的权标和王权要求的一切,就是缺少好运和资格。好运属于亨利,他堪掌王权。对国家的决定权掌握在萨克森人手里。”(44)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57;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38.维杜金德曾提到,康拉德登基时统治大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萨克森公爵、亨利之父奥托手里。在这里,维杜金德的逻辑是:萨克森两代公爵的“德”与“能”都堪配王位,所以亨利登基是正当的、合法的。维杜金德多次提到亨利指定其子奥托为继承人(45)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p.79,85,87;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58,61,62.,世袭权利自然是奥托登基称王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这里的世袭权还不是能自动带来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一种严格的法律制度,维杜金德没有这样的意识。他对奥托登基大典及其加冕宴会的详细描述表明,他的关注点既不在君权神授上,也不在世袭继承上,而在仪式本身和奥托与周围众人的“表演”上,尽管他明确指出了奥托是经由上帝选定并由亨利指定的继承人。仪式的象征意义在于:作为维杜金德心目中的伟大君主,奥托登基体现的是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的“三位一体”:君权神授、世袭权利和达官贵人的认可(选举)。所以仪式表现出来的奥托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由此来看,论者争论维杜金德究竟是更看重奥托的世袭权利(世袭制),还是达官贵人对奥托王权的认可(选举制),意义就不大了,这两方面在维杜金德那里本不是对立的两极。不过,从维杜金德对奥托登基和加冕宴会的描述过程看,他似乎更加彰显众人的认可,这种认可是亨利和奥托通过克服内外一切困难,成功应对挑战赢得的。这又是维杜金德贯穿全书的逻辑:亨利与奥托的权力根基,在于他们都继承并集中体现了萨克森人的勇武和智慧,他们是成功的统治者,是凭借自己的功业赢得特殊地位和权力的。
不少学者强调,个人化而非制度化的统治是奥托帝国的显著特点,这是学界的主流看法(46)D.Bachrach,“Exercise of Royal Power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The Case of Otto the Great 935—973”,Early Medieval Europe,2009,17(4),pp.389-391.作者驳斥了把奥托王权归结为非制度化王权的观点。。而《萨克森人史》似乎是对这种观点的有力支持。论者指出,个人是维杜金德社会和政治思维中的基本单元,个人之间的联系和友谊构成社会网络,领袖是克里斯玛式的个人魅力与民众支持和忠诚相结合的结果。“政治行为可以基本理解为个人利益,社会是个人的联合,这种联合依据的是个人利益,社会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关系和个人间的忠诚,几乎没有任何正规的政治制度。”(47)S.Bagge,Kings,Politics and the Right Order of the World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c.950-1150,p.94.《萨克森人史》的奥托统治,看上去似乎完全是靠个人关系维系并通过个人关系实现的。公爵、伯爵等显要人物对国王的忠诚及后者对公爵、伯爵等显要人物地位和尊严的维护,似乎就是上层人物之间的基本纽带。个人对自己地位和荣誉的追求与维护、个人之间的仇恨与友谊、忠诚与背叛,由此引发的矛盾和战争,以及惩处、宽恕与和解,所有这些构成了维杜金德书写的上层人物的基本活动。从《萨克森人史》中寻求制度方面的内容几乎是徒劳的(48)书中提到6世纪初萨克森人的社会制度,还述及遗产继承制度,见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p.43,96,97;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p.25-26,70-71。但全书这样的内容很少。。维杜金德一方面维护国王的尊严和荣誉,因此批评叛乱者背叛忠诚,破坏和平;另一方面对一些背叛行为也表现出一定的理解与同情,因而赞赏奥托对背叛者的宽恕,称此为国王一直以来的仁慈与宽厚的体现(49)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97;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71.。奥托兄弟亨利的反叛是奥托上台后几次严重的内乱之一,给奥托委实造成不少麻烦,但奥托最终还是原谅了亨利,并授予他财产和权利(50)Die Sachsengeschichte des Widukind von Korvei,p.115;Widukind of Corvey,Deeds of the Saxons,p.88.。奥托对冒犯者的安抚使他们不因曾经的背叛而失去其“高贵者”的地位与尊严。
从以上内容看,奥托的统治的确还不是基于脱离个人关系纽带的一套制度之上的统治,统治权尚包裹在个人关系的纽带之中。这正折射了那个时代政府制度还在形成之中。所以尚不存在摆脱个人关系纽带的制度,因而也就谈不上基于一整套制度之上的统治。但由此推论在奥托帝国中制度与个人、公共与私人是相互对立的两极,进而只是从个人关系的纽带看奥托帝国,则有失确当。教会的精神权威、贵族的社会统治地位,当然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社会制度,它们从根本上制约和主导着权力秩序,制约和主导了那个时代的政治世界。它们作为一般规范当然也制约和主导着维杜金德的社会和政治思维。他在书中呈现的上层人物之间所谓的个人关系,并不能超出这个一般规范。最显赫的一批权贵,包括教会上层,齐聚奥托登基大典和加冕宴会,展现的正是时代的一般规范:贵族政治的主导地位。既然是贵族政治,国家就需国王与其他权贵的共治,秩序就需国王与其他权贵的共维。国王的“荣誉”与“尊严”不得冒犯的同时,国王也需与其他权贵共享“荣誉”与“尊严”。看上去,似乎是个人意识主导着维杜金德的思维,但这是蕴含着公共意识的个人意识。出现在《萨克森人史》中诸如“整个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整个法兰克帝国”、“所有基督徒”、“基督教世界”、“国家”(respublica)、“共同的国家利益”、“公共与私人事务”和“公敌”等表述,以及维杜金德意识中的“内战”与“外战”之别,表明他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多层面的政治世界,不过这又是一个还没有脱离个人关系纽带的政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制度与习惯、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还不分明,因而彼此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这里的“制度”与“个人”之间不存在僵硬的界限。
本文的讨论说明,维杜金德《萨克森人史》的政治世界是由族群、帝国、基督教世界或欧洲构成的,因而是多重的、复合的。族群是这一政治世界中的基础性构成,其上有帝国、基督教世界或欧洲等范畴。“萨克森爱国主义”反映了维杜金德的族群认同,然而这一认同又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法兰克帝国、全体基督徒、基督教世界或欧洲等范畴,反映了他更广阔的政治视界,体现了他对更广泛秩序与权力的诉求。基督教世界或欧洲并非一种国家实体,但却是维杜金德社会和政治思维中的要素,是他判断事务是非曲直的根本性的道德基准。他笔下的“内战”与“外战”之分以及蛮族这一范畴,都源于这一基准。奥托帝国是维杜金德生活在其中的政治体,是他重点描绘的政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宗教与世俗、世袭权利与权贵选举、制度与个人、公共与私人,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范畴,其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奥托帝国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体。总之,维杜金德《萨克森人史》表现的是一个与二元对立思维不相协调的政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