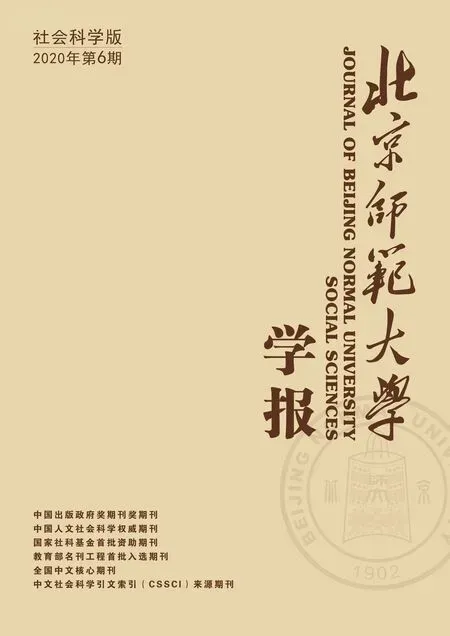人类政治的远古根脉
2020-12-12宋洪兵
宋洪兵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1)〔美〕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赵芊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页。研究人类政治思想,必先研究人类政治所面临的困境,政治思想是对政治困境的理论回应与反思。人类政治困境具体表现为一种走钢丝式的艰难处境:“人们在实现一己欲望和承认社会责任之间难以保持平衡。”(2)〔英〕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人之上升》,任远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政治思想史,必然以人类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人类政治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人类为此所提出的种种设想,构成了政治思想史的主要议题。研究人类政治困境,须先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考察前人类时代的群体秩序以及支配—服从关系。美国著名政治观念史家沃格林指出:“人类生活在生死方面的生存基础,实际上是最确凿的——虽说不是唯一的——本源。”(3)〔美〕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一,段保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8页。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既关涉文化层面的生存,亦关涉生物学层面的生存。仅仅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无法深入理解人类政治的来龙去脉。人类政治的根脉,可以追溯到人类祖先尚处于动物世界的时代。在那时候,人类政治蕴涵的种种困境就已初露端倪,人类祖先亦在生产生活中开始了种种实践性的探索,并由此形成了后世人类思考政治问题的“路径依赖”。
如何讨论史前时代的人类生活?这是一个问题。众多生物学家、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做出了巨大努力。19世纪的人类学家摩尔根曾以尚未“开化”的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为研究对象,探求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与生活状态。这种思路,曾深刻影响了恩格斯,他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及马克思据此做的读书笔记,撰写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曾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4页。人类学家认为,对现存部落社会的社会运转规则及生活状态的人类学调查,就可以推测史前人类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转规则。但是,人类学调查,针对的是已经脱离动物界的智人生活,这些所谓“原始人类”已经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懂得用火,并能制造工具等,他们只是进化缓慢的一类智人。现代人类正是由智人进化而来(5)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曾指出:“总的说来,在20世纪结束之时,人们倾向于承认智人(Home sapiens)是一种不断上升的灵长类,承认智人具有生物特性。”参阅〔美〕爱德华·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毛盛贤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人类学调查,可以为现代人推测人类的智人祖先的社会生活状态提供可能。问题在于,现代人类的政治生活仅仅可以追溯至智人祖先吗?前智人时代的人类祖先,是否在很多层面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智人祖先呢?社会生物学家的研究,进一步将对人类社会及其政治根源的考察,深入到人类祖先尚未脱离动物界的时代:人类天性以及人类政治,具有生物学的特征,这并不因人类进化而有所改变(6)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著作有:〔美〕爱德华·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毛盛贤等译;〔美〕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英〕苔丝蒙德·莫利斯:《裸猿》,余宁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只有骨头和化石,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远房表亲那里对我们祖先的行为有所了解。”(7)〔美〕卡尔文:《大脑如何思维:智力演化的今昔》,杨雄里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在自然界中,黑猩猩、猿猴等灵长类动物与人类具有基于生物特性的远亲关系,具有高度的亲缘性与相似性:“人和黑猩猩拥有共同的祖先,但黑猩猩不是人的祖先,两者在数百万年前已经分道扬镳。”(8)冉浩:《动物王朝:自然选择下的群体智慧》,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312页。“人类的心智和非人灵长类的心智之间存在进化上的连续性。”(9)〔意〕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猿猴的把戏》,吴宝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5页。“不管你是否接受”,我们人类所属的科“就是一堆巨猿”(10)〔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人类进化的过程,无可避免地受到各时代、各地域“文化”的影响,但其源自动物时代的某些社会特质,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政治生活。
前智人时代的人类祖先,与众多灵长类动物一样,过着一种竞争性的社会生活。群居动物具有社会性,也具有鲜明的竞争性。灵长类动物不仅具有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而且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其社会性体现在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群体生活,涉及不同个体之间的交往,涉及支配与服从,涉及争斗与结盟,涉及亲情,涉及性与欲望。社会性必然伴随竞争性,具有影响力的个体会尽力争取群体中的高级地位以便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以及性特权。群体生活天然地需要一种基于支配—服从权力结构的等级秩序。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属于灵长类动物,而且天生是一种群居动物。此外,大象、狮子等高级哺乳动物,也过着群居生活,也同样涉及支配—服从、合作与竞争的社会秩序问题(11)〔美〕凯特林·奥康奈尔:《大象的政治:分层社会中的奋斗》,刘国伟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通过观察和研究群居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的生活习性以及社会秩序特征,能恰当地推断史前人类甚至前智人时代的各种社会特质,从而对于深刻理解人类政治的起源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综合来看,非人的灵长类动物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政治问题:其一,社会秩序;其二,权力斗争与权力更替;其三,政治技巧及策略;其四,所谓“政治美德”。这些问题均为人类政治思想领域被反复思考和追问的核心话题。人类祖先早在动物时代,就已形成了“政治”的雏形。
二、以支配—服从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秩序
人类政治思想的终极目的,在于塑造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实现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独居动物,因为没有群居生活,故群体秩序并非其生存繁衍所必需。以独居动物为意象创造的自由自主观念,实则人类自我意志创造的虚幻故事,并不符合包括人类在内的群居动物的生存法则。群居动物则不然。一种聚集性的群体生活,必须以稳定的群体秩序为首要前提。没有秩序就没有稳定、没有和平、没有安全。作为动物的第一本能,维持生命的存续这一诉求使得群居动物本能地渴望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社会性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如黑猩猩、猿猴,其他非灵长类动物如大象、狮子等,均有稳定的群体秩序。人类种种形式各异的政治思想,若是指向一种完全自主毋需秩序的生活,势必具有反群居、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特质。绝大多数政治观念,均不反对群体秩序之于人类生存繁衍之必要性,只是在需要何种群体秩序层面,存在着各种分歧。如果说生存法则是所有动物个体的第一法则,那么稳定的群体秩序则是群居动物的第一法则。“作为灵长目动物,我们早已负载着等级制,这是灵长目动物生活的基本方式。”(12)〔英〕苔丝蒙德·莫利斯:《裸猿》,第95页。人类社会亦不例外。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也是第一法则。作为个体的生存诉求与作为群体的稳定秩序,构成了群居动物的必然生存境遇。当个体意识处于生命本能诉求时,群体的秩序稳定受到的挑战压力会很小。个体的抗争目标往往指向争夺群体支配权,而非质疑群体秩序本身所具有的强制特征与等级秩序。
群体秩序之形成,不是任何人为意志的结果,而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故毋需做任何哲学论证。这是一个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即便要论证,顶多也是做一种纯粹生物学层面的原因探究。“动物之所以要聚居在一起,肯定是因为它们的基因从群居生活的交往中得到的好处多,而为之付出的代价少。”(13)〔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就此而论,那些讨论人类为何能群的哲学论证,基本属于一种虚构的想象,意在表达一种价值立场而非一种人类社会曾经确实经历的客观事实。比如,霍布斯、卢梭意义上个体让渡权力的契约论,就是违背人类进化事实的理论假设。沃格林在阐述想象性的“小宇宙实在”(一种相对于宇宙神性秩序的人类社会秩序)时,就将“契约理论”视为一种基于法学模型构造出来的且受以色列约(berith)观念影响的政治观念,而以色列的约观念的底色则是犹太人与上帝之约(14)〔美〕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一,第68、135页。。毫无疑问,上帝是人类杰出想象力的产物。若不依据事实而进行的假设,即便产生力量,也是类似宗教信仰那样的信徒力量,而非基于客观事实而确立的政治原理。这是一种“文化适应”,而非“生物学适应”(15)〔英〕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人之上升》,第21页。。依据某种想象的理由来论证人类需要的价值,是人类政治特有的现象,但这并不影响人类作为一种竞争性的群居动物基于客观事实所天然具有的政治属性,也即:在一种支配—服从的秩序结构中以利益或权力为核心的竞争与合作。人类祖先,从未有过完全外在于群体秩序的单独个体,更不可能有基于单独个体协商的契约。群居动物之所以选择群居,根本原因在于有利于保障个体安全。卡彭特(C.Ray Carpenter)发现,社会生活为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对抗食肉动物的进攻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安全保障。有一次在巴罗·科罗拉多岛,他看到一只年幼的吼猴被一只美洲虎攻击,它随即发出悲惨的叫声,很快得到三只成年雄性吼猴的援助。钱斯(M.R.A.Chance)也指出,猴和猿的聚集一般是为了抵御被捕食的命运(16)〔美〕爱德华·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第489页。。基于保全生命的安全需求是社会性动物过群居生活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群体秩序,离不开以支配—服从关系为核心的等级结构。稳定的支配—从属结构,能够有效地平息各种争端。“稳定的等级秩序是群体中的和平与和谐的一个保证。”(17)〔美〕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第131页。否则,秩序就会因互相争斗而陷入混乱。支配—服从结构必然伴随社会分层与等级系统。社会分层与等级系统是稳定秩序的必备要素。这构成了多数群居动物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在大象群体中,存在着一种清晰的等级,存在着与年龄、体格甚至血缘密切相关的支配与服从关系(18)② 〔美〕凯特林·奥康奈尔:《大象的政治》,第33、81,3页。。“像众多其他动物一样,大象形成了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减少稀缺资源引发的冲突,例如水、食物,以及配偶。”②非洲狮群也存在着严格的等级结构(19)星巴:《守护狮群:星巴非洲野保手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非洲的青山:《超级狮群》,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版。。在灵长类动物中,黑猩猩的社会结构更是充满了复杂的支配—服从关系,以至于研究者将黑猩猩的行为用马基雅维利的学说来解释(20)⑦⑨ 〔美〕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第4、214、171页。。更有学者在详细探究了灵长类动物的行为特征之后,断言:“支配性和从属性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概念,只存在于行为研究者的头脑中。相反,它们深深地扎根于头脑和人类的身体中,也扎根于许多动物的头脑和身体中。……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的灵长类,都不可救药地迷恋支配和统治,虽然他们不需要意识到这一点。支配性深入人性的最深处,因此幻想没有支配性的社会关系是不现实的。”(21)⑧ 〔意〕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猿猴的把戏》,第63、54页。稍有例外的是蜜蜂。蜜蜂过着一种群居生活,但蜂后除了分泌一种“蜂后物质”以压制其他蜂后成长之外,对其他工蜂和雄蜂并不具有支配权力。但在蜂后争夺过程中却呈现出异常残酷的“优胜劣汰”场景(22)〔美〕托马斯·D·西利:《蜜蜂的民主》,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4、46页。。在支配—服从结构中,始终存在着作为权威的支配者、较高地位者以及低地位者的等级系统。
在支配—服从结构中,又会产生如下问题:谁来支配?支配者应该具备怎样的资质?被支配者凭什么服从?
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动物界盛行“最强者为王”的原则。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就认为,动物界奉行“最强者为王”的法则,而人类社会则更多强调宽容与亲和力:“与低于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们恰恰相反的是,一个人若想受尊重就必须慷慨大方或宽宏大量。”但是,弗朗斯·德瓦尔却主张,萨林斯的观点如果用在狒狒或短尾猴的话,他差不多是正确的;“但若是就与我们最接近的亲戚——类人猿来说,事情就要复杂得多,也跟人类的情况相似得多了。近来,西田利贞描述了一个关于马哈尔山上的一只雄1号黑猩猩的案例:这只雄黑猩猩通过精心设计的‘贿赂’系统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并使自己的地位维持不变的时间长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超过了10年)。他的做法是:有选择地向那些为他反对潜在的挑战者提供支持的个体分发肉食。”⑦在黑猩猩群体中,并不完全奉行“最强者为王”的原则,某个个体欲取得支配地位,除了身体力量强大之外(并不一定强大到无人能敌的地步),更多的因素还包括合群能力、在弱势群体遭遇欺凌时的保护能力、宽容与分享能力以及恰当运用策略的能力。简言之,黑猩猩的支配者除了应该具备强大的身体能力为群体成员提供安全保障外,还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必须获得群体成员的拥护和支持。这种依据实力博弈原则形成的支配者与服从者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群居动物包括人类社会政治最为隐秘的内核,姑且称之为“没有契约的契约论”。聪明的支配者总是会权衡自己的统治力量与被支配者的反抗力量之间的对比,然后采取恰当的策略来化解或消除反抗力量。
作为被支配对象的群体成员为何会服从?原因很简单,因为恐惧、利益或忍辱负重。服从或忠诚能够维护个体利益,至少不必付出代价。不服从,意味着对抗或挑战,势必遭到支配者及其支持者的排斥和打击。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选择对抗或挑战,将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害。“对于从属者来说,支配结构的好处在于能够减少损失。”⑧恐惧是一种动物本能,因为恐惧受到惩罚而选择服从,也是一种自然法则。当然,支配者负有保障群体安全的职责,使全体成员免遭其他群体的侵害。同时,支配者还应该维护群体内部的秩序,为弱者提供帮助,避免出现霸凌现象。此时支配者扮演着维护群体和谐与公正的形象。“一个领袖能够得到群体成员的支持和尊敬,是以他对群体秩序的维护为交换条件的。”⑨若是支配者总是偏袒或残暴对待群体成员,久而久之就会失去群体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和认可,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被其他有能力者取代。就此而言,社会动物界的支配者,一般都会采用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来实现其统治。当然,也有不甘人后的被支配者,忍辱负重,默默地观望形势,等待时机,期待有朝一日取而代之:“富有耐心对臣服者来说,就是美德”(23)③④ 〔意〕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猿猴的把戏》,第54、113、106-113页。。
在非人类的灵长类群体中,人类政治涉及的正当性问题,已经呈现于它们的社会行为之中。人类祖先尚未与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时,没有神圣的宗教,也没有荣誉感与耻辱感,更没有所谓政治美德与政治技艺的观念,但它们在实际的生活与行为中已经产生了谁来统治、为何服从等政治哲学问题,并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探索。当人类产生政治观念并反思人类政治正当性问题时,人类祖先的生存经验可以给出至关重要的提示与启发。
三、支配者的权力斗争与权力更替
群居动物的支配—服从等级结构,必然存在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权力更替是如何实现的?当然,这离不开群体内部的权力斗争。社会生物学家发现,大多数灵长类动物“有一个严格建立的社会等级制,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雄性统治着一个群体,其余的则在其下分列在不同的从属层次上。当领头的雄性变得太衰老而无法继续统治的时候,就会被一个较为年轻健壮的雄性推翻,于是年轻的就接过群体首领的衣钵(在有些情况下,篡位者真的接过了衣钵,长长的毛发长成了披肩的样式)。由于群体始终聚在一起,首领的暴君角色始终起作用。但是尽管这样,它常常是群体中最健康,最整洁和最有性感的猴子”(24)〔英〕苔丝蒙德·莫利斯:《裸猿》,第96页。。权力斗争伴随着权力更替的过程:“不经历激烈的搏斗,雄性首领从来不会放弃它们的地位,因而挑战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周,甚至几个月。”③
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曾详细分析过灵长类动物群体中“出人头地”的权力更替现象。他通过长期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及行为特征,并结合其他社会生物学家的研究,总结出三种“出人头地”现象:其一,“低调的外来者”。一只雄性猕猴离开原来的圈子,加入新的群体成为社会底层的一员,以“论资排辈”的方式逐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如果有才能或足够幸运,就有可能成为雄性老大,维持几年“猴王”统治,然后被其他同类取代。在达里奥的例子中,一个叫“比利”的雄性猕猴排名到老二地位时,老大忽然被做实验的人类研究者带走,以致猴群出现“权力真空”,比利抓住时机,想顺理成章地成为老大,然而却遭到地位仅次于比利的另外一只雄猴与其他高地位雌猴群体的围攻,最终被驱逐出了猴群,一年之后孤独而死。其二,“虚张声势”的外来挑战者。一只叫“兰波”的雄性长尾猴在身强力壮的时候赶走了老猴王,开始了它为期两年的统治,直到一个新的单身陌生猴来挑战它,并使它身受重伤,结束了它的统治。它被逐出猴群。伤愈之后,孤独的它再次挑战其他猴群,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受伤而死。其三,“年富力强的本地挑战者”。一只名叫“马克斯”的雄性长尾猴,低调而谨慎地生活,用两年时间观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最终在一天早晨信心十足地向雄性首领发起挑战,虽然雄性首领在雄性老二的支持下打败了马克斯,但它并未灰心丧气,在随后的两个月里不断挑战猴王,最终成功迫使猴王放弃统治权,落荒而逃④。
美国生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荷兰阿纳姆的布尔格尔斯动物园的大型户外黑猩猩群落圈养区。他生动描述了这个黑猩猩群落两次争夺雄1号的权力更替过程,呈现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历史编纂”特质。第一代雄1号叫“耶罗恩”,第二代雄1号叫“鲁伊特”,第三代雄1号叫“尼基”。在长达两个多月的不断权力争夺战中,鲁伊特与尼基结成一种“开放式同盟”,在有效孤立耶罗恩的情况下,鲁伊特成了领袖,尼基成了名副其实的雄2号,耶罗恩失去了统治权,它向鲁伊特表示臣服,成为雄3号。此时,雄2号尼基与雄1号鲁伊特的竞争日益激烈起来。丧失统治权的耶罗恩显然从尼基与鲁伊特的竞争中受益,他对尼基表示顺服,但却挑战鲁伊特,最终顺利将尼基推上雄1号的宝座,鲁伊特被取代。耶罗恩则通过扶持尼基而获得了类似“贵族”或“丞相”的地位:“尼基占据了最高职位,而耶罗恩则履行着控制群体内局势的职责,同时也享有与此相随的权威。”(25)两次权力更替的整个过程,详见〔美〕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第89-175页。德瓦尔的深入研究,得到了《裸猿》作者莫利斯的高度赞赏。莫利斯在为《黑猩猩的政治》一书所写的推荐序中认为,人类与黑猩猩这个多毛亲戚之间具有远大于人们之前所预料的相似性,最为相似之处就在于政治策略与权力斗争:“在我们仔细研究过后,猿类就会向我们展示:他们是擅长精妙的政治策略的。他们的社会生活充满了权力接管、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网络、权力斗争、联盟、分而治之的策略、联合、争端仲裁、集体领导、特权与交易等等,那些在人类世界的权力走廊中出现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在一个黑猩猩群体的政治生活中发现其胚胎的。”(26)参阅莫利斯为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一书写的序。〔美〕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第2页。耶罗恩、鲁伊特及尼基“三角关系”的权力斗争过程充满复杂性。1980年夏天,耶罗恩与雄1号尼基关系破裂,鲁伊特再次趁着权力真空夺取了统治权,又做了十个星期的雄1号。充满戏剧性与悲剧色彩的结果是,耶罗恩与尼基再次结盟,并在一个夜晚重创鲁伊特,咬掉了它的手指和脚趾,使其遍体鳞伤,更严重的是,它们还摘除了鲁伊特的睾丸。鲁伊特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27)⑥⑦⑧ 〔美〕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第249-251、91、194、190-194页。。
黑猩猩之间的权力斗争,甚至会演变为两个内部分裂群体之间的“内战”,著名的“贡贝战争”即是显例。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在非洲的原始森林观察黑猩猩长达38年之久,她尤其喜欢贡贝的一个叫卡萨克拉的黑猩猩群落。1970年之前,这个群落的黑猩猩相当团结,但随着一只高大威猛的“族长”老黑猩猩去世,群体内部分裂为两个族群,并在1974年正式“开战”,开始了长达4年的战争。直到1978年,较强的族群大败较弱的族群,并将它们全部杀死,整个族群被消灭(28)冉浩:《动物王朝:自然选择下的群体智慧》,第311-312页。。
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权力斗争的目的,当然在于取得支配权和实际利益。权力更替过程,往往伴随着权力斗争。问题在于,取得支配权能够获得什么利益?或者,支配权对于人类近亲来说,为何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支配权能够为灵长类群居动物的首领带来的好处有:吃到更好的食物,活得更长寿、更健康(29)〔意〕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猿猴的把戏》,第115页。。通过观察,生物学家发现,黑猩猩的首领总是得到其他成员表示臣服的恭顺“问候”(发出一种咕噜声),还可以时不时地对它的“臣民”进行威胁性的武力炫示。身居统治高位的雄1号的举止亦显得不同凡响,对此,德瓦尔甚至有非常传神的描写:“在耶罗恩占据最高统治地位期间,他的毛发总是略微地竖立着的,即使在他不卖力地进行那些威胁性武力炫示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他走路的时候总是迈着一种缓慢而沉重的夸张的步伐。这种让躯体看起来显得大而沉重因而具有欺骗性的习惯性做法是黑猩猩中的雄1号普遍具有的一个特征。……每当有其他个体将先前占据这一位置的个体取而代之时,他们都会这么干。”⑥权力能够给支配者带来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与实际上的好处。支配者能够让其他成员在态度和行为上对其表达恭顺和谦卑,而支配者则可随其本性而少有顾忌。一旦其他成员不够恭顺或故意冒犯时,支配者则可凭借手中权力对其实施惩罚。当然,最大的好处或最具吸引力的好处是,身为雄1号享有性特权:“雄性的兴趣集中在性与特权上。他们谋求权力的动力来自雄性的等级地位决定性的优先权这一事实”⑦。手握权力的支配者能够独占或优先与异性交配并生育自己孩子的特权。其他雄性只有在支配者默许或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能与异性交配⑧。性的原始欲望与权力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
权力野心,不仅仅对于人类,而且对于人类尚在动物时代的祖先,更对于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特别是黑猩猩群体,都是一种政治本能。就此而论,《韩非子·五蠹》讲尧舜禅让的原因在于尧舜时代物质条件差,身为天子却不能享受更为丰富的物质待遇。他的意思是当权力与利益不相关时,权力就没有吸引力,所以尧舜才会轻易将天子之位让出去。毫无疑问,韩非子的观念对于审视权力野心问题是一种洞见。然而,韩非子想象出来的权力观与人类历史的实际情况还是具有很大的差距。早在人类祖先那里,权力所伴随的各种优越感及现实利益,就已成为一种被人觊觎和争夺的稀缺资源。
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权力斗争与权力更替过程中,参与权力斗争的个体的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能力不仅仅意指个体的强壮,同时还包含该个体能否获得群体多数成员的支持和拥护。如果依靠身体强壮而迫使其他成员臣服可以称为“权力”的话,那么获得群体多数成员的支持和拥护,则可称为“影响力”。光有“权力”是不行的,还要有“影响力”。当然,身强力壮往往能够为自己产生“影响力”提供良好的先决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身强力壮就可以包打天下。“体力并非决定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唯一因素,而且,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它不是最重要的因素。”(30)〔美〕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第103页。在阿纳姆的黑猩猩群体中,鲁伊特的体力最为强悍,但它却被耶罗恩与尼基的联盟对抗,并且日益孤立,最终失去首领的统治地位。
人类政治中的改朝换代问题,革命与改良问题,涉及权力斗争与权力更替这一古老的政治议题。成功推翻前一任统治而继任的统治者,均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他们的政治才能,并不在其武艺高强,而在于他们能够发挥其政治影响力,能够调动群体力量战胜对手,从而获得统治权。这应该是人类政治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类政治与黑猩猩政治的最大区别,不在是否有权力野心、权力斗争,而在人类还有一套理想化的道德说辞。至于如何从德性的层面来装饰这一政治实情,则构成了人类政治思想史一幅美丽而漫长的画卷。人类政治以及政治思想的实质,并非改变了远古祖先的政治议题,而是在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中为这些议题提供理论论证而已。
四、合作与竞争的 “政治技艺”
权力斗争,离不开政治能力和政治智慧。人类政治如此,人类祖先的生存逻辑亦如此。最重要的政治能力,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个优秀的政治参与者,必然具备卓越的政治能力:发现问题并分析症结,迅疾提出解决方案并在实践中完美解决问题。这是一种结合现实条件来分析与思考的重要能力,需要独到的政治眼光和丰富的政治经验。作为人类近亲的黑猩猩的行为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洞悉人类政治奥秘的途径。
黑猩猩已经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表明这个人类近亲已有相当程度的智力水平。科学家发现,多数狗不能解开将其系于树上的皮带,小猴子无法解开笼门上的揿扣,但类人猿却有可能做到。所以,关黑猩猩的笼子必须要用锁,并且钥匙还不能留在那里。“猩猩会行使骗术,即猜测另一只猩猩可能在想什么,并加以利用。”(31)③ 〔美〕卡尔文:《大脑如何思维:智力演化的今昔》,第21、37页。某些猿类甚至具有“自我辨认”的能力:“黑猩猩、倭猩猩和长臂猿能从镜里认出自己,有的当即就行,有的则需几天时间。”③萨维奇·伦堡说:“我知道猿类每时每刻的行为都表明它们似乎有心智,与人类的心智很相似。它们可能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多、那么深,不如我们那么能作超前计划。猿在捕食猎物的过程中能制作工具,协调其动作,猴子也能。”(32)⑤ 转引自〔美〕卡尔文:《大脑如何思维:智力演化的今昔》,第50、54页。汉弗莱在《意识的回复》一书中指出:“灵长类群居正是它们建立并保持作为有计谋的生物系统本身的性质所要求的;它们必须能估测自身行为的后果,估测别的同伴可能的行为,估测得失的平衡,而所有这些都处于某种整体背景之中,在这种背景中其估测所依据的证据是瞬间出现的,模棱两可,又变化无常,丝毫不是其自身行为的后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群居技能’与智力并肩而行,最终其所需的智慧能力是最高级的。群居的计谋和反计谋的游戏不能仅在积累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我认为,它要求的智力水平是任何以其他方式生存的动物无法比拟的。”⑤红毛猩猩夏特克(Chantek)的DNA与人类相似度高达97%。它于1977年生于亚特兰大的一个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随后被送往田纳西大学,人类学家琳恩把它当孩子一样抚养,小夏特克也把琳恩当作自己的妈妈。它会用美国手语(ASL)与人沟通,成为第一只可以与人类交流的红毛猩猩。2014年成为纪录片《猩猩上大学》的主角。2017年8月,夏特克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去世(33)参见百度百科“夏特克”,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F%E7%89%B9%E5%85%8B/22075956?fr=aladdin。。“黑猩猩是一种智商很高的动物”,他们拥有“有目的地思考的能力”(34)⑤⑦⑧⑨ 〔美〕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第43-44、147、43、40、211页。。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的智力水平,为其参与复杂的社会活动提供了可能。这些活动主要涉及群体生活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一个支配者,为了维持其支配地位,应该具备以暴力为基础的强制力,能够使群体成员畏服或敬服。这是支配—服从结构最为基本的形式要件。然而,在黑猩猩群体中,仅仅有强制力还不够,还需要多数力量的拥护和支持。就此而论,支配者的群体影响力更有价值。攻击-笼络策略是一个支配者确立自己统治地位必不可少的环节。攻击和孤立潜在的挑战者,攻击来犯的敌人,都需要强大的力量为后盾。笼络策略的重要途径,就是寻求恰当的同盟者。政治联盟分为防御性联盟与进攻性联盟。支配者需要组织防御性联盟,近亲或关系密切者,成为政治联盟首先考虑的对象。同时笼络潜在的支持者,尤其需要笼络群体中具有实际影响力却又不会对自己构成挑战的个体。支配者依靠手中的权力以及强大的政治联盟,使得潜在的挑战者处于孤立和无力的状态,从而有利于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挑战者欲改变或冲击防御性联盟,必须另行组建更为强大的进攻性联盟,如此方能改变原有的支配状态。上述原则,在黑猩猩群体和猕猴群体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35)〔美〕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第242-248页;〔意〕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猿猴的把戏》,第119-124页。。简言之,一个支配者应该具备基本的“政治技艺”,包括“政治能力”、“政治策略”、“政治美德”。人类政治的自然根源,来源于此:“在人类和其他某些灵长类动物中,支配依赖于社会智力或政治智力”(36)⑥ 〔意〕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猿猴的把戏》,第60、154页。。
支配—服从的等级秩序,离不开竞争与合作。竞争决定了群居动物必然伴随欺骗、背叛。个体之间的互相合作有利于参与竞争,而合作离不开信任。信任关系的确立,除了血缘亲情的因素外(37)达里奥认为,“裙带主义作为一种现象,具有深刻的自然根源。……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裙带主义是指向家庭成员的利他主义。……许多种类的猴子和类人猿跟我们有亲缘关系,它们则把裙带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它们不仅在获取食物方面帮助亲属,也会在攫取和维持政治权力方面与自己的亲属同心协力,对它们毫不犹豫地伸以援手。”〔意〕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猿猴的把戏》,第79-81页。,首先需要基于互利互惠的原则来笼络其他个体,以便确立起一个互相合作的联盟。于是,在一个充满合作与竞争的群体中,勾心斗角的各种关系互动与博弈,纷纷上演。黑猩猩的社会如此,人类祖先曾经也是如此。
合作的基础不能指望友谊,友谊经不起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的考验。在荷兰阿纳姆的黑猩猩群体中,耶罗恩-鲁伊特-尼基形成了一种雄三角关系,为了有利于权力斗争,友谊会起一定作用,但它是一种灵活善变的东西,“它的更恰当的名称就是机会主义”⑤。友谊之所以脆弱,根源在于,当在合作中有利可图时,背叛是一种生物倾向⑥。黑猩猩具备互相欺骗的能力。“黑猩猩们都是伪装大师”⑦。在耶罗恩与尼基的一场打斗中,耶罗恩的一只手受了伤。为了避免遭受到再次伤害,耶罗恩走路开始一瘸一拐:“耶罗恩从坐着的尼基身旁走过,从他面前的一个地方走到背后的一个地方,在走在基尼的视野之内的这一段时间内,他就一瘸一拐的一副可怜相,但一旦从尼基身边走过之后,他的行为马上就变了,走路的姿态就恢复了正常。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每当耶罗恩知道尼基能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装出行走困难的样子。”⑧伪装、欺骗与背叛,为群居动物的社会生活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
在黑猩猩群体中,强壮的体力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统治能力。但基于联盟或合作的影响力才能真正确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在雄黑猩猩之间,联盟决定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雄性对雌性的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体力优势决定的。雌黑猩猩之间,看来,品格与年龄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⑨黑猩猩的政治能力还体现在决定谁是联盟对象的选择层面。黑猩猩的智商使其具备“非自我中心的社会认知”以及“三角认识”。所谓“非自我中心的社会认知”,来自桃乐茜·齐奈和罗伯特·赛法师通过观察猴子和猿的生活习性,发现它们能够学会理解自己不直接参与其中的社会关系,能够评估其他个体之间的等级秩序或其他群体成员所属的母系血亲关系。比如A能观察B与C的相互作用并评估B与C之间的关系;“三角意识”则是A通过理解和评估B与C的关系,进而衡量和选择A-B与A-C关系(38)④⑤ 〔美〕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第207、236、240页。。黑猩猩的政治,正是基于这种认知能力,才会有告密、欺骗、结盟等“政治行为”产生。如此,黑猩猩就具备挑选谁适合做自己的同盟者的能力,并能通过结盟壮大自己的影响力。
一个具备政治能力的统治者,还必须学会恰当地运用政治策略,包括恰当地呈现某种政治美德:宽容、分享(慷慨)、互惠。英国社会生物学家莫利斯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灵长类在其社会组织中都是独裁的。几乎总是存在着一个暴君,但它有时是一个仁慈宽大的暴君。比如强有力的大猩猩,它与较小的雄猩猩共同占有雌猩猩,在进食时也很大方。只在有些无法分享的事情突然出现时,或出现反叛征兆时,或在较弱的成员间出现任性的争斗时,它才施展自己的权威。”(39)〔英〕苔丝蒙德·莫利斯:《裸猿》,第96页。达里奥认为合作的基础在信任,信任的基础在一个好名声。好名声又与个体的政治魅力密切相关。一个个体乐于分享并具有慷慨特质,往往具有政治魅力:“在慷慨程度方面,拥有一个好名声还是坏名声,对于事业的好坏、政治的成败有重要影响。”(40)〔意〕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猿猴的把戏》,第143页。“对于物质的东西,雄黑猩猩们慷慨得令人惊讶,他们甚至允许某些雌黑猩猩从他们那里拿走某些物品。……如萨林斯所说,‘若要受人尊重,男人就必须慷慨。’”④慷慨能有效地在群体中确立起良好的个人形象和积极的个人声望,这将有利于形成以慷慨大方者为中心的政治同盟。一个成功的支配者,必须善于团结和笼络其他个体,寻求更多群体成员的认可和支持。对于支配者来说,无论是维护既有地位还是为寻求更高政治地位,都必须拥有一些被人类称为“政治美德”的品质,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为其拥护者带去切实的利益。在黑猩猩等灵长类群体中,并没有所谓“政治美德”的伦理观念,但它们本能地具备将“政治美德”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政治能力。
所谓的“政治美德”在激烈的竞争社会中,会呈现出两种类型的“美德”。一种是支配者自己的魅力光环,另一种是不依个体魅力而确立客观制度的公平与正义。实际政治实践中,过分强调制度层面的“政治美德”,不利于作为个体的支配者笼络人心,也不利于其壮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在人类祖先那里,个体魅力型的政治美德几乎笼罩着全部政治生活。聪明的支配者往往更愿意以个人名义进行一些慷慨、宽容及仁慈的行为,以便让支持者获利,从而获得拥护甚至崇拜。通过这种方式,支配者可以获得更多权力、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个人的政治地位。
合作、宽容、慷慨、互惠、信任等后来人类赞誉的美德,在人类祖先那里已经具备实践意义上的雏形。“黑猩猩群体的生活就像一个彼此交换着权力、性、友爱、支持、不容忍与敌意或对抗的市场。其中两条基本规则是:一、‘善有善报’;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像人类一样,黑猩猩之间的互惠行为同样是由公平与正义的道德感所支配的。”⑤为什么会在群居动物比如黑猩猩群体中出现合作、宽容、慷慨、互惠、信任及友爱并形成了“善有善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行为准则呢?难道灵长类动物也具备公平与正义道德感吗?关于这个问题,德瓦尔并没有给出理论解答。英国科学家道金斯解答了这个问题。道金斯借鉴博弈论的“囚徒困境”与史密斯的进化上的稳定策略理论(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ESS)解释自然进化中的利他与合作现象。根据ESS理论,从人类到动植物,到处都充满着“囚徒困境”的重复博弈,重复博弈是相对于简单博弈而言的。在简单博弈中,在“合作”与“背叛”的策略选择中,选择“背叛”是唯一的理性策略。但是,在重复博弈中,“背叛”将不再是最优策略,因为不断“背叛”将会被其他个体唾弃和疏远。重复博弈着眼于长远,会有多种策略,科学家发现有15种策略可供选择,在计算机模拟实验中,200次博弈之后,最后得分最高的策略是最简单、也最不聪明的一个,即所谓“针锋相对”(Tit for Tat)策略。这种策略第一步选择是“合作”,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依据对手上一步的行动而针锋相对进行复制。这是一种善良与宽容的策略。善良体现为第一步选择“合作”,宽容体现为对手“背叛”之后针锋相对但若对手及时认错选择“合作”时又回应以“合作”,不会怀恨在心。“好人有好报”可以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得到解释(41)② 〔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第230-258、94页。。由此,科学家们认为,进化论上的稳定策略对于基因的传承,带有善良与宽容的特质,它可以解释“一个由许多独立的自私实体所构成的集合体,如何最终变得像一个有组织的整体。”②换言之,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采取“针锋相对”策略的个体,具有更多机会将自己的基因遗传给自己的后代。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道金斯阐述的进化上的稳定策略,只是就基因的遗传能力而言,并非代表实际的社会选择,并不具备伦理的或道德的意味。一切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既有宽容或善良的基因,也会有攻击与邪恶的基因。在不同于自然进化的实际生活中,无论宽容、合作还是邪恶、攻击,都离不开自我利益的权衡与考量,一切都是一种维护生存的策略。
善良、正义与公正等品格,在灵长类动物中已经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开始实践,人类作为会说话的灵长类,继承了祖先的行为准则,并将之伦理化、道德化,将之视为某种“政治美德”。这为人类具备抽象思维能力之后讲“虚构故事”提供了可能。就其实质而言,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支配者展现某种“政治美德”,是一种有利于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有效策略。所有这一切行为准则,与各种欲望、权力斗争、结盟甚至战争等诸多因素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类祖先——一种属人灵长类政治生活色彩斑斓的图景。
五、人类政治之出现
人类祖先告别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应该是在智人出现的时代。由此,灵长类群居动物所具有的种种社会活动开始进入到“人类政治”阶段。作为裸猿的智人,依然过着一种竞争性的群居生活,依然在日复一日地演绎着灵长类祖先曾经不断发生的政治行为。同时也应看到,智人政治与前智人时代的政治,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政治”。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人类演变的历史十分漫长。5000万年前,狐猴具备向人类复杂的面部结构演化的微小痕迹,人类祖先正是从这时开始形成。3000万年前,在猴类演化的主线上,产生了向猩猩和人类进化的分支,此时的“埃及古猿”(Aegytopichecus)进化明显,鼻吻较狐猴更短,牙齿与类人猿相似,身材高大。到2000万年前,类人猿生活在东非、欧洲和亚洲,这一时期的“森林古猿”(Dryopithecus)脑容量明显增大,眼睛完全处于立体视觉的位置。但它的牙齿表明它还是一只猿猴,因为其犬齿与颌部咬合的方式与人不同。1400万年前,在肯尼亚和印度发现的“腊玛古猿”(Ramapithecus)第一次宣告了人类的诞生。腊玛古猿,可算作人科动物(hominids)。它的牙齿是水平排列的,更像人的牙齿,类人猿那种巨大的犬齿这时已不复存在,其面部也更加平坦。距今200万年时,非洲的“南方古猿”(Austrapithecus)脑容量增大,他有两大特征:一是制造石制工具,能够从事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二是有某种社会组织形式,收养、照顾和教育孩子。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伟大一步。100万年前,直立人(Homo erectus)开始出现。典型的直立人是在中国发现的北京人,时间大约在40万年前,其突出特征在于开始使用火。其后又出现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t),他们有3磅重的大脑,与现代人不相上下。尼安德特人在中东的一支很可能直接进化成今人(Homo sapiens)(42)〔英〕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人之上升》,第12-16页。。关于现代人类是否由尼安德特人进化而来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争议。赫拉利就认为,大约在200万年前,人类祖先开始走出非洲并发展出不同的物种,其中就包括“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智人最后几乎完全消灭了尼安德特人,成了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因为现代生物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中东和欧洲人只有1%-4%尼安德特人的DNA。而人与猿的分野,也大约在6万年前,“有一头母猿产下两个女儿,一头成了所有黑猩猩的祖先,另一头则成了所有人类的祖奶奶”(43)〔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5页。关于人类起源,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以达尔文为代表的非洲起源说,另一种是因爪哇人、北京人以及云南禄丰腊玛古猿化石的发现而形成的亚洲起源说。西方学者基本倾向于采纳非洲起源说,中国学者则倾向于亚洲起源说。参阅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0页。。
笔者并不关心人类祖先告别近亲类人猿的具体年代,这是古生物学家们关注的话题;我只在意从类人猿到智人阶段,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根本变化,使得人能够区别于类人猿。根本的变化在于,漫长的进化使得智人能够直立行走,能够制造工具,手与眼的功能以及行动协调能力空前增强,从而获得了远比其他动物大得多的脑容量并产生了语言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超前的预测能力、想象能力。布洛诺夫斯基曾发出疑问:“人究竟是怎样成其为人的呢?猿猴又是怎样变成了令我十分崇敬、灵巧机敏、善于思考、感情丰富、熟谙语言象征与数学,并具有从事艺术、几何、诗歌和科学等创造性活动能力、想象力丰富的人类的呢?”(44)④ 〔英〕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人之上升》,第9、18页。他给出的答案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任何动物,更不用说人,都是浑然天成的整体。当行为发生变化时,这个整体的每一部分也必然发生变化。脑、手、眼、足、牙,以及整个人体的进化,导致了人的特殊天赋的组合。……正是这些天赋,使人成其为人,比其他动物进化更快,行为方式也更加灵活多变。……人具有其它动物所不具备的各种官能的巧妙组合。”(45)〔英〕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人之上升》,第17页。赫拉利则认为这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参阅〔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34页。并且,他特别注意到了语言之于人类成为整个地球食物链顶端的重要作用:“像人这样行动缓慢的动物,只有依靠集体合作,才能潜步追寻、发现和堵截在茫茫荒原上奔跑着的庞大动物。狩猎活动需用语言有意识地作出计划和安排,集结成伙需要制作特殊的武器。的确,语言在为人们所使用时,本身就具有某种狩猎计划的性质。也就是说,人不像其他动物,他可以使用语言,用一些由可变单位组成的句子相互提醒,协调动作。狩猎是一项集体活动,这种活动的高潮——也仅仅是高潮——就是齐心协力把捕获的动物杀死。”④正是因为智人的语言能力使得群体沟通更为顺畅,从而能够有效地组成更大的集体参与狩猎活动,稳定地获得食物,缓慢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
赫拉利则对智人的语言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他将人类祖先从类人猿中分离出来的标志性事件称为一场“认知革命”。他认为,人类语言不仅便于人类了解外部世界,如“河边有只狮子”,而且更有利于人类了解自己,讨论各种生活中的秘闻趣事等,即所谓“八卦理论”。除此以外,他进一步指出:“人类语言真正最独特的功能,并不在于能够传达关于人或狮子的信息,而是能够传达关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据我们所知,只有智人能够表达关于从来没有看过、碰过、耳闻过的事物,而且讲得煞有其事。”(46)⑥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25、26页。人类的想象能力与抽象思维能力,藉助语言,就能够讲出诸多“虚构”的故事,这是智人语言最为独特的功能。“认知革命”之后,各种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便应运而生。人类运用这种讲“虚构”故事的能力,不仅让人类拥有想象,而且还能“一起”想象,编织各种共同的虚构故事。“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智人的合作不仅灵活,而且能和无数陌生人合作。正因如此,才会是智人统治世界,蚂蚁只能吃我们的剩饭,而黑猩猩则被关在动物园和实验室里。”⑥由此,人类可以组织远比人类的动物祖先规模更大的群体,通过和平协商或吞并扩张,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聚落,走向部落、走向国家。“认知革命”伴随某些抽象政治观念的产生,混杂着人类源自祖先时代的支配—服从这一政治现实,使得人类政治呈现更为复杂的面貌。
可以说,人类的政治观念,除了实事求是地描述人类祖先的政治生活情境具有某种真实与客观的成分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想法,都是“虚构”的产物。沃格林发现了这点(47)沃格林认为:“鉴于和政治观念有关的语言符号的基本功能是构造现实,我们就面临一个独特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一种基本的可能,就是把召唤术语用于类似描述的功能。为了理解这个问题,必须始终牢记住,语言使(人们)可以基于在经验上无指谓的术语,发展出精致的思想体系。语言的魔法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提到一个术语,总是伴随着一个预设,就是使用该术语时我们在指涉一个客观实在。……所有政治理论都力图把这个魔法小宇宙描述为某种被认为是客观真实的东西。” 〔美〕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一,第67页。,赫拉利也发现了这点(48)赫拉利认为:“无论是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例如教会的根基就在于宗教故事。像是两个天主教信徒,就算从未谋面,还是能够一起参加十字军东征或是一起筹措资金盖起医院,原因就在于他们同样相信神化身为肉体、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罪。所谓的国家,也是立基于国家故事。两名互不认识的塞尔维亚人,只要相信塞尔维亚国家主体、国土、国旗确实存在,就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彼此。至于司法制度,也是立基于法律故事。从没见过对方的两位律师,还是能同心协力为另一位完全陌生的人辩护,只因为他们都相信法律、正义、人权确实存在。……然而,以上这些东西,其实都只存在人类自己发明并互相讲述的故事里。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 参阅《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28-29页。。“虚构”的政治观念,具有多重功能,已然成为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第一层功能,对支配者而言,可以通过虚构故事,维持和巩固支配—服从这一等级秩序;第二层功能,对于服从者而言,可以通过虚构故事,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并藉此对支配者提出要求甚至对抗支配者的权力;第三层功能,无论支配者还是服从者,都在通过共同的或各自理解的虚构故事,来进行权力博弈并调节支配—服从关系的适当程度,要么支配者让步,要么服从者让步。总之,人类历史就是一场围绕着支配—服从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依据各种虚构故事而展开的权力博弈。人类政治思想史,实则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围绕政治问题而“层累地”虚构各种故事的历史。研究人类政治思想史,不应忘记一个基本事实:支配—服从的社会秩序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无可逃避的宿命。由此引申出来的难题始终困扰着人类: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平衡如何才能达成?于是,各种虚构故事纷纷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