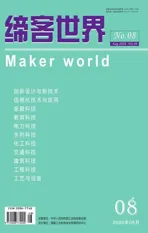论政府应急征用措施的限度
2020-12-11邓媛媛
邓媛媛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00)
关于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采取应急征用措施很有可能违法从而过度侵犯公民权力,因此,基于对突发事件危机下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价值考量,我们认为应当对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的限度做出规定。笔者从主体、客体、程序等方面来研究应急征用措施的限度。
1 政府应急征用的法律原则
突发事件下的政府应急征用原则应当有两类:第一类是与正常状况下的行政征用相同的原则,如:法治原则和比例原则,它们适用于所有的法律;第二类是应对突发事件专有的原则,如:应急原则和基本权利保障原则。
1.1 法治原则
有学者认为:只有在‘人民主权’和‘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统治基础时,传统的公共应急举措才由事实性的强权行为转变为法律性的国家权力行为,接受法律的调控。可见,起初紧急权力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强权或者说不受拘束的特权存在。在有了“民主”和“法治”后,这种紧急权力才具有法律性,因此,应急征用行为必须以以民主作为思想的法治原则为基础。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理解法治原则的基本内涵:(1)应急权力的行使必须依法行政。我国目前关于政府应急征用的法律体系层级十分完整,各层级均有相应的应急征用法律规范。(2)紧急权力的行使应当尊重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3)应急权应当遵循权责统一原则。非常时期,赋予政府及其部门行使紧急权力并非是一种法外行政的规定,它是为了保护更大利益的应有之义。
1.2 应急原则
关于应急原则的概念很多著作中都有表述,授权政府行政应急权基于突发事件的突发性、紧迫性、不确定危险性等特性,政府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障、社会秩序的维护、防止危机扩大等原因必须在第一时间行使应急权采取应急措施以有效应对突发事件。与正常情况下政府行使权力不得侵犯公民权利不同,在重大突发事件下,政府行使应急权可以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或剥夺,并且行使的程序也较平时更简便,多为简易程序;其行为也可以没有法律依据但事后得到追认。虽然从表面上政府行使应急权似乎违背了形式法治主义,但实际上,这是为了国家、公民更长远的利益,总体而言这种应急权的行使是利大于弊的,是正当的。并且,应急原则虽然可能会对公民权利造成一定的剥夺或限制,甚者超越法律行使职权但这并不违反法治原则,同样应急原则也非法治原则的例外。相反,法治原则要求应急原则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为政府行使行政应急权提供了正当性、合法性基础。
由于在紧急情况下应急权的行使可能赋予公民比常态下更多的义务,因此行政应急权的行使应当符合一定条件。
1.3 基本权利保障原则
紧急情况下,政府的应急措施必然会侵犯公民权利,但其不能违背基本权利保障原则。应急权的行使虽然会对公民的权利进行侵犯,但是并没有违反基本权利保障原则。
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理论表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公民理所当然地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但我们要谨防政府假借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名,过度克减公民权利。对政府行使行政应急权异化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虽然应急原则以法治原则为基础,但并不能打消这种合理顾虑。因此,在对政府行使行政应急权划定明确的界限时,也应当通过立法确立最低人权保障,明确公民权利克减、限制的范围、条件和程序。这样才能才能达到设立应急征用制度的初衷,更好的维护紧急状态下的社会秩序。
1.4 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实际上是权利和权力的一种平衡。政府行使行政应急权同时应当注意权力的行使要遵循一个合理的限度,即在遵守形式法治的同时兼顾实质法治。政府采取应急征用措施时,征用的时间、强度、方式等与公民权利被限制或剥夺的程度呈一种正相关。实际上,在紧急情况突发时,比例原则与应急效率是相反的,即不遵守比例原则,应急效率越高。但由于比例原则在政府行使应急权的价值不在于此,其更关注的的行为的正当性。2003年全国爆发疫情,部分行政机关为对抗疫情征用了高档豪华宾馆,取代征用一般的商品房屋给有关患者及家属,这种应急行为已经超出了必要限度,因而给部分商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财产损失。这一举措即为应急过程中违反比例原则的一处体现,我们应当吸取相关教训,真正地将比例原则运用到征用行为之中,使其成为政府应急权力的扩张与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之间的均衡点。
2 突发事件下政府应急征用措施的运用
疫情作为典型性的突发公共事件,政府行使行政应急权征收的行为势必要得到广泛的关注。现代法治国家将保护公民财产作为国家职责,虽然承认政府行使应急权,但是行使必须严格符合法律规定,以达到保护公民财产权的目的。这样也给应急法制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问题,即应急效率与公民财产权的平衡问题,如何平衡二者对于应急法制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此次疫情是在全国爆发,因此应急征用的范围、力度、对象,都十分少见。所有征用的物资中,以医院、宾馆数量最多也最为重要。据不完全统计,疫情发生后,全国340多支医疗队、4.2万余名医务人员奔赴战场,全国约1/10的重症医护力量集中武汉。武汉市改建16家方舱医院,改造86家定点医院,新增6万多张床位,征用530多个宾馆、培训中心、疗养机构改造为隔离点,扩容床位近11万张。宾馆、医院的征用主要用于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观察和医务人员的休整。武汉市作为疫情的集中爆发地,其征用的宾馆侧重于医院人员的休整,此外湖北咸宁征用高校作为集中隔离场所计划设置1700张床位。由于各地疫情不同,因此征用的宾馆也有不同的用途。疫情期间,黑龙江哈尔滨共征用了18家宾馆。根据该市的通知,9区9县(市)各有一家宾馆征用为密切接触人员或来自疫区人员的隔离观察场所。
此次疫情期间,我们可以根据各地各级政府征用的情况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1)各地区征用有差异但区别没有特别明显。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每个省市都有确诊的病例,尤其作为疫情的集中地武汉市,被征用的财产最多,其他地区虽然较武汉情况较轻但仍然很严重,全国只有西藏地区情况较轻,因此采取征用措施并不典型。(2)征用不同的物资采取的措施呈现多样性。(3)各地区征用的相同物资的主要用途有所区别,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应急征用措施的必要限度分析
从根本上来说,应急征用措施是符合群众利益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应急征用来说,亦是如此。应急征用,其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是以侵犯人民基本权利为前提的,只是个人权利在公共利益这种更大的利益的对比下,才获取了合法性和说服力。政府应急措施虽然获得了正当性基础,但是不能排除其行使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或对公民权力造成过度的侵害,因此为了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应当对政府这中应急措施做出必要限度。总结此次疫情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发现,最容易超出限度行使权力往往在三个方面:征用主体、征用客体和征用程序,因此,有必要对这三方面进行界定,以确定应急征用的限度。
3.1 应急征用的主体
行政征用的法律依据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突发事件应对法》是规定突发事件应对活动的一般法律,有观点认为其规定的征用主体应当是政府,而非政府部门。 不过之后该种观点被更新,持有该观点的学者并没有再次提及,而是认为征用的主体包括政府及其部门。本人认为,《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是一个原则性规定,第52条是一个具体性的规定,不能因此认为前后冲突或者否定政府部门的征用主体资格。《传染病防治法》全文都是围绕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展开,并没有规定其有行政征用权,因此本人认为,本法的意图是将卫生行政部门的征用权排除。在查询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权力清单时发现: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无征用权。同时,根据大理市卫健局征用过境防疫物资一事,经查明,在公布的大理市卫健局的权责清单,共有的193项,这193项中并无行政征收权,仅有一项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的行政征收权。 因此,大理市卫健局征用口罩一事,实属征用主体违法。
本人认为,《突发事件应对法》其作为应对突发事件的一般法律,应当以其作为基础,确认有权实施应急征用的主体包括政府和政府部门,但是应当同时兼顾特别法。因此应当对作为征用主体的政府部门主要限定于各级人民政府的应急管理部门,理由在于:如果确认所有的政府部门在紧急情况下都享有应急征用权力,那么当突发事件来临时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将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并且各部门实施应急权还可能产生冲突。
因此,对于应急征用的主体应当为政府、专门从事应急管理的政府部门和突发事件发生后临时设立的应急指挥部。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治各个政府部门越权行使应急征用权,给公民财产权造成过度侵害。
3.2 应急征用的客体
在应急征用问题上,《突发事件应对法》对客体有所列举。但若《突发事件应对法》没有明确列举,但是其他法律有规定,是否可以作为应急征用客体?本人认为,只要符合应急征用的目的,并且符合比例原则,对公民个人财产的征用都应当被允许。
另外,口罩能否属于应急征用的客体?口罩与其他征用客体有何不同?进行以下分析:(1)根据行政征用的特点,征用并不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 因此,征用主体承担返还的义务,但口罩的特殊性在于,其一经他人使用就失去价值,无法返还给所有权人,对于所有权人也失去了价值,那么对于使用后没有返还价值的口罩是否就不能作为征用客体?我们将口罩作为一种一经征用就毁损的财产,那么口罩是可以作为征用客体的。(2)对于征用客体的属性,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与《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对于重庆市政府采购交由大理市快递分公司承运的疫情防控物资,其所有权人并非大理市内的单位或个人,其属于运输过境物资。因此,大理市卫健局是无权应急征用所有权不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过境财产”。
综上,本人认为作为应急征用客体的私有财产应当做扩大解释,包含口罩等一次性用品,但应限于应急征用主体所管辖行政区域内的财产。
3.3 应急征用的程序
程序是征用措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当的程序,从反面上,看能够防止给公民的财产权利造成损害;从正面上,充分表达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出台,将应急管理的重心由部门转向政府,拓展了政府的应急职能。” 有学者提出“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实施公共应急管理,不得超越最低限度的程序义务”等立法建议。 应急征用的程序应含三个环节:(1)程序的启动。由于应急征用具有强制性,因此其无需相对人的申请即可启动,属于依职权的行为。启动的条件应当限定于处于突发事件危机下,应急程序的启动强调效率,其特点就在于程序的简便性。(2)应急征用程序的推进。(3)应急征用程序的终结。待危机解除或使用完毕后,行政主体应当履行及时返还义务,并就财产的毁损、灭失,给予补偿。
应急征用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紧急措施之一,实施应急征用具有紧迫性需要注重应急效率,因此会导致征用权力的扩张,极易造成公民权利的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就难以调动公民的积极性,突发事件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平衡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我们需要对突发事件中政府的应急征用行为做出明确的限度,以达到最大化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