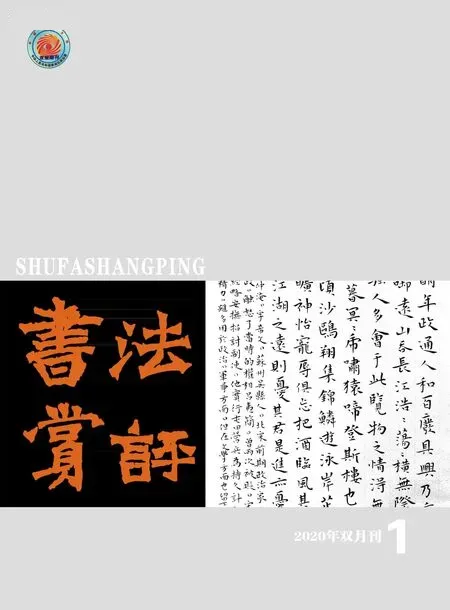魏晋书法中玄学思想探微
2020-12-10曹斌
曹 斌
“玄”作为哲学概念最先在《老子》中出现,如“玄牝”“玄同”等。《庄子》的《天地》篇讲“玄德”,《天道》篇讲“玄圣”。《吕氏春秋》有“玄明”,汉代杨雄明确以“玄”指“道”,张衡的《玄图》也以“玄”为“自然之根”。《晋书·王衍传》载:“魏齐王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1]到了魏晋时代,“玄”便成为极流行的观念。
汉末统治阶级的腐败,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到处都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残酷景象。社会的动荡加速了以地域宗法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势力的形成,即封建性的门阀世族地主阶级。门阀世族虽是乘着战乱而壮大起来,其内部充满着各种矛盾,加之反动与腐朽的思想,他们习于逸乐,沉缅酒色,“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刘惔传》)”,可见其思想的空虚。门阀世族将自己的政治需求和心理特征升华为哲学思辨,也正合统治集团的需要。贵无论玄学崇尚虚无,推崇老学,讲的全是适合于门阀世族的统治之术。门阀士族深感人生无常,他们的思想从“名教”的束缚中得以解脱,获得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生活在自成一统的庄园之中。放情丝竹,临流赋诗,高咏长啸,他们对个体人生价值意义的思考无法从儒学中找到支撑点,因而只能从重“情”和“养生”的道家哲学,特别是庄子哲学里寻找根据和支撑点,妄图给人以精神上的安慰。
一、魏晋书法中玄学思想的兴起
魏晋时期的艺术思想,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集大成。刘勰以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2]文的呈现恰恰是玄学精神贯注下的人的性情之自然。早在汉代,蔡邕《九势》中就谈到“书肇于自然”的论调,许慎《说文解字》谓“仰则观象于天,府则观法于地”,杨雄也有“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的说法,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到玄学的影子。
曹魏时期,统治阶层鉴于汉王朝衰亡的教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在学术上也兼采法家和老黄玄学,打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魏晋中国书法开姓走向心灵的“自觉”,这一时期书法的实用性明显减弱,艺术家们开始追求书法的审美价值。艺术的怡情达性的功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帝王及世族知识分子纷纷介入艺术创作中。玄学作为一种特定历史阶段上理论思维和文化心理表现的哲学思潮,它不仅是人们对世界的一种认识,也是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同时,学术文艺思想活跃,政治约束力相对松弛,名士们生活态度和处事作风发生极大变化。魏晋动荡的社会使名士们感到时代变革的来临,《周易》成为大家注目的经典,讲虚无放诞的老庄学说成为大家的处事哲学。士人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从倾心政权、企望致君尧舜转变为崇尚自然,追求超世脱俗的精神生活。
洛阳长期处于曹魏政治文化中心,因而魏晋书法“玄学”思潮首先在洛下兴盛起来。魏国书法,继承了东汉流风,谓之“鸿都流风,去之未远”,代表书家有邯郸淳、梁鹄、钟繇、卫觊等,他们都是由汉入魏的士人。古文方面,卫恒《四体书势》云:“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邯郸)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3]卫恒认为东汉的古文已经出现了变化。在隶书方面,《曹真残碑》已出现尖锐的挑笔、圆厚的捺笔,笔法也已经变化。钟繇的正书经过改造,吸收隶书俗体写法,把正书笔画规则化,点画敛笔顿按,横画的收笔采用“顿势”笔法。行书也有别于东汉行书,著名的行书书法家有钟繇和胡昭,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胡书肥,钟书瘦”,道出了这一时期行书特点。洛下新风的出现,标志着书法风气已出现变迁,书法家们开始采用在民间流行的俗写体势作书,造就了大写新体的风气,展现个性气质的风韵。新书体的发展带来的好处是书写简便,名士们借助畅快的书写,显示个人的风度,从而形成注重艺术表现的书写观念,“天然”“点画之间皆有意”等观念开始在书法中形成。
玄学家善书画,书画家懂玄学。“形神”“得意忘象”“言不尽意”等玄学思想对魏晋绘画艺术有较大影响,同时影响到书法。魏晋时代是钟情于美的时代,对能够带来审美情趣的事物,晋人怀着近乎狂热的衷情,《历代名画记》载桓玄“每请长康与羊欣论书画,竟夕忘疲”。魏晋人绘画重“神气、风度、风韵”,与两汉重骨相不一样。魏晋玄学所谓的“风度”,是针对那种纯粹形式上的秀朗俊逸的容止而言的。《世说新语·容止》说夏侯太初“郎朗如日月之入怀”,虽描绘出夏侯太初的性格,从内容上来说却是空虚的。随着山水画的兴起,老庄、佛教寄情山林,以丘壑喻方外。在评论人物时,也多以山水譬喻,如《晋书·王衍传》说顾恺之作《画赞》称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和评论人物相一致。凡魏晋士人,工画、善书、崇尚玄学之风尤盛。“王羲之书既为古今之冠冕,丹青亦妙。”[4]宗炳“善书画,善琴书,好山水”,[5]“以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均善书”。[6]从“正始名士”到“竹林七贤”,再到“中朝名士”的八子,他们不再像东汉名士专宗儒学经术,而是书画兼善,“儒玄兼综,礼玄双修”。
二、书法中的“天然”与“流美”
魏晋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巅峰,河东安邑卫氏、颍川长社锺氏、琅琊临沂王氏作为魏晋儒学大族,也是书法世家,代表了魏晋书法的最高水准。“钟繇擅长八分、正书、行书;卫玠精工古文、篆、八分、章草。”[7]东汉时,钟氏居住于黄河以南,卫氏居住于黄河以北。南方学风注重发挥理论,注重思辨,北方学风讲求根据来历,学识渊博。“钟繇书法借趋新而领袖时尚,‘以奇笔唱士林’,完成了俗体的雅化,重书写的表现性。”[8]“天然”“流美”的玄学思想在钟繇书法中开始出现。钟繇作为书法大家,亦深明玄学之理。《世说新语》注中引《魏志》说钟繇“家贫好学《周易》《老子训》”。宋陈思《书苑菁华》卷首辑录秦、两汉、魏四朝用笔法时谓:“魏钟繇少时,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二年,还与太祖、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议用笔法……繇曰:‘岂知用笔而为佳也,故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9]钟繇所说的“天”与“地”分属“用笔”与“流美”,出于《易传》以来的自然元气化成万物的理论,可以窥探到有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流美”“天然”是钟繇书法风格的体现
南朝庾肩吾在评张芝、钟繇和王羲之的书法时说“钟天然第一”,[10]“天然”即是自然,没有斧凿的痕迹。南朝人评价钟书“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唐太宗则认为钟书“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都道出了钟书的“天然美”特征。钟繇毕生致力于钻研笔法,然而他并没有就此停留在怎样用笔的探讨上,而是创造出一种“天然”的“流美”书法特征。
钟繇书法“流美”特征的形成,亦和他追求的超逸精神相关。今天所见钟繇书迹《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荐季直表》,南朝羊欣用“瘦”字形容其书法特征,唐朝李嗣真则以“寒涧窙豁,秋山嵯峨”的自然景象道出了其书法廋劲的意象特征。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钟繇不可能将视为正统的汉隶完全排除,在他的真、行书中仍有隶意的存在,这就给晋人以完善美化的余地,如“字细画短”“长而愈制”之类,所以后人评钟书“大巧若拙”,张怀瓘认为钟书“古雅”“道合神明”“幽深无际”,如此种种把钟书的“天然”美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钟繇的显赫地位和名门望族的追捧,钟繇所创导的正书、行书在士大夫阶层流行起来,逐渐成为一种书法时尚,即“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之所以有如此魅力,因为它们是玄学精神的审美化呈现,是士族文人推斥名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玄学精神的审美化呈现。”[11]
第二,从“天地”层面来讲书法的创造的“天然”“流美”
阮籍谓:“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人生天地中,体自然之形。”[12]强调“天人”关系的自然性。钟繇所说“天”,近乎蔡邕所说“自然”,所谓“流美”,即蔡邕所言“形势”。用天地讲书法艺术的创造,和蔡邕的“书乾坤之阴阳”“书肇于自然”有根本的共同点,这也是这一时期普遍观点。《淮南子·天文训》又言:“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13]王允的《论衡·骨相》曰:“禀气于天,立形于地。”就天地的形成而言,古人认为天在前地在后,天定而地成。天是清气所化,是无形的;地是重浊的,是有形的。魏初的曹丕用自然元气喻事物的美丑,在其《王珏赋》中,讲到玉之美如“包黄中之纯气”“体五材之表仪”,即认为玉之美来自自然元气。钟繇将此理论运用到书法创作中,用笔的方法需要长期的研习才能很好地掌握,而一旦形诸笔墨,则表现在书法的美感之中。所以书法家创造书法犹如天以其自然元气赋于万物,产生和创造地上万物的美。因而用笔似天,而流美似地,天定而地成,用笔精而流美现,用笔与流美互为表里。
第三,“天然”“流美”可以上升到“道”的境界
“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不及欣。’……孔琳之书,天然放逸,极有笔力。”[14]王僧虔在书法的创作中首次将“天然”与“功夫”结合起来,作为评论书法的两种尺度,来体现书法的结体和运笔,开启了后世以“天然”“功夫”论艺的先河。庾肩吾《书品》又谓:“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15]钟繇以自然元气论讲书法创造,强调书法美是一种“天然”的美。同时,钟繇认为这种美“非凡庸所知”,这与曹丕《典论·论文》强调的“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力而致” 也有相同之处。
刘勰强调艺术的美与自然的美一样,“夫岂外饰,盖自然耳”。陆机认为作文应“因宜适变”,一切顺其自然。书法的创造,“天然”美是很重要的。汉末赵壹《非草书》认为当时人学书是“每见万类,皆画象之”。在汉代,蔡邕《笔论》就强调了书法的“天然美”:“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16]显然,“天然”与魏晋玄学崇尚的“自然”是一致的。王弼谓:“天地任自然,无为无迹,万物自相治理。”郭象“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自然即本色、本性,往往用“素”“朴”代言之。玄学家们对“自然”的推崇,还表现在山水文学和山水画中。《世说新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17]自然美已经独立成为堪与艺术美并列的另一种美。在艺术创作中,“自然”要有感而发,不事雕琢,浑然天成。唐代李德裕《文章论》谓:“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玄学家讲究自然天成的创作方法。庄子谓:“天地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距,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18]“天地有大美”美就美在自然无为,以至于“庖丁解牛”的技艺能够达到“道”的境界。
三、书法中“自然无为”的精神
卫氏家族作为儒学世家,博通古文,卫恒在《四体书势·古文序》提到卫觊写的古文,与汲冢书相仿佛。卫氏家族以书法显名,始于卫玠,他“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19]在保持儒学门风的同时,卫氏家学不断汲取新的学术思潮。卫恒《四体书势》中“用心精专”“睹物象以致思”出自玄学的“言、意、象”。卫玠是在玄风炽盛的西晋成长起来的,“少有名理”,而且“善《易》《老》”。“卫玠却不治《庄子》,可见他吸收道家的思想是有选择,更注重学术与学理,行为上依然恪守着儒学礼法。”[20]因而,在学术思潮开放的魏晋时期,卫氏家族的学术面貌是“儒道兼综,礼玄双修”。这种思想不仅影响到卫氏书法,而且颍川长社锺氏、琅琊临沂王氏等儒学大族都受到影响。可从两方面理解“自然无为”的思想:
(一)“自然无为”是用自然万物来比喻书法的千姿百态
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21]索靖《草书势》云:“蝌蚪鸟篆,类物象形。”[22]都是用自然万物来比喻书法的千姿百态,自然美和艺术美在书法中得到统一。中国精神受“万物有灵观”的影响,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看成是有生命的,书法也不例外。张怀瓘《书断》评嵇康书法:“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使人神清,自然意远。”[23]虽然不见嵇康的书法到底怎样,但可以从其在《声无哀乐论》中从玄学出发对“自然之和”与“平和”之美的追求得到解释:“嵇康认为音乐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其本源为自然。音乐的特质为‘和’,有‘自然之和’与‘平和’,‘和’即为美。”[24]嵇康以“和”为自然乐的本体,从自然层面来说指阴阳的协调,也就是其《养生论》中所言“性气”“情志”,人的精神上的“和”。同理,老子“道法自然”,也是“道”本身存在和运动的内在原因,是一种不加外力干涉完全的自然状态,顺应自然,方能复归自然,自然而然,方能进入艺术的最高境界。
(二)“自然无为”是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最高境界
魏晋时期的书法家常常把“自然无为”视为创作与审美的根本准则和最高境界。从生殖崇拜到图腾崇拜,从山水诗到山水画,从建筑雕塑艺术到舞蹈艺术,都充满自然生命美。“书肇于自然”,当书家认识把握了自然的本质特性及其变化规律后,便可以得心应手,驾重就轻,从必然进入自由,从认知进入创造,达到“自然无为”的境界。
魏晋书法“尚韵”,与当时玄学一样,推崇平淡的自然美。在玄学看来,“自然”指天道的本来状态,天道是自然无为的。玄学最理想的圣人的根本点,在于如何处理好和体现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在自然观上,嵇康认为客观外界一切事物都是“自然相待”,以“元气”“五行”为其形成的物质基础,而“不假人以为用”。阮籍则认为“自然”指万物本体的“无”。“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25]因循自然的行为就是“道”,遵循“道”而治世,万物就能在自身体系里充分发展变化。“自然”为天地之源,“自然”、天地、万物相互贯通。“阮籍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是追求一种超越自然形质的,高度纯净的精神美。”[26]阮籍的《乐论》赞颂道家与自然合一,大胆批判儒家礼法,渴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同时,在赞美自然合一的最高境界时,又有着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并不赞赏道家的乐天安命思想。显然与卫恒的“儒道兼综,礼玄双修”思想高度一致。
四、“言、意、象”对书法的影响
东汉以后行草逐渐兴起,魏晋时代,经钟繇、胡昭和索靖等人的发展和名士的欣赏,开始“大行于世”。在南方,在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努力下,彻底去除分书遗迹,将隶书推进为行书,章草变为成熟的今草,其草书“焕若神明”,强调“意”的表现。
书法不单纯是模仿的艺术,而具有抽象的象征性质。魏晋时期,“心”“意”已成为书家十分重视的范畴。成公绥《隶书体》谓:“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27]索靖《草书势》曰:“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28]“意”都是通过书法的形态表现出来,强调书法物象与心意的结合。
卫恒《四体书势》谓:“睹鸟迹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29]书法之“意”是“言”所不能尽的。“言”指言辞;“意”指思想。《墨子·经说上》说:“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肯定通过一定的“言”,人们就可以了解和把握一定的“意”。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言”能达“意”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周易·系辞上》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30]“言”也不能完全表达“意”,但同时又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31]通过设立符号式的卦象来弥补“言”在表达“意”中的不足。显然,“意”是高于“象”的,“象”又是高于“言”的。而《庄子·外物》记载:“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种观点不否定“言”能表“意”的作用,而是强调“言”以“得意”为本。而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32]其在《庄子》的基础上,阐述了一个完整的意象观,“象”可以用来表“意”。
《笔阵图》谓:“执笔有七种,有心急而执笔缓者,有心缓而执笔急者。若执笔近而不能紧者,心手不齐,意后笔前者败;若执笔远而急,意前笔后者胜。”[33]王羲之认为执笔要与“心”“意”结合,具体讲了在书法创作中思想心态与执笔和运笔的关系。这种“意”,体现了晋人“尚意”的艺术祈尚,书法美不再是只具备形态美,而且还要表现人们的心理意愿。王羲之《书论》曰:“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34]羲之在作书、评书、论书时心中皆充满“意”,摆脱了“观其法象”的束缚,把主体内在的“意”摆在重要位置。
首先,书法中的“意”离不开“道”的情感体验
所谓书能“称意”,即书法创作中主客观沟通的问题,羲之《书论》中“大抵书须存思”即是如此。魏晋书家在倡导“意”的同时,同样进行“道”的追求。魏晋时期,士大夫们迷恋山水以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精神境界,特别是山水景物进入诗歌和绘画中,使得山水诗、山水画成为言玄悟道的工具。宗炳《画山水序》道:“山水以形媚道。”中国古代士人讲“道”,时时事事离不开“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中庸》)。从现存王羲之书信也可以看出其受玄学的影响:“省士。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吾所奉设教意政同,但为形迹小异耳。方欲尽心此事,所以重增辞世之笃。今虽形系於俗,诚心终日,常在於此,足下试观其终。”[35]“吾所奉设教意政同,但为形迹小异耳”,指羲之是信奉道教的,但他以为和佛教之意是相同的。最后又说其身处世俗而心实向教。显然,在他儒家思想深处深受玄学合流的佛学影响。
晋人是注重个性、崇尚自然的时代精神。王羲之的创作,受阮籍的影响是巨大的。以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其思想的实质是以庄子为主的“性情的玄学”。《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粲传》谓阮籍:“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羲之《兰亭序》开篇“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流觞曲水”,正是“竹林名士”“生活情调地玄学”,完全一副生活的山水画。陈传席认为“山水画兴起的直接根源是玄学”,[36]玄学家鼓吹玄学,何晏一派通过诗歌把玄学的哲理表达出来,于是创始了“玄言诗”。从谢灵运开始,玄言诗转向山水诗,“山水形象是表达玄理最合适的媒介,所以山水景物大量进入诗歌和绘画中,使得山水诗、山水画成为玄言悟道的工具。”[37]因此,才有“放浪形骸之外、畅叙幽情”的玄趣和圣人之“道”。刘熙载《书概》中说:“右军《兰亭序》言‘因寄所托’,‘取诸怀抱’,似亦隐寓书旨。”[38]道出了王羲之书论的精髓。
其次,“意”的变化美是对“象”的领悟
要求书法有变化的美感,羲之《笔阵图》中“点”,如“高峰坠石”,“竖”,如“万岁枯藤”等,从自然美的形态形容书法的变化之美。他在《书论》中说:“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39]根据王弼的观点,对“意”的变化,不能脱离“象”与“言”。书法的形体变化可以看作“象”与“言”,在创作时,首先要求得其变化,不能“状如算子”要有书法的神采风气。“意”要怎样变化呢?王弼认为:“真正对于‘意’的了解,是一种既需要‘象’但又超脱于‘象’的领悟。”[40]显然,形体运笔的变化之美,能更好地表现意趣。从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的“意在笔前”,到王羲之的“发人意气”,“意”的内涵在不断变化。玄学家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象”讲的是对美的主观感受,而“意气”就是美的最高境界。
第三,由“意”到“忘象”的境界
羲之《兰亭序》的“仰观宇宙之大、游目骋怀”,与魏晋以来在诗歌、绘画、书法中强调的“传神”是一致的。“得意”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领会到“意”。实际上得道的“意”并不是纯粹的物“意”,而是己“意”与物“意”共同化合的产物,因而在艺术创作中强调审美主体的创造作用。从郑板桥的“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可以看到由“意在笔前”到“得意忘象”的创作过程。正因为“得意忘象”,因而才有“意气”的出现。
显然,“意”的产生离不开现实生活中的“象”,因而“观其法象”便有了合理性。但是,如果拘泥于现实中的“象”,就不会取得艺术创造的进步。对“象”作为体现“意”的手段可以丰富多彩,在书法的历史发展时,不仅仅局限于“宛若银钩、飘若惊鸾”的具体物象上,必须进入一种不为任何物象所限定的自由精神境界。成公绥《隶书体》谓:“纷华璨烂,絪缊卓荦,一何壮观!繁缛成文,又何可玩!……仰而望之,郁若霄雾朝升,游烟连云;俯而察之,漂若清风厉水,漪澜成文。”[41]晋代书法受“自然”玄学影响,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美。庄学从自然情调上的超越,才能忘形发现“神”。《语林》谓温峤“姿形甚陋”,《晋书》仍谓其“少标俊,清彻英颖”,显然是忘形而发现“神”的结果。“忘象”作为玄学家们的生活准则,表现出他们对对精神世界的注重及精神自由的追求。
在玄学家们看来,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才能“忘象”,才能由形而神,便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即“神”的超越。
结语
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背景,出现了钟繇、卫恒、王羲之等重要书家及书法理论家。魏晋书家,大多崇尚“儒道兼综,礼玄双修”思想。从钟繇的“天然”“流美”,卫恒的“自然无为”,王羲之的“得意忘象”,无不体现“道”的内涵与“艺”的生命结合和“玄理”与“空灵”的想象结合。“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42]追慕逍遥自在的理想生活,到大自然中获得内心精神的满足,用自然界各种事物或各种自然现象展示书法之美。书体不再被汉隶所禁锢,逐渐从实用发展到书家的个性风格,从传统的篆隶演变出真、行、草书,从而才有“魏晋风韵”的书风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