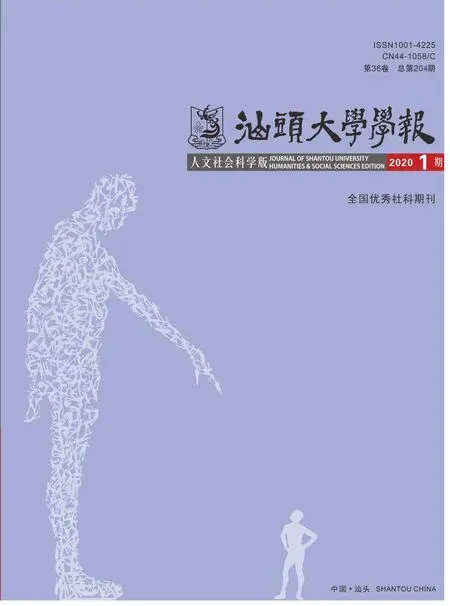仪克中《剑光楼词》与粤词风气之转移
2020-12-10
(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嘉道以后,粤词进入鼎盛阶段,风气丕变,由平和浅易转向清空醇雅,浙派开始主宰词坛。究其原因,实和学海堂词人群的兴起有重要关系。而在学海堂最早的词人中,除吴兰修外,仪克中是最有成就的一家。仪克中词继响姜张,格调醇雅,具有鲜明的浙派风味,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话》中谓:“余所见粤词,近推吴石华、仪墨农为最。”[1]2830江沅亦谓:“沅往岁薄游粤中,交吴学博石华、仪上舍墨农,俱喜为词……墨农之才学为仪征阮宫保暨诸先达所推许,以其余技为词,颇喜石帚、玉田……精妙独至。”[2]而吴兰修本人,对仪克中亦推崇有加;“吾粤百余年以来,留心词学者绝少。墨农以精妙之思,运英俊之才,发为倚声,大得石帚、玉田之妙。岭表词坛,洵堪自成一队矣。”[3]可以说,在嘉道以后粤词接受浙派词风的过程中,仪克中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在岭南词学史上,仪克中是一位绕不过的人物。
仪克中(1796-1837),字协一,号墨农,别号姑射山樵。先世为山西平阳人,至其父担任广东盐运使司知事,遂寄籍番禺。著有《剑光楼词》一卷,收词107 首,有咸丰十年(1860)半耕草堂刻本,光绪八年(1882)学海堂刻本。
一、“吹冷胭支”的凄怨之音
仪克中现存词包括伤春、伤别、羁旅、纪行、题画、咏物、感旧、悼亡、酬赠、抒怀等作,题材较为广泛,大多是其性灵的直接抒发和情感的自然流露,“修辞以诚”,真挚感人。就其总体而言,格调比较低沉,弥漫着一种缠绵悱恻的感伤幽怨情怀。江藩在《风入松·书仪君墨农〈剑光楼词〉后》中这样描述他读仪词的感受:“苹洲擪笛谱新词。吹冷胭支。”[4]确实,仪词中充满了“幽韵冷香”,凄清冷落是其鲜明的艺术特色。
仪克中词的感伤格调和悲悯情怀与其身世经历不无关系。“(仪克中)少有奇气,读书过目成诵。尝出市纵观告示,归,录出不遗一字,人咸异之……性灵敏,为文顷刻数千言立就。又能于方寸楮中作小楷数百,见者叹绝。阮文达公课士学海堂,先生和方孚若《南海百咏》,一夕而成,公深器之。”[5]366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督粤编修《广东通志》,参与其事者多为饱学硕儒、地方俊彦,仪克中时年22 岁,就被任为采访,缒幽迹险,剔苔扪碑,搜集到不少珍贵史料。仪克中虽然才高名重,但科举之途却并不顺畅,直至道光十二年(1832),广东典试官程恩泽于遗卷中发现他的文才,才得中举人。后任广东巡抚记室。道光十四年(1834),他受广东巡抚祁埙委托,至芦苞河疏通灵州渠,积劳发背疡,小愈又主持建惠济仓,达旦不寐,疾发而卒。仪克中虽有过人才华,而羽翼早摧,理想受挫,功业未显,其内心的纠结痛苦可想而知,这在其词中虽然没有直接表现,但仍以一种婉曲幽微的方式传递出来,让人在其“吹冷胭支”的笛音中悄然动容。
仪克中一生因为事业、生活等原因,奔波流离,足迹遍及岭南、江南、华北、西北各地,他在《霓裳中序第一·题江郑堂丈〈对酒当歌图〉》中谓江氏“平生多少事业。半付椠铅,半付轮铁”,正可看作是对自身际遇的写照。翩然沙鸥,江湖孤飞,因此词中有不少书写羁愁旅恨的作品,如下面这首《浣溪纱·松溪舟夜》:
月暗堤长树影连。一星萤火坠浓烟。夜凉如雨抱愁眠。
只有虫声来枕底,更无尘梦到鸥边。听风听水又经年。
此词描写舟旅夜况,起笔“月暗”两字为全词定下基调,所“暗”者不仅有晦暗的景象,亦有暗淡的心情。因为月色朦胧,所以江上、岸边的景物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只有一点在浓烟中坠落的萤火看得真切。“坠”字锻炼极工,让人联想到生命的失意及希望的破灭,但又不可实指,兴象玲珑,意蕴无穷。词人此时听到的是唧唧的虫声,如闻叹息,如对梦呓,想到的是“听风听水又经年”,于是只有在如雨的凉夜中“抱愁而眠”了。再看下面这首《卜算子·花洲夜泊》:
孤艇压芦花,人在烟中语。一阵风来又不闻,吹到江心去。
抛卷拥愁眠,冷梦和灯煮。水驿寒鸡唱早潮,数点敲蓬雨。
四围芦花,一叶小艇,举目四眺,茫茫无人,只能听到浓烟之中传来的隐约人语,可是一阵风起,连这人语声都给吹散了,这里所写的绝不只是环境的清幽,更反映了词人心灵深处的孤独,带有某种哲学意味上的普遍意义,以诗意的语言表现了人类的生存困境。环境如此寂寞冷落,词人只有抛书愁眠,一帘幽梦,四壁青灯,在报晓的寒鸡和淅沥的雨声中迎来又一个孤寂的日子。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作为多愁善感的文人,仪克中对爱情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悟。吟咏爱情的作品虽然在《剑光楼词》中并不是很多,却占据着特别的地位,其中赠妓词只有寥寥二、三首,绝大多数表现的是与妻子之间的深厚情感。仪克中和妻子情谊甚笃,婚后度过了一段琴瑟和鸣的生活,但是由于聚少离多,仪克中遂将缠绵悱恻之意化作绮丽小词,且看《浣溪纱》:
枕底新凉透鬓丝。孤灯残梦耐寻思。小楼人坐五更寒。
南浦绿波鸥梦远,西风红豆雁书迟。最无聊处有谁知。
小楼独卧,孤枕难眠,于是起床静思,直至天明,“南浦”两句则又加重一笔,写道归乡既难成,情书又不至,真是令人情何以堪。
婚后大约数年,他的妻子就亡故了。他在《浣溪沙·烛灺虚堂欲四更》的序中写道:“予悼亡一纪矣。壬辰六月,晤雨生于杭郡,信宿衙斋,谆谆以此事相劝。”按壬辰为1832 年,时其妻已亡故一纪,则当在1820 年,克中此时才25 岁,于是连这种远阻天涯的相思也成为广陵绝曲,但是他对亡妻的情意却丝毫未减,以致十余年不曾再娶。在《百字令·枯荷悼亡内》中,他抒发了对妻子的无穷思念:
水天惨碧,乍离魂欲堕,澹阳扶起。雾鬓风鬟凝望绝,零乱一匳寒翠。黯黯容华,恹恹气力,捱得黄昏几。断香残梗,此时争忍相对。
况是病骨支离,秋灯池馆,雨搅愁心碎。记取赤阑携手立,笑把双头曾指。梦冷鸳鸯,盟寒鸥鹭,不见凌波至。露华渐重,盈盈难搁清泪。
这首词将枯荷与亡妻合二为一,很多地方花即是人,人即是花,达到一种浑融的艺术境界。词人面对残花败叶,不禁想到亡妻,于是悲从中来,以致神思恍惚,分不清花也人也,遂以拟人手法,写下“离魂欲堕”等伤心句,及至“断香残梗”,才回到不忍面对的现实中:原来面前所对的只是枯荷,妻子早已香消玉殒。下阕词人复以奇幻之笔将人花合一书写愁思,至“记取”云云则脱离物象,追忆往事,盖此时词人已经情不能已,故放笔直书,直到“凌波”等句,情感方才稍稍平息,将笔触定格在那晶莹的露华(佳人的泪珠)上。这是一幅形神兼备的写意画,也是一曲跌宕起伏的抒情曲,高唱入云,感人至深。
仪克中才学既高,游历又广,因此结交了不少名士显宦,这些人对仪克中的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不仅他们的揄扬有利于提高克中的名气,而且相互的切磋也有利于提升艺术造诣,诚如谭莹所说:“孝廉则东南名士争拜下风,台省钜公缅怀旧雨。陆机入洛,敢问葫芦;韩琦帅扬,与赏芍药。复有朝廷人物,风雅总持;庆历词章,文昌下降。亦共呼为才子,许以台司。挥玉麈以谈诗,掷金龟而命酒。沈隐侯之名笔,见独王筠;丁敬礼之小文,定于曹植。唱《郁轮袍》而谁屑,读《宝剑篇》而夙知。鉴即千秋,师惟一字。”[6]此外,友朋之间的交往酬唱也为仪克中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素材,其中那些伤别之作,写得特别深婉缠绵。如《八声甘州·韩江送陈登之北上》:
算年来此别最关情,秋气况萧森。共栖迟客路,君兹远举,我费沈吟。待问古人怀抱,几辈解伤心。握手都无语,日暮江浔。
雁影一绳低处,把十段湘桥,练作愁城。更风风雨雨,满耳是离音。最难得,连宵剪烛。再相逢,还否念而今。凉波外,丹枫攒恨,目断遥岑。
“算年来”句劈空而来,直抒胸臆,说明词人已是情不能已。“共栖迟客路”表明这是客中之别,较之一般的别离更令人动容,而万千情意,只能尽在“握手无语”之中,盖情到深处,似有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下阕词人目睹城亦含愁,耳听雨作离音,使万物皆着我之色彩。然后回忆连宵往事,悬想重逢情景,都能看出一段缱绻深情。最后以拟人化的写景结束,含有不尽之意。纵观全诗,确有一种“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仪克中还与朝鲜诗人李尚迪(字惠吉,号蕅船)有过一段交往,堪称中外邦交史上的佳话。李蕅船于1831 年10 月随朝鲜使团来到北京,当时仪克中寓居北京,两人遂结文字之交。仪克中绘制《苔岑雅契图》,并且广征诗什赠之。李蕅船归国后,请本国首揆之子申少霞(命准)绘制《黄叶怀人图》,亲自题诗二十八章寄与仪克中,首章即怀仪克中,中有“多买五色丝,欲绣剑光楼”之句,仪克中感其意,遂作《海天阔处》答之,这首词主要表达了对二人友谊及李氏才学的赞美,虽然格调不似一般怀人之作感伤,但是从“听萧萧黄叶,波涛万里,浑一样、愁无奈”等句,仍能看出作者对友人深挚的怀念。
人在短暂的一生中,会经历很多变故,世事苍茫,盛衰更迭,敏心善感的诗人对此尤有体会,仪克中词中就有一些感旧伤怀之作,描写了生命的无常变化,表现了人在自然和时间法则面前的渺小无力,反映了人类生存的深层困境。比如这首《忆旧游》,序云:“丁亥岁游潮州,馆杨桂山观察幕,小春望后一日集来鹤堂,为消寒之会。歌者陈郎,十四年前旧识也,形容蕉萃,而声情渺绵。追忆旧游,不胜今昔之感。酒罢池亭徙倚,觉慵云恋树,寒月怯波,益增怅触,忽不知其词之所自云。”词曰:
正幽怀仗酒,雅会消寒,坐列清讴。蓦见参疑信,把十年旧事,都上心头。记得穗城南畔,笛谱按凉州。每斗挂高墉,云停隔浦,人倚层楼。
萍逢怅何限,且绾取红牙,拍散新愁。一样风霜里,怎可怜蒲柳,偏不禁秋。还顾冷吟身世,炯炯剩双眸。漫醉倚池阑,烟痕蘸月摇梦鸥。
这首词可以与老杜的《江南逢李龟年》并读,杜诗写于安史之乱以后,所以具有社会实录和史诗性质,但从表现的细腻程度和艺术技巧而言,此词则要略胜一筹。“蓦见参疑信”写初逢时的将信将疑,极为传神。然后转入抚今追昔,书写身世之感。词人痛感自己犹如风霜中的蒲柳,弱不禁秋,于是欲借红牙歌板“拍散新愁”,但是愁情弥甚,唯有狂饮大醉而已。又如《高阳台·故人几辈,凋谢经年,感旧悲秋,怆然有作》:
痩竹风嘶,枯荷雨碎,几番推枕难眠。一段幽怀,伤心又是经年。秋声渐到惾榈叶,听萧萧、秋已无边。最堪怜,短梦苍苔,旧雨黄泉。
湖山莫问欢游地,记歌嬴画壁,纸醉花天。蓦地销魂,西风吹散华筵。泪铅镕作辛酸句,任秋坟、鬼唱荒烟。更淒然,半壁灯昏,满砌虫喧。
词人在今昔的巨大反差中,追忆似水华年,感受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西风吹散华筵”,可以说是人生无常的一个隐喻,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如青春、理想、美貌,都被这无情的西风吹走了。词人以“瘦竹风嘶,枯荷雨碎”这样几乎字字泣血的文字,倾诉着自己心头的剧痛。
仪克中的一些词所表现的哀愁是不能尽指或不可确指的,并非某单一的元素,甚或说不清道不明,“幽约怨悱不能自言”,让人无从琢磨,而又无处不在,如漠漠烟云,笼罩四野;似霏霏细雨,湿遍年光。这实际上是对人生世道深广的忧患和悲悯在心境上的一种投射。比如《南浦·蓬窗听雨,坠梦如云,尽日怜春,闲愁似水,用玉田生词韵赋之》:
夜雨隔蓬听,乍成眠,却又莺啼催晓。坠梦觅江浔,东风软、况是闲愁难扫。垂杨夹岸,断烟浮出青山小。目送流红何处去,魂醉王孙芳草。
心头无限江山,向声声橹里、等闲过了。新恨未分明,销凝候、蓦地旧愁都到。回眸望渺。而今燕语鸥盟悄。一片归云留不驻,窗外夕阳多少。
这首词连标题在内,共出现三个“愁”字、一个“恨”字,但是其所愁所恨者何?却又不着一字道出。细绎之,似有舟船为家的客愁,“流红何处”的伤春,无缘鸥盟的思隐,但是这些又不足以构成本词的全部内涵。“坠梦觅江浔”,其梦为何?“心头无限江山”,江山何处?这些词句都有丰富内涵,极易兴起人的联想,但是却又难以实指。或许正是如此,作者才以“闲愁”目之。
总之,读仪克中词,我们总能感到一片伤心,无穷哀感,但是仪克中并非纯然文弱书生,谭莹谓其“前生青兕”,[6]叶衍兰谓其“平生倜傥尚侠气”,[5]366而他自命居处为“剑光楼”,亦可说明他除了一颗琴心,还有一颗剑胆。因此他不会沉溺于哀怨中不能自振,他必然要在词中实现心灵的自我超越。
二、“烟水酣春”的闲逸情怀
纪游及题画之作在仪克中词中占据重要地位。仪克中一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作为对这种生活的直接反映,除了羁旅行役词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纪游写景词。此类词以景物描写为中心,融进词人深厚的情感体验及丰富的人生思考,其中最为突出、最为动人的一点便是摆脱尘世喧嚣的山林之思。而山水是自然之画,画作是人工山水,或许正是因为自然山水与山水画作之间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仪克中的题画词才和纪游词一样,也充满了对归隐山林的的汲汲向往。因此这两类词在情感向度上是一致的,都体现为对忧愁苦思的消融与超逸。
仪克中在词中虽表现出隐逸情怀,但并不意味着他要避世隐居,放下尘世的功名事业,去做所谓的“方外之士”。实际上,魏晋以降,隐逸的内涵及方式逐渐发生演变,譬如唐朝,“盛唐诗里所谓的隐逸,往往是指朝隐或吏隐,即任官期间的假日休沐,或与同僚游览两京有名的别业。或在长安附近置有别业,每天下朝回家住在郊园里,也都可以称为隐居。”[7]6像这种暂时休憩于山林园泽的隐逸,其实是比较轻视形迹,而更重“心隐”的。仪克中的山林之思,当即属于此类。
仪克中的山林云水之游,大多具有一种“超然独往”的澹远之趣,“独往”是我们阅读其纪游词的突出感受之一。所谓“独往”,最早见于《庄子·在宥》:“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8]289《列子·力命》也说:“独往独来,独出独入,孰能碍之?”[9]207当然,形迹上的“独往独来”只是皮相,真正的“独往”在心不在貌,在神不在形,诚如葛晓音所说:“这种独往独来是指在精神上独游于天地之间,不受任何外物阻碍的极高境界,这与《逍遥游》里所说的超脱社会制约和自然规律的至人之道是一致的。”[7]6至于形迹上的“独往独来”只是一种修道方式,藉此更易达到精神上的“独往”之境,究其原因,当是人精神的不自由大多缘于“有待”,即有所追求,将功名利禄萦系于心,从而生出种种欲望及竞逐,而这些都是人作为社会性生物在尘网中难以避免的,而要做到“无待”,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隐居山林,远离喧嚣,从而泯却机心,收视反听。
仪克中常常在词中不着痕迹地表现“独往”的境界,有意无意地塑造“独往独来”的形象,在清空幽独的意境中表现其精神的了无滞碍、委运随化。如这首《小重山·秋日维扬泛湖夜归》:
荷气时从柳外闻。楼台无数好,傍斜曛。略抛几处与闲云。云难管,落叶占纷纷。
岑寂破秋雯。虹桥才棹过,已黄昏。星光萤火乱成群。偏无月,那辨二三分。
值得注意的是“闲云”“落叶”两个意象,云是“闲云”,而且“难管”,极力表现了云卷云舒、自由自在的状态,而落叶其实也是“难管”的,因此才能毫无拘束地“纷纷”而落。这两个意象实际上是词人自由心态的物化,唯有以不为物役的心态观照万物,才能发现(或者毋宁说是赋予)其逍遥自在的精神品质。而在人物冥契的境界中,词人浑然不觉时间流逝,所以当其棹舟经过虹桥的时候,才会惊讶“已黄昏”。此时天上无月,唯有暗淡的星光与飞舞的萤火交织成一片,浑然难辨,这种境界颇近似于庄子消泯万物差别的“齐物”之境,正是在这种境界中,词人才能做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从而“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8]14,实现精神的超尘绝俗与高度自由。再如这首《卜算子·湖上晚归》:
一觉冷泉亭,早是湖烟暝。虫语西泠唤月回,胜有闲鸥等。
遥认白沙堤,碧蘸寒灯影。暗绿迎人忽到门,柳下维渔艇。
在清幽孤寂中,自有一份物我冥感的惬意。词人泊舟湖上,悠然入眠,一觉醒来,已是傍晚,此时虫语唧唧,似在呼唤月亮出来与我相伴,而白鸥还在执着地等着自己。词人移舟返程,不知不觉间已到家门,门旁的绿草碧树早已侯我多时。词人完全打破物我的界限,创造出一种“万物有情”的境界,在物我的心灵交流中获得精神的抚慰与愉悦。这种境界,其实也就是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之境,或者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之境。仪克中不用任何玄言禅语,却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展现了清空孤寂的“独往”之境,体现了《列子》“独往独来,独出独入,孰能碍之”的精神,这种不落言筌的表现方式,正是其魅力之所在。
不过仪克中的纪游词并非总是表现为“独往”之境,偶尔也有一些烟火气和世俗气比较浓郁的作品,譬如描写词人和朋友在探幽访胜时的雅会,一群文士列坐于水湄山曲,花林茅篱,聆讴遣兴,飞觞赋诗,颇有些金谷芳会或兰亭雅集的味道。其打动人心之处,在于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对“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珍爱,对“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的流连,对一切美和爱的赏会和眷念。譬如这首《瑶台聚八仙》:
尺五天边。春耐老,风信遍约华鞯。也同欢侣,来趁满树红嫣。仙吏行厨金鑿落,粉侯纠席玉连钱。酒如泉。夕阳劝驾,犹腻香鞭。
回看人影在地,向断钟韵里,尚耸山肩。唤烛高烧,围坐未许花眠。多情客先破晓,又引蝶莺参烂漫禅。春聊饯,竟艳传日下,索看吟笺。
词前有序:“城南花之寺海棠最繁,游屐颇盛。己丑春杪,郑梦生、铁生醵诸同好携侍史十余人宴于花下。日斜宾散,予止谭康侯农部,招铭山明府,联榻僧庐,话几达旦。明日,林莪池大令来追昔欢,饮复抵暮。赋此以志俊游。”据此可知,本词所写是词人和友朋连日俊游欢饮的情形,上阕描写游者之众(“风信遍约华鞯”)、环境之美(“满树红嫣”)、宴饮之盛(“仙吏行厨金鑿落,粉侯纠席玉连钱”)及欢聚之久(“夕阳劝驾,犹腻香鞭”),已是神完气足。行笔至此,几乎令人无以为继,不料词人却能绝处使生,下阕继写秉烛夜宴的场面,颇有曹植、李白宴享诗的气度,其情其景,和太白“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颇为神似,词情至此达到高潮。词中景、事、人、情诸要素构成一个诗意的生态系统,具有特别兴发人心的力量。
关于游赏,古人有“身游”与“神游”之说,“神游”最早见于《列子·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9]41是指梦中游历。后则泛化,凡以精神游历者均可称为“神游”,如沈约:“迹屈岩廊之下,神游江海之上。”(《谢齐竟陵王教撰〈高士传〉启》)苏轼:“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念奴娇·赤壁怀古》)仪克中的题画词,多题山水景物,词人借咏作画者(或藏画者)的游踪旅迹,来抒发自己的林下高致,在此过程中,词人实际上经历了诸多“神游”。如下面这首《渔家傲·为姚述斋题〈桃源问津图〉》:
烟水因缘随处可。清溪曲曲刚容舸。夹岸桃花疑待我。从捩柁。倘逢渔父询曾过。
一段浓云津外锁。更无人处苍苔破。却喜沙鸥迎个个。天上坐。神仙只是闲人作。
众所周知,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塑造了一个虚无缥缈、似有实无的世外桃源形象,文章结尾特意点出太守遣人及刘子骥寻找桃花源,却均无果而终,用意即在于此。本词则一反其道,开宗明义,指出“烟水因缘随处可”,意谓桃花源无处不在。至结尾又补足其义,谓“神仙只是闲人作”,原来只要心中富有闲情逸致,便可过桃源中仙人般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否定了现实世界中的桃花源,而仪克中则肯定了心灵空间中的桃花源,实在都是各有其道理的。又如《声声慢·题李菊水明经〈春水垂纶图〉》:
嫩薲开处,新渌生时,清溪镇日粼粼。谁赋沧海,此中合有元真。知鱼果堪自乐,任桃花、空笑闲人。慵倚棹,看落红点点,争饵游鳞。
何日扁舟载酒,共南湖西塞,烟水酣春。短笠轻蓑,肯教更染红尘。从今莫谈旧梦,惹滩头、鸥鹭含瞋。待去隐,把浮生、都付钓纶。
上阕描写画图景色,“知鱼果堪自乐”用庄子“濠梁观鱼”典,表达纵情山水的快意;“闲人”并非真正避世隐居之人,而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李涉《题鹤林寺壁》)之人,所以才会任由桃花“空笑”。下阕抒发归隐之情,词人既从正面肯定了自己的理想,又从反面否定了以前的做法(“从今莫谈旧梦”,旧梦当指入世的理想,所以才会为鸥鹭所瞋),但是词人“扁舟载酒,共南湖西塞,烟水酣春”的归隐之志要实现又谈何容易,他只能暂时休憩于山林,并借词作抒发自己的隐逸情怀和自由精神。不过,以此句来概括词人在纪游及题画等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富于韵致的审美情趣及追求闲逸的精神特质倒是颇为恰切的。
三、“姑射山人”的浙派风味
仪克中词取法南宋姜张醇雅词风,具有鲜明的浙派风味,对此,诸家看法较为一致,仪克中同时代的人即已指出这点,上引江沅及吴兰修语皆为明证。郭麐在序《剑光楼词》时亦谓其“入姜、张之门,腴而弥澹”。[10]谭敬昭在《剑光楼词》的题诗中说:“姑射山人绰约姿,裁云镂月谱新词。”[11]显然亦着眼于此。仪克中本人对自己的词学观念曾有明确表述,其《徵招》词序云:“高凉客馆,雨中戴金溪观察见过,论词以石帚、玉田为正宗,竹垞、樊榭为嗣响,且示旧作,戛戛乎高唱也。赋此纪之。”词曰:
人生难得秋前雨,赏音更难同调。几日听阶桐,意悠悠谁晓。高轩勤顾我,领前辈、流风多少。大雅扶轮,清言霏屑,色丝天造。
妙喻拟宗门,姜张后、谁继南灯末照。法眼在鸳湖,剩传衣厉老。纷纷从论定,把豪杰、一时推倒。又何日,剪韭申盟,记此缘非小。
在序中,他介绍了戴氏的论词宗旨,并且深以为然,所以在上阕才称其为“同调”,下阕则申述戴氏之意,构建了一个从南宋姜、张到清代朱、厉的词学谱系,并且对之推崇备至。显然,以仪克中为浙派中人,诚为不诬。此外,在仪词中有为数不多的作品标明效体、用韵,其中多能反映出和浙派的联系。如《南浦》序云:“蓬窗听雨,坠梦如云,尽日怜春,闲愁似水,用玉田生词韵赋之。”表明用玉田韵。《续〈乐府补题〉五首和顾涧翁》用“天香”“水龙吟”“摸鱼子”“齐天乐”“桂枝香”5 个词牌,分咏药铫、红蕙、萍、笛、螾,而浙西词派之形成,正是从模拟《乐府补题》开始的。
仪克中的词,多数清气盘空,或清幽孤寂,或清润秀雅,如秋华、春秀,各臻其美,且都具有空灵剔透的特质,这是其得姜张遗风的重要体现。仪克中词之所以能够做到清虚空灵,其原因是多样的。其一即善于以丰富的的联想力和想象力,营造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使人进入一个“神观飞越”的境界中。如《齐天乐·题端州石室,旧滨沥湖,今去水远矣》:
何年星向人间聚。山川效灵如许。洞杳涵幽,崖穿透碧,招客瑶天深处。凌风欲举。问台畔双鸳,几时飞去。一线湖光,棹歌约略在遥渚。
愔愔昼常带雨。小轩凉梦醒,山月疑曙。石燕冲云,琪花坠雪,夜半仙归闻语。尘缘似缕。且剔藓镌题,莫孤游趣。古岸垂杨,想重来作絮。
小词描写石室石峰景色,清幽深秀,缥缈空灵,颇有白石老仙风味。词人特别善于调动手段,把人的思绪引向方外之界,如开篇即以坠星比喻山川,已经把人的视野置于辽阔的天地之间,下文的“招客瑶天”“几时飞去”都在有意把人的视线从人间引向天上,至下阕的“夜半仙归闻语”,更是使人如入幻境,不知仙也尘也。至于“涵幽”“透碧”“冲云”“坠雪”“剔藓”等意象的锻炼,“约略”“疑”等词语的使用,莫不为词增填了幽寂清冷的色调及朦胧要渺的意蕴。
其二是结构跳跃性强,陡转陡接,开合跌宕,令人莫测端倪。这样的词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在艺术上却自有其价值。如《探春慢·题汪湘舲〈苏台消夏图〉》:
偶结莺邻,难忘鸳侣,一夏山塘小住。如此烟波,个侬情致,况对蕅花无数。乍可流连里,那尚觉、人间有暑。朅来几度薰风,旧欢吹堕何处。
客况倩谁怜取,待小阁焚香,画图愁觑。石记三生,梦圆双笑,禅榻鬓丝如许。为想重逢地,知尚否、旧时眉妩。且释幽怀,凤城聊话秋雨。
上阕是一幅闲适的消夏图,下阕则是一幅缠绵的怀人图,这种结构上的陡转,造成词境词意上的空白,像书法、绘画上的“留白”或“计白当黑”一样,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从而使灵气流动其间。这种写法在白石词中不乏其例,如《一萼红》(古城阴),上阕抒发冶游之乐,下阕书写身世之感,但在结构上却没有任何铺垫,换头处直接接入“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数句,可谓硬语盘空,故被陈锐称为“挺接者”。[12]4196其实,仪克中的这首《探春慢》何尝不也是“挺接”呢?
浙派学习姜张词风,其末流常至于徒写性灵,空疏无物,肤廓饾饤,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仪克中词则无论是写哀怨之情,还是抒闲适之意,都具有较为真切的情感和充实的内容。但是不可否认,他也有少数作品内容空虚,情感寡淡,滋味不够深厚隽永,缺少感动人心的力量。如《红情·赋红梅》,陈永正评为“细细的勾勒,层层的渲染,真是‘体物入微’,但读者们很难从中猜寻出什么深刻的含义来。”[13]152又如《剔银灯·赋洋琴》,描写听洋琴所触发的愁绪,但是究竟为何而愁,却让人如堕云里雾里,不明究竟。咏物词的价值当然不只在于它有“什么深刻的含义”,但是毋庸讳言,情感沉郁、寄托深微显然是衡量咏物词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咏物词的高境是将作者的家国、身世之感融入其中,非徒摹形写貌,雕红刻翠,南宋咏物词高出一般咏物词的地方即在于此。仪克中虽然生于清朝由盛而衰之际,但是朝廷的空架子还在,所以其咏物词自然不及姜张等人的沉郁深厚。
仪克中词颇为醇雅,这也是其师法姜张的必然结果。其词之雅,体现在意与辞两个方面。以思想情韵而言,仪词主要书写身世之哀怨及隐逸之闲适,格调雅正,情意真挚;即使闺怨、赠妓等关涉男女之情的作品,绝大多数都能以严肃端正的态度写作,丽而不亵,沉而不浮。以语言艺术而言,仪词工于雕琢烹炼,颇多秀句俊语,又能做到不伤及整体的淋漓元气,无堆砌饾饤、生硬晦涩之弊。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九成台上,假榻兼旬,地迥天孤,江围岫列,每当幽夕,写以竹声)上阕:
浦远驰烟,城高滞月,万家树影冥冥。渐柝喧虫语,阑倚空青。江上数峰不见,想有人、鼓入湘灵。凝眸处,中流灯火,一片春星。
起笔用一组四字对,凝练工整,“驰”“滞”显系琢炼而来,前者是写烟雾浮动,状若奔马,后者辄写月亮高悬中天,寂然不动,一动一静,相映成趣。“柝喧虫语”“阑倚空青”又都采用了非常规的组合方式,便觉笔力矫健不凡,而下边数句却自然流转,毫无滞塞之感,可见作者调控语言节奏的能力很强。
仪克中注重炼字,善用动、形等词,又善运用比喻、拟人、联想及化虚为实等修辞格,语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如以“廿八弦敲愁里。只敲得、愁零碎”(《剔银灯·赋洋琴》)写听琴之感,“敲”“碎”等字让愁具有形状与质感。以“剩有夕阳,拖绿过窗纱”(《虞美人·垂杨不系东风住》)写春日暮景,“拖绿”一词可谓极尽巧思,将夕阳移动,窗外蓊郁苍翠的大树之影投射于窗纱上的景致细腻地表现出来,有画工所不能到者。以“正隐隐,风过也,茜裙响屧”(《红情·赋红梅》)写落梅之状,意谓风过之时落花之声隐隐,如穿着茜裙的西施在响屧廊中缓步,真是凄艳之极。以“莫讶归舟较重,满囊诗载秋还”(《木兰花慢·绕蓬青不断》)写秋游归兴,虽从李易安“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春晚》)化出,但易悲愁为诗囊,便觉饶有雅兴。诸如此类的句子,在仪集中不胜枚举,足见其语言之造诣。
不过,仪克中词的风格并不单一,非姜张所能完全笼罩。部分词作有苏辛之风,豪气鼓荡,壮怀激烈,时杂沉郁悲慨之音,虽然整体而言气势不及苏辛,但仍铿然有金石之响,堪称集中别调。此外,仪集中有少量词,一改醇雅的语体风格,以诗语入词,甚至运用俚俗语、佛道语,带有民歌或杂谣风味。
当然,在仪词中这样的作品终究属于“别调”,数量很少,仪词带有鲜明的浙派风味,其主导风格是姜张一脉的醇雅清空,这是毫无疑问的。
四、仪克中与粤词风气的转移
清代康乾词坛,浙派势力最大,流风所及,几乎达到“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程度。至嘉庆后,常州派影响逐渐上升,最终取代浙派,主盟全国词坛。不过,岭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风气,接受全国词坛的沾溉和影响具有一种滞后性,所以当嘉道时期,岭南词学开始昌盛时,其所受的最大影响,不是当时已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常派,而是仍有一定影响的浙派。岭南词坛一变之前平庸浅易之风,词作清空骚雅,字斟句酌,词艺大幅提升。作为此时岭南词坛的领军人物之一,仪克中对于当时词坛风气的转移影响甚大。
仪克中对词坛风气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学海堂实现的。学海堂由清代经学大师阮元督粤时所建,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挂牌课士,道光四年(1824)建筑落成。其创建目的,“是针对广州士人高谈妙论,空疏无据的学风,倡导实学,确立汉学在广州的学术地位。”[14]167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做了改革,“首劝经史,而诗赋具备,唯独不授举业,专勉实学。”[15]此举必然会使师生不受科举考试的指挥约束,从而得以从容地钻研、探讨学术与文艺。虽然在理论上,诗赋位在经史之后,但据统计,在收录学海堂学子优秀课艺的《学海堂集》(共四集)中,文学类作品所占比例要远高于经史考据训诂之文。[16]学海堂是当时岭南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包括词体创作及词学研究)的主阵地。学海堂不设山长,实行学长负责制,八位学长各有专长,共同协作,在日常教学及管理中负有重要责任,对学海堂自由笃实的学风之形成关系甚大。
仪克中曾在学海堂求学,深得阮元器重,此后又于道光十四年(1834)补为学海堂学长。在其之前出任学长而擅长词艺的,只有吴兰修与张维屏,吴氏当时词名藉甚,为词坛领军人物,对岭南词坛的繁荣及风气的转移有不容忽视的的影响,但其词风出唐入宋,既受南宋纯雅词派法乳,又受北宋婉约词派沾溉,所学并不限于姜张一脉。张维屏以诗坛耆老身份涉足词苑,词风偏于豪健,时入萧闲一格,实承康乾岭南词风之余绪,与浙派相去甚远。仪克中则几乎倾力以学姜张,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为岭南词坛树立了一个学习姜张的范本。因此,就对后世岭南词坛的实际影响而言,仪克中不仅在张维屏之上,甚至亦在吴兰修之上。在吴、仪死后不久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学海堂专科肄业生许玉彬等人就组织成立了岭南词史上最有影响的词社——越台词社。其成员多达二、三十人,多数来自学海堂,除许玉彬外,其他如沈世良、陈澧、陈良玉、黄玉阶、徐灏、谭莹、叶英华等人,日后都成为岭南词坛的中坚力量。越台词社的群体风格带有鲜明的浙派风味。[17]这与仪克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当有密切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吴兰修、仪克中同为学海堂人,又皆以词名,当时即有论者将其二人相提并论,但到了后世,仪克中的声望与影响却似乎不及吴兰修,不仅冒广生在论“粤东三家”之前的岭南著名词人时只言吴兰修与陈澧,不及仪克中,就连陈澧似乎也把仪克中忘记了。陈澧在《水龙吟》(词仙曾伫峰头)词序中云:“壬辰九月之望,吾师程春海先生,与吴石华学博,登粤秀山看月,同赋此调,都不似人间语,真绝唱也。今十五年,两先生皆化去。余于此夜,与许青皋、桂皓庭登山,徘徊往迹,淡月微云,增我怊怅,即次原韵。”显然对壬辰九月登山赏月、倚声填词的程春海、吴兰修极为怀念。其实参与壬辰之会的还有仪克中,按之仪氏《水龙吟》小序:“领荐后侍座师程春海祭酒同吴石华学博登粤秀山玩月山响楼。石华词先成,师次韵和之,命克中继作。壬辰九月十五夕也。”可证。而仪克中的被遗忘,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仪克中生年晚于吴兰修七岁,而卒年又早于吴兰修两岁,其行辈与影响自然略逊一筹;二是吴兰修曾参与学海堂的筹建,从学海堂课士即任教其中,后又担任学海堂首任学长达13 年之久(从道光六年至道光十九年),而仪克中担任学海堂学长仅有3 年(从道光十四年到道光十七年),故其弟子门生之数量与影响远不及吴氏,像组织越台词社的许玉彬就是吴氏弟子,而“师因生显”原本也是常理。三是吴兰修除善文艺外,于历史、地理及算学等方面亦颇有成就,为一文化通人,而仪克中的影响则集中在文艺方面,影响范围自然不及吴氏。但作为嘉道时期宗法姜张而卓有成就的最早词人,仪克中对此后粤词风气转移的影响,确实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