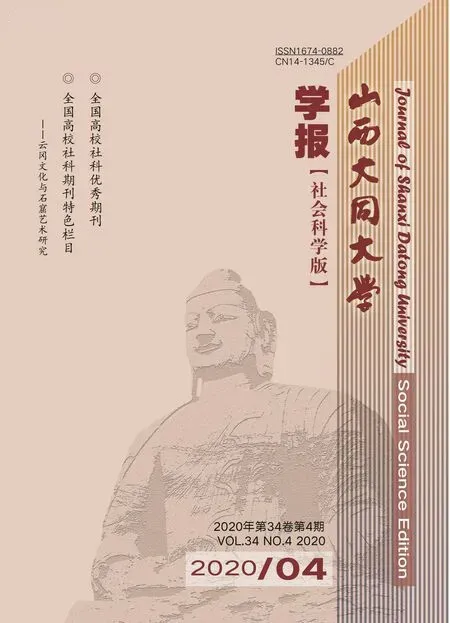王维《杂诗》(其二)“寒梅”意象指向性新探
2020-12-09樊梦瑶李定广
樊梦瑶,李定广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梅花”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写作的典型意象,通常会与高洁的品格相连。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1](P100)松、竹、梅作为“岁寒三友”,因其傲雪凌霜,坚贞挺拔,也通常被用来象征人品清俊。此外,梅花也常作为“思乡”的代名词,而其承载乡情和怀人主题,受到的关注度却较少。
一、部分学者对王维《杂诗》(其二)“寒梅”意象含义的过度解读
阅读诗词作品时,时常存在“过度解读”的现象,即将作者写作中本来不具备的含义牵强附会在诗作中,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读。在唐代诗人王维的《杂诗》(其二)中,“寒梅”意象的含义颇具争议。有学者将此诗与《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渡汉江》二诗做对比阅读,证明诗人常年客居在外,好不容易见到一位同乡,然而他向老乡询问的,却不是常理之中的家人安康与否或者家中琐事,反倒出人意料地问起窗前那株梅花的开落。这不能不说是他“近乡情怯”的恐惧心理在作祟,他因害怕听到来自家人的坏消息,因而不敢打听那些细节。[2](P65-69)更有学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举出年幼时语文老师与亲人分隔两地,再次重逢时,竟然关心起“家里的电灯还亮吗?”这样的小事。[3](P70-72)换句话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种所谓的顾左右而言他的情感是“互通”和“共鸣”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佐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样的诗句也被拿来当成了例证。
二、王维《杂诗》(其二)“寒梅”意象指向“思乡”
笔者在阅读唐宋诗词中,发现“梅花”意向大多被指向了“思乡”层面,并不包括恐惧或者顾左右而言他的心理状态。
王维《杂诗》组诗共有三首诗作:
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已见寒梅发,复闻啼鸟声。心心视春草,畏向阶前生。
这三首《杂诗》,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不能分割开来作单独解读。因此,要弄清诗中“寒梅”的指向问题,我们不妨将这三首诗逐一进行解读,以弄清三首诗在意蕴上的联系,这将有助于我们弄清问题的真相。
其次,“梅花”作为乡情的承载时,常被用在边塞音乐中加以表达。因此,如果我们弄清了梅花意象融入边塞音乐时与乡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会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明确。
(一)王维三首《杂诗》的主题都是思乡 如果各用一字来概括三首诗蕴藏的情感,那便是“盼”、“问”、“愁”。由此可见,王维的这三首组诗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思乡。三首诗分别从三个不同侧面描写,表达了复杂微妙的情感,其中“思乡”的主旨仿佛一根细线,紧紧地连接着这三首诗,使它们统一在共同的乡情主题之下。这颇有些类似于散文写作中“形散神聚”的笔法。“聚”是第一要义,而“散”只是表现形式上的不同而已。
在第一首诗里,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不完全等同于作者,而只能被视作由诗人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诗人情感的寄托)在盼望着那封家信能够如期寄到家人手中,让他们能够快些得知自己的近况。望着江面上来自江南的船只,他的心早已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
在第二首诗里,主人公向同乡询问故乡的消息。在无数个可能出现的问题中,诗人仿佛一位高明的“摄影师”,在众多芜杂的镜头里,偏偏饶有兴致地截取了其中最有“诗味”的一个。“诗人没有剪下记录问父母、问妻儿的那几段胶片,而是剪下了记录问寒梅的这一段胶片,因为连老家窗前的那株寒梅是否开花,诗人都问到了,至于其它问题,也就自不必多言。这里正显示了诗人“妙手偶得”的功夫,表达了他浓烈的思乡之情。”[5](P20-21)
梅花本是故乡的象征,而主人公的窗前,又恰巧栽种了几株梅花——也许,那几株梅花还是诗人自己或其父兄亲手种植的呢。有了这些因素的铺垫,见到同乡时,诗人的脑海中就不自觉地浮现出梅花在冬日傲雪开放的情态,于是就对着那位熟悉的同乡脱口而出:“寒梅著花未?”事情的来龙去脉本就如此简单。
有了第二首中对于故乡的深切思念,第三首中思归却仍不得归的愁苦才会变得顺理成章。“已见寒梅发”是乡人的回答,“复闻啼鸟声”亦是来自乡人的描述。而后两句则是这位游子在异乡的所见。他看着阶前的春草是那么的茂盛,因此想到时间又到了春天。这是一年的开始,也就意味着,游子的飘零之旅又过去了一年。可怕的是,他仍旧无法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没法和挚爱的亲人们团聚。于是,他开始变得畏惧春草的生长。他是多么希望日子不要这么快就溜走啊!这也反映出游子思归心切。
可以说,王维的《杂诗》三首诗中,思乡的情绪呈现状态是由浅入深的,诗韵悠长。正如清代诗论家宋顾乐在《万首唐人绝句选》中说:“以微物探悬念,传出件件关心,思家之切”。[6](P62-64)无独有偶,高适在《塞上听吹笛》一诗中,借用“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1](P200)一句,将梅花的飘落化作丝缕乡愁,书写戍边将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杜甫在《江梅》中,用“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绝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1](P512)四句道尽了梅花与乡愁之关联,那片片娇艳盛开的梅花,勾起了诗人浓浓的乡愁,越是无法返回故乡,诗人的思乡之情就越是深重。李频在《湘口送友人》中,用“零落梅花过残腊,故园归醉及新年”[1](P412)一句,表达了对友人在新年回家后与亲人欢聚一堂的祝福;秦观在《踏莎行》中以“驿寄梅花,鱼传尺素”[7](P100)一句表现了长久流放在外的羁旅游子对故乡绵长的思念之情。古代诗人用梅花作意象指向思乡之情的诗词名句不胜枚举,他们或者对自己庭院里那枝寒梅难以忘怀,或者对故乡那位叫做“梅”的姑娘无法淡忘,或者对父兄培育梅花之情难以割舍……
(二)“寒梅”意象与《梅花落》古曲思乡之情的关联性“梅花”意象作为思乡之表现,在诗词中常与北方边塞音乐关联,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是古曲《梅花落》。
顾名思义,《梅花落》取梅花凋零之意,借以传达思亲怀人的伤感,也就自然能让人们产生了缠绵的思乡之情。“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似乎梅花的凋落带给我们的总是无穷无尽的感伤。从演奏方式上来说,《梅花落》属于“横吹曲”。关于“横吹”一词的含义,音乐学界从来莫衷一是。“《律书·乐图》云:‘横吹,胡乐也。’张骞到西域时,将这种演奏方式传到西京,得到《摩诃兜勒》的乐曲。李延年之后,汉朝经常把这首曲子作为军乐,慰藉戍边将士。这段文字最早见于晋人崔豹《古今注》,唯宋代陈旸和元代马端临,在他们的著作中,把这段文字列在‘大横吹、小横吹’的条目之下,这就把古代的‘横吹’和宋元时期的乐器——大横吹、小横吹混为一谈,歪曲了《古今注》的原义。”[8]
用“横吹”的方式演奏的音乐类型通常是军中所用,是一种常用于北方边塞中的音乐类型。对于这一点,杨荫浏先生曾有过一段极为精彩的描述:“横吹,是军中马上所奏之乐。起初虽然横吹也称鼓吹,但后来区分渐精,而用横吹曲作为边塞音乐的常见演奏形式,通常是用箫、胡笳和鼓角演奏,而这些乐器通常乐音低沉,所以常被用来演奏低声部的思乡之曲也就是顺理成章了。”[9](P40)“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10](P119)这是范希文笔下的边地情景。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听到由鼓角演奏的边地乐曲时,整个边塞仿佛都呈现出一片凄凉肃杀之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戍边将士们产生思乡之情便是在所难免了。
唐代以后,“横吹曲”的主奏乐器由鼓角类转向了管乐。“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1](P108)这是李益笔下由芦管引发的日暮乡关之思。征夫们听到芦管吹奏的北方边塞音乐,从而勾起了他们“一夜乡心五处同”的思乡之情。
“横吹曲”作为一种边塞音乐的演奏形式,总是和思乡之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古曲《梅花落》就是“横吹曲”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因此,它与思乡怀人的情感关联,也就不言自明了。
与《梅花三弄》用梅花来表现高洁的人格不同,古曲《梅花落》的意象常用来表现思乡怀人之情。比如李谪仙《吹笛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1](P200)崔鲁《梅诗》云:“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11](P301)这些都是用《梅花落》古曲的乐声来表现征夫戍卒的思乡之情。
“《梅花落》古曲奠定了苍凉悲怆的感情基调,以曲传情,把音乐形象、景物特点和人物情感融为一体,或视觉、听觉、感觉有机地组合,构成深邃、哀婉的诗歌意境,显示音乐情绪的强烈感染力。戍边将士远离中原,深入胡地,听到胡音,孤独之感、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同时,音乐作为一种隐性语言,其旋律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意味。当它与歌词融合时,所蕴含的靠听觉感受的情韵,自然地转而与高度浓缩的曲调名结合,使得曲调名和乐器成为形式与内容合二为一的意象。一首首笛曲是全诗构思的基础和关键。体现了征人之苦的主题,表现了征夫戍卒羁旅在外的浓浓乡愁。不管是笛曲《折杨柳》、《关山月》、《梅花落》,还是“闻笛”时所兴的不同情感,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笛曲所表达的情感都是思乡和怀人。”[12](P35-42)上古时期,诗乐舞为一体,后来逐渐分离,舞蹈因为其对肢体的要求较高,因此较快分离出来。诗歌中却仍然保留着诸如韵、格律、叠句、衬字等音乐的因素。换句话说,相比舞蹈与诗歌,音乐与诗歌具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说,王维的《杂诗》(其二)中“寒梅”意象的指向性与古曲《梅花落》音乐传达的意象更为接近,即思乡之情。
(三)理解上要突破读者的“期待视野” 姚斯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出现的历史时刻,对他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这种方法明显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的尺度。”[4](P21)换言之,面对一篇文学作品,因为读者的阅历、经验、文化程度等的不同,他们会对这篇作品有着不同的接受和预判。这些固定的指向和观念结构,将会导致他们满足或是失落情绪的产生。
在一般读者既定的观念中,一个长久客居他乡的游子见到自己的同乡后,理应向他询问家中的一切状态。就像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诗,“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1](P2055)同样是他乡遇到老乡,诗人的询问从旧园到院中栽种的果树的成熟情况,一路问下去,真可谓事无巨细。无疑,这是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所以我们觉得这首诗所写的一切出自情理之中,是不奇怪的,也是乐于被接受的。回到王维《杂诗》(其二),抒情主人公竟然只询问窗前梅花的开落,这显然不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过去一些学者便对此诗中“寒梅”的指向性别做深解,认为是一种恐惧心理所致。
试想,如果我们暂时抛弃自己的固有观念和“期待视野”,忘记那些所谓的“本应该”和“就该是这样”,会不会为我们理解此诗拓宽道路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结论
首先,王维《杂诗》三首须被当做一个整体看待,不能单独进行解读。三首诗的主题都是思乡,只不过采取了三种不同的表达形式,逐层递进式地加深了思乡的程度。
其次,古代诗词中的“梅花”意象往往与北方边塞音乐紧密相关。古曲《梅花落》的演奏形式“横吹”通常被用于军乐的演奏中,最初用胡笳和鼓角演奏,低回哀怨的低声部音乐,加深了征夫戍卒们的思乡情绪;后来改用笛子和管乐演奏时,其指向的乡关之思和怀人情感也并没有因为演奏所用乐器的不同而减损。在古代“诗乐一体”的文化语境中,“寒梅”意象传达的主旨指向“思乡”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读者在理解本诗时,要突破习惯的“期待视野”,不要作过度解读,回到作品本身作自然而然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