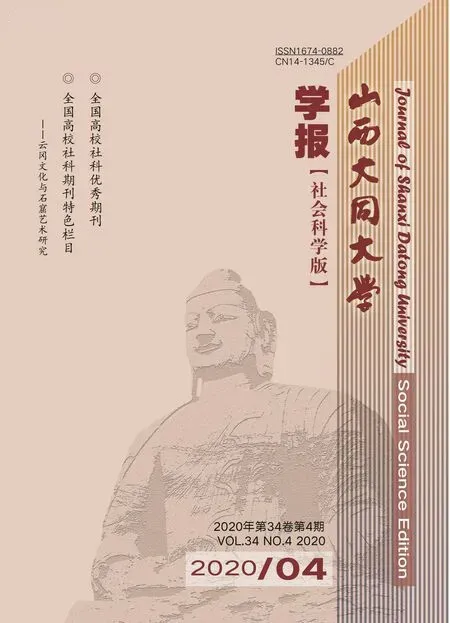元嘉十七年至元嘉末南北军事关系演进研究(440-453)
2020-12-09王永平
王 业,王永平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225000)
在中古史研究中,南北军事对抗是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这是由这一时期分裂和动乱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总的来看南北朝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南北均势逐渐被打破的过程,刘宋则处于这一过程之关键阶段。刘宋初年的疆域范围为东晋南朝南方诸政权之最,北魏明元帝时夺得河南之地,宋文帝即位后先后发动三次北伐,意图收复失地,均以失败告终,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北伐的失败,招致北魏南进临江,此后泰始年间刘宋又失去淮北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一系列重大军事事件的发生,标志着南北对立局势向着北强南弱发展。自太延五年(元嘉十六年,439)北魏统一北方起,至元嘉二十七年(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宋魏大战止,是太武帝南进战略逐步推进的时期,也是宋文帝北伐构想从酝酿到实践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堪称宋魏军事进程中最为激烈的阶段。陈金凤[1]、杨恩玉[2]、王永平[3]等学者先后就元嘉北伐失败的原因及影响等问题作了探讨。其实,无论是宋魏关于仇池的争夺,还是北魏的侵边给刘宋带来的震动,亦或是刘宋北伐的失败与魏军的南进,都应当放进南北军事进程中加以考察。本文拟由上述三件大事展开,重点讨论两国军事交争的背景,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南北观念的变迁。
一、北魏军事战略重心的南移与宋魏争夺仇池
据《魏书·世祖纪》载,太延五年(元嘉十六年,439)三月,“诏卫大将军、乐安王范遣雍州刺史葛那取上洛,刘义隆上洛太守镡长生弃郡走。”[4](P89)这是到彦之北伐后,南北之间军事冲突的第一次记载。此时北方尚有凉州未平,但其对北魏并无多大威胁。所以,此次北魏攻取上洛的行动,可以看做是其经略南方的试探之举。随着北魏南进战略的不断推进,宋魏之间围绕着“中间地带”[5](P14)的争夺自然会愈演愈烈。不过,此时发生的仇池动乱,将宋魏双方军事斗争的区域转移至了陇南一角。
氐族杨氏虽立足仇池前后计三百余年,但其政权常常附属于他国,《读史方舆纪要》就说“仇池尝臣附于南北间,故不称国”。[6](P146)刘裕代晋建宋后,刘宋旋即进仇池主杨盛车骑大将军,加侍中。[7](P2405)杨盛虽仍奉晋义熙年号,但告诫其子杨玄“善事宋帝”。[7](P2406)杨玄继位后,仇池虽仍为刘宋蕃臣,但不久即与刘宋发生冲突。据《宋书·吉翰传》载:“(元嘉)三年,仇池氐杨兴平遣使归顺,并兒弟为质,翰遣始平太守庞咨据武兴。仇池大帅杨玄遣弟难当率众拒咨,又遣将强鹿皮向白水。咨击破,难当等并退走。”[7](P717)这次事件起因当是仇池统治集团内部动乱,反映出刘宋与仇池之间并不和谐的关系。或是此事让杨玄认识到不能一味依附于刘宋,加之畏于北国的军威,当年十二月(426),魏军据长安讨伐赫连昌时,杨玄遣使内附,北魏以杨玄为都督荆梁益宁四州诸军事、假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南秦王,[4](P72-73)自此仇池开始依违于宋魏两国之间。
仇池动乱的根源,在于其内部不稳定的继承制度及统治者不度时机的对外经略。纵观仇池国前后三百余年的历史,多发生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继承权之事。[8](P229-253)杨玄死后,其弟杨难当废杨玄子杨保宗自立,杨保宗谋袭杨难当,事泄,为杨难当所囚,[7](P2406)杨保宗后逃往北魏。与此同时,杨难当不断侵扰宋魏边界。《宋书·氐胡传》载:
先是,四方流民有许穆之、郝恢之二人投难当,并改姓为司马。穆之自云名飞龙,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寻为人所杀。十年,难当以益州刺史刘道济失蜀土人情,以兵力资飞龙,使入蜀为寇,道济击斩之。时梁州刺史甄法护刑法不理,太祖遣刺史萧思话代任。难当因思话未至,法护将下,举兵袭梁州,破白马,获晋昌太守张范。法护遣参军鲁安期、沈法慧等拒之,并各奔退。难当又遣建忠将军赵进攻葭萌,获晋寿太守范延朗。其年十一月,法护委镇奔洋川,难当遂有汉中之地。以氐苻粟持为梁州刺史,又以其凶悍杀之,以司马赵温代为梁州。十年正月,思话使司马萧承之先驱进讨,所向克捷,遂平梁州,事在《思话传》。[7](P2406-2407)
据《魏书·世祖纪》载,延和三年(元嘉十一年,434)正月,杨难当克汉中,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长安。[4](P83)杨难当所送的雍州流民,应该就是克汉中掳掠所得。在被宋军击败后,杨难当又奉表谢罪,宋文帝“以其边裔”,[7](P2407)原而不问。此后,太延二年(元嘉十三年)、太延五年(元嘉十六年),杨难当又两次寇魏上邽,与刘宋的怀柔政策相同,北魏仅派兵击退仇池兵,又“以玺书责让”杨难当。[9](P3946-3947)宋魏两国对杨难当采取宽容态度,主要是因为仇池方隅之地,且非要冲,并无侵占必要。
元嘉十八年,杨难当再次“倾国南寇,规有蜀土”,宋将裴方明、刘康祖平仇池,杨难当奔北魏。魏太武帝即命古弼等人征仇池,同时移书至徐州。[7](P2334-2335)北魏在书信中不仅声称要为杨难当复仇,还指责刘宋元嘉七年的北伐活动。所谓“不欲违先故之大信也”。[7](P2334)当然是托辞,前面我们说过,此前北魏面临着复杂的军事形势,只是无暇南顾而已。因此,宋魏之间关于仇池的争夺,应当看做北魏南进战略实施的第一环。
若从南北之争的大环境下看待这一事件,那么仇池这一方隅之地的意义就决定者宋魏首次对抗的输赢,从北魏“十道并进,连营五千,步骑百万,隐隐桓桓”[7](P2336)的兵力部署也可看出其对此之重视。《资治通鉴》较为简略的记载了此次战事:“魏皮豹子进击乐乡,将军王奂之等败没。魏军进至下辩,将军强玄明等败死。二月,胡崇之与魏战于浊水,崇之为魏所擒,馀众走还汉中。将军姜道祖兵败,降魏,魏遂取仇池。”[9](P3963)虽然仇池之失对刘宋并无多大影响,但却昭示着北魏南进之初刘宋的失败。北魏虽取得仇池,却无法实现在这一地区的稳定统治,氐人不久即复推杨保宗弟杨文德为主,联合刘宋,屯葭芦城,“武都、阴平氐多归之”。[9](P3964)此后仇池虽仍偶有动乱,但已无法影响南北军事格局。
但对宋文帝来说,刘宋接连两次的失败是耻辱。史载仇池失后,“前雍州刺史刘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宝及善马,下狱死”,胡三省注云“宋人舍功录过,自戮良将,宜其为魏人所窥”,[9](P3965)胡三省并未明说明“过”指什么,笔者认为不单单指二人贪赃,或与仇池之失有关。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事件的刺激下,宋文帝开始着手北伐准备。元嘉二十二年,宋文帝先后以宗室三王出镇要州,即正月以抚军将军、南豫州刺史武陵王刘骏为雍州刺史,以湘州刺史南平王刘铄为南豫州刺史,六月又以刘铄为豫州刺史,七月以征北大将军、南兗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为徐州刺史。[7](P93)《宋书·孝武帝纪》载:“明年,徙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自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7](P109)又《宋书·文九王·南平穆王铄传》载:“二十二年,迁使持节、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时太祖方事外略,乃罢南豫并寿阳,即以铄为豫州刺史,寻领安蛮校尉,给鼓吹一部。”[7](P1856)可证宋文帝此举确实是为其经略北方做准备工作。
二、元嘉二十三年北魏的侵边与刘宋安边论议之兴起
元嘉二十三年,北魏遣兵侵略刘宋冀青兖三州。关于此次侵边的背景,《宋书·索虏传》载:
其年,太原民颜白鹿私行入荒,为虏所录,相州刺史欲杀之,白鹿诈云“青州刺史杜骥使其归诚”。相州刺史送白鹿至桑乾,焘喜曰:“我外家也。”使其司徒崔浩作书与骥,使司徒祭酒王琦赍书随白鹿南归。遣从弟高梁王以重军延骥,入太原界,攻冀州刺史申恬于历城,恬击破之。杜骥遣其宁朔府司马夏侯祖欢、中兵参军吉渊驰往赴援,虏破略太原,得四千余口,牛六千余头。寻又寇兖、青、冀三州,遂及清东,杀略甚众。[7](P2341)
《魏书》则全然未提此事,仅于《世祖纪》中记太平真君六年(元嘉二十二年,445)十一月选六州兵勇猛者二万人,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领,为二道,各一万骑,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太平真君七年二月,永昌王仁至高平,擒刘义隆将王章,略金乡、方与,迁其民五千家于河北。高凉王那至济南东平陵,迁其民六千余家于河北。[4](P100)不过,考虑到此时“盖吴扰动关右,薛永宗屯据河侧”,[4](P942)北魏大军忙于镇压叛乱,其突然发兵南侵,应当是有缘由的。《宋书·索虏传》的记载或为邻国传闻,但也有一定的真实性。
北魏侵边引起刘宋的较大震动,《宋书·何承天传》称“时索虏侵边,太祖访群臣威戎御远之略”,[7](P1705)此时何承天上《安边论》,[7](P1705-1710)详细阐述了他“安边固守”的主张。何承天虽属一介文士,《宋书》本传评价他“才非军旅”,其在到彦之北伐时担任右军录事,未必亲历前线,但一定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因此《安边论》是何承天对北伐惨败教训的总结成果。[10]我们知道,到彦之北伐失败不仅促使宋文帝进行反思,并使他在后来北伐谋划中更加小心谨慎,所以当北魏侵边时,宋文帝只是访群臣“威戎御远之略”,而非急于报复。
《安边论》所提出的“安边固守”主张,概括起来可分为“移远就近,以实内地;浚复城隍,以增阻防;纂偶车牛,以饰戎械;计丁课仗,勿使有阙。”需说明的是,何承天虽主张当务之急是安民保境,但并没有放弃北伐的打算,他认为只有等到“比及十载,民知义方”,才能“简将授奇,扬旌云朔,风卷河冀,电扫嵩恒,燕弧折却,代马摧足,秦首斩其右臂,吴蹄绝其左肩,铭功于燕然之阿,飨徒于金微之曲。”[7](P1707)因他的建议大多贴合刘宋的实际情况,在此不作过多论述。最值得注意的是,何承天提出放弃青齐地区的一部分土地,他说:
今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万家,此寇之资也。今悉可内徙,青州民移东莱、平昌、北海诸郡,兖州、冀州移泰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兰陵,北阨大岘,四塞之内,其号险固。民性重迁,闇于图始,无虏之时,喜生咨怨。今新被钞掠,余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土,宜其歌抃就路,视迁如归。[7](P2353)
何承天的这个建议,来自其对三国时期魏吴对峙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现实的考虑。《安边论》有云:“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戍,家停羡溪。及襄阳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徙沔南,以实水北,曹爽不许,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鉴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宋魏对峙虽在表面上与魏吴对峙有相似之处,但毕竟“三国时期是一种在没有游牧者入侵的复杂因素影响下形成分裂的典型例子”,[11](P12)仅以军事实力而论,北魏也非曹魏可比,因此,何承天援古证今是不妥当的。宋文帝在位时,刘裕北伐的成果仅余青齐一地,如利刃般插入北魏疆域,宋魏间历次军事冲突,青齐地区自然首当其冲。明元帝南侵时,曾派叔孙建等率众“徇下青、兖诸郡”,[4](P62)到彦之北伐失败,“青、齐搔扰”,[7](P1464)加之此次魏军的侵扰,引起了何承天的担忧。他认为应该充分发挥青齐地区地理优势,将易被北魏抄略地区的民众转移至拥有天然屏障之处,换言之,即放弃一部分边境领土。那么,这样的看法是否合理呢?
我们将目光投向北魏,孝文帝初年,北魏也面临着和刘宋类似的难题,《魏书·韩秀传》载:
延兴中,尚书奏以敦煌一镇,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群官会议,佥以为然。秀独谓非便,曰:“此蹙国之事,非辟土之宜。愚谓敦煌之立,其来已久。虽土邻强寇,而兵人素习,纵有奸窃,不能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进断北狄之觇途,退塞西夷之窥路。若徙就姑臧,虑人怀异意。或贪留重迁,情不愿徙。脱引寇内侵,深为国患。且敦煌去凉州及千余里,舍远就近,遥防有阙。一旦废罢,是启戎心,则夷狄交构,互相来往。恐丑徒协契,侵窃凉土及近诸戍,则关右荒扰,烽警不息,边役烦兴,艰难方甚。”乃从秀议。[4](P953)
韩秀认为移敦煌至凉州乃“蹙国之事”,可谓卓见。敦煌的优势除了“进断北狄之觇途,退塞西夷之窥路”外,更重要的是,能将北魏与外敌的战线往西推移。如果移镇凉州,自弃领土,不仅凉土会受到侵扰,更会造成“关右荒扰,烽警不息”的后果。韩秀的观点完全可证何承天移民说之妄。研究者业已指出,古代疆界缺乏近代以来政治地理中领土那样的严格意义,在不同时期和地方的国界线上,常见以变动频繁为其特点的不稳定性,以及随之在地域上所表现的宽幅接触地带,此种情形在国内分裂割据时期亦属经常而明显。[12](P146)南北间不断的军事冲突,造成边境线或南或北移动,更易模糊民众的疆界意识。
《安边论》又云:
今承平来久,边令弛纵,弓竿利铁,既不都断,往岁弃甲,垂二十年,课其所住,理应消坏。谓宜申明旧科,严加禁塞,诸商贾往来,幢队挟藏者,皆以军法治之。又界上严立关候,杜废间蹊。城保之境,诸所课仗,并加雕镌,别造程式。若有遗镞亡刃,及私为窃盗者,皆可立验,于事为长。
十余年来,宋魏双方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关系,除了仇池一隅的争夺以及当年北魏的侵边外,南北之间几乎无军事冲突,这也造成了顾琛所谓的“江东忘战日久,士不习兵”[7](P2446)的情况。何承天建议对双方往来“严加禁塞”,由此可见,在南北对立、民族隔阂的大环境下,双方边境地区仍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往来。可以说,刘宋“元嘉之治”局面的出现,也当归因于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
自五胡交争,中原沦陷,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数十年从未停歇北伐。历次北伐的目的复杂多样,既包括满腔热情之士力图恢复故土,亦有怀政治野心的权臣欲提升个人威望。桓温北伐收复洛阳,上疏反对“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13](P2573)要求还都旧京,其时“北土萧条,人情疑惧,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13](P1545)名士孙绰反对这一建议。他除了说明北方残破不堪为都外,又表示“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踰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餐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13](P1546)真实道出了侨人在安稳环境中形成的偏安心态。王羲之更是认为“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13](P2095)罗宗强先生认为,“偏安心态终于发展成为东晋士人的主要心态,这与东晋百年的偏安局面是紧密相联的。偏安政局之形成,实为其时南北政治格局使然。……要之,江左百年,从政局到人心,都没有创造出恢复中原的条件。北方既战争不断,南方亦动荡不宁,于是割据的局面得以维持。江左士人,也就在这样一个局面里寻找自己的人生天地。偏安的心态,也就在这样的局面里得到充分的发展。”[14](P292-294)当然,偏安心态并非玄学名士所独有,而是根植于保守、安于现状的农业文明的一种广泛心态。
三、宋文帝的北伐构想与太武帝的南进方略
与其父刘裕类似,宋文帝有着强烈的经略北方追求。史载元嘉二十三年北魏的侵边后,宋文帝“思弘经略,诏群臣曰:吾少览篇籍,颇爱文义,游玄玩采,未能息卷。自缨绋世务,情兼家国,徒存日昃,终有惭德。而区宇未一,师馑代有,永言斯瘼,弥干其虑。加疲疾稍增,志随时往,属思之功,与事而废。残虐游魂,齐民涂炭,乃眷北顾,无忘弘拯。思总群谋,扫清逋逆,感慨之来,遂成短韵。卿等体国情深,亦当义笃其怀也。”[7](P2341-2342)同一年,刘宋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广州刺史陆徽与(沈)演之赞成上意。及平,赐群臣黄金、生口、铜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谓之曰:‘庙堂之谋,卿参其力,平此远夷,未足多建茅土。俟廓清京都,鸣鸾东岱,不忧河山不开也。’”[7](P1685-1686)宋文帝一再表达北伐意愿,但刘宋为北伐所做的准备远远不够,除了前述元嘉二十二年三王出镇外,史籍所记的惟有元嘉二十六年,以竟陵王刘诞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后将军、雍州刺史,又“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7](P2025)
宋文帝疏于北伐准备,主要原因当与刘宋国内政治发展有关。如所周知,宋文帝在位时期,崇尚文教,励精图治,“元嘉之治”每每为史家所称赞。不过,研究表明,宋文帝猜忌心极重,元嘉一朝统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除去徐羡之等顾命大臣及檀道济、刘真道、裴方明等功臣被诛杀,主相之争成为元嘉年间政治发展的主线。宋文帝亲政后,为进一步强化皇权,削弱权臣和高门士族社会人物的权力,提携其弟刘义康主政。因宋文帝“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属纩者相系”,[7](P1790)加之刘义康性好吏事,招揽贤士,结党营私,甚至想取帝位而代之,引来宋文帝的不满,史称“自是主相之势分,内外之难结矣”。[7](P1791)元嘉十七年,宋文帝先诛刘义康同党成员,又贬刘义康为江州刺史。不久后的元嘉二十二年,宋文帝又借孔熙先、范晔谋反案,将刘义康及其子女贬为庶人,徙赴远郡,直至最后将其处死。[15]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发现,元嘉前中期,由于身体欠恙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宋文帝无暇外顾,因此北伐准备一拖再拖。此外,宋文帝的性格举棋不定,这一性格缺陷在二凶巫蛊之祸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上欲废劭,赐濬死。而世祖不见宠,故累出外蕃,不得停京辇。南平王铄、建平王宏并为上所爱,而铄妃即湛妹,劝上立之。元嘉末,征铄自寿阳入朝,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议久不决。与湛之屏人共言论,或连日累夕。”[7](P1848)或也影响了其做北伐准备。
田余庆先生说:“通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战争,似乎可以归结为如下一种认识。由于中国历史具有统一的传统,凡是统治北方的势力,都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暂时现象,都不自安于南北分裂状态,都企图南进以求统一。反过来看,南方的政权,大体也是这样。”[16](P241)太武帝亦是如此,其在统一北方后,南进战略便一步步推进。但是,作为一位久经战场的君主,面对着国力甚强的南方政权,加之苻坚淝水战败的前车之鉴,他不得不保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元嘉二十七年宋魏之间的战争,就是宋文帝北伐理想的实施与太武帝南进方略推进的结果。
《宋书·索虏传》载:
二十七年,焘自率步骑十万寇汝南。初,焘欲为边寇,声云猎于梁川。太祖虑其侵犯淮、泗,乃敕边戍:“小寇至,则坚守拒之;大众来,则拔民户归寿阳。”……焘初闻汝阳败,又传彭城有系军,大惧,谓其众曰:“但闻淮南遣军,乃复有奇兵出。今年将堕人计中。”即烧攻具,欲走。会泰之死问续至,乃停寿阳。遣刘康祖救悬瓠,焘亦遣任城公拒康祖,与战破之,斩任城。焘攻城四十二日不拔,死者甚多,任城又死,康祖救军渐进,乃委罪大将,多所斩戮,倍道奔走。[7](P2344-2345)
宋文帝告诫淮、泗诸郡之语,表明其时他无与魏军作战的想法,这当与上文所述宋文帝举棋不定与疏于准备有关。北魏围攻悬瓠不克,太武帝又闻汝阳败、彭城有敌军后大惧欲退走,亦可证其谨慎的态度。最能反映太武帝心态的,是他致宋文帝的两封信。[7](P2345-2348)
太武帝指责刘宋“使间谍,诱奸人”,[7](P2346)称与刘宋结好的北方诸国均已为其消灭,“以彼无足,故不先致讨”,[7](P2346)可见其对外战略划分的轻重缓急。所谓“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7](P2346)当指太平真君十年(元嘉二十六年)北魏伐柔然一事,此后柔然“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4](P2294-2295)他一再表明北魏军队依仗骑兵与习武的优势,其时北魏虽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文治,但从太武帝夸耀鲜卑“马背中领上生活”[7](P2348)来看,他对汉文化仍持保留态度。[17]他说“彼常愿欲共我一过交战,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7](P2347)又说“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度,如此释江南使彼居之”,[7](P2346)这又回到了前文所述太武帝的谨慎心理。在他看来,统一之事不可一蹴而就,由他开其端,成者或在后人。胡三省认为观此二书可见“魏人犹有惮南之心”,“盖高祖之余威,而边垂诸将犹为有人也”。[9](P4005)姚宏杰先生对胡氏观点作了申论,并进一步认为,太武帝实无统一意愿,瓜步之战也不过是北魏对刘宋进攻的反遏制行动。[18]就以上分析来看,这种观点是可商榷的。
也许是北魏侵豫州之举及太武帝两封带有侮辱性的书信的刺激,当年七月,宋文帝决意北伐,但“举朝为不可,唯(江)湛赞成之”,[7](P1849)沈庆之所言“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踰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7](P1998-1999)应该能代表一部分大臣的意见。与宋文帝临时决意相对的是刘宋匆忙的战前准备,这从《宋书·索虏传》中的一段记载可见一斑:
是岁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又以兵力不足,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其余悉倩暂行征。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7](P2349)
与元嘉七年到彦之北伐时北魏群臣的恐慌不同的是,此次他们只是请遣兵“救缘河谷帛”,太武帝则丝毫不担心,“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9](P4013)初期刘宋的三路北伐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然至九月,太武帝在安排太子拓跋晃屯漠南备柔然,吴王拓跋余守平城后,率军南进。[9](P4013)魏军汲取了此前南侵时攻城损失惨重的教训,直接略地至长江北岸,宋军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不过,魏军虽然饮马长江,但江淮间诸多城戍依然为刘宋所控制,太武帝亦自知无法实现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于是,宋魏双方相互妥协后,魏军于次年正月撤军。
史载魏军临江时,“上登石头城,有忧色,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9](P4025)宋文帝对北伐失利表示悔恨,但元嘉二十九年又再度北伐,则知亦是临时起意。此次北伐的决策当与鲁爽兄弟的南归及北魏形势有关。元嘉二十八年,鲁爽兄弟南归时上书云“虏主猖狂,豺豕其志,虐徧华、戎,怨结幽显。自盱眙旋军,亡殪过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7](P1923-1924)加之第二年太武帝去世,北魏内部争夺统治权,使得宋文帝认为有可乘之机。青州刺史刘兴祖建议伐河北,其言亦切直,然“上意止存河南,不纳”,[7](P2353-2354)可见宋文帝执念之深。此次北伐行军路线一仍其旧,将领亦无突出才能,其失败也是必然的。关于刘宋元嘉年间北伐失败之原因及影响,前贤时彦已有较为细致的讨论,在此不赘述。
就北魏一方而言,其虽属胜利者,但“士马死伤过半,国人并尤之”,[7](P2353)长期四处征伐造成国力衰弱,亟需修生养息,这预示着宋魏之间一段相对和平时期的到来。不过,宋文帝以后的刘宋诸位君主,已无经略北方的意愿,而北魏所面临的形势也迥异于太武帝前期,宋魏军事关系进入到崭新又复杂的阶段。
四、结语
宋魏仇池之争实际上是北魏南进战略实施的结果,边隅一角的仇池国,因卷入两国交争,最终国祚不保。元嘉二十三年北魏的侵边引起刘宋较大的震动,何承天的《安边论》提出“安边固守”的主张,实际上是东晋以来偏安心态的进一步发展。宋文帝虽有强烈的经略北方追求,但元嘉年间前中期国内政治矛盾及本人举棋不定的性格,使得刘宋疏于北伐准备,反观北魏,太武帝的南进战略虽逐步推进,但此时南北国力尚较均衡,因此元嘉二十七年宋魏大战造成了双方俱伤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