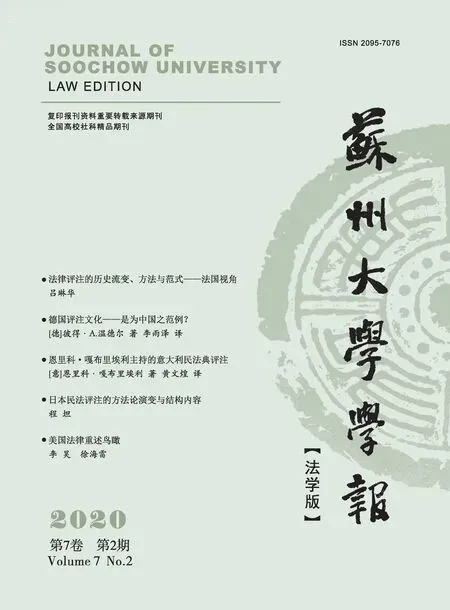德国刑法分则中的客观归责问题*
2020-12-09鲁道夫伦吉尔邓卓行
[德]鲁道夫·伦吉尔 著 邓卓行* 译
一、导论
客观归责理论如今的传播已经与寿星(罗克辛)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1)Roxin Gedanken zur Problematik der Zurechnung im Strafrecht, FS für Hönig, 1970, 133ff (根据:Schünemann GA 1999, 207, 212 “诞生时刻”); 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 特别是§11.在结果犯中,该理论的任务是为了说明这样一种情况,亦即,行为人“仅仅”在条件说或者合法则条件说的意义上引起的构成要件的重要结果,也能同时作为行为人的作品归责于他。详言之,除了事先确定的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外,额外的归责阶层也属于客观构成要件。对此,这涉及的基本是总则问题,因为必须明确这样一些条件,它们在塑造行为人的行为和构成要件结果之间的关系时,不受分则构成要件中的特殊犯罪要素的影响。(2)对此: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10, Rn.55, 98, 102; §11 Rn.41.
二、客观归责的内容
在特殊客观归责的框架下,罗克辛区分了三个归责阶层,即制造不允许的风险、实现不允许的风险、构成要件的范围。(3)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11 Rn.47ff, 63ff, 90ff.就此而言,下文阐述的目的应当是:
1.对于行为对象,行为人必须首先制造一个允许风险无法涵盖的风险。在风险降低的案件中便不存在不允许的风险。进一步来说,倘若行为人没有通过法所关切的方式提升法益侵害的风险,那么客观构成要件的归责就不会成立。对此必须具体追问,处在行为前的理性观察者是否会认为相应的举止具有风险或者具有升高风险的性质。如果涉及的是允许的风险,那么就应当最终排除归责,这便是罗克辛所理解的虽然“制造了法律上重要的风险,但它却是通常(无关个案!)被允许的举止”(4)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11 Rn. 60.。在此,只要社会相当性理论认为“一种举止不只是个案中的例外,而是从一开始便被一般性地允许,并且也不是犯罪类型或者不法类型,因此它就绝不可能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5)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10 Rn. 36.,那么社会相当性理论也就占有一席之地。
2.第二阶层要追问的,是行为人制造的不允许风险是否已经在构成要件的结果中实现。在此,需要对因果历程偏离的案件加以分类。当存在介入的因果历程要素时,就必须追问行为人制造的初始风险有没有通过法律上重要的方式提升了后续因果历程中的风险,没有实现的不允许风险将被排除归责。与之相应,这还适用于这样一些结果发生的情形,它们在合法的替代行为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或者无法被注意规范的保护目的所涵盖。
3.在“构成要件的范围”那里涉及的案例群,通常无法被(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故意毁财的禁令,等等)构成要件的规范保护目的所涵盖。除了参与故意的自陷风险之外,罗克辛在此还整理了——按照他的评价,还没有充分完善——“答责范围理论”(6)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11 Rn.112.。在这一关系中,强调的关键词有:救援者的事故、不当的医疗行为、被害人的不当行为、精神损害、间接损害等进一步被提及的领域。
三、客观归责的广阔空间
不容忽视的是,从寿星的视角来看,上文简述的客观归责理论(7)比如赞同的观点:Schönke/Schröder/Lenckner StGB,25 1997, vor§13 Rn. 91ff; SK-StGB-Rudolphi (1997年6月), vor§1 Rn.57ff; Jescheck/Weigend Strafrecht AT,5 1996, § 28 IV; Wessels/Beulke Strafrecht AT,30 2000, Rn.176ff.反对直至批判的观点:Armin Kaufmann FS für Jescheck, 1985, 251ff (罗克辛的回应:Roxin GS für Armin Kaufmann, 1989, 237ff); Hirsch FS für Lenckner, 1998, 119ff. 折中主张:Schünemann GA 1999, 207ff. 保守主张:Kühl Strafrecht AT,3 2000,§4 Rn. 42.与《德国刑法》第222条和第229条有着广泛的联系,其中的问题需要被研究。该理论的实践重点无疑在过失领域,不过罗克辛(也)强调它是一般化的构成要件理论,原则上也适用于故意犯。(8)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11 Rn. 39ff, 44. 对此的补充:Schünemann GA 1999, 207, 219f, 228.
讨论客观归责时,将需要确定的焦点集中在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上的做法,有其良好和可解释的理由。但是,此处非常容易忽视的情况却是客观归责理论的意义可以延伸得更远,并且会涉及很多其他的分则构成要件。本文的意愿便是指出客观归责的这一广阔空间。
罗克辛始终强调该理论涉及的是构成要件结果的归责,在此范围内,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对此,除了《德国刑法》第212条、第222条、第223条和第229条这些相关的结果犯,他还特别提到了《德国刑法》第303条(毁坏的结果必须是“行为人的作品”)(9)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10 Rn.55.和第263条(财产损失紧随欺骗而来)(10)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10 Rn.102.,这两个构成要件也是下文的论述重点。寿星还提到了其他构成要件,也就是《德国刑法》第185条和具体危险犯(11)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10 Rn.102, 103;§11 Rn.121.,此处就不再予以研究。
四、结果加重犯的客观归责
在分则中,对具体归责问题所涉及的情况而言,罗克辛只较为详尽地研究过结果加重犯的相关标准。他是这样论述的,有些特定犯罪具有引起更严重结果的一般倾向,立法者仅在这些犯罪中设置了结果加重情形,这符合“立法只在结果发生时才适用构成要件的目的,这些结果产生于基本犯的典型风险。只有它们才能通过结果加重犯的保护目的来加以涵盖”(12)Roxin Strafrecht AT I,31997,§10 Rn.108ff, 114.。就此而言,值得注意的是罗克辛拒绝“特殊的”归责理论这一命题,与之相对,对基本犯和加重结果之间的保护目的关系而言,他强调应当从一般的归责理论中提取决定性标准。(13)就此而言,与之相同的观点:Rengier Erfolgsqualifizierte Delikte und verwandte Erscheinungsformen, 1986; Ferschl Das Problem des unmittelbaren Zusammenhangs beim erfolgsqualifizierten Delikt, 1999.
这一观点出了名的有争议,同时它更可能与通说不符。(14)对此,Vgl.Hirsch FS für Lenckner, 1998, 128f; NK-Paeffgen (1997年1月),§226 Rn.7ff; Küper ZStW 111 (1999), 785, 792ff; Lackner/Kühl StGB,23 1999,§227 Rn. 2.不过,倘若罗克辛赞同致死性理论(Letalitätslehre)和德国联邦法院的判决(BGH NJW 1971, 152)(15)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10 Rn.115. 就此而言:Rengier Erfolgsqualifizierte Delikte und verwandte Erscheinungsformen, 1986, 196ff, 214ff; ders.Jura 1986, 143ff. 不同意见:Ferschl Das Problem des unmittelbaren Zusammenhangs beim erfolgsqualifizierten Delikt, 1999, 133ff(反对致死性说), 181f(同意BGH NJW 1971, 152).,那么他在进行《德国刑法》第223条的“保护目的解释”时,就会将该条作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基本犯,并得出限制性的结论。这些结论也被支持特别归责关系这一命题的学者所拥护,其相比于客观归责的标准更为严格。批评者在此可能会注意到那些反对客观归责理论的(某些推导具有任意性的)意见。目前,客观归责理论绝不会使评价的活动空间与关于保护目的的讨论变得多余。该理论更相信,它会为构成要件的不法提供一个更好的解释模型,并且更加清楚地表达所提出的重要问题。(16)Vgl.Schünemann GA 1999, 207, 227.对于结果加重情形的重要案例群,如果能成功使业已获得承认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由此避免“创造”新的因果关系理论,那么其中就蕴含着教义学的益处。通过结果加重犯与客观归责理论的结合,其评价方面就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了,倒不如说,不能通过讨论中对“特别”归责标准的宣称,来取消这些评价方面。
五、毁坏财物的客观归责
应当用一个构成要件来继续本文的研究(《德国刑法》第303条),罗克辛已经在《德国刑法》第211条以下、第223条以下之外关注过这一构成要件。(17)本文第三部分。比如,风险降低(身体受到外物损害,其影响尚能被削弱)或者没有制造风险(有人在怂恿他人实施“日常的”生活行为时怀着这样一种希望,比如希望被劝说者的汽车在一起事故中损坏)的“标准案例”在此就应当毫不迟疑地被发现(创造)。
在司法实践中,更棘手的归责问题最有可能发生在污染(Verunreinigungen)和污损(Verunstaltungen)领域(比如,张贴海报),在这些情况中,虽然行为人可能对侵害财产的、以清洁为条件的损失具有间接故意,但是在结论上,这些损失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被害人或其委托的第三人在清除时犯了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就此而言,符合构成要件的毁坏结果——特别是从判例的立场出发来观察(18)同意的理由及其整体问题:Rengier Strafrecht BT I,4 2000, §24 Rn. 9ff.——只是由于其他人的事后(过失、重大过失、故意)不当行为才发生的。
就此而言,能否将具体的毁坏结果视为“行为人的作品”?答案应该可以在不当的医疗行为这种类似的情况中找到,亦即第一行为人只是伤害了被害人,而不当的医疗行为却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对罗克辛来说,在划定第三人答责范围的方面,涉及的乃是“最困难最不清楚的案例群”(19)Roxin Strafrecht AT I,31997,§11 Rn. 111.。他就此问道,在不根据负责程度来进行区分的情况下,医生是否会通过其他的风险替代(“消除”)原有的风险,这里的其他风险只属于医生的答责范围。如果最终涉及的结果是由第三人造成的,那么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毁坏财物的案件中人们无论如何都能够拒绝归责:罗克辛可以这样主张,比如不当使用清洁剂的行为具有损害性,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风险则完全不同于(无损害性的)污损/污染所引起的风险。另外,对因果历程偏离而言,罗克辛曾使用过一个公式,该理解绝不是必然从这一公式中产生的。根据该公式,结果需要被归责,“如果未遂行为通过法律上重要的方式提升了后续因果历程中的风险,亦即结果是未遂所制造之风险的相当性实现的话”(20)Roxin Strafrecht AT I,31997,§11 Rn. 64.。
谁通过污染和污损侵害了他人的财物,谁就引起了一种违法状态,行为人从一开始就必须预料到被损害者会去消除这一状态——完全可以对比需要医生救治的被伤害者的案例。就此而言,文献中那些希望将财产所有人的清洁行为认定为打断归责的、自由答责的自我损害的意见,就都是不妥当的。(21)Momsen JR 2000, 173. 与此相联系:Schröder JR 1987, 359, 360. 同样拒绝的观点:Behm JR 1988, 360, 361.倒不如说,这符合客观归责的标准,(22)Vgl.Wilhelm JuS 1996, 424, 425.亦即,第一结果引起者通过自己不被允许的行为招致的那些与必要的消除行为联结在一起的风险,基本上也会被归属到他自己的答责范围内。在消除手段可以避免毁坏的情况下,归责乃是不言而喻的。正确的是,第二行为人的(过失)不当行为也属于从初始风险中发展出来的风险:其他人的不当行为并不能理所当然地解除第一结果引起者的责任。谁制造了需要投入人力去控制的初始风险,谁就必须根据自己的所有经验预料到有可能会发生人的(过失的,但不是重大过失和故意的)不当行为。这不仅适用于被害人,而且也适用于专业帮助人。(23)比如,相同观点:Burgstaller FS für Jescheck, 1985, 357, 365ff; Schönke/Schröder/Lenckner StGB,25 1997, vor § 13 Rn. 102. 对此,其他观点:Frisch Tatbestandsmäßiges Verhalten und Zurechnung des Erfolgs, 1988, 423ff, 446ff; Schmoller FS für Triffterer, 1996, 223ff.
对于职业人士,罗克辛却有不同的意见。(24)Roxin Strafrecht AT I,31997,§11 Rn.111ff.要承认的是,关于其背后的倾向,也就是在(一些)介入的职业承担者那里更有可能解除第一行为人的责任,这值得进一步思考。
六、参与斗殴的客观归责
作为下一个例子,我们选取《德国刑法》第231条及其构成要件,尤其是“通过斗殴”“引起”的特定结果,此乃该构成要件的前提。这一构成要件的独特之处在于,按照通说,因果性的结果引起被归类为客观处罚条件。客观归责理论是否应当因此失去效力,尚无定论。
罗克辛对这一问题没有直接表态。(25)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23 Rn.12.根据他的解释,斗殴的危险性类型化地产生于构成要件上重要的、严重结果的发生之中。因此,这一结果也同样属于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人至少要对其有所预见。寿星希尔施(Hirsch)对此表示赞同,并在结果方面要求存在过失。(26)LK-Hirsch StGB,10 1981, § 227 Rn, 1.对罗克辛来说,从过失方面可以得出理所当然的结论,亦即与之联结在一起的客观归责标准是有效的。
在文献中,施特里(Stree)(27)Stree FS für Schmitt, 1992, 215, 221ff.主要研究了因果关联问题与希尔施(28)LK-Hirsch StGB,10 1981, § 227 Rn. 12. 希尔施的限制性方案能够与此相联系,即他批判性地反对客观归责理论(Hirsch FS für Lenckner, 1998, 119ff.),比如为了在异常的因果历程发生时否定《德国刑法》第231条的适用,因此必须采用其他方案。(Vgl.Rönnau/Bröckers GA 1995, 549, 556.)尤其支持的限制的“直接关联说”(反对态度)。尽管施特里没有明确提及,但是他所得出的认识却明显通向客观归责理论的适用领域。毕竟,他在其他地方表明必须为因果关系作一个补充,即“斗殴的特殊风险恰好在严重的结果中表现出来”(29)Schönke/Schröder/Stree StGB,25§227 Rn.14.。特隆德勒(Tröndle)和菲舍尔(Fischer)原则上也赞同性地参照施特里,并谈及“类似第227条”的对“构成要件特殊”结果的要求。(30)Tröndle/Fischer, StGB,49 1999, § 231 Rn.6.此处必然令人惊讶地引出这样的结论,即人们明显是从因果关系的存在出发的,该因果关系既不适合条件理论的模式,也不适合结果加重犯的模式。对此,人们可以使用一个值得信赖的、自然而然产生的工具,即借助于客观归责理论。如果人们已经放弃了结果的责任方面,那么他们至少应该在客观领域承认这样一些规则,亦即尤其在过失领域,这些规则乃是以“归责”为前提的。(31)Günther JZ 1985, 585, 587; SK-StGB-Horn (1998年5月),§231 Rn. 8a.详言之,需要检查的是根据对于客观归责有效的规则,能否认为严重结果是斗殴整体过程中的风险实现。(32)Lackner/Kühl StGB,23 1999, §231 Rn.5; SK-StGB-Horn (1998年5月), §231 Rn.8a; Rengier Strafrecht BT II,3 2000, §18 Rn. 7ff; Geisler Zur Vereinbarkeit objektiver Bedingungen der Strafbarkeit mit dem Schuldprinzip, 1998, 304ff.
如果人们接受客观归责理论的可适用性,那么就会得出如下指导准则:斗殴所制造的不允许的初始风险必须在结果(死亡、严重的身体伤害)中实现。此外,因为斗殴不是客体化的,而是由多人参与的个人化产物,涉及的是这些人的可罚性,所以客观归责进一步要求,在斗殴及其后续的结果中,一种遭到否定的、通过行为人参与斗殴造成的风险也要起作用,这涉及他们的可罚性。
对解决方案而言,从这些指导准则中可以得出值得信赖的基础。施特里特别发展了这些解决方案,比如异常的因果历程和事后的不当行为。(33)Stree FS für Schmitt, 1992, 215, 221ff.此外,人们还能从中推出,《德国联邦法院刑事判例集》第14卷第132页(BGHSt 14, 132)的观点值得赞同(结果发生在参与者解散之后),而《德国联邦法院刑事判例集》第16卷第130页(BGHSt 16, 130)的观点则需要拒绝(结果发生在参与者的共同作用之前)。(34)对此已经论述:Rengier BT II (Fn.32), § 19 Rn.10f.
同样从客观归责理论的视角出发,《德国联邦法院刑事判例集》第33卷第100页、第104页的判决却不尽相同。详言之,尽管严重的身体伤害结果只在斗殴者身上发生,但是斗殴者的可罚性却依然得到了肯定。确定的是,对自身的伤害应当在这种情况中应当为行为人的可罚性提供依据——一种也考虑到这种犯罪的罕见情况,其(部分)保护的是公共利益(参见《德国刑法》第315条以下)。人们当然可以说参与斗殴者所制造的风险也能伤害其自身,但是此处涉及的针对他自己的风险并不是法所不允许的,因为法律不禁止这类自陷风险的行为。在这些情况中,如果施特里(35)Stree FS für Schmitt, 1992, 215, 225.反正都想一般性地适用《德国刑法》第60条,(36)此外,Vgl.Geisler Zur Vereinbarkeit objektiver Bedingungen der Strafbarkeit mit dem Schuldprinzip, 1998, 320, 330.那么人们就会追问,为什么不立刻选择更值得信赖的“构成要件上的解决方案”。(37)对此也有:Günther JZ 1985, 585, 586f; Schulz StV 1986, 250, 251; Rengier Strafrecht BT II,3 2000, §18 Rn. 9.
七、麻醉状态的客观归责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德国刑法》第231条的思考是否也能对麻醉状态的构成要件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尤其在麻醉状态和麻醉后所实施的犯罪之间——与斗殴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相适应——是否会(应当)产生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可以从客观归责的标准中推导出来。
由于责任原则也牵涉《德国刑法》第323a条,因此罗克辛要求,对于麻醉状态下所实施的犯罪而言,行为人的行为要具有过失。(38)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11 Rn.8ff.罗克辛并没有提及过失所涉及的其他方面,不过如果他将过失行为作为前提,那么他就肯定会考虑过失的客观方面。接下来,客观归责理论的适用可以引出如下指导准则:麻醉(状态)必须制造一个不允许的风险,对麻醉后所实施的犯罪而言,该风险在合法则条件说的意义上是具有因果性的,同时该风险也会在麻醉后所实施的犯罪中随之实现。换言之,从麻醉者身上产生的、法律想规制的风险必须在麻醉后所实施的犯罪中实现。
根据这种思考方法,即鉴于麻醉状态和麻醉后所实施犯罪之间的客观联系,很多结论都会被首先证实,在与对麻醉后所实施犯罪的要求的关系上,人们拥护这些结论是客观处罚条件。众所周知,人们通常认为《德国刑法》第323a条原则上有这样一种功能,那就是它可以“弥补”责任能力的缺失,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层面,一切麻醉后所实施犯罪的惯常要素却都必须具备。(39)Rengier Strafrecht BT II,3 2000, §41 Rn.13ff.具体论述:
1.在结果犯那里,客观归责标准同样属于麻醉后所实施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如果在清醒的行为人那里,由于异常的因果历程或者在结果中没有发生违反注意规范的情况,因此可能需要否定归责,那么对行为人麻醉后所实施的犯罪而言,就也没什么不同。必要时可以将麻醉后所实施的犯罪认定为未遂。倘若人们从事前的视角出发,即麻醉状态这一制造了风险的构成要件要素,来观察这些情况,并追问麻醉状态的风险是否会在麻醉后所实施的犯罪中实现,那么也不会改变结论:这是因为,比如,倘若麻醉的行为人想引起死亡结果,但该结果却是由医院火灾或者重大过失的不当医疗行为所导致的,那么在这种死亡结果中实现的就不是特殊的麻醉状态风险,而完全是另一种风险。
2.对于违法性层面和有责性层面,人们已经进行了对比性的思考。施本德尔(Spendel)(40)LK-Spendel StGB,11 1996,§323a Rn.212ff. (与库什的讨论:Kusch Der Vollrausch, 1984, 119ff).讨论了一些情况,亦即酩酊大醉者因遭到一只狗的扑咬而将这只狗杀死的情况、陷入防卫过当的情况,或者在海难之后,将清醒的乘客推下救命用的“卡纳阿德斯之板”,以致其溺亡的情况。在这三个例子中,将麻醉状态及其之后的犯罪与客观归责的标准联结在一起这种观察方式,会推导出排除归责的观点,即对于被侵害的法益而言,关键的危险并非产生自酩酊大醉,而是来源于动物、过当境况或者紧急状态。
如上所述,倘若在麻醉后所实施的犯罪中应当显露出麻醉状态的风险,那么在危险的麻醉状态和麻醉后所实施的犯罪之间,就必须产生一种因果关联。(41)对此也有:Cramer Der Vollrauschtatbestand als abstraktes Gefährdungsdelikt, 1961, 117f; LK-Spendel StGB,11 1996, §323a Rn. 158ff; Kusch Der Vollrausch, 1984, 68ff; aA RGSt 73, 173, 182; Tröndle/Fischer, StGB,49 1999, §323a Rn.10.这样一种设想,即一种完全不取决于麻醉状态的行为能够论证其可罚性,也许根本无法为构成要件提供依据。当然,在缺少自然法则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这些例子终究很难去构建。人们或许会想到一个惯犯,他每天17点左右实施盗窃,并且在做案时偶尔也会处于麻醉状态。从客观归责的角度看,或许应当否定《德国刑法》第323a条的适用,但是根据无须展开讨论的原因自由行为的基本原则,却可能需要肯定其可罚性。
在这一点上,就不再深入探讨细节性的问题了,应当展现的是客观归责理论也能对《德国刑法》第323a条的讨论有所助益。在结论上,人们也许不必像罗克辛一样走得那么远,在构成要件中不必认为麻醉后所实施的犯罪是过失方面的具体危险犯。在自我麻醉的情况中,抽象危险犯理论基本已经预设了不允许风险的制造,根据这一理论,(42)同意观点:Rengier Strafrecht BT II,3 2000, §41 Rn.6ff.已经在《德国刑法》第231条的框架下展示出来的指导准则,便能够证明是(更)可靠的:虽然麻醉后所实施的犯罪被承认为客观处罚条件,但是根据客观归责的规则,麻醉状态却必须与麻醉后所实施的犯罪联结在一起。
八、诈骗的客观归责
按照重点,我们希望专心致力于诈骗罪构成要件的研究,并探讨一些客观归责标准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问题领域。当罗克辛在此说明财产损失乃是紧随欺骗而来的时候,他就指出了这一构成要件的结果犯性质,(43)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 §10 Rn. 102.作为结果犯的诈骗罪也适用于包括客观归责理论在内的研究。(44)Manzano in: Schünemann/Gonzáles (Hrsg.), Bausteine des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strafrechts, 1994, 213.
也就是说,在欺骗和损失之间会形成一个诈骗罪的特殊归责关联。换言之,对于他人的财产,不允许的欺骗行为必须制造一个不允许的、在损失中实现的风险。对此,凭借关于中间环节——或者也叫作“中间结果”——的因果链条,欺骗与损失就和认识错误与财产处分共同联结在一起了。总之,欺骗产生的不允许风险必须在中间结果内持续起作用,直到这一风险被“传递”至损失中。实施欺骗者所制造的风险,必须总是恰好在损失中实现。
1.对于(在此只作简短讨论)彷佛是不允许风险制造的第一个层面,罗克辛提到的例子是对情感需求的无关紧要的欺骗。(45)Roxin FS für Klug, II, 1983, 312. 对于其他“具有社会相当性的”欺骗:Pawlik Das unerlaubte Verhalten beim Betrug, 1999, 94, 98f, 154 mwN.
2. 自我答责原则和被害人共同答责的思想,都在诈骗罪中扮演着合理划分风险的重要角色。如开篇所述,罗克辛在“构成要件的范围”的关键词下总结出了这个方面,并希望由此(“答责范围理论”)突出该观点的普适性。这一全面的视角无法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能够像模版一样或多或少强加给所有结果犯的自我答责“原则”。这自然是因为,从“特别”规范的保护目的中产生的评价必须融入答责范围的认定过程中。(46)Vgl.Roxin Strafrecht AT I,3 1997,§10 Rn. 114f, 111, 119.
第一,对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使自我答责标准发挥作用的努力尤其可以运用到有意识的、以欺骗为条件的自我损害的案例群中。(47)总结:Rengier Strafrecht BT I,4 2000, §13 Rn.61ff.对此,最后:Jordan JR 2000, 133ff.施莫勒(Schmoller)在他的《有意识无偿给付中的诈骗》(Betrug bei bewusst unentgeltlichen Leistungen)一文中强调,对受骗者的财产处分而言,某些欺骗行为是否涉及自我答责判断这个问题,应当最终归入(规范性)限定答责范围的一般问题领域中。(48)Schmoller JZ 1991, 117ff, 127.格劳尔(Graul)(49)Graul FS für Brandner, 1996, 801, 819.基本同意这个方案,他参考弗里施(Frisch)(50)Frisch FS für Bockelmann, 1979, 647, 659, 666. 也同意归类为规范的客观归责问题:Jordan JR 2000, 133.的主张,强调这是一个规范的归责问题。梅尔茨(Merz)也重视自我答责的标准,并得出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根据规范标准,自我损害不再是受骗者自我决定的表现,不再是其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的实现,欺骗行为只能在这一范围内具有意义;如果财产上重要的目的受到欺骗,那么自我决定就受到了影响。(51)Merz “Bewußte Selbstschädigung” und die Betrugsstrafbarkeit nach §263 StGB, 1999, 196.作者明确指出,应当借助客观归责的机制来实现诈骗罪构成要件对财产上重要欺骗行为的限制。(52)Merz “Bewußte Selbstschädigung” und die Betrugsstrafbarkeit nach §263 StGB, 1999, 193f.帕夫利克还更加鲜明地强调,他想以客观归责理论作为其诈骗罪理论的根据,以便有效解释客观构成要件,(53)Pawlik Das unerlaubte Verhalten beim Betrug, 1999, 65.并在“被害人优先负责”的情况下“打断”归责关联。(54)Pawlik Das unerlaubte Verhalten beim Betrug, 1999, 148ff.
尽管上述作品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却是相似的。人们可以赞同性地认为,只有在欺骗行为无涉作为交易基础的根本给付目的时,有意识的、以欺骗为条件的自我损害才能打断归责关联。在这种提示下,经典教学案例涉及的乃是“被骗取的”(高额)捐款,其中邻居已经被证实是极为慷慨的。(55)对此也有:Graul FS für Brandner, 1996, 801, 806ff, 816ff; Pawlik Das unerlaubte Verhalten beim Betrug, 1999, 157f, 274ff; Merz “Bewußte Selbstschädigung” und die Betrugsstrafbarkeit nach §263 StGB, 1999, 174.对一个设定其给付标准的人而言,重要的是倘若他在此只是为了或者同时为了显示自己同样“慷慨”“不吝啬”等等,那么他就会落入自己的答责领域中。
第二,在与认识错误教义学的关系中,对于被欺瞒事实的真实性而言,受骗者产生怀疑时的被害人共同答责问题引发了激烈的讨论。(56)Hassemer Schutzbedürftigkeit des Opfers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1981; Hillenkamp Vorsatztat und Opferverhalten, 1981, 18ff; Kurth Das Mitverschulden des Opfers beim Betrug, 1984; Ellmer Betrug und Opfermitverantwortung, 1986.众所周知,如果受骗者认为真实性是可能的,并至少因此受到激励而去实施处分行为,那么通说便会就此肯定认识错误。(57)观点立场:Hillenkamp 40 Probleme aus dem Strafrecht BT,8 1997, 173ff; Küper Strafrecht BT,4 2000, 210, 212f; Rengier Strafrecht BT I,4 2000,§13 Rn. 21.据此,如果受骗者认识到了不真实性(尽管如此,他还是实施了处分行为,因为他可能相信其中或许存在真实情况),那么就应当否定认识错误。换一个视角看:倘若行为人实施处分行为并造成了自己的损害,那么这一犯罪就不再属于欺骗者的答责范围,而是以自我答责中的自我损害为基础的。
不清楚的问题是,受骗者对事实真实性的怀疑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此之强,以至于必须否定认识错误,或者根据自我答责原则“转移”答责范围。在《德国联邦法院刑事判例集》第34卷第199页的“灵丹妙药案”中,被害人在所有夸大之事中都相信这种药适合于减肥、变年轻或者促进头发生长。根据通说,她的轻率还没有导致答责范围的转移。如同已经说过的那样,倘若被害人供述道,虽然她可能已经抱有怀疑,但认为两种情况——有效与无效——具有相同的可能性,那么也不会改变任何情况。
人们目前可以在理论上使怀疑程度(对不真实性的间接故意)不断扩大,直至受骗者认识到不真实性。如此一来,在《德国联邦法院刑事判例集》第34卷第199页的案例中,被害人就可能会分析那些赞美之词,并在这一想象中实施购买行为。她可能会相信所有这些都不正确,但也许有40%、30%或者20%的可能性“相信其是真实的”。因此,即使行为人撒谎的可能性有60%、70%或者80%(等等),她也或多或少想尝试一下这个微不足道的机会。在这一想象中,人们会抵达这样一个领域,阿茨特(Arzt)曾用销售幻想来说明它,并使这一领域与排除可罚性的自陷危险思想联结在一起。(58)Arzt FS für Hirsch, 1999, 431ff, 447f;《德国联邦法院刑事判例集》第34卷第199页、第201页指出,订货人本质上希望得到实质上有效的产品,而不只是一个幻想。
通说的公式足以肯定认识错误,也就是受骗者认为真实性是可能的,并至少因此受到激励而去实施处分行为。凭借这一公式,被害人认为真实的可能性是较低的这种情况,也能涵盖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之中。因此,如果受骗者相信所宣称之事的虚假性,超过了他相信所宣称之事的真实性,那么就绝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认为可以排除行为人的答责。(59)如联邦法院所认为的(经济刑法:1990, 305)(但却没能谈到相应的“判例”); 此外:Schönke/Schröder/Cramer StGB,25 1997, §263 Rn. 40.
同样,在本文看来,根据此处被推到中心的客观归责思想与具体化的答责范围理论,正确的方案并不在“百分之五十的界限”中。(60)反对意见,Vgl.LK-Lackner StGB,10 1979,§263 Rn.79f.倒不如说,人们应当在评价性的整体观察中追问,(比如在《德国联邦法院刑事判例集》第34卷第199页所提及的案件中)受骗者对被宣称事实的可能怀疑是否如此之强,或者就被宣称效果的实现而言,受骗者对以欺骗为条件的、但仍然为其所接受的事实的“剩余”期待是否如此之弱,以至于被害人不再能理性地接受行为人所宣称的效果——也就是说,风险现在必须由被害人承担,其不能再归属到行为人的答责范围中。
3.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下一个问题至今少有关注,它能够与客观归责关联起来并且应当被研究。梯德曼(Tiedemann)曾在一篇关于“谈判诈骗”的论文中支持这样一个命题:“辅助人的(专业)认知应当归责于企业掌控者。对于谈判行为,辅助人是被请教者,他在自己的领域内代表企业掌控者。这种认知归责可以被称为超越谈判诈骗的、普遍有效的原则。”(61)Tiedemann FS für Klug, II, 1983, 405, 417(只在此强调)。根据完成的底稿:LK-Tiedemann StGB,11 2000, §263 Rn.82.
我们举三个典型的参与人:欺骗者T、受损害的企业掌管者G和他的代表者R。在初始案情中,我们设想R在前台活动且没有产生认识错误,而处在幕后的G——没有从他的(我们称为)漠不关心的代表者R那里获得澄清——却陷入了认识错误,并遭受了损害。这个案例可以很快得到解决:直接受骗者R没有产生认识错误。同时,T完全没有导致缺席的G的认识错误。就此而言,人们不需要用认知归责这一工具去否定诈骗罪的可罚性。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初始案情中,规范的涵射已经使客观归责的思想清晰可见:谁让代表者好像被派往前线一样,谁就要承担风险。继续这个比喻,此处的风险在于“前线”会拒绝传达信息,也就是“前方”所认识到的骗局无法直接传达到受害者所处的“后方”。
倘若R和G都亲自参与了谈判,但是其中只有R看穿了骗局,G却没有,那么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和有趣。现在G也是直接受骗者,就此而言,T惹起了G的认识错误这一假设基本上就很有可能是对的。不过从现在起,认知归责的问题便会不由地出现:一旦代表者看穿了骗局,R和G是否必须被作为“认识错误的统一体”来处理,也就是在整体上不再有认识错误?
进一步的问题随之而来:认知归责是否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R有没有通过某种方式向G说明情况,比如给一个提示?如果R没有直接澄清G的认识错误,深信不疑的G因此敲定了具有损害性的买卖,那么是否可以肯定归责?如果在认识错误方面有更多的代表者(比如,来自不同部门和专业领域的顾问)参与,同时或许只有一个人看穿了骗局,他甚至还可能收受了贿赂,那么判断是否会改变呢?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在此无法给出答案。只能说这么多:梯德曼所探讨的认知归责思想基本上可以从答责范围的理论中推导出来。具体而言,多少具有偶然性的出席代表数量,可能不如这样一种情况发挥的作用大,也就是企业掌管者——同样多少具有偶然性——是否亲自参与了谈判。只有在贿赂的情况下,人们才必须排除认知归责,因为该风险是行为人方面制造的,它与企业掌管者为“他的”认识错误方面负责无关。
本文想借助一个决定性的例子来说明上文的论述和问题,根据一些条件,这个例子同时还能提出其他问题,在这些条件之下,人们会成为代表者:一对夫妇共同购买了一辆汽车。销售商就某个要点进行了欺骗,该要点导致了这对夫妇1 000马克的损失。丈夫/妻子曾认识到这个要点,但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她无论如何都想拥有这辆车。在已经认识到欺骗的情况下,妻子/丈夫本不会同意购买。
当然,这个例子可以被进一步改编,比如根据实际的购买需求、根据共同作用的强度或者根据陪同人员的功能。(62)补充说理,Vgl.Pawlik Das unerlaubte Verhalten beim Betrug,1999,94,98f,154 mwN. 他提出了被骗者“特别认知”的归责可能性问题。
在结论中,客观归责思想与答责范围理论的联结会指明方向,人们需要在其中寻找很多所提问题的答案。
4.还应该讨论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诈骗罪的方面。可以引出这样一种思想,它借助客观归责理论赋予了三角诈骗情况广阔的教义学基础。这样的借助是容易想到的,因为人们通常会在这一关系中谈及“归责的统一体”,其中第三人的行为将“归责”于受害者。在帕夫利克看来,三角诈骗的问题在于“划分那些信息风险的范围,通过客观归责的方式,分工经营自己财产的企业掌管者会遭受这些风险”(63)Pawlik Das unerlaubte Verhalten beim Betrug, 1999, 211.。在财产所有者和产生认识错误者之间,人们只能谈及诈骗罪上重要的归责统一体,“如果后者的审查可能性可以追溯到前者规范上重要的自我约束行为的话”(64)Pawlik Das unerlaubte Verhalten beim Betrug, 1999, 213.。
帕夫利克立场的某些部分显著偏离了通说的观点,即使人们不同意他的立场,对传统的诈骗罪理论而言,他的方案也同样是卓有成效的。从客观归责的视角来看,在三角诈骗那里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对受害者的财产来说,如果第三人处分被害者的财产,那么行为人通过欺骗制造的不允许风险在多大程度上也还能作为受害者的自我损害而实现。倘若第三人像陌生人一样从“外部”干预受害者的财产,那么人们就不能讨论这种自我损害。也就是说,第三人必须处在“内部”才行。如同在客观归责领域中一样,这种处在“内部”的情况是否存在,本质上会受到事实标准的影响,在该标准的评价那里,答责范围理论可以起到辅助作用。无论如何,“阵营理论”的事实性观察方式被证明是一个正确的方案。
在细节上,要作为归责标准来考察的是:受害者自己制造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性)风险,亦即特定的第三人拥有接触其财产的途径,并且能够(事实上)处分他的财产。受害者有意识地使他的利益遭受风险,即第三人能够通过可预见的方式处在这样一些境况之中,其中,第三人应当为受害者作出实施处分行为的决定。如果有人使第三人进入自己财产的临近位置,那么第三人的这种“代理性的”处分行为就会归属于这个人的答责范围,根据具体情况和生活经验,这是必须要考虑的。
倘若人们以这样的标准——它无疑还具有扩展的能力和补充的需要——为基础,那么就可以证实很多“阵营理论”或者“事实授权理论”所得出的结论。边缘案件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在客观归责的屋檐下却或许能够引出可以理解的答案。在著名的“错误大学同学案”中(65)Roxin/Schünemann Jus 1969, 372ff; Roxin/Schünemann/Haffke Strafrechtliche Klausurenlehre,3 1973, 249ff.,人们在其原始版本中,即女房东曾经频繁参与交付行为,大概也会根据阵营理论得出(三角)诈骗的结论,而在改编的案情中,即女房东是第一次交付其转租人的物品,(66)Rengier Strafrecht BT I,4 2000,§13 Rn.40ff, 48.天平托盘就会向盗窃的间接正犯倾斜。
对于被讨论的有争议的问题,这同样能产生新的角度,亦即第三人的主观想象——特别是有意识地逾越界限或者在涉事者的意义上去行为的信念——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界限的划定。(67)对此,Vgl. Kindhäuser FS für Bemmann, 339, 360; Küper Strafrecht BT,4 2000, 373, 374, 378; Pawlik Das unerlaubte Verhalten beim Betrug, 1999, 215ff; Rengier Strafrecht BT I,4 2000, §13 Rn. 47.如果这个人,也就是使其他人与自己的财产建立特定紧密关系的人,必须承担这样一种认识错误所带来的风险,即这些其他人会通过可预见的方式遭受的风险,那么涉事者就必须也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去对抗由他所制造的认识错误风险中的危险,比如通过明确的方针、指示,等等。例如,根据特定的决定境况,如果女管家的(随后的)受害者严格禁止她在没有特别指示的情况下交付任何物品或者被命名的物品,尽管如此,她还是(以欺骗为条件)逾越了禁令,那么在事实上也许就会认为这种处分行为不再能归责于受害者;人们大概能够说,这是因为从现在开始,更确切地说是在此期间,女管家未取得同意的行为是处在他的答责范围之外的,就像不需要认识到违反禁令的迹象一样。
九、结语
上述分析的努力在于,使传统上定居在总则中的客观归责理论的效用,也在我们所选择的分则领域中(更有力地)受到重视。要是没有罗克辛的指导性工作,这一思考是不可能存在的。本文的字里行间都对他饱含着诚挚的问候、万分的感谢,同时也将所有美好的祝福献给罗克辛教授的70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