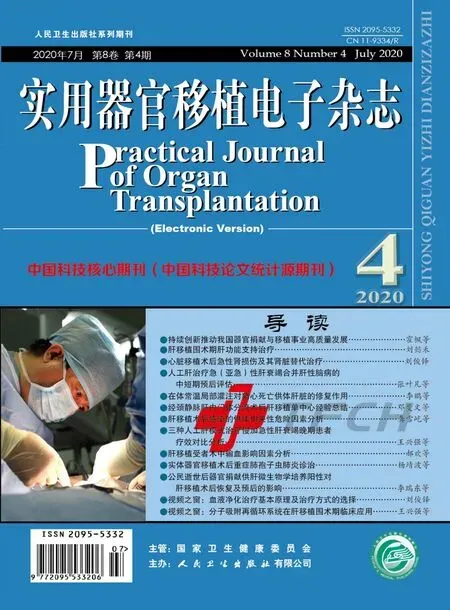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进展
2020-12-08耿海刚张汤安苏肖云飞腾旭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17
耿海刚,张汤安苏,肖云飞,腾旭(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7)
历史上首例人类肝移植由Starzl 等在1963 年完成,经过50 多年的不断发展完善,肝移植技术已逐渐成熟并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病患者的唯一手段。然而肝移植术后发生的免疫排斥反应会造成移植肝失活并降低受者存活率,成为临床工作中限制肝移植应用的一大难题。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防治免疫排斥反应并让肝移植患者的长期生存成为可能,但同时也带来了骨髓抑制、肝肾功能损害等一系列不良反应。临床上应用于移植术后抗免疫排斥反应的主要选择是传统西药,但长期应用易造成肝肾功能减退和增加恶性肿瘤发生的风险,近年来许多中药及新型免疫抑制剂也逐渐被研发并应用于肝移植术后的抗免疫排斥反应治疗。本文对近年来临床工作中常见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及发展进行简要概述。
1 传统西药在肝移植术后抗免疫排斥反应中的应用
1.1 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s,CNI):以环孢素A(cyclosporine A,CsA) 和他克莫司(tacrolimus,Tac)为代表药物的CNI 是目前临床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类免疫抑制剂。CNI 通过抑制 T 细胞活化和混合淋巴细胞反应发挥作用,其中Tac 的抑制效果为CsA 的10 倍以上,而肝毒性更小,因此Tac 在临床上作为首选药物。CsA 与Tac 相比,前者增加心血管风险,而后者对葡萄糖代谢有负面影响[1]。有研究表明,Tac 与CsA 对患者病死率和急性排斥反应发生风险无显著差异[2]。在使用此两种药物时应注意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不良反应。如肝移植术后常用的他汀类药物。与CsA 相比,Tac 不增加他汀类药物的暴露,也不增加他汀类药物相关的安全事件,因此Tac 可与他汀类药物一起使用,无需因药物间的相互作用而进行剂量调整[3]。Tac 在不同个体中的药物代谢与供体CYP3A5 基因多态性有关[4],对于受者每日所需的Tac 剂量,CYP3A5*1/*1(AA)基因型的受者大约是CYP3A5*3/*3(GG) 基因型受者的1.5 倍, 并且受者携带的*1 等位基因(A)越多,浓度/剂量比(concentration/dose,C/D) 比率越低[5]。而受体CYP3A5 基因多态性对Tac 药物代谢的影响尚存在争议,研究表明,受体CYP3A5 基因多态性和供体在移植后的1 个月左右时影响Tac 的药代动力 学[6]。另有研究认为Tac 的药代动力学可能与供者是否为CYP3A5 基因表达型相关, 而与受者CYP3A5 基因多态性关系不大[7]。此外,对于不同生存期肝移植患者,Tac 抑制免疫细胞免疫功能的效果亦有差异[8],因此合理掌握Tac 的应用指征对于肝移植患者的预后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1.2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抑制剂
1.2.1 西罗莫司(sirolimus,SRL)又称雷帕霉素,可降低抗原和IL-2 等免疫活性物质对T 细胞的刺激,进而抑制T 淋巴细胞的增殖活化。肝移植术后患者,长期应用CNI,会导致患肿瘤、肾功能不全、脑认知功能下降的发生率增加。SRL 能安全且有效地在降低上述不良反应概率并预防肝癌再复发,进而提高移植患者的生存率。SRL 主要用于肝移植后CNI 的最小化治疗,它可以降低CNI 的用量,因而对于肾功能损害和肿瘤复发高风险的患者更为适用。鉴于应用SRL 后肝动脉/门静脉血栓和败血症的发生率较高,因此禁止在移植后立即使用SRL。然而有研究表明,这些药物在移植后1 个月的安全性已得到改善[9]。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Zhou 等[10]对回顾性分析了36 例符合旧金山加州大学标准的晚期肝癌患者的资料,这些患者接受肝移植,然后用SRL 为主的胸腺嘧啶和槐耳颗粒(SRL 组; n =18)治疗,或用Tac 为主的治疗(对照组; n =18),比较两组的生存率和复发率,结果提示SRL 组相较于对照组有更高的生存率和较低复发率。其机制可能是以SRL 为主的联合免疫治疗方案可降低肝癌肝移植术后Fox P3 + Treg、IL-10、TGF-β 的表达,且并不增加排斥反应发生率,临床应用安全、有效[11]。而相较于Tac,SRL 可能引起高脂血症,皮炎等不良反应,其发生胃肠道及和皮肤及皮下组织的时间依赖性不良事件概率也大大升高[12]。
1.2.2 依维莫司(everolimus,EVE)是SRL 的衍生物,相较于SRL,EVE 吸收进入人体循环的速度快、程度高,具有不同的血液代谢物模式且终末消除半衰期较短,能够拮抗CNI 对神经元和肾细胞代谢的负面作用,刺激线粒体氧化,并能更有效地减少血管炎症[13]。选择基于依维莫司的免疫抑制方案可能有助于避免肾功能不全肝移植受者发生重大心脏事件[14]。关于这两种mTOR 抑制剂在实体器官移植受者中的安全性和耐受性的研究尚未有报道。尽管EVE 对肝移植患者术后有诸多益处,但其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较高,主要为口腔炎、肺炎等。其中口腔炎发生率最高,Arena 等[15]研究统计了包含了8 201 例使用EVR 的患者,结果显示发生口腔炎的发生率为42.6%。依维莫司作为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愈发受到重视,已逐步应用于临床,为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1.3 抗代谢药物:抗代谢药物以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A)和霉酚酸(mycophenolic acid,MPA) 的衍生物(包括霉酚酸酯和霉酚酸钠)为代表。霉酚酸是一种体内免疫抑制因子,它通过阻断嘌呤核苷酸的合成从而进一步抑制免疫细胞的增殖以及免疫活性物质的分泌。此外它还能够诱导抗原活化的T 细胞凋亡,减少抗体的产生从而抑制黏附分子的表达,减少细胞炎症部位的白细胞和单核细胞,具有抗纤维化特性。霉酚酸相较于CNI 发生排斥反应的发生率高,故一般不单独使 用[16]。Saliba Faouzi 等[17]对肝移植受者无糖皮质激素(corticosteroid,CS)方案联合Tac 和剂量强化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单独调整的可行性和潜在益处进行了一项随机多中心开放性试验。报道称,将成年肝移植受者在移植当天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从3 g/d 开始,根据MPA 暴露量 (A 组)和持续6 个月的CS、Tac 和固定剂量MMF (2 g/d)(B 组)从第5 天开始调整剂量。观察移植后第1 年经历活检证实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的患者比例。结果证实在新肝移植受者中,增强和单独调整剂量的MMF 联合Tac 可使CS 在移植后第1 天停用,且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和极低的排斥反应发生率。与AZA 相比,MMF 在预防急性排斥反应方面更有临床应用价值,但在接受环孢素免疫抑制的肾移植受者中,两者对长期移植肾和患者存活率显示出相似的作用[18]。此外,临床上MMF 无明显肝毒性、肾毒性和骨髓抑制也是相较于AZA 被更广泛应用的原因。MMF 作用性质较为温和,其最常见不良反应为巨细胞感染[19]。临床上MMF 常与Tac 联合应用,两者联用会导致氧化应激诱导在脾和骨髓中起毒性作用,增强不同的遗传毒性终点,在体内起到骨髓抑制和致突变作用[20]。
1.4 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曾是器官移植术后免疫抑制的一线用药,但因长期应用造成的显著不良反应,致使关于肝移植术后对糖皮质激素的使用一直存在争议。刘懿禾[21]认为糖皮质激素在肝移植术中的免疫诱导和控制肝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两方面较其他免疫抑制剂效果更好。低剂量糖皮质激素预防可减少移植物抗宿主病,从而减少类固醇的总剂量,这可能有助于降低感染和成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发病率和提高无复发生存率[22]。Manzia 等[23]对27 例肝移植患者进行了7 年的随访,其中13 例移植患者应用CsA + AZA 的无激素治疗,另外14 例应用CsA +糖皮质激素的激素治疗,在对两组患者的存活率、移植物存活率、感染率、心血管不良反应以及代谢病发生率进行比较后发现两组无显著性差异,无激素方案组并不增加移植物远期发生纤维化的风险。所以肝移植术后是否有必要应用糖皮质激素,应在何种情况下应用、应用多大剂量仍存在争议。为有效避免激素带来的不良反应,降低肝移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并提高受者的生存质量,无激素术后免疫抑制方案受到广泛应用。但糖皮质激素在肝移植术后的免疫抑制中仍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如何在众多方案中取舍以达到免疫抑制方案最低剂量、最少毒性组合和最优疗效,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尝试。
1.5 生物抗体制剂:抗体免疫诱导剂包括多克隆抗体和单克隆抗体两大类,临床被广泛应用于器官移植的免疫诱导治疗。多克隆抗体主要包括抗淋巴细胞球蛋白(antilymphocyte globulin,ALG)和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ntithymocyte globulin,ATG),ATG 强效清除T 细胞并抑制其增殖反应,对于群体反应性抗体高或再次移植等具有排斥反应高危风险的器官移植受者更为适用。而ALG 由于不良反应多,临床上已不再应用。临床上应用于肝移植的单克隆抗体主要是IL-2 受体拮抗剂和利妥昔单抗。利妥昔单抗是抗CD 20 单克隆抗体,其在ABO 血型不合(ABO-Ⅰ)活体肝移植中取得了良好疗 效[24],且利妥昔单抗预防并不增加活体肝移植后肝细胞癌复发[25]。IL-2 受体拮抗剂是临床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抗体免疫抑制剂,主要包括达利珠单抗和巴利昔单抗等,其原理为通过结合活化T 细胞上IL-2 受体的α 亚单位,从而阻断IL-2 受体介导的T 细胞增殖。大量前瞻、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表明,使用IL-2 受体拮抗剂行免疫诱导治疗,可以明显降低排斥反应发生率,减轻排斥反应的程度,即使发生也更容易逆转[26],且2 种药物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无显著差异[27]。近期有报道称达利珠单抗有致重度肝损伤的风险,其在肝移植中的应用还需进一步证实。抗体免疫诱导剂能推迟并降低肝移植术后早期应用CNI 和减少糖皮质激素的应用,防止CNI 对肾功能的损害和降低激素带来的不良反应,但其应用仍受价格昂贵以及可能致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等多种因素的限制。
2 中药在抗免疫排斥反应中的应用
2.1 雷公藤:雷公藤(主要成分为雷公藤多苷)是一种具有良好的抗移植排斥作用中药免疫抑制剂。雷公藤及其提取物通过影响Tand-B 细胞的增殖和活化、T 细胞亚群比例、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的炎症反应、以及多种细胞因子的分泌免疫功能发挥作用[28]。雷公藤多苷能够明显减少肾移植患者术后蛋白尿的发生[29],现已广泛应用于肾移植术后治疗。已有实验证明,雷公藤多苷能通过抑制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从而提高大鼠肝移植术后生存 率[30],其在临床肝移植中抗排斥反应的潜力尚需发掘。雷公藤多苷不良反应较多但大部分不良反应较轻且多呈现一过性,停药一段时间后这些不良反应可自行消失,但长期大剂量服用会引发严重的毒不良反应,器官特异性分析表明,雷公藤多苷治疗可引起肠毒性、生殖毒性、肝毒性、肾毒性、血液毒性、皮肤毒性和其他损害[31]。降低雷公藤多苷毒不良反应的关键在于严格控制用药剂量和疗程,并在用药期间定期进行检查肝肾功能的检查。
2.2 青风藤:青风藤的主要有效成分为青藤碱,青藤碱具有很强的免疫抑制作用,临床上主要用于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各种风湿免疫性疾病及心律失常的治疗。近年来青藤碱在器官移植免疫耐受方面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王欣玲等[32]对肝癌大鼠肝移植术后用青藤碱处理,发现移植肝组织中IL-2、IL-6 等细胞因子含量显著降低,证实了青藤碱可有效提高肝癌大鼠肝移植术生存率。因其具体免疫抑制机制仍不明确,影响了其在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的应用。但青藤碱在免疫抑制方面展现出了良好的药理活性,且毒性小,在器官移植后免疫抑制方面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2.3 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别称冬虫草,是一种具有免疫效能的药用真菌。目前已有研究证实,冬虫夏草作为常规免疫抑制剂治疗的辅助物有利于改善肾移植患者愈后[33]。冬虫夏草与低剂量环孢素联合应用于肾移植患者的长期治疗,有利于减少术后并发症[34]。邹佩霞等[35]研究发现,对于应用硫唑嘌呤进行免疫抑制的肝移植大鼠,冬虫夏草可升高其血浆蛋白含量并明显降低感染率,同时又不影响硫唑嘌呤的作用,证明冬虫夏草在肝移植术后的双向免疫调节作用。肝移植术后患者应用Tac 治疗,辅以冬虫夏草制成的中成药制剂百令胶囊,可显著降低患者的肾负荷并减慢肾功能恶化,为防止Tac免疫抑制治疗带来的不良反应提供了新思路[36]。
3 新型免疫抑制剂在抗免疫排斥反应中的应用
3.1 FTY-720:FTY-720 是一种新型免疫抑制剂,它由冬虫夏草中免疫活性物质ISP-Ⅰ改造而成。FTY-720 通过去除可能导致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潜在有害TN 细胞,以及保留可促进受者免疫的有用细胞来优化G-CSF 动员的移植物的免疫特性[37]。此外,T 细胞的增殖活化是导致急性排斥反应最重要的原因,而FTY-720 可以更显著地减少CD4+T细胞的数目,使CD4+/CD8+呈现比例倒置现象[38],可以防止肝移植术后的急性排斥反应。CNI 是通过减少IL-2 的产生来减少活化免疫细胞的数目,进而发挥免疫抑制的作用,FTY-720 并不通过此机制发挥作用,且不良反应更小。另有研究表明,FTY-720 对Tac 所致肾损伤具有抗炎、抗纤维化的肾脏保护作用[39]。其成药芬戈莫德已在国外上市应用于多发性硬化症的治疗,在国内也已经开出首批处方,在未来临床的器官移植方面还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具有应答范围广、效果强和作用持久等特点。
3.2 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抑制剂及PD-L1 抑制剂:近年来肿瘤免疫研究趋向于靶向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研发是其研究热点。PD-1及其配体 (PD-L1)抑制剂是最典型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代表药物有武利尤单抗和帕博利珠单抗等。肝癌细胞中的特异性表达PD-1 与PD-L1,提示它们可以作为肝移植后肝癌免疫治疗的特异性靶点[40],特别是对于那些未能从常规治疗中获益的患者,PD-1 抑制剂可以使肝癌患者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41]。国外已有研究证明PD-1 抑制剂及PD-L1 抑制剂治疗可显著降低肝移植后移植物排斥反应发生率并提高存活病例的中位生存时间[42]。另有研究表明尽管已有免疫抑制治疗,PD-1 抑制剂治疗对肝移植后肝癌复发仍能取得临床疗效[43]。虽然PD-1 抑制剂有良好的抑制肿瘤复发的作用,但其作用后产生的T细胞不仅对抗肿瘤抗原,而且也对抗供体同种抗原。应用PD-1 抑制剂发生急性高排斥反应导致移植失败的风险很高,导致PD-1 抑制剂在移植患者中的应用受到限制[44]。目前临床尚不提倡特别是移植术后早期应用此类药物,只有在建议PD-1 抑制剂作为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的患者,在进行一线免疫抑制药物传统治疗的期间密切随访,若发现疾病进展的征象,在权衡应用利弊后,才能启动PD-1 抑制剂的治疗[45]。PD-1 抑制剂及PD-L1 抑制剂现今已在国内上市,临床效果评价也很好,但过于昂贵的价格仍限制了其应用的普及。
4 总结与展望
免疫抑制剂已普遍应用于器官移植的术后医治,肝脏作为“免疫特惠器官”,在肝移植术后合理规范的应用免疫抑制剂是提高患者生存率、减少并发症的关键。目前肝移植术后应用最为广泛的仍是传统的西药三联抗免疫排斥制剂(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抗代谢药物+皮质激素类)。在传统西药中,降低CNI 的暴露,加强肝脏保护,采用无激素方案或者少激素方案,成为术后应用传统西药对抗免疫排斥反应的发展方向。中药运用其辩证论治的思想,在不良反应及对整体调节方面强于传统西药,但其免疫作用机制仍待深入探究。新型免疫抑制剂因不良反应少、免疫抑制效果强而受到广泛关注,但其临床应用仍受价格高、临床试验少等限制因素仍是推广使用的障碍。众多免疫抑制药尚处在动物实验阶段,仅有理论支持,如何使这些免疫抑制剂真正应用于肝移植的临床工作中,真正造福患者,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免疫抑制的最终目的是诱导产生、建立并维持供者特异性免疫耐受状态,使患者在能对抗各种外来因素(细菌、病毒等)入侵的同时,防止急慢性排斥反应。今后免疫抑制剂的发展趋势必定是由单一的免疫系统向神经内分泌网络体系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效果强、不良反应少、价格低廉的免疫抑制剂应用于患者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