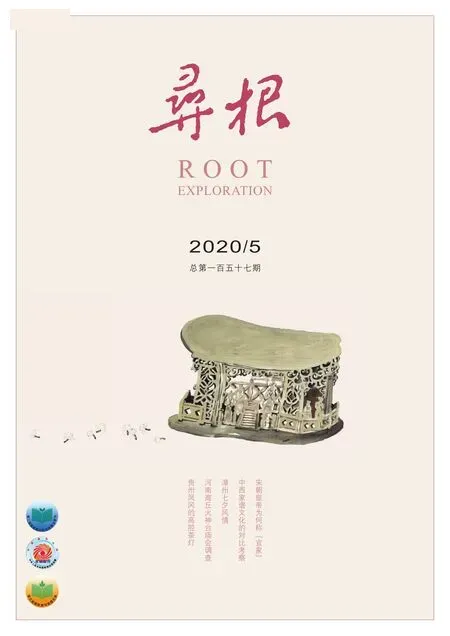孔子化行中都与汶上圣泽书院
2020-12-08武振伟
□武振伟
汶上县距曲阜50余公里,春秋时期为鲁国的中都邑,战国时为齐国的平陆邑。金泰和八年(1208年),始将县名定为汶上,延续至今。汶上因孔子曾任中都宰而闻名,公元前501年,孔子任中都宰,行之一年而四方则之。今汶上境内尚存孔庙、孔子讲堂、孔子沟、中都故邑碑、平陆祠等遗迹。
孔子为中都宰事迹
据历代志书记载,中都故城位于今汶上县境内。万历《汶上县志·古迹》记载:“故致密城,《郡国志》曰:须昌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兖州府》:“中都故城,在汶上县西。春秋时鲁邑,夫子为中都宰,即此……”《元和郡县图志》:“中都故城在今中都县西三十九里。”据考证,鲁中都城遗址,在今汶上县城西南25里的次丘镇湖口村附近。
孔子为中都宰,在《春秋》及《左传》等文献中均无记载。最先见于《礼记·檀弓上》:“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兖州府志》《汶上县志》等史籍文献也有明确记载。《史记·孔子世家》:“(鲁)定公九年,阳虎奔于齐。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钱穆分析说:“鲁国既经阳虎之乱,三家各有所憬悟。在此机缘中,孔子遂得出仕。在鲁君臣既有起用孔子之意,孔子遂翩然而出。”
孔子为中都宰的事迹以《孔子家语》的记载最为翔实。世人一直将《孔子家语》视为伪书,但其也有价值,不能简单判定其内容全部为伪。《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按其记载,孔子在任中都宰时制定了养生送死的礼节:不同年龄的人享有不同的食物,强弱不同的人分配不同的任务,男女行路各走一边,捡到行人的遗失物品不能据为己有,制作器物不能人为地雕画;安葬死者时用四寸厚的棺、五寸厚的椁,依丘陵为坟,不聚土成坟,墓地不种植树木。实行一年,各诸侯国都纷纷仿效学习。《墨子·节葬下》曾记载了当时厚葬的社会风气:“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厚葬之风的盛行,对于发展生产、培养民风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孔子宰中都在当时和后世对鲁国尤其汶上县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发展演变,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兖州知府金一凤为《续修汶上县志》写的《序》中写道:“今汶上者,古中都也。去圣人之世虽远,而流风善政,无不班班可考。”
可以说,中都是孔子从政生涯的起点。孔子宰中都的从政实践,在儒学发展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非常独特的作用。《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贾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孔子后来任鲁司寇的做法和成就,也被认为是他治理中都做法和政绩的继续和光大。战国时代的孟子曾到中都。西汉司马迁也曾为“观孔子之遗风”,来汶上实地考察。
最著名的是“汶上三孔”,即孔庙、圣泽书院、思圣堂。思圣堂建在县署内,始建于北宋元三年(1088年),由县令周师中创建,目的在于“求孔子之意而行其政”,“以己之心思圣人之心,以己之政行圣人之政”。其后,虽多经改朝换代,思圣堂却不断得到修缮,成为汶上旧县署镇衙之宝。
孔堂和钓鱼台,相传为孔子宰中都时遗迹。万历《汶上县志·古迹》记载:“孔堂,俗名讲书堂,相传孔子宰中都时,政暇,与弟子谈经于此。旧址在县西南二十五里,今移建城中,为圣泽书院”;“钓鱼台,即在孔堂旧址。相传为孔子钓处。”乾隆《兖州府志·卷九·阙里志》也将“中都城”“汶上旧讲堂”列入至圣遗迹。据《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大致可推断孔子为政中都时,是其名声提升的重要时期,也是一个收徒的高峰期。
元代大学士李谦的《圣泽书院记略》载:“城野之南,湖水之侧,有讲堂故基存焉,乃吾夫子与群弟子讲道之所,后人钦慕圣泽,不忘云耳,其兴废不能悉考,所可知者,魏孝昌丙午条石,记兴建之由。”可知,讲堂可追溯的历史至迟在北魏孝明帝孝昌丙午(526年)时,记讲堂重修之由,那么讲堂的始建年代至迟也为北朝。李谦《圣泽书院记略》:“天宝壬辰旧刻吴生所画宣圣、兖公小像,额则徐浩所题,其上复有颜鲁公书、程浩所撰《夫子庙堂记》。元四年(1089年),南阳周师中作宰是邑,重加修建,王尧年为之记……二百年来,荐罹扰,毁于灰烬,鞠为瓦砾。”可知,天宝十一载(752年)修建了夫子庙;元四年,知县周师中重修夫子庙。可以说,历代对于孔子的遗迹重视不衰。康熙《续修汶上县志》记载,到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衍圣公建修讲书堂。
圣泽书院的创建
万历《汶上县志·学校》记载:“圣泽书院,旧为讲堂,在城西南二十五里开河之东。昔孔子宰中都,政治之暇,与群弟子讲习地也。俗名讲堂,旁有钓鱼台,相传孔子钓鱼于此。兴废莫考。魏孝昌丙午有断碑存焉。唐吴生有画宣圣、兖公小像,徐浩题其额,又有颜鲁公所书、程浩《夫子庙堂记》。宋元四年,南阳周师中宰是邑,重修葺之。岁久灰烬,鞠为瓦砾。元至元间,马栎庵,东平教授也,得地十二亩,构堂藏书,以授生徒,而都水少监马之贞则建大成殿三楹,中肃圣容,旁列十哲,堂室、门庑、庖库、池井,无不具备。”对于讲堂的历史,圣泽书院的记载也是依据李谦的《圣泽书院记略》而来,内容基本相同。对于圣泽书院的创建时间,此处记载比较笼统,而李谦的《圣泽书院记略》则记载较为清楚:“故东平教授栎庵先生马公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得地一十二亩,藏书千余卷,构亭讲诵,其后都水少监马之贞复建大成殿四楹,中肖圣容,旁列十哲像”。记文虽略有不同,但从中可知,圣泽书院创建于至元三十年,经马栎庵和马之贞相继修建完成。此时的圣泽书院,属于初创期,虽规模粗备,但讲学、藏书、祭祀功能齐全。
北宋汶上知县周师中在县志有传,据万历《汶上县志·宦迹志》记载:“周师中,南阳人,哲宗时知汶上县,为政宽猛适宜,锄奸恶,抚良善,百姓安之。尝取中行之义刻准字池于堂,又移建圣泽书院,以育生徒,置思圣堂以自励云。”周师中,嘉靖《山东通志·名宦》、万历《兖州府志·岁贡》均作“周中师”,按李谦的《圣泽书院记略》记载,应为“周师中”。按县志记载,周师中有“移建圣泽书院”之功,但具体移建于何处,因王尧年所撰记文没有流传,其事迹已不可考。据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楚潭周御圣泽书院碑》记载:“至金石之刻,则有若吴生之所画,徐浩所题,颜鲁公之书,程浩、王尧年之所撰,悉胪列于左右。”唐、宋碑刻尚存,圣泽书院之历史班班可考。如按周师中传记载,则圣泽书院的创建当在北宋元四年。
圣泽书院迁建城中考
明嘉靖年间,圣泽书院迁建于城中。万历《汶上县志·学校》记载:“皇明嘉靖初,抚台陈公凤梧求遗址,县令吴公瀛请建于城内西南隅,中为正殿三楹,前为拜殿,又前为门,缭以周垣。继修之者,则赵公可怀、张公惟诚(改为复古书院,郡人于慎行为记)及尚公瓒,殿宇一新,而门易以坊焉(仍题圣泽书院,郡司理周公御为记)。”这一段简短的记载蕴含的历史信息考证如下。
嘉靖初年,山东兴建了许多书院,这跟时任山东巡抚的陈凤梧有直接关系。嘉靖《山东通志·职官》记载:“陈凤梧,文鸣,泰和人,丙辰进士,嘉靖元年以副都御史巡抚,至右都御史。”万历《汶上县志》言“抚台陈公凤梧求遗址”,可以作注脚的是道光《沂水县志·书院》记载,明嘉靖年间巡抚山东的官员要求,“一各所属公署、山川、亭檄、寺观、碑刻,凡有关系山东地方名贤古迹等项,俱要汇写成集,依限上报”。可以确定,道光《沂水县志》所言山东巡抚即陈凤梧之后任袁宗儒。查《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世宗即位不久,“升河南按察使陈凤梧为山东左布政使”,不久升任巡抚都御史。陈凤梧巡抚山东期间,对先贤遗迹高度关注,不仅要求各地将先贤遗迹整理上报,而且将先贤的祭祀也进行了整顿,使对先贤祭祀正规化。在陈凤梧及其后任的直接要求下,汶上圣泽书院迁建城中。知县吴瀛将书院建于城中西南隅,当在嘉靖初年。万历《兖州府志·学校》记载:“国朝嘉靖二年(1523年),知县吴瀛移建城中。”这在万历年间重修圣泽书院时周御所撰圣泽书院碑中有所记载:“世宗初,巡抚都御史陈公凤梧始下檄,移建今县治太仆寺之南际,旧制益拓,编役司守,严事有容,衿绅之士斌斌焉,居无害祀,省入庙,专为讲肄之所。”此次迁建,将祭祀的功能并入文庙,而书院成为讲学肄业的专门场所。
吴瀛创建书院后,知县赵可怀、张惟诚对书院进行了修缮。《邑侯赵可怀德政记》:“赵公可怀,四川巴县人,嘉靖乙丑(1565年)进士,以司马中丞出镇于楚。”“赵公当嘉靖末而为宰,春秋盛而敏,宣慈而肃,在政四年。”据此可知,赵可怀重修圣泽书院当在嘉靖末隆庆初。万历《兖州府志·学校》记载:“隆庆元年(1567年),知县赵可怀重修。万历元年(1573年),知县张惟诚改为复古书院。”
张惟诚,隆庆壬申(隆庆六年,1572年)调任汶上知县,其到任不久即将圣泽书院改名为复古书院,还创建了汶阳书院。郭朝宾《邑侯张惟诚爱养坊记略碑》:“万历二年(1574年)春正月,天下有司各述所职,以会于阙下。诏举廉能异等,得二十五人,吾邑张侯与焉……侯复莅县。”可知,张惟诚两次任汶上知县。据万历《汶上县志·学校》记载:“汶阳书院,在预备仓右。创自永清张公,堂轩爽垲,号舍曲回,建坊构桥,引流种树,诸士伊吾其中,而政治之暇,亦时临辨义也。郡人于慎行为记。盖数年而废。邑令彭公健吾因改为察院云。”可惜的是,于慎行所撰复古书院和汶阳书院记文在县志和府志中均未收录,对于书院的具体情形已不可考,而从张惟诚建立汶阳书院后的行动看,汶阳书院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汶上县的主要书院,圣泽书院虽然改名为复古书院,但已不复盛况。
此后不久,即遭遇明代数次毁书院之风波,圣泽书院虽未被毁,但却陷入荒废状态。周御记文中提到:“又五十余年,而书院之禁下矣,坐是荒芜不治,萤飞虫走,垣若毁,殿宇若撤,残碑断碣,□□于澹烟荒照之中,识者有鲁壁金丝之感。”按“五十余年”记载,当指万历年间张居正辅政时期的禁毁书院事件。万历七年(1579年),首辅张居正辅政,“诏毁天下书院”,“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明通鉴》卷六十七)圣泽书院虽荒废,但地基尚在。
至万历年间,知县尚瓒将书院修葺一新,重改为圣泽书院。关于尚瓒重修时间,万历《汶上县志·学校》没有记载,宣统《山东通志·学校》则明确记载:“(万历)十二年,知县尚瓒重修,改名圣泽。”但周御《圣泽书院碑》记载:“表章先圣之遗迹,修复累朝之旷典,尚侯之功,皆其功也。考厥成功,为今万历二十八年。”明确记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是重修年岁,当以周文为准。尚瓒,“锐精治理,留心圣迹”,据周御《圣泽书院碑》记载,尚瓒对汶上的缙绅之士说:“汶为古中都,先师筮仕之地,讲堂则颜闵游夏辨志之区……假令讲钓之迹遂荒,则圣泽之谓何?”命县儒学教谕董光为督工,率领诸生掌管钱财,“榛秽诛之,洼平之,硗陋廓之,拉旧易新,拨篆丹,檐楹斐尾,周垣邻菌,外设戟门,中置黼座,至金石之刻……悉胪列于左右。庖库井池,咸亦粗备焉。而圣像俨然南面矣,令率父老子弟行释菜礼告成”。重修圣泽书院,虽然是重视先贤遗迹,不使其毁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更有现实的目的,意在“自今以往,吏于其土者,洵夙夜惟先师之政;生于其乡者,亦夙夜惟先师之学。有能圉生民、登咸往哲、无愧门墙而有当祀典者,请即俎豆于先师之旁,倘亦修之之意乎”?不仅激励为官者,也激励为学者,如有业绩即可陪祀于先师之旁。
明末崇祯年间,圣泽书院正式纳入由曲阜衍圣公府系列的孔子祭祀体系,由衍圣公保举奉祀官,书院山长也改称太常寺博士,成为朝廷命官。民国《续修曲阜县志·政教志·书院》记载:“明崇祯间,衍圣公题准以第三子袭授太常寺博士,专主圣泽书院祭祀。”此项规定,直至民国年间。民国23年,圣泽书院奉祀官为孔祥瑜。乾隆《兖州府志·阙里志》记载:“太常寺博士。圣泽书院即孔子宰中都地也,明设太常寺博士一员,以主祀事。例以衍圣公三子承袭。崇祯间,五经博士孔允钰以违例罢职。”清军入关后,定鼎北京,迅速祭出了尊孔的大旗。清顺治元年(1644年),孔允钰被命为暂主圣泽书院祭祀官。乾隆《曲阜县志·职官二》记载:“太常寺博士,正七品,奉圣泽书院祀。”康熙《续修汶上县志·人物》记载:“孔衍钰……国初补太常博士,主圣泽书院,受事之后,整庙貌,肃明。”之后历任奉祀官都经过了朝廷任命。圣泽书院也成为曲阜县外专门祭祀孔子的书院之一。
清代圣泽书院考
清代圣泽书院史事资料缺乏,《阙里文献考·林庙二之三》记载:“国朝康熙五十一年,六十八代衍圣公为世子时又重修。”六十八代衍圣公即孔传铎。
因自康熙之后汶上县未再修志,宣统年间所修县志未刊行,只存手稿本。据1996年出版的《汶上县志》记载:“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知县龚聪劝捐一千二百金修缮书院。浙江中丞刘玉坡(汶上人)慨捐千金,以六百归兖郡考棚,以四百归圣泽书院。孔衍钰劝募衍圣公捐助京钱一千串。后相继捐款者多人。圣泽书院增建了学舍,并建东西考棚等。圣泽书院原址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因外扩湖堤,没于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令各省书院均改为学堂。汶上圣泽书院遂于光绪三十年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后相继改称县立第一小学、书院小学等)。圣泽书院以学田租银为主要经费来源。道光元年,有学田2864亩,多为南旺湖田。光绪十九年,知县刘鉴复查出南旺湖公田5900亩,丈入圣泽书院3900亩。”
据乾隆《新泰县志·选举下》记载:“(元)单肇,东平路圣泽书院山长。”乾隆《曲阜县志·学校贡举》记载:“(金元时)孔思范,圣泽书院山长。”
与其他衍圣公府管理的书院不同,圣泽书院并没有成为徒有书院之名的孔子专庙。道光《重修平度州志》记载,有一个平度人曾任圣泽书院主讲。戴金鼎,道光《重修平度州志·列传五》记载:“金鼎,字调梅……嘉庆癸酉举乡试第一……在汶上六载,从游者多,汶上令并延主圣泽书院讲席。”道光《重修平度州志·艺文上》收录的《戴公心泉先生传》也记载:“乃以道光丙戌(1826年)大挑,选汶上县训导,训迪有方,从游者日众,邑宰遂延主圣泽书院。”
孔子讲堂遗迹距县城二十五里,在明嘉靖年间移建书院于城中后,少人问津,遗迹逐渐荒废。民国5年汶上人马焕奎《讲堂钓鱼台留地保护记碑》记载:“明嘉靖间,移建城内,此地遂鞠为茂草矣。然圣泽之名犹存也。至我光绪三十年,书院易为学堂,而名亡矣。夫圣道上下与天地同流,岂同君子小人泽约五世而斩者?今圣泽之名虽亡,而堂台故址之实,尚幸啧啧于耕夫牧竖之口。”在知县的主持下,众人决心保护先贤遗迹,具文上报,并得财政厅清理官产局批复:“除故址面积外,各留陈地六亩,以重圣迹而资保护,饬县清查定界,绘图贴说,报上存案,永禁侵渔,并饬立碑记事。”
因先贤遗迹而兴建书院,又因迁建书院而致使遗迹荒废湮没,令人惋惜。民国初年虽有保护,但两处遗迹在1978年土地平整时被铲平,幸运的是,先贤遗迹又得到了恢复。千载之下,先贤遗迹的真伪,难以考究,但应发挥先贤遗迹的感召作用,为当今的文化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