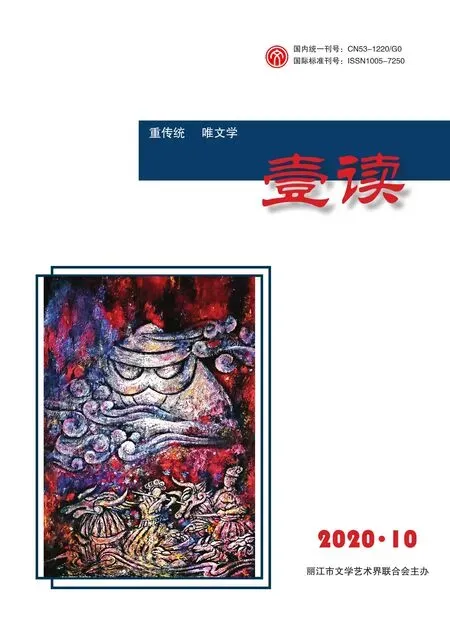父亲的秘密
2020-12-08
1
父亲曾带着我,去他工作的学校。
那所群山之中的学校,如藏在草丛中的一枚石子。破旧的四合院,土坯房,最多不过两亩地。那所小学先是完小,后来实行集中办学,小学校被简化成了办学点,设学前班和一二年级,共两个老师。
父亲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带着一个比他年纪小许多的年轻老师。教了二十多年书,熬了大半辈子,风水终于轮到他这儿,父亲成了这个学校的负责人,这多少让他有些欣慰。他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嘴巴上对这个比芝麻小几十倍的官,不屑一顾,他说他希望要么就成为那种武可安邦,文可治国的历史人物,要么就穷困潦倒一辈子。让他活在一个夹缝里,他不情愿。
事实上,他周末显得更忙碌,他回家一会儿,就要忙着去准备三十来个学生一周的伙食,以及应付乡上中心校大小会议,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时间洗头发,头发黏成一片,像顶毡帽,遮住沟沟坎坎的脸。好长一段时间,父亲没有时间过问我们的学习。直到大姐参加高考,他才如梦初醒,嘟哝道:“时间这么快,大闺女都要上大学了!”
为了方便我们姊妹三人念书,父亲把家迁到县城,两间连在一起的出租屋,摆几张床和一套简易的沙发。平时只是我们和妈妈一块儿住,周末父亲回来会显得拥挤些。父亲托人帮母亲在一中找了个食堂炊事员的活,每个月一千块,匀出一半刚好可以付房租。在这个县城的某个角落,像我们这样租房念书的人家不计其数,更多的是留守老人带着留守儿童,三四个人挤在一间八九平方米的屋子里,睡觉跟做饭都在一间屋子,在外打工的青壮年父母,定期将生活费寄回来。有的人家,甚至只是把孩子托付给亲戚,半年都见不上一面。有的孩子背着学校和家里人,跟街上的二流子混在一起,上网,抽烟,喝酒,打架,抢劫……
面对这灯红酒绿、波涛汹涌的小城世界,母亲一有空就向我们不停地唠叨,像念紧箍咒。在这方面,父亲却表现出对我们一百个放心。我们的乖巧和懂事,一半与生俱来,一半受到父亲的影响,他为人正派,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师的傲骨,即使穷,也光明磊落。
2
父亲初中毕业,代课十多年才有机会进入地区民族师范学校进修,进修结束,政策却变了,不给马上转正,于是全县代课老师八九十号人,一起聚到县政府门口静坐,跟领导讨说法,得不到领导的圆满答复,他们又去市里,前前后后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七八个人挤一间二十块一晚的旅社,每顿只吃两个馒头,下点咸菜。口袋里的一百多块钱,还是跟同校的老师借的。上级领导终于松口,答应给他们机会考试,但规定只录用其中的百分之八十。经过一番折腾,父亲才幸运地得以转正,父亲说还有十多个老师,没转成,回家当了农民,到现在都住在那些鸟不生蛋的山沟沟里,日子过得平铺直叙,像清水煮萝卜。父亲说,有人已经代了将近二十年的课啊,就为了转正吃上公家粮。
这样想来,父亲是幸运的,连他自己也这么说,生活是眷顾他的。虽然比不上那些中专毕业就分配进来,如今工龄长、职称高、待遇好的老师,但至少每月能拿到两千多,节衣缩食能勉强供我们念书。
母亲始终认为,她嫁对了人。尽管在父亲代课时那几十块的工资,不被任何人看好,而如今,摇身成为国家的人,被当地人称为“干部”,国家干部。母亲是舅舅家的女儿,在包括丁良村在内的整个彝区,这样的姑表通婚,被认为是标配,一方面是因为知己知彼,更重要的是为了延续亲上加亲长久的亲戚关系。
母亲温柔,却不识字,在生活上处处表现出对父亲的顺从,甚至是巴结,只要父亲提高嗓门,母亲就唯唯诺诺,把不满和委屈立马咽回肚里。这种不符合逻辑的婚姻,已经持续了二十余年。
然而,父亲对母亲的认识,却恰恰相反。
“不幸”这两个字,是他对他婚姻的定论。
与母亲毫无感情基础的父亲,一度抑郁。
抑郁的父亲,在小山村的学校里便经常参与同事们玩扑克,酗酒买醉。与其他乡村老师不同的一点,父亲是上进的,喜欢读书,书比酒重要,所以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只要有一本好书在手,读到精彩处,他便不再参与喝酒,无论别人怎么劝,都坚决不喝。父亲利用业余时间,看了许多文学书籍,精力充沛时,他也涂鸦,写一两首小诗,现在大家偶尔能看到父亲的作品,登在县里的杂志上,这成为我们姊妹三人的又一个骄傲。他读的书多,在说话中能经常恰如其分地嵌入一两句古诗词,显得谈吐更有内涵。所以,父亲被校区的老师们评价为知识水平较高的一位。
正因为如此,他越来越看不上母亲的“无知”。她不懂幽默,累了倒头就睡,每天从食堂回来也不知道打扫一下个人卫生,身上经常带着油烟味。并且说话也总说不到一块。他们犹如两条并行的河流,怎么也流不到一起。
所以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父母的争吵频频发生,母亲总是坐在床上哭哭啼啼,父亲则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父亲曾对我说,要不是因为我们三姐妹,他早就和我的母亲离婚,远走他乡了。
3
父亲是在虚拟世界里认识那个女人的,他不得不由衷感慨,网络,真好!那是他去校区开会,看见中心校长的智能手机,能像电脑一样上网。可价格却贵得离谱,又挨了两年,这款手机降到八百块,父亲这才下咬牙买了回来,换掉了那款老式诺基亚。
父亲用手机上网,聊QQ,后来是微信,他在虚拟的世界里寻觅,邂逅,倾诉,之后就无比轻松,他称这叫“网络沐浴”,确实有沐浴之后的轻松和快感。
也许父亲被压抑得太久,亟需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慰藉。
和所有的人那样,父亲无厘头地在上面搜索着一些陌生的名字,上面的那些网名比森林里的树还多,比花园里的花还千姿百态,他宛如一只采蜜的蜂,从那些妩媚的头像里,初步辨别,是否停下来,俯下身去,深入到这朵花里。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我隐约感觉到,春天,在我四十八岁的时候,就会来临!”
父亲在遇到“一碧千里”之后,预示着他与预言越来越近。期盼已久的爱情,被点燃,迅速成为燎原之势。
一碧千里,A城教师,这些字眼同那个微胖的头像联系在一起,让他浮想联翩,从她那淡淡的忧郁的眼神里,父亲似乎感受到些什么,那种似曾相识,相见恨晚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由于彼此有着相同的职业,他们共同的话题很多很多。从素质教育到课改,从学区房到教育公平,从校园欺凌到校园贷,从学校去行政化到教育家办学,针砭时弊,他们的观点,很多都会不谋而合。
她是A城第二小学语文科的骨干教师,学校的学科带头人,拿着地方政府的特殊津贴。而我的父亲,是市级作家协会会员,百度一下,能搜索到他的几篇文章。
他们聊得最多的,是文学。李清照的婉约,仓央嘉措的煽情,莎士比亚现实与浪漫的完美结合。他们手挽着手在诗人们的田园里漫步,聆听彼此的心跳。
每个生命,都是面对死亡而存在,而文学,是一个随时可以将生活焐热的电暖宝。毋庸质疑,一碧千里就是父亲多年来寻找的知音。他们隔空相望,彼此守候。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他们之间的谈话变得毫无顾忌,父亲自然而然跟一碧千里讲起苦难的童年、不幸的婚姻,以及压抑的心。
父亲的学业,是被他的继母断送的,也就是我现在的小奶奶,这个走路一瘸一拐的女人,曾经不让父亲念书,差点毁掉了父亲的一生。她不希望一味地拿出钱来供父亲念书,她迫不及待地要父亲成家立业,承担起供养几个弟弟妹妹的重担。爷爷是个懦弱的男人,对小奶奶言听计从。父亲不服从,便被小奶奶辱骂鞭打,一次,父亲曾带着五块钱离家出走半年多,在丽江城扫地,刷盘子,看仓库,尝遍世间的酸甜苦辣,开地下赌场的一个女人看中父亲,要父亲帮她看场子当打手。幸好那时爷爷得了一场重病,家里托人找到父亲,叫他赶回去。要不然,父亲的人生,可能又是另一番天地,或许混迹江湖,或者早被打死。
等爷爷病稍好,小奶奶便迫不及待地为父亲张罗婚事,父亲顺从了小奶奶的意愿,结婚。
小奶奶对我们的深度歧视,还在于母亲和我们三姊妹。在丁良村,生下的三个全是丫头,是会被人耻笑的,表明这家人断了香火。因此我们一家更不被小奶奶待见。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未正眼看过我们,更没有抱过我们。她宁愿把一碗剩饭加几块肉,端给村东头的傻子李,也不愿给饥肠辘辘的我们。
那些年,父亲的代课工资低得可怜,有时还被乡政府截留下来,生活捉襟见肘,有时一两个月还吃不上一顿肉,一两年都添不起一件新衣。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父亲如一只背负千斤重担的蜗牛,举步维艰。
那本发黄的笔记本上,留下父亲当年的日记:婚姻是一座坟墓,我就是被迫埋在这座墓里的活死人,我希望有一天成为掘墓人——
父亲的人生,宛如深山的羊肠小道,异常崎岖。
4
一碧千里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不开门面,拎个包,见到什么行当赚钱就干什么,有时两三个月都在外面跑,有时几十天都闷在家里,酗酒睡觉,不修边幅,看上去蛮横粗鲁,对她和儿子漠不关心。他的眼里只有钱和吃喝。
在一碧千里的眼里,他就是个俗人。与原本憧憬的美好,大相径庭。他们不缺钱,缺的是温情,是交流,是沟通,是感情。女人的心是异常敏感的,受不得风吹雨打,需要像婴儿一样去呵护。
结婚不到三年,她就想离婚,可是那时他们已经有了儿子,为了不伤害儿子,她一忍再忍,一拖再拖,直到现在。
除了QQ 和微信上不断地聊,他们还经常打电话,关心彼此的吃饭,睡觉,交友,工作,还有其它琐事。超过一个小时不回信息,她就会打电话过来,埋怨父亲。有时也会因过分在意对方而争吵,比如一碧千里喜欢在周末跟朋友打麻将,父亲就会怄气;比如父亲身体不好,却爱喝酒,一碧千里也会发脾气。而很多时候,都以一碧千里的妥协而收场,她像哄小孩一样哄我的父亲,又如妈妈一样说教,母爱般的迁就最终让父亲转怒为喜。他们穿越时空,互相惦念着,监督着,祝福着。
网络上聊了两个月,一碧千里跟父亲提出见面。这是父亲一直以来所期盼的,但是当对方真的说出来,他还是犹豫不决,脸红,心跳,有种说不出的害臊,毕竟年过半百的男人,还像半大孩子那样搞网恋,还像年轻人那样激情澎湃,是不是一个靠谱的男人?父亲只好保持缄默。
一碧千里继续要求,父亲找各种借口推脱,上面要来学校检查工作,女儿马上要期末考试,妻子住院……
好几天,双方都在为见面的事纠结不已,话语少了,电话也少了,最后一碧千里没了回音。一整天,父亲发了许多信息,没人回,打电话过去,关机。彻底失联了。父亲心烦意燥,寝食难安,一碧千里如同一团空气,父亲失去了这团空气,身子软得像一堆泥,瘫在沙发上,就再没力气起来。
或许她早已感觉到自己的敷衍,自己的没诚意,自己的决绝,这对一个渴望出口,渴望呵护,渴望爱情的女人来说,是何等致命的伤害。自己真不是人,真不是男人!父亲后悔得要命,他甚至想掐死自己,拿一把刀把自己发信息的手指剁掉。
如今既成事实,他不知道拿什么去弥补。一连几天,父亲彻夜难眠,半夜,喝下一壶酒,将自己灌醉,才蒙头大睡。
父亲在日记上写道:“心中燃起的火苗被彻底浇灭了,眼看就是阳春三月,不想迎来一场冰雪。”同时,父亲写下一首绝望的诗,他在记忆的时空里流连忘返,分不清天上的是太阳还是月亮,看不清地上是月光还是阳光。
那个周末,父亲骑着那辆破旧的摩托车回到家,看上去憔悴得很,眼睛红肿,显然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母亲忙给他打洗脸水,问他怎么啦?是不是生病了?他不做声,摇摇头,母亲便不再问。吃过晚饭,他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之后便精神好了许多,一直躲在屋子,拿着手机不停地聊了起来,直到十一点多我们上床睡觉,他还在旁若无人地玩着手机。我们催促他,他让我们先睡。
在父亲的日记本上清楚地记录着:那个电话是一碧千里打来的,她跟我解释,前几天丈夫一直在家,他这次做生意亏了本,喝闷酒,冲她发脾气,甚至还翻看她的手机,她一生气,将手机狠狠摔在地上。今天丈夫出门了,才出去买了个新的,马上就给我打来电话。
一碧千里一直向我的父亲道歉,向他撒娇,请求他原谅。希望他不要再生气,并保证以后不再无缘无故的失联。
父亲发现,一碧千里已将个性签名改成:你不来,我将一直在原地等你!
一碧千里对我父亲说,你就是我的阳光,没有你,我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接着一连打了十个哭泣的表情。
父亲的心瞬间软下来,如一团包在气球里的水。他有什么理由不原谅她呢?他感觉就像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抱在怀里都舍不得放下,他喜极而泣。现在,他们生怕再度失联,生怕失去对方,手机仿佛成了父亲的心肝宝贝,就连吃饭时,他也忍不住要瞅几眼。
这次,他们迫不及待地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
他们像在策划一场地下党的接头行动,盘算,规划,憧憬,力求做到有条不紊,周密部署,万无一失。
5
父亲的这次见面,显得水到渠成。
父亲提前做了精心准备,重新剪了头发,熨好衣服,找借口请假。
他告诉母亲,他要去出差,中心校派他到A城学习几天。母亲帮着他收拾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的东西,烙了荞粑粑,煮了一堆鸡蛋,父亲埋怨说,又不是陈焕生进城!说完这句话,他马上反应过来母亲不知道谁叫陈焕生,接着补充说,真是乡巴佬,土包子进城!这是学习,学习懂么?人家有高档酒店,酒店里有餐厅,吃喝拉撒都可以。话说到这份上,母亲便不再多言,不再插手。
父亲转了一次汽车,才坐上到A城的火车。这是父亲第一次离开小县到A城,他的大女儿也在这个城市念书,大姐当时考上大学,父亲只把她送上火车就折回来了,来回车票钱都要好几百呢,父亲省下来给大姐做生活费。他那点微薄的工资,处处得节约着,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家里吃的用的过得去就行,至今还没有一床好的被褥,幸好我们姊妹三人的学习,不再需要父亲操心。这次,要不是一碧千里给他汇来一笔钱,父亲还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从工资里拿出钱来,必然影响到女儿们的生活费。
想到这些,父亲的心甜滋滋的。
父亲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窗外的风景,一拨拨从眼前掠过,山川,森林,田野,草地,像些奔跑的孩子,在盛夏里兴高采烈。父亲的心也随着这些风景一路狂奔,有激动,有欣喜,也有疑虑。
对面坐着一对年轻的情侣,正拿着ipaid看电影,可能被剧情吸引,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父亲打心里觉得,年轻真好!可以天真,可以浪漫,可以无忧无虑,可以肆无忌惮。
父亲曾有过一段恋情,在乡上读初中那会儿,班上转来了一位女同学,叫星雨,沧阳人,父亲在乡上开小饭馆,她放学后就去给父亲帮忙。星雨长得小巧玲珑,脸上有一对小酒窝,说话时那种浓重的沧阳口音,有磁性还有音韵美,好像歌声一样吸引耳朵,他经常给我的父亲带好吃的,瘦肉,三川火腿,鱼干,悄悄塞在父亲的课桌里,让父亲中午下饭吃。我的父亲成绩好,为了报答星雨,他经常给她讲作业题。后来,在学校里,她几乎跟我的父亲形影不离。星雨是在父亲辍学前一学期搬走的,她家的小饭馆被一帮地痞赖账,酒后还砸桌子,跟她的老爹动了手。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她家的小饭馆开不下去了,只能走。星雨其实很不愿走,在给我父亲递来最后一张纸条时,我的父亲分明看到她脸上挂着两道长长的泪痕。我的父亲跟老师请假去帮忙她家收拾东西,搬上车,然后看着他们关上卡车车门,车子消失在视线之外。
辍学后,父亲曾去星雨的老家沧阳找过她,她的父母都很热情,星雨晚上还带他去镇子上的录像厅看录像,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紧紧搂住星雨的脖子,她不挣扎,双手抱住我的父亲的腰,父亲接着又将唇贴上去。父亲至今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美丽的夜晚,她那柔软而温润的唇,香香的,如触电一般,带着青春气息的两片唇,像贪吃的猫。他们记不清那晚是怎样离开录像厅的,又怎么回家的。星雨抓住我父亲的手,放在她胸前的蓓蕾上,星雨要把身子给他,他不敢,战战兢兢地将她送回屋。
父亲在星雨家住了三天,她的父亲依旧在镇子上开小饭馆,星雨希望父亲留下来,做上门女婿,她家还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了,按照当地的习俗,她将来得招姑爷,赡养父母。
但是父亲始终拿不定主意,他很想继续读书,对知识的渴望始终占据着他的心,他迫切地希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离开小山村,离开小奶奶的视线。三天之后他离开了沧阳,搭车去丽江,他想打工挣钱,挣够钱就回去读书,考个中专,中专毕业就顺理成章成为吃公家粮的人了。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和星语断了联系,后来,听说她结婚了,男的是个四川人,他们在沧阳的小镇上盘下一栋楼,下面开餐厅,上面开旅店,用沧阳人的智慧悉心经营,生意还不错。
6
火车钻出一个隧道,又钻入一个隧道,如一个时光机器,有时让人极度恐惧,有时又让人豁然开朗,兴奋不已,风景聚散,人世悲欢,这些大概是上天已经注定了的。父亲在座位上、在风景里、在思想中行走,迷迷糊糊之中,好像走过了一年,十年,二十年……
火车到站时已是华灯初上,父亲被一股人流推着往前走。一碧千里穿着大红的旗袍,在出站口不远处等他。他们一眼就认出了彼此,那么顺其自然,她走上来熟稔地挽住父亲的手,汇入来往的人群。
一碧千里带着父亲在路边的餐馆吃完晚饭,就开着车,载着父亲,驶向酒店。他们如两条缺氧许久的鱼,需要对方供氧和抚慰。他们已经忘记了各自的年龄,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家庭,在狭小的房间里为对方舔舐生活留下的伤口,修复疤痕。
一连几天,一碧千里带着父亲,如久别重逢的情侣,白天出入A城的大街小巷,商场,饭店,晚上手牵手去电影院。他们仿佛要把多年来没经历过,没有过完的生活,一并补上。他们彼此真正感觉到那种叫爱情的东西,他们奋力吮吸,弥补之前的营养不良。她给父亲买了手表,皮带,衣服,鞋子。父亲那古铜色的脸散发出生机,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七八岁。现在走在大街上,他也像城市人一样穿着,一样吃饭,一样哼歌,毫无顾忌的评头论足。
每个男人心里都藏着一座火山,一旦爆发出来,便势不可挡。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什么是爱情,这就是爱情;什么是生活,这就是生活。这些年活得太憋屈,我们都成了繁衍后代的工具,生殖机器,忽略了自己,掩埋了情感,更别提生活质量。
儿子住校,丈夫不在,她把父亲带到家里,四环海滨公园旁的别墅,三层小楼,和之前微信传过来的照片一模一样。他们在客厅亲吻,在她的床上燃烧激情。然后她为父亲做甜点、磨咖啡。一碧千里说,她从来没有这么全身心投入过,她和丈夫,每次都像是例行公事,不得不完成任务。他们爬上楼顶,打开玻璃房乘凉,沐浴海风,欣赏A城的华灯。
直到中心校给他打来电话,他才如梦初醒,父亲已经在A城待了一个礼拜了,超出假条上的日期两天。跟他搭档的那个老师在回校的路上骑摩托摔伤,他得回去给学生准备下一个礼拜的饭菜。一碧千里给我们三姊妹每人买了一双鞋子,给母亲买了一双手套,然后把父亲送上火车。
父亲说,等我回来!
一碧千里说,我等你!
7
二姐考上大学后,父亲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由于二姐念的是专科,所以没申请到助学贷款。为了家中多一点收入,父亲买了些东西,去求在县医院当副院长的本家弟弟,替母亲在医院谋个清洁工的活,他之前打听过,医院的工资可能要比食堂多一倍,活也轻松一些,空闲时还可以顺便收集矿泉水瓶,攒了拿到废品收购站,算是赚点外快。
正因为如此,父亲同时鼓励大姐,假期留在上学所在的城里打工,一方面是补贴家用,另一方面也是锻炼自己。找个管吃管住的活,一个假期挣三五百也好。他要求大姐提前步入社会,穷人家的孩子没有背景,一切要靠自己。
暑假,父亲安排我和二姐回到丁良村,采摘花椒,我家的老宅院周围,还有几十株花椒,价格好的年景能卖到千把块钱。顺便买些营养品带给爷爷,这个一辈子老实巴交的男人,已经患白内障两年了,此时父亲已经不再记恨他们。小奶奶有时会来城里,父亲就用医保卡,刷一些日常用的药品,让她带回去。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人活着,冷不丁就会被生活蜇一下,很多年过后,想想蜇人的蜜蜂,其实它也怪可怜的,蜇伤了别人,它自己也活不久。
这个假期,父亲没有闲着,连日的雨水已经把办学点的瓦片和墙体,淋得七零八落。他利用假期的时间,到中心校和教育局争取一些资金,趁学生不在,请几个工人,将屋顶翻修一遍,在修屋顶的同时,父亲找来工具,将学生的床架,桌椅板凳修理一下。
父亲不在家,母亲就在医院将就着吃,医院有一个专门向职工开放的食堂,医生护士象征性的交点伙食费,像她们这种临时工,食堂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副院长亲戚很照顾母亲,好几次在楼道碰面,都叫她进去坐。让她顺便把办公室的旧书报、矿泉水瓶都收了,拿去卖。
母亲去医院工作后,第一次发了工资,跟着新同事去逛街,在别人的鼓励下,买了双皮鞋。他拖地洗拖把的时候,经常被水龙头的水淋湿布鞋,她的买完,又分别为我们买了一双。没想到第二天就涨房租了,东西已经买了,剩的钱不多,房钱自然不够,为此母亲后悔了许多天,愁了许多天。
学校修缮完毕,父亲垫付的资金迟迟没有兑现,中心校让他去找教育局,教育局又让他去找中心校,他来回几趟,像皮球,被踢过来踢过去,窝得一肚子火,有人背后劝他,你何必那么尽心尽责,掏心掏肺,学校又不是你家的?那些房子坏了,你就不用待在办学点了,到公路沿线的学校来,回家近,还可以坐车。你骑的那破摩托车走在路上也蛮危险的。有一次父亲骑车在路上要不是及时刹车,再加之一块大石头挡在前轮前面,他肯定会连车带人冲下山崖;还有一次在雨水天骑车,路面泥泞车轮打滑,他连人带车跌倒在路边。由于长期在寒冷中骑摩托,父亲早已患上严重的风湿,气候稍有变化,就钻心地痛,有时疼得他整夜睡不着。
几十年了,父亲第一次将这些苦水一股脑地倒出来,他跟母亲交流很少,而我们三姊妹又太小,他觉得不适合跟我们讲这些!所以他只能将这些疼痛与委屈深埋心底,像休眠的火山,不敢轻易去掘开,他怕一触即发,便不可收拾!
那一夜,他独自睡在学校狭小潮湿的房间里,向一碧千里敞开心扉,一边啜泣,最后竟失声痛哭起来,他的哭声打破了寂静的山村,引来村里的野狗,叫唤了一夜。
8
一碧千里说,我们走吧,离开这个鬼地方,去澳大利亚,重新开启新的生活。我们去悉尼歌剧院,去“帆船之都”奥克兰,去北岛的温泉城,去墨尔本,布里斯班、阿德莱德、珀斯、大堡礁、黄金海岸和塔斯马尼亚……那些看不完的景,就我们两个,我们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生活。
她的哥哥在那边做工程师,姐姐在那里开公司,他们很早就让她离婚,移民过去那边,工作不用愁,直接进公司,不想干闲着也可以。可她舍不下儿子,儿子是她的命根子,是她十多年来生活的希望。儿子学习成绩不错,而且很懂事,每次她和丈夫争吵,儿子就悄悄躲在一旁流泪,当丈夫打她时,儿子就跑到中间,用娇小的身体护住她。现在,儿子即将大学毕业,二十一岁,一米八的个头,有能力自己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她现在完全没有什么牵挂了,只等着父亲的答复,如果父亲同意,她马上就去办理出国手续。
漫长的对话中,父亲反复权衡,学生、学校、家庭、孩子,这些围绕在他身边的名词,如一块块巨石,挪不动,更搬不开,将他紧紧困在中间,逃也逃不掉。
办学点的学生越来越少,减少了一大半,才剩十多人。国家搞扶贫攻坚,鼓励建档立卡户易地搬迁,政府给一部分资金,银行有贷款优惠项目,有点积蓄,胆大的人,都陆续搬走,剩下的人家,要么爷爷奶奶老弱病残,要么父母没多少本事。教室一个一个空下来的学生座位,像他心里一点一点增加的伤痕。学生没有了,他这个教师还有存在意义吗?现在,他只需要炒一锅菜,煮一锅饭,就足够他们吃一整天了,他带着十来个孩子围在火塘边吃饭,犹如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仔。
跟他一起教书的那个年轻老师,腿伤治好之后,便跟中心校强烈要求,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公路沿线的完小去上课。听上面的意思,文件马上就会下来,这段时间他几乎一直猫在家里,等待通知。
冬天里,寒风刺骨,似乎是山峦都要冻得凝固了。父亲看着稀疏的村庄,无限苍凉。如果有好的去处,都走吧!父亲喃喃地说,年轻人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困顿一辈子,终究没多大出息。
父亲想象着地球那边,那个遥远的澳大利亚,那些迷人的风景,那儿的春暖花开。想不完整,想不具体的地方,就用手机百度搜索一下。一碧千里的电话,打得更勤了,她告诉我父亲,她讨厌她的丈夫,她一直独自睡在自己的书房,不让他进去,他就踢门,像一条疯狗。我父亲安慰她,你顺着他点吧,亲爱的!当我父亲说出亲爱的这个词时,他感觉到自己的脸滚烫。她说她无法容忍,她的丈夫让她恶心,她怀疑自己为什么会逆来顺受这么多年。
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孩子们要走三四公里的路才能到家,所以不得不早些放学。山村的夜晚是孤独的,现在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人,幸好有一碧千里在网络那端陪伴,他们的话,好像总也说不完,如同从地下冒出的泉水,源源不断。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孤独,就是站在人群中,找不到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所谓幸福,就是独处的时候,总有一个人陪伴。她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他又打我了!一碧千里对我父亲说,他喝醉了酒,撕我的衣服,我不给他,他就打我,掐我的脖子,我被他掐得差点背过气去。
这个畜生!父亲吼道!你等着,我绝饶不了他。
那个周末回到家,父亲跟母亲说,他又要到A城学习去了,可能要去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父亲已经同意跟一碧千里一起去澳大利亚,她星期一就可以拿到两人的护照,机票也已经订好了。当“私奔”这两个字从父亲脑海中不经意跳出时,他感觉到脸红心跳。这个与年龄不相匹配的决定,这个与年龄错位的行动,这份迟到的感情,让他背负的压力颇大。可是既然选择了,就这样吧。他把办学点的十多个孩子放了,又跟中心校的领导请假,说最近身体不舒服,需要到大医院检查一下,还在财务那里支了一笔钱。
母亲照例一边做饭,一边为他准备出门的衣物。现在已是隆冬了,天冻得嗓子打结,母亲尽量把厚实的衣服装进他的旅行袋。父亲坐在沙发上,打量着母亲,这个皮肤黝黑的女人,仅有的一点姿色也被岁月给掩埋了,二十多年的相处,漫长,平淡,乏味,甚至是煎熬。马上要离开她,离开三个女儿,离开出租屋,离开这片土地,此刻父亲倒有些不舍,希望把一切留在记忆之中。
父亲转乘火车上去,一碧千里去拿护照,他们约定在省城国际机场会合,然后登机。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要不是幺女儿的那个电话,要不是我突然意识到还有三个女儿在上学,正需要我供养,离开了我这根顶梁柱,她们可能就轻易被生活压垮,不然我肯定跟她走了,去那遥远的地方,丰饶,美丽,幸福。这或许就是命,苦与乐,上天很早就安排好了。
那天我提前从学校回来,跟母亲要钱,学校要收高考资料费,母亲不在,我开始做饭,不小心被液化灶烫到手,钻心地痛,我哭着给父亲打电话。
父亲接到电话,停下脚步,迟疑了片刻,将登机牌塞在一碧千里的手里,折身跑出来。边跑边大声地回头对她说,“我要回家!”任她在后面怎么呼喊,怎么哭诉,父亲都没有停下来。
他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火车站。
当父亲匆匆赶到家,母亲刚从医院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她让父亲歇着,她马上去做饭。父亲看到,出租屋外小院的铁丝上,晾着母亲为他洗好的衣服,随风轻轻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