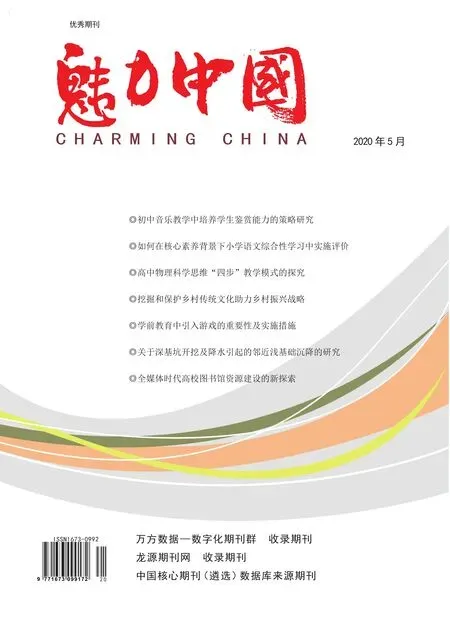中国真的缺乏集团生活吗?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
2020-12-07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今天我主要想就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以下简称《要义》)浅谈一下自己的读后感。本书集白话文和文言文于一体,读起来并不是那么通畅,因此,我主要是就书中自己感兴趣的“西洋人的集团生活与中国人的家族生活”论述了自己的一些小小思考。
梁漱溟老先生在开头就说西人所长吾人所短的在于“公德”,即公共观念、纪律、组织能力、法制精神。梁老认为中国人缺乏这些“公德”,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集团生活,本人对此打上了疑问号。我认为中国人并不缺乏集团生活,只不过中国人的集团以家族为主体。梁老斩钉截铁的把“家族”与“集团”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个人觉得有失偏颇。与梁老同时代的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对“集团生活”的见解可以以此为证。通过浏览卢作孚的遗著,可以发现卢氏的现代化之梦始终与一种强调秩序与集体的“集团生活”概念紧密相连。在卢作孚的笔下,这种新式“集团生活”的建立,不仅是民生公司和北培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更是现代化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卢氏的现代化实践也是一种以“集团生活”模式为基础铺展开来的,并由此打造中国社会改造。此外,卢氏所倡导的“集团生活”,不仅强调秩序、集体组织,带有一种鲜明的领袖主导型团体主义色彩,而且同样也具备三个特征:整个生活相互依赖、集团间之悬为标准相互竞争、有强有力的规定人们行动的道德条件,这些与梁老所认为的西洋人之集团生活殊途同归。卢作孚曾在《民生公司的三个运动》中指出,集团生活本身并非现代化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存在集团生活。中国传统的集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推而广之最多只囊括以某一家庭为核心的各家族亲朋邻里关系集团,集团生活便是家庭生活,集团间的竞争便是亲朋邻里之间的“门阀之争”。这里特指的是中国传统社会里集团生活,大部分人们主要是为家庭和亲朋牟利,很少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和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差序格局”有异曲同工之妙。费老用亲族或关系圈来比喻中国人的“公”与“私”,并由此得出结论“当圈子的外延如水面上的波纹一般以个人亲族圈为核心无限推广下去,乃至囊括全天下时,‘私’便转化为‘公’了”。在费老的这个比喻中已经暗含了卢氏的现代集团生活内涵。通过分析西洋人的集团生活、卢作孚的集团生活和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本人认为卢作孚老先生所描述的集团生活为现代集团生活,其在传统集团生活基础上,将集团组织的外延进一步扩大、推广,由家庭、亲族和邻里形成的集团,扩展为事业、地方和国家,这也和卢氏建立集团生活理念以推动中国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不谋而合。因此,西洋人的集团生活与中国人的家族生活并不是割裂开来的,两者也有共同之处。对于一些学者片面的将其社会法治混乱,组织能力低下及公德缺失的现象归结为中国集团生活缺失或将集团生活缺失理解为就是缺乏合作精神的这些看法,本人表示十分的不赞同,这是对集团生活概念的扭曲理解,更是对中国问题的单向度理解,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建设。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就梁老所说的中国人缺乏公共观念、纪律、组织能力、法制精神谈谈自己的看法。纵观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学者对梁老的观点马首是瞻。一部分学者不加思索就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的原因、弊端和解决措施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此我并不加以否定,因为那些学者可能是站在社会学、政治学或者历史学等其它学科角度来理解梁老的观点,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出身的我,则要站在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对此辩一辩。今天我只谈一点——法治精神。梁漱溟老先生在《要义》中指出:“一家之中,老少、尊卑、男女、壮弱,其个别情形彰然在目;既无应付众人之烦,正可就事论事,随其宜更且以朝夕同处……而相亲如骨肉,相需如手足,亦必求其细腻慰帖,乃得关系圆满,生活顺畅。此时无所用其法治,抑且非法所能治。”近几年有的学者就此展开谈论,认为中国一直以来以家庭为中心,缺乏集团生活,这使得社会好循人情,缺乏法治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遇事总喜欢托人情,找熟人办事,不相信中国的制度和规章,并认为中国的法制不健全,直到现在我国的法治还不够完善。对此,我疑团满腹,深叹一句:如今中国的法治不够完善吗?如果说中国古代法治不够完善,我绝没有反驳之由,因为我从小也是深受《三字经》、《论语》、《传习录》等儒家经典所影响,并且中国儒家治国,讲究仁义道德,以纲常伦理规范人与人的关系,对此我深信不疑。但细致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发展历程,可以清晰看出我国的法治建设逐渐呈现出一种全方位、全覆盖的大格局与新气象。吉林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白显良对中国法制40 年的历程、轨迹和经验的总结可以以此为证,他指出中国法制的历程分为法制创建新时期、依法治国新阶段和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 。除此之外,武汉大学的秦前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李林、东北师范大学的刘桂芝教授等众多学者对中国新时代的法制进行研究,这也突显了法制如今在中国的地位。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中国并不缺乏集团生活,梁老以中国人缺乏公共观念、纪律、组织能力、法制精神为标准来定义中国的集团生活,也许在他那个时代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事物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发展就需要辩证的否定,现在一些学者以“学而不思”的姿态对梁老的观点深信不疑,这种单向度思维不仅不利于经典著作的传播发展,而且也可能引诱我国发展走向歧途。因此,作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有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勇敢亮出批判精神的宝剑,以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看待任何事物和任何观点,这将成为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