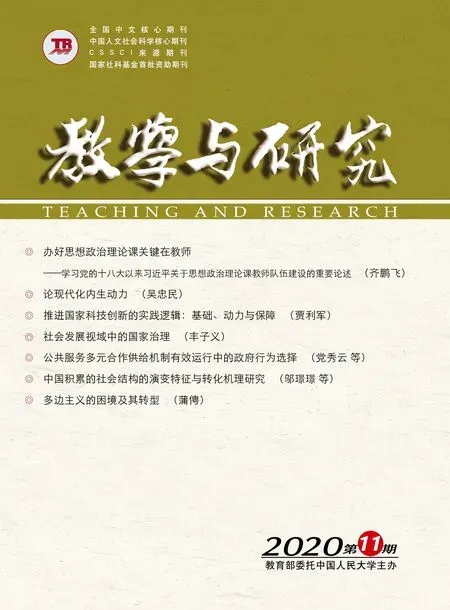西方左派对中国道路的认知形态及时代回应*
2020-12-07张晓
张 晓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中国道路不仅成为当代中国自立自强历程的高度凝结,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为争取民族发展而进行奋斗的现实标杆。在此背景下,西方左派学者普遍对中国道路的认知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但也有部分学者存在着偏见和误解。这意味着,尽管中国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如何基于中国发展的已有成果,阐述好中国道路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回应西方左派对中国道路的种种误解,依旧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不仅事关对中国道路的人类价值定位,还事关国际共产主义的未来整体航向。
一、西方左派的中国道路认知形态:一种阶段性梳理
20世纪后半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复苏并呈现短暂繁荣,给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造成了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扰。正当西方左派阵营内部不断发生分歧、理论共识不断肢解、总体步入沉寂之时,中国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给西方左派学者重新带来了崭新的研究素材。相当一部分西方左派学者纷纷关注这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著书立说,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拓出一片新的发展空间。西方左派对中国道路的认识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此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除了阿尔夫·德里克(Arif Dirlik)等少数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政治体制转变之外,(2)Arif Dirlik, “ Socialism Without Revolution: The Case of Contemporary China”, Pacific Affairs, 1981—1982, 54(4):632-661.大部分西方学者仍然更多地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进行研究。特别是在美国的哈佛、康奈尔等一些著名高校中,有相当一批学者依旧热衷于研究中国的阶级革命状况。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但是,这种政治体制能否继续发展中国,他们是持有质疑的。(3)Richard Curt 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5.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造成社会主义阵营遭遇重大挫折,资本主义右派阵营弹冠相庆,不断抛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背景下,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人在政治、文化、理论等层面审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将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解模式用于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导致对中国道路的未来发展并不乐观。(4)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71.同时,尼·维克托(Nee Victor)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关注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发展,但也提出了质疑,认为从传统的市场经济角度来说,中国在处理社会公平方面,会面临一系列的难题。(5)Nee Victor,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 56(6):267-282.当然,这些担忧往往也是基于缺乏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量化认知而武断产生的。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党的十八大。其间,西方左派对中国道路给予了全面的关注,对中国道路逐渐认可,但是保守主义态度依然浓重。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变革,全世界愈加关注中国道路。西方左派也纷纷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带来的实质性意义。一方面,从经济领域来说,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成为西方左派学者在当时热议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到90年代末本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一体化潮流的步伐日益加快,并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左派学者们对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产生怀疑。(6)Lin Ch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85.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市场持续扩大开放,使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国内以“中国创造”为特征的产业转型。(7)Michael Keane, Created in China: The Great New Leap Forward, Routledge, 2007, pp.33, 152-153.另一方面,从政治领域来看,有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模式仍然需要面对西方的挑战。例如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等人基于中国经济的重大发展,重新思考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存在形态。(8)Martin Hart-Landsberg,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Critical Asian Studies,2005,37(4):628.罗伯特·韦伊(Robert Weil)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国情得到极大改变,也令社会主义在中国得以发展下去,但仍需处理好“社会主义与改革之间的关系”。(9)Robert Weil, Red Cat, White Cat: China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6, p.264.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指出,中国在政治领域遇到的最大阻碍,是如何保持与西方式民主制度差异的同时,摆脱苏联社会主义的传统弊端。(10)Joseph Needham, 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4.中国道路给包括左派人士在内的西方带来的不仅仅是对传统政治优越感的挑战,更加重要的是对一种包含市场经济的新型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困难。
第三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西方左派对中国道路的人类意义有了进一步认识,保守的立场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西方左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产生新的研究动机。一些理论者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正确地处理好“原创”与“再造”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苏联模式所代表的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原创”。苏联的失败也意味着一意孤行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由此,中国真正“再造”了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道路,让社会主义在中国经历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种种讨论,依然表现出了强大的活力。奥德·阿恩·维斯塔(Odd Arne Westad)等热衷于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他们认为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从“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的跨越,最直接地体现为其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当前的中国,是“令人满意的或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改革的和突破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11)Ramachandra Guha, ed., Makers of Modern 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99-214.从世界发展的横向视角来说,包括西蒙·弗莱尔(Simon Fry)和伯纳德·米斯(Bernard Mees)等学者基于2012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情况,把中国同周边的日本、韩国发展经历进行比较,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处于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之中。还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凸显出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鲜活的参照。(12)Simon Fry and Bernard Mees,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Asian Socialist-transition Economies: China, Vietnam and Laos”,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16, 28(4):1-19.中国证明了社会主义仍然能够在这个时代具有强大的活力。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姿态进一步明显,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动向。在西方,2008年金融危机给社会造成重大冲击,“新自由主义西方撤退”的声音不绝于耳;民粹主义的崛起,更是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平稳复苏增加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在这一背景之下,有学者通过对中国社会多个领域的分析,对当前的中国道路予以了肯定。例如,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认为,习近平正带领全中国进行系统深刻的改革,创造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境界。(13)Barry Naughton, “Is China Socialist?”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 31(1): 21-22.或是结合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和未来中国在“新时代”的发展目标,描述了中国道路的既有轮廓。(14)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Cai Fang,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U Press, 2018, pp.63-65.而更多的学者还是关注中国当前在全球一体化中的表现,尤其是中国在与西方贸易过程中的地位变化。例如丽贝卡·E·卡尔(Rebecca E. Karl)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快速建立起独立化的经济模式,寻求新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给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5)Rebecca E. Karl, “Reflections on Revolution and Socialism in Our Times”, Cultural Critique, 2018, 98(Winter):278.不过,更多的左派学者更加侧重思考中国的崛起给地区和世界格局带来的变动,特别是结合当前中美的关系加以讨论。他们认为,中国的强大所带来的对美国地位的挑战已经大过机遇。这是造成部分西方国家宁可违背全球一体化趋势,也要采取一系列激进的措施针对中国全球贸易的原因。例如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认为,一方面,西方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针对中国的种种措施,会给世界贸易造成多种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西方之所以采取这一系列举动,却也是出自他们对当前在世界贸易,特别是在与中国贸易关系中地位的反思而做出的。(16)Susan Watkins, “America vs China”, New Left Review, 2019, 115(Jan Feb):12-14.综合来看,当前西方左派对于中国道路的评价持越来越多的肯定态度,对于中国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影响也予以充分的重视。但是,理论者们对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却仍然未触及到深层次。
二、西方左派关于中国道路认知的理论诊断:基于“三大规律”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一条科学的、独创性的,并且符合中国时代需求和时代规律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1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勇于探索、科学探索,总结出发展中国道路的重要规律,成为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当前,西方左派对中国道路的认知缺乏,从理论角度来看,正是源于对中国道路规律的内涵把握不清,导致无法对中国道路进行准确的理论定位,更无法从人类发展视角,对中国道路进行科学准确的历史定位。
第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把握不清。自从上世纪中后期西方工人运动走向沉寂以来,西方左派政党长期处于资本主义政治的渲染之中,早已丧失了政治斗争的决心,使得西方左派无法切实体会到无产阶级政党之于社会的内在意义,也就无法体会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真实含义。西方左派理论者在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时,无法跳出西方现有的资本主义民主氛围,因而无法切实掌握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建设凝练而成的执政规律。这是造成西方左派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把握不清的客观原因。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充分把握,已经成为中国道路不断取得胜利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与西方政党的执政理念产生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同广大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而并不是代表特定人群的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是一切源于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精确表达。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升执政水平,归根到底,都是在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时代发展同向。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是与时俱进的政党。其指导思想、治国理念、治理能力能够随着治国理政过程而不断发展,既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指导实践,又能够从实践中不断发展理论,从而能够基于时代、先于时代。西方左派政党及至整个左派阵营由于缺乏经验,又不能够从一次次运动和执政的挫折失败中吸取教训,自然导致无法掌握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长期执政的、取得巨大民族成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规律。
第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把握不清。西方左派对中国道路的批判,是在一个非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下,普遍缺乏社会主义建设认知的基础上开展的。他们只能基于资本主义批判社会主义,对中国道路的现实和前景认知尚显狭隘。西方左派眼中的中国道路,依旧是在西方话语语境中构建的。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开始阶段,因而就提升人民实际生活质量而言仍需要走完漫长的道路,“漫长的革命”仍然适用于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真正发现并利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真正推到更高水平,成为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可能方案。这对于任何一个西方政党来说,都是无法具备的优势。中国道路是属于中华民族的道路,更属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它突破了苏东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束缚,是人类历史和马克思历史道路的创造性发展。中国道路的开辟和延伸,象征了这一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人类步入20世纪之后,重新焕发新的生机,更加意味着,一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图景已经生动展现在世界面前。当代中国生动诠释了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让马克思主义更加鲜活地展现在人类和未来面前,让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不断得到彰显。西方左派未能从改革开放的具体探索中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特殊性,更不能体会这一阶段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应当说,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性和阶段性缺乏足够的认知。
第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不清。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科学表达,也是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逻辑表达。但是,西方左派亲身经历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长期沉浸在西方政治氛围之中,难免会对马克思主义描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产生歪曲化理解。他们不断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将一些除经济基础的其他因素加入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中,力图淡化稀释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作用。恩格斯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指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08页。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左派阵营中呈现出众多形式,归根结底,是左派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新变化,往往只是借用马克思主义解释而非揭露资本主义的发展,将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本末倒置。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都是革命的对象,因而马克思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哲学,绝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当前的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将马克思主义用于解释过去和当前,极大磨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可想而知,在对待中国道路时,西方左派不能从人类社会发展出发,将中国道路真正理解为中国历史和人类发展的必然路径,更不能将之作为验证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解释和预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佐证,导致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备的未来意义和人类意义。
三、西方左派关于中国道路认知的意识障碍:缘由与对策
中国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阐释,是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指出:“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8页。正确区分共性和个性、普遍和特殊,是正确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态度。但是对于西方左派来说,如何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固有意识,摆脱西方普世观念,能够根据各民族各地区的具体实际,理解社会主义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多元化存在,进而真正尊重世界各个民族的多元化发展,却成为他们不得不面临的意识障碍。
一方面,西方左派仍然无法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僵化意识,导致不能够用客观心态评价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是探讨人类最终发展的科学推论。而中国道路的顺利开辟,使得人类解放之路获得了现实印证。这对于西方的传统文化认知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必然会受到来自左右两派的共同批评。西方左派对中国的误解和质疑,从源头来看,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解偏差。他们关于中国道路的种种质疑和误解,我们可以定性为是在传统苏联模式退出历史舞台后,对于一种新的符合本土发展规律的新社会主义模式的疑惑。长期掌握世界话语权,令西方中心主义早已扎根西方。一种文化、制度,甚至是种族优越感,成为影响他们看待其他人种和民族的意识。他们极力向世界推广他们的普世价值观,将世界同一化,忽视多元化,成为他们无法正确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制约。
另一方面,西方左派仍然过度依赖主观臆想,未充分置身于社会主义中国开展实践调查。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包括西方左派在内的西方学界的普遍问题,是往往避开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实际情况,或片面就某一方面情况进行理论阐释,维护自身的理论制高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困境,与其说是源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挤压,不如说是西方左派在缺乏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现实关注情况下,仅仅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闭塞改造,已形成一种封闭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在对待中国问题时,往往根据思维惯性,对中国道路进行主观化评判,既脱离中国的具体发展实际,也脱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现实和主观思维的科学阐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真理观。
中国道路,与人类之前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轨迹都完全不同,不可避免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关注和质疑。特别是在当前西方整体发展速度滞后、中国快速崛起,中国道路获得越来越多的世界认可的情势之下,西方中心主义会愈加容易反弹。针对西方左派对中国道路的意识障碍,国内学界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应对。
第一,要在提升道路自信的同时,正视西方左派的中国道路认知问题。西方左派对中国道路的认知问题,往往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价值取向。西方学者往往囿于理论和环境局限,对中国道路的看法出现认知偏差和认知不足,其中还会涉及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要始终认识到,西方左派对中国道路的认知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和道路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醒,当前,国内外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多种认知错误。(22)参见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这些错误背后既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认知偏差,也反映了对中国道路之于马克思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意义的认知偏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断敞开,国内学术界与包括左派学者在内的西方学者的正面对话不断增多。其间,更要秉持中国道路的科学内涵,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真理普遍性与马克思主义在各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的关系,界定好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性差异。
第二,要继续阐释好中国道路的结构内涵,凝练好中国话语。用马克思主义话语阐述中国道路,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又是应对西方质疑和误解的重要理论准备。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提升中国道路理论的系统性。阐述中国道路,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最新成果紧密结合在一起,做到以理服人、以现实服人;另一方面,要充分阐述中国道路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断再创造的过程。要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丰富中国道路实践,也要用中国道路的最新实践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防止将马克思主义成为“论坛上”和“讲台上”的马克思主义。(23)陈先达、孙乐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总体来说,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描绘好中国道路,切实提升中国道路的理论传染力和说服力。
第三,要提高理论辨别能力,对西方左派的错误认识予以坚决回应。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依旧严峻,这要求学术界随时提高警惕,防止各类扭曲、误解中国道路的观点流行于世。应当正视而不是回避西方左派的错误认识,并且从理论层面和意识层面予以回应。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内核的同时,认真辨析西方左派的中国道路观点的本质,把西方左派对中国道路的认知偏差和不足,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话语表达的契机,在理论批判中不断丰富中国道路的阐释。要明确指出,中国道路是位于世界东方的古老中国,为人类开创一条人类解放道路。这条道路打破了数世纪以来西方对世界的价值观主导,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有力回击了过去来自西方的种种质疑。要充分借助理论武器、基于现实素材向世界表明,所谓“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社会主义失败论”已经失败;(2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3页。中国道路也必定能够成为人类寻求解放的现实模板和科学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