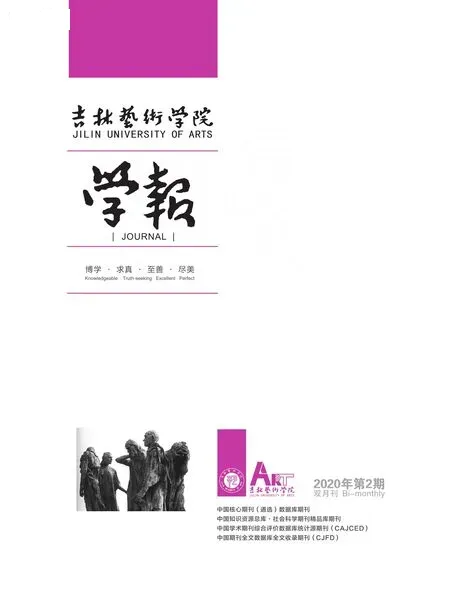厝火积薪的当代生存想象
——病毒题材灾难片叙事美学解读
2020-12-07高超
高超
(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天津,300387)
灾难片在好莱坞类型片发展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危机的反思往往来自关于灾难的经验及联想。灾难这一概念的辐射范围涉及多个层面的表现形态,而灾难题材的创作通常会包含着原发性自然灾难、人为性灾难、外星文明威胁性灾难等基本类型模式。但实际上又存在着整体叙事性效用和审美接受心理设定的差异,不同影片在表现人类为了谋求生存与灾难展开抗争时,创作者在处理题材情节模式、人物体系建构以及主题切入角度上,也会采取不同的创作姿态与方法。由于受到灾难书写过程中选题同质化的影响,如洪水、地震、海啸、飓风、雪崩等的传统自然灾难或外星种群入侵地球等科幻色彩浓重的灾害情节类型都日趋陷入难度较高的创作瓶颈,因此灾难形式的选题突破成为灾难片叙事建构的首要问题。与上述提到的两种灾难形式不同,病毒题材灾难片往往借助某种病毒的传播及蔓延为契机,由此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随着病毒的蔓延而引发的多层面危机延宕也成为矛盾累积和深化灾难情节的主要过程。早期的灾难片创设,往往多注重自然灾难或科幻灾难的题材书写,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全面实现以及人类生态的持续恶化所导致一系列世界性现实灾难的发生,使人类自身生存危机意识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面对医学难题的日益凸显,人们遂对于微观世界中近乎神秘存在的病毒生发出清醒的无奈与恐惧,病毒题材灾难片也由此成为灾难片创作中的重要分支,其成熟的类型叙事经验、精准的恐惧心理投射、强有力的社会现实观照决定了这一亚类型影视作品强大的市场效应和深刻的艺术意蕴。
一、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及“罪与罚”式主题呈现
病毒作为一种集神秘色彩与强大摧毁力于一体的微观生命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类世界的生存与繁衍,其爆发和蔓延带有与其他灾难一样无法预测的偶发性特点。因此,病毒灾难片借助人类与自然抗争的灾难历史以及与人类生命休戚与共的危机事件,表现出观众心中对自然环境、社会秩序、生态伦理等问题的焦虑与恐慌,从而能够更好地对接当下社会生活,引起人们深层次的生命思考和现实反思。病毒灾难的取材设定,可以取得生命个体以及社会群体的双重认可,主要原因不外乎其充分调动了人类心理深处对于“被毁灭”“被灭亡”的恐惧认同感,即灾难的来临也并非等同于虚构的神话劫难,而是完全脱胎于“人总会生病”的日常生活经验,病毒灾难片将此经验的可能性进行了有效的戏剧延伸,而后将灾难的源头直指人类贪婪、自私的欲望索取以及无法回避的宿命惩戒。这类影片虽然通常会强调病毒爆发的偶然性,但往往在故事的开端会以一种戏剧化的姿态让“病毒”这一主要角色“登场”,在强调其潜在威胁性的同时也交代出灾难的渊薮,形成强烈的心理悬念,激发观众后续灾难的联想,显然这些都体现出鲜明的“潘多拉魔盒”母题的寓言特质。如被视为病毒灾难片始祖的经典影片《卡桑德拉大桥》(1976年),故事开篇是恐怖分子闯入日内瓦的国际卫生组织总部,欲实施恐怖袭击,受到了保安人员的阻击。在追捕过程中,警员不小心将实验品鼠疫细菌打碎溅到恐怖分子身上,一名歹徒当场感染腐烂而死,另一名则窜逃到一列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上……我们不难发现,“打碎”的鼠疫细菌在叙事层面的意义所指就是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未来注定带来灾难。作为诱发式矛盾在这样的偶然事件中注定附着了很强的悬念色彩和神秘感,也必然成为电影故事构成最需要的叙事特质。
科学实验作为现代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却成为病毒蔓延的源头,故事开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类对于自身存在和文明的深刻反思,鼠疫细菌被打碎散布出如古希腊悲剧神话故事中的“神谕”一般,表明这是一场“罪与罚”叙事母题下的人类命运历险想象,对于人类发展进程中日渐明显的生态恶化、灾难降临等共性经验的认知成为该想象成立的前提,因此在许多后来的病毒灾难片中这一共性经验常被隐去,以具体化的继发性事件作为具体故事背景,使得故事整体节奏更为紧凑、悬念情境生成更加直接。在影片《极度恐慌》(1995年)中,开篇直面残酷的战争灾难场景:1967年在非洲的扎伊尔莫他巴河谷,美军军营被突如其来的疾病笼罩之后,紧接着军营被炸弹摧毁,附近林中的白脸猴发出阵阵惊叫声。直到90年代,一个美国年轻人在非洲扎伊尔捕到一只小白脸猴,并带回国出售,因此一种新型疾病在旧金山开始蔓延……作为这个故事的开端,历史时空的回溯不仅仅交代了一个叙事背景,更重要的是以“预言”的口吻阐释了恶疾爆发的根本原因,暗示着“罪与罚”的历史隐喻。这种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及“罪与罚”的故事形态,在病毒灾难片中被大量运用,也借此作为一种对现代社会尖锐矛盾的体现,以及对人性自私与贪婪的警戒。在影片《流感》(2013年)的故事开端采用同样的灾难情节模式:一群东南亚偷渡客历经艰险来到韩国,但是整个集装箱内的偷渡客几乎全部死亡,只有一人拖着羸弱的身体侥幸逃入闹市之中,短短一天内,病毒迅速蔓延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人不知不觉间被感染,死亡的阴影笼罩在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上空。病毒的“流出”与扩散,来源于未知的世界,偷渡客作为实施不法行为的越境迁徙者,是地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受难者,偷渡更是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一个典型缩影,所以这一事件带来的恶果既有个体性,也有群体性。
电影作品是人类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对于灾难的想象多来源于内心深处对现实世界的未雨绸缪,病毒作为一种与人类同生共存的客观存在,以四两拨千斤的巨大威胁将人类轻而易举地置于“存在或是毁灭”的荒诞境地,虽然传统好莱坞类型片多被视为人类精神寄托的“梦工厂”,但是病毒灾难片与现实世界直接对话的姿态将人类内在的脆弱与恐惧本质加以放大,观看影片既有当头棒喝的警醒反思,又获得一种精神的慰藉与生存的勇气,关键原因便在于病毒题材叙事所蕴藏的劝诫式主题内涵。
二、经典英雄救世与当代神话书写
1. 病毒世界的“最后一分钟营救”
在病毒灾难片中,病毒的爆发和蔓延是一条贯穿始终的核心叙事线索,人与病毒的对抗可以围绕多层矛盾关系展开,高强度时间压力和封闭式空间成为叙事情境创设过程中最为显著的重心元素。病毒灾难片延续了灾难片叙事危难降临的紧张感和意料之外的戏剧可能性,“在形形色色的灾难片中,生与死的矛盾都是最具有张力的戏剧前提”,[1]因此带有古典三一律色彩的戏剧模式在大量此类影片剧作中被运用。如在《卡桑德拉大桥》中,满载乘客的列车无法停止地向一座将要坍塌的危桥疾驰而去,而乘客并不知情,因为他们正置身另一层危险之中,即致命性传染病毒的大肆蔓延,死神随时会出现在眼前。摆在影片主人公医生张伯伦面前的“营救”任务是无比紧迫且艰巨的,他必须与前妻联手并领导车上乘客对抗军队武装人员的强行管制,抢在列车完全冲上卡桑德拉大桥前使得列车脱险得救。由此我们可发现《卡桑德拉大桥》被大众共推为病毒灾难片叙事范式的原因,而后来的此类影片都或多或少保留了其中的一些情节痕迹。在《极度恐慌》中类似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情节依然在病毒对抗的叙事结构中作为高潮部分出现,当主人公山姆医生的妻子也不幸被感染病毒而生命垂危之际,政府做出了准备投放炸弹摧毁镇子以确保病毒不扩散的决定,但此时山姆医生查出了病毒的来源,他必须赶在镇子被炸毁前找到具有抗病毒血清的原始病毒携带者,因此“营救”迫在眉睫。
从上述影片情节可以看出,在病毒灾难片中“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戏剧张力往往还来源于剧作中多重人物行动阻力的设置,在庞大的新闻舆论以及社会秩序的整体影响下,病毒蔓延所形成的危机情境并非仅仅是一种针对病毒对抗的向内膨胀的戏剧压力,也同样变成一种外向式的戏剧压力,即人与现实社会的深度博弈。如影片《流感》的故事结局,盆塘市已被病毒攻击沦陷,灾民众人绝望的请愿昭示着叙事事件的戏剧突转与“升级”,由人们与病毒对抗的显性灾难对抗变为人与国家机器、权力秩序的对抗,因此“营救”的戏剧效果也随之“升级”,并达到人们对现实社会情感投射的共情效果。
2. 救世英雄与“遗憾”结局
在以“营救”为宗旨的整体叙事脉络中,承担核心叙事任务的第一责任人,即主人公往往在角色设置层面具有鲜明的舍身取义的卡里斯马美学特质,情节推进的过程即是其作为救世英雄逐步肩负起终极对抗病毒灾难的全过程。这样的救世英雄再次印证了人类原始的英雄崇拜,当然也契合了大众文化语境下普通观众在影像世界的现实消费理想,同样“英雄主义也是灾难电影提供给观众进行消费的商品之一,英雄在灾难中的历险,成为消费者的一次兼具审美和娱乐效益的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英雄主义又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2]。
但相较普遍意义上的灾难片而言,病毒灾难片中的英雄人物一般都直接对应现实世界中的社会角色,而非在角色身份设置上可以进行任意虚构或科幻假设,所以这些与病毒对抗的英雄形象往往多倾向于病理科学家、医生、警察以及其他具有社会普遍认知度和职能代表性的职业身份,这样的职业身份让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或较早地获悉病毒传播的“秘密”。他们本质上还是“秘密”外泄的民众“吹哨人”,虽然在过程中会面对难以抉择的利益取舍及人性选择,但其特殊的职业身份已经注定他们成为英雄的必然性与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可推卸性,这种宏大悲壮的历史使命为他们的叙事身份平添了不凡的救世光环,为力挽狂澜的戏剧反转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与其他灾难片中较为宏观的地震、海啸、火灾、火山爆发等灾难形态相比,病毒灾难片与之最为明显的区别是矛盾对抗体为肉眼不可见的细小病毒或细菌,在影像的显性呈现上无法直接形成震撼惊悚的直面体验。英雄通过与病毒直接的二元对抗达到最终叙事目标已然不可能成立,于是此类影片中常见的英雄救世往往采取较为“迂回”的叙事策略,在英雄与病毒这层显性与隐性不对等的二元对抗的叙事关系链条中加入一层或多层典型的社会关系,继而将此转换为“救人”,最终完成英雄身份的确认及升华,生成英雄形象在病毒题材灾难叙事中的主题意义。这种变化从整个事件叙事逻辑的角度,再次验证了电影叙事学中的人物“行动元”与“角色”的内在关系。
为了达到英雄救世的行动目标,分担主人公“拯救”的行动压力、增加人物关系体系的戏剧存在,英雄人物往往采用两人或多人搭档式的人物关系形态,还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搭档关系的每个人都倾向于具有承担公众责任的社会角色,这种模式在《卡桑德拉大桥》中就已经存在,张伯伦医生与女作家珍妮佛属于夫妻关系,英雄之间的联手合作在无形中照应了对社会现实责任的承担,也增加了大众对超现实色彩病毒叙事的认可度。如影片《流感》开篇就搭建起的消防队救援人员姜智久和女医生金仁海这一对人物关系,成为抗击病毒的合作搭档,这种将女性角色设置为直接参与灾难“拯救”的英雄角色,可见英雄形象的性别设定在此类题材影片中有新的变化。如今在《神奇女侠》系列等以女性英雄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好莱坞大片风靡全球的整体形势下,英雄书写也已经不再单纯以男性为中心。在《传染病》(2011年)中也有关于这一创作趋势的明确表征,该片带有鲜明的女性叙事特点,从病毒灾难爆发的受难者到拯救者都以女性为主体,最后也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人员利奥兰特斯与美国疾控中心研究院艾琳博士这样的女性角色联手抗击病毒灾难的,这在编导的救世理想层面带有独特的意味。
虽然病毒灾难片对于事件书写都倾向于将英雄救世作为结局,但在面对客观存在的病毒灾难时做到力挽狂澜并完美收场却又显得不切实际,编导往往在病毒灾难片的最后采取一种“遗憾”的结局。在《卡桑德拉大桥》的最后,极速奔向大桥的火车被炸断了,后面车厢的旅客得以逃生,但头部的车厢没能躲过厄运,大桥瞬间坍塌,旅客掉入河中死伤无数。再如《釜山行》(2016年)中,在开往釜山的列车上,主人公拼尽全力阻断了灾难,依然没逃过被丧尸感染的结局,英雄以自我牺牲成就了抗击病毒灾难的胜利,这种在“毁灭”与“存活”之间的选择性收场,是“遗憾”的结局模式对人类命运的现实主义观照。
3. 思辨底色的正义救赎
通常在病毒题材灾难叙事的情节构成中,创作者尤为重视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较量,可以说存在于无形的病毒蔓延不仅仅作为一种叙事矛盾的显性存在,且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秩序与文明发展的“试金石”。与病毒的抗争过程本质上是对“人本主义”核心价值及人类正义存在的重新审视,带有“缺憾”意味的结局一方面充分显示出人类自我“惩戒”的内在精神反思,另一方面以乐观的叙事姿态确认了危难之际正义秩序的绝对价值。病毒灾难带来的后果,需要人类经历苦难和牺牲去完成自身救赎,在此过程中人性世界与生俱来的阴暗、自私、贪婪、邪恶也随之暴露,可见这些都是我们对于自身无法消除的“原罪”的苦恼,因此,与病毒灾难作斗争的英雄,宿命般地需要经历充满艰险与苦难的路才能实现成功。
病毒灾难片会在结构安排上设定一种有悖道德伦理的叙事矛盾,借以展现源于人类社会秩序的异化与失控,从这种创作特征来看,病毒灾难片的叙事更具有明确的“醒世”寓言的意味。在影片《盲流感》(2008年)中关于“白盲症”这一病症的隐喻直指坐视不理的冷漠社会风气与人性阴暗面,当“白盲症”传到城中后,政府决定采取极端手段将病人全部送去隔离区自生自灭,使得人性中安全自保的丑态尽显。作为失明的城市唯一的记录者,创作者借医生太太的眼睛看到了政府对待民众的虚伪和冷漠,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因为生存而丢却尊严的残酷现实,人性的自私与阴暗成为“白盲症”病毒灾难散布传播的“原罪”,在影片结尾的一句话充满了发人深省的隐喻论调:当整个城市失明的人恢复视力的时候,她或许会“盲”。她是灾难的参与者、记录者、拯救者,也是一个悲哀的人,她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也看到了自己生命渺小的格局。影片中所呈现的正邪较量是隐形的却又无比震撼的,主题的表达透露出一种绝望苍凉的悲剧意味,以此抵消了影片开篇全城疾病弥漫散布的恐慌,以反诘辩证的深层叙事口吻将观众的注意力再度引向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长存的契约秩序。思辨底色的基调设置,让病毒灾难片的审美心理不再局限于“惊恐、震撼”的表层观影刺激,而是更具有对当下人类社会存在居安思危的洞察与启迪。
三、病毒灾难类型叙事下的世俗想象
病毒灾难片在题材呈现层面具有灾难片类型叙事中固有的戏剧性和震撼力,同时现实社会的进步与人类文明的演进为其提供了“温床”般的先天叙事背景。以病毒爆发作为开端的故事具备了对接人类现实生活的基本前提,而且后续的情节推进无论以现实主义基调或科幻想象姿态都将会符合自然且明确的戏剧性逻辑要求。从剧作层面而言,这种开篇的情节模式也完全吻合好莱坞类型片经典三幕式剧作“秩序—失序—恢复秩序”的结构要求,灾难的发生、演进、完结,都承接“应对病毒”这一集中的核心矛盾线索紧紧维系,使得这种故事模式既可以采取相对单一的叙事思维进行讲述,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散思维的故事联想。虽然不同影片在叙事架构上存在较大差别,但通过梳理甄别这些影片的故事构成,便会发现其情节内容层面存在诸多共性母题情节或情节序列。由此也使关于世俗温情的集中书写成为三种主要故事创作类型在叙事情感上的共性倾向。
1. 情节关键词
(1)恶性病毒
此类影片中灾难的爆发,其病毒源头要有充分的戏剧可能性,而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生理病毒或生活细菌,为了强调其爆发性和破坏力并形成震撼的戏剧情境,通常将病毒设定为“原始的”“远来的”“禁忌的”“失控的”等,依此架构叙事的开篇情节,如《极度恐慌》中“非洲雨林曾感染过瘟疫病毒的小白脸猴被带回国出售”、《流感》中“东南亚偷渡客隐藏在集装箱来到韩国”、《卡桑德拉大桥》中“警员为了对抗恐怖分子失误打碎鼠疫细菌实验品”、《传染病》中“美国女人在香港旅行期间吃了感染猪瘟病毒的饭菜而后返程”等。
(2)封闭的空间
在病毒蔓延的前期,人们嗅到灾难爆发的先兆“气味”时,通常会主动或被动采取一定的抵御性手段,形成封闭式空间的戏剧情境,为后续灾难的持续发酵和爆发奠定充分的危急氛围,并很快上升为一种关乎命运的危难“生存”境遇,如《极度恐慌》《流感》《感染列岛》都有“由于疾病传染性极高,政府紧急出动军队封锁城镇”的情节;《盲流感》中“所有致盲者都被关进一座废弃的精神病院,重兵把守,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防止疾病的扩散”;除了人为“封闭城镇”这一模式之外,封闭式空间的存在还有另一种模式,即事件发生的场景或背景就限定了空间的封闭性,如《釜山行》《卡桑德拉大桥》中“开往某地的列车上”等。
(3)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由于病毒灾难片在观影心理上具有奇观化的美学诉求,为了达到对抗病毒的戏剧效果和渲染英雄救世的精神感染力,“困境”几乎贯穿灾难爆发的始终,观众的注意力则投注在主人公如何在灾难面前取舍决择并挣脱各种束缚完成救世的最终目标,于是时间压力成为任务行动线叙事推进的关键因素,如《卡桑德拉大桥》中“军队对飞驰的列车实行不停站管控,张伯伦医生和其他人必须抢在列车到达卡桑德拉大桥前将无辜的旅客们救下”、《流感》中“当女儿被带走之后,生死不明,唯一的血清来源也断了线索,女医生金仁海几乎失去了一切与病毒对抗的可能,整个城市也随之陷入绝望”等,虽然在其他亚类型灾难片中也大量存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情节模式,但相较而言,病毒灾难片植根病毒抗争这一渐进式矛盾链条中,在叙事的有效性层面对于时间压力的强度要求更高,任务完成的情境危机感也更加强烈。
2. 温情的共性表达
灾难片注重在主题意蕴层面以悲悯怀世的温情动人,病毒灾难片也延承了这一精神内核,在叙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建构中重视人类三大感情母题的运用,亲情、友情与爱情往往交织出现在病毒蔓延和对抗的叙事进程中,世俗温情景观与病毒灾难奇观织就病毒灾难叙事的经纬纹理。与冷酷、危险的灾难情境形成对比的是人类情感世界里的温存和美好,双重美感的并驾齐驱使得整体叙事节奏鲜明、层次丰富,审美韵律质朴中不乏灵动。
血缘是在灾难降临时直接关乎社会秩序及生命延续的人伦关系,在影片《釜山行》中父亲与女儿的日常隔阂,既是“父女”踏上这次危险旅程的初始背景,也是影片在结尾部分主题升华的关键条件,关于“父爱”的传奇书写,让一个普通的父亲在灾难来临时不惜牺牲自我保护孩子,也让一个平凡的人变身一位救世英雄。影片借助“爱”的力量既呈现了人类与恶性灾难的英勇对决,也完成了对于永恒的“血缘”与“人性”的现实书写。在影片《感染列岛》中也有同样的亲情描写,三田护士不幸感染病毒导致遇难,她留给小女儿一条没来得及发出的短信留言,这样的细节使得悲壮叙事更平添了真实动人的人性光芒,“即使最后的结局可能并不如意,但他们永不放弃救援的过程,为了家人执着的心反而令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更为有血有肉”。[3]相较于亲情,爱情书写虽然在各种类型书写中更具有普适性,但其独特的审美意味使之往往具有天然的“情节吸引力”,因此,以灾难叙事作为叙事主线在故事中往往对其运用偏于谨慎保守,避免爱情情节的泛滥书写干扰观众对于叙事重心主次关系的判断,导致类型倾向含混,如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类型认知,观众则倾向于确定的爱情类型书写。影片《流感》以消防救援人员姜智久与漂亮的女医生金仁海的闹剧相遇作为故事开篇,而后两人情感关系的升温成为灾难对抗的节奏调剂时隐时现,最后两人的爱情关系在病毒对抗“合作”中到达顶点,爱情关系成为促成人物“合作”的助力剂,也成为冷峻基调的抗灾过程中的一抹亮色。这种关系的运用在《卡桑德拉大桥》中更为巧妙,主人公张伯伦医生与前妻在危难行进的列车中相遇,并联手对抗灾难,最终成为“伙伴”式爱人关系,虽然二人的爱情归宿在结尾处没有明确点出,但这种复杂的人物关系更能呈现出现代社会爱情关系的实质,即“磨难”与“爱情”相映成辉,不失为一份病毒灾难片爱情关系运用的有效经验。而友情书写在病毒灾难片中大量存在的叙事原理,不外乎抗击灾难的合作关系需求,因此“友情”更似一种人物关系必不可少的“调和剂”,象征着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性、团结性的生命存在,这也是战胜病毒灾难的力量源泉。
3. 病毒灾难书写的叙事倾向
病毒灾难作为灾难片创作中与日常生活审美距离较近的题材,常以直面的姿态将现实社会景观纳入叙事内容书写,秩序杂乱的城市街景、流离失所的难民、气氛压抑的政府指挥所、命悬一线的敌我对垒、逆行救世的英雄等都成为必不可少的类型影像标识。相对固定的类型元素,是保证叙事有效的重要基础,然而在病毒灾难片创作过程中为了避免情节同质化,通常在主题方向、力度和亚类型拓展层面进行有效创新,造成了病毒灾难书写截然不同的类型审美。
秉持现实主义姿态,以日常生活化的客观质朴美学观念“就地”解决灾难困境,并遵照戏剧矛盾的处理原则,将病毒灾难的爆发视为人类日常现实中的一次“生存预警”,这是叙事呈现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处理方法,其本质是借助生活经验进行内心焦虑和文明反思的典型化寓言书写,在主题旨向层面也倾向于反映现实社会的弊病及风险。如《卡桑德拉大桥》中人类对科学试验的驾驭与防控隐患,《流感》中的“偷渡”难民迁徙风险等国际问题,《传染病》中呼吁全球一体化、不同职能部门合作问题,以及国际联手抗击病毒扩散等合作意识等。另外,在灾难影像奇观化创作趋势影响下,病毒题材的书写更倾向于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进行科幻联想,并借此拓展其创意价值与叙事吸引力,实现现实影射与未来想象融合的美学共谋,因此太空宇宙、外星文明、基因变异、丧尸等科幻元素大量被植入灾难叙事逻辑链条,抗击病毒灾难的过程也带上了超现实色彩,不仅与前者创作模式形成显著区别,在观众心理感受层面也实现了类型交叠的审美沉浸,如《釜山行》《末日传奇》等。此类模式的有效创作运用,还需要提及一部具有自身特点的影片《天外来菌》(2008年),此片中病毒的爆发起因是一颗人造卫星的偶然坠落,卫星回收之后小镇上的人大批离奇死亡,随后病毒“仙女座菌株”大肆蔓延。发射这颗卫星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外星生物,岂料在遭遇虫洞之后发生坠落,总统为了阻止事态扩大决定向灾区发射核弹,却不幸加速了病毒蔓延,好在经过研究科学家们发现这种病毒存在天敌,是一种古老细菌,这种细菌藏身的海底却已被人类破坏殆尽,经过培养成功根除了“仙女座菌株”,这时军方高层产生了分歧,一个神秘团体暗中将一份“仙女座菌株”样本通过卫星保存在外太空,也就注定了人类在未来仍会受到此病毒如“达摩克利斯之剑”般的困扰或袭击,也许时间之环正是在此闭合。显而易见,其采用科幻哲思的创意进一步深化了病毒题材,无论叙事逻辑上是否存在被诟病的可能,都不失为未来病毒灾难片在此模式创作观念下的可行性经验。
人类文明的持续前行,离不开居安思危、“厝火积薪”的传统经验与智慧,病毒灾难片正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它以直面灾难、勇于反思的姿态准确诠释了与当代文明相伴而生的世俗生存焦虑,“噩梦”照见现实的寓言棒喝充分证明了其类型叙事美学的成熟,也预示了其必将在类型片发展史上留下独特的生存哲学影像化创作的美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