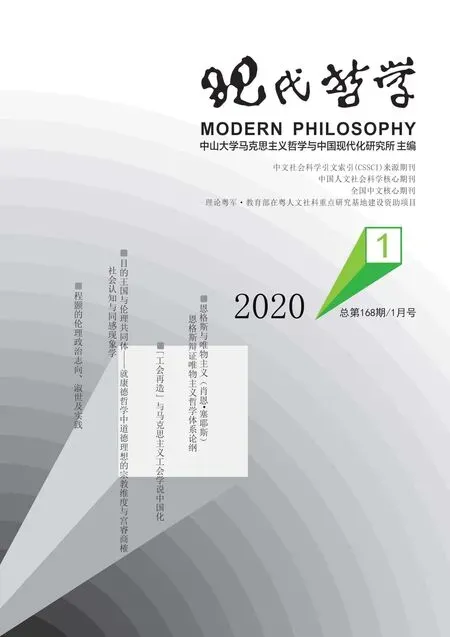双重立义、机械力与能力
——论胡塞尔实践世界的触觉基础
2020-12-06王继
王 继
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尤其是感知直观,一般会潜意识地将其等同于视觉直观。这是情理之中的,正如罗蒂所说,直观、表象这些传统形而上学的常用词暗含着视觉中心主义隐喻(1)视觉中心主义是罗蒂(Richard Rorty)等当代哲学家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注重表象性、在场性思维的标签化提法,德里达也提出光是形而上学传统的奠基性隐喻,国内学者高秉江专门就视觉中心主义与现象学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参见高秉江:《现象学视野下的视觉中心主义》,《哲学动态》2012年第7期。。但往往被忽略的事实是,在胡塞尔的诸多文献中,视觉与触觉经常是成对出现的,他同时提及视直观与触直观(Tastanschauung),而且认为触觉是元场(Urfeld),强调触感知相对于视感知的优先性,进而将触摸行为视作实践活动的基础。不过,胡塞尔的这些论述大多以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方式分布在其生前未出版的手稿中,这也是导致其触觉思想被忽视的一个原因。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讨论触觉与视觉及视觉中心主义的关系,只是借此引出现象学中常被忽视的触觉问题。首先,笔者将通过触觉的双重立义特征来探讨其元感觉场地位,并结合相关争议,给予其合理辩护,继而引申出其作为元实践场的意涵。然后,从元实践区域中对象和主体两方面的构成入手,深入分析触觉的实践优先性,一方面实在物原初构成的关键一环是因果关系或机械因果力的显现,另一方面实践体现了遵循动机关系的主体性能力。机械力代表自然,能力代表自由,它们为何都被称为力,这两类不同的力是如何原初显现的,这在胡塞尔的文献中是隐而不显的,尚未有学者对此做过探讨。笔者在本文将表明,基于触觉的双重立义是机械因果力与主体能力这两种力得以类比显现的基础。通过对触觉基础地位的系统性解释,同时期待能够打开一个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新视角。
一、从元感觉场到元实践场:触觉的优先性
胡塞尔对触觉的关注正如其纯粹意识现象学一样,并不是无端生出来的,而是受到近代经验论和同时代心理学家的影响,其中的典型代表有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卡茨(David Katz)。贝克莱认为,空间距离感依赖于触觉而非视觉,因为视觉不能超出自身而感受到一种外在的距离,通过触觉才能感受到外部的延展性和距离性(2)[英]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2—43页。。胡塞尔在空间物构成中对触觉的重视,可以说延续并深化了贝克莱的触觉观。卡茨是胡塞尔在哥廷根时期的学生和同事,曾参与过胡塞尔的课程和研讨班,其1907年的博士论文也受到胡塞尔的审阅和指导;他对视觉和触觉都做过专门研究并分别出版了专著,例如对手的各种触摸行为做具体分析,区分了触觉的主体性感受与客体性感受维度等;胡塞尔在对触觉的探讨中无疑与其有着相互的影响(3)关于卡茨与胡塞尔触觉观的关系介绍,参见Dermot Moran, “Between Vision and Touch: From Husserl to MerleaucPonty”, Carnal Hermeneutics, ed. by Richard Kearney&Brian Treanor,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14-234; Dermot Moran, “Husserl, Sartre and Merleau-Ponty on Embodiment, Touch and the ‘Double Sensation’”, Sartre on the Body, ed. by Katherine J. Morr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10, pp.41-66.。不过,胡塞尔的突破之处在于,在触觉问题上同样经过先验纯化,即通过现象学还原排除了对触觉的心理学和生理学预设。比如,贝克莱认为触觉是一种实在的心理状态,穆勒和卡茨将日常经验意义的身体视作不言而喻的前提。胡塞尔认为这些预设都是不可靠的,排除这些预设后,在纯粹意识中才可以清楚描述原初被给予的触觉现象。作为原初的感觉体验,胡塞尔把触觉抬升到本原的地位,将其视为感觉的感觉或元感觉。
关于胡塞尔的触觉思想,被提到最多的是他在《物与空间》中所举的左手触摸右手及《观念 Ⅱ》中自我触摸的例子,这个例子借由梅洛-庞蒂的发挥而广为人知。为了清楚分析胡塞尔的触觉观,在此引述这段出自“视觉领域和触觉领域间的区别”这一节的话:
因此这里(4)“这里”指触摸外物时。存在着双重立义 (Doppelauffassung):同样的触觉既被立义为‘外在’客体的标志,又被立义为身体-客体的感觉。而且在身体一部分同时成为身体另一部分的外在客体的情形下,我们拥有双重感觉(Doppelempfindungen)(每一部分有它自己的感觉)和双重立义,后者是作为物理客体的这一或另一身体部分的标志。(5)Edmund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Zweites Buch. Phä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 Band IV, Hrsg. Marly Biemel,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52, S.147.以下简称Hua4.本文涉及到该书的引文同时参考了中译本[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很明显胡塞尔在此提到两种情况:1.触摸外物时,有基于同一感觉的双重立义,即通过触觉分别立义了外部物理客体和身体客体;2.自我触摸时,既有双重立义,又有双重感觉,后者即触摸感和被触摸感。通过这个例子,胡塞尔首要想表明的是,与视觉等其他感觉类型相比,触觉更具有基础性和优越性。然而,梅洛-庞蒂重点发挥的是双重感觉,进而扩展说明触觉在双重感觉这点上并不具有优越性,视觉和听觉等其他感觉类型也具有双重感觉的特征,即所有感知行为都具有可逆性和交互性,或说自我同时是行为主体和行为客体,这是肉身之我在世之在的方式,“梅洛-庞蒂在其后期著作中给予了双重感觉以存在论意义”(6)Dermot Moran, “Between Vision and Touch:From Husserl to Merleau-Ponty”, pp.214-234.。
本文无意就胡塞尔与梅洛-庞蒂的触觉观进行具体比较,只是想同情地理解胡塞尔,并为其做一些合理辩护。胡塞尔的运思路径是,通过对不同感觉类型的抽象隔离,来凸显触觉的本质及其优越性。单就触觉而言,当触摸进行时,是能够形成双重立义的。根据意向行为的结构可知,感觉材料是意向立义的基础,通过触摸可以获得触摸感觉(Tastempfindung),如硬、冷等,它是双朝向的,即一方面通过这些触摸感觉能立义具有硬、冷等性状的物体,另一方面这种触摸感觉会被定位于(lokalisieren)某部位,如定位至触摸着的手。而具有感觉定位的部位被立义为感觉承载者,即感觉器官,所以手被立义为触觉器官。假如原初抛开触觉的参与,单就视觉来说,看是单朝向的,按胡塞尔的说法,在看时眼睛不能视觉性地显现(7)Hua4, S.147.,这不同于触摸中手所具有的触觉定位。也就是说,单纯通过看是不可能获得视觉在身体上的定位的,所以不可能将眼睛立义为视觉器官,从而不能说有了视觉。类似地,其他感觉类型如听觉、嗅觉等亦是如此。当然这只是抽象分离,实际上为什么会有视觉、听觉等感觉呢?这是由于触觉遍布全身,而其它感觉器官伸布于触觉性身体中,因此它们首先是被触觉所定位的,于是才能被立义为各种感觉器官。触觉“总体上是所有一般感觉(和显现)存在的前提,也包括视觉和听觉,后者在身体中并没有原初定位”(8)Hua4, S.151.。可以说,躯体(Körper)通过弥漫的触觉定位才被立义为有感觉的身体(Leib)(9)在胡塞尔那里,Körper指一般意义上的有形体或物体,Leib指有感觉的躯体即有生命物。本文遵从常用译法,将前者译为躯体,后者译为身体。,“身体只可能如此这样原初地构成自身,即在触觉中,和在一切凭借触感觉被定位者如温暖,寒冷,疼痛等等中构成自身”(10)Hua4, S.150.。所以,胡塞尔称触觉场为元感觉场(11)Edmund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Drittes Buch. Die Phänomenologische und Die Fundament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 Hrsg. Marly Biemel,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1, S.5.,它是所有其他类型感觉能成为感觉或被感觉到的基础,是身体之为身体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触摸中的双重立义而非双重触觉才是其基本特征。正如鲁汶胡塞尔档案馆研究员麦腾斯(Filip Mattens)指出的,胡塞尔认为触觉具有提供双重经验的特征,即提供了所触摸的客体和进行触摸的感知身体两种经验(12)Filip Mattens, “Perception, Body and the Sense of Touch: Phenomenology and Philosophy of Mind”, Husserl Stud, (2009)25, pp.97-120.。在双重立义的基础上,才可能在自我触摸时产生双重感觉:一方面,正是有了触觉的可定位性,才可能在自我触摸时既有触摸感又有被触摸感;另一方面,作为触摸感和被触摸感的双重感觉其实体现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的双重性,而主体和客体的分立意识恰恰是在原初触摸外物时所产生的,即通过触摸将外物立义为客体,将触摸行为的载体立义为主体。
但是,很多现象学家忽略了双重立义,和梅洛-庞蒂一样,将关注焦点放在双重感觉。比如,莫兰(Dermot Moran)在比较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触觉观时,将双重感觉视为胡塞尔触觉观的特征,并没有提及双重立义(13)Dermot Moran,“Between Vision and Touch:From Husserl to Merleau-Ponty”, pp.214-234.,这显然是有误的。而卡尔曼(Taylor Carman)更是站在梅洛-庞蒂立场,对胡塞尔所说身体的意向性立义依赖于触觉提出两点质疑:一是将触觉定位到我的身体部位预设了我的身体为前提,二是将身体作为感觉承载者这样的对象来认识,预设了一个超越于身体的先验自我;而梅洛-庞蒂的优势在于并不将身体视为认识对象,而是视为自我投身于世界的恒在视域(14)Taylor Carman, “The Body in Husserl and Merleau-Ponty”, Philophical Topics, Vol.27, No.2, 1999, pp.205-226.。
笔者认为,卡尔曼的批判代表了一种通行的误解,有必要对胡塞尔做辩护。针对第一点,胡塞尔显然没有预设一个身体,然后将触觉定位其上,相反,恰恰是通过原初的触觉体验,即通过触觉定位的伸布性及界限,如不能将触摸中的冷感定位于空中的飞鸟或任何其他外物,而只能定位于进行触摸的部位如手,这样才使对同一的、有感觉的身体的立义成为可能。针对第二点,胡塞尔确实强调先验自我的绝对性,但笔者认为,不进行构成的先验自我是现象学还原的起点,当基于原初体验进行意向性立义时,先验自我就具体化为具有感觉体验的单子自我,因为原初体验必然是以感觉为基础。当身体尚未成为主题时,它是隐匿的、非对象性的,在感觉体验中显然已经存在着,这一点胡塞尔并未否认。只不过,他所强调的是对身体的认识或身体概念是如何可能的,这就要回到原初的触觉体验。通过这种认识论的迂回,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身体,并在更高层次进入生存论和存在论(15)关于纯粹意识具身化问题,参见王继:《从隐匿到实显的身体——对胡塞尔纯粹意识具身化维度的一个理解》,《天府新论》2018年第3期。。
如果说元感觉场的提法只是从静态结构显示触觉的优越性,那么胡塞尔后期通过对生活世界的深入探讨,可以说将触觉场提升到元实践场的地位。在《生活世界》的手稿(胡塞尔全集第39卷)中,胡塞尔说物感知是元实践(Urpraxis),其他类实践如审美、价值行为都奠基于其上(16)Edmund Husserl,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Texte aus dem Nachlass(1916-1937), Band XXXIV, Hrsg. Rochus Sowa,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8, S.382-384. 以下简称Hua39。,这与《观念 Ⅰ》所说的物实在作为其他一切实在的基础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物的实在性(Realität)是奠基性的存在信仰,是主体的意向性实践所投射的、关于此世界的最基本的信仰样态。因此,实在性的世界意味着是以最源始(Ursprünglichst)的方式和感知的方式实践着的世界(17)Hua39, S.399.。这里,胡塞尔重申了触感知相比于视感知等其他类感知的优先性(18)Hua39, S.396-400.。既然感知是元实践,那么便可以顺利成章地说触觉场是元实践场。因为亲密性(Vertrautheit)是触觉性被给予的基本特征(19)[德]胡塞尔:《空间构造札记》,单斌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19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2期,第279页。,只有凭借亲密的接触行为,物才能切近前来与我构成一种实践性关联,“每一未被触及(getastet)的事物没有进一步‘到手(zuhanden)’”(20)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Zweiter Teil:1921-1928, Band XIV, Hrsg.Iso Kern.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3, S.554.。需要说明的是,实践相关于行动,而触感知本质上可以是静态的,比如对周围环境冷热的触觉或者被触摸等。这其中是否有矛盾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胡塞尔在《物与空间》所说的,动感(Kinästhese)是原初的,其原初形态是自我运动的感觉,比如姿势的随时调节(21)Edmund Husserl, Ding und Raum:Vorlesungen 1907, Band XV, Hrsg. Ulrich Claesges. Den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3, S.86-87; Edmund Husserl, Thing and Space: lectures of 1907, trans. by Richard Rojcewicz,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p.73-74.,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动是动的一个极限形态。所以,触觉原初是跟自我运动联系起来的,触感知的原初形态体现为进行摸索的触摸动感(Tastkinästhese),即通常所说的触摸行为。根据上述触觉的双重立义,并结合 Hua39“实践世界的触觉构成。触感知相对于视感知的优先性”这一节,触摸行为的实践优先性之体现可以概括为:通过触摸动感中所具有的张力(Kraftspannung)要素,一方面对象物获得不同于视觉侧显的原初自身展示,另一方面主体对世界的参与性也原初显现出来(22)Hua39, S.396-400.。这里,胡塞尔的描述比较简略,需要结合散见于其他手稿的相关论述,从对象和主体两极的原初显现入手,就触摸实践的优先性做具体阐发。这主要涉及两个互相关联的核心问题,一是对象侧机械力或因果关系的原初显现,二是主体侧能力意识的原初显现。
二、触觉中的阻力关系:对因果关系原初显现的补充性阐释
在元实践领域,就意向对象侧而言即实在的感知物。实在性是感知行为的存在设定,构成感知物的一个本质特征。在胡塞尔这里,物的构成可以分为两个彼此关联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空间幻相(Phantom),到了第二个层次,结合因果关系(Kausalität)才能真正构成实在物(23)关于这两个层次的划分,可参考《物与空间》一书的编者Ulrich Claesges在该书“编者导论”中的说法(Edmund Husserl, Thing and Space: lectures of 1907, pp.xxii-xxiii.)。。也就是说,因果关系与物的实在性或物的本质是直接相关的,因此,解决因果关系如何在原初体验中必然显现的问题,就等于解决了实在性问题。这既可以回应休谟的因果怀疑论,又可以反驳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认为因果关系是自在存在的自然法则,与人的实践无关。胡塞尔则相反,认为因果律是在主体行为的基础上才被构成的。然而,胡塞尔在《观念 Ⅱ》描述因果关系如何原初被给予时,并没有像在《物与空间》中解决空间幻相那样,严格回到原初体验进行详细阐述,这使得对因果关系的辩护还不够有力,也使后来现象学家们缺乏对其因果关系的关注和解释。仅就笔者目前所看到的资料来看,只有伯恩哈特·让(Bernhard Rang)在其《因果关系与动机》一书中对因果关系问题做过探讨,但他也主要是从因果性与动机化的关系角度来考察,并未将因果关系的显现与触摸体验联系起来(24)Bernhard Rang, Kausalität und Motivation. Untersuchungen zum Verhältnis von Perspektivität und Objektivität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Netherlands: Springer, 1973, S.233-243.。笔者认为,既然触摸实践具有优先性,那么触摸体验与因果关系的显现理应有内在关联,这在胡塞尔的手稿中也有零散线索可循。我们知道,自然因果关系又被称为机械(mechanical)关系, mechanical同时有“力”之意,于是因果关系就等于力的关系,所以牛顿将宇宙万物间的关系视为普遍的力的关系。接下来,本文就将着眼于力的原初显现,表明原初触摸行为中的阻力感构成普遍的机械力关系的体验基础,从而补足其对因果关系的辩护。
先看《观念 Ⅱ》对因果关系的描述。首先简单说下幻相。在原初体验中,幻相是指尚未达到物的实在性立义的单纯显像层次,比如颜色、广延的显现都可以无关乎其实存与否,而以幻相的方式原初被体验到(25)胡塞尔在这里是从实在性立义的可能性前提来界说幻相的。幻相不是指日常经验意义上所说的想象(Phantasie)或虚构(Fiktion),而是相对于高层阶实在来说的低层阶显现,也就是说,未能达到实在设定的前现象阶段是幻相层次。而想象或虚构已经立足于实在,是后者的当下化变样。,所以胡塞尔说“幻相是原初被给予的”(26)Hua4, S.37.。唯有和因果关系结合起来,实在物才得以构成。胡塞尔将因果性的原初显现状态描述为物与环境(Umstand)的依赖性(Abhängigkeit),或者直接说是因果依赖性(kausale Abhängigkeit)(27)Hua4, S.41-44.。在此,他提到两种情况来说明因果依赖性与实在性显现之间的内在关联:一种是颜色与光源的关系,即一物色彩的显现会随着周围光源的变化而协同地、有规则地变化,在这种规则地显现变化中,我们把握到贯穿其中的不变的光学性质,这就意味着凭借对该物与环境的依赖性关系的直观,我们对其实在特性有了把握;另一种是弹簧与冲击它的外物之间的关系,即在外物不同强度的冲击力(Anstoβ)下,弹簧会有相应地伸缩变化,通过这种规则性地伸缩变化,我们将其把握为具有某种恒定的弹性,这使弹簧的实在性得以显现。
表面上看,胡塞尔在这里对因果关系与实在性的证明是有力度的。我们还可以通过反例来辅证他的观点,比如,一幅画中的树木不会因图画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不能将它立义为一颗实在的树。事实上,胡塞尔只是从静态结构上描述了物与环境的依赖性关系,只是摆明了因果性与实在性有本质关联,尚未证明因果依赖性如何原初被给予,因此还无法回应休谟问题。这两个例子都可以依照休谟的思路进行质疑:其一,我们只是看到色彩显现的变化与光源的变化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却无法直观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二,为何能把对弹簧的牵拉说成是力的作用?我们并没看到力这种关系,只是看到外物牵拉与弹簧伸缩这两个事件。当然,胡塞尔承认这是就物质对象结构的描述。但在《观念 Ⅱ》第三章,他回到感知体验基础来分析物何以如此显现时(28)Hua4, S.55-90.,主要是讨论物的感知显现与其实在特性的内在关联,并没有对因果关系的感知前提给出明确解说,这是不符合明见性原则的。结合他对触觉的零散描述,笔者认为,只有将因果关系拉回到原初触觉体验中,才能使其获得明见性。
由于因果关系是基于两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将触觉在两物关系显现中的优势概括为内在关联的两个方面:1.两个事物间的区分源于触觉定位;2.触摸中的阻力感为一物推动另一物的因果力提供了前提。关于第一点,我们要说的是,两物间的区分源于自我与对象的区分,因为根据现象学原则,同一与差异意识必然基于原初体验,而最基本的乃是作为体验载体的自我的同一性,这包括自我的同一和其界限,而后者来源于触觉定位。正如上文所说,基于触觉的多重功能,我们才区分出没有触觉定位的外物、有触觉定位的我的身体、基于触觉体验的我的心灵,也就是说,分别意识是基于触觉体验才产生的。
关于第二点,因为基于触觉才分别出自我与对象,那么自然地,二者便以触觉为纽带显示了一种相互关系,一是进行感触者,一是被触知者。这种相互关系又可以区分出两个类型,一为力的关系,一为非力的关系。可以说,最原初的触觉体验是阻力体验,因为阻抗在自我体验中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如最直接的触觉是双脚与地面的接触感,这构成一种阻力(Widerstand)关系,正如胡塞尔所说,“我以我的‘重量’压着它”(29)[德]胡塞尔:《空间构造札记》,单斌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19辑,第280页。;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说动感是原初的,这在触摸行为中直接体现为由接触产生的阻力感,比如胡塞尔在《观念 Ⅱ》中用张力感(Spannungsempfindung)、压力感(Druckempfindung)来描述触觉的原初定位(30)Hua4, S.151.,在 Hua39中说触摸可以通过张力而成为按压(Drücken)、碰撞(Stoβen)、推移(Schieben)等,从而使外物获得主观性显现(31)Hua39, S.399.,比如获得硬度、弹性等各种实在特性的显现,这又进一步证明了自我与对象的区分和关联来源于触觉。
触觉中除了力的关系,还有非力的关系,如皮肤从周围环境中获得暖感。表面看,这种触觉不构成自我与环境之间力的关系,甚至热源可能离我有一段距离,但这仍然构成一种亲密的接触关系,比如可以说环境包裹着我。而且,由于触觉中的阻力体验是普遍的和最原初的,在此基础上才能区分我与外物(环境),所以本文认为,皮肤与环境的关系构成对力的类比统觉(analogische Apperzeption)。类比统觉在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中起着基础作用,它不是指经验的类比推论,而是对经验类比、类概念的起源学回溯,即起初某些类似要素得以被体验为类似物的原初统觉,其中某个在先的类似要素被称为原始促创物(Urstiftung),是触发类比的原初因素(32)[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德]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这里触觉中的力构成原始促创要素,它触发类比统觉,使皮肤与环境的关系能够被统觉为一种力的关系。
触觉中力与非力的关系可以进行类比统觉,这种类比统觉是否可以推及到外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答案是肯定的。物与物之间的区分和关联源于触觉体验,当我们用“接触”“挤压”“碰撞”等词语来形容两物间的作用力时,显然也是基于触摸力的类比运用。一方面,外物间的碰撞和推动等力的因果关系是对直接触摸力的类比运用,比如胡塞尔所举的外物冲击弹簧的例子,冲击显然是一种力的关系,唯有在触摸中把握了一种自我与对象间的冲击感,才可能将两物间的关系立义为冲击力。另一方面,外物间非力的因果关系是基于触觉中非力关系的类比,比如对光源与色彩显现之间因果关系的把握,是源于如环境与皮肤间有亲密的触觉关系。同时,正如触觉中非力的关系可以被类比统觉为力的关系,外物间非力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被类比统觉为力的因果关系。
进一步,触摸行为中自我与对象之间力的关系,可以比照胡塞尔所说的间接运动,即由他物所推动,而非自发运动(33)Hua4, S.152.,这恰好是“机械的或力的”(mechanical)一词的本意,所以说触摸中的力为机械力的显现提供了基础。当我们说自然因果关系是机械因果关系时,其实就是将因果关系看作机械力的关系。这样,就将万有引力这一自然定律拉回到原初的触觉基础上,而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认为引力是自在存在的,与人的体验无关,从而构成对自然主义态度的颠倒。经由对自然主义的批判而回到原初体验,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使命。同时,回到触觉体验的本质,摆明对力进行类比统觉的触觉基础,就证明了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因此,胡塞尔把主体的实践视为投入普遍因果世界中的实践,并认为对周围物的实践作用拥有因果序列(34)Hua39, S.397.,从而构成对休谟因果怀疑论的一种回应。因果关系虽然是物与物之间的普遍关系,但它恰好构成物的本质,通过因果关系,物的实在性质才得以显现。将因果关系拉回到触觉的阻力体验中来解释实在物的构成,可以更好理解胡塞尔所说的触摸中有物的真正的自身展示(eigentliche Selbstdarstellung)(35)Hua39, S.399.。正如段义孚所言:“触觉是对阻力的直接经验,它告诉我们世界是一个压力和抗拒组成的系统,也让我们能够认清独立于我们想象的现实存在。”(36)[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9页。
三、从机械力到能力:类比统觉的触觉基础
在原初的触摸行为中,不只有自我与对象间机械力的显现,还显示了主体进行触摸的能力。机械力与能力,这是可以类比却又完全异质的两种力,一个代表自然因果律,一个代表自由因果律或动机化因果律,但都用了“力”(Kraft)及相关词语来表示,这是令人诧异的,目前尚未得到反思性关注。笔者认为,当我们回到触觉的双重立义进行解释时,这两种力的类比统觉便会获得明见性。
关于机械力与能力的类比,大致可以从对象和主体两个视角来审视。首先,从侧重对象视角来说,可称为从机械力到能力的类比。解释了触摸中的机械力,对能力的说明就容易了。在触摸行为中把感受到的阻挡称为力时,一方面如揭示了自我与对象间的因果关系,即两物之间的机械关系,另一方面触摸行为本身使主体产生能自发行动的意识,即通过触觉定位意识到身体是我的身体,我能够控制它,由自身发出一种触摸运动,因而胡塞尔在《观念 Ⅱ》中紧接着触觉优先性这一节提出来主体自由运动的权能(Vermögen,不能是能的一种变形),以区别于由他物所推动的机械运动(37)Hua4, S.151-152.。自我通过触摸行为所产生的“能”意味着能引发机械力,也能感受到阻抗并能越过或推开阻抗之物,这就使凭借触摸中的力要素而将能引发力者类比统觉为“能力”得以可能。由于主体的能力以意向性的方式原初展现在各种动感实践中,所以胡塞尔把意向性的朝向与充实视为力的紧张(angespannt)与放松(entspannt),相应地将动感的静止与活动表述为在零位的松弛与行动中的紧张(38)See Hua39, S.397-398.。
其次,从侧重主体视角而言,可称为从能力到机械力的类比。上文从触摸中力的显现角度解释了因果关系为什么是力的关系,这里则要对“因为-所以”(weil-so)何以显现进行分析,这就要将因果关系纳入动机化关系来考察,并通过触觉来解释动机行为的原初引发。从静态的原初体验角度来说,出自主体主动性的因与显现的果构成“因为-所以”的立义前提,比如因为我击打玻璃、所以玻璃碎了。我与外物间通过接触性触摸行为所产生的这种因果关系是亲身体验到的,而外物间的关系没有直接的亲身体验基础,故此,只有在触摸性接触体验的前提下,才能将直观到的外物间的接触与运动类比统觉为因果性的。不过,胡塞尔对这种主体性的“因为-所以”行为赋予一个新的关系术语,即“如果-那么”(wenn-so)的动机化因果关系(motivierte Kausalität)。如上所说,原初的触摸行为体现了主体的能力,这就意味着我能够这样或那样,这是与自我的动机相关的,而不只是机械地受外物所推动。
同时,胡塞尔将动机化关系视为一种新型的刺激关系,它不同于生理学预设的刺激-反应关系,而是主体与周围世界之间的意向性关系(39)Hua4, S.189.。也就是说,这种刺激是意识性的,是由意识对象给意识主体所施加的触发力( affective Kraft),该触发力将主体的注意牵引到该对象上从而构成意向性关系,“我们在触发(Affektion)的标题下理解意识上的刺激(Reiz),理解一个被意识到的对象对自我施加的特有的拉力(Zug)”(40)[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年讲座稿和研究稿》,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80页。。继续回溯,这种刺激的触发又基于触觉上的可刺激性(Reizbarkeit)。正是由于触觉的可引发性,才使身体作为感觉器官得以可能,以至于胡塞尔说可刺激性成了身体区别于躯体的本质特征(41)Hua4, S.157.。进一步,基于触觉的触发,自我才成为具身化的主体,身体才能作为身体持续地以意向性方式行为着,从而构成持续的动机引发系统,或称为动感的动机引发(kinästhetische Motivation)(42)Hua4, S.150.。不过,并不是任何事物都能触发主体的意向性朝向,意向动机遵循着一定的法则,胡塞尔将动机引发法则视为理性的基本原则,动机引发法则简单说就是意向活动作为持续积淀的关联域而期待和要求着类似的、新的体验的实现,这种动机倾向的强弱又被他称为动机化力量(Kraft)(43)[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 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34页。。动机力与触发力分别从主体侧和对象侧刻画了二者之间的意向性-趋向力的关系,它们是一体两面的,共同引导着身体实践的生成。总之,在触摸行为中既产生阻抗感,又产生时间性的动机引发系统,这就为自然因果关系几个要素的显现提供了前提:机械力、时间上的先后次序,以及因为-所以关系。
无论从机械力到能力的类比,还是从能力到机械力的类比,结合触觉的双重立义来看,其实都应归于原初的意向体验,即从原初触觉体验中才把握到对象与主体两极,以及机械力与能力这两种力。正如胡塞尔所说,通过触摸行为,不仅物获得了不同于视觉侧显的原初自身展示,而且主体对世界的参与性、实践性也得以显现(44)Hua39, S.399.。如果说机械力代表的是自然,能力代表的是自由,那么正是通过触觉才使自然和自由一起显现出来。反之,自然和自由恰好构成实践的两个维度:一方面,实践必然是在世界中的实践,要遵从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实践是主体的自主性行为,体现了主体的自由。同时,基于触觉的实践本身体现了自我的能力,对自然物的立义则是实践的低阶区域,因而通过触觉体验展现了动机化因果律相对于机械因果律、自由相对于自然的优先性。
本文从触觉的双重立义入手,为胡塞尔触觉思想做一个基本定位,并由此在元实践场中引出机械力与能力及二者进行类比统觉的触觉基础,并系统性阐发了触觉置于实践的自然和自由两个维度的原初显现。胡塞尔触觉思想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甚至可以说潜在地引导了哲学的现代转型。比如,梅洛-庞蒂从胡塞尔的双重触觉思想引申出自我与世界的可逆性,从而打破传统形而上学注重视觉表象的主客二分性;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伊丽格蕾(Luce Irigaray)在借鉴梅洛-庞蒂等人触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用视觉隐喻来表示男性同一性文化,用触觉来代表女性性征,从而引向性别差异共生的伦理学。这样一条基于触觉思想的发展线索是非常有意义和值得挖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