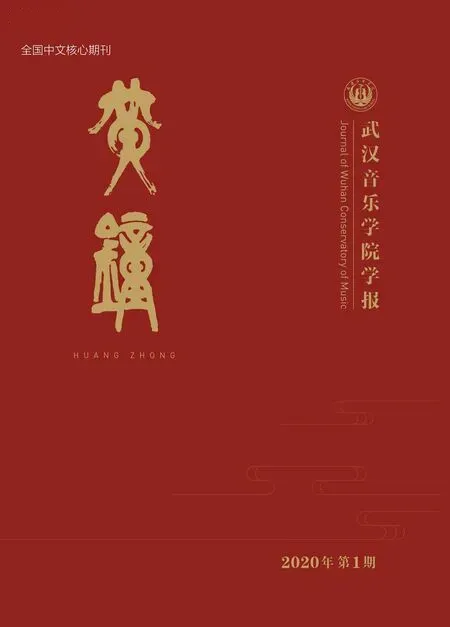《为易变提出的恰切卜题》译后记
2020-12-06周勤如
周勤如
在一次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80年之后的世界音乐创作》研讨课上,笔者以包括约翰·凯奇的最后一部作品《25》(Two5,1991)在内的实验乐派新近作品为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课后,部分研究生希望我推荐一篇论文给他们假期翻译,之后由我审校修订成为这篇译文。
或问:凯奇1992年就去世了,此人大家都知道,旧话重提是否有必要?我认为:“有。”因为第一,温故而知新。这也是原作者的意思。安吉拉·杨在原文副标题中特意用了“revisited”(重访,引申为“重温”),并且在文章的最后点明是对“一些盖棺论定的思考”的“进一步澄清”,可见她对当时有关凯奇的“热议”是另有所思的。第二,凯奇和他的追随者推崇的一些极端的实验性做法遭人诟病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与《易经》结缘的来龙去脉以及他潜心磨砺从自然永恒变化中把握机遇来临的“一瞬间”的信念和“无我(遵从自然法则与自我约束)”与“我在(以提出恰切问题控制偶然机遇的合理进程)”的哲理思考却并非人人皆知。这也是原作者反复强调的意思。像凯奇这样的“先知”,其行为往往具有复杂性,所以不能轻下非黑即白的结论。我们翻译这篇论文,并非看重凯奇的作品和技法,而是对从1736年传入西方的《易经》如何先在小范围的汉学圈中发酵,最后由凯奇扇动的偶然音乐的翅膀引起大面积的“蝴蝶效应”感兴趣。第三,显而易见,至少从主观上来说,凯奇的心离中国很近,很虔诚。然而,我们对凯奇的认识足够吗?我看不是。我所浏览的国内音乐文论、所听名家讲演和在不同场合所接触的学生给我的印象大多是谈论《4’33”》及重复一些“定论”,其他所及甚少。然而,如果接受凯奇的启示,将东方哲学化为新理论,引领像他所理想的“向未来包含所有声音的音乐”的“当代过渡”,这难道不是一个具有前沿性的课题吗?这种以东方哲学为内核的研究难道不是我们的长项吗?这种非我莫属的“机遇”我们难道不应该去主动攫取吗?所以,话题不在“新”“旧”,在“心有灵犀”之中。
谨记。
2019年5月10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