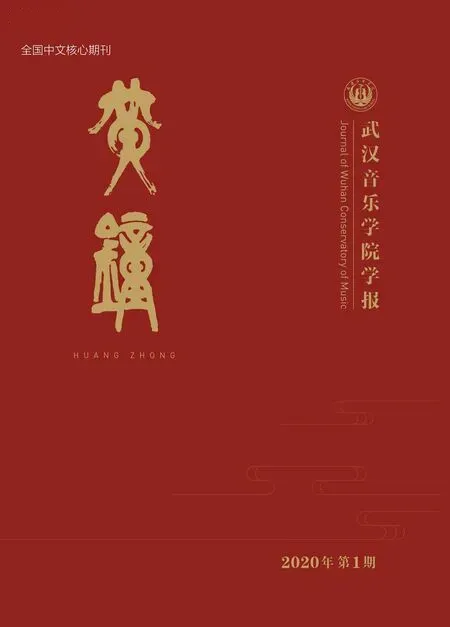近代中国音乐史加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学术意义
2020-12-06夏滟洲
夏滟洲
历史学层面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内容包罗万象,领域十分宽泛。日常生活史既是具体的历史存在,又是综合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理论范畴。从理论上,日常生活史研究具体的人与社会生活方式、人的实践行为及其观念的历史。内容涉及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个方面。前者是与日常物质文化相关的各种日常实践行为;后者是与大众日常实践形为相关的观念活动,这种观念活动既受大众内在的精神文化需求驱动,又与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有关,作用并反作用于外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可见,由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绘就的日常生活,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发生、发展的接触点。事实上,历史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绘就的,人的求知欲促使我们想了解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及与之相关的情境,日常生活史研究无疑可以完美建构起丰满、均衡的中国近代音乐解释体系。
从发展眼光来看,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理论探讨对象之一面,一是学科自身建设的需要,二是可以引领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研究注重以问题意识整合不同类型的史料,进而加强对史料与音乐本体之外的历史语境的想象与理解。下文拟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讨论开展日常生活史研究之对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研究拓展的积极意义。
一、近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音乐与研究
作为人类发明的一种智性形式,音乐史是一门在历史的框架内研究和理解人类所创造的音乐作品,以帮助我们发展和理解当下的音乐艺术。它既包括揭示隐含在音乐作品本身之中的历史,又包括从音乐作品的内在建构中读解到作品的历史性质,还包括依据那些传世的音乐作品的作者、创造过程及与之相关的情境的探索。事实上,检索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界的研究,不难发现学界聚焦于中国社会音乐文化思潮的变动,及大量的音乐本体研究等方面,甚或在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的理论方法总结性研究,都取得了丰富、富有创建的成果。现如今,笔者提出把日常生活史当做一个理论探讨的视角和领域,原因在于音乐史一方面与其他学科的交融趋势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是以音乐为出发点而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要求使然。当音乐的形式结构和风格、材料运用与音乐欣赏自洽,音乐文化的时代精神得以完成建构。然而,音乐史作为我们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必要形式,我们要尽可能宽阔地从人类活动背景中去探索和理解音乐家的创造。可见,基于日常生活的音乐史研究,在深化中国社会音乐文化思潮的变动,和大量音乐本体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解释音乐作品与世界和社会的关系,从而更为全面地展现音乐之为人类精神持续进化的历史面貌。
音乐的客观存在,始终与其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环境融为一体。常态下的音乐文化即我们所称谓的传统音乐,特别是与特定民俗、礼仪和之间联系密切的传统音乐,长久生存于小农经济社会秩序之中,在漫长的发展中凝结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稳态属性,在近代音乐发展中,发挥了音乐基本结构的均衡性,丰富了大众日常生活,反映了社会与时代共同的文化特征和习惯作用。针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学者们深入田野,进行社会调查,采用民族音乐学通常的研究方法,从本体分析到乐种形态描述,再到民族志、风俗志描述,一批批成果如陕北民俗音乐研究、河北固安屈家营音乐会研究、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等,将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属性、音乐的社会功能及其在特定社会风俗或特定意识中的功用做出具体研究。
更多历史学视野下的研究,揭示出任何社会的音乐都是奏鸣于时代之弦上的。面对近代中国日常生活,音乐史学研究者紧紧抓住历时演化的基本现实,从历时的角度将纷繁的史实梳理出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和问题。同时,诸学者务尽其力遍访史料,考证错舛,于琐碎难寻的第一手资料中辑录出版了大量的音乐家全集、作品集、音乐文论、文集等,既为研究近现代音乐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又深化拓展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研究维度。基于历史学层面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这些成果标识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中音乐史学本体意识的确立,以及在具体研究路径、观察视角上反映出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与差异等研究特征,影响要大于所收获的研究成果。造成这一局面的出现,原因在于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对研究者的束缚。换言之,面对我们身边的音乐生活,究竟应该抱持一种什么样的立场重构“让史料说话”的客观主义治史传统?
将音乐纳入意识形态领域,也是近代中国日常生活研究中的一部分。音乐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存在和发展不仅深受社会物质生产的现实影响,还要受到政治、法律以及宗教等常态活动的影响。近代中国在历时上经历着传统向现代的逐渐转化,共时上经历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和反压迫、国内多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文化斗争,刺激新兴音乐文化发展,涌现出各种思潮。继20世纪上半叶发生诸种论争和多元思考以来,学界收获了相当成果,如张静蔚①张静蔚:《近代中国音乐思潮》,《音乐研究》1985年第4期,第77-92页。、冯长春②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余峰③余峰:《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等的研究,将中国近代有关音乐思潮史实加以梳理,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阐述了音乐文化的时代精神,平衡了音乐研究中的哲学维度,筑起了音乐研究的理论之基。
以往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除了上述三个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把日常音乐生活视为一个观察点,认为日常生活是人们为维系自身存续和再生产,在一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中一切常态活动的总和,从而在研究中以一幅幅特写式的画面展现丰富的近代中国音乐生活,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音乐家的创造和人们精神生活的表现形式之一,又是人们娱乐交往和影响自身精神世界的介质。学界部分地采用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路径,或以人物为主线,以点带面描述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如孙继南的黎锦晖研究④孙继南:《黎锦晖评传》,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版;《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或站在当时日常音乐活动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指出诸如早期西方音乐传入中国时,虽然是西人娱己的日常行为,但也潜在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宫宏宇的系列研究⑤宫宏宇的系列研究文论:《“贝多芬”在上海(1861-1880)》,《中国音乐学》2016年第1期,第36-43页;《晚清上海租界外侨音乐活动述略(1843-1911)》(之一、之二),连载于《音乐艺术》2015年第2期,第19-29页与2016年第1期,第87-101页;《晚清海关洋员与国际博览会上的中国音乐——以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3-19页,等等。;或针对一些留学国外音乐家、在华外籍音乐家的活动展开研究,有社会历史背景,也有音乐家的工作行为、人际交往等日常生活,如韩国鐄的研究⑥韩国鐄:《留美三乐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实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韩国鐄音乐文集》(一~四),台北:台湾乐韵出版社1990年版(一)、1995年版(二)、1992年版(三—四);《自西徂东》(二辑),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一)、1984年版(二),等等。,“使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步伐得到提高。同时也纠正了一些因为粗略研究而形成的错误结论”⑦刘湜湜:《从<留美三乐人>看韩国鐄的史学研究》,《交响》2010年第3期,第107-112页。。特别是洛秦⑧洛秦的有关研究文论:《音乐1927年叙事——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诞生中的中国历史、社会及其人》,《音乐艺术》2013年第1期,第6-28页;《论上海“飞地”音乐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空间》(上、下),连载于《音乐艺术》2016年第1期,第68-86页和2016年第2期,第44-61页,等等。的有关研究及其基于“地方性知识”的区域音乐文化论域——“音乐上海学”,与熊月之主持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⑨如葛涛:《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马军:《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系列研究殊途同归,以人类学所强调的研究中“他者”的立场,关注上海城市社会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拓展了近代中国音乐生活的解释空间,更新了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研究旨趣。
二、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三个关联层次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音乐学家郭乃安就发出呼吁“音乐学研究应该关注人”。郭先生在其《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一文中指出,“音乐,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创造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乐的意义、价值皆取决于人。”还说,“在音乐本身与外部诸条件的交互关系中有一个中心的接触点,那就是人。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⑩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第16页。个中道理,世间日常音乐生活是人的创造、人的需求,无论哪一方面都离不开人的因素和人的推动;而对日常音乐生活的研究,亦是在通过关注平凡之人重复的日常音乐生活的研究,来寻找历史的动力和意义,开拓新的内涵和研究空间。到2012年,史学界始见这一看法,如常建华认为,“社会生活史就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联接社会各部分的历史。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该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生活史立足于民众的日常活动,从生活方式上把握民众,民众生活镶嵌于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岁时节日、生命周期、聚落形态中才能体现出来,并揭示民众生活与政权的关系以及历史变动带来的影响。”⑪常建华:《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历史教学(高校版)》2012年第1期,第7页。
艺术基本原理告诉我们,音乐生活的构成包括社会、音乐家、作品和受众几个环节,活动随人类日常娱乐、仪式、礼俗等实践活动过程中的需要存在和发展,其发生经历着流动与互联反馈的动态性活动过程。对日常音乐生活的研究如前所述,我们可采取历史学、或社会学、或人类学、或民族志风俗志的描述以及跨界学科等方法,针对不同研究对象分析其具体的、日常的现象,通过这种分析找寻日常生活与历史特征的契合点。联结各个条件的中心接触点即“人”。因为,音乐生活的主体(音乐家和受众环节)是人,音乐的物化载体(作品环节)也是人的创造,社会更是主体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态环境,正是在那里,人们日复一日重复着听赏音乐、使用音乐的各种活动,于是,在一个历史的框架里,基于主体的活动我们有了考察音乐日常生活的触角,凭借日常生活史我们有了理解人类历史的必要形式。毕竟,一部音乐作品的存在,并非意味着音乐史的存在,对其的研究,亦不能完全立足于音乐本身。
从理论上说,以“人”为中心,运用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和领域可以在三个关联层次中得到确立:
其一,加强日常生活史研究与历史变动的关联。历史研究,就是探索、理解人类过去所发生的,或想象中发生过的特殊事情的因果关系。历史存在的形态有两种,一种是常态的、在一定时间内历史事情基本处于不变的状态,一种是动态的、在相对时间内历史事情发生变化的状态,即非常态的。非常态的历史事情就是历史变动。历史变动还表现在,受政权分治、更替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动,在不同时空中的发展有差异,影响文化、民族、语言、风俗、思想、宗教等方面虽然会有实质上的不同,但却有着恒常的内在联系。日常生活史恰好注重把握历史事情的内在联系,通过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的观念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上去理解、把握各种特殊事情的意义,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历史融为一体。其现实意义则是通过日常音乐生活史的研究认识过去时代的物质文化变迁,通过对前人音乐生活的观照来认识当下。
其二,加强日常生活史研究与音乐学研究中叙事与分析的关联。叙事与分析是历史撰述的基本方法和要求。历史是被记录下来的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历史本身并不会叙事,我们对过去所发生的,或想象中发生过的特殊事情的因果关系的探索、理解,就是历史叙事。叙事强调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并在梳理和提炼文献的基础上叙述历史、还原历史。日常生活史强调自下而上地观察历史,理解的历史生活实景,仅靠单一的材料远远不够。除文献载籍、图像遗物外,还需搜罗区域社会调查资料、民间文献、地方志及分志(风俗志)、民间日记、艺人抄本、口述史、乐器实物、乐谱类、音像类、报刊、宣传海报、节目单等与人类音乐活动有关的各种资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综合运用和综合性分析与叙事,以走进历史主体,揭示社会生活的表象及其与主体经验的内在联系,还原音乐生活世界的特征。从这一关联层次上,日常生活史研究可谓拓展了史料的范围。
其三,加强日常音乐生活史研究与跨学科的关联。音乐作为一个独立自在的世界,依据其自身的逻辑与存在方式呈现特点,同时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音乐还要受到其赖以生存的整体文化环境的限制。音乐史研究既是对具体的音乐作品所作学术研究,如具体作品形式与风格分析和材料研究,又是以音乐为出发点,运用相关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化史理论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前者为所谓“内部音乐史”,即关注音乐理论自身合理性发展与自洽性建构的历史,一般指欣赏、形式风格分析和材料研究,它对音乐的内部理路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后者为“外部音乐史”,也就是把音乐放在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和心理因素层面加以考察的历史,它对音乐的发展起着影响作用,好似音乐艺术的外部土壤一样。⑫提出历史研究“内部史”(in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与“外部史”(ex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解释模式的,来自英国哲学家T.S.Kuhn为《国际科学史百科全书》撰写“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词条时所区分的概念(T.S.Kuhn: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D.L.Sills(ed.),New York: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1968,2nd.1979,Vol.14,pp.75-83)。我国历史学家葛兆光提出中国思想史的理论解释范式即内部理路与外部土壤的关系问题,大意与之相同(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一段时间以来,这一范式为史学界所采用。事实上,在音乐史研究中,这种区分是十分机械的,它无助于对个体音乐家的理解。而日常音乐生活史研究并非完全以日常音乐生活为背景的研究,其研究范围相当宽阔,并不局限于风俗史、民族志的路数。日常生活史研究有细腻的视角,但材料却又十分重要,不仅有明确的史学学科边界,还有相对集中的研究主旨。因此,我们倡导实践日常音乐生活跨学科研究,不仅可以从外部促进音乐学研究中的社会学、符号学、经济学、心理学的诞生,而且可以从学科内部深化且加强哲学、历史学的研究。⑬夏滟洲:《音乐学研究中的“跨界”认识》,《音乐研究》2014年第2期,第17-21、81页。还有助于揭示音乐作品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打破机械的“内部音乐史”和“外部音乐史”的阐释立场。
三、以“人”为中心走进近代中国日常音乐生活
举二例说明以“人”为中心走进近代中国日常音乐生活的学术意义。
(一)有关近代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生活日常
中国社会在近代的转变,源自欧洲的音乐文化表现形式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新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深远影响。受变法维新思潮影响,国内开始设立新式学堂,学校音乐教育逐步兴起。一时间,办新学,唱乐歌,国内主要城市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中小学音乐教育有了明显的发展和进步,成为20世纪初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反观既往近代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研究,论域广、成果丰,从多个层面将近代中国音乐教育因袭过程中出现的诸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这些研究着眼于大视野、大结构、大过程和大比较,偏重于上层研究力图从整体上说明近代音乐教育的客观存在,解释其发展规律,具有“社会科学化”特征。
学科的分化使我们的研究更富意义。源头上,无论历史学家的任务还是教育的功能,本来目的都是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提高人们认识水平,以史育人。因此,从民族志到音乐人类学,其学术理路旨在开启音乐史运用“平视”历史的视角来叙事,于是,历史人物、历史事情取代了人类学的“初民”与“文化事象”“社会行为”,解释空间骤然扩大。而音乐社会学的引入,以音乐为媒介,运用相互性视角综合观察人和社会的关系,既要注意到人和社会的显性关系,又要发掘二者的隐形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那种坚持系统整体论、合力论以求大求全的追求倾向。⑭夏滟洲:《音乐社会学学科规训及操作机制新论》,《音乐艺术》2005年第3期,第120-128页。在具体的历史及情境中,人们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首先是源于生活的需要,继而在特定的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发展并服务于人们的生活。从人类学到社会学,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无疑是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及研究进度的更新。
从日常音乐生活史与音乐教育研究的关联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理路上的更新。在近代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研究领域,诸多文献为之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支撑,除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⑮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等之外,像俞玉滋、张援的《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1840-1949)》⑯俞玉滋、张援编选:《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1840-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孙继南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⑰孙继南编著:《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和张援、章咸的《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⑱张援、章咸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是关涉音乐教育的参考文献。这几种文献不仅提供了大量反映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及先辈们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教训,还为我们勾勒出了20世纪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基本面貌,也是当今音乐教育工作者了解自身所从事专业的历史及近代中国音乐教育生活的主要来源。其实用价值毋庸置疑,已然是众多研究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论题的必备读物。大量相关研究,据之以长时段、大跨度的宏观视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观察近代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律,并无不妥。但是,存在于那种大结构、大过程之中的历史研究,缺少对“人”的关注,以及发生在具体的“人”身边的一些鲜活的材料,即便有具体个案研究,仍是理论总结居多,生动不够。
对于近代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活动的研究,理应有多样鲜活生动的叙事。近代中国继新学堂的音乐教育之后,各地开办的学校音乐教育,具体情况有深有浅,执行国民政府颁行的“壬戌学制”也有差异,且在加强音乐知识传输,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轻松地掌握知识、创造愉快教学环境诸方面,有着一致观念。各地注重音乐(美育)教育既是生活的日常,也是日常生活的必须,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不同。基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既可以看到各地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水平,又能通过总结当时日常教育的经验以给今天以启发。如1923年夏天老舍应邀在京师第一中学任教时,“舒老师不仅在音乐课中把昆曲当作教材,而且在国文课上也唱过戏,这使学生们大为惊讶。有一次他讲解诸葛亮的《出师表》,大讲《失街亭》里的诸葛亮,……便学着当时红极一时的名演员谭鑫培的念白‘悔不听先帝之言,错用马谡,乃亮之罪也’。他告诫学生们说:‘以后听戏,不要只听那些味儿,要看有益身心的感人之处,诸葛亮就知错认过嘛。’……还有一次,讲解骆宾王的文章,突然唱起了昆曲《弹词》,只见他一板一眼打着拍子,一本正经地唱下去”⑲王晋堂主编:《古校迈向21世纪——北京一中校史稿》,北京:华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老舍在讲授国文、音乐与修身课程时,运用京剧、昆曲等传统音乐丰富课堂教学的记载,还原了民国中学学习生活和音乐教育生活的图景。再看沪江大学附中的学生生活,“什么我最近学会了一种舞呀;啊,兴奋极了,大家表演起来。‘喳……喳……,美丽的摩登舞!’‘ⅠfⅠhad a talking picture of you’,‘Ⅰlove you!’呀,震人心弦的洋歌!‘借灯光,暗里里……’呀,苍凉圆滑的京调!”⑳周怒安:《一学期》,载《中学生文艺》(年刊)1931年第1期,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类似学生们课余的娱乐生活记载,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上海社会流行的摩登歌曲与传统音乐形式及民众的音乐欣赏观念。同时期音乐社团的蓬勃发展也深深地影响到了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为追求身心平衡、和谐发展,民国中学生主动选择文化发展道路,砥砺学识,纷纷组建社团、成立乐队,培育才能,一时成为风气,强化了音乐教育的实践能力培养,延伸扩展了课堂知识学习,间接地为社会培养后备音乐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在1920年后的广东,“广东华侨……还捐钱购买了许多管乐器,送回广东的学校,建立管乐团。象台山、中山、梅县、新会这些华侨较多的县份,中学、师范都建立了乐队。……这些乐队多则八、九十人,少则三、二十人。”㉑李凌:《二十年代后期广东大、中学生的音乐生活》,载于李凌:《音乐杂谈》第三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182页。根据《冼星海全集》所载图像资料,我们可知1924年冼星海就在其就读的岭南中学参加乐队,担任单簧管演奏。㉒《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冼星海全集》第七卷,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前置插页第4页。1933年南京金陵中学存在的23个业余学生社团中,即有“国乐研究会、西乐研究会、话剧社、平剧社、国术研究会”㉓南京市金陵中学编:《南京市金陵中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北师大附中的国剧社成员还集资购买乐器,“每星期六下午一大堆响器如单皮、铙钹、小锣、大锣、堂鼓、胡琴、二胡、月琴都带到学校里来。为了使国剧社正规化,聘请了罗小宝的堂弟担任教师。……使我们很快达到彩唱的程度。像《法门寺》、《二进宫》、《武家坡》、《坐宫》等罗先生也一一给予排练,使大家对京剧增加了兴趣。”㉔北师大附中编:《北师大附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这些中小学课余音乐社团的学习及演艺(剧)活动,是校园文化的有机构成,也是对学校音乐课程的有益补充。
这里略举几则材料,试图说明音乐史研究中采用日常生活史方法来叙述民国中学生的音乐生活,抑或说明课堂教学之外文娱活动的开展。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社会音乐文化的传播度、学生对音乐的接受度,和学校对学生业余文娱生活的重视度,还有当时学生在传播音乐、推动中西音乐文化发展形成过程的潜在作用。正是在这一层面,它十分恰当地定位了近代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尚乐之风”的历史存在,深化了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活态研究。
上例不成系统的研究还告诉我们,社会教育是个人生活社会化及人格形成的过程。在传统和近代两个不同社会中,社会教育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互动,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在社会秩序的规范、人格的养成、修养的提升上则是一致的,这些教育的功能旨在培养人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塑造人性,调节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协调发展。然其同与不同,似乎只有“以小见大”的研究才能消弭之。日常生活史研究力图解决的正在于兹。
(二)交集:任光与聂耳的生活日常
对近代中国音乐家的研究,绝大多数都集中于生平事迹的考订、作品分析和历史地位认识方面,鲜见对作曲家生活、作品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分析,实难见其在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一个客观的事实,就任光与聂耳这两位在近代中国音乐史上尤其在中国新音乐运动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的音乐家而言,学界对前者的关注稍逊于后者,原因众所周知。倘若将二人有关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及其音乐创作加以综合观察,我们或许会得出些许与既往研究不同的看法。
任光和聂耳相差12岁,有着不同的出生、学习和成长轨迹。他们于1932年7月23日在上海相遇,开始了二人从事革命音乐活动的历程,开始二人的交集。作为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因素——时间,在任、聂二人的交集中,虽然只有短暂的2年9个月不到的时间(其间还包括聂耳1932年8月7日离沪赴京到11月8日乘火车回到上海的3个月在内),但却是聂耳完成全部音乐创作的阶段、任光毕生音乐活动最为活跃的阶段。此间他们二人的生活状态反映了持主流价值观的国人对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思想和认识。下文先从大的时间点出发:
1931年4月22日,到上海才不到一年但过着窘迫生活的聂耳,以“聂紫艺”的名字考入黎锦晖组建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演奏员。1932年7月23日,任光代表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去明月歌舞剧社审听民乐合奏节目,初识聂耳,二人当场进行了钢琴与小提琴的合奏;不久聂耳离开上海打算攻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然而考试不第,生活难觅,不得已返回上海;11月26日,在田汉等的帮助下,进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一厂工作。任、聂二人再一次晤面,是在1933年1月,他们一起在上海成立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2月9日,包括任光、聂耳在内的31人当选“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此后他们频繁相聚,切磋音乐创作。1934年1月24日,聂耳被联华影业一厂辞退;4月1日,进入百代公司,主要工作是“帮助(音乐部主任)任光的一切收音工作,经常地教授歌者,抄谱,作曲”㉕李辉主编:《聂耳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页。文中括弧里的内容均为笔者所注,后同。;5月,二人组建起百代国乐队(对外称“森森国乐队”);7月,任光受公司委托去香港录音,“上海的事务,全由他(聂耳)负责”㉖徐家瑞:《聂耳的一生》,《中原》1945年2卷第2期,第62-71页,上海:群益出版社。;11月下旬,聂耳从百代公司辞职。1935年1月,聂耳担任联华影业公司二厂音乐部主任,4月15日,在党的保护下,聂耳离开上海,拟途经日本赴欧洲和苏联考察、学习;此间,任光在上海百代公司将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4月25日)和《义勇军进行曲》(5月9日)灌制唱片,聂耳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留日学生艺术聚餐会做报告时热情推荐任光的《渔光曲》(6月2日);7月17日下午,聂耳在日本东京西南方向55公里鹄沼海滨游泳溺亡,终年23岁。
根据日常生活史视角,任、聂二人的生活工作空间(以上海为中心)和工作内容(以音乐为中心)十分具体。在时间上,他们与普通人一样过着平凡和重复的生活,但在生活的日常性与综合性方面,有着普通人所没有的日常行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我们从中观察这种日常生活所具有的历史问题,而发现了历史的动力和意义,仅从三点加以分析说明。
其一是黎锦晖城市知识分子身份的确立。任、聂二人的交集其实也与黎、聂二人的交集重叠。倘若没有黎锦晖的中介,任、聂二人的交集也许会推后甚或不可能发生。客观上,灌制唱片是任光所工作的百代公司主要内容及黎锦晖凭借唱片推广其歌舞音乐的需要,黎锦晖与作为音乐制作人的任光因为灌制唱片而建立联系。20世纪20年代唱片逐渐走入百姓日常生活。继1927年黎锦晖在法商百代公司推出第一首中国近代流行歌曲《毛毛雨》后,上海社会流行歌曲热潮升腾;1934-1935年,电台作为一种新兴文化媒介而迅速发展,以唱片为媒介,歌星与流行歌曲逐渐融入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以黎锦晖为代表的都市音乐歌舞创作的盛行,是市民娱乐之需,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上海自1843年开口通商,随着经贸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已与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传统生活有了很大变化。商业化的生活方式下,产生了新的生活需要。从1927年到1929年,黎锦晖通过举办中华歌舞专修学校、中华歌舞团、明月歌剧社,致力于都市音乐歌舞发展,顺应了上海城市日常生活发展之需,迎合了市场,也解决了日常生活之需。从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来看,如果没有良好的商业化运作收获,黎锦晖定然难以接纳徘徊街头的聂耳,为之提供生存机会。然而日渐流行的社会新风尚,与世代相传的传统礼俗及人们历来尊崇的伦理多有违背,加之随后的社会现实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与城市所需新生活大相冲突,都十分容易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这也是造成聂、黎冲突的社会根源。
1932年,聂耳先是通过《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㉗聂耳:《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时报》1932年7月13日,载《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聂耳全集》下卷,北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5页。一文表示了对黎锦晖的不满,接着在7月22日发表《中国歌舞短论》㉘黑天使:《中国歌舞短论》,《电影艺术》1932年第1卷第3期,载《聂耳全集》下卷,第48页。,狠狠地对年长自己21岁的黎锦晖进行了批判。批评持续到了1935年,“作曲家黎锦晖先生本年度印刷的歌曲集也颇为不少……,这可谓一大盛事。这些歌曲都有一个甜蜜的或壮伟的名字,……充分表示了那种玩意儿不过是供人享乐、没有多少价值的东西。”㉙聂耳:《一年来之中国音乐》,《申报》1935年1月6日,载《聂耳全集》下卷,第86-87页。在《中国歌舞短论》见报后,黎锦晖并无怨恨地语于聂耳,“你既然吃我的饭,就不应该骂我!”㉚郑易里:《黑天使时代的聂耳》,《新音乐月刊》1949年8卷2期,第9页,重庆:新音乐社出版。1935年,黎锦晖在给聂耳的祭文中,只字未提二人的分歧,反倒对聂耳称赞有加,十分宽容:“目不离谱,手不离琴,口不离低唱浅吟”,“耳音”正确,恰巧姓“聂”,“真的比常人多了一双耳朵”㉛黎锦晖:《悼聂耳记》,《人生旬刊》1935年1卷5期,第5页,上海:声美出版社。。纵观黎锦晖1936年之前的音乐活动,及聂、黎二人在音乐创作上因趣味不同而存在分歧,但人生之艰辛与无奈恐怕唯有他自己最清楚,在当时,黎锦晖以一种经过世事变迁之后的包容与平静,彰显出一位知识分子的品格,具有鲜明的城市知识分子的特征,“城市知识分子是流动的,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自由行走,历史感淡薄,空间感敏锐。”㉜许纪霖主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其二是任光兼作曲家、音乐制作人与社会活动家的多重身份认识。㉝参阅任静:《任光研究》,西安音乐学院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中采用音乐社会学理论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所见诸材料绘就任光一个单纯、清晰的画像。1919年,任光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中国一大批革命志士赴法勤工俭学的经历一样,抵达法国后参加左翼人士组织的文化协会,㉞俞玉滋:《革命音乐家任光及其创作——为纪念任光牺牲四十年而作》,《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54-57页。积聚了奔向革命的动力。当他回到祖国后,就充分地利用在外企工作不受国民党政府检查的便利条件,为中国革命新兴音乐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作曲家,积极从事革命音乐创作;并以自己所学加强革命音乐创作力量的辅导。㉟如1933年2月12日聂耳日记所记,“从今天开始,他(任光)改正我很多在‘乐句’与‘味儿’上的错误。”李辉主编:《聂耳日记》,第405页。作为音乐制作人,通过百代制作大量革命歌曲唱片发行,发挥了新兴传媒的载体作用,为革命音乐传播打开了积极的局面;他灌制大量民族民间音乐唱片,保存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社会活动家,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音乐文化组织,争取和开拓了左翼电影音乐阵地;接济被捕的“左联”文艺家家属,或将私人住宅用来接待聂耳、吕骥、张曙等“常客”,㊱田汉:《聂耳及<聂耳>影片》,载于田汉:《田汉文集》第1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528页。保证革命文艺工作者有安全的活动场所,或驾驶私人汽车将同志们转移至郊外等,掩护同志们不受反对派的迫害;㊲任光在百代公司的工作也有不顺的时候,他所灌制反帝抗日内容的歌曲,一度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干涉,以至于公司不得不将已灌制好的唱片原版毁掉,为此任光被停职2个月。以上材料均见于徐士家:《关于任光生平的一些史料》,《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55-56页。等等。
在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里,任光以其专业技能、职业身份和尚处优渥的生活资源,团结帮助了致力于左翼音乐运动的几位重要人士,在促进进步音乐家的交流、学习和合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28年,任光成为法商东方百代的高级职员,期间租住在徐家汇华安坊8号的一处花园式洋房里㊳《民族的号手——任光》,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20110111期。任光在哈冈路民厚南里有一套房子的事件,田汉也有回忆。田汉:《聂耳及<聂耳>影片》,载于田汉:《田汉文集》第11卷,第527页。,有一架很好的钢琴,还备有一辆奥斯丁牌的小汽车。㊴杨静:《嵊州:被“遗忘”的任光》,《安徽商报》2009年12月25日,第B09版。在百代公司,任光的薪资不一定算高,但在当时上海普通人的工资待遇中是比较高的,“中国当时唯一的最高音乐学府‘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校长萧友梅的月薪是400块大洋,而任光在百代公司时月薪高达800块大洋。”㊵向延生:《“民族号手”任光和他的绝笔之作<别了皖南>》,《音乐周报》2001年1月19日,第03版。冼星海也曾说过,他在百代公司里有月薪100块大洋,“百代公司待遇的不平(有些技术很差的人薪水比我多八倍)”。据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这里不含其它经济来源。再看聂耳的经济状况,总体上在百代公司要好于明月歌舞剧社。每月除基本薪资外,还可通过写剧本、文章、演员、教提琴增加财源。如1931年9月5日,聂耳顶王人艺离开明月歌舞剧社的空缺,担任乐队第一小提琴,月薪25块,生活暂时得到保障。到1933年,5-7月份每月收入28块,写文字获得稿费10元;9月份未领工资;10月份是30块。支出中,如10月份,房租11块,饭10块,娘姨2块,洗衣2块,车资、零用10块,总计35块㊶1933年10月19日日记。载李辉主编:《聂耳日记》,第427页;《聂耳全集》下卷,第513页。;常常出现“已借到下月的钱了”㊷1933年5月15日日记。载李辉主编:《聂耳日记》,第421页;《聂耳全集》下卷,第508页。的情形。由于有了任光的帮助,1934年4月聂耳到百代公司后,“最近收入较丰”㊸1934年2月24日日记。载李辉主编:《聂耳日记》,第432页;《聂耳全集》下卷,第508页。,所以这一年成了他的音乐年。㊹1934年1月29日日记。载李辉主编:《聂耳日记》,第431页;《聂耳全集》下卷,第516页。就在1934-1935年间,聂耳完成了他全部8部电影的配乐创作,为早期中国电影音乐做出了贡献,创造出了独具鲜明特色的中国革命新兴音乐。
其三是聂耳作为中国革命新兴音乐开创者的定位。聂耳到上海2年后,积极与“左联”文化工作者的接触,于1933年初在田汉介绍、夏衍监誓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1月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后,2月12日与任光、吕骥、张曙、安娥等在沪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4年春,任、聂二人参加田汉发起成立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随着左翼音乐运动兴起,聂耳的创作热情高涨,同时不忘加强音乐技能的学习。站在日常生活史中立的研究立场,我们尚能发现,来自黎锦晖及明月歌舞剧社、任光的帮助、影响,特别聂、任二人相识后,从1933年2月分别作出其第一首歌曲,标志着二人同步开始新兴音乐的创作实践,到1934年初步找到创作的形式和风格,是聂耳自身努力学习的结果,也是聂、任二人共同进步、互相影响的结果。从《开矿歌》到去世,聂耳留下了35首歌曲,聂耳在学习的过程中丰富音乐基础、提升音乐创作水平,㊺参阅陈聆群:《王人艺先生谈聂耳和黎锦晖》,《音乐艺术》1985年第4期,第14-17、25页;陈聆群:《八十回望——我的音乐历程》,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梁茂春:《黎锦光采访记录及相关说明》,《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13年第1期,第55-71页;李辉主编:《聂耳日记》;等等。成就了自己的音乐理想,如他进入百代之后创立百代国乐队而留下的4首民乐合奏作品,显示了已然掌握多方面作曲技巧。在聂耳仅有的三年不到的创作时间,其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堪称他自己对中国新兴音乐光明前途展望的体现与定位,确证了他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中袒露的心迹,“新音乐的新芽将不断生长,而流行的俗曲已不可避免地快要走到末路了。”㊻聂耳:《一年来之中国音乐》,《申报》1935年1月6日,载《聂耳全集》下卷,第87页。
结 语
以具象的“人”为核心,在各具个性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发现历史。然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围之大,但再大也绕不开每个具象的“人”及其的生活。所以,以“人”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想从复杂丰富的历史图景中叙述社会样态和具象的“人”的面貌,从追寻历史事情的发生与发展中,达到实事求是。如同李长莉研究晚清上海社会变迁后所得,“我们需要回到民间社会,回到历史上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去探寻中国社会生活近代化的实态,从中追寻中国社会近代化变革的内在源流”㊼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引言”第4-5页。。因此,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紧扣普通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时代是如何影响固有的生活节奏与社会秩序的历史。以此检视近代中国音乐史加强日常生活史研究,贴近社会底层看历史,深入“人”的日常生活,对于推演出任何时期历史事情的基本结论都会发现一些之前不被注意的信息,甚至会得出一些不同于既往研究的认识。这样的研究还不流于琐碎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