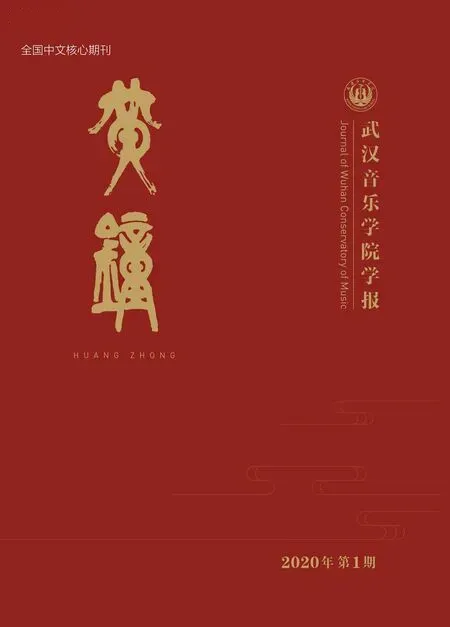范畴与角度: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态研究问题
2020-12-06蔡际洲
蔡际洲
序 言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形态研究是一个老课题。回顾该领域的学术史,我们似乎走过了一个“形态—文化—形态”的三阶段,颇有“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意味。如今我们重新重视音乐形态研究,主要是基于其在学科建设中的基础意义。本文意在讨论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是研究范畴;一是研究角度。
所谓范畴,在这里主要是指研究对象的范围、领域,或者说是指“研究什么”的问题。一般说来,各学科都有自己研究的基本范畴。①如哲学中的矛盾、质和量、本质和现象;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化学中的化合、分解等等。详参百度百科“范畴”,https://baike.baidu.com/item/范畴/4127668#viewPageContent.但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对此进行专门讨论者并不多见。在已有文献中,大多是作者自己的不同研究主张。在回答“研究什么”的问题上,不尽相同。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需要对这些不同看法进行总体观照。然而,目前尚无人对此进行系统梳理。
所谓角度,是指人们观察问题的“切入点”,或曰介入途径。因此,在这里有“怎么样研究”“如何介入”的意思。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角度,笔者曾撰文作过探讨;②蔡际洲:《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角度》,《黄钟》2007年第1期,第78-83页。但这是指根据不同研究目的,而形成的几种角度。此外,沈洽从研究主体不同的文化立场出发,对在形态研究中产生的两种角度——“规范的”与“描写的”——作了分析评价;③沈洽:《描写音乐形态学引论》(导言),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页。伍国栋从形态分析的民族音乐语境的角度做了探讨。④伍国栋:《音乐形态分析的民族音乐语境》,《黄钟》2017年第1期,第105-111页。目前看来,因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时空关系,以及因研究成果的性质和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等方面而形成的不同角度,尚无人涉及。
因此,笔者拟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此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初步的归纳;同时,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关于研究范畴
(一)现状
如上文所述,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的研究范畴有哪些?学界的回答并不一致。以笔者接触的文献而论,至少有如下几种:
其一,自王光祈、杨荫浏、黄翔鹏以来的学术传统中就有关于“律调谱器”的表述,⑤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黄翔鹏:《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王光祈先生诞生百周年随想录》,《音乐探索》1993年第1期,第4-8页。这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形态的研究范畴。
1.律——有关律学的研究;
2.调——有关乐学的研究;
3.谱——有关乐谱的研究;
4.器——有关乐器及其他音乐文物的研究。
这一表述,具有简洁、精炼,综合性强等特点。当年王光祈的一部《中国音乐史》,基本上就是以“律调谱器”为架构撰写的。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后在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为代表的学者中传承发展,并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但由于那个时代的语言表达特点,再加上单个汉字的多义性,学界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尽相同。如有学者认为“律调谱器”=“音乐本体”;⑥项阳:《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自觉、自信与自省》,《中国音乐学》2018年第1期,第5-14页。但也有学者认为“音乐本体”=“声音—概念—行为”。⑦伍国栋:《音乐形态 音乐本体 音乐事象——与研究生讨论民族音乐学话语体系中的三个关键术语》,《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3期,第63-68页。如此等等。
其二,赵宋光在关于民族音乐形态研究的构想中,提出建立“四大目标”的看法。其中也有四大研究范畴的涵义:⑧赵宋光:《对民族音乐形态学的构想》,《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8-10页。
1.在全面整理采集的基础上,进行音乐形态的比较研究;
2.探索民族音乐发展演变的条理、系统与规律;
3.总结民族音乐的作曲技法,充实作曲教学;
4.根据系统化的实际材料,配合音乐社会学、心理学,探讨美学规律。
这是赵宋光关于民族音乐形态学的研究构想。也是受“东欧民俗音乐学学派”⑨伍国栋:《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学术思想的转型(上)》,《音乐研究》2000年第4期,第3-14页。影响,在音乐形态研究方面的新主张。其目的除了音乐形态本身的基础研究、美学规律探讨之外,还在于建立中国式的“四大件”,为中国式的作曲理论做基础工作。按作者简略的表述及笔者的粗浅理解,以上第一条,侧重横向的区域性特征的研究;第二条侧重纵向的历时性变迁特征的研究;第三条是在以上两条的基础上,总结出民族音乐的作曲理论并用以为创作服务;第四条是将形态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旨在探讨更深层的美学规律。
其三,沈洽借鉴“描写语言学”的方法,提出了“描写音乐形态学”之说,涉及描写内容的五大方面:⑩沈洽:《描写音乐形态学之定位及其核心概念(上)》,《中国音乐学》2011年第3期,第5-18页。
1.音乐声本身的描写;
2.支撑发出音乐声之物件的描写(如乐器、人的嗓子、身体等);
3.发出音乐声之行为方式、方法的描写;
4.音乐声中词语的描写;
5.乐谱的描写(广义的乐谱,含曲线、图形,甚至舞蹈、仪式等等都有乐谱的功能)。
显然,这是因受语言学、西方民族音乐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的影响,对音乐形态的研究范畴作出的不同解读。沈洽的主旨在于,立足于客观的文化立场,进行“描写的”而非“规范的”形态研究。与王光祈、赵宋光不同的是,特别是与以往传统意义上的形态研究多以乐谱为本的做法不同的是,作者将描写音乐形态学定位为“是研究音乐声轨迹的学问,主要是对各种音乐声的轨迹进行描写、分析,并作类型化处理。”⑪沈恰:《描写音乐形态学之定位及其核心概念(上)》,第7页。当然,其中还涉及音乐行为、方法的描写等等。
其四,伍国栋在论及中国民族音乐学的音乐描述对象时,将音乐形态分为“声音形态”和“响器形态”两大类型。⑫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182页。
作者认为,所谓声音形态,即由“乐声”(乐音之声)与“音声”(非乐音的音响)构成。其中“声音形态”还可分为六种不同类型:
1.音乐的音组织(音体系)形态——音阶、音律、音程;
2.音乐的体组织(曲式体系)形态——句读、句式、段式、曲式、多声织体;
3.音乐的音位组织(旋律体系)形态——腔型、曲调型、装饰型、调式、音域、调性;
4.音乐的音速组织(历时体系)形态——节奏型、节拍型、速度型;
5.音乐的音量组织(力度体系)形态——重音、弱音、强弱趋型、强弱变型;
6.音乐的音品组织(音色品质体系)形态——真声、假声、气声、哑声、鼻音、喉音、泛音、模拟音、亮音、暗音等等。
此外,响器形态还可分为四种类型:弦鸣乐器、气鸣乐器、体鸣乐器、膜鸣乐器。
我们可以看出,伍国栋的以上主张,是在他1997版《民族音乐学概论》(第五章第一节)中提出的描述对象的修订与发展。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提出了“声音形态”这一概念。同时,还对此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做了界定与说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有关声音形态六种类型的划分及其进一步对各类型中分析要素的展开,更是较为系统地展示了声音形态中各层级的描述内容。
其五,杨民康在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法的思考中,提出了三大分析范式。⑬杨民康:《音乐形态学分析、音乐学分析与民族音乐学分析——传统音乐研究的不同方法论视角及其文化语境的比较》,《音乐艺术》2014年第1期,第69-79页。其中,不同范式涉及的对象,也有研究范畴的涵义。
1.音乐形态分析——音乐形式分析;
2.音乐学分析——音乐形式分析+社会历史文化分析;
3.民族音乐学分析——音乐形式分析+社会历史文化分析+音乐主体(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文化身份、立场)分析。
作者的本意在于,除了比较这三种分析范式的异同之外,还旨在推崇民族音乐学分析这种范式。并认为,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这是一种“应该首先予以考虑的一种分析思维和方法。”⑭杨民康:《音乐形态学分析、音乐学分析与民族音乐学分析——传统音乐研究的不同方法论视角及其文化语境的比较》,第74页。从研究范畴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杨民康的见解与以上诸种说法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提出了对社会历史文化和音乐主体(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文化身份、立场)这两种分析范畴。诚然,这里的音乐主体是否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音乐形态”?可以讨论。但是,音乐主体的观念、行为等等,是否也有其“形态”意义?值得我们思考。
其六,褚历参考作曲技术理论的形态研究思路,提出了中国传统音乐分析的三大领域:⑮褚历:《中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分析》,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
1.音乐的表现手段——音乐的基本表现手段、音乐的定型表现手段;
2.音乐的发展手法——旋律发展手法、其他发展手法;
3.音乐的结构形式——一部曲式、单二单三多部曲式、复合曲式、变奏曲式等。
作者的目光聚焦于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的一个“单元”——曲式结构,并运用归纳的方法,从民歌、歌舞、戏曲、曲艺、器乐等诸种体裁的若干个别之中,对中国传统音乐具有一般意义的曲式结构体系进行抽象。显而易见的是,这是对上文所述赵宋光的“民族音乐作曲技法”研究构想的具体化。除了一般的基础理论研究意义之外,还对民族作曲(或中国作曲)理论的建构具有参考意义。
其七,蔡际洲参考近年来音乐学界的研究成果,按传统音乐的不同存在方式,提出形态研究的六种类型:⑯蔡际洲:《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分析概略》(未刊稿),2019“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人才培养”授课讲稿。
1.音响形态——所收录的各种音频、视频中音像数据的形状与表现;
2.乐谱形态——各种乐谱记录中的音乐语言要素的形状与表现;
3.器物形态——乐器、人嗓及其他发声物的外形、构造及表现形式;
4.表演形态——传统音乐表演的技术、技巧的形状与表现;
5.传承形态——传统音乐的传授习得方式、方法与技巧的形状与表现;
6.观念形态——传统音乐家在实践中形成的各种认识的总和及其表现。
这种看法并非一次性完成。最初是在拙文《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定性分析》⑰蔡际洲:《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定性分析》,《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4期,第63-73页。中提出的五种形态:乐谱形态、音响形态、器物形态、表演形态、观念形态。后来,在2019年7月星海音乐学院主办的“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人才培养”的授课中,增加了“传承形态”。
以上六种存在方式,也可理解为传统音乐依附的六种“载体”。这些载体,就成为我们进行形态研究的不同范畴。或者说,我们所研究的音乐形态,也主要是通过这六种不同的存在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如音响形态,即以“音响”为载体的音乐存在方式。对其进行描述、分析时,务必以“音响”为依据。当然,我们可以适当参考乐谱或其他相关材料,但“音响”的主导地位和不可替代性是毫无疑义的。如王庆沅关于湖北兴山特性三度体系民歌的测音分析,⑱王庆沅:《湖北兴山特性三度体系民歌研究》,《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3期,第61-78页。再如郭苗苗、蔡际洲关于汉剧名家程彩萍润腔艺术的研究,⑲郭苗苗、蔡际洲:《汉剧名家程彩萍的润腔艺术——不同时期代表性唱段的音响形态分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17-28页。等等。
(二)问题
根据以上的现状描述,在有关形态研究范畴的不同看法中,笔者以为有如下若干问题值得关注、思考与讨论:
第一,在以上关于研究范畴的不同表述中,这几种不同范畴是一种什么关系?是按一定时序“进化”的“高低”关系呢?还是多元并存、相对互补的关系?对于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56个民族的传统音乐而言,有没有一种能得到音乐学界普遍公认的,且最具普适性、科学性的研究范畴?
第二,什么是“音乐形态”?学界对此下一完整定义者似不多见。⑳音乐学界不仅较少对“音乐形态”进行讨论,而且不同学者所下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如音乐理论家、音乐美学家叶纯之先生对“音乐形态学”的解释:音乐形态学是“根据音乐的形态即具体作品的样式、结构、逻辑等来研究音乐的形式与内容诸关系的学科”。详参叶纯之:《音乐形态学》,载《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816-817页。音乐史学家刘再生先生则认为:“音乐形态是音乐在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方式。……抽象地说,音乐形态作为音乐整体性的存在方式,它浓缩着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音乐作品其内容与形式方面‘形状和神态’之主要特征……具体而言,它又分别包括了表演形态、器乐形态、音网结构形态、曲式结构形态,等等。”详参刘再生:《论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音乐研究》2000年第2期,第41-53页。民族音乐学家伍国栋先生的看法是:“民族音乐学话语体系中‘音乐形态’的涵量,既包括‘乐声’性质的‘音乐形态’,又包括‘非乐声’性质的、凡与人类文化活动相关的所有‘音声形态’。”并倡导用“声音形态”来逐步取代“音乐形态”。详参伍国栋:《音乐形态 音乐本体 音乐事项——与研究生讨论民族音乐学话语体系中的三个关键术语》,第63-68页。笔者曾在一部教材中对此给出的定义是:“‘音乐形态’这一概念,一般系指从音乐本身,即音响、乐谱、表演、图像、实物等中表现出来的内部构造和表现形式。”详参蔡际洲:《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9年版,第373页。那么,讨论传统音乐形态研究的范畴,要不要先讨论何谓“音乐形态”,特别是何谓“形态”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说,是否首先要弄清“音乐形态”特别是“形态”的内涵——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然后,再来讨论其外延——“有哪些”的问题?最后,才能回答传统音乐形态的范畴——“研究些什么”的问题?
第三,参考权威工具书关于“形态”的定义,《辞源》的解释是:“形状神态”;㉑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缩印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74页。《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事物的形状或表现”。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59页。此外,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指事物存在的样貌,或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㉓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形态/10967692?fr=aladdin.人文学者郑传寅教授的看法是:“所谓形态,是指状态、样式,除了耳目可接的显性的样貌、形式之外,还包括当以神会的精神风貌、状态。”㉔郑传寅:《中国戏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页。综上,我们可否将音乐形态定义为:音乐存在的样貌,或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
第四,据以上第三,如果说“形状”“样貌”等属耳目可接的“显性”之物,可对应我们传统音乐中的“音响”“乐谱”“器物”之外,那么,有关传统音乐表演的技术、技巧,以及有关传授习得的方式、方法是否也属耳目可接的“显性”之物?诸如周大风㉕周大风:《越剧唱法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甘尚时㉖甘尚时、赵砚臣:《广东音乐高胡技法》,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的研究,以及杨晓㉗杨晓:《小黄歌班中嘎老传承行为的考察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2届硕士学位论文。、李白燕㉘李白燕:《泉州南音演唱教程》,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研究等等,是否也是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五,据以上第三,形态还有“神态”“表现”的含义。也就是说,除了上述“耳目可接”的“显性”样貌外,是否还有“当以神会”的“隐性”样貌?如果有,那么,在与“隐性”样貌有关的内容中,是否存在一种音乐的“观念形态”?或者说,传统音乐家的音乐观(或音乐思想),以及在他们思维、意念之中“意欲表达”的音响,㉙黄汉华:《音乐作品存在方式及意义之符号学思考》,《音乐研究》2005年第4期,第56-66页。是不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或曰“形态”?
第六,音乐观念,在我们约定俗成的看法中是与音乐形态相区别的。但是,也可见到音乐学者在讨论音乐思想“是什么样”的时候,用到“形态”这一概念。㉚吴毓清:《礼乐思想的早期形态——从<左传><国语>看春秋时期音乐美学思想》,《音乐艺术》1983年第3期,第11-17页。如果从以上各种关于形态的定义上推敲,思想也好,观念也好,不也都是“事物的形状或表现”吗?不也都是“事物存在的样貌”吗?如此看来,音乐形态是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系指我们通常所认知的“显性”样貌(有形之物);广义者,除狭义外,还包括一般不为大家所公认的“隐性”样貌(无形之物)?㉛一般认为,观念似为一种无形之物或非物质的,何来“形态”之说?其实不然,在一定意义上讲,观念与意识、精神、思想同义,系指高度组织起来的特殊物质即人脑的机能与属性。如“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其他学科运用较为广泛——[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南帆:《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第七,19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态研究“为创作服务”屡遭诟病。然而,至今似乎没有见到有人对此说作过系统、有力的论证?令人疑惑的是:如果音乐学某学科的研究,能建立起自己独特、系统而完备的学科理论体系,具有自立于各学科之林的独立品格,那么,它的理论成果能为创作服务,能对其他各种音乐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又有什么不好?或者说,能用于指导音乐创作的形态学研究成果,它不具有学术研究的认知意义吗?
第八,在音乐的诸种存在方式中,音响(或声音)与乐谱的关系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之一。笔者赞同音响是音乐(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本源,乐谱只是其“定格”“转码”的某种形式的看法。那么,在这一认知前提下,乐谱研究还有意义吗?如果说我们的研究都要以音响为本,那么乐谱研究还有否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音响、乐谱作为音乐存在的两种方式,它们在学术研究中是否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属性?
二、关于研究角度
(一)现状
在我们研究中,除了笔者在序言中所提及的几种角度外,传统音乐形态的研究角度还大致有如下几种:
其一,按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可分为“系统性分析”与“选择性分析”。
所谓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即我们所分析的各种“零部件”。在相关文献中,有些音乐形态分析的要素较为全面、较为系统;而有些则只是研究对象的“局部要件”。显然,这二者是有区别的。在此,笔者将前者称之为“系统性分析”,后者称为“选择性分析”。
系统性分析是一种“相对全面”的分析。所谓全面,即对研究对象的“所有零部件”进行尽可能无遗漏的分析。上文所述伍国栋先生在《民族音乐学概论》中提出的“声音形态”“响器形态”及其细部的各类分析要素,亦可看作是系统性分析之参考。这类实例在学术专著、博硕士学位论文中较为多见,研究对象主要是解决对某乐种、某体裁的音乐形态的属性判断。
如杨予野的《京剧唱腔研究》㉜杨予野:《京剧唱腔研究》,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即属于乐种研究中系统性分析的例子。作者以“京剧唱腔”为对象,其中几乎涉及京剧唱腔的所有常用腔调:二黄、反二黄、西皮、反西皮、南梆子、四平调、吹腔、高拨子等。同时,在每种腔调之中,又按不同板式如原板、慢板、摇板、散板、跺板、流水、快板、二六分类展开。然后在每种板式中,再按该腔调的结构、旋律、起板、过门、收束、附加句,以及不同板式的连接转换等,进行逐一的分析。较为系统地为读者展示了“京剧唱腔”的音乐形态特征。
再如汪静渊的《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的奥秘:浙江民间器乐曲音乐形态研究》㉝汪静渊:《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的奥秘:浙江民间器乐曲音乐形态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则是音乐体裁研究中运用系统性分析的案例。作者的研究对象,诚如书名所示——“浙江民间器乐曲”。在该书中,作者从“音阶调式”“旋律发展手法”“曲式结构”三大方面逐一分层展开。其中,音阶调式涉及:音阶与立调手法、犯调手法;旋律发展手法涉及:重复法、变奏法、特性音调贯穿法、展衍法、剪裁法、集曲法;曲式结构涉及:小型乐曲曲式、变奏曲式、循环曲式、套曲曲式等等,以及在这些内容上的进一步分析。因而,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浙江民间器乐曲”的音乐形态。
此外,我们还可见到另一种分析情况,即只是对研究对象的“部分零部件”进行分析。由于这种类型具有较强的主观选择性,故此称为“选择性分析”。
如杜亚雄探讨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族民歌的关系,㉞杜亚雄:《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歌之比较研究》,《中国音乐》1982年第4期,第22-26页。其中涉及民歌音乐形态的比较分析。但作者并没有将目光投向这些民歌所有的音乐形态要素,而仅仅聚焦于其中的四点:五声音阶、五度结构、前短后长的节奏型、下行级进至主音或四五度下行跳进至主音的典型“终止式”。再如刘正维对二黄腔渊源的考证,㉟刘正维:《二黄腔论源》,《音乐研究》1986年第1期,第73-89页。其中涉及二黄腔与弋阳腔、宜黄腔、四平调,以及与鄂皖赣三省的地方戏曲音乐、其他民间音乐的关系。作者也没有对二黄腔的所有形态要素进行系统分析,而仅仅选择被认为是二黄腔最基本的“四大特征”——词格、结构、句式、音阶调式——进行分析、比较。显然,这些并不是二黄腔形态构成要素的全部。
其二,按研究成果的性质,可分为“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所谓研究成果的性质,即研究结论在学术论文表述中体现出来的特征。如研究成果为各类音乐事项的属性、特征者,即属于定性分析。如研究成果系各类音乐事项的数量描述者,即运用的是定量分析。或者说,定性分析是对音乐事项的“质”进行的研究,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定量分析是对音乐事项的“量”进行的研究,主要解决“有多少”的问题。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来自于自然科学。后逐渐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得到运用。从方法论的层次上看,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属于“一般学科”的方法,㊱研究方法若按应用范围分类,通常被分为由宽而窄的三大层次:哲学的方法、一般学科的方法、具体学科的方法。在学术研究中运用较广。
有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态研究中如何体现?目前在这方面进行总结、回顾的文献十分少见。关于定性分析,笔者曾撰文作过粗略的探讨。㊲蔡际洲:《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定性分析》,第63-73页。提出了定性分析的五种类型,并结合不同研究案例进行了具体介绍:
1.识别属性——对音乐事项有哪种或哪些特征进行的分辨剖析;
2.要素分析——对音乐事项的各个部分进行的分析研究;
3.结构整合——对音乐事项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综合考察;
4.价值判断——对音乐事项的各种功能、作用进行的阐释说明;
5.原因分析——对音乐事项形成的各种原委、理由的探讨。
关于定量分析,更是如此。由于种种原因,音乐学界在运用定量分析方面尚处初始阶段。出于教学需要,笔者曾在两篇未刊稿中,㊳蔡际洲:《音乐学研究方法》(未刊稿),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材,2010年编印;蔡际洲:《定性与定量:形态分析的多重视角》(未刊稿),2019“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人才培养”授课讲稿。对传统音乐的定量分析做了一点简略归纳,提出定量分析的四种类型:
1.状态定量——对音乐事项的属性进行的数量描述;㊴张明霞:《赣南信丰县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武汉音乐学院2014届硕士学位论文。
2.关系定量——对音乐事项的诸种要素及其关系进行的数量描述;㊵蔡际洲:《京剧抒情性唱段句幅变化的统计学研究》,《黄钟》1999年第3期,第28-35页。
3.空间定量——对音乐事项在不同空间中的状态进行的数量描述;㊶蔡际洲、向文:《长江流域“巴蜀—荆楚”音乐文化区划问题——运用音乐数据库资料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尝试》,《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1期,第100-109页;刘清、蔡际洲:《鲁南五大调的流变》,《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66-74页。
4.时间定量——对音乐事项在不同时间过程中的状态进行的数量描述。㊷蔡际洲、许璐:《鄂州牌子锣的变迁》,《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4期,第5-13页。
其三,按研究对象的时空关系,可分为“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
研究对象的时空关系,是指研究主体介入客体时,由时间、空间不同而形成的不同角度。所谓“静态分析”,是指对脱离了某种音乐的时间延展过程与特定表演背景的一种分析。静态分析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最早在经济学领域得到运用,㊸“静态分析”(Static Analysis),也称“静态均衡分析”(Static Equilibrium Analysis)。主要运用于经济学领域。“静态分析”是分析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以及有关的经济变量达到均衡状态所具备的条件,它完全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具体的变化过程,是一种静止地、孤立地考察某种经济事物的方法。详参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wiki/静态分析笔者在此将这一概念借用到音乐学领域。诸如上文我们提及的杨予野关于京剧唱腔的研究、汪静渊关于浙江民间器乐曲的研究,他们并没有涉及京剧唱腔在某剧目中、浙江民间器乐曲在某民俗活动中的表演背景,及其时间延展过程中的表现。而是将其中代表性的唱段、代表性曲目作为一种“相对静止”的形式进行剖析,以期解决研究对象的形态有何特征的问题。这种角度,是我们目前最为常见、最为常用的一种分析类型。
无疑,音乐是一种时间艺术,都是在时间中展现的。同时,不少音乐并不都是一种孤立的音乐形式,诸如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歌舞音乐、仪式音乐等等,它们都与一定的表演背景相结合而存在。因此,我们还可见到另一种类型的分析——“动态分析”。“动态分析”这一概念,也系借用自经济学,㊹动态分析(Dynamic Analysis),也称动态均衡分析(Dynamic Equilibrium Analysis)。是针对于“时间路径”上的变化进行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动态分析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并把经济现象的变化当作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看待。详参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wiki/动态分析。是指结合某音乐的时间延展过程和特定表演背景的一种分析。如王震亚先生关于京剧《玉堂春》音乐的分析,即是较早的实例。㊺王震亚:《京剧<玉堂春>音乐分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3-16页。在该文中,作者首先将研究对象分为“衙内、升堂、审讯、结尾”等几个部分,并结合剧情展开的时序对其中的各种音乐形态进行了要素分析;然后,又以“唱腔与说白、板式、上下句、京胡与锣鼓”等诸要素为对象,对其在该剧中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结构整合。与以上的静态分析相比,这显然又是一种不同的分析类型。
在我们的形态研究中,动态分析要大大少于静态分析。因此,动态分析的研究方式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比如戏曲音乐的剧目音乐研究、曲艺音乐的曲目音乐研究、仪式音乐的现场实录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音乐学界在这方面已有改观。在一些运用动态分析的案例中,尤其是在研究音乐形态与相关背景的各种关系方面作出了一些探索。诸如:有侧重戏曲唱段内部的结构与唱词关系的研究;㊻钱国桢:《昆曲<牡丹亭·游园>的戏曲艺术分析》,《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61-69页。有侧重戏曲音乐与剧情、人物关系的研究;㊼钱国桢:《梅兰芳京剧<穆桂英挂帅>的艺术分析》,《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112-125页。有侧重民俗音乐与民俗活动程序关系的研究;㊽许璐:《鄂州牌子锣研究》,武汉音乐学院2009届硕士学位论文。有侧重全剧不同唱段的运用与时长关系的研究;㊾何林慧:《蕲春县春蕾黄梅戏班音乐研究》,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10届硕士学位论文。有侧重曲艺音乐表演中“唱与说”的时长关系的研究;㊿李曦:《张明智与他的湖北大鼓音乐》,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还有侧重戏曲音乐中人声与表演动作关系的研究;[51]杨越:《昆曲<牡丹亭·游园>音乐与表演分析》,武汉音乐学院2013届学士学位论文。等等。
其四,按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可分为“直觉式分析”与“逻辑式分析”。
所谓思维方式,即思考问题的根本方法。这里特指在形态研究中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时所运用的根本方法。在我们的研究中,可见到不少侧重感性与侧重理性两类不同的案例,前者为“直觉式分析”,后者为“逻辑式分析”。
所谓直觉,即直观感觉的意思。直觉式分析特指凭借自己长期的田野考察、实践经验的积累,对音乐形态所做出的分析、判断。如有关“民歌色彩区”的划分、“乐音带腔”的研究,以及关于某乐种音乐特征的归纳等等,均属这种类型。在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研究中,作者往往告诉读者其研究结果是什么,而不说明这一结果是如何得来的。
逻辑,这是与直觉相对的一个概念。如果说直觉思维是没有经过分析、推理的话,那么,逻辑思维就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来反映客观对象的。就像做几何题一样,依据的是已知条件和逻辑推理,而不是自己的“感觉”。“感觉”A=B,与“证明”A=B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直觉式”的,而后者则是“逻辑式”的。因此,我把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进行的形态研究,称为逻辑式分析。
如定性分析的例子:黄翔鹏对曾侯乙墓出土的“均钟”所做的考证。[52]黄翔鹏:《均钟考——曾侯乙墓五弦器研究》(上下),《黄钟》1989年第1期,第38-50页;第2期,第83-91页。作者认为,曾侯乙墓的五弦器是秦汉时失传的“均钟”——一种为编钟调律的音高标准器。但这一结论的得出,系作者依据其形制并结合相关文献,历经“专为调钟而设的律准”“均钟准器与后世律准之辨”“准器与乐器之辨”“夏尺考”“均钟五弦考”等问题的论证,一步步推导出来的。再如定量分析的例子:刘清等关于鲁南五大调渊源的探索。[53]刘清、蔡际洲:《鲁南五大调考源》,《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71-80页。作者的结论是认为鲁南五大调的部分曲调来源于苏北曲艺音乐。以其中鲁南五大调与苏北曲艺音乐的比较为例,其中涉及定量分析的形态要素有“骨干音”“旋律音列”“句幅与字腔关系”三种。对这三要素,作者都有相应的概念界定、计算方法、选择理由的文字说明。最后在比较结果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
可见,以上的直觉式分析与逻辑式分析,也是我们在音乐形态研究中的两种不同角度。其主要区别,就在于二者的思维方式不同。
(二)问题
有关研究角度的问题较多,至少有如下这些值得思考、讨论:
第一,我们应如何看待系统性分析和选择性分析?这两种分析角度的应用背景各有什么特点?如果说“系统”在此有“全面”的内涵的话,那么对某具体的研究对象来说,如何才能做到“全面”?如果说“选择”带有一定主观性的话,那么这种选择是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个人偏好,还是研究对象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呢?
第二,系统性分析与选择性分析与特定的课题选择、特定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关系?目前看来,系统性分析好像是为了客观地揭示研究对象的基本面貌和形态属性,而多用于“音乐本体研究”;选择性分析则多与“历史渊源研究”中的“曲调考证”关系密切。那么,这两种分析角度还可运用于哪些其他研究领域,哪些其他不同的课题?在不同乐种、不同体裁的研究中,有否规律可循?
第三,在目前的大量音乐形态分析的文献中,我们一般较为注重定性分析,而忽略定量分析。如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知识结构问题,还是音乐观念问题?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忽略定量分析是否值得反思?人们常说定性分析偏于主观,只能借助自然语言,且不够精确可验证性差;定量分析倒是客观,但在纯然理性的数据与活生生的音乐实际之间,与人们的音乐感受之间似难达到一定之契合。因此,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两种分析角度的特点与不足?
第四,除上文所述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几种类型外,这类分析角度还可在哪些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不同的研究类型中得到运用?在定性分析中,“识别属性、要素分析、结构整合”多与音乐形态关系密切,但“价值判断、原因分析”似与音乐形态关系较远。我们能否从音乐形态的角度,对研究对象作价值判断和原因分析,从而实现研究方法的多元互补呢?在定量分析中,我们大多研究案例属于“描述性统计”,而缺少“推断性统计”。[54]“描述性统计”与“推断性统计”,是两种重要的定量研究方法。也是统计学中的两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描述统计学、推断统计学)。所谓描述性统计,是研究如何取得反映客观现象的数据,并通过图表等人工语言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和显示,进而通过综合与分析,得出研究对象规律性数量特征的一种方法。推断性统计(亦称“归纳性统计”),主要是如何根据部分数据(样本统计量)去推论总体数量特征及规律的研究方法,是借助抽样调查,从局部推断总体,以对不肯定的事物做出决策的一种统计。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描述统计学是推断性统计学的基础,推断统计学是描述统计学的拓展。详参王崇德:《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要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309页。那么,能否根据特定研究对象与所需解决的问题,尝试运用“推断性统计”的方法,从而拓展我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呢?
第五,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各自的应用背景和分析功能有何特点?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特点?这两种类型的分析是相对研究对象的“时空关系”而言的,那么,在我们的研究中,应如何运用这两种分析角度,从而实现研究中观察视角的互补?目前看来,动态分析运用较少,其主客观原因是什么?新研究角度的产生与运用,是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发现机制。这种“发现”的产生,是否与我们的学术视野、思维方式有一定联系?
第六,无论是静态分析也好,还是动态分析也好,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一次“相对的定格”。倘若需要回答所研究的音乐事项“是什么”“有哪些”等问题,这里是否涉及研究材料的代表性与典型性?如果是,那么我们的这两种分析角度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或者说,我们在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中,如何做到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相结合?
第七,从思维方式看,“直觉式分析”的结果是“感觉”出来的;“逻辑式分析”的结果是“推理”出来的。如果说“感觉”是感性认识的表现的话,那么“推理”则是否是理性认识的反映?一般认为,直觉思维具有自由性、灵活性、自发性、偶然性、不可靠性等特点。[55]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直觉思维/8408383。因此作为学术研究而言,我们的感性认识是否还有待提升至理性认识阶段?按学界公认的学术研究规范之一[56]葛剑雄:《学术研究规范》,载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2页。——作者必须在论文中说明自己研究结论得出的经过,但直觉式分析难以做到。[57]哲学家孙伟平研究员认为:“直觉的产生是思维过程中的质变与飞跃,由于其整个运作过程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突然的颖悟,主体不能明确地意识到并控制它的运作过程,因此也就不可能用语言将该过程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样就使直觉蒙上了一层朦胧神秘的面纱。”详参孙伟平:《论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的互补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第92-99页。因此,我们在研究的思维方式上是否还面临着一个“范式”转型的问题?
第八,学界大多认为,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58]孙伟平:《论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的互补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第92-99页。同时,不少自然科学家还十分认同直觉思维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作用。[59]周义澄:《论科学直觉思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6期,第35-43页。那么,我们应如何认识直觉思维在音乐学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可否这样理解:“直觉”,是我们认识研究对象的先导,主要表现为在田野工作中的现场体验;“逻辑”,是我们研究工作不可逾越的过程和必由之路,主要表现为在案头工作中的计划与思考?直觉思维的灵动性、或然性,对我们判别、认识音乐事项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它必须经过逻辑思维阶段,才能得到确立和证明?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研究范畴与研究角度两个方面,对目前有关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大致梳理,并提出了若干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无意解决什么问题,只是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和疑难和盘托出,聊供学界同行参考、继续研究而已。
个案研究与回顾思考,是我们学术工作中两个重要的不同环节。没有个案研究的学术积累,回顾思考成了空中楼阁;没有回顾思考的反思作用,个案研究难以达到一定之高度。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态研究方面,同样如此。
2018.07草拟于武昌两湖书院
2019.11二稿于武昌两湖书院
2020.02定稿于羊城历德雅舍